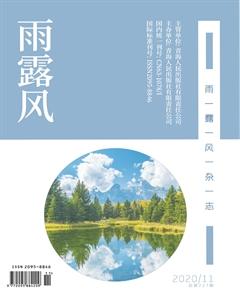父亲与旧土(外一篇)


父亲把麦地又翻了一遍,因为麦地偏远,所有的农用机械都上不去山,走不了弯路,能上去的只有烧油的三轮小车,就这样,每次去田里干活,都会背着长长的锄头,走好长的路,也因为这样,山里农村人大都习惯了走长路。麦子在收割之后,要重新翻地,这样来年种下去的才会有力的生长起来,等地里长出新芽,田里的野草一样长了很多,和谷物争取养分,这时,家家户户都开始了灭草行动,锄草是个细活,我本以为父亲生性粗鲁会做得一塌糊涂,我没见过父亲除草的样子,在家里他总是让我和母亲觉得他是个糙汉子。
清晨,父亲说要把麦田里的草锄掉,我抓住这次机会,要亲眼目睹一下父亲是如何干细活的。早饭是奶奶做的,和往常一样,他吃得不多,简单的馒头和咸菜,然后再打一碗蛋汤。在我看来,这是农村人最惬意的食物。这样的饭菜會给人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他很快就吃完了。换上一身脏衣服,从上到下,把每一粒歪歪扭扭的扣子码齐了。虽然穿的是旧衣服,但看起来比城里的年轻小伙还精神,跨上一支带土的锄头就出发了。山路上父亲偶尔踢飞一块路上的石头,这是父亲最活泼的样子就像个孩子。
看!父亲指着前面发芽的麦苗,平静地说,那就是我们家的麦地了。
我仔细打量,父亲用佝偻的身姿,寻找藏在麦子下面的杂草,挥舞锄头把每一块麦地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我在一边看着一边模仿,父亲的动作一高一低,样子比我小时候还可爱。一会挺直了身子,一会又弯下去。他一边除草,一边自言自语,好像在与麦田亲切的交谈,不知从哪来的风吹过,把眼泪吹了下来,父亲说它最热爱土地,恨不得在上面住下。
从早上出发,到中午,累了,就会坐下来歇一歇,看着被锄干净的麦田,嘴里嘟囔着,今年只要气候合适,又可以有个好收成。其实住在农村的人都知道,天气的好坏影响收成,一坐下来他就给我讲以前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地里种的梨树,因为接二连三的暴雨天气,那一年的收成几乎全部遭了殃,当然也没有卖个好价钱。父亲很生气,一直埋怨天不遂人,所以每次种地他都会认真仔细的收听天气预报,以前没有电视他就在收音机里和村里的广播里听,并把播种、施肥、浇水安排的妥妥当当,他小时候跟着爷爷一起种地,现在爷爷不在了,那几亩地就成了自己的天下。
在山上,傍晚的山像喝醉人的脸,云也是这样,夕阳把它们烧得通红,这样的火烧云,有一丝残缺,但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或许只有土气的山,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色。晚风摇摇晃晃的将羊群拉进山路,在这条有着许多布鞋脚印的土地上仰头,看高处的云,谈及我出生的地方。那时山上还有很多人,会一起吃晒干的馒头,穿最省的衣服,夕阳落山时未回去的人,会聚一起谈谈今年的收成,玉米的黄,高粱的红,这些都是农村人最关心的问题,就连飞鸟,也有自己的语言。
站得高看得远,我常常听到这句话,“远方”这个词总是比较神秘,或许我认为远方就是太阳吧。小时候我总觉得太阳和山挨得很近,幻想着如果跑到山峰是不是就可以触摸太阳。把一块石头用力抛得更远,太阳就能被我砸出一个大洞,这样在夏天就没有那么热了。当然,这些天真的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步一步消失了。远方变得更模糊而不是清晰,在山上瞭望,烦恼的事都会随视线抛得很远。
秋天是最繁忙的日子,在家里能听到柴油机的声音,到处都飘散了柴油味,这在城市是闻不到的。从小到大,每次看到土地,由黄色翻出来变成新红,像树叶的轮回。家里后院的一小块地,父亲也不会让它闲着,他总说买来的菜有农药,不新鲜,自己家种的菜,才是健康的食物。后院的地不大可以种下许多蔬菜,黄瓜、茄子、西红柿都是我爱吃的,一块儿地用好了,可以用一辈子,土地养活了奶奶一辈子,再往上不知养活了祖祖辈辈多少人,在我眼里,它已经不是土地,而是家的象征。
临近冬天,很少有人在山上走,花草成了秋天的遗物,秸秆是枯黄而湿露的,像老年人干枯的眼睛。冬天的土地不同于其他三个季节,没有春天的绿色,夏天的朝气,以及秋天的忙碌。反而有一种宁静,他们说是凄凉的,而我觉得这种宁静是美好的,尤其是到了霜降,清晨如果到田地走走,大地被白霜覆盖,尽管没有下雪,但白茫茫一片,给人一种安静的美,被冰封起来的田地,把蚊虫也一块冰封了,所有的植物都等待来年的复兴,对于农村人来说,冬季是最不忙碌的,他们似乎最不喜欢,认为冬天就不能赚钱,不能换来生计。他们对土地是极其热爱的,有一句话叫入土为安,在乡下,人死后都要被埋进土地,在地上打一个长方形的深坑,用人力将这一切都打点好。是的这里的人一生都在陪伴土地,最后连身上的筋骨也变成土地了。
对我来说,土地是深沉的,谦虚的。也是上了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怀念土地,有时候冥思,后山的桃花是否继续开着,那条通往山顶的河流是否已经干涸?再回到坡上,依稀可以看到,夕阳下的老人背着镰刀,是回家,还是散步?被汽车碾烂的泥路,现在也全部铺成了硬石灰,去山顶似乎变的方便,但脚印的故事仿佛也被这新的变化给葬到地底了。我顺着一条路可以很快到达山顶,不累。坐下来看看山上的夜色,此刻的月亮是又圆又大,冰露反射的光,像一个个发着脾气的萤火大声嚷嚷着白天,地面被零星的灯光点缀,把星星和夜色送往新的高度,最吵的是蝈蝈,像是对每一个说话的人询问,来自哪里?去往何处?寺庙的灯在黑夜也微微泛着金黄,如果现在能看见一个人在田里耕耘,那便是佛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张佛的脸,因此他们能活得更长久,这里的老人大多是期颐之年,当然,也和这山的清泉有关,这里的水是清澈而甘甜的,有很多营养,可惜,渐渐的越来越少,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知道移居到哪去了。如果父亲此刻在,他一定会给我讲小时候的故事,虽然已经听过很多遍,但一次比一次的味道浓。从这能隐约得看到通往车站的铁桥,所有的记忆都从那儿运进来,但也从那儿运出去了……
再回到这里,常去的地方走上一圈,会发现植物比以前稀少了。童年一起嚼过的土,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地板。在田野里,学着父亲的样子锄草,模仿他的笨拙和仔细,可是,我分不清哪些是杂草,哪些是青菜。是的,父亲从没能教会我这些,只让我学如何在大城市应对生存。可是草越来越多,庄稼越来越少,也不会有人在黄昏下聚堆,把消失的棋子摆起来,我多希望有人来弥补这一切。
在山上盘坐,亿万年前的风,不停地击打野人的身体,我想起了古老的山顶洞人,仿佛他们在耕耘、做饭、洗衣、生火,你追我打。那些不见底的窑洞,藏着一家人的秘密。最后,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埋入大地,等待后人。若干年后,考古队第一次发掘,将他们的传承从土里掀出,那藏了万年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我也仿佛看到了祖先们,在土地里孕育下一代,在土地上,用生命将田里的谷子扬起老高。
忆年事
如果不是落日,我便不会坐在阳台上赏花,和来之不意的阳光撞在一起。被窝在腐蚀了无数个日月之后,将自己裹起,早不是以前的温度。如果不是新年,我不会想起一桩往事。和大多数人一样,年的滋味,大概是淡了。母亲仔细地打量灶台,类比以往,每年腊月二十五,她总是清理着给我带来许多饭菜的灶台。灶台是爷爷之前用麦秆,水泥砌成的,这样更结实。可我只知道,麦子带给人类太多太多,连秸秆都被用来“筑窝”了。人们习惯用做事接触事物,像走山路,很多人会觉得远,时间长了也自然觉得疲倦。每次路过寺庙,风铃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故事。过去一年,叶子又要重新生长,光秃秃的树上,鸟窝会显露出来,像大树留下的斑点。到了冬天看不见鸟了,柳树自然下垂,树木把枯绿色拢进巢穴,像一副暗淡的山水画,也像一个愁眉苦脸的女生,我也许是太喜爱冬天了,所有的事都靠年近一点,可母亲不喜欢。自从上了大学,回家的次数就少了,她是盼着我回来,又不想让我在家里待太久,可能家里冷的缘故吧!
临近年的几夜里,我数尽黑暗里细小的事物。叶片在路灯的反射下映成的形状像天上的月亮。 因为过年,树枝上都挂满了灯笼,当月亮和路灯两种光同时打在身上,我分不清,就像我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花园很久没修了,南坡土路上的草也一米高,如果天还亮些可以看到老人在“骑马”“射箭”,我指的是下棋,通常他们可以玩很久,直到路边的猫狗都耐不住困。如果村里有一条明净的河,我定会停下来坐一坐,看一看莲塘、鱼儿……还可以借着水波散去烦恼。路灯像两个冲着你发笑的眼睛。远处的声音没有什么比狗叫声更令人讨喜,如果加上一些民间野调,农村的味道就更加重了。冬天这些河会结冰,会冻住许多鱼,他们漂浮在冰面上,野猫会吃掉它们的尸体。可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有条河,来观赏的就真不止我一个人了。集市上的人也越来越多,只是后来我不怎么去了。依稀记得一些水果摊位和蔬菜的位置,连老板姓什么都叫的来。每天早上老大娘总会收拾一些烂掉的菜叶喂宠物。街道被长长的人流拥挤,有时候人多了,机动车是很难挪动一步的。我喜欢看这样的“长龙”。在大地上,很吵也很热闹。也不知怎么,自从上了大学离开家,就开始怀念这种场景了。
说到心情,自然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每每走到街上看到老人、小孩儿、宠物和不知名的植物。玩得最简单的东西,火炮、咋耍、卡片……老人依然只是闲谈。人越长大越简单吧。有时候发呆,如果老了没有工作,生活也就只剩下看书了。人们总渴望静下来,不管是人群还是大街上。想回到最真实的自己。过年是越来越吵了,也越来越安静了。人们不会安顿自己的生活,即便是鞭炮、舞狮子。也被快速的生活沉淀下去。相比之下,还有很多人因为疫情就地过年。他们相对是孤獨的,回家才真正地放松。在异国他乡确实少了很多东西,过年最重要的就是和家人团聚。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孩子,人们的心情大概如此,都是在欢喜的氛围中深沉下去。 新年,很多事都清晰地在人们脑子里。我有意识的时候,年是最开心,也是最渴望的,虽然小时候穿不上买的新衣,但是奶奶会用缝纫机做,一做就是几个月。家里穿衣的太多,我们兄弟就三人,每次看到奶奶找补料和针线,就觉得新年要更近了。大多装的是棉花,比现在暖和,虽然赶不上最新的布料,但也是很珍贵的。小时候不知道那样的衣服有多好,长大了才知道留恋,我家的阳台在二楼侧面的栅栏里,不近不远的刚好可以看到远处的闹市,因为疫情人少了,以往这个时候总是人来人往,这里的集市大可以摆上三天足够置办所有的东西,也是过年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可能自己长大了,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认识。坑坑洼洼的路,没有了艰难的步鞋。在地区偏远的村里,有很多人写大字,摆上桌子红色的纸和金色的笔,今年稍有些迟。但是文绉的场景还是能见到的。乡下人写字颇有特点,称不上高谈阔论的大篇幅,能写的百姓们懂,容易看的字。大多是楷书和行书,到腊月二十号就开始摆了,因为疫情,每次到这个时候。有钱人看不上印刷体,手写的大气又容易保存。乡下比不上大城市,但也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笔手”,如果不是在农村,这样的场景还真是碰不到。
过年去过很多地方,虽然有些地方经常去,可是过年,每次去心情都不一样。这里的景点不多,舜帝陵是个很好的地方,在我小时候是需要门票的,虽然只要30块钱,但是那时还觉得很贵,现在变成了舜帝公园不需要门票了。作为华夏“三皇五帝”之一,自然是给家乡添了浓重的色彩。仿佛舜帝的道德深深烙入故乡的大地上。孟子《离娄下》中曾经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它也在历史上经过很多次破坏,但空气依旧是清新,就像刚修缮过的老楼。门口又建起喷泉吸引很多人前来围观。沿着里面的大道前进,被两旁的树林包揽,他们叫夫妻柏。再走上几十步,陵庙门上,就能看见用石头砌成的坟墓。高3米,周围有50米的范围,还刻有邢其任写的“有虞帝舜陵”的石碑,周围还有千年的老槐树,非常茂盛。如果再向北走就可以看到皇城,又名离乐城。有高高的拱形门,东西两侧,结构严谨,左右对称。在大殿内,有泥塑的舜帝像,神态庄严,仿佛真人盘坐。是因为岁月,他们被深深地烙在了土地上,那是故乡,一个自己都认不全的地方。能写的地方太多,可我怎么也写不出,他们说年味淡了。也大概只有以前,我能感受到年。母亲忙碌的时候,家里人贴对联、包饺子。把旧的铺盖拆下来重洗一遍,现在也这样,但是味道却变了。过去,年三十晚上奶奶和爷爷说的话,都颇有滋味。过了12点,家家都放烟花爆竹,实在是不安静。那个阳台,如果我站在那儿,定会数数有多少烟花,会留意谁家放的。淅淅沥沥的鞭炮声,从凌晨到天明,甚至是早上十点钟。接下来的几天也定会做重复的事,虽然我不常喝酒,但我还是会说醉话。让过去的一年,都醉烂在酒里。
作者简介:于康杰(2000-),山西运城人,笔名桑田,太原市作家协会会员,写诗,散文。作品散见《星星》《诗潮》《散文诗》《诗歌月刊》《五台山》《太行文学》《都市》《雪峰》等,获知音诗会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零零国际诗歌奖等。有诗集《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