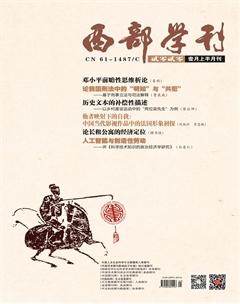浅析抗战对重庆地区教育理念转变的影响
姚瑶
摘要:对于重庆的教育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阶段无疑是抗战期间的大内迁。在抗战中,国民教育形态逐渐完善,促进了重庆的教育发展,特别是大批科研机构、工商企业、政府部门、高校及其人口等战略转移对于重庆的教育理念影响巨大,由普遍落后的“学而优则仕”理念,逐渐转变为抗战时期的“民主”“科学”“爱国”“全面”等教育理念,奠定了重庆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总体趋势,也为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抗战;重庆;教育理念;影响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079-03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和观念,是面向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要求。[1]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加上高校内迁、教育形态的完善等,促进了重庆地区的教育理念的转变:由普遍落后的“学而优则仕”理念,逐渐转变为抗战时期的“民主”“科学”“爱国”“全面”等教育理念,这样的转变对于重庆地区的教育而言,促进了教育的科学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了教育形态,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延续国脉”
(一)内迁续文脉
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一系列行迹引起了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担忧。他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经过对西部的重庆、四川进行了考察后,于1937年正式在渝筹备设校——南渝中学(后改名为南开中学,现重庆市南开中学前身),開启了中国东部先进文化向西部迁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央大学迅速将全部物资分批次转移到了重庆的沙坪坝,顺利完成了西迁,在重庆大学借出的松林坡建造校舍开学,成为高校内迁的开始。
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形势所迫,加上重庆相对安定的环境,更有国民政府的陪都地位,一大批学校纷纷开始迁移至重庆:主要有国立山东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兵工学校、陆军大学、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等30余所大学。随着西迁的顺利完成,各个高校设校开课,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师生身负国仇并继续艰苦奋斗,逐渐形成了在抗战时期享誉中外的重庆文化三坝: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三地”集聚了内迁的大量科研机构和学校,并以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而享誉中外。
(二)国民教育形态逐渐完善,促进重庆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其工业等相对落后,虽有大量的工业企业也伴随着内迁重庆,然而民众的素质仍然较低,技术人员急缺,而大量的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内迁,为培养技术人才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加大重庆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大批国立、省创、县办的职业学校孕育而生;同时,国民政府用专款在众多优秀的职业院校中推行职业训练班,重庆职业学校从1936年的9所,发展到抗战结束的42所,还不包括许多部委署和兵工厂等大型企业办的数十所技工学校[2]。职业教育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迅猛发展,不仅完善了重庆地区的教育体系,更为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除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外,重庆地区的基础教育也蓬勃发展。由于内迁的人口增多,基础教学不仅在数量上不能满足于现状,同时在质量上也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大力支持基础教育,不仅增加学校的数量,也注重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各类国立、省立、地方基础教育学校纷纷成立。到1942年,重庆中学增加为53所,在校学生21129人,到1944年中学增加为72所,在校学生25449人[3]。小学教育更是以“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其健全体格,陶冶其良善德行,教授以生活之基本技能”为宗旨,学制也采用“多轨制”,在制度上健全小学教育,在宗旨上丰富其精神。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规定“每一保必设一国民学校,每一镇必设一中心国民教育,以期完成建国之国民教育。”此外,为了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利,1940年3月21日,教育部制定《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国民教育之普及以5年为期。国民政府不断调整小学学制,使之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建立国民教育制度,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推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重庆及全国其他基础教育的发展。到1941年,重庆地区拥有各类小学136所,入学儿童44740人,教师1296人;到1944年发展到284所,入学儿童73937人,教师3316人[4]。不仅如此,幼儿教育也朝气蓬勃地发展,随着中国儿童保育会由武汉迁到重庆,重庆沙坪坝地区也随之成为全国儿童保育事业的中心,重庆育幼院在歌乐山的成立、重庆第二育幼院在向家湾的组建、陪都育幼院在高滩岩的设立、丛林坡中央大学校内成立第四保育院等等,这些保育院的成立,在战争时期为苦难的儿童创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成长乐园。
二、“居危思未”——烽火续辉煌
(一)西迁而来的教育理念
在西迁过程中,各高校、机构等以崇高的爱国主义为精神动力,克服艰辛万苦、历经万难迁往大后方:中央大学师生乘民生公司轮船举校搬至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学生赶着牲畜家禽长途跋涉西迁重庆;国立山东大学师生从山东徒步行至重庆;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到万县,由于图书、档案等遗失、损毁严重,教育部下令停办,师生转入国立中央大学等。历史现实磨砺师生身心、坚韧其精神,正如联大校歌所唱的那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褐。”[5]内迁高校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和发扬优良的校风、学风,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办学成绩。内迁高校除少数迁往城市外,多数迁往经济文化落后、自然条件极差的小城市或农村,但各个高校坚持教学科研并举,并结合时局科学办学。高校学子在艰苦求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将脚踏实地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将“求知”“求实”“求是”的教育理念彰显。一时,重庆教育众学子中不良风气大为好转,新的教育理念冲刷着重庆学子心灵。
(二)新理念影响下的改变
从国民政府高屋建瓴的学校课程改革,到学校负责任的办学态度和“民主、科学、进步、爱国、全面”的教育理念,再到教师艰难时期忘我的教授知识,学子发愤图强的求知欲望,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一时间重庆教育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在教学形态上,形成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完整的教学形态,与抗战前各个阶段教育学校、机构数量的对比,形成巨大的跨越。从师资结构上看,由于西迁高校、科研机构的影响,民国时代的优秀科研工作者、名师大家进入重庆的教育系统,壮大了原本较为薄弱的师资力量;在教育理念上,一扫“过去学而优则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树立了科学、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理念,从而改变学生的求学态度。在办学性质上,除了国民政府投入资金等兴建的学校外,社会力量也参与办学,根据社会需求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学业。对比彼时全国的其他地区,重庆在高校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居于前列,同时,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也为教育提供了一片净土,在这样的优势条件下,重庆教育培养出大批人才: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才达200多人,“航天四老”中就有两人深受沙磁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并有多名“两弹一星”元勋在重庆完成了求学时代的学业任务,重庆成为人才培养的教育强势地区。
三、教育理念转变对重庆教育的影响
由于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工作者的勤恳工作,莘莘学子奋发图强,使得重庆教育在特殊时期得以迅猛发展,而全面、科学、求是等教育理念也对近代重庆教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也正是如此,奠定了重庆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总体趋势,也为国家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新的教育理念给重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
知识分子、科研机构、高校内迁所带来的诸多新的教育理念,诸如:科学、民主、兢兢业业、全面、求是等。正是这些思想理念,给重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虽然战时教育部颁布高校共同学习的课程,其中包含各大高校共同的必修科,但是让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增加内容,所以各校合理安排专业课程,狠抓教学质量和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这样的科学、求是的态度,让学生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各个高校积极进取,取得丰硕的成果:例如重庆大学在抗战时期兴建无线电实验室和高压电实验室,开展远距离电波传送研究等。国立教育学院在抗战时期注重研究、教学以及推广,尤其注重研究,为此该学院专门成立研究部从事研究设计、编辑出版、收集资料三个方面。而在中学教育方面,1940年的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了中学生接受地质、矿物相关知识的要求,以此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同时为满足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的要求[6]。同样是经过教育的科学因素的注入,教育工作者通过通俗的教育活动,提倡科学的生活态度,诸如放弃女性小脚陋习、不分性别的接受教育、讲究清洁卫生、男女同学混合学习等。通过这些科学的思想传播,改变了重庆落后的教育思想,对于提升教育结构、发展教学理念、受教群体扩大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先进的教学理念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状态,又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在政治生活方面,各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其中
例如,南开中学学生热情洋溢地在磁器口演出街头话剧《当兵去》以宣传抗日;1940年12月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因抨击孔宋而被捕,重庆大学师生予以声援,商学院学生起草撰写《成情书》并以罢课予以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庆大学师生积极宣传造势,在舆论上施加压力,国民政府最终释放马寅初并让其重新回到商学院任教,而孔祥熙也因此逐渐失去蒋介石信任并最终离开政治舞台。1946年,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召开,各界积极参与,其中不乏有大量的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大学的学生、育才中学的学生等,他们以崇高的敬意参与并憧憬着未来民主生活,但是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会未能顺利进行。会后,社会大学学生举行集会活动,强烈谴责国民党的阴谋行径,并在教师的带领下参与慰问受伤的市民,以此表达对独裁政治的不满。这些民主抗争的意识广泛传播,并影响着教育民主化意识的发展,培养了学生民主、团结的思想,提升了受教育者和谐、民主、协商意识。在学校教育中,民主理念的加入,使师生开始认识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让学生从受教育阶段开始,便认识到以民主的态度解决社会问题重要性,极大地宣扬了民主理念。
(三)在民主的教育理念中,德育教育让学生认识到“和而不同”、尊重人的个性差异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日益注重全面发展。在学生发展的中学阶段,国民政府从整体上规划了学生的基本课程标准,从内容上涵盖了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又不失时宜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同时,在中学阶段,各学校也积极研究如何使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在高校中,教育部在颁布的大学公共课基础之上,允许各学校设置专业课程,而广泛并具有积极影响的各类活动(讲座、话剧演出、抗日演出、文艺展览、丰富的各类文艺作品、教育实习、社会活动等),也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对于学生爱国热忱、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各方面、各层次的提高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增强了全面教育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对近代教育中学生的全面发展理念的普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总结
抗战时期的高校、科研机构、民主团体内迁到重庆,对于重庆教育的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别是教育理念的改变,对于重庆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使重庆教育焕然一新,不分贫贱、地域、民族、性别等的平等教育,使得人才培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高校等在抗战胜利后开始回迁,但清新、科学的教育理念仍然扎根于重庆,重庆的教育工作者又利用遗留下来的物资条件等成立了新的学校、机构等,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高校回迁所带来的空白。而如今,在丝绸之路、第三个国家级工业合作园区落户重庆、重庆交通等优势条件下,重庆更应该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以教育来促进各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平水,万碧波,韩敏.教育理念的价值及其实现[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張洋波.抗战时期重庆职业教育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12.
[3]常云平.抗战时期大后方人口变迁——以重庆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4]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5]谢先辉,唐润明.二战对国内城市重庆的影响[J].民国档案, 2002(3).
[6]邓瑞珍.浅析抗战时期重庆中学教育的特点[J].青葱岁月, 20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