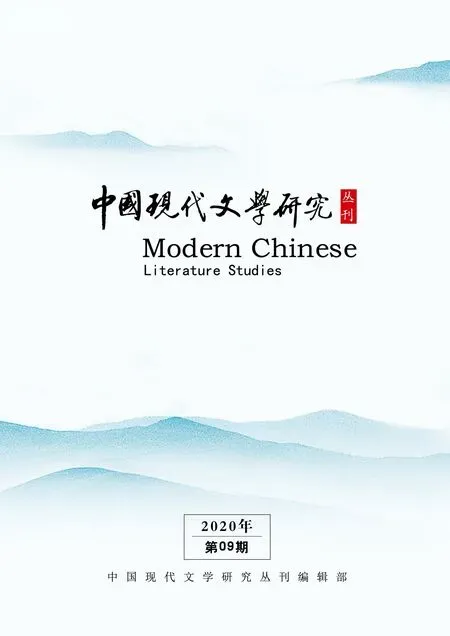“泡沫”:程青小说中的梦想书写※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所激发的现世梦想已成为当下国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程青小说对梦想的书写更多地从理性层面揭示人们生存状态的真相。在她的文本世界里,梦想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所诱发的隐秘欲望,既抚慰着人们饥渴困苦的心灵,赋予他们忍耐挫折的心力,又像一个个“泡沫”最终趋向破裂,昭示了其虚妄性本质;至于巧妙多样的叙述视角、对比呼应的人物设置、逆转开放的故事结尾等叙事策略,则以严谨有机的结构形态凸显了深邃稳定的人性内核。“泡沫”是程青小说对当下人们梦想的形象概括,更是历久不熄的人类梦想显露出的新面相;和钱钟书的“围城”、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等意象构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对照与呼应。
作为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的获得者,程青小说一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这或许与其独特不无关系:她在创作生涯之初,就有十年的停顿,这在当代作家中是极为少见的;而在当下女作家乐于强调自己的性别角色,纷纷采用感觉、躯体写作时,程青却选择运用日常笔调描绘普通人们的当下生活;此外她的作品拥有好看的故事外壳、明白晓畅的语言和非常机智的细节,没有故意吸人眼球的奇异外表。所有这一切可以指称的独特,虽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程青被关注的程度,似乎也成就了其创作的从容,使她能够以个人的节奏“在纸上构建自己的世界”1,以透过繁复纷乱的生活情境捕捉到内隐的社会心态,“泡沫”即是其文本内部象征人们梦想的独特意象。因此,从文本意蕴、叙述策略等系统梳理程青小说的梦想书写,无论对于怎样理解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生存真相,还是对于重新认识小说如何介入现实,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 现世梦想的多面相观照
程青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的审视,并在其中折射了她对时代变革所引发的个人欲望、梦想追求的叩问与反省;无论早年短篇《泡沫》《帐篷》,还是新近长篇《回声》《绿灯笼》,其题材范围、人物类型虽多有不同,但对市场经济下人们现世梦想的书写贯穿始终。
阅读程青的小说,我们首先遭遇的是她文本世界里那个绵延不绝的梦想者家族。无论是都市的老人、乡村的孩子,还是小镇的少女,他们都怀有或大或小的梦想;而且他们的梦想都是中国社会转型所激发的内心隐秘的骚动和欲望。《最温暖的寒夜》中,“不高不帅还没钱”的宋学兵,梦想借娶条件好的女人来改变自我命运,他认为“你心里喜欢谁跟你结婚的那个人基本上是没关系的”。2只要能摆脱现有的困窘生活就行。《泡沫》中两个同叫于洁的女孩,经历命运各不相同,但都在梦想的牵引、驱使下,努力拼搏,寻找着自己的罗马之路;狱中于洁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而记者于洁则不懈地追求着符合感觉的婚姻。而《艾琳简历》中那个出生在苏北小城的少女艾琳,一心想凭借文学创作出名,梦想成为当代的“天才作家”。《帐篷》中的图书馆员黄英则整日梦想着成为“爱而不得所爱”式的爱情悲剧主角。《画像》中八岁的放羊娃小盐粒,在目睹了美术学院的大学生为村民画像的过程后,萌生了对现代都市的强烈向往。更令人难忘的是《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中的吕非,他的梦想是体验一切人生悲欢,包括同性恋,“什么我都想尝尝,不好就扔下,我最看重体验,不体验就是浪费,是暴殄天物”。3“梦想”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层面反复出现,既是程青观察社会、探寻人类存在真相的特殊视角,也成为她小说文本最重要的主题。
程青对当代普通人的梦想描绘是和对转型期社会的剖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准确无误地把握了时代跳动的脉搏,即传统价值体系散落后的商品大潮给中国大众所带来的冲击或解放;并令人信服地把人们的梦想或希望书写成了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的梦想不再是稳定的工作、完整的家庭、富足的生活,而是渴望获得更多的机遇、刺激、体验与自由。在这样一个任何幸与不幸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时代里,个人的梦想不再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是基于心灵的躁动、焦虑,基于对自身生活的日常性、平淡性的厌倦,基于对更高的发展平台与更大的自由空间的追求。《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中雪荔与陆海平的婚姻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他们已不满足于以往的幸福家庭观念,而产生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他们的生活已达到预期的小康水准,再向前发展的余地就只剩下更换配偶。《做媒》中李薏费尽周折获得的满意婚姻,却在转眼之间消失,究其原因却是丈夫苏东平觉得“婚姻的责任是时时要负的,而婚姻的那点利益却很有限”。4在责任与自由之间,人们开始偏向自由。所有这一切人的期待和梦想,无不表明它们是扎根于中国社会这块广沃厚实的土地上,并沐浴着商品经济时代的风雨而成长起来的大树,这在1990年代之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时代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它改变的不是生活表象,而是生活模式,甚至是社会意识。”5可见,程青对于人物梦想的时代色彩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
梦想是人们活着的动力,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梦想,正如尤金·奥尼尔所说:“生活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幻想促使我们去斗争、去希望、去生活。”6程青文本世界里的人物不仅怀有梦想,而且梦想成了他们活着的依据;梦想是黑暗生活中的明灯,是纷乱心灵的抚慰;既凝聚了他们零散的生命激情,启动了他们突破自我的心理机制,又赋予他们的现实存在以意义,使他们能忍受苦难、战胜挫折。《艾琳简历》中艾琳为了“天才作家”的梦想,不惜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师生恋、婚外恋、单相思、多角恋等,还从故乡小城奔波到南京、上海、北京去发展自己、推销自己,最后干脆辞去赖以生存的工作,用父母半生的积蓄换来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始做“自由作家”。还有《泡沫》中的两个于洁,狱中于洁为了成为记者的梦想,在报社做勤杂工时,竟能弃绝过去的恶习,脱骨换胎般地勤恳工作;在梦想可能化为泡影时又铤而走险。而记者于洁则在一次又一次的结婚、离婚中追逐着符合感觉的婚姻。总之,梦想成为他们的生命所在,不仅越来越多地占据他们的心灵,而且支配着他们的生活,改变着他们的命运。因而,梦想成为程青塑造人物、构筑情节的依据与出发点。
梦想是人们克服困难的动力,甚至已化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可贵的是,程青并未把自己对民众心灵的画像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她在把梦想、欲望最大化的同时又昭示了它的虚妄,换言之,程青一面让她笔下的人物追随美梦,另一面又坚决地不动声色地击碎这个梦想,使人物形象的梦想无一例外地像泡沫一样破裂。《帐篷》中的黄英喜欢做菜和做梦,并按照自己的梦想设计恋爱过程;不幸的是,在她的精心安排与狂追不舍下,邵力很快就被她的一手好菜和一腔火热所俘虏,致使她那成为爱情悲剧主角的梦想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中的吕非,为了尝试多彩的人生(多角恋、同性恋等)完全放弃了应有的责任感,但当他对“小歌星”动了真情,并“打算从一而终时”,“小歌星”将吕非利用完后也毫无责任感地宣布自己压根不曾爱过他。《最温暖的寒夜》中,宋学兵因与家境好的樱桃结合,改变了经济困窘的生活现状,成了有家有业的男人,最后他却希望“只要能和刘冰清在一起,不管吃多大苦,他情愿一切推倒重来”。7其他还有于洁、艾琳、李薏等被梦想驱使的凡夫俗子,也都不曾如愿以偿。程青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品尝到了梦想破灭与虚妄的滋味。
如果说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在放出灾难、战争、瘟疫、疾病之后,被骤然关上,从而把“希望”留在了里边;那么程青则在自己的小说中让我们窥视了那个盒子——里面空空如也。潘多拉的盒子是对人性的洞察,即在任何困境中人都怀有希望或梦想;程青又对这种人性加以冷静观照,并揭示其真相,梦想只不过是人们将自我欲念的夸大与美化,恰如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旦触碰到它,就会瞬间破裂。“我始终认为讲个好故事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要告知读者真相。”8对人性真相的执着既使程青与那些沉溺于抒写个人情爱挫折而欲罢不能的女性作家区别开来,也使她的小说同整个人类的心理状态相关联,闪耀着一种智慧之光。
二 现世梦想的策略性叙述
对普通人现世梦想的理性观照,得自于程青对世事的体察和人性的了悟,这或许与她的记者生涯不无关系,她以自己特有的智性叩问当代国人的生存状态,使我们接近了国人甚至人类的真实存在;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9而关注当下、紧贴日常生活的程青,又是怎样将如此深远的主题意蕴融入细密驳杂的感性经验中的呢?在此,我们无法忽略她那举重若轻的叙述谋略,包括视角的选取、人物的设置、结尾的安排等共同构成了程青小说精心别致的叙述话语,不仅有效地凸显了梦想泡沫化的主题,而且直接化成为文本魅力的重要来源。
作为一个理性型作家,程青与林白有着鲜明的区别。林白的小说更多地书写女性感性世界的复杂丰富与美丽多彩,与此相应,她的叙事方式也呈现为非中心化的零散、片段式形态,并借助情绪与感受的层叠聚合,在无序中显露出深情灵动的轻盈美感。而程青的小说常能超乎性别限制,“我在创作中是选择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都要从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找一个最好的方案,一个最佳路径来表现,这无关我个人的性别”。10她能多方位、多层面地选取生活片段,来观照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并用巧妙多样的叙述视角、对比呼应的人物设置、逆转开放的故事结尾等叙事策略,在严谨有机的结构形态中凸显深邃恒定的人性内核。
与陈染的自叙传式小说不同,程青能保持与描写对象的适当距离,这使她的观察冷静而具有尖锐的穿透力,也使她的故事叙述可以采用巧妙多样的切入视角。程青的文本叙述人不管是以“我”还是以“他”的面目出现,总是自觉以某个特定人物的观察为切入点,采取限知视角;而且叙述人的身份是复杂多样的:年轻姑娘、老人、小女孩、男性骗子等,让这些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普通人体验、感受、言说生活,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泡沫》以年轻女记者“我”的视角来观察和叙述两个于洁的内心梦想和现实经历;同样,《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也选择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见证吕非的爱情历程,“我”与他们都有密切交往,甚至是比较要好的朋友,所以对他们的现世梦想既能给予同情理解,也能给予冷静思考;这样,叙述人“我”对于小说主题的言说就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还能反观、审视自我,并联想扩展到人类的心理状态——梦想不得实现。“她作品立即表现出明确的风格,即讲别人的事,但叙述者‘我’的观察与活动又深深地介入其中,甚至不可缺少。”11最有意味的是《今晚吃烧烤》,全篇以男性骗子王必盛为叙述视角,小说以第一人称从内觉的情感诗意的一面,细致描写骗子王必盛现世梦想的实施过程与最终落空,与外在社会对他的定位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游离了传统的道德评价层面,使读者和他一起历经梦想的美好强大和现实的真实残忍。“我的《今晚吃烧烤》之所以选择男性视角,是因为它需要这样一种表述的语调,以男性第一人称自述,看起来既像是调侃,又像是自嘲、自我剖白、自我洗涮、自我美化。”12可见,究竟采用哪个人物形象的视角切入故事,完全依据主题意蕴表达的需要,而非作者的个人喜好或自身性别。
巧妙恰当的切入点,使单个故事的言说具有真实感、独特性;而在我们阅读了程青的绝大部分作品后,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多样的叙述视角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不同的生活场景,在真切地复活了生活原貌的同时全面透视当代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使小说的梦想主题变得澄清而自明。当然,多样的叙述视角也面临着一定的危险,即作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趋近儿童、老人、男性骗子的感知世界,使作品摆脱观念控制的痕迹,并获得独立丰盈的生命形态。这恐怕是程青无法回避的挑战,也将是她今后继续探索的方向。
程青之所以能在饱含生活气息的日常叙事中揭示人类深潜的心理状态,除选取精妙的切入视角外,还在于精心设置的人物形象关系。一般而言,她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不是太多,但每个人物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人物之间既相互差异构成对比关系,又相互关联构成呼应关系;他们相互说明与强化,又相互否定与消解;从而使读者在清晰地洞察到当代社会普通男女形形色色的内心欲望的同时,体悟到小说主题的深层意蕴。在《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中,作者设置了雪荔、陆海平和红莲、晓月、刘佳两类人物,他们生活在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并通过“我”的游走联系起来;前者生活在一应俱全、富有情调的豪华住宅里,却因厌倦了生活的日常性而梦想婚外恋,后者挤住在黑暗潮湿的破旅馆里,却为了生活富裕的梦想而相濡以沫;但这两类差异对比的人物又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和呼应性,他们都被现世梦想占据心灵并付之行动,而且在红莲夫妇、刘佳与晓月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几年前的雪荔、陆海平辛苦奔波的身影,而雪荔夫妇今天的生活正是红莲她们梦想实现后的将来;雪荔夫妻现实生活的苦恼确凿无疑地消解了红莲们的梦想。而《今晚吃烧烤》中王必盛与五个女人之间也构成了对比呼应的关系,从社会现实层面看,王必盛是说谎者、行骗者,与他相爱的女人们则是受骗者,从而构成了对比关系;从社会心理层面看,王必盛之所以把自己梦想、打扮成一个有钱有闲有地位有爱心而又多情的男人,是因为女人们都梦想嫁给这样完美的男人,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王必盛把自己假扮成浪漫、温柔、体贴的男人,结果是通情达理的谢蓉、浪漫考究的李素素、美丽绝伦的唐心虹、精明能干的蔡菊花和单纯热烈的王菱都爱上了他,他也同时爱着这些不同格调的女人;但是他与其中任何一个女人的关系都消解了其他女人的梦想,而他的假冒身份则使所有女人的梦想化为泡影;王必盛周旋在五六个女人之间所感到的辛苦疲惫也显示了他那美妙梦想的虚妄,而他那以诈骗罪被起诉的结局,则是无情的现实打破了所有人物的梦想。现实的残酷与梦想的虚妄,得以在短小的篇幅内充分展示,不能不归功于对照互证的人物形象设置。
除视角选取、人物设置外,程青还借用逆转式结尾来凸显文本的梦想主题。逆转式结尾是小说在行将结束之际把故事所演进的趋向性翻转过来,以一种浑然天成而又别具匠心的方式,预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既进一步深化了观照人们梦想心理的主题,也使小说文本具有了意蕴上的无限性、结构上的开放性,带来了出奇不意的阅读效果。《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中“我”之所以到上海出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除昔日密友雪荔夫妇的婚姻危机;但在上海的36小时,一切都未按“我”的预想发展,小说随着“我”的离开上海而结束。这样,“我”出差前的使雪荔夫妇言归于好的强烈愿望与最后心安理得的无功而返形成鲜明的逆转;而且故事并未随着小说的结束而结束,故事将通过读者的想象继续发展,即上海的朋友仍将在梦想的召唤下按各自的轨道生活下去,该搞推销的搞推销,该搞婚外恋的搞婚外恋;一切都不会因为“我”的出现而有所改变,因为存在着一种比“我”更强大的支配他们行为的力量,即人物所生活的时代或社会。《情人节》则以老秦和李英的简短对话作结:“她睡意朦胧地问他:‘你怎么啦?’他回答说:‘没啥,睡吧。’”最日常的夫妻问答,却传达着无限丰富的逆转意味:二十几年前老秦就背着老婆丁淑英与李英相好,李英丈夫病死后,他忍痛舍弃一双儿女离了婚而与李英结婚。情人节这天,前妻丁淑英为了省却买墓地的钱,专门来找老秦商量死后二人是否可以合葬,老秦因深爱李英而未置可否,孰料李英明确表示不与老秦合葬,而要与早已病死的前夫合葬。李英的取舍,使老秦刹那间探得了自我追求的真相:八十二岁的他,与李英大半生的情感经营原来都是空的,这一发现使他对李英的问话,只能答“没啥,睡吧”。这一结尾使读者领悟到真正的幻灭是无法诉诸言语的,也预示了老秦今后情感倾向的逆转。其他如《艾琳简历》《有雾的小岛》《成人游戏》等作品,主人公都在旧梦想的泡沫破灭之际,升腾起一个新的梦想。小说在最富有包蕴性的一刻结束,既承接着故事的过去,又暗含着故事发展的走向,使读者获得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强化了小说的主题,即人的心灵总是被不断破灭又不断再生的梦想所占据,而且梦想是虚妄的,永远得不到实现。
可见,程青借助巧妙多样的叙述视角、对比呼应的人物设置、逆转开放的故事结尾使小说的叙述精简整一,且最大限度地深化、提升了小说的主题内涵,使读者在对当下人们的心理状态有了真切把握的同时,也在她那理性之光的烛照下,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姿态。程青虽然是写于洁、艾琳、黄英、王必盛等梦想的追求与失落,但由于这样的故事在今天这个时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作者是在审视于洁们,其实也是在反观、剖析自我,是在写你、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经济发展、文化转型的时代,追逐梦想并为此付出相应代价。当然,古今中外的人们又有谁能抗拒希望、梦想的诱惑呢?所不同的只是梦想的具体内涵:爱情、金钱、名声、地位、权力、美貌等;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所捕捉的“天边外”心态、钱钟书所描绘的“围城”心态、米兰·昆德拉所定格的“生活在别处”心态等都是对这一人性的深刻把握。对梦想的追求或许是造成悲剧的根源,但除此之外,人们又从哪里汲取生活的动力呢?“没有乌托邦就会使一种文化迅速退回到过去。现实之所以生气勃勃,就是因为它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张力之中。”13程青的文本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当下人们梦想心态的范本,“泡沫”成了今天人们内心梦想的象征。这是历久不熄的梦想在今天的新面孔、新姿态,带着社会转型所特有的躁动不安,当然这种象征意蕴不是对人性的简单图解,而是作者对纷繁散乱的当下生活的感觉与发现,并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叙述出来,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创造。在她的小说中,我们感悟到了人性的普遍状态,同时也更深切地洞悉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
冷静、机智、善于观察是程青最显著的优点,这与其记者身份密不可分,她那干净利落的文风和明白晓畅的语言,使文本简洁干练、内蕴悠长,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不知疲倦地苦心经营则是其获得更大成功的有力保障,艺术以束缚为生,死于自由,“束缚”指作家自我的克制,“自由”指杂乱无章,一个不会克制的艺术家便破坏了他的艺术自由;善于将自己的主观性控制在隐忍克制状态的程青,随着艺术感悟力的提高、生活深广度的增加,文学创作也一定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程青小说理应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其丰厚的内在意蕴、多变的叙事策略也将会得到更充分、深入的阐释,我们期待着。
注释:
1 程青:《纸上的世界》,《中华读书报》,2017年1月4日第3版。
2 7 程青:《最温暖的寒夜》,《当代》2013年第1期。
3 程青:《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4 程青:《做媒》,见《今晚吃烧烤》,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5 程青:《小说从哪里来》,见《天使》(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6 [美]尤金·奥尼尔:《论悲剧》,见《美国作家论文学》,刘宝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3页。
8 10 12 江水:《小说应该在作家的个人经验之上:访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程青》,《新华书目报》,2017年9月22日,第4版。
9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11 李冯:《花开两朵,三种可能》,见《今晚吃烧烤》(序二),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3 [乌拉圭]费尔南多·艾因萨:《我们需要乌托邦吗?》,见张穗华主编《大革命与乌托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