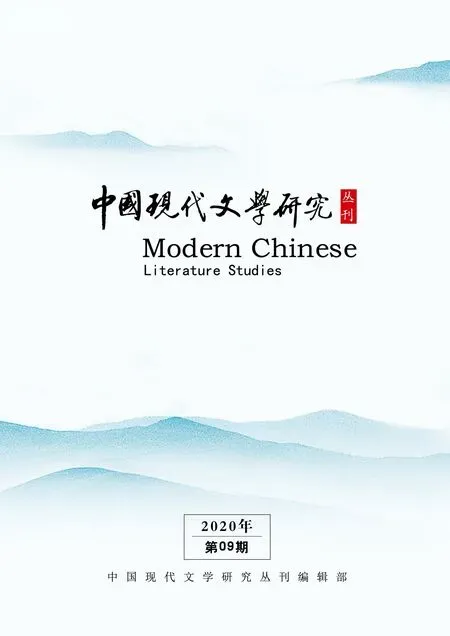“晦涩”论争与现代诗派的诗学构建※
内容提要:1930年代的晦涩诗风论争,大大增强了现代诗派的理论自觉和流派意识。经由对“晦涩”诗艺的深入阐扬,现代诗派的诗学主张和艺术理想得到进一步完善、传布。论争的深层动因是,中国新诗所借鉴的诸多西方文艺思潮在本土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板块冲撞,其间涉及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等。论争过程中,现代诗派及其同盟者梳理、开掘了这些诗学资源的源流演变和丰富内涵,特别是围绕诗歌与散文的分界问题,着力区分了意象主义的“散文性”与胡适、梁实秋“散文化”理论的差异,有效修正了“诗体大解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遗留的种种积弊。
1932年大型文学刊物《现代》在上海创刊出版,有力推动了现代主义诗潮的兴盛。现代诗派凭借极强的辐射力、包容性和创造性迅速取代新月派、象征派而成为1930年代诗坛的主宰。然而就在现代派诗歌蔚为大观之际,曾针对李金发等象征派诗歌而提出的“晦涩”批评,再度指向《现代》。首发质疑者是《现代》的普通读者,后继有梁实秋、胡适等权威评论家接连发难,论战不断升级。这场晦涩诗风论争旷日持久,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才有消歇。藉由论争,现代诗派的诗学主张、艺术理想得到有效宣传,强化了理论建构之于创作实践的支持与导引。现代诗派对“晦涩”品格的积极辩护,为诗歌争取到了独立于散文的艺术疆域,有效修正了五四初期“作诗如作文”“诗体大解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积弊,同时推动了西方现代诗艺与东方古典诗学在更高艺术层面的融通化合,在诗的表现对象、表现方式、艺术形态上都有了新的调整、完善和突破。
一 晦涩诗风下的诗学建构
《现代》是一种综合性文学刊物,主推小说与诗歌,兼有戏剧、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及译介等。其所发表的诗歌作品风格多样,既有臧克家、老舍所写的现实主义诗作,也不乏散发着浓郁新月气息的浪漫诗作,但整体上还是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主导。但这类作品很快就遭到了读者的批评。有读者致信编辑部,认为《现代》发表的一些诗作缺少韵律节奏和明晰的情感表达,内容奇异玄奥,读之“如入五里雾中,不得其解”,“想是受了戴(望舒)、李(金发)诸象征派诗人的毒”。1施蛰存择取两份读者来信,分别于1933年9月、1934年6月在《现代》“社中谈座”栏目刊出,并撰文回应。
主动刊发读者的批评信件,及时回应讨论,体现了《现代》的办刊姿态,“把本志编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而非高于读者、喜好说教的“师傅”2,这也包含了许多策略性的考虑。《现代》标榜自己无意倡导任何流派,却又积极利用回信读者的机会,借助对“晦涩”的辩护而大力宣扬现代诗派的诗学理念、文艺标准。这种书信式讨论,比居高临下的理论宣讲更有效果。施蛰存在复信中指出,诗歌摆脱韵律,不是不注重形式,而是从旧形式向新形式转变;至于“读不懂”,可能与作者技巧相关,但更在于,诗歌原本不同于平直的散文,表意“较为曲折”,可以直抒,也可以使用“曲写”和“暗示”,不必以“一读意即尽”来苛求。3在与读者的书信讨论过程中,施蛰存及时推出了后来被视作现代诗派理论宣言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以近乎绕口令的表述廓清了现代诗派的边界:“《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4
以现代情绪的现代表达为理由,《现代》有力驳斥了读者基于传统诗学观念或散文阅读期待而提出的质疑,为现代诗派争取到更多理解支持。精研于象征主义的梁宗岱就撰文声援,认为“纯诗”是通过感官与想象的感应而产生“符咒似的暗示力”,伟大的作品往往高深精微。面对自己读不懂的作品,读者或批评家要更多反思“我赶不上作品”。5稍后,施蛰存再次登载一封读者来信。信件重点论述了诗与散文之别,散文须明达晓畅,诗歌则务含混蕴蓄。譬如胡适《乌鸦》《车夫》一类诗作,虽不失为好诗,但现在读来终究有些“浅薄幼稚”。6
在这一阶段论争中,《现代》可谓收放自如,不仅成功将“社中谈座”改造为传递自己诗学观念的平台,极富引导性地将“读者意见”统一到了编者立场,而且在与胡适诗歌的比照中凸显了现代派诗歌艺术质地的纯粹,以及晦涩诗风在诗歌进化链条上的合法性和未来趋向。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与推崇“胡适之体”、恪守“明白清楚”法则的梁实秋一派的矛盾。
1936年年初,梁实秋在《自由评论》相继发文《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7以及《诗的意境与文字》8,借胡适“明白清楚”的诗歌主张而抨击现代诗派的晦涩风格。他坚持,诗人创作首先要对人说话,语言文字自当清楚明白。这不独是“胡适之体”的特点,且应成为白话诗创作的普遍准则。当下诗坛日渐盛行“晦涩的崇拜”,写出许多不明白、不清楚的诗作,根源就在于模仿了“象征主义”这样的“堕落的外国文学”。梁实秋视“象征主义”为堕落文艺的偏激主张,遭到现代诗派及同盟者的合力反击。邵洵美、金克木、天水、吴奔星等纷纷撰文回击,“胡梁二先生的诗论贻害诗的前途匪浅,凡是对于诗有信仰有研究的人,都该鸣鼓攻之才对,千万别为他们的声名所慑服”。9
这些辩护文章大体都立足艺术本体而展开学理探讨,“晦涩”作为现代诗歌的重要品质由此得到多侧面的论证。主要观点有:一是诗歌有不同于散文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其具有很强的个人性,无须为迁就他人而拆成散文以致失去自己的完整与精确;表现内容上,诗歌往往超越于逻辑推理和科学证明,“根本拒绝了散文的教师式的讲解”。10二是解诗需要读诗者与作诗者拥有同等的智慧,不能将自己读不懂的诗简单判定为“谜诗”。三是诗的语言有别于白话。诗的语言讲求经济和最大效果,蕴含着实指、感情、语气及用意等多种成分,绝非“清楚明白”的“白话”可以涵盖。当然也有批评家如朱光潜尽可能依学理表达“持平之论”,认为诗作要产生“明白清楚”的效果,需要“作者的传达力”与“读者的欣赏力”相近;诗歌语言依然要讲求文法通顺、表意到位,但“言”与“旨”的关系乃是相对的,不能奢求人人都能明白。11
梁实秋并不甘于论战失败。稍后他与胡适又上演一出“双簧戏”,再度攻击现代诗派。1937年6月,梁实秋化名“絮如”,假托“一个中学国文教员”的身份,投书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指责“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还特别举例卞之琳的诗作《一盏灯》和何其芳的散文《扇上的烟云》,斥其为“糊涂诗”“糊涂文”,对中学生国文教育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胡适在“后记”中应和:“做这种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的能力太差,他们根本没有叫人看懂的本领。”12胡梁二人的唱和,并没有进一步推进有关“晦涩”的学理探讨,反而将论战由现代诗派扩展至京派文艺。毕竟卞之琳、何其芳都是京派主将。不久周作人、沈从文就去信《独立评论》驳斥梁实秋。周作人分析了晦涩的成因,认为普通读者并无权以“懂与不懂”去判定文艺的价值优劣。13沈从文则认为有风格的作品不是缺少表现,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表现方法;不是疏忽于文字,而是过于专注于文字。14这场围绕现代诗派而展开的晦涩之风论战,牵涉到诸多复杂的派别冲突和人事纠葛,但整体上还是限定于文学场域内部的观念分歧,还是就“诗何以为诗”的本质性命题的阐释而重新规划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和演进形态。
二 “晦涩”诗风与西方诗学资源
梁实秋有言:“新文学的最大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5语虽偏颇,却着实凸显了西方诗学资源之于中国新诗形态演进的巨大影响。循此思路,我们不妨对晦涩诗风论争各方所秉持的西方诗学资源作一探析比较,以窥矛盾之根源。
现代诗派所接受的西方诗学资源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西方象征主义,其二英美意象主义,其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诗派从西方象征主义体内汲取了丰富的晦涩因子,借鉴对象整体经历了从前期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人向后期瓦雷里、里尔克等人的转变。不同阶段的象征主义,对“晦涩”的理解阐发不尽相同,同一阶段不同个体所追求的艺术风格亦千差万别。择取哪一触点,以何种方式与象征主义发生关联,对现代诗派成员的艺术风格,包括晦涩程度都有很大影响。这当中,卞之琳诗作的晦涩程度最为突出。卞之琳初期追求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后又受前期象征主义以及中国晚唐、南宋诗风影响,注重融古化欧,喜欢设置戏剧化场景;及至1930年代中后期,更多受到后期象征主义瓦雷里以及艾略特的牵引,加速驶向主智化道路,晦涩因子的浓度明显提高。
相较之,作为现代诗派首领的戴望舒,其对东方古典的吸纳同样偏重晚唐五代,也曾学步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一度迷恋于超现实主义技艺,但诗风并不如卞之琳那样晦涩。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戴望舒基于“情本位”而择取的独特的中西诗学交汇点,以“诗情”而非“智性”为其艺术内核。最令其倾心的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不是瓦雷里,而是风格柔婉清丽,注重精微感受和别致想象的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等几位。“情本位”根基贯通于东方古典诗歌的抒情血脉,在审美体验、阅读感受方面会降解部分晦涩因子。同属“主情”一路的诗人,还有何其芳、李广田等。
与象征主义相比,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20世纪初兴起的先锋艺术思潮往往更加荒诞费解。如果说象征主义的“晦涩”主因是“所指”艰深繁复,“客观对应物”背后蕴含着深邃意旨。那么未来主义等则崇奉于无意识、梦幻、“自动写作”“速度之美”,极力斩断“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联,制造出扭曲变形、抽象混杂的艺术场景。但其对现代诗派的影响比较有限。《现代》杂志编发过不少有关这些思潮的译介文章,但作用于创作实践还是集中体现在徐迟、路易士、程江帆等几位偏重都市生活描绘的诗人。不过在晦涩诗风论争中,徐迟等并没有成为主要靶子。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徐迟、路易士等人的诗歌创作起步不久,尚属现代诗派中的晚辈,没有吸引太多注意力。二是他们以上海为背景展开的都市描绘,对乡土中国来说非常新颖独特。由声光色影搭建的艺术幕景,一定程度上打破、改变了作者、批评家传统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期待,使其不再苦苦探求“微言”后的“深情”与“大义”。三是徐迟等人的都市书写,没有像未来主义等激进派那样过分张扬非理性、反道德色彩,没有一味把创作当作“情绪喷射器”;相反,他们与意象主义结合,努力把现代都市的新感觉纳入到意象当中,强调艺术的凝练性。值得一提的是,以象征为形式、以古典为内容的戴望舒同样熟谙西方先锋文艺,他一度大加赞颂未来主义者马里奈谛,还在超现实主义诗人苏拜维艾尔、艾吕雅、洛尔迦等人的启发下创作了《灯》等一批注重直觉表现的作品。但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梦幻与现实交融的精美意象的拼贴组合。现代诗派在吸纳以未来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先锋文艺时,又自觉借助其他艺术资源对其非理性的一面加以改造、抑制,对降解“晦涩”起到积极作用。
三 “意象主义”与“晦涩”的繁复关联
与意象主义关系最密切的现代派诗人是施蛰存。作为《现代》刊物主编,他不仅刊发了徐迟、邵洵美等论及意象主义的译介文章,在《美国文学专号》上登载大量意象派诗作,还亲自选译了《美国三女流诗抄》,介绍了陶立德尔、史考德、洛威尔三位意象派女诗人。除此之外,他借鉴意象主义,创作一组“意象抒情诗”。借助《现代》平台,施蛰存有力推动了意象主义风潮的兴起,且整体性地覆盖、渗透了现代诗派,“现代派诗的特点便是诗人们欲抛弃诗的文字之美,或忽视文字之美,而求诗的意象之美”。16但饶有意味的是,反对晦涩诗风的胡适同样奉意象主义为圭臬,其发动“文学革命”“新诗革命”都深受意象主义启悟,其所执守的“清楚明白”的诗论主张,亦深得意象主义支持。不过更令人费解的是,与胡适并肩反对晦涩诗风的梁实秋却自“五四”起就对意象主义颇有微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晦涩诗风与意象主义的繁复关系,以及意象主义在中国诗坛本土转化过程中发生的多向阐释和丰富异变。
从西方现代诗学的演进流变来看,意象主义对后期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构成双重反动。它把意象定义为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力图以客观准确的意象来代替主观情绪的发泄和抽象理念的探寻。为强调这一点,意象主义者时常拿散文来类比诗歌创作,“要写出好诗,就至少要写得像优秀散文一样好”。17意象主义诗歌对“散文性”和坚实清晰艺术风格的追求,对于中国新文学、新诗的发生都有重要启悟。
但问题是,意象主义以散文来比拟诗歌创作实乃策略性表述,目的是挤掉“湿淋淋”的感情和“干瘪瘪”的理念,留余精确客观的意象和具体清晰的意义,提取到“干而硬的诗”,“我们要除去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要教诗的文字即如说话,用简单如最简单的散文,而成为心的呼声”。18其本意并非要取消或淡化诗歌与散文的分界;相反,意象主义明确拒绝以散文来阐述诗歌,“让散文表现理智,把直观留给诗歌”19,“相信诗的意思应当集中,不同散文里的意思可作松散的排列”。20早期意象派理论家赫尔姆更是对阐释诗歌深恶痛绝,“解释,拉丁文explane,就是把事物摊成平面”。21总而言之,“散文性”仅是意象主义在特定向度上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其前提依然是散文与诗歌有明确分界,彼此在关注对象、表现内容、呈现方式等方面迥然相异。
此外还需注意,意象主义虽然向象征主义发起挑战,反对读者去探寻“客观对应物”背后的幽深语义,主张还原意象本身的具象性,但并没就此放弃对感情、思想和观念的挖掘。从庞德的定义“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22,就能看出意象主义依然非常注重主客体的契合感应,所调整的只是主客化合的形态与方式。在此意义上,意象主义部分承续了象征主义的血脉,故有意象主义乃象征主义之分支,“其源肇于法”的说法。23
然而对于意象主义在“散文性”之外所坚持的诗学主张、所经历的源流演进,胡适没有充分注意到。“五四”初始,面对新旧体诗歌的激烈交锋,胡适非常巧妙地借助意象主义的“散文性”来攻克古典城堡,有效推进了新诗革命的进程,但却忽略了诗歌独有的文体疆界、艺术品格和精神气质同样是意象主义所执守的重要的诗学目标和美学理想。
及至现代诗派,其对意象主义的认识已远超“五四”一代,能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开更加全面深刻的检视反思,能够穿透意象主义关于“散文性”的表述策略,将学习重心真正放在“意象”上。它在意象主义基础上主动复合象征主义以及其他思潮流派的诗学观念和艺术技巧,积极会通东方古典诗学,强调诗歌创作的艺术自足和内心发掘,“回到各自的内在,谛听人生谐和的旋律”,“藏在各自的字句,体会灵魂最后的挣扎”。24与“五四”白话诗、新月派诗歌或象征派诗歌相较,现代派诗歌的意象普遍更加醇厚、隽永、富有个性,更具备“坚实而清晰”的特征。但也无须讳言,在意义阐发上,现代诗派的作品时有晦涩难解的情形。不过就论争所牵涉到的诗人诗作看,晦涩成因基本不是诗人的表现能力差,而是运用独特的诗歌技法,挖掘出了许多无法用散文转述的自我生命形态。这恰恰是与意象主义保持了一致,即拒绝散文对诗歌的阐释。但这也“引火烧身”,将梁实秋对意象主义的批评引向了现代诗派。
梁实秋鼎力支持“胡适之体”,将“清楚明白”当作诗歌第一要义,主张以散文的标准来规范诗歌,“把诗译成散文,然后再问有什么意义”25,但对于意象主义的“散文性”始终没有给予积极呼应。作为新古典主义者,梁实秋对中国新文学一味学步西方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一方面强调理性的至高地位,须对情感状态作出强力的监控引导,防止逾越伦理道德、永恒人性的边界;另一方面又要求以饱满的情感、丰盈的生命来支撑理性。梁实秋理想的文学形态就是在二者矛盾中实现平衡。表面来看,讲求理智与情感相融的意象主义,恰恰契合于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理想。但事实上,梁实秋不仅不满于现代诗派所借重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者等,“其他的如什么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未来主义等等,那全是出奇立异的勾当,其结果是自寻坟墓”,对于意象主义同样极度排斥。缘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意象主义大大放松了对于诗歌形式和内容表现上的约束,推动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对理性法则、道德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二是意象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早期白话诗歌,其意象过于直接客观而几近于无情感含量的物象。三是现代诗派挖掘的内生命常常携带有潜意识、非理性意识,容易逸出理性边界,部分诗作的抽象玄思又挤占了情感的空间,“凡是写出令人不懂的诗的人,一定是他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可写的,或是糊里糊涂的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所要写的情思,所以结果是产生一些不成熟的晦涩无意义的作品。有的人美其名曰象征诗”26。在梁实秋看来,意象主义所招致的自由化、物象化、智性化和非理性趋向,都不符合新古典主义法则;而现代诗派在意象主义基础上还吸收了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种西方现代文艺,不仅在形式、内容上反叛理性,而且严重偏离了“情本位”根基,制造了“晦涩”效果。梁实秋不遗余力地与“晦涩”作战,主张以散文标准衡定诗歌,目的就是要取消诗歌的自治特权,一并纳入到由理性统辖的艺术世界,充分维护新古典主义的文学秩序。如此一来,不仅驱走了“晦涩”诗风,更切断了经由诗歌而抵至个体隐秘生命的重要通道。
晦涩诗风论争大大增强了现代诗派的理论自觉和流派意识,推动其在诗学建构和创作实践领域取得双重突破。现代诗派及其同盟者在为“晦涩”辩护的过程中,进一步还原了意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丰富内涵和多维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往新诗过分“追新逐异”“为我所用”所造成的理论偏颇和创作积弊。不仅如此,现代诗派对“晦涩”的阐释和实践,具有很强的创造性。许多原本在西方语境中呈线性演进的思潮流派,被纳入到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内实现新的会通融合,着力服务于新诗艺术品质的提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现代诗派准确把握了意象主义追求的“散文性”主张与胡适、梁实秋宣扬的“散文化”理论的本质差异,肯定了“晦涩”之于维护新诗文体独立、开掘个体生命、丰富艺术形态的积极意义。不无遗憾的是,这场论争在1937年之后伴随社会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而消歇。但这并不意味着“晦涩”问题失去了讨论价值。事实上,1940年代的九叶诗派、1980年代的朦胧诗歌都曾因晦涩风格遭受指责。只是与时代语境有关,此后再度兴起的晦涩论争,更多集中于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调整上,对于文学场域内部的诗学问题的探究远不及现代诗派参战的这一场。
注释:
1 3 编者:《关于杨予英先生的诗》,《现代》1934年第5卷第2期。
2 施蛰存:《〈现代〉编辑座谈》,《现代》1932年第1卷第1期。
4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1933年第1期。
5 梁宗岱:《谈诗》,《人间世》1935年第15期。
6 吴奔星:《诗的读法》,《现代》1934年第3期。
7 梁实秋:《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1936年第12期。
8 灵雨(梁实秋):《诗的意境与文字》,《自由评论》1936年第12期。
9 吴奔星:《诗的“新路”与“胡适之体”》,《文化与教育》1936年总第88期。
10 柯可(金克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937年第4期。
11 朱光潜:《心理上个别差异与诗的欣赏》,《大公报·文艺》第241期,1936年11月1日。
12 絮如(梁实秋):《看不懂的新文艺》,《独立评论》1937年总第238期。
13 知堂(周作人):《关于看不懂(一)》,《独立评论》1937年总第241期。
14 沈从文:《关于看不懂(二)》,《独立评论》1937年总第241期。
15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1931年第1期。
16 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清华周刊》1935年第1期。
17 庞德:《关于意象主义》,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8 20 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诗》1922年第2期。
19 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现代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9页。
21 [美]约翰·迪尼、刘介民主编《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3页。
22 [英]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23 梅光迪:《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8月8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7页。
24 刘西渭:《“鱼目集”》,《大公报·文艺》第126期,1936年4月12日。
25 26 梁实秋:《一个评诗的标准》,《偏见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