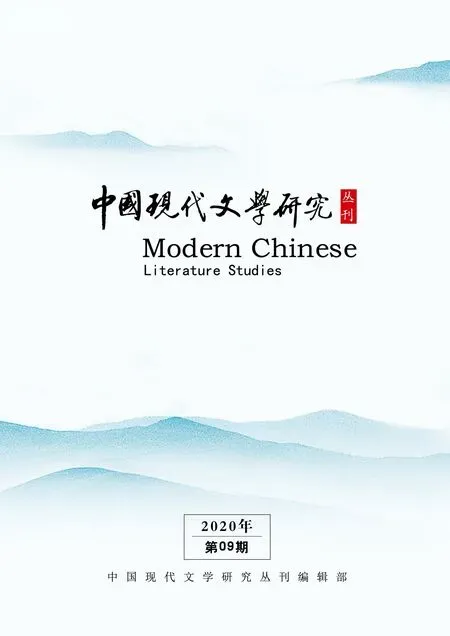“民族文学运动”与长篇小说《狂飙》※
内容提要:1942年,陈铨在抗战文学热情减退的历史背景下,发起了一场“民族文学运动”,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狂飙》,其用意就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鼓舞抗战士气。在这场运动当中,陈铨提倡“力”的文学和英雄崇拜,主张民族之上与国家之上,并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毫无疑问,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无论“民族文学运动”还是长篇小说《狂飙》,都旋转升腾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绝不是什么法西斯主义的中国翻版,而是一个心系祖国、热爱民族的中国作家,在激情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正能量的文学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陈铨是一位著名的现代作家,但由于他是“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并且还发起过“民族文学运动”,所以才没有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无论“战国策派”还是“民族文学运动”,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爱国行为,他们提倡民族之上与民族复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学观念问题,而不是什么政治立场问题。陈铨本人远离政治,“一生都不愿做官,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推荐陈铨担任政府要职,但是被陈铨婉言谢绝”1。他之所以要发起“民族文学运动”,并用长篇小说《狂飙》作为实践,充其量是在表达“知识人的理想、文学家的真诚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深深的危机感,而不是执政者的肆意、当权者的威仪或者意识形态掌控者的傲慢”2。因此,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自由知识分子呼唤民族主义,主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的直接体现。
我们首先来看看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1942年5月13日,陈铨在重庆《大公报》“战国策副刊”第24期上,发表了《民族文学运动》一文,正式提出了“民族文学”的理论主张。陈铨发起这场运动的思想宗旨,主要是批判和否定五四新文学的“西化”倾向,强调中国文学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陈铨认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他所主张的民族意识,就是作家对于国家民族的赤诚之爱。以此为衡量标准,陈铨把新文学分成了这样三个不同阶段:五四时期是“个人主义”阶段,1930年代是“社会主义”阶段,七七事变以后是“民族主义”阶段,“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这一个集团,不但要生存,而且要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大前提下——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中华民族只有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中国的文学,从现在起,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将来”。3
陈铨虽然充分肯定了五四启蒙的积极意义,但是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客观存在的历史弊端,也有着清醒而理智的思想认识。他指出“五四”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以世界主义去消解民族主义,只宣扬西方的人文精神,却忽略了它们的虎视眈眈。第二个错误是以个人主义去消解集体主义,其结果是一切都以个人为出发点。第三个错误,就是“虽然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缺点,因而有新文学的出现,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提出民族文学的旗号”,相反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凡是外国的东西都是新的”。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陈铨决定发起一场“民族文学运动”,其“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他们要为祖国展开一幅浪漫、丰富、精彩、壮丽的人生图画。有了这样的民族意识,伟大的民族文学运动才可以成功”。5
“民族文学运动”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了统一战线内部左翼作家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民族文学运动”强调“力”感之美与英雄崇拜,无疑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强权政治的中国翻版。如茅盾曾斥责,陈铨不加思辨地推崇以暴制暴,这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两样。6张子斋则认为,陈铨崇拜尼采式的天才英雄,蔑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违反了群众的要求,违反了时代的需要”。7戈茅等人干脆把“民族文学运动”,直接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文学运动,认为其言论实质“是一派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为虎作伥与谋皮的谬论”8,是一种与人类历史潮流相背而行的“反理性主义的逆流”9。这些出自左翼阵营的批评意见,显然带有很大的思想偏见性。
不难发现,“民族文学运动”口号的提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其一,五四后期很多知识精英都在进行自我反思,他们发现反传统的可怕后果,是“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10。他们明确反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文艺复兴运动”,因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重新认识,而“‘五四’运动却不然……当时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认识如何呢?态度又如何呢?我们是虚心的,切实的研究过,还是一律加了封条,说是封建思想,扬言打倒孔家店,徒快一时之口而已呢?这都是不必深问而尽人皆知的事,以那样的认识,那样的态度,我们如何能和西洋文艺复兴相比呢”?11其二,反思五四的真实目的,显然是要重识传统文化、重构民族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从1930年至1942年,中国思想界一直都在强调“民族”立场的根本原因。比如,1930年黄震遐等人所发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意在提倡振兴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1935年王新命等10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意在重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1940年国统区和延安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争鸣,更是意在为新文学发展指明方向。而陈铨发起的“民族文学运动”,只不过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已。其三,1930年陈铨从美国奥柏林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他又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时期,德国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国内经济的日益衰退。希特勒大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体系,不仅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复苏,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畸形繁荣的德国神话。陈铨目睹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同时也预感到一个世界“战国时代”即将到来,他迫切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有所准备,因此陈铨和《战国策》同人,都主张“‘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目的就是宣扬“民族之上,国家之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12这无疑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的强烈表达,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个人非常认同这种说法,陈铨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所宣扬的思想与其说是有些人所指责的法西斯主义,其实不如说是较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13。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却具有鼓舞民族士气、提振民族精神的积极意义。
陈铨不仅是“民族文学”的理论倡导者,同时也是这一口号的创作实践者;1942年长篇小说《狂飙》的出版发行,便是“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这部作品刚一问世,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陈教授的故事叙事方法是‘做’的,而不是‘创作’,很有些文字在全书中无存在价值,‘自我性’的文体,会使读者们有种不好的观感,觉得一切对话,文字都是陈教授的,而不是属于书中人物的”14。也有人嫌《狂飙》的语言太啰唆,认为作者叙述主人公“怎样从个人主义蜕变出来的过程,虽然费了很大的篇幅,却像很多嘴的老太婆讲述一个毫不动听的故事一样”15。即便是到了现在,仍有学者说《狂飙》的叙事结构布局似乎有些不成比例,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奇怪感觉。16但我个人却不太赞同这些说法。陈铨是学哲学出身的,而逻辑严谨性又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仅从情感叙事这一角度去看问题,那么将会大大低估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陈铨曾毫不隐瞒地告诉读者,“怎样从个人的‘狂飙’达到民族的‘狂飙’,这正是全书的结构,也就是怎么样从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转变到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关键”17。作品的故事情节与叙事逻辑也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比如,五四以前并非《狂飙》故事的叙事主体,但是为了呈现这部作品情节发展的完整性,陈铨借一位小学校长的开学致辞,把许多重大事件都不露痕迹地一笔带过:
(中华民国)今年他九岁了。在这九年中间,他曾经害过许多的疾病。四岁的时候,袁世凯称帝;六岁的时候,张勋复辟;七岁的时候,南北对峙;八岁的时候,和平会议又失败了。今年开始九岁开头,又有直皖之战。这些病都是很危险的,但是他并不因此丧失了他的性命。同时在外部,他也经历了许多的危险,这些危险,现在不惟没有减轻,比以前更加厉害。……特别是这一批小朋友,他们是将来国家的主人翁,他们一定不会忘记了他们的责任!18.
陈铨把民国比喻成一个命运多舛的“病孩子”,既扼要回溯了民国初期的真实状态,也深刻表达了作者本人的忧患意识。至于《狂飙》为什么会把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五四至全面抗战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因为陈铨着眼于反思“个人狂飙”对民族观念的巨大破坏性;而几位年轻主人公从“个人狂飙”回归到“民族狂飙”,只不过是为了要让他们完成自我觉醒的救赎过程。这种严丝合缝的叙事逻辑,又集中体现为《狂飙》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以李铁崖为代表的辛亥前辈,始终都坚守着民族主义立场;以立群、国刚、翠心、慧英为代表的现代青年,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这种由“代差”所造成的矛盾对立,直接反映着五四以后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然而,无论现代青年表现得有多么“自我”与“叛逆”,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民族立场——国刚等四名青年后来投身抗战、英勇献身的故事结局,反映的就是他们对于民族身份的自觉认同。
铁崖既是《狂飙》的灵魂人物,也是陈铨思想的代言人。他曾是日本帝国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捐献了家产、中断了学业,那种牺牲自我、天下为公的革命精神,就连“同党的人都佩服”。然而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看到新政府的贪污、因循、麻木和无耻,故他失望之极,先是出家后又返乡,并把拯救民族的未来希望,寄托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身上。正因为如此,铁崖对于五四启蒙颇有微词,他指出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外国列强一直都在虎视中国,然而启蒙却提倡个人主义,幻想着和平主义与世界大同,这令他感到焦虑万分。铁崖强调必须通过教育,去强化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首先,是教育国民在群雄环视的世界格局中,“民族主义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一个国家处在这个时代,要求生存,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机构,都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建设”。其次,这种教育要从儿童时代开始,就灌输一种民族危机意识,让他们懂得“要求生存,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机构,都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建设”19。最后,若想不被别人欺负,不再重蹈鸦片战争的悲剧,就必须“富国强兵”“科技兴军”,所以他鼓励国刚和立群要刻苦学习,好好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因为一旦发生战事,是要靠国防力量去说话的。铁崖不仅宣传民族主义理论,同时还身体力行、亲躬实践,如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他已未雨绸缪组织起了一支拥有万人之众的农民“义勇队”。另外,铁崖也经常教育自己年幼的孙子,要“常常都想到战争,常常都预备战争”20。仅以铁崖这一艺术形象而言,他为了中华民族奉献出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视为生命的唯一爱子,其爱国主义情操就值得人们去敬重。
立群、国刚、翠心和慧英是《狂飙》中的五四青年,他们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但是立群与翠心、国刚与慧英这两对人物,最终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立群是个富商子弟,从小进入贵族学校,“读书、打球、练洋操、唱歌,还有许多游戏”21。他与慧英既是一块成长的发小,又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两人之间知根知底、相互了解,并不存在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在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立群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在南京读中学时,校长是位北大的毕业生,“他最佩服胡适之先生。胡适之先生随便讲什么话,他都赞成。胡适之先生有一部书叫《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杰作,他曾经读了二十几遍,每次都发现新东西。他劝我们也读。……他说他以前也写旧诗,后来同胡适之先生谈了一晚上,他知道旧诗毫无价值,就决心写新诗了”22。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陈铨就是在讽刺那位校长,盲目地崇拜胡适和新文化运动。进入到大学以后,立群开始追求“恋爱自由”,抛弃了相恋十几年的慧英,又爱上了她的挚友翠心。用翠心自己的话来解释说,她和立群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但是自私自利又有什么不好?人类不是求生存吗?生存的目的,不是寻快乐吗?”23故他们二人根本就不管身边正在发生的民族危机,“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上下已经掀起了一场抗日救亡的爱国浪潮,可是人在北平的立群与翠心,却无动于衷、尽情浪漫:“生活方面,他们是很舒适的。穿可以穿好的,要吃什么有什么,住的屋子,优雅清洁,对于吃,他们特别讲究。北平有许多年代悠久的馆子,都有特殊的作风,他们家里,新雇了一个手艺极高的厨子,他们还嫌吃得太腻,常常两人到外面馆子去吃饭。”他们一直这样鬼混,既忘记了父母亲人,更忘记了国家民族,“少年意气,尽销磨了”24。在陈铨本人看来,立群与翠心的自我堕落,就是“个性解放”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青年都像他们一样,只顾自己享乐而无视国家命运,那么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其实陈铨早就在《论英雄崇拜》一文中,明确地表达过这种焦虑情绪:“五四运动以来个人主义的变态发达——对于一切的传统都要打倒,对于任何英雄都不佩服。他们相信的,崇拜的只有自己,在这一种空气之下,社会一切都陷于极端的紊乱。”25
国刚与慧英是陈铨笔下另外一种现代青年的艺术形象,他们也曾接受过五四启蒙的精神洗礼,却又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陈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真实意图,无疑是要为中国青年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榜样。国刚从小受父亲铁崖的思想影响,立志要做一名保家卫国的坚强战士,他既是父亲铁崖的思想继承者,也是陈铨本人复兴民族的情感负载者。国刚进入大学读书的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去报效祖国。国刚是一位非常理智的现代青年,从不盲目崇拜各种外来的思想言说,他认为只有一个繁荣昌盛的强大祖国,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故他大学一毕业,便报名参加了中国空军,随时准备去为国家民族征战沙场,同时他还劝告立群和翠心,不能只顾个人享乐而没有民族信仰,“我们青年人,处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应当把个人的问题,暂时摆在一边,努力准备着,来挽救整个的国家民族”26。慧英也是陈铨笔下的理想人物,她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宽容大度、仪容端庄,可以说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几乎都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铁崖和薛家一直都认为,立群与慧英是一对完美无瑕的绝世佳配;未曾想立群竟在自由恋爱的时代大潮中,鬼使神差地抛弃了慧英而选择了翠心。慧英为此感到十分痛苦,且萌生过一种厌世念头,然而为了自己所爱之人,她又甘愿去替立群背负骂名。一直默默爱着慧英的国刚,用他的爱与真诚感动了慧英,他们二人不仅最终结成了生活伴侣,同时还都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战士。陈铨笔下的两对青年,明显带有一种象征意义:立群与翠心象征着“歧途”,国刚与慧英象征着“正道”;只有摆脱个人主义的黑暗“歧途”,才能走上民族复兴的光明“正道”。这才是哲学家陈铨所要表达的“狂飙”哲学。
小说《狂飙》从第32节到第37节,是描写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作者以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诗性语言,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蛮横霸道的“狂飙”景象:
狂飙是无情的。它没有人道,没有正义,没有和平。谁和它讲人道、正义、和平,谁就要被它征服、蹂躏、消灭,它有庞大的力量,它力量的表现,就是生命的丧亡。
……
正是无情的世界,吹起了无情的狂飙。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畔,突然发出一阵的枪声。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仿佛感觉,震摇宇宙的狂飙,已经发动了。
……
狂飙发动,全世界都改变颜色了。天空、海底、陆上,到处都染遍了人类的鲜血。
狂飙左顾右盼,满怀得意。等到全世界变成焦土,它要唱壮丽的凯歌。27
陈铨用“狂飙”突袭来形容德意日法西斯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寓意深刻,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英、法、美等国,都试图以一种绥靖主义政策,去同法西斯主义进行妥协。中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世界更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所以德意日法西斯才会以摧枯拉朽之势,为全世界带来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巨大灾难。小说《狂飙》通过立群、翠心和德国人雷柏等人的观察视角,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在这场疯狂肆虐、惨无人道的“狂飙”突袭中,翠心目睹了中国人所遭受的屈辱和伤害,她终于意识到“这就是二十年来和平主义、个人主义,内战和懒惰,给我们的严重教训”28。所以她自愿放弃了离开南京的最后机会,坚持参加由外国人组织的难民救援工作,在被日军抓去以后为了不被侮辱,她用一把藏在身上的小刀自杀身亡。国刚则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殉国,慧英也为了保护伤员献出了生命。立群回到了无锡乡下,接替铁崖去领导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殊死血战。铁崖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立群说:“这一次大战结束,非战主义、国际和平的思想,又要抬头,但是战争是人类的,中华民族必须要时时刻刻准备战争,不要再上别人的当,提倡战争的民族,别人不敢欺负,也到可以免战,信仰和平的民族,旁的国家,一定要乘机而来,战争反而不可避免。”他“希望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成为战士。只有一群战士组织的国家,才是独立自由的国家”。29小说《狂飙》的故事结局,是立群与国刚的儿子兴儿的一段对话:
(兴儿)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立群)梦见什么?
(兴儿)梦见太阳从天上掉下来了!
(立群)是吗。
(兴儿)薛伯伯天明了没有?
(立群)天已经在明了,你看,东方已经起了一道曙光!30
无须多做解释,“东方”那“一道曙光”,既反映着陈铨对于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也反映着他期待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
陈铨发起“民族文学运动”与创作长篇小说《狂飙》,还有一个直接涉及抗战文学自身问题的重要因素,即从1940年开始,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战争初期文学的战斗热情退减了”,直接描写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减少。31为此施蛰存曾喟叹道,“如果把田间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抗战文学,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32。在抗战刚开始时,罗家伦就呼吁要用“充满了真理的伟大文艺”,去“唤起民族的觉醒”;33然而抗战文学的热情减退,不仅使苦难同胞失去了精神支撑,同时还使中国文坛弥漫着一层压抑气氛。恰恰正是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催生了“民族文学运动”和长篇小说《狂飙》;故这绝不是中国文坛上的一股逆流,而是一种充满着爱国主义正能量的文学现象。
注释:
1 13 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76、61页。
2 李怡:《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龃龉——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其历史命运》,《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3 5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张昌山编《战国策派文存》(下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9~712、718页。
4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试论》,《文化先锋》1942年第1卷第9期。
6 茅盾:《“时代错误”》,蔡仪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书系》(第二编 理论·论争 第一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
7 张子斋:《从尼采主义谈到英雄崇拜与优生学》,蔡仪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书系》(第二编 理论·论争 第一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93页。
8 汉夫:《“战国策”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群众》第7卷第1期,1942年1月。
9 胡绳:《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读书月报》第2卷第10期,1941年1月。
10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文化建设月刊社1936年版,第10页。
11 李长之:《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李长之文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2 《战国策·本刊启示(代发刊词)》,《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
14 幸郭:《读狂飙》,《民族文学》1943年第1卷第1期。
15 未生:《读〈狂飙〉》,《浙赣路讯》第4版,1948年11月11日。
16 袁昊的《〈狂飙〉与陈铨“民族文学”实践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4期)与陈思广、徐家盈的《作为哲学家的陈铨的长篇小说》(《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春之卷)都持这种观点。
17 陈铨:《编辑漫谈》,《民族文学》1943年第1卷第1期。
18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0 陈铨:《狂飙》,中正书局1942年版,第55、203、399~400、11、77、192、365、277、374~375、383、429、431~432页。
25 陈铨:《论英雄崇拜》,张昌山编:《战国策派文存》(上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31 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32 施蛰存:《文学之贫困》,蔡仪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书系》(第二编 理论·论争 第一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33 罗家伦:《“新民族”的前奏曲》,《新民族》周刊1938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