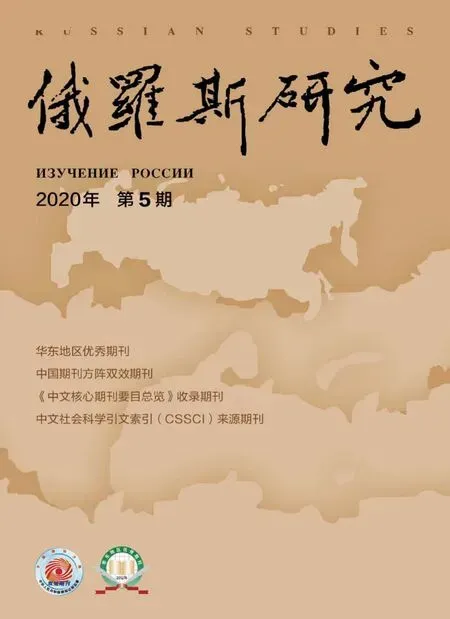拧紧螺栓: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
理查德·萨克瓦
拧紧螺栓: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
理查德·萨克瓦**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僵局已经形成,“螺栓”正在被拧紧,看不到可行的出路。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权力均衡以及相关的概念框架已不再稳固。世界秩序的危机加速上演,其特点是大国冲突再度出现和国际政治开始重回两极结构,其中的一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方是中国和与它相联合的国家。中国当然不赞成集团政治的理念,但是随着对抗升级,对该理念的拒斥可能会使中国付出失去盟友的代价。就像在“第一次冷战”中两极格局初始阶段所发生的那样,一些大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外交政策自主性,但是它们的行为越来越被中美对抗加剧所产生的权力场域所塑造。正如1914年之前“螺栓”被拧紧时那样,在当前的核时代,人类又面临着挑战,需要寻找一条摆脱大国对抗、避免战争的路径。
新冠疫情 国际体系 世界秩序 自由国际秩序 中美关系
2020年的新冠病毒危机令世界陷入停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它是一场“完美风暴”,同时包含一种致命而具高度传染性的病毒、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全球治理的削弱和国家内部分裂的加剧。[1]这不是一次无法预言且又后果严重的“黑天鹅”事件,而是一头“灰犀牛”——既可以被预见也得到了预言。21世纪已经多次发生此类事件——2002-2004年的SARS、2009-2010年的H1N1和2013-2016年的埃博拉病毒,但对难以避免的新传染病仍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2]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新冠病毒疫情是一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月11日宣布它是一场大流行病,并将这种新型疾病命名为Covid-19。该病毒的毁灭效应被它的特点放大,包括易感染、症状延迟表现、症状范围广(含无症状携带者)、致命性等。
这场危机成为一个关键时刻,加速了早已酝酿成熟的发展变化。并非所有的流行病事件都是这样的。1346-1353年欧洲黑死病(腺鼠疫)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是通往现代道路上的第一次大流行病。它使劳动力短缺,工人的议价权得到提升,因而加速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转移。那场瘟疫最早侵袭中国是在14世纪30年代,后来又在1353年伴随着欧洲的疫情再度来袭,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大范围社会紊乱。然而,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则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的,尽管它导致更多人死亡,人数高达1亿,但它的长期影响比战争要小。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基本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将暴露出我们各国社会的何种潜在真相?它将加速怎样的长期变化?尤其是,这场健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混乱,会对国际政治造成什么影响?结果会出现一种新的全球和区域权力均衡吗?
这场疫情暴发之际,国际体系内部不同世界秩序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一个危机点。正如瓦尔代俱乐部的两份报告所指出的,旧的秩序正在“崩塌”,而新秩序的面貌还远未清晰。[3]这场疫情再次表明,国内政治和国际事务是如何紧密地相互关联的。的确,它最直接和突出的影响之一,就是重新确认了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深了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已然显现的危机。本文认为,新冠危机进一步“拧紧螺栓”,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和国家内部的不满情绪。全世界并没有团结起来相互合作,以缓解疫情对健康的影响并减轻它的经济后果,与之相反,各国采取了“人人为己”()的应对方式。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G20这样的多边组织帮助协调共同应对之策,而与此不同的是,这一次国家利益似乎冲在了前面。只有民族国家拥有合法性、权威和能力来管控疫情所带来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影响。然而,由于这场危机具有全球特征,显然需要国际合作。世卫组织当然在发布健康警示和指导方面肩负起领导职责,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谴责该组织反应迟缓以及在疫情暴发初期没有质疑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将首先考察“正在崩塌的”国际体系的特点,重点分析术语的含义。该部分要考察这样一种正在增强的趋势,即随着两类世界模式之争的加剧,国际政治呈现出一种松散的两极特征。第二部分将概述疫情的起源、直接后果和一些相关的政治争论。第三部分将考察这个对抗性新时代下的大国政治。结尾部分将讨论“拧紧螺栓”的各个方面,关注疫情改变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螺栓”的比喻意在说明,紧张的情势正在酝酿,没有清晰的退出路径。而“第一次冷战”结束时,民间外交帮助改善了“敌人的形象”,为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超越对抗的逻辑铺设了道路。[4]
领导人的作为十分重要,里根、戈尔巴乔夫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之间的独特化学反应是终结“第一次冷战”的重要因素。[5]然而,当结构性因素出现矛盾时,想结束正在酝酿中的“第二次冷战”对抗局面,需要真正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创建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国际体系,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尽管它最终也在大国敌对的加剧中“崩塌”。这开启了为期三十年的战争、革命、经济危机和不确定性,直到1945年新的国际体系建立。“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是联合国及其组成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所组成的安全理事会。雅尔塔体系吸取了国际联盟和“二十年危机”的失败教训。[6]然而如我们所见,苏联阵营的崩溃和1989年以后的苏联解体对雅尔塔体系造成了巨大挑战,因为冷战两极体系中的构成元素之一宣称自身等同于整个国际体系。这就是它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以及最终与中国出现持续紧张关系的原因。正如1914年之前“螺栓”正在被拧紧时那样,在当前的核时代,人类又面临着挑战,需要寻找一条摆脱大国对抗、避免战争的路径。
一、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
疫情暴发的当下,权力均衡以及相关的概念框架已经不再稳固。世界秩序的危机加速上演,其特点是大国冲突再度出现和国际政治开始重回两极结构,其中的一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方是中国和与它相联合的国家。中国当然不赞成集团政治的理念,但是随着对抗升级,对该理念的拒斥可能会使中国付出失去盟友的代价。就像“第一次冷战”中两极格局的初始阶段所发生的那样,一些大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外交政策自主性,但它们的行为越来越被中美对抗加剧所产生的权力场域所塑造。
(一)若干定义
本部分将聚焦四个关键术语。其原因显而易见:当代学术分析和政治评论有太多是在缺乏准确性和混淆专有名词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本文无意故作面面俱到,或是进行独家阐释,但也的确认为,对研究计划进行概述能够帮助我们穿越文本的迷宫。本文提出的模型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如前所述,它提供了国际事务运行的统领框架。西方传统中有很多这样的体系。概略地说,现代时期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在1648年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主权国家组成,基于“教随国定”(eius regio, cuius religio)的原则,树立了国际行为的广泛原则,其遗产留存至今。这个国际体系的元素包含在维也纳公约以及雅尔塔协议之中。简言之,国际体系是国际事务运行的最顶层框架。
体系内部存在不同的秩序(orders),它的定义是体系内关于全球主义的具体模型。1989年以前,有两种秩序脱颖而出,一种是苏联秩序,另一种是基于大西洋联盟(冷战期间形成的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世界)的秩序。1989年以后,大西洋体系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并宣称是普世的,同时支持一种特定类型的全球化。2014年被视为转折的象征时刻。由于乌克兰危机所造成的关系破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俄罗斯和中国所组成的反霸权联盟的挑战,还有对该联盟忠诚度不一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主要在“后西方”机构中进行抱团,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联合组织)。[7]
第三个元素是由英国学派的思想家们定义的,即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英国学派区分了国际社会的各种“基本制度”,包括主权、领土、权力均衡、战争、国际法、外交和民族主义,并且阐述了这些诞生于欧洲的元素是如何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的。[8]而所谓的“次级制度”包括联合国及其机构体系,如世卫组织和其他很多组织。英国学派又进一步区分了多元主义体系和团结主义(或译为:社会连带主义)体系。为数众多的多边组织力求在多元的国际体系中推动团结的实践。[9]在这个方案里,国际社会塑造了国际事务的运行。它有效地充当了润滑剂,使轮毂在第四个范畴内实现运转,即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个范畴总体上涵盖了世界主要国家与别国互动和参与国际事务的短期情境反应。这四个元素共同创立了做出决策、制定战略和界定国家利益所依循的框架。
(二)今天的国际体系
要理解现如今国际政治的运行,就要理解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的特点,以及它在近些年里演变的方式。雅尔塔国际体系可以理解为三个层级(或者一栋建筑物的三个楼层),它们相互之间有多条连接线,而不必全部经由中间一层。[10]这个三重体系的顶层是全球治理的多边制度(英国学派称之为“次级制度”),主要是联合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还有各种联合国的组成机构(特别是当前语境中的世卫组织)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再加上国际法律、环境和其他一些经济治理机构。强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这些多边机构对国际政治的运行几乎起不到任何影响,但他正确地指出,美国这样的大国对多边主义给其行动自由施加的限制感到恼火。[11]处在顶层的还有各种自由主义贸易协定,以及1989年后被称为“全球化”的全球商业和服务的基础设施。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关于全球长供应链和相互依存经济体的40年周期问题。换句话说,目前对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批评愈演愈烈。去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投资和就业回流、供应链缩短,以及国家支持工业战略的重新出现(尤其聚焦于事关卫生安全的领域,如药物、扫描仪和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制造)。
处在模型中层的是相互竞争的国家以及伴随它们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s),比如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捍卫主权国际主义的中俄等国。这催生了一个所谓的“多秩序世界”。[12]也有人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多元复合”特征。[13]大国之间的关系包含着推行各自霸权的图谋,其表现形式是彼此竞争的世界秩序议程。换言之,与政治和军事对抗同时存在的,是对如何阐释世界秩序的认识论斗争。1989年后的大西洋权力体系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随着两极格局和其他平衡力量的终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便可宣称等同于秩序本身而没有阻碍。这意味着,处在国际体系顶层的制度实际上被宣布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附属物。一个具体的秩序整个替代了体系。关于这种论调合法性的斗争构成了当今时代大国冲突的基础。这就是名词解释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亨利·基辛格在他关于世界秩序的权威研究著作中忽略了两个概念——体系和秩序——的差异,造成了学术上的混淆和政治上的失调。[14]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便可以看到,秩序之间可以发生冲突,但最终它们都能保卫发生这种冲突的国际体系。
这种认识论斗争发生在模型底层,在这里市民社会团体、智库、政策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试图塑造政治的文化图景。其中有那些试图在全球议程中推动应对气候灾难的团体,也有为种族和历史正义而抗争的运动。这里也滋生了草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跨国公司在这里展开竞争,一些“新寡头”也寻求塑造国际事务。身为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领导者的乔治·索罗斯,长期以来是这方面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激怒了匈牙利和俄罗斯等国,被指控为干预内政,也惹恼了美国,挑战了美国的某些政策。疫情也使主要的医疗卫生和流行病机构走到台前,特别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引发了无休止的阴谋论。
总而言之,国际体系可以被视为硬件,而相互竞争的世界秩序模型是软件操作系统。自1945年以来,没有哪一种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那样强大和有影响,它在美国的支持下创立,获得了某种普世的身份,最终因为模糊了体系和秩序的分野而危及自身的存续。这就好比一款软件程序试图获得它所运行于其中的系统的特征,模糊了基本的区别,从而同时威胁到两者的存在。
(三)大替代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早期的自由主义秩序起源于威尔逊国际主义和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1945-1989年冷战期间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承了这些传统,并且初期是相对温和的。它的基础是保护各国领土完整的《联合国宪章》(尽管也拥护反殖民的民族自决)、多边制度和开放市场。甚至苏联实际上也能接受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反对该秩序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这个阶段的后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偏离了布雷顿森林时代受管制的资本市场,朝着商品和服务的金融化方向发展,伴随着出现的是被归结为“四个自由”(劳动力、资本、商品和服务)和更加开放的市场。与此同时,各国若非出于自卫,被禁止使用武力。
在1989年冷战结束后的第二阶段,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硕果仅存的具有真正普世性抱负的秩序,其野心勃勃的特点变得更加突出,包括激进版的全球化、民主推广和政体更迭。使用武力的禁令(联合国制裁除外)被削弱,这在1999年轰炸南联盟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中得到证实。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保护的责任”(R2P),代表着对主权国际主义的偏离,确认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合理性。[15]批评观点认为,这个自由霸权的激进版本“注定会失败”,因为它的野心铺得太大,到了可以被归为妄想的程度,最终将激起内外反抗。[16]实际情况并不是威权主义挑战者削弱了秩序,而是秩序的内部矛盾引发了衰落。最重要的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乌托邦主义遮蔽了判断力、外交和实用主义(即英国学派所定义的国际政治“基本制度”)。激进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它与外部力量和内部替代者之间的关系中,设置了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17]虽然该秩序号称多元主义是其基本价值,但是价值体系的刻板僵化意味着它对内部不包容,对外部具有攻击性。[18]而且它在确保内部发展方面缺乏建树,因为工作机会外包给了海外,而内部存在着剥削机制。
第三阶段始于自由主义秩序如日中天之时,但其权力地位开始面临挑战。[19]中国和俄罗斯制约着自由主义秩序想要取代国际体系的图谋,捍卫国际体系的独立自主。这意味着捍卫国际法而不是“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如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Lavrov)反复指出的,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不能等同于国际法的严格应用;在我们的时代,国际法的行使权力属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20]美国也开始背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朗普总统拒绝接受它的一些基本假设。特朗普质疑北约的效能和它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中心地位,这种质疑态度已经在“责任分摊”的争论和奥巴马的“转向亚太”战略中得到了预示,但是特朗普的言论将批评带上了一个全新的层次。特朗普的交易型和重商主义方式以及对多边主义的拒斥,是对1945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所依据原则的背弃。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所代表的,不是回归位居雅尔塔体系基础地位的主权国际主义,而是退回某种更加发自自我的、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东西,让人联想起1914年之前的大国竞争和帝国主义。
不出意外,特朗普向民族主义和“美国优先”的转变,激发了自由国际主义和大西洋权力秩序保卫者的强烈反应。这完全符合“被动反应”的字面含义,期望回到一种已然落后于时代的状态。特朗普的政治“天才”是在一个衰败的秩序中投石问路,致力于赢得主要选民的忠诚。悲剧之处在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第三阶段的发展越来越被认为是退回到右翼立场——朝着民族主义、大国冲突、贸易战和社会非自由主义的方向。美国的民粹主义明确了其关切的问题,但是“来自左翼”的应对措施是不成熟和令人困惑的。
(四)今天的国际政治
新冠疫情暴露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结构性弱点:首要的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矛盾,以及主要成员长期以来过度发展军事力量,使其社会、治理和基础设施走向衰败。冷战结束时,美国并没有变成“一个正常时代的正常国家”,而是与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的建议相反,仍继续试图改变世界。[21]因此矛盾越积越深,并将在局势紧张时爆发出来。
1978年以后,中国利用美国管理下的全球化之便,实现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转型。然而,中国的政治系统仍然保留了主权。尽管有段时期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准备容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试图替代整个体系的主张,但是清算的那一天总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届时中国方面将会捍卫国际体系的独立自主,具体形式是维护联合国的独立地位和全球化进程的公平正义。[22]俄罗斯对此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认为这种替代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霸权主张的一部分。俄罗斯支持处在模型顶层的多边组织,但是抵制它们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滥用。因此,俄罗斯要捍卫的是国际治理制度的自主地位。这便是俄罗斯和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世界关系疏远的根本结构性原因。随着北约逼近俄罗斯边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军事力量扩张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疏离。大西洋国家有充分的理由辩称无意将俄罗斯持续排除在外,但是其中仍然“没有俄罗斯的位置”。[23]
加入大西洋权力秩序意味着莫斯科接受华盛顿的霸权,俄罗斯有一批人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此一来,俄罗斯将可能变得像法国或者英国那样,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联合事业的一分子。考虑到历史因素,这绝不会成为中国的选项,尽管其领导人一直在寻求推迟对抗时刻的到来。这样的时刻显然正在来到,奥巴马的“转向亚太”战略就已包含明确的“新遏制”信息。在2011年10月关于该问题的重要演讲中,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中国崛起定义为一个正在出现的威胁,并描绘了一种全面的战略应对,包括巩固传统安全联盟、拓展贸易投资和多边伙伴关系、在新的竞技场上扩大军事存在,以及推动民主和人权事业。[24]这个议程在特朗普时代被新增加的“贸易战”所强化,在疫情期间对抗变得更加剧烈。
俄罗斯的立场有时被认为是对雅尔塔体系的一种保守捍卫。该体系孕育了联合国,并且赋予俄罗斯在安理会中的特权地位。然而,莫斯科的关切并不在于重建雅尔塔模式,而是范围更窄的议程,即捍卫雅尔塔-波茨坦体系所代表的国际主义模型。俄罗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双重标准的指责是由于此种秩序的霸权主张,如,随意界定国际法如何以及何时适用。矛盾的是,随着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于过度全球化(包括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流向别国)的反应日渐强烈,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也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国际主义的捍卫者对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非常警觉,因为这股力量在倒掉全球化洗澡水的时候,可能会把自由主义霸权的孩子给一起倒掉。
二、疫情政治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新冠疫情加速了已经出现的趋势,加剧了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在体系层面,危机重新激发了国家的角色。在此之前,全球化表明某些经济规则超越了国家政策。然而,当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时,动起来的是国家。这些问题可能是全球范围的,但是国家的应对至关重要。国家福利和医疗补贴的重要性得到提升,而自从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及2011年欧元区危机以来,多年的紧缩政策已经使其在欧洲不少国家降到了危险状态。应对疫情的效力成了衡量政府是否称职的新工具,美国的表现不仅糟糕,而且是“相当糟糕”;相反,中国的影响力被其及时分享新型病毒基因结构和抑制病毒扩散的坚决行动所提升。在德国,高效的中央政策、强健的联邦和地区治理、合理的医疗和福利投资以及高度的社会信任缓解了危机。疫情挑战了美国例外论的叙事,危机充当了“历史的加速器,加快了美国和欧洲影响力的衰落”。[25]
这场危机加速了40年的社会生活周期走向终点,即新自由主义否定国家行动主义的时代。这种迹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已经表露无遗,但最后银行业得到救助,生活又恢复了正常。主权国家的优先地位被再次确认,但同时多边机构和问题共担的重要作用也再次得到彰显。全球金融危机见证了领导权从G7转移至G20,前者由意识形态接近的民主国家组成,而后者是更多样化的国家组合。G7在1975年成立,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论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的缺失,导致1999年出现创立G20以加强全球金融架构的倡议。正如一项研究指出,“G20有两个起源:一是确信全球性危机要求全球化、包容性的解决方案,二是认为需要成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开展非正式对话的常设论坛。”[26]G20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2008年举行首次领导人峰会,今天它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协调的主要论坛。
然而,这种多边主义遭到了新冠危机的挑战。大国没有吸取过去流行病和全球卫生危机的教训。与之相反,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削弱了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诉诸范围逐渐扩大的制裁行动和贸易战。随着美国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贬低,其长久以来关于全球治理机构的模糊态度被推上了新的水平。危机严重之际,美国甚至取消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然后在2020年7月7日提前一年发出了退出该组织的正式意向通知,这将使该组织的预算减少几乎四分之一。美国指控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疫情不力并充当中国的“傀儡”。作为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Ghebreyesus)表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在全球和国家层面上缺乏领导和团结。我们不能靠一个分裂的世界来击败这场疫情。病毒因为世界分裂而扩散蔓延,但是当我们团结起来,它就会落败。”[27]
特朗普更喜欢双边而非多边解决方案,导致G20被边缘化。该组织没有能力重拾它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所扮演的协调角色。更广泛地说,新冠肺炎加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衰退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碎片化”,正如格伦·迪森(Glenn Diesen)的观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只有在霸权之下才会出现。”[28]然而,我们可以认为,各项国际制度的集体霸权以及欧盟等区域组织的支持,原本能够维系自由主义贸易体制。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破坏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来达到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目的,这样做实属有意为之。由于新的斗争是在威权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展开的,这再次为霸权对抗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29]
一些负面后果,在疫情暴发初期就已经显现出来,包括国家利己主义增强、国际层面冲突尖锐化,以及展开了围绕收回海外投资和生产的斗争。在欧盟,废除内部边境的《申根协定》签署25周年之际,区域内几乎所有的人员流动都被禁止。随着土耳其开放与希腊的边境,移民危机在2020年初卷土重来,而为求应对,“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的元素重新恢复。已然显现的去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同时,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某些普遍主义元素遭到否定。伴随其出现的是反民主、孤立主义以及强人威权主义。也有一些积极趋势:欧盟在2020年4月4日举办筹款会议,以获得疫苗研发和推广所需的资金,后来又建立大规模团结基金,帮助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在很多国家,政见对立的政党相互合作,为公共卫生提供了跨党派支持。[30]
三、新对抗时代的大国政治
新冠疫情凸显了多边合作、加强国际组织以应对其后果的需要,但是实际趋势似乎是国际政治的“再国家化”。疫情是对合作的严重挑战,而大多数多边机构没能从容应对。[31]与此同时,虽然存在主要以欧盟为中心的合作倡议,但危机仍进一步加剧,深化了目前的紧张局势。在中美相互对抗的作用下,新的全球两极格局态势更为突出,其他国家被迫选边站队。这就是为什么二战的比喻被重新拿来形容眼下的冲突。同时出现的还有代理人战争和激烈的宣传攻势,它在今天的口号是对“假新闻”和不实信息的斗争,此外还有各种形式被网络强化的信息战。
奥巴马时期的白宫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将美国外交政策界形容为“变形怪体”(the Blob)。这个群体主要分布在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对美国霸权的明显衰落感到忧心忡忡:“它的突出特点是没有意愿或能力去重新思考或重新排序二战后所界定的、但在冷战结束以后基本上处于无人驾驶状态的美国国家利益。”[32]迈克尔·格伦农(Michael Glennon)认为,1945年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下,美国国家结构的变化造就了一个“深层国家”(deep state)。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美国受到“杜鲁门式”实体的掌控:这是被冷战催生并发展起来的复杂的国家安全架构及相关的企业群体。[33]宪法的约束失去效力,因为国家安全问题有其内在复杂性,而且两党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权”有着牢固的思想共识(在特朗普时代被重新定义为“伟大”)。[34]根本的悖论是,“曾经受到美国自由派质疑的深层国家,在特朗普时代变成了被追求的目标。”[35]
这个因素能够解释中美两国在对抗中所实施战略的错配。中国保留了话语武器,而美国用上了冷战中练就的所有手段,包括巩固盟友集团并惩罚与对手联合的国家。特朗普上台时自信能将莫斯科带到华盛顿一边来,尽管他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促成这种转变。不管怎么说,中俄的联合是深度结构性的,上文关于国际体系的讨论指出了这一点,而只有国际体系遭受重创才能迫使其(中俄联合)发生改变。这就是关于美国需要将俄罗斯“从冰冷关系中带出”以平衡中国的言论,不太可能持续下去的原因。[36]
德米特里·西梅斯(DmitrySimes)强调,“要重构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必然要认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西洋两岸全球精英的战斗号角——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幻想和双重标准的。”他认为,自从古希腊创立政治共同体,关于民主和威权孰优孰劣的争论便一直存在,“以及什么样的两相结合对特定环境下的特定社会最为合适。”他回应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认为将“民主推广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目标之一,注定会造成激烈的国际反弹。它使得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利益,并迫使美国和欧洲对其同盟国家的不当行为进行洗白,只因为它们宣誓忠于大西洋霸权。”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政策影响。同样地,美国的同盟体系,尤其是北约,“其目前的形态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包括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内的很多评论者警告称,北约扩张会使俄罗斯变成一个危险的对手,而这最终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如此,“这些盟友还将美国卷入了欧洲国家的内讧之中。”[37]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他们给出的方案是,美国要做亚洲和欧洲的“离岸平衡者”[38],而不被卷入其中。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拒绝自由秩序中的普遍主义,排斥“人道主义”干预和政权更迭,此举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更加关注国内发展需要的基础性再平衡。然而,同时出现的是长期冲突愈演愈烈。这尤其涉及与中国的关系。2018年底打响的贸易战在2020年初以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而暂告解决。然而,由于美国受到大面积暴发的疫情牵累,死亡率居高不下,特朗普最初对美国面临病毒威胁的漠然态度逐渐反噬自身。危机放大并暴露了特朗普执政风格的缺陷,以及美国医疗卫生和危机管理体系的失灵。于是特朗普把关注点投向中国,不仅指责中国早期没有控制住武汉的疫情,后来又针对危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索取赔偿。其他国家也在新的两极格局中寻找位置,澳大利亚是其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而英国著名的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发动议会和社会对抗其所认定的中国威胁。该机构强调军事多边主义优先于经济全球化,它的一份报告指出,“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成员共有831个门类的进口商品依赖中国,其中有260项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39]
即便在此之前,俄罗斯就已经是制裁加码的对象,新近一次制裁针对的是2019年12月穿越波罗的海通往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的完工。尽管特朗普在2016年声称有理由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但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指控阻碍了双方关系的转圜。特朗普对普京的善意言辞或许是出于对他权力的勉强敬意,但最重要的是离间中俄关系的战略目标。中俄联合自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在2014年以后、“第二次冷战”爆发以来大幅提速。特朗普不可能实现逆向的基辛格式外交运筹,争取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加入美国一方。与2016年对待北约如出一辙,特朗普在2020年5月宣布G7是不合时宜的——“它是一个非常过时的国家团体”。[40]特朗普企图在2020年晚些时候将在华盛顿举行的G7会议范围扩大至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搭建反华联盟。但就连G7原定在9月举行的定期会晤也因为安吉拉·默克尔本人拒绝参加而推迟。她以健康原因拒绝参会,但是这样一次会议意在证明危机已经远去,商业活动能够恢复正常,提升特朗普在11月大选中再次当选的概率。特朗普未经协商便宣布将驻扎在德国的9500名美军士兵重新部署到波兰,此举被认为是对默克尔拒不出席G7峰会的报复行动,但也符合特朗普长期以来对德国的谴责,即德国没有达到北约国家军费开支占GDP2%的目标。
疫情只是确认了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和缺陷,以及俄罗斯和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世界关系中根深蒂固的僵局属性。尽管有要求解除制裁的呼声,军事演习也一度暂停,但是疫情的共同挑战并没有使欧洲或美国解除制裁,军事演习也恢复进行。随着俄罗斯身陷三重危机的困扰——新冠疫情、油价崩溃和长期经济停滞——中俄联合进一步加深。中国开始“在未来时期实施分层级的防御”,把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作为战略核心,而俄罗斯也只能从中国方面寻求缓解压力。这全然意味着“世界分裂为相对的两极”。然而,季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Bordachev)指出,“新两极格局”与主导1945-1990年的两极格局相比,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新两极格局”叠加在经济相互依存之上,这不同于冷战时期处在两极的国家基本上是在两个世界的情况。旧两极格局的主要擂台是在战略军备领域,但它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逐渐得到管控。今天的中国缺少(苏联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对外依存的程度要高得多,这容易造成关系紧张,能够导致某一方以一种强力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41]
在双边关系方面,很少有迹象显示疫情使国家间关系变得更为紧密。美国妄称病毒是从武汉一所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并且被中国政府掩盖,这种言论毒化了中美关系。对罪责方的追溯使疫情变得政治化。[42]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尤其是涉及2020年7月1日在香港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美国对华为公司开战,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参与其5G网络建设,并用强力手段达到此目的。英国政府也在2020年7月萧规曹随,承认这更多是地缘政治而不是安全问题。[43]美国甚至计划对9200万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实施旅行禁令。美方的总体基调反映在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贬低中国政策的长篇大论中。他指称中国搞“经济闪电战——这是一场侵略性的、精心谋划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战役,以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超越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44]就连西方的一些左翼人士也加入了批评中国的阵营,再次混淆了国际体系和特殊国家体制的区别。[45]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巩固中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4月29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允许国家福利基金(National Welfare Fund)投资人民币和中国国债。危机加速了中俄在交往中去美元化的相互行动,作为两国摆脱美国制裁和美国领土范围以外其他形式压力的更大策略的组成部分。中俄两国重新启动了第二条天然气管线的谈判,甚至计划修建一条连通北极港口和印度洋的铁路。更及时的是,中国在油价暴跌、生产商打算抛售过剩产量之际向俄罗斯施以援手。2020年3月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同比增长三分之一,给受到欧洲经济衰退、需求滑坡打击的俄罗斯企业抛下了救生圈。新冠疫情同时向莫斯科和北京显示了在共同挑战面前结成统一阵线的战略意义。这可能会导致投资和生产真正实现向欧亚地区转移,关于这种前景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实施起来犹豫不决。[46]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稳步深化,双方建立了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在某些方面向准同盟关系发展。[47]尽管俄罗斯在经济上大不如前,但它仍然是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大国。总之,两国对国际体系有相同的看法,在涉及他国内政问题上强调主权国际主义和不干涉。两国都自认为是美国霸权野心的受害者,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取代国际治理制度独立自主地位的受害者,都厌恶被置于从属地位。当然,有人担心俄罗斯最终会是中美冷战加剧的输家,在这场斗争中沦为北京的次要伙伴,但俄罗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地位使其在两国关系中获得了重要筹码。在这对关系中无疑存在“结构性的不确定因素”,但从目前来看,“面对与美国的加剧对抗,中国将更加需要俄罗斯——其仅有的大国朋友。而对于俄罗斯,除非中国有意愿持续购买其能源和其他商品,否则它的经济难以恢复。”[48]
尽管如此,危机被证明是深化中俄关系的压力测试。随着疫情暴发蔓延至全球,俄罗斯在2020年1月31日关闭了与中国的边境。此后,随着中国公民陆续回国,俄罗斯成了中国感染人数增加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于是关闭了与俄远东地区的边境,使得很多中国公民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周围地区。[49]这些行为并非民族主义的表露,而是在诸多未知因素的情况下试图控制危险传染病的威胁。有评论将这些举动解读为中俄关系恶化的标志,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推迟关闭它与欧洲的边境。事实上,中国的愤怒是冲着美国和它的一些西方盟友来的,它们把中国当作“自己国家新冠病毒灾难”的替罪羊。[50]中国被指利用危机牟取政治利益,方法是向欧洲国家输送检测设备和个人防护服。事实上,中国的应对办法为实施严格而有效的抗疫措施树立了榜样,被亚洲的其他地区效仿和发扬。[51]中国现在同俄罗斯一道受到西方的贬斥,原因还包括它们成了“主动散播虚假信息威胁”的一个源头。[52]
随着一些国家开始着手缩短供应链并从中国撤回基本医药和其他物资生产线,以及日本在2020年4月向撤回在华生产线的企业提供资金奖励,俄罗斯成了与中国坚定站在一起的少数国家之一。拉夫罗夫表示,要求中国进行赔偿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震惊的”。2020年4月16日与习近平通话时,普京称赞中国政府采取了“持续有效的行动”,表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俄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特殊性质”。[53]
四、拧紧螺栓
国际事务中有因为疫情而导致的显著变化吗?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一些深刻的变化以更加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新冠病毒加快推动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转变,同时凸显了国家的作用。[54]然而,国际事务中的“不变”(固定性)胜过了变化进程。在国际事务更大的结构性转移方面,并没有迹象显示新冠危机导致了任何体系转型,反而是一些已然显现的趋势加快发展。疫情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但它加速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并且已经实现独一无二的成功的国内治理架构——能否经受住疫情的考验?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战争、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应对不力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化危险都表明,重新思考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优先事项势在必行。但与此相反,奥巴马的总统任期恢复了“一种正常状态的假象”,根本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特朗普在2016年被选上了台。疫情暴露出依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挥霍数十亿美元追求“永久战争”的方式,并没有使美国变得更安全。将更多资源用于民众医疗健康、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或许是更为明智的投资。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所长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认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昂贵的军事力量与二战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致命的国家安全威胁,并不紧密相关。”疫情既是一个诅咒,更是美国人理解自己“并非上帝特使”的机会。[55]卡耐基基金会主席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则针对“削减开支”发出了警告,同时反对任何简单恢复美国国际政治旧模式的做法。相反,他呼吁“重新创造”,“找到我们的抱负和局限之间的平衡”,同时利用好多边主义工具以迎接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管控与中国的竞争。[56]但伯恩斯的文章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新思维”和“新创造”的迹象。
疫情暴露出美国不仅在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方面有巨大缺陷,其治理体系也存在很多短板。有印度评论人士将此解读为“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加速衰落”的证据,使美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全球竞技场主导权”的行为变得更加危险和不确定。在此背景下,“中俄在与美国加剧对抗中相互站台和支持,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所有迹象都表明,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形势中,美国的帝国主义将更为暴力、更具压迫性。”[57]就某些方面而言,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变成了一个“流氓国家”,不仅质疑它的传统盟友,也挑战它在1945年后参与创建的这套国际体系的基础。
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早先曾经对美国面对中国挑战的过度反应表示担忧,但语气更为谨慎。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崛起时曾出现过类似的反应,但最终被证明是夸大其词。日本是美国盟友体系的一部分,而中国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他指出美国在苏联这个例子中过度反应的结果,引发了麦卡锡时代的国内混乱、越南战争,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军事干预行动”。他也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从不只有接触这一项,其“对冲战略”是多种形式的遏制和威慑,包括持续对台军售,长期并且加大在亚洲地区驻军,与越南和其他中国潜在的对手保持密切关系等。他还指出,尽管中国没有变成一个自由民主政体,但仍然是一个极负责任的国家,尤其是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提升经济治理,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扎卡利亚质疑美国五角大楼对中国“战略竞争者”的定义,指出两国之间存在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他呼吁华盛顿方面“保持冷静”,维持接触和威慑的战略耐心。[58]他的观点很重要,但这场疫情只是加剧了他所警告特别需要避免的方面。
至于美俄关系,新一轮“重启”的迹象寥寥无几。两国关系经历了长期恶化,期间有几次因出现其他危机而重启关系的机会,“9·11”事件就是如此。在特朗普这位喜欢大国交易和私人关系的交易型总统治下,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美俄关系再次启动的机遇。2020年春天,普京和特朗普的电话交流,比特朗普上任后至此时的全部时期都更为频密。双方在3月30日的通话为签署削减石油产量的OPEC+协议扫清了障碍,稳定了剧烈下跌的油价——这是由2016年12月的协议崩溃、需求大幅缩减和供应显著过剩引起的下跌。普京在这次通话中建议向美国提供医疗设备,特朗普则表示感谢并予以接受。然而,特朗普与俄罗斯达成“重大谈判”的腾挪空间极其有限。不仅国会的民主党人会断然拒绝任何妥协,共和党的很大一部分成员也并不赞同特朗普的观点,即俄罗斯在与中国的斗争中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制裁机制现在被国会法案锁定,特朗普被迫签署生效,制裁的对象不仅包括俄罗斯企业和个人,也包括购买俄罗斯军事设备或者帮助修建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的第三方。
鉴于俄罗斯正遭受自普京2000年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多重危机挫折,“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中大国竞争的支持者认为,当新冠病毒、石油和经济危机余波使俄罗斯真的有可能从近似对等的竞争者下降为非对等的竞争者时,美国向莫斯科抛下救生圈的做法是荒谬可笑的。”[59]特朗普的选项非常有限,而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提名候选人乔·拜登则发誓要“让俄罗斯为违反国际规范付出真正的代价,并且与俄罗斯的公民社会站在一起,它一次次勇敢地反抗普京腐败的威权主义系统”。[60]普京在乌克兰、叙利亚或者其他诸如北约东扩等引起纷争的政策问题上都没有退路,否则会丢掉海外威望和尊严,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俄罗斯的麻烦缠身当然会鼓动“普京注定失败”这类思维,但是尽管他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挑战,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危机是长期的。针对2020年3月俄罗斯议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使普京能够在2024年现有任期结束后再执政两届任期——的全国公投,从4月22日推迟到了6月25日至7月1日,并高票获得通过。根据官方数字,78.58%的大多数表示支持,投票率为68%。
第二个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新冠病毒是对国际和国内治理的一个重大冲击,但是为什么国际政治仍处于停滞状态?随着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针对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市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事件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变成了一个全球现象,关于奴隶制的记忆、历史、悔恨和补偿问题愈演愈烈,也提出了长期存在的不公正问题。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但是通过把争论的场域转移至身份认同甚至“文化战争”,使得一些基础的、结构性的问题被掩盖了起来。反战运动中的有些人把特朗普当成“一个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策略性盟友”,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想要在国内发动战争”。[61]美国国内争取正义的斗争,的确可能改变对外政策的方向,但是短期内,对国内混乱的关注只是强化了国际事务的僵局。国际关系中的纠葛太深,而来自各方的替代性制度、理念或政策选择的缺失,也意味着僵局会持续存在下去。
特朗普是作为强力搅局者上台的,他践行了减少美国参与多边主义架构的承诺。然而,至于主动作为的议程,包括与俄罗斯“交好”,他显然没有取得成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选项受到“通俄门”的牵扯,而最大的制约还是来自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特朗普认为“杜鲁门式”的多边主义国家安全体系是僵化保守、不合时宜的,尤其是北约,并对其发起了挑战,这似乎恰好确认了军事情报共同体的担忧。但是仅靠新冠疫情削弱不了杜鲁门式国家的力量,或是改变其意识形态捍卫者的观点,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比拼谁的立场更为激进。[62]他们一起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挑动了一场比之前一次更复杂的“新冷战”,全球化时代培育形成的供应链相互依存的复合进程被大肆拆解。“第二次冷战”将是一场全领域的冲突,两个实力相近的竞争者争夺领先地位,而如何应对这样一场冲突,几乎没有规则可循。
五、结语
僵局已经形成,“螺栓”正在被拧紧,看不到可行的出路。自由国际主义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搅乱,不能提供一条逃离僵局的通道;对于混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第三阶段的替代方案,其轮廓还不够清晰。俄罗斯和中国捍卫主权国际主义的模型,守护多边主义,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两极格局轮廓正在形成。民族主义的幽灵再次被释放,只有战后的多边主义架构能对其加以约束。
特朗普是一个强力搅局者,而对疫情的管控暴露了他的领导不力。他也对美国的多边主义承诺提出了质疑。如果对冷战模式(集团对抗)进行反思,那么特朗普这样做是受到俄罗斯和国际和平运动欢迎的。然而,如果考虑到二战后发展形成的全球(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主义,那么特朗普的搅局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欧盟对美国肆意行为的制约能力不足,当然它有能力缓解部分消极影响,主要方法是通过投资来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在经历了蹒跚起步后,欧盟的确投资了一些新的团结机制,与遭受疫情重创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成员国加强了联系。尽管如此,疫情还是加剧了各种政治摩擦,右翼民族主义者利用危机推动其议程,有时候这是在保卫公民自由、对抗封锁限制的荒谬伪装下进行的。[63]
危机深化了中俄的联合。无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预计华盛顿方面还会持续搅局,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中俄会建立正式同盟关系。俄罗斯一如既往地准备与任何打算回归正常外交接触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但是冷战结构的制度和思维惯性意味着,就连新冠疫情这样的严重危机也难以改变已经根深蒂固的模式。
这场危机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场考验。国家的能力和胜任力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检验,重新激活了国家能动主义和社会福利。疫情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政体的特性——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威权主义——并不是衡量有效治理的主要方式,统治精英的决策和治理结构的质量才是关键。在全球治理层面,G7被再次证明范围过窄,不能对管控危机起到多大作用,而G20也不能担负起它自2008年秋天金融崩溃以来一直扮演的领导角色。疫情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和全球事务中的干扰因素增多,多边制度的弱点凸显。危机加速推动在国际事务中出现一个不断扩散但可能持久存在的两极秩序。随着发展与合作的努力遭遇消极后果,“第二次冷战”爆发的压力正在积聚,全面冲突的危险再次浮现。
(翻译 丁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The coronavirus crisis of 2020 brought the world to a halt, with the screws tightening yet without any clear exit route. The pandemic struck at a time whe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associated ideational frameworks were already in flux. The intensifying crisis of world order was marked by the re-emerg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a nascent return to a bipolar structur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the US and its allies on the one side, and China and those who align with it on the other. China, of course, repudiates the idea of bloc politics, but this conceptual rejection may cost it allies as the confrontation intensifies. As in the original period of the bipolarity in the First Cold War, certain major powers (India, Russia and some others) retain a degree of foreign policy autonomy, but their behavior is increasingly structured by the power field generated by the intensifying Sino-U.S. confrontation. Just as before 1914 the screws are tightening, but in the nuclear age humanity is challenged to find an exit path from great power confrontation that can avoid war.
the Covid-19 Crisis,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World Order,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Sino-U.S.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вызванный пандемией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уж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винты» закручиваются, и выхода из этого тупика не видно. В нынешней эпи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баланс сил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рамки больше не стабильны. Кризис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усиливается. 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м конфликтов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 биполяр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в которой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ША и их союзники, а другой — Китай и страны, к нему приближённые. Китай, конечно, не одобряет идею групп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о по мере обострени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отказ от этой идеи может стоить Китаю потери союзников.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биполярной модели в «перв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некоторые великие державы(Индия, Россия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сохранили определённую степень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однако их поведение всё больше определялось силовым полем, созданным усилением китайск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Так же, как когда «винт» был закручен до 1914 года, в нынешнюю ядерную эпоху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снова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йти способ избежать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избежать войн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либераль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Dmitri K. Simes, “The Perfect Storm”,, 24 April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erfect-storm-147791?page=0%2C2
[2]Michael T. Osterholm, Mark Olshaker, “Chronicle of a Pandemic Foretold”,, July-August 2020, Vol.99, No.4, pp.10-24.
[3]Oleg Barabanov, Timofei Bordachev et al.,, Moscow,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 October 2018; Oleg Barabanov, Timofei Bordachev et al.,, Moscow,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 May 2020.
[4]David S. Foglesong, “How to End a Cold War”,, 2020,Vol.4, No.1, pp.49-59.
[5]Archie Brow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6]E.H. Carr,, Reissu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material by Michael Cox, London, Palgrave, 2001[1939].
[7]Oliver Stuenkel,, London and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Oliver Stuenkel,, Cambridge, Polity, 2016.
[8]Hedley Bull, Adam Wat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9]Barry Buzan,, Cambridge, Polity, 2014, pp.32-36.
[10]这个三重模型是对以下作品中所提出模型的修改版:Richard Sakw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该书俄文版:РичардСаква. Россия против остальных. Кризис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20.
[11]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94/1995,Vol.19, No.3, pp.5-49; John Mearsheimer,,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1.
[12]Trine Flockhart, “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 2016,Vol.37, No.1, pp.3-30.
[13]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8 September 2017, https://www.ethicsandinternationalaffairs.org/2017/multiplex-world-order/
[14]Henry Kissinger,, London, Allen Lane, 2014.
[15]Philip Cunliff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16]John Mearsheimer,, Lond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John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2019, Vol.43, No.4, pp.7-50.
[17]Philip Cunliffe,,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18]Anatol Lieven, John Hulsman,, New York, Pantheon, 2006.
[19]Milan Babic, “Let’s Talk about the Interregnum: Gramsci and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2020,Vol.96, No.3, pp.767-786.
[20]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Remarks and Answers to Questions During the Online Session ‘Russia and the Post-Covid World’, Held as Part of the Primakov Readings International Forum”, Moscow, 10 July 2020, 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 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217691
[21] William S. Smith, “Jeane J. Kirkpatrick: 30 Years Unheeded”,, 13 June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eane-j-kirkpatrick-30-years-unheeded-162667
[22] Lee Hsien 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July-August 2020, Vol.99, No.4, pp.52-64.
[23] William H. Hi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24]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11 October 20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25] Katrin Bennhold, “‘Sadness’ and Disbelief from a World Missing American Leadership”,, 23 April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3/world/europe/coronavirus-american-exceptionalism.html
[26] Hosse Almutairi, “G20, G7 and Covid-19: an Opportunity for Cooperation”, ISPI Online, 10 June 2020,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blicazione/g20-g7-and-covid-19-opportunity-c ooperation-26454
[27] Peter Beaumont, “Covid-19 Outbreaks Out of Control in Many Countries, says WHO”,, 10 Jul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l/09/covid-19-pande mic-accelerating-says-who-as-review-panel-named
[28] Glenn Diese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fter Covid-19”, Valdai Discussion Club, 15 July 2020,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he-international-economic-system-aft er-covid-19/
[29] Samir Puri, “Today’s Imperial Rivals”,, July 2020, https://www.chatham house.org/publications/twt/today-s-imperial-rivals
[30] Ashley Quarcoo, Rachel Kleinfeld, “Can the Coronavirus Heal Polariz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 May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5/01/ can-coronavirus-heal-polarization-pub-81704
[31] Stewart Patrick, “When the System Fails: Covid-19 and the Costs of Global Dysfunction”,, July-August 2020, Vol.99, No.4, pp.40-50.
[32] Hunter DeRensis, “The Blob Strikes Back”,, 23 October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lob-strikes-back-90476
[33]关于“连接政府、保守智库、游说集团、法务公司和国防工业的旋转门”的详细研究,参见Richard Cummings, “Lockheed Stock and Two Smoking Barrels”, Corpwatch, 16 January 2007, https://corpwatch.org/article/us-lockheed-stock-and-two-smoking-barrels
[34] Michael J. Glenn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5] Adam Shatz, “America Explodes”,, 18 June 2020, pp.4-8, at p.7.
[36] Matthew Dal Santo, “Yes, to Balance China, Let’s Bring Russia in From the Cold”, Lowy Institute, 7 July 202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yes-balance-china-bring- russia-in-from-cold
[37] Dmitri K. Simes, “The Perfect Storm”,, 24 April 2020.
[38] John J. Mearsheimer,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July-August 2016, Vol.95, No.4, pp.70-83.
[39] James Rogers, Andrew Foxall, Matthew Henderson, Sam Armstrong,, London, Henry Jackson Society, May 2020, 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publications/breaking-the-china- supply-chain-how-the-five-eyes-can-decouple-from-strategic-dependency/
[40] Antonio Villafranca, “Europe: Rising Frictions with Trump’s G7”, ISPI Online, 10 June 2020,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blicazione/europe-rising-frictions-trumps-g7-26448
[41] Timofei Bordachev, “Threat of a New Bipolarity?” Valdai Discussion Club, 30 April 2020,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hreat-of-a-new-bipolarity/
[42] Vasily Kashin, “Why Did it Happen? On the Issue of China’s ‘Guilt’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Valdai Discussion Club, 5 May 2020,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on-the- issue-of-china-s-guilt-for-the-coronavirus-/
[43] Toby Helm, “Pressure from Trump Led to 5G Ban, Britain Tells Huawei”,, 18 Jul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jul/18/pressure-from-trump-led- to-5g-ban-britain-tells-huawei
[44] Lily Kuo, Julian Borger, “US Considering Travel Ban on up to 92m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17 July 2020, p.2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 2020/jul/16/us-considers-travel-ban-on-millions-of-china-communist-party-members-report
[45]例如Maurice Glasman, “As Globalisation Fractures, the West Must Champion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Face of China”,, 3 July 2020, https://www.newstates man.com/world/asia/2020/07/globalisation-fractures-west-must-champion-internationalism-face-china
[46] Jonathan E. Hillman,, Washington DC, CSIS, July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and-russia-economic-unequals
[47] Dmitry Gorenburg, “An Emer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Trends in Russia-C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re for Security Studies, No.54, 29 April 2020, https://www.marshallcenter.org/en/publications/security-insights/emerging-strategic-partnership-trends-russia-china-military-cooperation-0
[48] Artyom Lukin, “Western Media is Wrong, Russia and China are not Going to Clash over Covid-19”, RT.com, 5 May 2020, https://www.rt.com/op-ed/487832-mainstream-media-russia -china-relations/
[49] Ankur Shah, “Trouble on the China-Russia Border”,, 5 May 2020, https:// thediplomat.com/2020/05/covid-19-trouble-on-the-china-russia-border/
[50] Artyom Lukin, “Western Media is Wrong, Russia and China are not Going to Clash over Covid-19”.
[51] Vladimir Popov, “Learning from Asia: How to Handle Coronavirus Economic Recessions”,, 28 April 2020.
[52] Jennifer Rankin, “China Joins Kremlin on EU’s List of Active Disinformation Threats”,, 11 June 2020, p.22.
[53] Dimitri Alexander Simes, “Will Russia Be the Real Loser in the New US-China Cold War?”, 2 May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russia-be- real-loser-new-us-china-cold-war-150071
[54]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It Takes a State”,, July-August 2020, Vol.99, No.4, pp.26-32.
[55] Andrew Bacevich, “Wi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Survive the Pandemic?”, 22 April 2020, https://spectator.us/american-exceptionalism-survive-pandemic/.
[56] William J. Burn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Foreign Policy”,, July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7/united-states-needs-new-foreign-policy/614110/
[57] M. K. Bhadrakumar, “Russia-China Entente Deepens in the Shadow of the Pandemic”,, 2 May 2020.
[58] Fareed Zakaria, “The New China Scare: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 January/February 2002, Vol.99, No.1, pp.52-69.
[59] Nikolas K. Gvosdev, “Don’t Bet on Reset: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the Coronavirus”, Russia Matters, 22 April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dont-bet- reset-us-russian-relations-wake-coronavirus
[60]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March/April 2020, Vol.99, No.2, pp.64-76, at p.73.
[61] Adam Shatz, “America Explodes”,, 18 June 2020, pp.4-8, at p.5.
[62]例如,参见Victoria Nuland, “Pinning Down Putin: How a Confident America Should Deal with Russia”,, July-August 2020, Vol.99, No.4, pp.93-106.
[63] Richard Youngs, “Coronavirus and Europe’s New Political Fissures”, Carnegie Europe, 10 June 2020,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0/06/10/coronavirus-and-europe-s-new-political-fiss ures-pub-82023
D50
A
1009-721X(2020)05-0024(26)
*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出自RichardSakwa, “Multilater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n Era of Disruption: the Great Pandem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Moscow, MGIMO), 2020, No.3. 作者对该刊授权中文发表使用表示感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2)的阶段性成果。
**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肖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