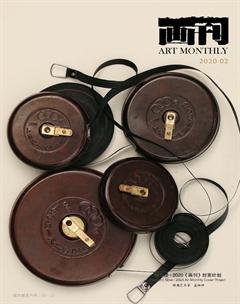艺术批评怎样统一?(三)
[美]詹姆斯·埃尔金斯
你将要阅读的这篇文章最初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在18世纪的英格兰,有一种传统的小册子:它们是以非正式文体写的小书,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出版的。人们过去常常随身携带它们,并在公开辩论中使用它们。我写的《艺术批评发生了什么?》就是用这种传统小册子书写的。书中提出艺术批评家变得对赞美艺术比对分析和判断艺术更感兴趣。我认为艺术批评已经变成中立的了。
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引用了当时刚完成的一项调查,证明北美的艺术评论家不喜欢批评艺术。那已是15年前的事了,但很幸运的是第二项调查也刚刚完成,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很可惜的是这两项调查,都仅针对北美的艺术批评家。如果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调查就好了,尤其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关于全球性艺术批评的研究。
人们对于艺术批评本身知之甚少。当今有一个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AICA,但他们不分析批评本身,他们的出版物也不是艺术批评的典型例子。艺术批评仍然是艺术界研究最少的领域之一。相较之下,国际双年展或展览通常会有多种语言的图录,许多艺术史书籍已经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但是,艺术批评却很少被翻译成母语之外的语言:如果一个评论家用爱沙尼亚语写了篇文章,然后在当地报纸上发表,那它可能永远不会在爱沙尼亚以外的地区被翻译或阅读,其结果就是艺术批评就如同一个未知的大陆。如果将更多的艺术批评文章从中文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也有从许多其他语言翻译成中文和英语,那将是极好的。翻译将是唯一的方法,以决定是否有一个全球性的艺术批评实践,或是否在不同国家其实践并不相同。
《艺术批评发生了什么?》也是我正在撰写的一本有关全球艺术批评的书的第一章。在2019年,我对欧洲和美洲的艺术批评现状进行了调查,包括视频记录和线上杂志的最新发展情况。这项调查可在网站academia.edu(tinyurl.com/y6xg86ju)上查询。
我非常欢迎每一位读者给我写信,提出问题、发表评论和告知最新信息,我的邮箱是jelkins@saic.edu。(詹姆斯·埃尔金斯)
(接上期)
6.描述性艺术批评
描述性艺术批评是20世纪的又一大发明,也是整场灾难的第二大罪魁祸首。这是一种试图不作出评价,但又以批评的姿态呈现的艺术写作,也是20世纪下半叶令人费解的悖论之一。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通过对美国排名靠前的230位批评家(即那些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周刊和国家性新闻杂志写作的人)进行调查发现,批评家们觉得“批评”的关键是“提供一个准确的描述性观点”。我将这一诉求称之为“描述性艺术批评”(descriptive art criticism)。其中一位调查对象认为:艺术批评是在艺术家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展开一段“对话”;另一位调查对象的兴趣点是“激励读者观看并购买艺术品”;第三位调查对象希望向读者介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观点”;第四位调查对象(在调查中他们都是匿名的)干脆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向读者介绍城市里发生的事。”对话、唤醒、动机、介绍、桥梁:这些都是良好的“叙述”的同义词。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可以与哥伦比亚大学这项调查形成比较的国际艺术批评家调查。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t Critics,AICA)的章程算是全球艺术批评家最具代表性的章程了,它对“描述性批评”只字未提。相反,章程认为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应当为艺术批评找到“合理的方法论和道德基础”。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大多数艺术批评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方法论或道德层面。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中,排在“描述性”之后艺术批评的第二个目标是“提供历史和其他背景信息”:(我理解为)某种类似艺术史的理想。正如某调查对象所说:“艺术批评应该将某件作品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之下。”这个目标不存在任何争议,因为历史语境天生就是批评的一部分,也是艺术批评不可或缺的。但严格地说还不够,因为那样的话艺术批评就变成艺术史了。我同意库斯皮特(Kuspit)的观点,即批评家的部分任务是找到作品在历史中的位置,并贏得“历史法庭听证会”(的席位)。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艺术史的参照,但它不是艺术批评。
一些描述性批评确实是以艺术史或未来艺术史素材的形式出现的。几位看过早期这类文本的批评家写信告诉我,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描述”。其中一人写道,“我们互相交谈,以便将正在发生的事情转化为历史记录”,为的是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比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首席艺术批评家迈克尔·基默尔曼(Michael Kimmelman)就认为他在《肖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卢浮宫等处与艺术家交谈》(Portraits: Talking with Artists at the Met, the Modern, the Louvre and Elsewhere,1998)一书中记录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机构选择艺术品时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独特的遭遇,因此这几篇访谈可能会成为未来艺术史的重要素材。然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份参考资料,因为基默尔曼在导论中对艺术史进行了调侃:“我认为这些艺术家对以往艺术(品)的追溯重拾了某种历史学家们担心或者忽略的感受……伦勃朗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喜欢他的作品。”(在这里)艺术史被描述成一门回避批判且屈从于不切实际的历史的学科。对于基默尔曼来说:“艺术家们更像是充满了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古板气息的批评家……”他们“会用同样的紧迫感和轻蔑感来看待古代大师和新的艺术”。一般来说这种观点没什么问题,但有很多当代艺术史以品质和关联性为出发点的,并将其自身的派系(源流)当作历史来认真对待。如果这是一部编年史(historiography)著作,我可以追溯艺术史学家们感知紧迫、轻蔑、恐惧和疏漏等方面的历史。这样的历史(研究)已很容易地发展成为囊括了整个民族传统的艺术史,而事实证明这种历史与基默尔曼著作中的评论家和艺术家一样,在历史判断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在基默尔曼看来,将批评家和艺术家与艺术史学家区分开来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艺术史学家往往不会过多关注艺术家个人的喜好。基默尔曼指出:他采访的艺术家常常会赞扬某些相同的作品,比如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秋天的旋律》(Autumn Rhythm)、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的《街道》(Street)和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在基默尔曼的书中反复出现的还有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巴尔蒂斯(Balthus)和十几位前现代艺术家。尽管艺术家自己的代表作或许并没有出现多少历史性的作品,但艺术家们在做选择时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反复无常或特立独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波洛克挑衅的姿态带来的惊喜和挑战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观众(对作品的)反应(方式),而基默尔曼采访的那些艺术家在表达类似的情绪方面也并不是原创的。加斯顿的(图像)遗产也发展成为老生常谈的应对方式:他图像借喻(figuration)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了那些想和图像修辞反对者(anti-figural rhetoric)拉开距离的人们的试金石,不过他作品中纯粹的悲伤仍会招致人们的追捧或者背弃[在基默尔曼的书中,苏珊·罗森伯格(Susan Rothenberg)说,她觉得街上的垃圾桶盖“很可爱”,并把它们比作“光环”。我想加斯顿会认为这种反应是很可怕的]。艺术史数据库显示,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以毕加索为研究主题的专著和论文比其他任何现代或前现代艺术家都多,但艺术家仍然发现他的(图像)遗产存在问题,甚至并不重要:正如一些艺术史学家已经指出的,这是由艺术史学家们自己都未察觉的有意压制造成的某种关系。为了避免任何的批判性,基默尔曼让艺术家自己选择他们想要讨论的作品,并且不要求他们说明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的选择)是没有理由的,20世纪艺术的各种观念对他们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基默尔曼希望他的书能够疏离于艺术史,也疏离于由批判驱动的艺术批评。他希望能在(艺术史)论争之外找到一点空间,(在那里)艺术家们可以用自己的谈话方式创造一种新的对话。这种做法赋予了艺术史以“紧迫性”(urgent),同时指出并不只是艺术史研究才能填补艺术家的话语与其他人关于现代艺术著作之间的鸿沟,但其问题和困难在于:如果没有建起这座桥梁,基默尔曼的书将毫无意义。倾听艺术家们谈论他们感兴趣的艺术作品可能会给理解他们的作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但只有将它们与某些先于历史的,先于学术的东西进行对比时,它才有意义。基梅尔曼的选择是多样的,但都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巴尔蒂斯、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urry)、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苏珊·罗森伯格(Susan Rothenberg)、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等。或许基默尔曼还有机会采访到更多其他的人选;但总的来说他选择的艺术家确实构成一个群体,即获得了艺术市场青睐的艺术家,而市场反过来又与批评和艺术史的整体机制相关联。我并不是说基默尔曼的选择是由市场驱动的:我的意思是,这些艺术家之所以显得有意义,而且比较独特,恰恰是因为基默尔曼所说的艺术史整体机制与他的这项计划格格不入,毫不相干。在比较理想的艺术史和批评中,它们已经或至少尝试去说明这些艺术家为什么会比较重要,还有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即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并不连贯,就好像从某种非沉浸式的访谈中截取一段与其前史(prior history)毫无关联的对话就可以了,或者与其前史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样,为了使(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看起来比较合理,艺术家的话就没有必要与其前史进行关联了。
这是我在基默尔曼的书以及描述性批评中发现的问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问题是能否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采访更多的艺术家,直到它们自己形成某种独立的、可供完善的议题来建构一个更加宏大也更为长久的观念。《肖像》是一本很谦逊的书,除了16次采访外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但这意味着,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关注艺术家自己的选择和说话方式,那么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真实又充分的视觉艺术思考方式。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艺术家在《肖像》中表达的各种观点只有将其置于先前的观点、判断、研究、写作和宣传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而这些构成了20世纪艺术史的总和。要沿着《肖像》的道路走下去是不可能的,就好比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17世纪法国艺术史时,在不加阐释的情况下直接引述普桑(Poussin)说卡拉瓦乔(Caravaggio)想毁掉绘画。这样的叙述只作为在无法获知卡拉瓦乔本人的视角和观点时的权宜之计,这时才会考虑普桑、卡拉奇地区(Carracci)以及古典与现代之争等替代性方案。就其本身而言,普桑的判断是出乎意料的,也是非常独特的,因此很有吸引力。但是,正如路易·马丁(Louis Martin)在其著作中证明,普桑的意图可以通过17世纪的教育和著述来阐明:即通过研究同时代的艺术史和批评。基默尔曼著作一个更有野心的版本还涉及了艺术家阐述的历史和批判性评价;它会被解读为艺术批评或艺术史,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不是其他的某些概念。描述性艺术批评就像是刚刚开采出的矿石原石,它本身并不是我们想要以其为材料制造出的那件东西。
基默尔曼的《肖像》可能是习惯于下判断的报纸评论家写的第一本描述性批评的书。比较常见的描述性艺术批评是报纸或杂志的评论,这些评论通常会避免强烈的判断的。我的朋友和同事詹姆斯·尤德(James Yood)许多年来一直是《艺术论坛》驻芝加哥的记者,他长期以来对发表在印刷物上的艺术品没有评判的兴趣:他认为自己的评论是一个让观众对新艺术产生的感觉的机会,而不应该对作品发表意见而毁掉读者自己的体验。他非常小心地使用形容词,以撰写某种既不太积极也不太消极的中性评估。在一篇关于画家约翰·皮特曼(John Pittman)的文章中——和凯特·谢泼德(Kate Shepherd)相似,展览中的绘画是由细线构成的松散网格,尤德写道:“某种渐进式延展的知觉和从容的节奏避免了这幅绘画看起来过于缜密或严酷。”这是一句四平八稳的话:它强调了作品可能会过于缜密或严酷,但也指出“渐进式延展”让其节奏并不僵化。请注意,这是多么精细的拿捏:用“节奏”平衡了“从容”这个听起来比较糟糕的词汇,又用“从容”调和了“节奏”这个比较有活力的词汇。似乎这还不够微妙,接下来的句子更符合这种描述:“相反,它微妙的动感赋予了它们一種随意且自然而然的轮廓,这显然非常高明的设计痕迹。”这是评论的最后一行,它给这件作品评价留下了几乎完美的权衡,在最后的赞美之后立即写下了既热情又谨慎的修正:作品“非常高明”,但这种高明只流露了一点“痕迹”。
当然,这些都是在做判断。我不怀疑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观念——描述就是判断。正如彼得(Peter Schjledahl)所说“精确的语言是最好的判断”,一个精心思考的判断只能用精挑细选的词来陈述;否则,微妙之处就会被抽离。我不怀疑这种描述是判断,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区分出有意的判断,还是有意不去做判断。后者会伪装成前者,而前者会滋生后者。当代艺术批评沉迷于尽可能地避免去下判断,而那些把描述和判断等同起来的批评家对做判断的逃避有时只是自欺欺人。
在我看来,尤德的拿捏和基梅尔曼对提供原始素材的兴趣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他们的做法与历史上被称为艺术批评的做法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描述性批评通过否认这是个问题去回避什么是批评这个问题。正如我想象的,论证必须是这样展开的:我们可以避免基默尔曼提到的那种布卢姆茨伯里式的批评(即个人投入的、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写作),这意味着艺术写作领域确实存在着一片清理了过激判断的净土。这一事实还意味着回避某些枯燥中立的艺术史也是可能的,艺术批评可以在历史先例的压力之外占有一席之地。我不这么认为:新的非判断性写作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但这种愉悦往往来自于对历史性判断这一责任的逃避。
正如上面两个例子所展示的那样,描述性批评的特征并不容易辨识。有些源于对艺术史的怀疑,还有些则是不愿影响人们艺术直观体验的天平。鉴于其复杂的动机,描述性批评有多个起源这个事实就很容易理解了。据我所知,它至少有七个来源。(这七个来源的名单和“海德拉之首”(hydra heads)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碰巧在收集描述性批评的资料时,以七个来源结尾。)
(1)杰里米·基尔伯特-罗杰夫(Jeremy Gilbert-Rolfe)提出了一个我并不完全相信的解释。他在2001年的一次会议上说:画廊的租金不断上涨迫使画廊主做出更安全稳妥的选择,这反过来迫使艺术批评家为了出版(著作)而默许。那当然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它更适合曼哈顿而不是较小的城市,并且更适合作为目录短文的注解(即第一个“海德拉之首”)。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批评家更喜欢描述而不是做判断。
(2)另一种解释描述性批评的方式是要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意识到艺术市场的巨大力量。一些批评家以此为契机,用当时的话来说,附庸艺术市场。严肃的艺术批评似乎是多余的,而且对艺术传播来说似乎批评家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解释当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也未能解释为什么众多批评家选择写描述性批评。因为艺术市场自20世纪90年以来已经逐渐崩溃,所以对此人们对这股力量的影响并没有太多非议。
(3)据说描述性批评源于对波普之后艺术风格激增(这一现象)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刚性的判断是不合时宜的。这种描述性批评一直有一位辩护者:托马斯·麦克艾维利(Thomas McEvilley),他提出后现代主义批评应该是一种解释性的而非辩论性的实践。它的目的是在地性的,关注作品的特性,并引起共鸣。
(4)豪尔·福斯特(Hal Foster)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跟随格林伯格(Greenberg)和第一代《艺术论坛》批评家之后开始写作的艺术批评家是在“反对”艺术批评“要做判断”这一属性。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极简主义(minimalism)和制度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都使艺术批评变的无关紧要。在2001年秋季举行的一次有关艺术批评现状的圆桌会议上,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u)说:在观念艺术领域,“批评家的介入遭到了历史性的蔑视和谴责”。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可以看出《十月》与更广泛的艺术批评实践是孤立的,它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描述性批评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重要的艺术运动,这场运动反对将批判性思想和艺术作品进行区分。
(5)1971年,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提出:在现代主义之后,艺术批評应该成为(对艺术作品)进行检验的论坛,而不是为某个展览做出判断。1985年,她在《前卫的原创性及其他现代主义神话》(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的序言中说:批评应该揭示“那些在判断行为之前的所有选择和预判”。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把艺术的统一性与判断力本身作为前提,因此“批评的要点与价值有关,而与方法无关”。按照这种理解,对判断的反思是一种打开后现代的关注点和格林伯格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之间空间的方式。如果我们认为“现代主义艺术似乎已经结束”,那么判断本身现在就成了反思的对象,更进一步说,如果批评已经“公开地打开了……向方法开放”,那么这种做法就没有彻底的或者大体上遵循批评实践中对判断的质询(原则)。事实上,克劳斯的著作将艺术批评置于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从字面上看,她所倡导的批评完全集中与阐明他人判断的各种(先决)条件。(但)大多数描述性批评没有那么纯粹的动机。
(6)一些描述性批评源于对艺术史的兴趣,即在不介入的情况下就可以讲述事物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n)重新产生了兴趣,研究对象是以前的人对艺术的看法。最纯粹的接受史与其主题的性质、重要性,甚至其真实性都是保持中立的。研究19世纪艺术的历史学家马克·戈特利布(Marc Gotlieb)曾写过一本关于接受史的书,内容是艺术家们有自己的工作室机密,并代代相传。[最著名的例子是扬·凡·艾克(Jan Van Eyck)所谓的油画秘方。]戈特利布(Gotlieb)关注的不是秘密存在的真实性,而是这种机密观念对人们看待艺术家和作品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还有一些接受史比如关于凡·高(Van Gogh)(追溯他死后如何成名)和保罗·克利(Paul klee)(记载他的画廊老板努力为他塑造形象,并且推动他的事业)也有出版。当接受史被用来研究艺术中仍存在争论的议题时它会变得非常有趣,因为这时接受史将自己单纯地呈现为过去思想的产物。对于大多数在世的艺术家来说,凡·艾克的油画是否有特定的配方并不重要,但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思想是否仍然具有影响力——如果这些思想可以被认为适用于某些类型的绘画,甚至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则意义重大(对格林伯格的长期质疑表明,至少他的一些想法仍然令人信服)。卡洛琳·琼斯(Caroline Jones)有关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研究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现代接受史议题,因为琼斯感兴趣的是“纯粹性”“前卫”“扁平”“抽象”等概念在何种情况下才会被认真对待,以至于能够成就格林伯格这类批评家的职业生涯。实际上琼斯对诸如“抽象”和“真相”等概念的价值或者连贯性并不关心,这可能会让大多数仍旧遵循或者尚未接触过格林伯格原著观念的艺术家感到震惊。(根据我的经验,后者包括了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画家。)对于那些刚刚意识到格林伯格的想法的人来说,琼斯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呢?
(7)描述性批评的另一个来源是体制批评(institutional critique)。这是一种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艺术批评实践,尤其与艺术批评家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有关。在包括布赫洛在内的《十月》圆桌会议上,艺术家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举例说明了体制批评,她说“艺术界的劳动分工从根本上说是合法性的分工。而后者是信念产生的基础”——注意这句话,“信念的产生”一词使她与实际的信念拉开了距离,“我们通过让艺术作品展现的出自发性的投入或自发性判断来衡量其价值,就其价值的物质层面以及该作品创作过程中所涉及的个人或行业利益层面而言,(其价值)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升华”。就她的立场而言,价值是通过劳动条件制造出的某种建构、某种幻觉,或某种信念,这是一段一气呵成的雄辩。按照这种理解,做出更多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理解他人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将其奉为真理的。
在体制批评中做判断是无效的,它被来自两个方向的假设所牵制。一方面,人们认为在任何明确的表述中都会存在或伴随着判断,所以没有必要弄清楚那些判断究竟是什么,而且这种尝试意味着判断是可以从思想矩阵中分离出来并加以挑衅和操纵,这是有害的。如果我对一件艺术品发表评论,意味着我在不经意间已经对其做出了判断,而且从内容窥探形式并没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判断是先前文化状态的遗留:它们是现代主义的化身,或者更糟的是它们是现代主义之前几个世纪的(文化)化石。这种判断标榜自己具有内在保守性,不适合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这两个主张在判断的历史基础与持续不断地、坚定的、野心勃勃的判断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变得毫无用处。
因此,在我的小型谱系中,非判断性批评(nonjudgmental criticism)至少有七个根源。我意识到,这些都是片段,我知道它们并不能很好地回答我标题中的问题。可能是该主题本身不倾向于任何单一的解释,或者我们离它太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时刻留意这片海洋的变化:判断的退潮是上个世纪艺术界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七种解释中有几个与市场有关,所以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在《艺术评论》(Art Review)和《华尔街时报》(Wall Street Journal)等杂志上刊登的纯粹经济市场报道,在它们声称要评估艺术品而不仅仅是报道价格时,也要被视为描述性批评。佩妮拉·霍姆斯(Pernilla Holmes)为朱尔斯·奥列茨基(Jules Olitski)撰写的“成绩单”(Report Card)与经济学家报告中常见的数字运算一样。1990年,在萨兰德·奥·莱利(Salander O Reilly)开始购买作品后,霍姆斯说:“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油畫的估价在6万英镑至12万英镑之间,突然间就猛增至20万英镑以上。”然而,这篇文章并不完全是经济学。霍姆斯还发现,“当时的艺术批评大师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称奥列茨基是在世的最伟大的画家”这一点“意义重大”。在这里,艺术批评成了市场中的一个元素,以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脱离了它的语境和论争,异化成了原本应该是由它创造出来的交换价值。我不认识佩妮拉·霍姆斯,但我认为她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资本家,因为她也写关于20世纪绘画的评论,而这些评论与销售数字无关。但至少在这份报告中,艺术批评就像市场分析师分析圣诞节的欢庆对道琼斯平均指数的贡献一样,被无情地中立化了。
另一种看待描述性批评的方法是将其比喻为“海德拉”的两个头颅,一种混合型的神话学隐喻,把它想象成“海德拉”的两副面孔。一面是良性的,目的是提高读者的艺术感受。《新共和》(New Republic)的艺术批评家杰德·佩尔(Jed Perl),用演说家狄米特律斯(Demetrius)“平实”的语气写道:直截了当、条理清晰、描述性强,始终专注于作品。就像狄米特律斯所倡导的“平实风格”(Plain Style),其目的是在不借助双关语、专业术语或夸张手法的前提下感染读者。描述性批评的另一方面是被动的破坏性,因为这样的写作总是会冲淡判断的动力,将艺术批评从判断和艺术史中分离出来,并使之变成无害的外交辞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