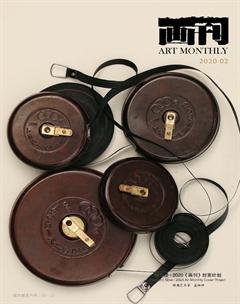“星星美展”:梳理、再现、重构
巫鸿

我很高兴“星星1979”展览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举办。OCAT研究中心的定位是既要做当代艺术,又强调研究性。“星星1979”是一个研究性的展览,涵盖了文献、档案和艺术。策展人是容思玉女士和我,容思玉(Holly Roussell)是一位独立策展人,做了很多关于中国当代美术的展览。她的硕士论文的内容是关于第一届“星星美展”,对其做了档案学的研究和考证,不管从博物馆学还是其他的研究方向来说,都是一个有意思的个案研究。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了一个合作的可能。
这个展览能举办还与黄锐有关。前几年黄锐从日本带回一个皮箱,里头装的都是 “星星”的老档案。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一看这些原始档案就很兴奋。和星星艺术基金会、和以黄锐先生为代表的一直在继续进行艺术创作的“星星”艺术家们的合作,也是这个展览很重要的一块。他们提供了很多自己收藏和整理的材料,而且作为参与者,他们有着相关的回忆,这种“活”的材料也特别重要。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料都是原来没有展出过的。能够将如此之多的资料收集整理并呈现出来,是OCAT研究中心和他们一起联合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比如当时的几位摄影师,以及其他目击者和研究者。
关于展览的展览
我们做“星星1979”这个展览,是和OCAT研究中心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OCAT首先是一个研究中心,也有展览的机能,但它主要是做研究,希望把历史研究和当代艺术放在一起。所以,和一般美术馆、画廊不一样,OCAT研究中心不光是把展品挂出来,还有很强的研究性,要研究和梳理当代艺术的历史。之所以这次聚焦在“星星美展”上面,就是因为它在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当代美术开始发展的阶段。我们还意识到,虽然大家都知道“星星”的重要性,但对它的历史还要进行梳理和研究。比如一些很基本的事实:第一次展览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一共有多少件作品?作品是怎么展陈的?等等。这些事实对于将来的艺术史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我的角度而言,我们不是参与者,我们是研究者、是整理者。所以这次展览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展开工作,希望能够给将来的美术史研究、当代艺术研究打好新的基础。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展览,利用我们整理出来的文献,在此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因此,今天的展览是一个“关于展览的展览”,是用一个展览去展示以前的一个展览,把它搜集、分析,然后再提升。我们进行了两个方向的工作:一个是“星星”的成员,他们在40年前做了一个划时代的展览,之后也一直在继续创作。他们为这次展览提供了很多资料。另一个就是策展人、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在做的工作。这两个方向凑在一块,形成了今天这个展览。
“星星美展”是一個历史上消失了的事件,但留下了很多记录。“星星1979”这个关于展览的展览是当下的、今天的一个展览。它本身的定位既是学术性的,又是艺术性的,所呈现出的是当今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现象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和艺术创作不太一样,它带有很强的历史研究梳理性质,但是还要用一个空间把它展示出来,它当然也是展览。
虽然今年正好是第一届“星星美展”40周年,但是我们展览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纪念。“星星1979”主要的目的是利用这个契机来做一个很扎实的文献梳理和分析。同时,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也要说明,虽然我们做了这个展览,但并不是说就做到头了,需要继续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现在把这个展览呈现出来,大家还可以不断提供新的材料,进行参与。
情境重现
今天我们看到的展览,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从实物到最后的呈现方式,观众可以看到这些努力如何导致这个“关于展览的展览”——不是关于作品,而是关于展览和当时的情境。所以,我们的展示即从20世纪70年代的情境开始。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可能对那个年代没有感觉,我们因此在展厅第一部分放映了一部小电影,是一个法国人拍的当时的北京街头。从这个情境开始,告诉大家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看当时的北京人是什么样,当时的那种色彩、气氛、街道是什么样。然后进入第二部分,是“今天”和“星星”,一个文学团体、一个美术团体,两者之间强烈的互动。这部分里还有一个小屋子,重构了当时他们进行集会、讨论的场景。所以展览的前两部分是再现当时的情境。第三部分,即展览主体,就是对第一届“星星美展”的重构。这个重构不太容易,因为当时没有详细的记录。经过了很多人的研究,包括容思玉、黄锐及其团队,还有刘秋旭等人,大家进行了很多的核实工作,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工作。这部分是基本性的,力图还原当时的展览。重构并不是事无巨细,但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回避。比如说,当时的场地是露天的,我们就要显示出室外的气氛和感觉。我们还要弄清楚在那样一种场地里,作品都是怎么排列的。人们对“星星”的了解往往限于少数代表性作品,比如王克平、黄锐的几件作品。但实际上当时展出的作品有100多件,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参加者都是各处来的年轻人。我们需要把当时的情境和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把一个40年前的事拿出来再做展览,意义何在呢?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多重的。对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研究者,我做历史研究,也做展览。中国的当代艺术相对西方来说发生得比较晚,拿1979年做一个时间点,也就是40年,还是比较短。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特别迅速,在这40年里发生的事情特别多。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回顾做得比较粗糙,这也是一个原因。我们需要把中国当代美术中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中的细致环节、人的作用和语境挖出来,这样将来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深入的对自己当代艺术发展过程的理解。我觉得这也是本展览的一个意义和希望,因为“星星”这个事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谈艺术,谈的就是画、作品,而文本、背景、相关资料等好像不太重要。我觉得需要对这种做法画个问号。比如说有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当时的“星星美展”里有不少文字,有配诗。我在写这段美术史的时候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后来的历史写作把这段割裂了:研究文学史的人就盯上了“今天”和他们写的诗歌,把它们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学现象来研究;研究艺术史的人就把“星星美展”,特别是里面的几件作品说个没完没了;研究政治史的人就盯上了西单民主墙。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包括有关当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艺术的关系,这几方面都是紧密不可分割的。

“星星1979”这个展览恰恰就是要解决这个割裂的现象。这个展览不是要把這个事件进行所谓的分类,一边是作品、一边是背景,而是把这些元素放在一起。所以我们想恢复的不仅是一个展览的原貌,还有它当时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其中人的因素。我们想把人的因素凸显出来。比如“星星”艺术家们都有很多故事,有当时的回忆和记忆,这些都会很有意思。另外,我要强调,对一个场地和情境的重现还得包括当时观众的反应,这非常重要。“星星美展”有很多留言本,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所写所言。还有观众看了展览以后为之作曲,我们把那些曲子复原,挂上耳机给大家听一听。所以作为一个展览,它有前因后果、有语境,有当时的艺术家和组织者的工作,还有当时观众的反应。我们就是想把这些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来,展出一个活生生的1979年的“星星”。
档案研究作为方法
我们在策划“星星1979”的时候,强调艺术性和文献性并重。我们希望以这个展览做一种尝试,即我们作为策展人、研究者,如何通过展览的方式对一个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同时呈现给大家做这件事的方法。这个展览模式的意义所在,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思路和方法论,在这个方法论的基础上可以再考虑别的一些历史上的展览。历史上的关键大展都应该做,比如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做?毕竟那次大展众说纷纭,现在大家对很多具体情况已不是很清楚了。
艺术史的研究和梳理得靠资料、档案。虽然像黄锐等“星星”成员们自己也有这个意识,但是上升到真正的艺术写作、艺术史研究、艺术教学层面,我们有必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方法和手段。西方对艺术史的梳理非常仔细,相关的档案非常翔实。比如关于达达等艺术运动,相关书籍资料就不知道有多少。关于“星星”的展览和研究,可以参考的翔实的书很少。吕澎写的书,还有我自己写的书,关于“星星”的内容可能也就那么一两页,研究基本都是粗线条的。“星星”的参与者们自己也出了相关书籍,但对细节的梳理也还是比较粗粝。
前几年,我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一书,这也是我和OCAT合作的开始,和黄专老师一起做的,我们都对资料、原始积累特别重视。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就得做个案,不能囫囵吞枣,否则没法总结。因此,把“星星1979”展览当作一个关键历史事件,通过档案的整理梳理,使其重要性真正进入艺术史的序列,这就是这次展览的目的。
注:本文根据2019年12月20日“星星1979”展览开幕现场访谈整理,已经作者审核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