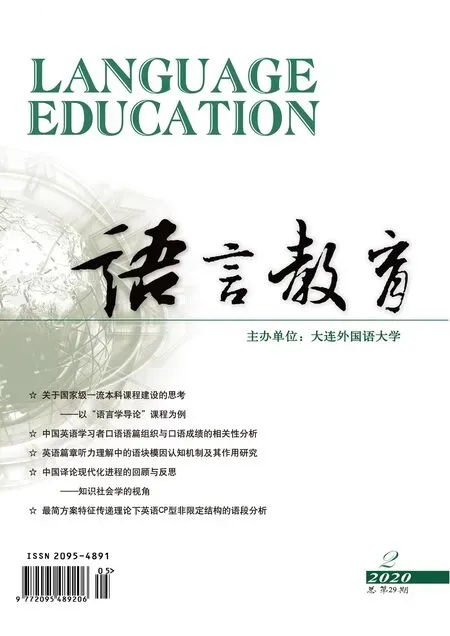物质女性主义研究
王薇薇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作为术语出现较晚。2008年,斯黛茜·艾莱默(Stacy Alaimo)和苏珊·贺克曼(Susan Hekman)联合主编的《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s)的出版才奠定了它的学术基础。它是由科学中心女性主义、赛博格女性主义以及达尔文女性主义等理论进行整合、演变,开始理论尝试。
从词源学来看,物质女性主义是由形容词material和名词feminism组合而成。material为形容词时,在词典中有多层意思:物质的、肉体的、辩证的、唯物的、重要的、决定性的等。一开始,Materialism进入国内时被翻译为唯物主义,尤指马克思所倡导的唯物主义。目前,通过马克思唯物论的视角来思考的女性主义,主要有马克思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与唯物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sm)。因此,material feminism中的material之所以被翻译成为物质的,一是因为它所研究的“物质”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所研究的“物质”有本质的区别。二是物质女性主义理论更多是受到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理论的影响。新物质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于“物质论”的定义有根本的区别。唯物主义的“物质论”更侧重于与社会生产的关系,而新物质主义的“物质论”则与量子力学、达尔文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关系密切。而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新物质主义对待世界的方式和目的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通过改变生产物质来改变思想从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新物质主义则更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去重新理解、阐释和适应世界。历史唯物主义侧重改革社会,而新物质主义则偏向适应世界。学者柏隶曾说,物质女性主义中所考虑“物质”主要有三层意思:首先是自然界的物质性,其次是人身体的物质性,第三是科学技术对自然和人体的物质的改变(柏隶,2012:107-109)。除此之外,物质女性主义的物质还包括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交换的物质,以及两者之间交换后产生的新物质,以及量子力学中“现象”所代表的物质等等,这些都与唯物主义的“物质论”有本质的区别。简而言之,从词源学来看,物质女性主义当中的“material”之所以翻译成为“物质”原因有二:一是理论主要涉及到人类身体和非人类的物质性;二是此“物质”概念深受新物质主义和量子力学的物质定义影响,而非唯物主义中与社会生产相关的“物质论”。
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1955-)为当代美国作家及博物学家,曾获美国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荣誉奖,是美国自然文学、生态批评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她的代表作《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不仅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真实的“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它描述了人类在面对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灾难和悲剧时候,人的身心和自然界如何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又如何从中寻求心灵慰藉。本文欲将结合其给予分析、阐释物质女性主义的相关思想及观点。
1.什么是物质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与物质的关系源远流长,将物质与女性主义放在一起谈论并非物质女性主义首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都曾把物质与女性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且二者都曾对何为女性主义中的“物质性”进行讨论,但未能达成共识。唯物女性主义主要从女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女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关系以及女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出发去探寻女性在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受压迫的物质性根源问题,试图清除性别差异的“生理决定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关注更多的是女性物质生活条件问题,以及物质亲密性问题,如:通过阶级、种族、伦理、年龄和国家所构建的一切。女性与生产的关系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关注如何把妇女的从属地位由资产阶级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中剥离出来。尽管,它也提出超越、改变经济与性别分离的“二元性”,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管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它们的主要理论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论有关。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的概念,主要还是关注物的生产以及金钱的获得(雷蒙·威廉斯,2005:3)。然而,物质女性主义理论与以上两个理论中“物质”有本质的区别。在理论源起方面,物质女性主义缘起于新物质主义。在理论的内容方面,物质女性主义更多受到身体女性主义、环境女性主义以及女性科学研究的影响。尽管很多“物质女性主义”理论家被认为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但是,他们关于“物质”的定义却远不止于马克思主义(Alaimo & Hekman,2008:18)。深受马克思、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女性主义从未超越其生存的资本主义体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物质女性主义试图从一个新的维度,也是一直被西方女性主义忽略的维度——物质的维度,来寻找出路。
由此得知,物质女性主义理论的“物质”既是核心概念,也是发展命脉。“material”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中有两层意思:作为名词时意为“材料、原料,布料、织布,事实、资料”;作为形容词时意为:“物质的,身体需要的,重要的”。“物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古时中国,“物质”的意义更广。古人认为,物为杂色牛,杂色牛通灵,可作牺牲。许慎在《说文解字卷二》中称:“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物之灵,类如萨满之灵神弥漫在宇宙万类之中,贯穿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从杂色牛到牵牛座再到涵盖万物,人类以物概括和指代“物质”(matire)以及各种“对象”(object)的思想进路,经历过漫长的史前文化酝酿。“物”之“神”气不仅是人类心智萌发之酵母,也是文明启动之前奏(栾栋,2010:188)。物质女性主义中“物质”一词的意思颇有此意味,其“物”回归它的本质意义,指人类躯体的物质和非人类世界的物质,以及它们之间经过内部联动而产生的扩展、相连、互换、纠缠和演义,并非关于金钱或者拜物,也非指社会生产之物质。同时,此“物”与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之“物”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此“物”深受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影响,具有后人文主义的意义。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中“物质”的意义,其代表性人物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及其从量子力学中引申并扩展的“物质”意义无法绕开。
量子理论起源于原子观念的发展。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经典物理学中根本局限性。公元前5世纪,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就凭着直觉提出物质具有神奇或活动性。他假定所有物质都是由不可分的微小单位组成,并称之为原子。原子本身是不变的,具有固定的大小和形状等性质,但它们能在空间运动,也能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这样,它们构成的宏观物体就显现出变化了。于是,永恒性与流动性就协调了(保罗·戴维斯 约翰·格里亮,2013:1)。但是,这种极端唯物的思想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反对。1687年,牛顿(Isaac Newton)发表了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简称《原理》(Principia)。《原理》中牛顿提出了著名的运动定律。认为物质是被动的和具有惰性的。惯性(即惰性)在他的世界理论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根据牛顿定律,如果物体处于静止,它将永远保持静止状态,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18、19世纪,牛顿的物质观在蒸汽机和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促进下,得到人类中心主义的认可和支持。同时,牛顿力学巩固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地位,使得二元对立思想从此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20世纪初,量子理论提出了以牛顿力学中心的经典物理学中不被人发现的局限性。它提出两样东西打破牛顿原来的时钟宇宙:一是物质的构成。二是物理系统的非线性活动。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的理论为凯伦·巴拉德的物质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源和基础。巴拉德把它运用于女性主义,建构了她的新理论——“能动现实主义(Agential Realism)”。这一新理论为原来普通的术语,比如:物质、能动力等,赋予新的意义。首先,在“能动现实主义”中物质意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牛顿认为物质由“固体的、厚重的、不可穿透的、可动的粒子”构成。量子力学打破经典的、传统的理论,认为物质不是独立的、固定的物质个体,不是单独的“原子”和“粒子”,而是没有固定的边界和特性的、具有量子波的、不断生成的现象。物质不再是厚实的、不可穿透的物体,而是具有由德布罗意方程决定的量子波。量子波可由普朗克常量的量来计算,波长与物体的质量的大小成反比。物体的质量越大,波长就越短。每个物体都只能穿越厚度与其波长相当的势垒(保罗·戴维斯 约翰·格里亮,2013:142)。因此,那些看似很坚固,看似不可“穿越”的物体,只不过,量子波的空隙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并不代表不存在。量子波的存在就说明物体间存在“缝隙”。因此,“坚实的”物体间出现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可能空间。确切来说,在量子的物质图景里,固体的、不可穿透的物质烟消云散了,只留下奇异的、看不见的场能量的激发和振荡。在这个理论中,物质与虚空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差别,看似虚空的本身也跳荡着瞬间的量子活动(保罗·戴维斯 约翰·格里亮,2013:4)。《心灵的慰藉》中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看似一个“坚固的物质”,而美国最大的水禽保护区——熊河候鸟保护区也看似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地区。还有作为摩门教徒的威廉斯家族,貌似与“物质”也毫无关系。然而事实却相反。由于威廉斯家族家住大盐湖畔,深受美国核试验基地影响,随着盐湖的湖水不断上涨,保护区的鸟类也不断受到威胁,逐步死去或者消失。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自然“物质”,其实息息相关,互为“前景”与“背景”。它们都不是“坚实”的物质,是可以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能量。在此,物质与人类、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人类身体和自然世界的物质性是不断生成的现象。其次,量子力学认为,物理系统不再是单向线性活动,而是多向非线性活动。我们不是生活在直线性活动的宇宙时钟里,而是生活在多向线性活动的网络中。多向线性活动能产生出丰富又复杂的活动,它甚至能使物质从固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产生多种可能。巴拉德认为,“物质不是具有固有本质,而是,物质是内部联动的生成(intra-active becoming)——不是一种物而是一个动作,一种能动力(agency)的凝结”(Barad,2008:146)。笛卡尔认为物质是消极的,本身是被动的,服从于机械论中的物理因果关系原则受到挑战,二元论的地位开始动摇。《心灵的慰藉》中也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大盐湖)、女性与动物(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以及女性与自然(大盐湖)都是密切联系的,而且呈多线性活动。人类活动——美国的核试验——深深地影响着大盐湖中物质的变化,水位的涨落。湖水的涨落也反作用于动物、自然和女性。湖水不断上涨吞噬着熊河候鸟保护区,鸟类开始死亡或消失,作者的祖母、外祖母、母亲以及六位姑姑接踵患有乳腺癌,其中七人最终离世。由此可见,人类与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共同拥有一部自然史”(特丽·威廉斯,2010: 19)。最后,“水利资源局关闭提水站”,大盐湖水终于得到控制并回落至4204.70英尺,“七年来通往候鸟保护区的路第一次畅通无阻”,作者的病情也得到控制。可见,女性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的物质不是消极的,而是能产生能动力,并相互作用的。正如巴拉德在《后人文演义》清晰地展示出“身体物质具有它自己的历史性”。“物质性就是话语”,在那里“话语实践和物质现象并不是外在一个接一个相关联”,而是它们是“相互交涉在一起”(Iovino,2012:134-145)。也印证了物质女性主义的观点——世上一切,一如量子力学中所指,不再有清晰的、单独的个体;也不再有厚重的、不可穿透的物质。世界的一切都在进行着非单向线性活动,物质从此被释放出来,人类与非人类不再泾渭分明,一切都成为内部联动的生成和演义。所有的物质都是世界不断重塑(ongoing reconfiguring)的一部分,包括人类。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主宰,而是和其他非人类物质一样,共同作用于世界的不断重塑。一如人类的认知(knowing)过程和存在的个体(being)是无法完全独立分开的,双方是相互理解和诠释对方的。认识实践活动不再只属于人类。能动力的产生也不再需要主体(agency without subject)。能动力不是一种属性,而是,内部活动的一种生成/动作(being/doing)。人类与非人类物质都能通过内部联动释放出能量,产生能动力,使得二者能够平等地进行着相互交涉、相互联系、相互交换物质。物质女性主义理论中人类与非人类都属于“物质”也隐喻着打破主体、客体二分中传统思维模式,也打破了男人、女人传统的性别划分,批判父权主义的思维模式,摆脱男权思想,为建立女性话语权,改变西方固有男权中心思想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道路。
物质女性主义以“有故事的物质”为切入点,重新思考了人类身体与非人类的物质,重新解读其物质性,其表现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女性身体的物质与非人类物质经过内部联动,交换、交涉、相互影响和改变对方的物质性。人类身体与非人类物质在内部联动中,一切都是不断的生成,形成动态的网络。《心灵的慰藉》就体现出这一观点。威廉斯家族长期居住在熊河候鸟保护区,该区处于美国核试验基地的下风口,深受污染。因此,居住于此地的威廉斯家族中多半的女性身体“物质”均受改变——患有乳腺癌。这个家族女性的命运时刻与大盐湖水相连。湖水水位的涨落,与该家族女性的身体、大地的“身体”以及熊河候鸟保护区鸟类的命运和存亡“不断产生内部联动”。在这里,湖、鸟、人、癌细胞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也不再是只有人类单向线性地作用于鸟、湖等非人类物质,而是人类身体和非人类物质形成动态的网络、糅合成不可分离的总体。盐湖、核试验物质不再是静态的、惰性的物质。自然也不再是人类剥削的资源、等待文化书写的白板。正如文中所说,土地、水和空气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能够自主地演义,与鸟类、人类经过内部联动,交换、交涉、相互影响和改变对方的物质性。本书中,特丽·威廉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将女性的悲剧与自然的悲剧糅合在一起,说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息息相关,正所谓“大地出了毛病,而我们也不会健康”(特丽·威廉斯,2010:307)。二是科技飞速发展,女性受到外来技术而改变本体的物质性,使得男女性别界限变得模糊。比如:唐娜·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一种有机体与机械的糅合。她提出通过技术和器械的移植缩小男性和女性在性别上的差距。比如,她提出“后性别世界的生物”,通过无性生殖技术则模糊了雄雌两性在生殖活动的分工,模糊了男女生理性别的界限,促进“新主体”的产生,为消除两性差异提供了新的可能。物质女性主义理论的“物质性”的新意义,不仅扭转了传统女性主义中一直存在的二元对立的偏见,也进一步改变一直以来深受二元对立主义影响的西方思想结构。
物质女性主义试图超越以前的本质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文化建构主义,以非二元论的方式去协调物质与话语的关系。它关注一切物质,包括人类身体的物质、非人类的物质、以及它们之间物质关系等。讲述物质与人、物质与物质、人与人之间物质的关系。物质女性主义通过重新关注“物重要性”,发现人类与非人类物质皆存在能动力,并不断地发生内部联动。世界万物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物质存在,所有的人类与非人类都是相互联系的动态现象。它们之间产生联系,形成关系网。现象产生意义,意义需要依赖物质现象。因此,物质与意义、物质与话语之间不再界限分明,而是合为一体,物质就是意义,物质就是话语。于此,它旨在消除二元对立,消除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对立,树立本体-认识论的观点。世界不再有主体与客体之分,打破传统世界中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整个西方文化固有的思想结构,提出物质、女性和男性均处于平等地位。
2.物质女性主义的缘起与发展
物质女性主义的缘起受多重因素影响。从理论的内容来看,物质女性主义深受身体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科学研究的影响(Alaimo& Hekman,2008:18)。2008年前,赛博格女性主义、科学中心女性主义以及达尔文女性主义等领域零散出现相关论文。2008年,斯黛西·艾莱默(Stacy Alaimo)和苏珊·贺克曼(Susan Hekman)编著并出版的同名书《物质女性主义》,奠定了物质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的地位,并迅速发展。
从理论的根源来看,物质女性主义缘起于新物质主义(neo-materialism or new materialism)。20世纪90年代,新物质主义由曼纽尔·迪兰(Manuel Delanda)和罗西·布雷多迪(Rosi Draidotti)提出,属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理论,也是一种文化理论。随后,各界理论家开始重新改写它的定义,并运用于各个领域,如:地质学、数学、文化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Dolphijn&Tuin,2012:38)。“新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概念框架和一种政治立场出现,它拒绝了语言范式,重点强调的不是架构而是渗透在社会力量关系中复杂的身体物质性。新物质主义避开了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提出几项主要的、与现代主义不同的观点。首先,主体和客体不是分离,而是纠缠在一起,通过内部联动形成现象。其次,物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一块白板等着人们去书写,而是不断变化的“生成过程”,这是物质能动力的具体表现形态。“物质和身体不仅是由语言、文化和政治的力量形成的,还由它们自己本身组成。他们认为身体或者物质是有着自己独有的、有区别的能动力,它既不是直接的或者偶然发生于人类意识,而是有着自己的动力和轨道”(Frost,2011:70)。这也表明,能动力是不需要任何器官指挥产生的,是人类和非人类都具有的表演能力。它能用来应对多种可能,并可以重塑纠缠。最后,与笛卡尔侧重语言的二元论不同,新物质主义通过探索一元论,探索二元论中忽略的物质,寻求物质与话语的平等地位。同时,这些关键概念及其相关的观点,如:能动力、物质、纠缠和一元论等,也成为物质女性主义的主要概念和内容,并在其基础上得到发展。但是,新物质主义观点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也为物质女性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埋下线索。新物质主义对于二元对立的观点持二分态度。比如:曼纽尔·迪兰等学者认为拒绝二元对立不应该成为新物质主义的关键点(Dolphijn& Tuin,2012:44)。以及它并没有完全把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唯物主义排除在外,而只是把它们的思想横向串联起来。新物质主义并没能完全从旧思想中剥离,也为物质女性主义继续探索新的一元论埋下伏笔,为挑战了女性主义的桎梏——二元对立思想奠定基础,为物质女性主义的萌芽播下种子。
从理论发展的趋势来看,物质女性主义是后人文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属于对后思想的反动和承续。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更多关注语言和话语。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他们要打破西方一直以来的语言与现实、文化与自然二元论思想;后结构主义也尝试解构西方传统意识形态中二元对立的关系。它们的优势在于动摇了一直存在于西方女性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不足之处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想一直排斥现代主义中的物质元素,坚持话语建构世界的观点,从而走向话语的极端。“尽管很多社会解构主义者的理论都支持物质现实的存在。这个现实经常是被塑造成一个完全与语言、话语和文化分开的领域。在实践中,分离的设想意味着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和文化研究几乎都是关注文本、语言和话语”(Alaimo& Hekman,2008:18)。因此,即使它提出打破二元对立的观点,却唯独保留的话语与现实的二元对立。近几十年来,开始出现关于“身体”的学术话语,如:朱迪斯·巴特勒作品也是关于身体的研究。然而,它们大多都偏离了身体的物质性,更多关注身体的话语分析。不过,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赛博格的演变,女性主义开始关注生物学和身体研究中“物质”的缺失,意识到了生物与身体中物质的能动力的存在,质疑根深蒂固的因果关系假设以及多年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分析的固化。物质女性主义是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建构世界观点的“反动”。同时,又是对它们提出打破二元对立的思想的“承续”。
3.物质女性主义发展、影响与局限
物质女性主义应时代而产生。当今世界新兴科技层出不穷,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之前的女性主义理论无法完全满足新时代所产生的复杂问题。这也使得一批女性主义者开始把目光从话语、语言建构转向身体和自然的物质,从而萌生了物质女性主义。物质女性主义理论对“物质”的重读大胆地挑战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人类中心思想,否定人类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能动力的主体,或者说,它发出了“能动力的产生不需要主体”的口号,提出建立人类与非人类物质的平等,跨进后人文主义的领域并促进后人文主义的发展。物质女性主义发展与局限并存,仍需要我们不断去实践和探索。
物质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生态意义。物质女性主义中自然不再被理解为消极的、被掠夺的资源,人类的身体也不仅仅是等着书写的白板。在这里,人类的躯体是属于“后人类”的,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形成艾莱默所提出的“交互躯体(trans-corporeal)——某个时空中人类的肉体都与‘自然’和‘环境’不可分离。正如《心灵的慰藉》中女性的身体与自然、环境的物质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形成能动的“交互躯体”。交互躯体作为理论观点,是身体理论和环境理论生产性地相遇和混合。它是跨越了物质与话语、自然与文化、生物与文本的领域的纠缠”(Alaimo,2008:238)。通过重新解读自然与身体的定义,物质女性主义改变女性和自然被置于二元论中低等的、被剥削的地位,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和自然,具有生态的意识,也拓展了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发展新方向。
物质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发展的物质转向。语言和话语转向一开始都把物质排除在女性主义之外。女性主义更是对物质主义谈虎色变,导致女性主义离“物质”越来越远。然而,有三个女性主义领域的学者——女性主义身体理论、环境女性主义和女性科学研究——开始转向物质,并致力于对物质世界创新理解及进行重新定义。物质女性主义打破固定概念模式,为所有理论概念都提出不确定性,重新把人类身体和非人类物质拉回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再一次思考和解读其意义。同时,一些理论家唐娜·哈拉维、维奇·科比(Vicki Kirby)、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和凯伦·巴拉德等通过重读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理论家的作品,在他们基础上以更具生产性的方式重新解释了“能动力”“思想”“身体”和“自然”的活力等概念,把它们拓展到物质领域,提出女性主义的“物质转向”。它清晰地阐释生物学/社会(社会性别/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论,并协调了后结构主义遗留下来的物质-话语二元对立的问题。为解决女性主义关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歧问题,它提出本体-认识论,从非二元论的视角使得“物质-话语”和“文化-自然”得到协调。
物质女性主义的物质性理论出现和发展应历史而生,并对其他理论有重要影响,比如:科学研究、环境女性主义、身体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残疾研究、种族和伦理研究、环境正义、(后)马克思女性主义、全球化研究和文化研究(Alaimo & Hekman,2008: 9-10)。物质女性主义理论中,男女基于传统观念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家庭中的所有差异及距离慢慢在缩小、甚至消除。它通过超越以往传统不变的概念对身份的认识,如以民族、种族、国别、性别和阶级来界定人的优劣,从而为人类与非人类物质建立一个多元的、没有清楚界限的和平等的地位。这也为以上理论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的维度。
目前,物质女性主义的继续发展也有它的困难与局限。物质女性主义发展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内容,都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跨文化性和跨国性。研究范围之广,涉及内容之多、跨越学科之大,并非一人之力可以承担,需要多方的合作与支持。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内容共享范围扩大,希望这些问题尽早得到解决。其次,物质女性主义过于依赖科技的改变来解决女性主义的问题。科技虽然能改变女性身体的物质,部分解决两性的、种族的问题,但是,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还需得到政治上的关注与援助,需要女性精神与物质的自强。最后,物质女性主义的研究将会面临巨大的伦理问题。如今是混合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它的发展伴随着技术与技术的融合,以及人与技术的融合。它既为人类带来自身强大感,也造成虚拟与身份错乱,科技与人类、人类与非人类孰为主宰,物质是否具有思想等问题,以及何为人类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