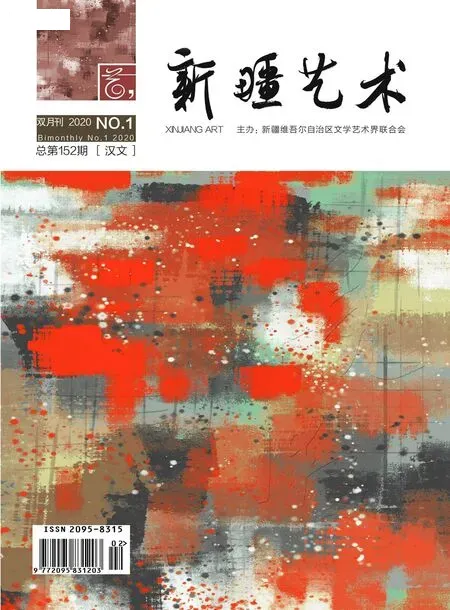民间·民族·哲学·艺术
——论刘慧敏童话的多元美学价值
□ 王 欢

除了儿童文学作家之外,刘慧敏还有一个身份是《江格尔》研究者。刘慧敏自小生长在新疆天山脚下的伊犁河谷,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情同一家,她对蒙古族文化充满景仰和深情,熟读并深谙《江格尔》,并历时多年将《江格尔》中的英雄故事以简洁生动的语言重新提炼撰写,加入作家的情感和理解,并配以画家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插画,汇聚成十四本《江格尔》绘本故事,引领广大少年儿童读者走进民族的历史,领略到英雄史诗豪迈、壮美的强大魅力,也为古老的民族史诗赋予了新的生命,令其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更好地传承下去。或许是《江格尔》中众神崛起、征战四方的英雄传奇开启了作者对人类童年时代的遐想,又或许是草原民族那浪漫顽强、率性自由的性情与生活方式早已沉潜入作者的生命,刘慧敏的原创童话也呈现出特别的审美风貌。
一、“民间”与“民族”相得益彰
刘慧敏童话乍一看很像民间童话,她运用了很多民间童话的原型、母题、结构模式等艺术特征。比如故事背景,《远方》是发生在人神混居的古代和硕草原,《巴根与查干》发生在古老的草木时代的精河草原,《恰德尔和玛依拉》则是在很久以前布尔津巴彦阔克阿德尔山青青的草场上,这和我们熟知的民间童话“很久很久以前”的时间设定是相一致的,十分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特征,对葆有原始心性的儿童特别有吸引力。但如果你据此推断刘慧敏童话属于民间童话的范畴,那你就错了,它们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作家原创童话。
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源流。几乎所有国家、民族的儿童文学都起步于对民间文学的改编。而民间故事、民间童话又多意味着情节单纯、人物扁平和故事模式化。当现代作家在创作中极力摆脱民间文学的痕迹时,刘慧敏却逆流而上,用民间童话的外衣来包裹她全新创作的故事,因为她明白“民族”与“民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用“民间”这个精美的旧酒壶,才装得了原汁原味儿的“民族”美酒。
刘慧敏的一系列原创童话都散发着浓郁的“民族风味儿”。主人公多用蒙古族或哈萨克族的名字,《远方》里的达西、阿爸、额吉和黑萨满,是蒙古族的称谓和身份;《巴根与查干》里的巴根是土尔扈特部落的牧马英雄,仙女不是达芙妮也不是嫦娥,而是用了一个好听的蒙古姑娘的名字:查干;“恰德尔”和“玛依拉”则是哈萨克族的名字。《巴根与查干》的故事发生在古老的精河草原,在这里人与天鹅、白鹤、麋鹿、野驴为伴,这些都是新疆当地的特有物种;《寻找身份的人》中出现的冬窝子、梭梭柴、马头琴也极具地域和民族特征。《恰德尔与玛依拉》的开篇,巴克斯用羊拐骨为玛依拉占卜,后来在《消失的黄金部落》中用四十一粒羊粪为其算命,恰德尔凭借一颗狼牙和一颗狼髀石去寻找玛依拉的心,羊拐骨、狼髀石、羊粪等都是草原上的常见之物,既用于少数民族神秘的占卜之术,也可以是草原儿童的天然玩具。玛依拉出生后,“马拉提汗高兴地大摆宴席,所有的阿吾勒巴斯、阿克萨卡勒、乌露巴斯都送来了丰盛的礼物,整个牧场充满了欢乐的味道。”这无处不在的民族风物,传递出浓浓的草原气息。
更可贵的是,作者不是仅仅将这些“民族特色”拿来作为文章的装点,而是将“民族性”深入到文字的肌理之中,甚至化作自己的思维方式。比如作者将富饶的家乡比作佛祖的宝瓶,是草原民族常用的比喻;“一碗马奶酒的功夫”也是草原民族描述时间的方式。这样的比喻收放自如,这得益于她在民族环境中的多年浸润和对民族文化的探求,当然,还有她选择了“民间”的叙事策略,令民间元素与民族元素相得益彰。
二、悠远的意境与深邃的哲思
刘慧敏童话的文字清浅,内蕴较深,有一种过目不忘的力量,不是浅显的惩恶扬善,而是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远方》是刘慧敏哲学童话的代表作。故事很简单,讲少年达西渐渐长大,对外界和未来充满好奇,独自踏上去远方的旅程。文中写到那“携带着远方气味的风,常常吹得他躁动不安”,准确地刻画出每一个生命在成长壮大时那原始而强劲的悸动和渴望。“远方”象征着理想、追求、幸福和选择。一般的童话寓意到达这一层就结束了,而这仅仅是《远方》的开端。将《远方》的表层故事剖开,我们看到作者逐层深入地探讨了关于“存在与追寻”的四个哲学层面的问题。第一层,达西出发前,阿爸嘱咐他过河时不要受黑萨满的物质诱惑,“否则会被引上他的远方,错过了自己的远方”。将远方划分为“自己的”和“他人的”,这就已经具有了哲学意味。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别人的路再令人艳羡也不是你的路,你代替不了别人的生活,别人也代替不了你的幸福。第二层,黑萨满问达西要去什么地方,达西并不清楚,黑萨满嘲笑达西:“你要去一个你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方?”而达西平静地回答:“是的。如果我知道了远方的一切,我就在家喝奶茶了。”达西与黑萨满看似简单而矛盾的对话恰恰揭示了生活的奥秘所在,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未来正因未知才充满吸引力,这也是人生的魅力所在。第三层,黑萨满认为弟弟当年抢走了他的新娘就是抢走了他的远方和幸福,始终活在仇恨和诅咒之中。作者借黑萨满的遭遇提出了一个人生路上的难题:假如别人抢走了你的远方怎么办?文末黑萨满的幡然醒悟告诉了读者答案: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远方并不是只有一条路,与其消极地损耗生命和怨怼他人,不如选择“放下过去”,主动地创造未来,将命运和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第四层,“远方”有没有终点?作者揭示了“远方”的终点是家,人在看遍风景历经沧桑之后,最终让他感到幸福和内心真正的安宁的,还是家。从家出发去寻找远方,最后又回到家,这就是人的一生一个完整的轨迹,即“寻找—成长—顿悟—回归”的过程。作者讲述的虽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却能解开现代人的心结,几句最质朴简单的话语,就直击人心,因为回到生命的本原,才能参透生命的真谛。
三、奇谲的想象与瑰丽的语言
想象是童话的命脉。刘慧敏擅长想象,她的想象不同于一般童话常见的“鸟言兽语”或“魔法冒险”,而是糅合了“民间”、“民族”、“哲学”等多种文化背景之后产生的超越儿童世界的想象。
《死亡之鸟和舌法神》是刘慧敏最奇谲诡异的童话,不光意象奇特,还以上帝视角揭破了人类生存的迷思。三名游泳运动员要游过喀纳斯湖去取金芙蓉的种子,其中“歪鼻子”生性消极软弱,承受着同伴“尖脑袋”恶毒的言语攻击,当他产生“死了又如何”“生活的意义何在”的念头时,死亡之鸟钻出了水底,起初是“湿漉漉一只丑鸟,只有一只眼珠,没有羽毛,用一只眼珠定定地盯着人”;当歪鼻子第二次想到“还不如死了呢”,那只黑鸟“又长出了一只眼睛,射出冷光”;歪鼻子第三次想到死亡时,黑鸟的翅膀上长出了粗壮的黑色羽毛;第四次,黑鸟一下子长成了巨鸟飞到他身旁,歪鼻子着了魔般向它的背上爬去……作者将人内心隐秘的心理变化过程“显形化”了,虽然全篇笼罩着死亡的恐怖和阴影,但对孩子来说却是一次触目惊心的生命教育。
刘慧敏还擅长造境。新奇的想象和她瑰丽的语言一经组合,便产生出令人惊艳的化学反应。试以《远方》中的一句为例:“汗国的大萨满有一个银盘,月圆的时候,放入牛初乳和红色的雪莲花,就可以再现过去之事。”首先这是一个宗教仪式,具有民族色彩;时间是月圆之夜,充满神秘色彩;使用的贡品是牛初乳和雪莲花,具有地域色彩;在黑夜背景下银色、白色、红色的调和,又具有美学色彩。这明明是作家编造出来的一个施展魔法的方法,却令人忍不住信以为真,并为作家构织出来的这样一个空灵绝美的意境而沉醉。
民间、民族、哲学、艺术是刘慧敏原创童话的四个关键词,也构成她童话的特殊美学风貌,期待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多的价值,也期待她的更多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