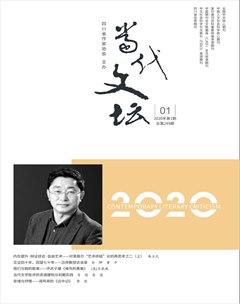论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
洪治纲
摘要:文学批评之所以常常受人诟病,主要是太多的批评文章缺少必要的问题意识,只是罗列一些所谓的特点,很少从“为什么”角度进行有效的追问。正常的文学批评,不应该离开“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个维度的理性质询,这是批评家将问题意识贯穿始终的审美阐释和艺术评判。问题意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体现了批评家的主体精神建构,还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经典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意识;创作实践;审美判断
近年来,我在为学术刊物做论文评审的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评论文章的基本模式是——从评论对象中归纳几个所谓的“特点”,然后顺便做一些古今或中外的关联性分析,洋洋洒洒,看似视野宏阔,阐释丰沛,可是我读后总觉得意义寥寥。有时深入地追问一下,这些所谓的“特点”,也未必是批评对象独一无二的特质,只是作者无视其它创作而盲目得出的结论。这类评论的真实用意,其实只想为评论对象增添几笔自我认定的亮色,很难看到作者的审美眼光和批评情怀。另外,每逢文学评奖,便有约稿者找来,让我根据当年写批评文章质疑文学奖的思路,再谈谈最近文学奖的评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这两点其实都聚焦于一个核心:文学批评越来越缺少问题意识。这里,我使用“缺少”这个词可能有些暧昧,更科学的说法,应该是批评越来越回避问题意识。因为在太多的评论文章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作者不想追问,甚至连最简单的“为什么”都不想回答。你评价这部作品是一座关于什么的丰碑,那么你至少要回答一下“为什么”。既然它是一座丰碑,它应该成功地突破了哪些重大创作障碍,成为文学史中的某种标杆;既然它是一座丰碑,它应该对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某些前瞻性的经验,体现了某些常人难以企及的审美思考。没有这些必要的回应和分析,只是对作品中的几个特点进行简单的归纳,便自信地给出这样的判断,至少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说服力。遗憾的是,这种没有任何问题意识的文学批评,如今随处可见。所以,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像中国足球,谁见了都可以轻松地唾弃一下。
没有问题意识的批评,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廉价的、可无限复制的技术操作。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文艺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就是因为它始终离不开问题意识,离不开批评对创作实践中各种问题的深入追踪。从早期的社会历史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到后来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義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文学批评一路走来,诞生了很多重要的批评理论。无论这些批评理论成熟或不成熟,它们都对文学理论的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具体的文学批评,便没有各种批评理论,而没有丰富的批评理论,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条逻辑链不言自明。
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一下,这些批评理论又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当然是具体而有效的批评实践。如果再继续追问:什么样的批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一种批评理论?各种暧昧的回答可能随之而现。譬如,有人会认为,有些人文科学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批评理论的诞生,像精神分析批评理论,就是源于弗洛尹德的精神分析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则完全依赖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也是来源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农的“属下理论”和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更是依托于女性主义的性别文化理论等等。这种渊源性的梳理,似乎可以说明,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诞生,并非完全是文学批评实践的结晶,而是人文社科研究相互影响、彼此并构的结果。
我无法认同这样的判断。理由是,任何一种他律性的理论成果,如果能够在自律性的范畴内确立自身的理论价值,唯一的检验路径就是具体的、有效的实践。文学批评也不例外。当我们在使用社会学、文化学或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进行文学批评时,一定是觉得它能够解决一些特殊的创作问题,而不是从“此理论”到“彼理论”的简单旅行,更不是一种理论之间的互置。当退特将物理学的“张力”概念引入诗歌批评时,是因为他发现了诗歌中始终存在着一些相反方向的情感因素,共同支撑了诗歌的丰富内涵。如果没有具体的创作问题存在,退特对张力概念的袭用就没有价值,也没有生命力。同样,正是因为大量小说创作中的人物言行,存在着无法用理性逻辑来阐释的非理性形态,或者有些作家的创作中始终存在着某些隐秘的、非自觉的精神因素,才使我们在运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批评时,获得了别样的阐释效果。这也就是说,每种其它领域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够演化为文学批评理论,都是因为它确实有效解决了文学批评对具体创作问题的精确诠释。如果文学批评不能发现文学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持续性的关注和探讨,如果不能从问题深究中提炼出一般性的规律,即使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多么丰富,也未必能转化为文学批评理论,并指导人们很好地提升批评的效度。
我们不妨从新批评的形成过程中,看看文学批评是如何从问题意识入手,来提升文学批评效度的。在新批评出现之前,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作家与作品之间的从属关系。人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依然会自觉地立足于诗人或作家的个体心性进行分析,这导致人们在评判一些开拓性、异质性的作品时,总是将创作主体与文学传统割裂开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具体创作的审美价值。针对这一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诗人艾略特便发表了有针对性的重要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明确提出诗歌的非个性论观点,认为诗人不可能超越传统,“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①文学批评不能只关注诗人的创作个性,而应当着眼于诗歌本身,即具体作品的内在审美特质。随后,瑞恰兹针对具体诗歌作品中的语言,又将语义学成功地引入文学批评,有效阐释了诗歌的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本质差异,从而为诗歌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在《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瑞恰兹明确指出了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差异在于,科学语言求“实证”,是可以通过实验等方法得到验证的“真陈述”;文学语言求“情感”,是一种仅在文学文本内部有效的“拟陈述”,它不能直接对应现实,但它引人产生联想,引起情感反应。在瑞恰兹那里,“复义”被视为是文学语言的必然结果,因此,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就是对其作语义层面的修辞性分析。
无论是艾略特还是瑞恰兹,他们之所以为新批评提供了开拓性的研究方法,关键在于他们始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围绕创作主体与具体作品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解决了文学批评对于具体作品的有效性。这种“去作者化”的创新思维,无疑为新批评打开了一条文本批评的通道。所以,紧随其后的兰色姆,便在《新批评》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本体论批评”的理论构想。燕卜荪则更进一步,在《含混七型》中细致地归纳了诗歌语言所拥有的多义性或歧义性,以及在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态度或感情。燕卜荪甚至说,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就会产生语言的含混现象。②这种语义上的“含混”就是诗歌的基本特质,文学批评必须关注不同诗歌文本的词语中所承载的联想、暗示、反讽、隐喻、含混和悖论等语义或修辞要素。沿着这一路径,新批评最终将文本细读提升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手段。
无论人们对于新批评有着怎样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种开拓性的批评实践,它的本体论批评、含混美学、张力结构、反讽以及文本细读,都是我们至今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经常动用的理论方法。也就是说,新批评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最终试图解释一些具体作品(尤其是诗歌)的批评方式。从这一批评理论的具体发展过程来看,没有问题意识,也不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批评实践。
无须讳言,并非所有的文学批评都需要解决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既没可能也没有必要都肩负起某种批评理论的建构任务,因为这类批评显然已经超越了大多数文学批评的职责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就可以放弃任何问题意识,只需操弄一些人畜无害的感想。说到底,文学批评离不开分析、阐释和评判,无论是针对具体作品、某个作家还是某种文学现象,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专业性的批评,就是要体现一个专业读者在阅读思考之后的审美发现。这个发现,不是简单地找出其中的几个特点(当然,真正的特点提炼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批评家研读具体对象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最渴望谈论的想法,它体现了批评家意欲发言的立场和方向,折射了批评家对某个问题的关注焦点。“为什么”则是沿着“是什么”的路径,认真探析批评对象之中所包含的主体思考,尤其是创作主体对历史、现实、自然或人性的不同探求,以及这些探求的价值意义或局限。作家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時,都会试图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看法,他的文化视野、思考深度和叙事能力,都会直接影响这种表达的深刻性。批评所要追问的,正是这些探索和思考有没有价值,是平庸、浅薄还是独辟蹊径。“怎么样”是在完成“为什么”的论析之后,在审美层面上的艺术评判,即它动用了哪些审美策略,运用了哪些表达手段,体现了怎样的艺术效果。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很多作家的创作谈远比作品本身要写得深刻,恰恰就在于他们的表达能力、作品的艺术效果与主体意愿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有趣的是,很多批评文章总是以作家创作谈中的相关表述作为依据,替代自己对“怎么样”的认真评析,其结果自然是难以令人信服。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和“怎么样”,我以为,这是所有文学批评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体现了批评家最基本的问题意识。
如果我们认同批评就是通过具体的文本,让批评家与作者在审美上进行一种隐秘的对话或心智的交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承认,“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从事文学批评中无法绕过的首要问题。它是批评家在研读批评对象之后,首先要确定的立场、观点和看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什么”没有绝对统一的正确观点,套用新批评的理论,完全允许必要的误读,但“是什么”是批评家的判断和看法,它亮出了批评家所关注的重要目标,也展示了批评家与批评对象进行智慧交锋后的锋芒之所在。读过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市井生活,又读过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日常,当我们再读金宇澄的《繁花》时,有什么独特的感受和思考?人们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评论《繁花》,但我相信,每位批评家所亮出的“是什么”一定不一样,或内涵,或结构,或语言,总之,他一定有一个关注的重心。这个重心,确立了他进行批评的主攻方向,也体现了他在研读《繁花》之后所聚焦的核心问题。如果一篇批评文章在“是什么”上暧昧含混,左摇右摆,人畜无害,在接下来的分析和阐释中,将注定会混乱无序,四处挠痒,跟着感觉走。事实上,在给一些刊物的匿名评审中,我常常碰到这类文章。它们看似维度颇多,旁征博引,理论厚实,却始终看不清作者意欲表达的观点,用奥登的话说,“我们从他的引文获得的教益要比从他的评论获得的教益为多”,这类批评的价值令人生疑。在奥登看来,真正的批评应该让我们获得卓越的洞见,“如果一个批评家所提出的问题是新鲜和重要的,则他就显示了洞见,无论我们多么难以认同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解答。绝大多数读者可能都难以接受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里所下的结论,但是,一旦我们读罢这本书,我们就再也不能漠视托尔斯泰提出的那些问题。”③
无论立足于哪种角度的批评,批评家在亮出“是什么”的同时,不仅表明了自身的评判立场和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他也展示了自己所关注的目标之重要性。在给《当代文坛》主持“非虚构写作”的评论专栏时,我曾按照非虚构写作研究的不同角度,设置了诸多“是什么”之类的话题。譬如,非虚构写作通常都隐含了一整套别有意味的叙事策略。尽管它们叙述视角单一,结构也并不复杂,基本上遵循线性发展的故事走向,但是,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它们依然动用了一系列特殊的叙事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第一,在细节上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与虚构,最大程度上追求现场感,作家的所有主观思考随现场而产生,现场成为作家想法伸展的实证性依据。这种依靠虚构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现场,为什么轻而易举地构成了作家主观思想的证据?第二,无论是书写现实还是探索历史,非虚构写作总是极力追求“揭秘性”的审美趣味,似乎真相只存在于作家的笔下,其它现象或事实都具有遮蔽性。这种追求,隐含了哪些内在问题?第三,非虚构写作在叙事上极为重视读者的代入感,不断引导读者参与叙事现场,以情感共振的方式,最终实现作家主观思想的接受。这种叙事策略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一种反艺术化的叙事逻辑?我们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设计,其实就是希望让有关批评聚焦到一些核心问题上。
在确立了“是什么”之后,文学批评接着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的问题。这个“为什么”,包含了批评家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深度探析。第一,批评家要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论证自己在“是什么”的判断上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很好地回答自己为什么提出这种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借助具体的创作,在丰沛的归纳、分析和推衍过程中,很好地阐明自我判断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如果你认为这部作品是一座丰碑,那么你就必须立足于作品的解析,在相对可靠的纵横坐标系中,充分证明它无论是在作家个人的创作中,还是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确属一座艺术的丰碑。否则,就意味着你最初的判断只是信口雌黄而已。这是考验一个批评家专业能力和解析智慧的关键之所在。为什么有些批评文章显得非常草率或武断,就是因为它们只亮出了“是什么”,却从没打算回答“为什么”,套用蒂博代的话说,这类批评家只是喜欢充当文学的法官,而不愿做一个诚实的检察官,毕竟检察官需要用大量的事实和缜密的分析来论证自己的任何一种指控。④
第二,批评家还要深度探析作家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即“是什么”的问题)。既然我们从创作中发现了作家意欲表达的核心意图,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他在创作中对此提供了哪些独特而又有效的思考?或者,他在哪些方面又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如果将这个核心意图放在特定的文学境域中,它是否有价值?价值几何?说实在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不仅存在着大量平面化、同质化的惯性之作,而且存在着很多看似异质性突出、实则思想苍白的伪深刻之作。在有些重要作家的创作中,一些细节相同的叙述,甚至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新作之中。我曾经在评述那些“底层写作”的作品时,就调用了大量的作品来说明“底层写作”的模式化、经验化和道德化问题,并试图深入探讨作家对现实生存思考的孱弱和精神的慵懒症——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⑤但遗憾的是,我看到太多的评论文章,依然在为这类并无多少思考深度的创作高唱赞歌。究其因,我以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评论喜欢就事论事,并没有从创作主体的审美意图和思考力度上进行必要的质询。
在完成了“为什么”的探析之后,批评通常还需要回到“怎么样”的层面上,对作家的审美意图和表达效果进行艺术上的评析。如果说“为什么”是为了揭示批评对象内部不易被人察觉的思想内涵,剖析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与生存思考,那么“怎么样”就是要评析创作主体借助哪些表达策略和艺术手段来传达自己的艺术思考,这些策略和手段在表达主体思想的过程中具有哪些审美效果。一句话,“怎么样”需要解决的是批评对象的艺术特质及其价值。譬如在评论“寻根文学”时,当我们揭示了它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各种现代反思时,我们还必须回到“怎么样”的层面,充分评析他们所动用的各种现代叙事手法及其表达效果,从而得出哪些寻根文学更具有开拓性的艺术价值。事实上,在当年的寻根大潮中,确实有一些迷恋于“怪力乱神”的民间传奇性叙事,一直被评论家排除在“寻根文学”之外,如贾平凹的《五魁》《美穴地》之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李庆西直言不讳地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批评的难度,说到底,就是既要发现批评对象内部所隐藏的独特之处,又要从内涵与形式上充分诠释这种艺术探索的价值意义,不认真分析“怎么样”的问题,将很难从艺术的自律性上作出科学的判断。
批评的路径多种多样,批评的方式更是千变万化。但批评之所以成为批评,最核心的要素就是问题意识。它是批评家与身俱在的专业素养,也是文学批评被称为“审美发现”的基本保障。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其实就是批评家根据艺术自律性的要求,通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审美眼光,对批评对象进行卓有成效的、富有洞见性的审美阐释与评判。它不是像唐·吉诃德那样,整天拿着长矛四处乱怼,而是要像牛虻那样,看到目标之后便紧盯不放。它拥有批判、质询和解构的天职,同样也拥有赞颂、首肯和捍卫的权利,只是,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批评家的问题意识之上,并通过精辟而又令人心悦诚服的阐释来实现。
问题意识并非一种外在的苛求姿态,而是批评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批评主体的精神建构及其专业素养。——当然,讨论批评家的精神建构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危险的事情,但是批评家肯定不是怀揣短枪或匕首的杀手,整天喜欢杀人越货;也不是手持鲜花的门童,见到谁都献上一支红玫瑰。他应该类似于江湖中的侠客,内心里时刻装着有关文学的“正义法则”,永远坚持除恶安良的行动准则。这种所谓的“正义法则”,涉及他对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也包含了他对生命与人性的敏锐洞察,构成了其精神建构的主体部分。我始终认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并非主体与客观的关系,而是主体的间性关系。这种主体间性,可以确保批评家与批评对象维持着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一种有关思想和艺术的碰撞和交锋的状态。也正是这种主体间性,才能有效规避某些捧杀或棒杀的批评,规避某些人云亦云或哗众取宠的跟风式批评。没有主体意识的批评,注定不会有艺术的洞见,因为它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立场和评析目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深究批评家的主体意识,我们就会看到,他在批评中的维护或否定,都一定带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只有将问题意识放在前面,他的批评才能展示自己相对稳定的评判标准。无须讳言,并非每位批评家的问题意识都是科学的,都具有前瞻性,但无论批评家所秉持的问题意识存在着怎样的偏差,都远胜于没有问题意识的批评家。
对于艺术自律性的建构与完善,批评的问题意识同样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记得十几年前,文艺理论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争,本质主义认为文学存在着某些亘古不变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文学理论的基石,但建构主义认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一些恒定不变的属性,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会出现相对稳定的性质,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很多特性都会处于变化之中。这场争论无疑涉及文学理论建设的价值与方法,绝大多数学者最后都认为建构主义更为科学也更符合实际。我同样也持这种观点,理由之一是文学理论本身确属一个不断建构的产物,而且这种建构本质上离不开文学批评的长期实践。没有文学批评的深度参与,或许就没有一个相对健全的文学理论。如果有,这种文学理论基本上属于理论之间的旅行或移植,即从其它领域的理论中移用而成。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形成,既不可能完整全面,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须对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创作实践进行不间断的跟踪、总结和提升,才能一步步地得到建构。这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理论的形成,永远离不开文学批评紧随创作实践的各种艺术总结。当然,文学批评所做出的这些总结,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需要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让批评家敏锐地发现一些创作实践中的特殊动向,并及时找到一些具有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美学取向,为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完善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对喜剧与悲剧的理论建构,到中国古代的无数诗话,这些具有元典意义的理论,其骨子里都脱不了文学批评的痕迹,或者说就是文学批评系统性总结的结果。
从文学经典的生成来看,问题意识也是文学经典得以建构的重要推动。有很多人喜欢从本质主义角度讨论经典文学,认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天生具备了一系列经典化的艺术成分,诸如永恒性的主题、丰实的情感内涵、高超的艺术技巧、多元的阐释空间等等。但我觉得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按照经典的基本释义,经典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理由去反复阅读的作品,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根据自身的审美趣味和人生体验不断批评和阐释出来的,没有批评的长期参与,没有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反复解读,它就不可能成为經典。李白和杜甫的诗如此,《红楼梦》亦是如此。而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在跨越时空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聚焦于某些作家和作品,正是因为批评家们发现了其中存在着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者前人没有发现的审美内涵。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批评很难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也很难拓展一些作品的解读空间,经典也就未必能够形成。
更进一步说,正是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各种经典才能在不同的时代赢得不断的关注,从而为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照。就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史而言,其建构法则终究离不开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他们犹如历史长河里的一个个航标,确定了文学史的主航道。即使我们从“潜在写作”的路径上来重新梳理文学史,也依然绕不过那些具有共识性价值的经典作家或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同样对文学史的建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潜在作用。
当我们在讨论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时,我们也不能否认,问题总是存在着真伪之别。真正有效的文学批评,当然是建立在对真问题的求索之上,而不是随意虚设一些伪问题,而事实上,批评常常会针对一些伪问题而喋喋不休。这些伪问题,其实就是经不住具体的创作实践来进行反证的问题,或者是那些与具体创作并没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不过,这涉及另一个话题,不说也罢。
注释:
①[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② 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③[美]布罗茨基等:《见证与愉悦》,黄灿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④[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9—150页。
⑤洪志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