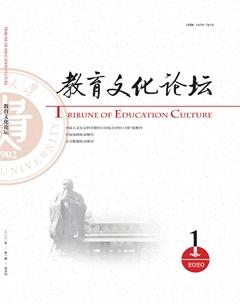日本侵华时期汪伪政权统治区学校教科书探析
吴洪成 于明珠
摘 要:汪伪政权为配合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需求,积极秉承侵略者意旨,在统治区制定并实施奴化教育政策及课程,建立教科书编审机构,加强学校教科书的修改、编审活动。这些教科书凸现出日本奴化教育的特色,对中国青少年学生产生了思想控制及精神毒害,对此应有警醒的认识,并加以深刻清理。
关键词:日本侵华时期;汪伪政权;奴化教育;课程设置;学校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0)01-0009-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0.01.002
An Analysis of the School Textbooks by Wang Puppet Government over the Period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U Hongcheng,YU Mingzhu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China, 071002)
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Japans full-scal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actively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enslaving education policies and courses in the ruling are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gressors intentions. Also, the puppet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extbook editorial institutions to strengthen the revision and editing operation of school textbooks. These textbook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enslaving education which exerted an extremely negative ideological influence on Chinese young students. The study is meant as a call for the depth of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extbooks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se books should be thoroughly cleaned up.
Key words: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ang puppet government; enslav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school textbook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一年多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调整对国民政府作战策略,1939年成功诱使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叛国,脱离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受侵华日军羽翼保护,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主席兼行政院长。从此,汪伪政权作为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怪胎”,日本扶持最大的傀儡政权登上历史舞台。其核心统治区域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市,但势力影响则辐射至华北、华中等地区。日本侵华期间,始终将“思想战”“文化战”放在战略高度,汪伪政府更是将学校教育的奴化渗透与管理视为实行“和平、反共、建国”纲要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本文在梳理汪伪统治区奴化教育政策、学校课程设置情况下,探讨学校教科书的编审、内容设计,并分析其中的主要特点,深刻揭露汪伪政府秉承日本意旨对青少年实施奴化教育的实质。
一、 汪伪政权的奴化教育政策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为协同日寇对华军事侵略的政治需要,在“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殖民教育方针,并在沦陷区大肆推行。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伪政府完全顺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战略步骤,制定的教育政策由战前的“和平反共建国”转变为“完成战争之使命”,在相应中国沦陷区前后两个阶段对奴化教育政策作了调整,并在学校课程设置及教科书编写中深深地打了上烙印。
1.太平洋战争前的奴化教育政策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为满足日本侵略戰争和殖民统治的需要,1939年8月,汪伪政权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会议通过了“政纲”。教育部分主要包括:“发扬民族固有之文化及道德,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强行纪律训练,养成健全国民,重编教科书,尤其强调教育重心在于吸收适用于国情之外国文化”“睦邻政策之精神”以及训练专门人才“以适应新中国之建设”[1]。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汪伪政权亲日思想的教育渗透及具体化。
1940年3月23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的讲话,强调将对国民心理进行“根本的改造”确立为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主张“心理建设”就是要强化“亲日和平教育”。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政纲第十条更加明确表述为通过施行“反共和平建国”教育,以实现清理“浮嚣空泛”的学风[2]。这里所特定的“学风”指的是学生关心国家要事,实则是抗日反汪的斗争。很明显是要让广大青少年在日伪构建的知识体系里接受影响,进而沦为受殖民统治奴役的工具。同年8月制定的关于中小学“训育方针”中规定,训练、培养学生具有“和平亲善敦睦友爱之精神”“忠恕诚实礼仪廉耻之美德”,更明显反映从小学开始,教育的核心思想就离不开“亲日”和“复古”。
以上所述奴化教育政策的精髓同样渗透在大学教育之中。1940年8月11日,汪精卫在会见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和副校长钱慰宗等人时,要求中央大学要更正青年学生的错误思想,须加紧亲日和平教育[3]。汪伪政府内外政策秉承着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推行奴化教育政策,在学校课程和教科书相关方面据此要求下了很大功夫。
2.太平洋战争后的奴化教育政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汪精卫便在《中华日报》公开宣称:教育体系归入战时轨迹,“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4]。为此,教育政策也必然以“完成战争之使命”为核心,为“大东亚战争”服务。1942年,汪伪教育部在苏州专门举行中学学校以上的训育人员会议,强调训育以“军事化、劳动化”为原则,对学生加强训练,使他们达到“生活一致,思想一致,行动一致。”[5]在具体的训育中,则效法德国和日本模式,在青少年学生中广泛建立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943年2月18日,汪伪政权颁布《中国青年团童子军思想训练纲要》,要求各“国立”学校实际施行。6月10日,汪伪政府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叫嚣学校师生应“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并勉励达到“思想之清厘,观念之肃整,与科学技术之发展。”[6]33从以上汪精卫屡次颁布教育政策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毒害学校师生的思想意识弥漫其中,并在沦陷区各伪政府所推行的教育制度中得以充分展现。
为加紧适应教育体制的需要,汪伪政权还在统治区实施社会教育来拓展教育方式,进一步拓宽教育的空间。从一开始的“和平反共建国”到强调“改造国民心理”,从实行“亲日和平教育”再到《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的规定,汪伪在沦陷区文化教育领域留下了不可忽视的踪迹。奴化教育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以華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野心和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服务的。汪伪政权在其存在的5年4个月里极力推行奴化教育,而且将这种教育政策渗透到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的内容中,以此对其统辖区域学校的教科书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
二、 汪伪政权奴化教育背景下的课程设置
汪伪政权所推行的奴化教育课程及其教学内容,完全是与其奴化教育方针政策相协调和统一的。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着重强化日语及训育等奴化学生的内容。此外,汪伪政权还开设文化复古课程,其间有意篡改历史史实,妄想以封建复古思想瓦解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降低民众抵抗日伪统治的心理意识。
1.重视日语课程
1940年7月,日本兴亚院文化局局长和使馆书记先后致意汪伪教育部,要求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并以此视作亲善日本真诚与否的一项指标。为表达“亲日”诚意,汪伪政府教育部按照日方旨意,批准在初中以上学校开设日语课,并列为必修课。但日本统治者并不满足,再三宣称:“语言学从小学一年级即为开始乃为最上策”[7]。于是,伪教育当局又马上出台《小学校日语课程调整原则及过渡办法》,主要内容如下:所有乡村及城市小学前三年日语课程必修,后两年城市小学增加日语课程;目前尚未实施日语教育的小学应该在五、六年级加授;三年以后无论是城市小学,还是农村小学,都应一律开设日语课程。
汪伪统治区所辖的教育部门百般献媚,依据符合日本语言文化侵略的举措,对日语教学做出相应调整,无论是教学时间的安排,还是课时的比例,学校课程计划多半向日语课程倾斜,甚至高居首位。一些中学日语课每周多至6小时,甚至部分小学也高达5小时。例如苏北第一师范学校,1941年11月下半年课程表中有关科目设计如下:每周日语6小时,国文4小时,修身、劳作各3小时,生物、历史、地理、农业、音乐、美术、体育各2小时,生理卫生、矿物、珠算、国术各1小时。江苏省兴化县伪教育局明确规定:“日语课同国文、英文、数学一起定为四门主课,若四门主课中有两科列入戊等或三科列入丁等者,不予毕业或升级,并无补考资格。”[8]在其后的实际教学中,由于汪伪当局对英美现代民主教育思潮采取坚决扑灭的极端措施,英语课程在学校中很快就被日语所取代,日语成为最重要的课程,与国文、数学学科并驾齐驱。
从上述可知,汪伪当局在学校广泛开设日语课,意图让中国学生自幼即淡化本民族语言,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日本历史文化熏陶,养成日语表达思维习惯;学校营造沦陷区学生的日语沟通交流环境,从而使他们逐渐接受日本侵略论调与价值观念,并进而发生立场错位,以日本侵略者的逻辑维护战争掠夺的殖民统治利益。
2.开设复古课程
汪伪政府在所辖沦陷区学校中更多地开设封建复古课程,竭力将侵略的殖民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结合起来,为推行奴化教育寻找依据。在汪伪“政纲”的“教育部分”就有一条宣扬“保持并发扬民族固有之文化及道德”的规定,这实际上就是恢复与发扬封建腐朽文化的代名词,其实质是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忠君”的封建思想,根据侵略意图对儒学文化思想加以歪曲,甚至篡改。日军御用文人中山久四郎曾以孔子思想与日本文化相比拟,曲解为与日本社会道德“同流合轨”。因此,提倡孔子的学说,有助于从历史、传统的文化关系上,“促进中日关系的提携”[9]。
为灌输所谓“仁爱”“王道”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学校的课程安排多侧重于复古内容,反复借用,甚至有意误读《三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文化经典中的传统知识,禁锢学生的头脑,削弱他们的反抗意识。汪伪政权统辖的学校所开设的复古课程名称虽不尽相同,却都无一例外地将“涵养国民德性,修炼国民精神”放在教育的首位。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修订1928年《戊辰学制》后确立“国民道德科”占总学时的5%,汪伪政权将之改为“建国精神科”后竟增至12.5%,由此,沦陷区学校课程引发了一股严重的“复古”逆流。1943年6月,汪伪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苏州特别区教育状况时指出:“公民皆改授修身一节,因(日)特务机关主张以修身教科书可以体现东方道德精神,只得以修身暂为代用。”[10]初中学校则将历史与地理学科合并为综合性的“修身课”,并归为重要学科,占总学时的1/2,以向学生实施“皇国之道”的教育。所谓的“建国精神科””修身课”等课程,不过是讲一些“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和“民族协和”之类的内容。说到底,其教育的奴化性、欺骗性不仅依然故我,而且更加浓郁。
3.增设军事训练课程
1941年8月,林柏生在伪中央大学开办了青少年团训练班,从南京市公私立中学及伪中央大学挑选60名学生进行训练,其中日伪规定有军步、军号、刀斧使用、旗语、造桥等训练竞赛项目。从以上训练项目中,已看不出一点中学生应有的学业知识,有的只是军国主义下残酷的武士训练。汪伪政权开办青少年团的目的就是要求中国的青少年在接受军事化训练后,去保卫日本侵略下的东亚,谋取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和平。除青少年团以外,汪伪政府还在各地建立伪青年防共团,开展定期或不定期培训,并在南京开办伪青年团指导训练所。各地则纷纷举办伪保甲讲习班、自卫团训练班等,进行军事训练与教育。
1943年9月,汪伪统辖区内学校广泛设立“青年模范团”和“童子军”,作为训练机构,为培养经过奴化教育洗脑且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强壮劳力做基础。这两个学生团体完全采用军事管理模式,并尊奉汪精卫为最高统帅,会议事项最后裁判权属于领袖。在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还附设有一所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由汪精卫担任校长、林柏生任教育长,专门培养青年主干,以推进各地伪青年团和童子军活动开展。在具体的训育教育实行中,汪伪政府效仿德国和日本的办理模式,在学校设有“国父遗教”“领袖言论”等课程。此外,为了深化奴化教育的需要,在汪伪开办的县立中学每星期设有两节“青训课”,由伪教育局派专任教师对学生进行严苛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在“青训课”上,教师可以肆意体罚学生,要求学生唯命是从。并且学校规定:如果“青训课”考核成绩不合格,那么不论其他学科成绩多好,都不允许考生进级。
汪伪政权统辖下的学校开设的这些训育、集团训练等极富欺骗性的军事训练课程,标榜着“为训练学生之体格并养成其服务精神”名号,却依旧不能掩盖其对青少年实施奴役、驯化为核心的奴化实质。
三、汪偽统治区学校教科书编审状况
为充分扮演日本奴化教育政策实际执行者的角色,汪伪政权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1940年8月,汪伪教育部教育编审委员会设立“国立”编译馆,负责协同编审委员会编辑和审定“国定”教科书。但中小学教科书的审查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设立,开展相应的活动,而是统一由伪教育部编审委员会负责,实施编审合一制。
1.删改学校教科书内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反日和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日渐高涨,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编纂的《国耻教科书》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这会妨碍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对于刚上台不久的汪伪政权统治极为不利,所以必须立即禁止原教科书的使用。但又考虑到编纂符合奴化统治思想教科书的工程浩大,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缓冲,而又不能放弃教科书这一有效的方式来宣扬“新的国家观念”和“皇民化教育理念”。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下,汪伪政府决定初期采取对学校原有教科书进行审定与删改的措施,作为缓兵之计。为此,汪伪教育部命令:一方面将各大书局已发行的各类教科书分别加以审查,其有“不合时宜”或“不臻完善”之处,标注“基本适用”“不适用”“修改后适用”三种处置方法,列表后分发各地教育部门或学校,分别加以针对性处理;另一方面则令编审委员会及“国立”编译馆加紧编纂各级学校用书,以代替原有教科书,实现奴化教育的目标和意图。
为适应奴化教育推行的需要,伪教育部考虑到原有体现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教科书不符合奴化教育宗旨,于是,提出修改的标准:排斥共产主义及不纯正的三民主义;坚持东方道德精神;清除排日精神,打破欧美极端思想的侵袭。修改的方法:先将各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加以增删,然后将小学教科书全部另编[6]504。这些都明显反映汪伪政权“亲日”教育政策的精神实质。1938年12月26日,汪伪教育部公布《小学暂行规程》,要求删除排日字眼和民族意识的文字,添加反共、中日提携的内容,以合乎日本奴化侵略的宣传需要。受其指令驱使,汪伪教育部门组织人员从事该项活动。例如,《高小国文读本》第一册,只要有“报国仇”的相关文章内容一律删除;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三课“风雨同舟”被解读为“日华提携”;第六册二十七课,“孟母择邻”,则称国家亦须择邻,须“与日本互助合作”;第七册内更增添“富士山”“日本的东京”等课文,极力描述日本的风光、设施及城市形象,虚夸日本的强大和美好,借以麻痹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心理。小学《历史》教科书不仅将《戚继光平定闽浙倭寇》一文中的“倭”字全部删除,还加以诡辩称:中国史籍记载倭寇,“实系中国海盗”[11]。御用机构及文人不仅将日本在历史上侵华的事实加以抹去,连历史上中国抗击外来侵略、英雄人物和事迹的也要抹去。按照上述手法加以歪曲处理后的教科书已是面目全非,如《初中新国语》第二册中“王冕少年时代”“战地一日”“济南城上”及“抗战受伤的追忆”,《初中新国语》第五册“川原中尉战毙记”和第六册“南口喋血记”等文章在原教科书中已无迹可寻[12]。同时,汪伪教育部发布的审查表中列举了必须加以改写的教科书篇目内容名单,其中如《初中新本国史》第四册“济南惨案”,《初中本国历史》第五册“五卅惨案”“新生活”,《初中外国史》下册“九一八”事变等课文都要加以“修正”。
如此种种,删改教科书原编课文内容,歪曲事实,推卸责任,把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释义为不得以之举,甚至美化侵略为“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建立“王道乐土”的“大东亚世界”。所有这些在教科书内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编审学校教科书
汪伪政权成立后,为进一步贯彻奴化教育政策,对中小学教科书的使用采取了严密的控制,作了如下规定:伪教育部统辖下的教育编审委员会负责编辑和审查教科书,其附设机构“国立”编译馆将教科书中有关进步教育思想的丝毫内容都要加以排除,经过重新编写、修改或审查的教科书由指定的书局出版,然后发行到所统治的沦陷区各地,由中小学教学使用;同时,对未加以修改、审查的教科书,则严禁各地中小学采纳或选择。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往往听候日本机关差遣,进一步在普通教育领域推行教科书“国定制度”,同时辅之以“审定制度”。要旨为:宣传“大亚洲主义”,鼓吹“和平、反共、建国主义”。在教科书的内容及程度上,汪伪教育管理部门结合各个教育阶段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教科书具体编审要求,极力通过教科书媒介把奴化教育思想灌输到青少年头脑中。各级学校均以日语替代其他外国语,教科书中但凡涉及中国历史、地理与民族文化的内容,往往被歪曲甚至颠倒,以断绝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
此处列举教科书编审的一些史实状况:1939年8月24日,汪伪新成立的教育部《中学暂行规程》规定:中学须采用经过审定的教科书,教员自编之课本须适合“部定”课程标准,并在每学期开学前送呈审核及备案。1940年8月20日,伪教育部发布命令,规定各省、市、县的初小、高小一律采用新编的“国定”教科书。同年10月19日,汪伪教育部为送该部工作报告“致行政院呈文”中对此项活动的进程及绩效有所呈现,表明自从教育编审委员会成立后,就着手编审中小学教科用书,现在出版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两部分共计9种:初小3种:初小国语、初小算术、初小常识,高小6种:高小公民、高小国语、高小历史、高小地理、高小算术、高小自然。另外还有3种民众教育使用的教科书,至于中学教科书正在编订当中。考虑到“国定”教科书编印发行尚需要时日,为了应急,审查坊间已出版教科用书,并列表公布,作为“国定”教科书未公布之前的临时补充教材。总计坊间送审教科书共计62种262册,初级小学用书10种80册,高级小学用书16种68册,初级中学用书30种97册。除上列坊间已出版之教科书外,尚有书局、机关团体及个人稿件之呈请审查者,计共35种95册,其中政华书局19种64册,新民音乐书局6种19册,三通书局4种4册等。以上各书均在审查当中。另据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调查显示:到1942年,湖北省云梦县伪政府所设之各级初等小学教科书均经敌宣抚班再次核查,才能供教学使用,内容多系宣传“东亚和平”,蒙蔽抗日意识之亡国论调;广州市内设立初级小学80余所,主要科目为新民课本及日语;上海成了奴化教育的重灾区,汪伪政权限定各校一律采用伪政府教育部门审定的教科书,违者重罚。
中学各科教科书的编纂进度虽然缓慢,但编写与审定大纲中却更加要求恪守“和平反共”的精神教条,其中涵盖“对和平反共国策之认识”“总理大亚洲主义之真谛”“中日和平条约之内容”“东亚联盟之意义”等要目。初中教科书由于科目繁多,加之时间紧促,一直到1940年11月才陆续完成编纂修订工作,并交付出版。至1943年初,新印初中的《公民》《中外史地》及修订初中第四版各教科书,总计15种32册 [13] 。该套初中教科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封面上印有显眼的“国定”教科书字样,且署名均为“教育部编审委员会”。书中从目录到正文则大量充斥着吹嘘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消除抗日斗争意识等内容。
汪伪政府教育编审委员会在对“国定制”教科书的编审事务上,重点不是编而是审。编审过程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将原有教科书中不符合日本侵华战争和殖民统治利益需要的文字内容加以删改,同时歪曲历史真相,蒙蔽儿童青少年以及社会民众。相比之下,日伪对于高中教科书的编审有所迟缓,规定在遵从奴化教育政策的背景下,先由各校选择国内各出版机构原来编写发行的教科书,然后由当地伪教育部门组织审查、讨论,完成改订工作后,推荐各校使用。但各地伪政府教育部门大多流于形式,中学各科教科书基本上是由任课教师自编讲义,组织教学。因此,各地学校所使用教科书花样繁多,教学体例混杂,内容深浅有别,教学水平更是差距甚远。事实上,直到汪伪南京政府垮台之前,也根本未能编印出一套完整的高中教科书,加之日本忙于太平洋战争,出于为其提供战争所需军资的巨额支出,教育经费紧张,使得教育“只能给战争让路了” [14] 。
总之,在汪伪政权统治时期,各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完全是为其奴化教育的推行提供保证,并妄图达到奴役学校学生精神心理的目的。
四、汪伪政权统治区教科书特点分析
可以说,学校教育目标是通过课程和教科书为媒介的教学活动而实现的,两者相互联系并相互貫通。日本羽翼下的汪伪政权所推行的奴化教育教科书内容完全与其奴化教育政策相契合,尤其是在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上重点强化日语、复古及军事训练等方面。以下就汪伪统治区学校教科书特点加以尝试分析。
1.以奴化教育的宗旨为取向
汪伪政府为贯彻执行“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政策,曾以教育部的名义多次发布训令,强制规定奴化教育内容。在课程设置上,秉承日本奴化教育意旨,将日语列为主要科目,并在课时的安排上增加比重,这样势必打压其他学科的教学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军占领。1942年7月,伪上海市政府规定:租界区域之中小学校自当年下半年起,一律添设日语课,初中每周4小时,高中2小时,高小2小时。并指令市教育局大量招聘日籍教员,分发各校任教 [15]1 029 。学生学习日语,所使用的课本统一采用由日本东亚同文院编的4册《日语教科书》。该套教科书以历代天皇、武士所谓的“丰功伟绩”为基本素材,宣扬“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日汪扶携”等。如对侵华战犯乃木大将一家,用很长的篇幅写成课文《乃木大将及夫人》编排其中,占据显著位置,要求中国学生学习乃木如何忠于天皇,如何光宗耀祖等[16]。因此,学生学习规定的教育内容过程,其实也就是被灌注日本殖民教育理念的过程。
史地课程及其教科书也反映出奴化教育的重要特征。日本侵略者名义上是将史地课放任汪伪当局自行安排,但实则是按日本侵略意图办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科书的体例及章节内容大讲特讲日本地理条件优越和历史辉煌,中国地理与历史内容则涉及不多。至于那些自然学科教科书,也紧紧地为日本侵华对沦陷区殖民地占领的经济掠夺和技术训练服务。这种实用主义的教材观,早已使科学教育的思想面目全非了。
虽然汪伪教育部把持着教科书的编审权,但是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实际上受日本机关的监控,教科书中所选内容要合乎日本主子的胃口。正如迷途的现代文学家周作人供认“文化沟通、经济提携、军事合作”三原则是日本对沦陷区教科书的本质规定[15]1 032。受其引导,“和平反共建国”“大亚洲主义”等亲日论调通过教科书得以泛滥,腐蚀并毒害少年儿童的爱国情感。例如,有的小学语文教科书编选了这样的课文:“天亮了,弟弟妹妹快站起来,一起拜太阳。”显然,这样的内容,明显会使学生产生对日本国旗的崇拜心理;“国定”教科书《初中本国史》第四册有的课文鼓吹侵略者所宣扬的大东亚战争及“和运”汉奸思想;1943年1月第4版《初中公民》第二册中所选入的文章甚至大肆渲染日本的贡献,并辩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真正希望的是与中国协力,使之兴隆,而不是征服中国,使之灭亡。这些经过日伪篡改后的教科书,成为奴化中小学生思想的利器,发挥稳定日本殖民统治的消极作用。
2.充斥封建伦理道德思想
汪伪政权将扩张侵略的殖民理论与儒家思想的落后元素,及其他曲解后的文化统一起来,以期寻找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的生存空间。当然,日伪所利用的是传统固有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或者是根据其自身意图需要对儒学文化思想加以篡改的解读。在沦陷区开设的各中小学灌输“仁爱”“王道”观念,尤其是通过“修身课”向学生渗透封建道德思想,养成逆来顺受、绝对服从的国民奴性性格。《修身》教科书中内容大多体现封建礼教和“愚忠”观念,如宣称初、高中女子《修身》教科书编纂目的在于:“实践固有道德,适应时代趋势,造就新中国健全女子”。由此,沦陷区学校掀起“复古”风潮,教科书内容中的封建伦理道德沉渣泛起。
汪伪政府规定中小学课程须偏重于经学为主,因为唯有“六经”才能使学生成“圣人”。自1942年秋起,在国文、修身科目课程编制中,以传统经学教材作为选择的重要题材资源,规定小学读《论语》,初中读《大学》《中庸》,高中读《诗经》《左传》,并利用孔孟儒家封建理论欺骗学生,将《礼记·大学》中的“亲民”改为“新民”,意图在于使沦陷区的学生都能知“仁”懂“礼”,借以欺骗、麻醉青少年学生,甘愿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汪伪政府在小学校设置综合的“国民科”,在初中及以上学校,设“建国精神科”,把历史、地理、自然等课,共期归于“国民道德”,其主要内容有驯服中国学生的“学生之本分”“报恩感谢”,美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友邦之仗义援助”“满洲之建国”,吹捧傀儡政权的“皇帝登位”以及“民族协和”。日本侵略者通过对教科书的选择或篡改,极力“发扬光大”所谓儒学“圣道”,其实是披上“忠君”“爱国”外衣,为其殖民统治提供依据,实质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服务。
3.贯穿宗主国殖民奴化意识
汪伪政权成立后,将殖民奴化思想贯穿到各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编纂之中,其教育目的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即办学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要从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向学生传授经过精心组织、挑选和裁剪的特定素材及资源[17] 。
教育活动的组织方法注重向学生灌输所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实施法西斯训练。所有这些意旨都以不同的程度和内容体现于教科书中。如历史教科书突出向学生宣传日本的“天照大神”及日俄战争的胜利;地理教科书多是以描述日本的建筑及城市景象为内容,加以详细介绍。此外,沦陷区学校的实务课和勤劳奉仕活动大大增加,相应的文化课却有所缩减。汪伪政权还在南京等地举办了“青少年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理论作为训导教材,其实质无非是对学生进行武士道精神的训练及宣扬亲日卖国的汉奸主张。
出于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和管理,并有助于实现奴化教育的目标要求,汪伪政府发布独裁式命令:每天早晨,沦陷区的学校一律举行升旗活动,师生面向日本太阳旗,行敬礼仪式,并朝东方遥拜日本天皇;各中小学每周实行一小时“精神训话”,阐发“和平反共建国”的殖民理论。这其实是对课堂教学的部分延伸与补充,从而使奴化教育教科书的作用发挥更为有效。1940年,伪上海市教育局在推行上海市小学界和运实施方案中,进行精神谈话的材料主要有:讲述时事问题,讲述身心修养问题,处理偶发事项等。1943年11月29日,汪精卫在上海演讲以《光明的方向》为题的训话,要求大中学生以“勤奋刻苦、精进勇猛”的理念去实现日本“大东亚宣言”的目标内容。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起到了管控教科书使用的监督作用,而且发挥了潜在课程的熏陶习染及引导暗示功能,其本身与教科书的奴化教育角色扮演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历史的评价
综上所述,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汪伪政府为降日媚外,反共反人民,制定并设计了奴化教育政策和奴化教育体制。为此,伪政权不惜通过设置奴化教育课程,修改、编写教科书,以及根据军事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实际需要,篡改历史及歪曲知识内容。此类行径旨在以养成沦陷区学生的奴性为根本出发点,而丝毫不顾及学生的身心健全发展。这是充满侵略意图和殖民目的的教育,一种殖民教育暴力的隐藏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以及在沦陷区利用伪政权实施野蛮残暴的殖民统治,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了难以治愈的创伤。这种惨痛的代价是无法用简单的数字估算的,并同样反映在通过教科书实施的奴化教育领域,以下对此加以简略分析。
汪伪政权上台后,经过一番快速炮制,满足其殖民统治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陆续出版,并分发到沦陷区各地使用。但由于沦陷区内各书局和印刷厂对汪伪政府的奴化教科书大多采用抵制态度,印刷缓慢。同时,日伪只是控制了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大中小城市,對于为数众多的城镇和乡村尚无法有效统治。因此,这些教科书在发行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各地中小学开学后,甚至两三年内都领不到课本,所用教科书几乎混乱不堪。
根据汪伪政府中小学教科书审查具体清单可知,伪政权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意旨,任何不利于养成学生“皇民化忠良国民”的教科书都要取缔,其核心意图是要钳制学生的思想和精神。这一方面反映在消除教科书中不利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异端思想”内容,更进一步体现在严格扼制有关“异端思想”可能出现的其他载体。为此,伪政权建立专门的审查机构,组织人员,对中国主要出版机构编写发行的教科书加以地毯式搜索和密网式排查。教科书一旦涉及抵御外侮、反抗侵略以及国家独立等民族意识的内容全部去除,而代之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类的谎言。日伪不但明确要求中小学必须使用通过审查或由日伪专门重新编写的教科书,同时还加强了对学生接触书籍的限制。查禁图书的范围很广,既包括有关抗日、共产党内容的书籍,还包括当时一般发行有一定传播量和影响力的报刊杂志、辞典工具书。至于普遍使用的中国历史、地理、语文等小学、初高中教科用书,更是首当其冲。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和传媒事业先进地区,教科书的出版业也以此为中心。据当时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五家大型书局统计:1942年3月,未通过日伪审查的书籍而被扣押的中小学教科书总数达到19164017册,其中小学教科书占15178284册,比例为79.2%,中学教科书1464817册,比例为20.8%。小学教科书占据比例更高,这充分说明了日本授意汪伪政权通过教科书对小学生实施思想控制和精神毒害的重视程度更大。
汪伪政权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在其统辖区推行奴化教育,这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所取得成就的摧残和未来教育前途的封杀。通过肆意篡改、删除和编审教科书的多种方式,汪伪政权对沦陷区文化教育的摧残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教科书作为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媒介手段,在教育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汪伪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组织专门的机构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按照奴化教育的方针政策要求,肆意篡改、删减学校教科书,按照奴化教育性质编写和审定教科书。这些教育的侵略行径不仅在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高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力图从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情感方面体现日本文化的核心地位,使中国人从孩童伊始就开始趋向“日本化”,长大后成为日本的二等国民,中华民族的亡国奴。这与军事侵略相比,更有其深层的威胁和持续的破坏力:一方面阻碍了中国民族文化历史的合理传承及青少年民族心理的健康养成,打乱了受害国青少年教育的合理体制和活动;另一方面侵略者通过教科书以及其他方面所构成的奴化教育形态,对学生与中国民众的健全人格、心理健康、民族感情及精神品质都产生了毒害,而且就其影响而言,是内隐而持续的。
日伪政权挖空心思地在教科书中渗透“和平、反共、建国”“三民主义”及“大亚洲主义”等亲日媚日思想,以此论调麻醉儿童及青少年。这种观念认识成为删改、杜撰或选编教科书素材的首要标准。对此上文已有所论及,此处再作例证从中呈现奴化教育教科书的部分实情。譬如,《高小国文》第三册课本中“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和“自强”“奋斗”等词句被篡改,《吴阿毛的故事》《岳母刺字》《阎典史传》等国家民族意识强烈的课文均被去除。初中国文教科书还编入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1940年冬天自撰的《欢迎日本众议院来华诸君》一文。其中的核心论调是中国应放弃对日本抵抗,尽其力量与日本合作,实现“共同努力于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以达到东亚各民族共存荣”的目的。1943年1月版《初中外国史》下册有的内容赞扬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对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伟业”。同年1月第4版《初中公民》第二册选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声明“日本之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灭亡,而在中国之兴隆;不在征服中国,而在与中国协力”,并对此加以肯定性的描述和渲染。此外,该课本还对日伪侵略占领其他种种谬论大加赞赏。1944年1月第9版《高小地理》第三册蓄意将东三省地图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来,改为伪满洲国地图,破环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同时,还鼓吹中日提携,共建“美好的亚洲”,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这些经过日伪篡改后的教科书不仅是毒害沦陷区儿童的素材,更是对民众进行奴化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其结果会打消沦陷区民众的抗日积极性,甚至对全民抗战产生消极影响。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并保持深刻的警醒。
通过对汪伪统治区教科书的探讨,将有助于拓展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学科领域,丰富特定历史时期教科书史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分析汪伪政府奴化教育的危害,从而深刻批判日本右翼势力掩盖甚至美化日本侵华时期在中国实施殖民教育侵略的历史史实,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展望未来,日本应该清醒地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防止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才能与亚洲各国建立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中日两国的合作共赢和世代友好,从而造福两国人民,并为人类的福祉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美真,张云.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94.
[2] 申报社.申报年鉴[Z].上海:申报社,1944:941.
[3] 蔡德金,李贵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8.
[4] 曹必宏.汪伪奴化教育政策述论[J].民国档案,2005(2):114.
[5] 江苏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教育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34.
[6] 宋恩荣,余子侠.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7] 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687.
[8] 吴洪成.日本教育研究论丛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220.
[9] 齐红深.日本对华教育侵略[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90.
[10]夏军,沈岚.汪伪统治区奴化教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9.
[11]南京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教育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274.
[12]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69.
[13]吴洪成,张华.血与火的民族抗争: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史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221.
[14]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240.
[15]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等.汪伪政权全史: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6]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8.
[17]黄骏.汪伪政权的“奴化教育”[J].民国档案,2003(1):55.
(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