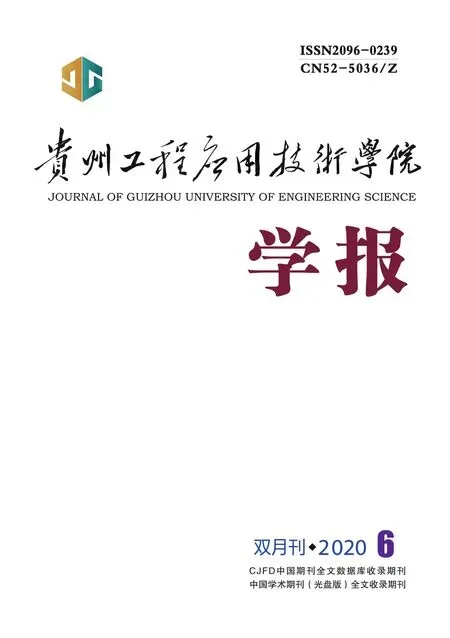权言——鬼谷子的修辞发明观
周念哲
(三明学院海外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0)
一、引言
《鬼谷子》一书是先秦纵横家学派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除了展现运筹帷幄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阐述了纵横家的言说艺术和修辞观。例如,与先秦儒家在《易经》以“修辞立其诚”将言说艺术定义为“修辞”相似,《鬼谷子》将其命名为“饰言”并给出了如下定义:“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①[1]738在《鬼谷子》所阐述的“饰言术”中,其针对游说过程所提出的言辞权衡观举足轻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权篇》中。对于《鬼谷子·权篇》,南朝陶弘景题注为:“权者,反复进却以居当也。”[2]172当代陈蒲清在对此篇注解时认为,“权”字,本义是秤锤,引申为衡量、变化。[3]70如此看来,倘若鬼谷子的“饰言”等于修辞,那么“权(衡)言(辞)”应当可以视作他的“修辞发明”。
西方古典修辞传统中将修辞活动分为五大任务:发明(invention)、谋篇(disposition)、文采(elocution)、记忆(memory)、发表(delivery)。“修辞发明”是指修辞活动中“根据话题和目的,发现论点和论据,提出诉求”这一任务或环节。美国修辞学者George Kennedy在梳理了西方古典修辞中的“发明”观并总结出了以下看法:“修辞发明涉及的是仔细思考、想出主题(subject matter):确定好待解决的或争议中的问题,这个问题被称为演说的争议点(stasis);还要思考出能让受众接受言说者立场的可用之劝说方式。这些劝说方式首先包括直接证据——比如见证词与合同——这些证据只是被使用而非被发明出来的。第二个是人为劝说方式……人为的劝说方式使用‘话题’(topoi),也就是论证得以构筑的伦理或政治前提,或者因果论证之类的逻辑策略。”[4]4-5
美国修辞学者Richard E.Young认为,“在修辞研究领域,发明——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修辞发明的艺术”——传统上被认为是发现话语内容的一种表达明晰、高效有序的方式(explicit and organized way),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发现劝说性话语内容上。”[5]350纵观《鬼谷子》一书中有关言说艺术方面的论述,其所提出的言辞权衡(下文简称“权言”)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以表达明晰和高效有序的方式来发现和组织劝说性话语(游说)内容”的思想,也就是体现了修辞发明(下文简称“发明”)思想。
二、鬼谷子的权言观
鬼谷子的权言观主要体现在权量、权变和权宜这三个方面。权量主要是通过因言听辞、揣情、摩意等方式对受众情境以及与受众相关的环境、背景、形势等从数量、程度、态度等方面进行衡量把握,进而从中总结出游说内容与策略上的依据,也就是根据诉求或针对修辞目的来发掘有效可用的论点和论据。权变主要强调在言说活动中根据特定受众、特定主题、特定环境等修辞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变通,也就是对所发掘的论点论据进行斟酌损益改换。权宜则主要是根据不同受众对象而采取差异化和适宜的修辞策略,以及在言说活动中把握时机和拿捏分寸,也就是按优先度、价值性、时效性等来具体选用最贴切的论点论据。权量、权变和权宜三者所体现的修辞思想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中的修辞发明观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一)权量
关于权量或者“量权”的具体内容、对象,《鬼谷子·揣篇》中是这样描述的:“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群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候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能知。如此者,是谓权量。”[1]735同时,《鬼谷子》一书中还提供了权量的三种主要方式:因言听辞、揣情、摩意。在“因言听辞”方面,《鬼谷子·反应篇》又提出了以“反求应出”和“象事比辞”这两种方法获得“实情”:“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1]726-727关于揣情,《鬼谷子·揣篇》强调要顺应受众的情感状态以探求其“隐情”或者使其无法隐情:“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知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谓测深揣情。”[1]735-736关于摩意,《鬼谷子·摩篇》突出以“隐”和“饵”来测探“内情”:“摩之符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索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窌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应之,事无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1]736-737
总而言之,权量主要是修辞者根据特定修辞目的和劝说主题,通过因言听辞、揣情、摩意等方式对受众的以及与受众相关的包括客观状况和主观情境在内的“实情”、“隐情”和“内情”进行考察,并且侧重从数量、程度、态度等方面进行衡量把握,进而从中总结出游说内容与策略上的大体倾向或依据。权量是为了发掘、发现各种潜在的或显然的已然事实和情态依据并将其加以汇集梳理和权衡分析后转化成可资利用的论点论据,从而实现游说中“出言有据”,这一点与西方修辞传统中“发明”的任务内容颇具比较性。在西方古典修辞传统中,“发明”意味着“修辞者针对面临的具体修辞形势②和任务进行构思和立意,寻索、发现、确定和初步组织可说、该说、值得说的话的那个过程”。[6]61两相比较,《鬼谷子》权言观里“权量”的目标对象与西方古典修辞传统中修辞发明的任务内容之间既有交集也有差异。交集在于二者都先入为主地关注各种已然事实和情态依据并以此形成论点论据,差异在于“权量”侧重于探讨如何发掘事实或情态依据方面的技艺,而西方古典修辞传统的修辞发明则不仅着眼于发现事实,更是形成了一套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以“事实”为起点、经由“定义”和“性质”、最终聚焦“程序”的修辞发明理论——争议点理论(stasis)。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同属于修辞发明范畴,权量技艺和争议点理论的应用场景不同,前者主要用于政治修辞(审议修辞),而后者多见于法律修辞(庭辩修辞)。
(二)权变
《鬼谷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强调在言说活动中根据特定受众、特定主题、特定环境等修辞因素的变化而进行言说上的变通,同时要善于对外界纷繁变易的相关形势和言论进行分析权衡。具体而言,《鬼谷子》有关言说上的权变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言说过程中,修辞者的言说内容和方式等要根据主客观环境、时势、情态、主题等变化而灵活变通,做到“时虑变言”。例如: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事而至,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1]736(揣篇)又如: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1]729(内楗篇)第二,修辞者要根据受众的反应或表现来评估自己的劝说是否得法,根据受众的疑问所在而改变劝说内容,根据受众的言辞反应而总结劝说要点,做到“因疑变说”: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1]741(谋篇)第三,修辞者要擅长修辞批评,对纷繁杂乱的舆论信息进行条分缕析和价值评判,做到处变不惊、观要得理:故口者几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观要得理。[1]738-739(权篇)第四,事物、事情会不断变化,变化有原则;针对外在变化要在说辞上有变化多样的储备和应对办法,这样就能以变制变。换言之,在言说中要贯彻“言多类,辞贵奇”: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1]740(权篇)另外,《鬼谷子》还将“言多类”大体上分为“始言”和“终言”两大类,再将其余的子类言辞统括在这两大类之下,并且强调要“言善始事”和“言恶终谋”: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为谋。[1]725(捭阖篇)鬼谷子所罗列的这些言辞类型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论据,这与西方修辞传统中的“话题(topos)”概念颇为相似。“topos”的字面意义是“地点或居住点”,它最终引申为“论证之据点”或“论(证之依)据”的意义。[7]84亚里士多德将“话题”分为“专门话题”和“通用话题”,并且在论述前者时指出:任何论据甚或一丁点的知识信息——只要能证明其有用或无用、权宜或非权宜、明智或不明智——对审议性言说者而言都是一个有专门用途的论据。[7]85
总而言之,《鬼谷子》的言说权变观主要是强调修辞者在修辞实践中要根据受众情态及其心理、主客观情况和舆论形势等等因素在劝说内容和策略方面做到“灵活变通”,以便实现修辞上的意图或目的;修辞文本④的构思和变换必须以受众和主题为中心,以实现受众的认同或服从为出发点,根据时机、情态、形势、场合和条件等等语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鬼谷子的这种言说权变观事实上与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所倡导的“言说变通”思想如出一辙。昆体良认为,“对于修辞者而言,最重要的才能莫过于一种明智的变通(wise adaptability)”。[8]124“他引用并极大地发挥了西塞罗简略提到过的一条原则,即在言说中,没有哪一种文风适合于所有事例、所有受众、所有场合、所有言说者”。[7]125他还认为,修辞者必须根据说话对象来决定自己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根据言说场合来决定采用哪一种语调;根据受众身份来决定采用什么风格。此外,昆体良提醒修辞者对于地点和时间也必须特别予以关注。(同上)
(三)权宜
《鬼谷子》中提到的言说上的权宜主要是提出根据不同受众对象而采用差异化、适宜的修辞文本和修辞策略。具体而言,《鬼谷子》有关言说上的权宜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根据目标受众的具体身份、地位等特点,对不同受众进行劝说时做到区别对待、因人而异、因人制宜的“言有所依”。例如,“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1]725(捭阖篇)又如,“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1]740(权篇)
2.修辞者要根据目标受众的利益愿望、价值取向、兴趣偏好、忧心挂虑、欲念追求等心理机制或特点,在言说中内容上应当投其所好、顺好避恶、审意说重,而不是刻意对受众进行说教或者强加意志;在形式上也要展现出受众喜闻乐见的言说方式和语言风格。例如,“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岨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1]733(飞箝篇)又如,“无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1]742(谋篇)再如,“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⑤[3]65(摩篇)
3.修辞者在言说活动中要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借势发力: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知用其所用也。[1]739(权篇)《鬼谷子》里虽然没有具体谈到修辞者应当如何扬长避短,然而联系到亚里士多德所论及的三种人为举证方式(诉诸道理Logos、诉诸人格ethos、诉诸情感pathos),由于不同修辞者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及其相应的举证擅长,在劝说中诉诸什么哪一种举证方式,除了考虑到客观可能性和必要性,修辞者还要知其所短、扬其所长。一般而言,理性者更擅长诉诸道理,而感性者更擅长诉诸情感来触动受众。
4.修辞者要照顾特定目标受众所因循沿袭的或特定受众群体所共享默认的包括措辞、日常话题、言说主题内容等在内的传统禁忌,以免冒犯受众引发抵触从而使言说失效或无效。简而言之,要注意“言有忌讳”: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1]739(权篇)
5.修辞者在言说过程中应当符合事实或有事实依据,换言之,其言说内容应当不违背显然的公认事实或道理;如此一来,修辞者的言辞才能不失之于荒谬,才能在受众头脑中具有可接受性;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到“言之有据,说必合情”: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1]737-738(摩篇)
简而言之,《鬼谷子》的言说权宜观可以归结为“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1]729(内揵篇)落实到修辞实践上,也就是修辞者要琢磨适宜的时机和恰当的分寸以便对受众进行相应的劝说并促成力图实现的效果或行动。《鬼谷子》的言说权宜观与西方古典修辞传统中的“kairos(适恰/适中)”观念颇为相似。西方学者James L.Kinneavy通过多方引证,在梳理了前人有关kairos的主要观点后,将其定义为“做某事的正确或合适时机,或者说行为举止中恰当的度(the right or opportune time to do something,or right measure in doing something)”。[9]58此外,他还论证了kairos的两个基本要素:适时性和适度性(the principle of right tim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a proper measure)。[8]60由此可见,《鬼谷子》的言说权宜观和西方修辞传统中的“kairos”观念都主张修辞者应当在言说活动中敏锐地抓住时机、切实地把握分寸。
三、结论
综上所述,鬼谷子的言辞权衡观与西方修辞传统中的修辞发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但也存在一些差异。相似之处主要在于二者都旨在构思出适用于特定人物和特定主题的劝说话语并将其形诸文字和策略性地付诸修辞实践来实现劝说目的,以及二者都认识到“变通”和“机宜”在言说活动中的重要性。差异主要在于鬼谷子的言辞权衡观着重对具体技巧、经验和策略的总结,主张基于捭阖的“始终之言”、以“因言听辞”求实情、以“揣”测隐情、以“摩”探内情。西方修辞传统中的“修辞发明”则强调对原理和理论的探讨,从而形成了“三种修辞体裁”、“三种人为举证方式”、“话题”、“适恰”和“争议点理论”等一般性的理论、原则或观点。在对鬼谷子的言辞权衡观与西方修辞传统中的修辞发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鬼谷子“饰言术”偏于实践技艺和西方传统的“修辞学”侧重理论指导的认识。
注释:
①《鬼谷子》原文有诸多版本,各个版本的文本内容略有出入。本文所引用《鬼谷子》原文选自大都选自道藏本《鬼谷子》繁体字竖排版。
②“修辞形势(Rhetorical Situation)”是由美国修辞学家比彻(Lloyd F.Bitzer)所提出的一个修辞学概念。比彻所提出的“修辞形势”包含“缺失(exigency)”、“受众(audience)”和“修辞局限(rhetorical constraints)”三个因素。“缺失”是指因为突发事态或紧急状况而出现了一种亟待解决的不理想或不如意局面;它是一种缺憾,一个障碍,有待完成的某件事情,不应如此的某种境况。“受众”有别于一般的听众和读者,它有两个特征:一是能够通过话语受到修辞者影响和争取;二是能够成为言辞产生效应的媒介。“修辞局限”是指对于与修补“缺失”所需的受众相关决定或行动形成限制的不利因素,例如在形象、事实、传统、信念、偏见、成见、态度、兴趣、动机等方面对修辞者的修辞努力所形成的障碍。
③“争议点理论(Stasis)”普遍地被认为归功于公元前2世纪的古希腊思想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赫尔玛格拉斯的争议点理论实质上主要包含了四个步骤或议题:1.“事实(fact)”争议点。2.“定义(definition)”争议点。3.“性质(quality)”争议点。4.“程序(procedure)”争议点。第一个争议点问题涉及事实存在还是不存在。第二个争议点问题涉及一个事实或行为的定义或分类。第三个争议点问题涉及既定事实或行为的性质。第四个争议点问题涉及程序和裁判权。
④“修辞文本(Rhetorical Text)”一般是指修辞者带着修辞目的以修辞手段“封装”过后形成的文本或话语内容。
⑤道藏本此处“焉”字断句疑似有误,改用陈蒲清版同时也是当代较为常见的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