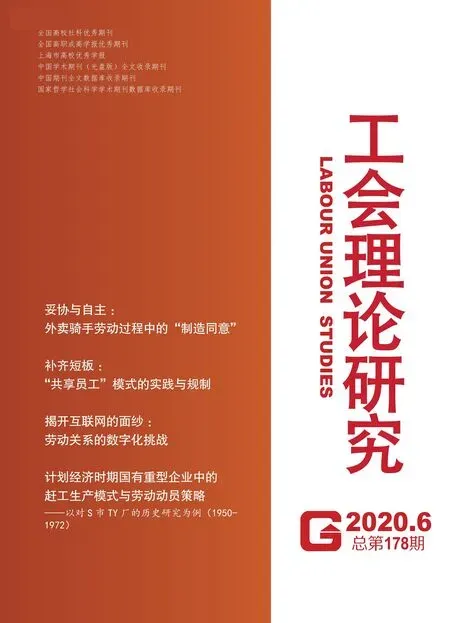日本工伤的认定与启示
宋晓波 问清泓
(1 武汉音乐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0;2 武汉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5)
一、日本工伤保险制度概述
在日本,劳动灾害简称劳灾,是对工伤的统称,工伤保险制度被称为“劳灾保险”。劳灾保险是指为了迅速公正地保护由于工作事由以及上下班导致劳动者负伤、生病、残疾、死亡等而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必要保险制度。①[日]菅野和夫、江頭憲治郎:ポケット六法,東京都,有斐閣,2008,p.1703.
《劳动基准法》与《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是日本工伤认定的主要法律依据。因《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的补偿标准高于《劳动基准法》,日本劳动灾害补偿实践一般以《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的具体规定为基准。《雇佣保险法》《劳动者安全卫生法》《国家公务员灾害补偿法》《地方公务员灾害补偿法》《事故保险法实施细则》是日本工伤认定的辅助性法律法规。为适应日本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历经数次修订,关于工伤保险补偿的内容不断扩充,保护措施更加全面,补偿水平持续增长,在工伤保险制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日本工伤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依据《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第一条的规定,工伤保险适用于日本所有行业的雇佣人员,政府强制要求所有雇主为雇员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对雇员人数少于五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企业不做强制要求,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工伤保险。②郭晓宏:《日本劳动安全管理与工伤保险体制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日本工伤保险制度已实现全行业的广覆盖,在日本工作的劳动者,皆受工伤保险的保护,制度的适用范围极广。因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日本通过《国家公务员灾害补偿法》和《地方公务员灾害补偿法》,确立了公务员的工伤保险制度。
(二)日本工伤认定的管理机构
日本的工伤保险由厚生劳动省负责管理,厚生劳动省下设的审议委员会专门处理工伤保险具体事务性工作。厚生劳动省在日本各地设有基层劳动基准局,管理当地的工伤保险事宜。各劳动基准局下设劳动基准监督署,负责所在区域内的工伤认定、伤残鉴定、保险费征收等具体工作。①应永胜:《德美日国家工伤保险制度探赜与启示》,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23-28页。劳动基准局是日本工伤认定的主要管理部门,专设工伤事故补偿部、工伤事故管理科、工伤事故补偿科,工伤事故保险业务室是工伤事故补偿部的内设部门。
(三)特别加入制度
特别加入制度是日本工伤保险的一大特色,是在不与工伤保险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允许那些虽不是纯粹的薪金参保者,但从其工作特点、通勤事故及灾害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参照《劳动者灾害补偿法》中关于工伤保险的要求,将其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的特殊制度。②郭晓宏:《日本劳动安全管理与工伤保险体制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该制度以与企业建立雇佣关系的劳动者以外人员为对象,将其纳入日本工伤保障的范围,在不改变现行工伤保险体制的前提下,解决了日本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问题,是工伤保险制度的一大创新。
涉及特别加入制度的被保险人分为三类:第一类,农业、林业、制造业、运输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主及其家属从业人员;第二类,个体运输人员(包括使用汽车进行旅客或货物运送的人员,以及使用摩托车进行货物运送的人员)、无雇佣的个体工匠、渔业人员、废旧物品回收人员、护理工作从业人员、作家、工会干部、农林机械操作人员等;第三类,被派遣到海外工作的人员。其中,使用摩托车进行货物运送的人员、喷药无人机操作人员为2013年特别加入制度新增的行业适用范围。③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官方网站,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rousai/kanyu.html,2020-11-01.特别加入制度将日本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个人,实现了工伤保险待遇的普适性。
日本工伤保险为强制性保险,无需劳动者申请,但在特别加入制度中,相关从业人员必须提交特别加入书面申请,按照申请要求提交相应证明材料,且为排除个人申请加入之前罹患职业性疾病的情形,在申请加入前要求到指定医院进行身体检查,体检报告和申请资料一并交至当地劳动局。随后,劳动局按照特别加入规定,审查申请资料是否符合特别加入的具体要求。
根据日本《劳动者灾害补偿法》的规定,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劳动者不用缴纳任何费用。因特别加入行业与适用人群的特殊性,特别加入制度中的工伤保险费用由特别加入者自行承担。依据行业类别,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工伤保险缴费率,每三年调整一次。从历史数据来看,特别加入者保险费率呈现逐步降低之势。
针对相关从业人员的高流动性,特别加入制度创设了加入人员的行业变更和退出机制。如特别加入人员更换行业岗位导致保险缴费的变化,必须及时进行特别加入变更申请,以获取更全面的工伤保障。加入人员与企业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之后,则应退出特别加入制度。变更与退出的制度设计,很好地解决了从业人员在不同行业与地区流动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充分保证了特别加入的制度弹性。
特别加入人员的工作内容与形态,有别于传统劳动者,其业务开展是遵循个人意志独立完成,不需听从他人指挥或命令,从而如何判断其工作的遂行性是工伤认定的难点。为此,对于特别加入工伤保险人员的工伤判定,由劳动基准局局长依据相关标准作出。
二、日本工伤的认定
日本的工伤认定是指在劳动基准监督署的主导下,针对受害劳动者的负伤、疾病、死亡、通勤灾害与其从事工作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的工作。
(一)“劳动者”的认定
根据日本工伤保险制度,日本工伤认定的第一步是确定职工的“劳动者”身份。《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对《劳动基准法》上的劳动灾害受害者给予工伤补偿,《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中的“被保险人”即为《劳动基准法》中的“劳动者”。
《劳动基准法》第九条将“劳动者”定义为,无论职业种类,在企业或事务所工作并获得薪金支付的人。由该定义可见,不论劳动者的职业、雇佣形态(正式职工、临时工),只要符合在企业或事务所“工作”与获得薪金“支付”两个要件,即可认定为日本《劳动基准法》中的“劳动者”。此处的“工作”是指遵从企业管理者的指令或命令进行劳动,即为使用从属性。劳动者从企业获取薪金报酬,并以此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即为经济从属性。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属于企业生产运营活动的一部分,则为组织从属性。从属性的判断是日本学界对传统劳动者身份性质判定的基本标准,依据上述使用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三个基准中的某一个或多个进行不同的组合,来判定是否是从属劳动,即是否为劳动法适用对象的劳动者。①田思路、贾秀芬:《日本劳动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当前市场竞争激烈,日本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人力成本,更愿意通过业务委托、外包的形式,使用外部劳动力。这些接受企业委托,为委托者提供个人劳动力,并以从委托者获取报酬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就业者,日本劳动法学界称之为委托型就业者。②[日]镰田耕一著,田思路译:《个人外包、业务委托型就业者的法政策——民事法与劳动法之间的“契约劳动者”的保护》,载《中国劳动》,2016年第22期,第4-11页。面对业务委托、外包等新型就业形态,传统从属性的劳动关系判定基准难以适用。日本法学界为解决新型用工形态就业者的劳动性质判定问题,从以下方面予以应对:第一,厚生劳动省校正了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扩大了劳动者应获取的保护范围,雇佣新型用工形态劳动者的用人单位亦需遵守《劳动基准法》的相关规定。第二,按照劳动给付的实际形态判定是否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当从属性判定出现困难时,则根据就业者选择的契约形式进行综合判定,如果对照劳动法的宗旨,目的存在合理性,该契约可被推定为劳动契约,给予就业者与传统劳动者相同的法律地位,提供劳动者相对应的工伤保护。①田思路、贾秀芬:《日本劳动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如上所述,在新型用工形态领域,厚生劳动省针对不同劳动形态的受雇者的特殊性予以特别规定,在现状的研究、法律地位的权衡等基础之上,认为在特别必要之时,可给予新型用工形态的受雇者与传统劳动者同等的工伤保护待遇,以为其撑起工伤保护伞。
(二)工伤认定的范围
日本工伤的认定范围包括业务灾害和通勤灾害两部分。
1.业务灾害
业务灾害是因业务而引发的灾害,即劳动者在业务上的负伤、疾病、失能,②林良:《日本过劳灾害之行政认定基准的行程》,载《台大法学论丛》,2017年第107期,第25页。具体为劳动者在雇主的支配下,在工作时间或加班时间内的工作过程中发生的灾害。《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罗列了业务灾害的具体适用情形:(1)工作过程中或与工作相伴随的附带行为过程中;(2)作业准备、事后处理与待命过程中;(3)在企业设施内休息的过程中或企业内部餐厅就餐过程中;(4)上下班途中利用企业通勤专用交通工具过程中(此通勤与后面即将介绍的通勤灾害有所区别);(5)发生天灾、火灾等不可抗力的紧急过程中;(6)因企业需要外出从事相关业务过程中;(7)因他人或自身的故意行为所引发的灾害(包括过劳自杀);(8)符合特定条件的职业病;(9)其他原因导致的灾害。③罗筱媛:《日本工伤保险制度概述》,载《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9期,第47-49页。
在日本工伤认定中,关于“业务”的概念进行了扩张性解释,如上述罗列情形中的工作附带行为和作业准备、待命行为等,虽然该行为可能不发生在工作时间内,但行为之目的是因工作而做出的,更为强调业务的目的性。
2.通勤灾害
通勤灾害是指劳动者在日常通勤行为中发生的负伤、疾病或者死亡的事故灾害。④田思路、贾秀芬:《日本劳动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将“通勤”定义为:因为工作需要,劳动者按照合理的路线和方法,从住所到工作场所之间的往复行为。“因为工作”强调了工作是劳动者往复行为的主要目的,行为的发生属于工作开始前与工作结束后必要且不可或缺的。“工作场所”是指完成业务的场所。“住所”是指劳动者日常生活所居住的固定场所,包括租赁房屋、与家庭成员的合住房。“合理的路径和方法”是指劳动者往返住所与工作场所时,所采用的路线、方法、时间、经济上的合理性。近年来,日本逐步放宽了通勤灾害的认定标准,对于类似在通勤途中购买日用品、到医院就诊等行为,以通勤灾害进行判定。
因通勤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在时间、路线、往复性等方面相对稳定,相应行为皆与业务紧密关联,故以不同于传统工伤的保护方式,将通勤灾害纳入劳动者事故保护的范畴,并在缴费形式、缴费费率、休业等待期等实践层面进行了一定微调。
(三)工伤认定的基准
1.业务起因性和业务遂行性
业务遂行性和业务起因性是日本工伤认定的两大基准。业务遂行性是指劳动者以劳动契约为基础在雇主支配下的行为。①田思路、贾秀芬:《日本“过劳死”和“过劳自杀”的认定基准与启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19期,第102-108页。它既反映了劳动关系的本质,也是对劳动者所遭受伤害可获补偿与否的首选判定标准。
对劳动灾害业务遂行性的判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劳动者在雇主的监督管理下提供劳动;第二,劳动者虽处于雇主的管理状态下但未提供实际劳动(如待命过程);第三,脱离雇主的实际监督,但受雇主派遣提供劳动。由以上因素可见,“业务”概念不仅包括了劳动者的本职业务,亦囊括了从本职工作的附随行为到工作开始前的准备行为与工作结束后的收尾行为,一直到必要行为、紧急行为,甚至包括反射性行为等。②[日]河野顺一:《劳动灾害通勤灾害理论和实际》,日本:东京中央经济社2002年版,第3页。业务遂行性更为看重劳动者的工作是否属于雇主业务范围以及雇主是否因劳动者的工作获得利益。
业务起因性是指劳动灾害因工作事由引发,即工作与劳动灾害之间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意在突出劳动灾害的发生是因业务而起。日本学界有关业务起因性的学说,最主要且被普遍认同的当数“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指:“应当在使结果发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中选定若干条件,这些条件不论在特定情况下或一般情况下,都同样有可能使结果发生,将这些条件作为适当条件,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③髙野伸:《業務起因性をめぐる相当因果関係説の内容》,新日本法规出版社,2008,p.215.
日本劳动省所用的相当因果关系,与民法中的相当因果关系有所区别。民事侵权关系中,强调行为人对于损害结果是否具有主观预见的可能性,但在工伤认定中,则强调客观性因素(排除行为中的主观因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的影响。在工伤认定时,业务与损害结果间具有条件关系,且法律上认为两者应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一方面,对于业务与损害结果间,要求达到若员工没有执行该项业务,则不会发生损害结果的条件关系;另一方面,若因为劳动者执行了该项业务,就经验法则或根据一般社会通识加以判断,通常会有该损害结果的发生。④李辜:《论因果关系在工伤认定中的法律适用》,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8页。
“相当因果关系说”对于工伤的判断,排除了职业灾害中的主观因素,更为看重责任的成立,对于在业务内或对附随危险现实化限度内发生的不可抗力偶然事故,依然可做出工伤认定。例如,电力公司员工在高架电线杆上作业时,突遇龙卷风,致其坠落地面死亡,因其工作性质,根据经验法则,在龙卷风等恶劣天气下作业,易发生高空坠落事故,故承认工作与伤亡结果间存在因果联系,确定该劳动者工伤的业务起因性。
在日本早期的工伤认定中,劳动基准监督署遵从严格的业务起因性和业务遂行性的认定标准。一般先确认劳动者遭受的劳动灾害是否契合业务起因性,随后判定案件中的业务遂行性,两者是工伤认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随着日本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劳动者及其遗属的工伤权益,对于工伤认定,学者们不再严格坚持业务起因性与业务遂行性的同时具备,在认定技术上,偏重于业务起因性,缓和了业务遂行性的认定,工伤认定的标准呈现日趋宽松之态势。以“过劳死”的工伤认定为例,因“过劳死”多为工作随附的有害作用长期积累而缓慢产生,其发病时点不确定,与自身疾病不易区分,且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多等,导致业务遂行性确定上的困难。为了减轻受灾劳动者举证的困难以及确保认定的迅速、公平、标准统一,日本《劳动标准法施行规则》规定,“过劳死”只需满足业务起因性,即可认定为工伤。①田思路、贾秀芬:《日本“过劳死”和“过劳自杀”的认定基准与启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19期,第102-108页。
2.“过劳死”的工伤认定
日本从1987年就已开始对“过劳死”进行工伤认定,并制订了有关脑血管和心脏疾患的工伤认定标准。在1995年第一次明确了“过劳死”工伤认定的法律依据,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的范畴。随后在1999年,将“过劳自杀死”作为工伤,使以过劳死为起因的法定工伤事务范围得到扩展。1995年2月,日本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再修订,将由于过度劳累造成的健康损害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2001年12月,日本厚生劳动省修订了“过劳死”的认定原因,增加了日积月累的工作疲劳和工作紧张两个因素,并将判定时间拉长,从原来的1周改为症状前6个月。②王素芬、陈晓冬:《“过劳死”的日本立法与我国镜鉴——兼及对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修正》,载《行政与法》,2018年第2期,第100-104页。
当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对于“过劳死”的认定标准的设定,以处理业务过重性与原因竞合的判断为重点。过重性判断是指受灾劳工在发病前一段时间(评价期间)相较于一般劳工(基准劳动者)来说,是否从事过重业务,综合评价期间、基准劳动者、业务具体负荷状况等多方面予以分析。考量劳动者在死亡前6个月是否在工作时承担过重的精神或物质负担或过度劳动,并结合发病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时长、加班时长、出差强度、轮值班和深夜工作情形及工作环境中的湿度、噪音等一系列细化的客观数据来判断劳动者是否过度负荷,从而作为其能否认定为工伤的一项因素。③张雯娣:《“过劳死”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初探》,载《职工法律天地》,2017年第3期,第36-40页。对于业务因素与非业务性因素的原因竞合,以“相对有力原因说”进行处理,即在导致发病的全部原因中,业务原因相较于其他原因而言更为有力,方可认定业务与发病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四)工伤认定的流程
劳动灾害发生后,受害劳动者被立即送至劳灾指定的工伤医院治疗,同时雇佣企业需提交劳动灾害详细报告,并为受害劳动者开具事故证明。受害劳动者填写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附上雇佣企业的劳动灾害报告与事故证明材料,一并提交给日本工伤医院内设的工伤保险申请受理部。收到工伤申请之后,工伤医院的工伤医师从医学专业角度提出医学认定与审查意见书,并将所有材料提交给劳动基准监督署。劳动基准监督署随即对申请资料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做出是否为工伤的认定。受害劳动者住院医疗费用先由个人垫付,工伤医院只收取小部分治疗费作为保证金,一旦被判定为工伤,垫付的治疗费将返还至受害劳动者账户。
工伤认定涉及医学专业知识,对从事工伤认定人员的专业与知识背景要求较高,为保障工伤认定及伤残鉴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日本创设了工伤医师制度。工伤医师是日本工伤认定工作中的一大特色。日本从工伤医师的准入门槛、资格认定等方面,制订配套制度,全力提高工伤认定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工伤医师划分为中央工伤医师与地方工伤医师两类,中央工伤医师主要负责提交医学认定意见、参与医学认定培训、审查工伤认定申述等业务,地方工伤医师则负责地方职工工伤起因关系论证、提出工伤审查意见书等业务。
(五)工伤认定争议的处理
工伤认定的举证责任一般由受害劳动者承担,但当受害劳动者以雇主违反安全注意义务,请求损害赔偿责任时,则雇主承担举证责任。
“不服申诉及诉讼制度”是日本工伤制度的另一大特色,该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不服申诉的先行”原则。不服申诉是当受害劳动者或其遗属对劳动基准监督署作出的不为工伤认定有异议时,必须先向工伤保险审查官提出审查请求,如对工伤保险审查官的处理决定不满,则再向劳动保险审查委员会提交再审查请求。只有穷尽以上两级复议程序之后,受害劳动者或其遗属方能到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日本设立“先行申诉”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受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由于司法诉讼程序冗长、维权成本高昂,然而工伤保险机构具有专业经验与相关知识背景,工伤认定争议先经过复查,可让受害劳动者以快速且低成本的方式解决工伤争议。
三、日本工伤认定对我国的启示
(一)构建完善的工伤保险法律体系
日本工伤保险制度发展较早,《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劳动基准法》关于工伤保险的规定详细,配套措施完善,法律体系完备。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自2003年出台,距今已十七年之久,相关内容稍显粗糙,法律层级较低。虽然涉及工伤保险制度的法律规范数量多、内容多,但是体系差、效力层级不一。①郑尚元:《〈工伤保险〉之立法构想》,载《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39页。为构建公开、透明、科学、公正的工伤保险法制,建议政府尽早开展《工伤保险法》的立法工作,提高工伤保险制度的法律层级,完善我国工伤保险法律体系,以期更好地保障职工的工伤保险权益。
(二)扩大我国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
日本工伤保险是全行业参保,工伤保险制度几乎惠及所有劳动者,并将公务员群体也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充分体现了工伤保险的生活保障性与公平性。通过规定企业在成立注册登记之时自动加入工伤保险的强制性参保制度设计,保证了受害劳动者不会因雇主拖延办理或未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而影响工伤保险待遇的获得。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6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2.54亿人,工伤保险覆盖率不足百分之三十,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bjs/201912/t20191202_17130371.html,2020年10月11日访问。与日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伤保险参保率相比,我国差距尚远。
随着我国工伤保险事业的发展和扩面工作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获得了工伤保障。但是,近年来伴随共享经济出现的新业态就业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直播人员等,其工伤保险权益的实现是一个现实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在具有稳定劳动关系基础之上,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捆绑在一起,劳动者与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必要前提。然而,新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员是劳务关系,其劳动关系认定存在政策障碍,从而被排除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之外。另外,很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在工伤维权之路上异常艰难,究其根源在于用工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①赵一阳、周丹丹:《破解工伤职工维权难题》,载《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9年第4期,第42页。当前我国劳动法学界对于将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扩展至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呼声很高,有学者提出:将劳动关系与工伤保险“松绑脱钩”,从传统典型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方面出发,对工伤进行分层设计,以覆盖包括劳务关系和雇佣关系在内的广义劳动关系。②问清泓:《共享经济下社会保险制度创新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86-98页。也有学者主张新业态从业人员以“类雇员”方式参加工伤保险,从而保证其基本权利。③娄宇:《平台经济从业者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1-161页。以上观点均指出,面对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新业态从业人员数量激增,该群体的职业安全权益保障已到亟需解决的地步。为此,扩大我国工伤保险的覆盖人群,实属必要。
为让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后得到更好的工伤保障,做到应保尽保,化解劳动者的职业风险,实现劳动者工伤保障的共济,兜住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底线,我国应借鉴日本工伤保险的全覆盖模式,全面扩大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突破传统劳动关系的界定,将工伤保险与传统劳动关系“解绑”,④张岩:《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探析——以平台工作者为视角》,载《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90-94页。在遵循不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相冲突的基本原则下,根据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特点,创设适用于他们的工伤保险特别加入制度。首先,科学界定“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内涵,明确工伤保险特别加入制度的适用范围。建议将“新业态从业人员”定义为: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且具备劳动能力,从事社会职业的非劳动关系人员。该定义可将各类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其中。其次,通过搭建网络平台,以实名认证和网上申请审核的方式,将新业态从业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保护范围,实现我国工伤保险制度适用人群的全覆盖。
关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费用缴纳问题,可借鉴日本特别加入制度的经验,细化各行业缴费率,由新业态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结合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⑤李坤刚:《“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149页。保证新业态从业人员遭受工伤后享有公平、公正的工伤保险待遇。
(三)引入“工伤医师”与“不服申诉的先行”制度
工伤医师制度的设立,保证了日本在工伤伤残鉴定、职业病鉴定、过劳死认定、保险待遇支付上的科学性。工伤医师作为厚生劳动省劳动基准署的助手,在工伤认定中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而“不服申诉及诉讼”制度保证了日本工伤争议处理的上下贯通,大幅提高了工伤争议的解决效率,更好地保护了受害劳动者的利益。
我国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工伤认定工作。司法实践中,工伤认定部门要求劳动者提供劳动关系材料,如果有争议,首先得提起劳动仲裁,确认是否有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确认后,工伤部门受理工伤认定,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可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正常情况下,完成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需八至九个月。如对再次工伤认定结论不服,重复诉讼又需耗时八至九个月。工伤认定的制度缺陷导致工伤认定时间漫长、程序复杂、诉讼成本高,严重阻碍了工伤职工的权益及时兑现。
工伤认定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聘请医学专家提供专业上的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因此,建议引入日本“工伤医师”的成功经验,在我国成立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工伤认定审核委员会,提高工伤认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同时,借鉴日本“不服申诉的先行”制度,取消用工单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环节,让劳动者可以直接申请工伤认定,进而提起民事诉讼,简化工伤认定流程,提高工伤认定效率。
(四)调整我国工伤认定标准及内容
1.构建我国工伤认定的一般性条款
日本工伤之判断要点主要有二:其一是“工作上”,即具有工作关联性;其二是“负伤、疾病、残疾或死亡”,即表明可补偿的损害类型。至于何种情形属于“工作上”以及应采取何种标准判断是否属于“工作上”,则由法官依据案情进行自由裁量,立法并未加以限制。在具体的工伤认定中,日本采用颇为严格的业务起因性与业务遂行性标准,用以辅助及控制“工作上”的解释,使其不至过于原则,认定标准趋向宽松。①郑晓珊:《工伤认定一般条款的建构路径》,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9-135页。
我国工伤认定标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工伤保险条例》通过列举式立法,罗列了普通工伤的多数情形,但也无法穷尽将来之所有工伤情形;且列举式规定相对于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现实是静态的,无法适应新就业形态下的复杂劳动形式,部分工伤职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二是传统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的工伤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具体工伤认定执行时过于教条化,如严格限定三要素的同时满足,必定将本应受工伤保护的劳动者挡在门外,缺乏制度的包容性。
而工伤认定的一般性条款可以作为一把标尺,对工伤的现实情形进行概括和分类,突破“三工要素”的桎梏,对动态的劳动力市场情形给予包容,保证工伤认定制度的弹性。因此,笔者建议,借鉴日本的工伤认定标准,在现有列举式立法条款的基础上,增加可以进行普遍性工伤认定的一般性条款作为法律兜底。对于一般性条款的内容,可从以下两方面设定:第一,强调工作的关联性,在考量“工作遂行性”和“工作起因性”时,秉承总量控制的原则,动态审视“工作遂行性”与“工作起因性”,在具体工伤判定中,不论两要件的此消彼长,只要达到总量的最低限度即可。第二,扩大“人身伤害”的内涵,应将职业病、过劳死等对劳动者普遍造成的伤害纳入人身伤害的范畴。工伤认定的具体标准应当是人身伤害与工作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对这种关联性的确定辅以“工作遂行性”和“工作起因性”这两项具体有形的参考标准。②江贯沆:《我国工伤认定标准的法律问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7页。
2.将“过劳死”纳入我国工伤范围
日本厚生劳动省先后公布了四次“过劳死”认定标准(分别是1961年、1987年、1995年和2001年),从最初的灾害主义立场修正为过重负荷主义,并不断细化操作标准、放宽认定范围,用于迅速、准确地处理劳动者请求劳动灾害保险给付事项。四次标准的制定和发展,可以说是厚生劳动省对“过劳死”标准的自我修正。①张雯娣:《日本“过劳死”的法律认定与启示》,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7页。
我国目前并未将“过劳死”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但近些年关于“过劳死”的案件频发,社会关注度较高。特别是当下流行的“996”工作模式,现实中劳动者因工作时间过长引发的身体不适甚至死亡的案例并不鲜见。为此,从回应社会广为关切之角度,将“过劳死”纳入工伤保护不容回避。因而,笔者建议,现阶段有必要将“过劳死”纳入现有工伤保险体系,借鉴日本“过劳死”的认定经验,从评价时间的确定、基准劳动者的确立以及原因竞合的处理等方面着手,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过劳死”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