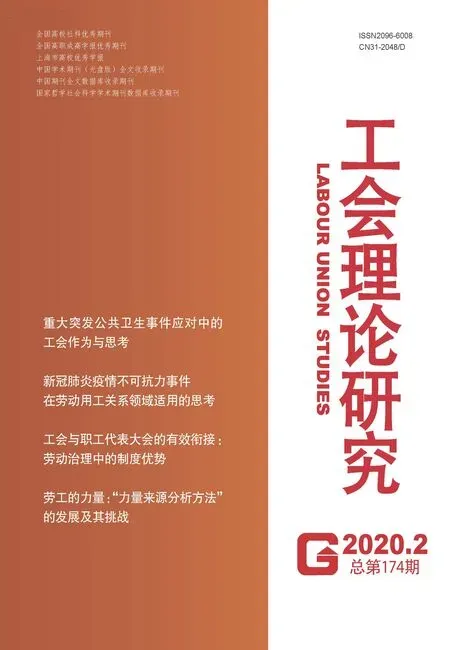欧洲福利制度下的工会危机
汪思余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欧洲拥有工会运动与阶级斗争的传统,工会在争取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产生重要影响。战后欧洲各国基于去商品化程度、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自由主义、法团主义和社会民主等三类福利体制,欧洲工会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建设福利国家这一核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状态,福利国家面临转型困境。与此同时,欧工联的建立使欧洲工会得以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影响,推动政治结构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引发工会的代表性和动员危机,促使其重新调整政策主张、推进福利制度改革。那么,欧洲工会究竟如何促进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其发挥作用的主要路径和基本模式分别是什么?未来将如何影响福利国家的转型?
本文简要梳理了战后欧洲工会的发展阶段,从原则、制度、平台和手段等角度论述工会影响福利制度的主要路径,探讨了福利政治框架下工会运作的基本模式,分析了工会未来面临的挑战及对福利制度的影响趋向,最后对西方工会制和资本主义福利制度进行反思和总结。
一、战后欧洲工会发展概述
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的、用以争取和捍卫劳动者权益的重要组织,在二战结束后得以迅速发展,欧洲工会便是最早取得合法地位的典型。
(一)背景:福利国家的建立
受到欧洲阶级斗争传统的影响,早期有关欧洲工会的研究大多从阶级与历史的视角出发,聚焦各国工人运动史,或是结合抗争政治理论,展现工会抗争中劳资双方的博弈。①[美]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上海: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71-97页。事实上,二战后西方最重要的制度转型便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战后欧洲工会的发展始终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重塑,即如何建设福利国家这一核心问题。与单纯的工会斗争理论相比,工会如何影响福利制度的形成和转型更值得探讨。
福利国家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俾斯麦政府建立的强制保险制度和二战期间英国实行的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模式,前者以职业作为核心条件,后者则由政府为全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保。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丹麦学者埃斯平-安德森依据去商品化程度,将战后福利制度划分为三大模式:英美等国实行的自由主义体制、法德等国采取的法团主义体制和北欧国家建立的社会民主体制。②[丹]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苗正民、滕玉英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38页。总的来看,福利制度的核心在于国家干预,即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制度安排及具体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付,帮助国民抵御社会风险,减少社会不公。③周弘:《福利的行政化与政治化》,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3期,第2页。
在福利国家何以形成的问题上,卡斯尔斯、马歇尔、埃斯平-安德森等学者认为,群体抗争、精英博弈与多重社会力量互动是福利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④Castles, F. (1986) : Working Class and Welfar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5-56.其中,埃斯平-安德森具体指出阶级动员的性质、阶级政治联盟的结构以及体制制度化的历史遗留是影响互动的重要因素。⑤[丹]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苗正民、滕玉英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页。劳动者是去商品化的主要载体,由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工会是动员工人阶级参与抗争和博弈的重要工具。正是在工会和国家机关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工会的力量得以增长,福利制度作为工会运动的成果得以建立和发展。
(二)欧洲工会发展的四个阶段
朱斌参照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以1951年社会党原则宣言的通过和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作为划分节点。⑥朱斌:《19世纪以来欧洲工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载《工会博览》,2004年第5期,第42页。史艳婷以欧工联建立为轴心,将战后欧洲工会的发展划分成分散活动和走向聚合两大时期,前一时期又可细分为战后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阶段。⑦史艳婷:《从分散到聚合——战后欧洲工会活动述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4页。两种分类存在的问题都是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发展对工会的影响,事实上这一阶段对工会形式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综合上述分类方法,并根据工会目标和组织形式的变化,本文大致将欧洲工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1.阶段一:战后恢复和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是欧洲各国恢复经济生产、完善民主制度的重要时期,西欧各工会将从法律上重新确立工会地位、保障工人权利作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如联邦德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委员会,意大利成立了代表工人的管理委员会。作为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工会组织,英国工会的发展表现在加入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劳、资、政三方共同协商经济活动。在法国,劳资的集体谈判得以制度化并在主要经济部门展开,作为工会运动的成果,补充退休金、失业补助制度先后得到确立。
在东欧等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会获得了全国大多数劳动者的支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进行改革:有助于政治民主化,有利于理顺工会与党政的关系,有利于强化工会的代表和保护的职能。①参见《苏联东欧工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载《探索》,1988年第3期,第37页。以波兰工会为例,1945年11月,波兰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波兰工会联合会作为统一的工会组织。波兰工会在参与建立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的工人政权、增进劳动者权益等方面起到助力作用。
2.阶段二:积极斗争与干预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除东欧以外,欧洲多国的工会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劳动斗争,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例如,20世纪70年代,全德工人联合会多次就雇员权益问题向政府和议会提出建议,联邦德国采纳其建议并颁布《企业条例》和劳动社保领域的系列法律。在工会的积极影响下,各国政府得以进一步协调劳资关系,加强干预社会的能力,完成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转型。
东欧工会则是在斗争中谋求改革。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一度为波兰、匈牙利等国工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此后的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激化社会矛盾,使东欧国内政治形势愈发紧张,工会运动更多表现为工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但另一方面,以匈牙利工会为代表的东欧工会进行改革。匈牙利共产党开始强调工会的自主性,进一步扩大工会权利。1967年后,匈牙利将扩大工会的权限视为扩大工人的权利,从立法上规定工会具有“否决权”,并开始实行“工会小组长会议制度”。②姜列青:《匈牙利工会初探》,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83年第1期,第38页。
3.阶段三:由分散走向聚合
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陷入“滞胀”状态,由于严重的失业危机,工会不敢轻易发动罢工,在劳资谈判中往往处于下风、屡遭挫折。③史艳婷:《从分散到聚合——战后欧洲工会活动述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页。这一时期工会活动出现的最大变化是1973年欧洲工会联合会的创立,欧洲工会由分散走向聚合,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其影响,进而推动政治结构的转变。
欧工联旨在解决工会内部的分裂问题,试图以一个声音说话,增强工会本身的号召力,并将欧洲社会模式作为政策主张。这一模式追求借助一系列制度安排、组织机构和价值信念,使欧洲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呈现出持续平稳、同步发展的和谐状态。④张尚:《欧洲社会模式下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0页。欧工联自成立后规模不断壮大,随着欧洲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职工和机构并入其中。欧工联成为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欧洲工会代表,在参与制定社会政策、保障劳工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阶段四:代表和动员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东西欧工会普遍出现了代表和动员危机。
对于西欧和北欧国家工会而言,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新型劳作方式,工会组织日益分散、组织动员能力受到削弱。第一,大量外国移民、新行业工人、临时工的出现,增强劳动者流动性,降低了工会的吸引力。第二,工会集体谈判能力降低,制度性对话被分解,谈判层次向下移动至行业、部门甚至个别劳资互动。第三,国家、资本、劳动力三方平衡被打破,逐渐呈现“强资本”与“弱劳工”的状态。①郑秉文:《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6期,第38-45页。
东欧国家工会面临的冲击和动荡更加明显。由于政治体制发生根本变化,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工会出现裂变,主要体现在从社会主义工会模式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工会模式,由统一的联合工会分裂为多元松散的众多工会,由民主集中制转为联合会制等组织原则,强调工会的独立属性并积极向西方靠拢。②姜列青:《东欧各国工会的演变及其特点》,载《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第23-24页。许多旧成员不再将工会视作工人利益的代表,新工会又因目标不清晰、官僚化等问题引起诸多不满。即使转轨期过后,东西欧工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仍相距甚远。
二、工会影响福利制度的主要路径
工会目标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与福利国家关系密切,那么在战后七十余年内,欧洲工会究竟如何影响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其发挥作用的主要路径是什么?
(一)主要流派对影响路径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动员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和合作主义理论都曾对工会运动的手段、途径、机制等内容进行分析。
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动员理论,这两大理论都从权力结构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理解工会活动的意义。戈夫、马克伦德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把工人阶级组织视为塑造公共政策的关键行动者,③Gough, I.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Marklund, S. (1982). Capitalisms and Collective Income Prote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in Europe and the USA, 1930-1975. Res. Rep,. Dept. Sociol., University of Umea, Umea, Sweden.认为工会在三方面起重要作用:第一,福利国家建立在正式承认工会的基础上,工会的结构性作用包括集体谈判和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能够平衡不对称的劳资权力,超越毁灭性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④[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第二,工会权力通过竞争而获取,力量受限制与赢得霸权地位是相对的,政治的根本层面就是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斗争。⑤[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第三,资本主义系统的不同部门去商品化和组织化的程度不同,垄断部门的工会实力更为强大,竞争部门的工会组织化程度更低。⑥[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阶级动员理论来源于社会民主政治经济学,代表学者有科皮、瓦伦斯基、卡斯尔斯等人,①Korpi, W.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Wilensky, H. (1981):Leftism, Catholicism and Democratic Corporatism. In P. Flora and A. Heidenheimer (eds),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Castles, F. (1981): How does Politics Matter? Structure or Agenc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Public Policy Outcom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p.9.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更强调工会的动员功能,并补充指出这一功能在推动建立福利制度时也会受到积极的反作用,即福利国家能强化工人运动,通过提供动员和团结集体力量的先决条件,为工人形成重要的权力资源。
其次是社会民主主义,代表性政党如何更好地改革福利国家是最终目的,工会被视为组织工人、发展出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力量,将阶级斗争转变为政治博弈。②Theda Skocpol and Edwin Amenta, “State and Social Polic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2 (1986), pp.131-157.1917年,韦伯就曾表示:“工会、社会民主党组织起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平衡作用,以避免乌合之众通过纯粹表决的方式达到直接而非理性的统治。”③[德]马克斯·韦伯:《议会与德国重建过程中的政府》,见C. Roth和C. Witrich(编著):《经济与社会(伯克利,1978)》,第2期,第1460页。冷战结束后,面对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矛盾激化的国内形势,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者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改革福利国家,建设投资型国家,创建积极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家庭”。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除了作为连接大众和政府的纽带外,工会还起到监督企业和政府、参与提供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实现公私福利机构合作等方面的作用。
最后是合作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会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在于以劳工组织代表的身份参与协商、达成三方伙伴协议。合作主义源于批判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社会思潮⑤白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其趋向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4页。,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成为分析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米什拉的概括最具代表性,他将合作主义定义为:“根据总的国家形势,为谋求各种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状态,而在社会层面上实行的三方伙伴。”⑥[加]R. 米什拉著,郑秉文译:《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60页。在伙伴关系中,国家对经济和生产进行适当干预,工会和雇主组织则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承担福利方面的责任,在妥协和共识中形成良好的制度安排。
(二)工会作用路径及其发展变化
上述观点各有侧重但分析框架尚不全面,结合怀特和西尔弗的研究可以构建完整的路径理论。怀特区分了工人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指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如工会与政党,后者指由于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产生的力量,包括市场谈判和工作场所谈判两类。⑦[美]贝弗里·J.西尔弗著,张璐译:《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基于怀特的研究,西尔弗系统地提出了工会的权力结构理论,他认为工会具有结构性和联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中最重要的是以罢工为武器动员大规模示威活动,联系性权力则是工人能够组织工会或政党,并扩大与其他社会运动合作斗争的能力。①王铁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82-99页。
综合既有观点,本文认为欧洲工会代表工人阶级而产生,又作为社会组织而存在,拥有结构性和联系性两大权力,能够采取谈判与非谈判、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参与抗争和博弈。在和国内行为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福利制度作为工会运动的成果得以建立和完善。具体来看,其影响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工会遵循自由、公正、民主、妥协、合作原则,这些原则扎根于历史文化之中,促进福利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左翼社会民主党是福利国家建设的主要倡导者,其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是自由、公正和民主,认为实现全面民主化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②朱斌:《19世纪以来欧洲工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载《工会博览》,2004年第5期,第45页。反对进行根本变革而是应考虑广泛阶层的利益,互相妥协合作,改良资本主义。从19世纪至今,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影响欧洲尤其是北欧工人运动和工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工会开展斗争和博弈的目的便是完成福利制度设计,以落实国家责任、保护社会权利、实现普遍幸福。上述原则始终存在于战后的欧洲工会中,即便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各国纷纷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破坏原有的劳资契约,资方对工会加紧实施对抗政策,工会仍然普遍坚持旧的社会契约,坚持改良和妥协。③[挪]阿斯布约恩·沃尔、郭懋安:《欧洲工会运动振兴的道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2期,第26-29页。客观上,推动了福利国家内部的阶级妥协与合作。
第二,三方合作制、多层次协商制与公民参与制是背后的制度保障。三方合作制指国家、资本、劳动力三方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互相妥协、达成合作,其中国家代表通常为政府部门,资本方主要是雇主联合会,劳动力代表则是工会。多层次协商制主要指将三方协商和劳资协商相结合,这种复合协商制度因国家和福利制度不同而有所区别,有文章表明德国、奥地利等国的集体谈判在产业一级展开,而英国和部分国家主要在企业层面进行。④朱斌:《北欧社会模式与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第43页。公民参与制下公民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是北欧社会的典型特征。工会作为最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制度影响下得以搭建劳、资、政三方对话平台,调和福利制度设计中群体间的矛盾,并起到凝聚各界共识、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制度为工会促进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重要条件,工会本身也在推动制度化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第三,工会是联系劳动者和主要政党、议会、政府的纽带,与政党、民众一同构成支持与被支持的利益共同体。首先,工会自诞生之初便代表了构成工会的劳动者的利益,工会活动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工人权益、增进劳动者福利。基于此目的,工会通过向议会提供方案、向政府提出建议等方式,反映改革建议,巩固组织基础。其次,工会与政党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一方面,工会与政党都能吸引和吸收人们的政治能量⑤[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5页。,但唯有政党是垄断提名权的社会组织,工会只能在合作者与反对派的立场上进行转换。另一方面,工会与工党、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格外密切,如北欧多国总工会主席担任该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常委,①朱斌:《北欧社会模式与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第42页。工人运动不断为内阁输送高层官员。可以认为,工人越充分地被工会和重要政党组织起来,工会本身的政治代表性越强,与政党、议会和政府的接触越密切,就越容易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现代福利国家就能越早越完全地实现发展。
第四,工会采取的手段包括但不仅限于动员罢工、直接提供福利、监督政府、工会合并、工会联合等方式。从工会权力结构来看,工会行使结构性权力主要体现在组织劳动者进行示威罢工,在斗争中避免削弱社会福利。联系性权力则表现为以集体谈判、提供建议的方式,在博弈中试图加强劳工权利。从直接和间接角度来看,工会既可以直接承担某一领域的福利责任,也通过监督政府以间接地落实福利政策。从国家和欧洲层面来看,为了增强工会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实力,不仅普遍存在国内企业和行业间的工会合并,而且出现了跨产业、跨国工会联合。从变化趋势来看,自战后恢复和发展阶段至今,欧洲工会的手段经历了“确立法律地位—提供政策建议—开展集体谈判—联合各国工会”的发展过程。福利政治框架下,尽管工会的结构性权力受到限制,其联系性权力仍然保持不断增强的态势。
借助上述渠道,欧洲工会在协调劳资关系、重新订立社会契约,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改革,完善民主制度、推进福利国家转型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劳资关系为例,欧洲将工会所代表的工人视为企业的一大支柱,其诉求必须在企业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②郁喆隽:《欧洲劳资冲突背后的工会身影》,载《社会观察》,2009年第9期,第61页。因此有效的工会组织在与资方保持对立的同时,能够减少潜在的冲突成本、实现劳资双方的和谐。可以认为,欧洲工会提供了理性对话的平台,促进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此外,赖因、埃斯平-安德森等人在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工会协助加速前资本主义体系衰落,代之以集体的市场契约。③[丹]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苗正民、滕玉英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5页。例如,随着工会加入谈判,传统福利救济形式的养老金逐渐被集体谈判的、契约式的养老金方案所取代,社会养老金体制得以最终形成。④Rein, M. (1982): Pension Polic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Welfare and the Delivery of Social Services, Berkeley, Ca. (November).
三、福利制度下工会的基本模式
受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长期影响,从横向上看,福利制度下各国工会的作用模式不尽相同,但整体上仍可归纳出几类基本模式。
(一)现有的欧洲工会模式分类总结
西班牙工人委员会书记哈维尔·多斯提供了较详尽的分类,基于对各国工会传统、实践等方面的考察,他将欧洲工会分为五类⑤毛禹权:《欧洲工会运动的现状、问题和前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5期,第23-26页。:第一类以英国职工大会为代表,不存在地方性代表机构,全国的产业活动彼此独立、配合较少;第二类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工会,多元化和分裂化明显,但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影响力较强;第三类是荷兰工会,主要通过社会对话达成重大的社会和劳工协议;第四类是德国和北欧工会,团结和一致性较强,共同参与社会民主模式的创立和一般政治问题的解决;第五类是奥地利工会,产业工会掌握内部的权力,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全国产业集体合同。
与多斯的分类相比,布吕纳对工会模式的划分更为简洁: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即北欧模式,代表性国家有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工会在拥有强大干预力的同时彼此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一种是多元模式即地中海模式,存在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工会观念强但通常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一种是行会主义模式即英国模式,英国职工大会垄断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①[法]贝尔纳·布吕纳、吕殿祥:《欧洲工人工会和雇主组织:三种社会文化模式》,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0年第12期,第27-29页。
总的来看,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划分德法工会,以及是否要将南欧模式单独作为一种基本模式。首先,有必要明确工会的特征与本国福利制度紧密相关。评价福利制度的依据是去商品化程度,划分工会的标准应当是工人阶级去商品化程度、工会的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其中竞争力和影响力体现出工会系统的效能。法国有合作主义和多元主义传统,管理机构较为分散、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劳资手中,②于蓓:《法国是个什么样的福利国家?》,载《法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5页。工会多元化程度较高、通常以行业为单位割据成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工会模式和南欧模式更为接近。尽管德国在国家主义、稳定的三方合作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下,工会竞争力适中、政治影响力大,其工会参与福利制度安排的程度与北欧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而更适用于欧陆国家的法团主义模式。
其次,南欧模式应被单独列为一种影响模式。与法团主义模式不同的是,南欧模式拥有家庭而非工人互助会的传统,在社会保障的基础上不论是工会还是政府实力都较为薄弱,无法同法德等国相提并论。并且由于少有文献从理论上分析意大利、西班牙等“较为失败”的南欧模式,③有限文献可参考[希]曼诺思·马萨噶尼斯著,吴颖蕾译:《无所适从?困境中的希腊福利》,摘自陈明明、刘春荣主编:《保护社会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5-95页。而探究何以失败与何以成功同样重要,因此有必要单独对南欧工会进行研究。需要补充的是,由于中东欧国家多处于转型阶段,工会运动薄弱,工会呈现多元化,因此暂不将其单独列为一种工会类型。
(二)北欧、英国、南欧和欧陆模式
综上,本文根据竞争性、团结性和干预力的强弱,将福利政治中的欧洲工会分为四类:北欧模式、英国模式、南欧模式和欧陆模式。其中,竞争性体现在工会数量和分散程度上,团结性表现为不同工会联合起来活动的难易程度,干预力则指工会通过一系列途径影响制度设计的能力。
一是北欧模式,即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工会所采取的竞争性较弱、团结性强、干预力强的团结模式。这种工会模式通常主动采取集体谈判、劳资对话等非暴力途径,并且具有范围广、介入深、效率高的特点,工人代表不仅以共决方式参与对企业的管理,还可以参与一般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①毛禹权:《欧洲工会运动的现状、问题和前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5期,第23页。在瑞典,雇主被迫接受工会在发生劳资冲突时掌握解释法律文件的优先权。②[法]贝尔纳·布吕纳、吕殿祥:《欧洲工人工会和雇主组织:三种社会文化模式》,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0年第12期,第28页。需要指出的是,北欧模式的优越性与其人口数量、历史传统有密切联系。朱斌认为北欧和谐的劳资关系与民族传统中的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密不可分,③朱斌:《北欧社会模式与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第41-45页。这一理念被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所贯彻。周弘在研究丹麦工会时表示,由于丹麦保存了农业文化及相对平均主义理念,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妥协、宽容、互助价值观成为福利国家的文化根源,社会政策更倾向于保守和渐进,能控制工会运动的激烈程度。④周弘:《丹麦社会保障制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载《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2期,第32-36页。
二是英国模式,即自由主义体制下英国工会所遵循的竞争性弱、团结性弱、有一定干预力的行会模式。英国模式较为特殊,首先,英国工会实行严格的行会主义传统,英国伦敦城市行业公会等产业工会具有真正权力并且彼此独立,能够影响政府和议会决策。其次,英国职工大会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工会机构,但无领导权和约束力,只能为其他产业工会和下属工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⑤郭稳才:《英国和奥地利工会运动的几个特点》,载《工会博览》,2004年第20期,第42页。最后,英国工会存在工会合并与多工会结构两大特征,⑥刘彩凤:《英国劳动关系的发展——工会、集体谈判与劳动争议处理》,载《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60页。其中合并包括防御性、巩固性和扩张性三类,⑦Undy, R, Ellis, V., McCarthy, W. E. J., and Halmos, A. M., The Development of UK Unions Since 1960, London:Hutchinson, 1981.多工会结构不仅包括工会数量和种类的多样,而且指劳动者可同时参加多个工会。与其他国家工会相比,英国工会缺乏协调、灵活性较差。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受到保守派势力的削弱,难以联合起来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达成强有力的协议,只能借助与工党政府的合作改善劳资关系,以增进社会福利,实现工会复兴。
三是欧陆模式,即法团主义体制下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工会所适用的有一定竞争性、团结性强、干预力较强的对话模式。与北欧模式相比,欧陆模式下国内工会数量更多,彼此存在竞争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工会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的演变趋势。与此同时,工会被赋予的权力有限,而且并未放弃使用游行罢工手段。以德国为例,德国工会联合会是国内最大的工会组织,下设有八大行业工会,包括五金工会、化学与能源工会等,由于以行业为基础,不同工会的类别之间存在交叉,为吸纳更多劳动者,工会恶性竞争和互相拆台的情况不可避免。⑧张莉芬:《对德国工会制度的反思——从德铁大罢工谈起》,载《工会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第41页。但总体上,欧陆模式下的工会组织比较温和,由于国内三方合作、集体谈判等机制较为稳定,工会能够在制定社会政策上发挥有效的影响力。
四是南欧模式,即地中海模式体制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工会所采取的竞争性强、团结性弱、干预力较弱的参与模式。南欧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工会在行业、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如法国存在法国总工会、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天主教工人联盟等工会组织。在意大利,宪法笼统地规定工会“团结一致”签订集体协议的有效性,并未限制企业等机构具体的工会活动,①丁骥千:《意大利工会组织的特点》,载《工会博览》,2004年第9期,第43页。即在事实上承认了工会的多样性。多元化的弊端是工会难以团结起来并达成共识,导致共同行动的力量分散化。此外,此类模式下劳动者采取街头罢工、游行示威的方式较为常见,如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2月,法国和希腊分别爆发了全国大罢工。在这些国家中法国较为特殊,一是法国工会权力相对较大,负责管理社会保护领域,②Bruno Palier, “The Long Good Bye to Bismarck? Changes in the French Welfare State”, in Pepper D.Culpepper, Peter A. Hall and Bruno Palier eds, Changing France: The Politics that Markets Ma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ian, 2006, p. 110.但随着国家对社会保障支出的介入加深,国家正在加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控制。③李姿姿:《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及其启示》,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5期,第151页。二是与此同时工会系统整体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碎片化程度尤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工会密度始终保持在10%以下。④顾昕、范酉庆:《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会运动:以欧洲主要国家为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4期,第59页。
四、欧洲工会的挑战及未来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跨国经济的发展,欧洲工会面临的挑战愈发严峻。欧洲工会未来将如何转型?如何影响福利制度的发展?
(一)工会危机和对福利制度的影响
本文认为欧洲工会的危机和对福利制度的影响趋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工会同时面对新旧双重社会风险。旧社会风险通常指从事传统行业的工人,由于退休或疾病、失业等工作中断的情况而承担的社会风险,与男性作为主要家庭供养者相关。⑤Taylor-Gooby, Peter F, “New Social Risk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ome Evidence on Responses to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from Eurobaromete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 57, No. 3 (2004), pp. 45-64.新社会风险主要指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被传统工会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所面临的新社会压力。根据瑞士学者博诺里的研究可以将其归为三类:协调不断增加的工作量与家庭责任关系的困难、知识型社会中低技能工作者随时面临失业和贫穷的困境、职业生涯中断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⑥Giuliano Bonoli, “New Social Risks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Social Politics”, in KlausAmingeon and Giuliano Bonoli (eds), The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6-7.与传统工人不同,承担新社会风险的群体主要是处理家庭与工作矛盾的女性、低技能工人和失业人群。
对于工会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新型劳作方式,工会成员不断流失,组织、动员和集体谈判的能力受到削弱,传统力量的基础受到侵蚀。当前,欧洲各国政府普遍以削减福利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主要方向。为了维护既有利益、巩固自身地位,工会不得不重视原先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增强吸纳整合的功能,重新调整工会角色。这对福利制度的影响是:一方面,工会通过新一轮更新、合并与重组,代表更广泛群体的利益,在工会活动中要求为不被社会保护的人群提供新福利。另一方面,由于新社会政策必须在传统社会政策领域的基础上拓展其干预的社会领域,①岳经纶、颜学勇:《走向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载《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5-98页。面对试图收缩福利的政府,能否避免工人的利益在谈判中被分权化和去管制化所侵害,②余南平、梁菁:《新社会风险下的西欧国家工会》,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85-106页。成功达成三方合作仍然是未知数。
第二,不同部门与行业工会间冲突加剧。首先是部门差异,早在1972年托马斯·加维特就撰文指出,在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私营部门的工会主义呈现衰落趋势,与之相反的是传统公共部门工会发展迅速,大量雇员协会兴起。③Thomas W. Gavett, Trade Union Membership, Business Economics, Vol. 7, No. 4 (Sep 1972), pp. 31-34.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斯平-安德森的研究表明,后工业社会中工会在不同部门间的差异变得突出,同时对于瑞典等部分国家而言,公私差异与性别分割相联系,并由此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冲突。④[丹]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苗正民、滕玉英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6页。其次是行业差异,蓝领工人一直是工会的核心关注,但蓝领工会日益受到服务业和白领工会挑战,不少研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欧洲工会面临的两难境地,便是争取高技术专家和白领的参与还是帮助缺少保障的低技能群体。⑤余南平、梁菁:《新社会风险下的西欧国家工会》,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95页。
这种矛盾使工会更关注短期利益,在涉及社会福利的重大议题上难以团结起来,采取更理智的方式应对,长期来看容易导致工会体系的内耗和分化。工会能否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发挥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能否搁置争议、暂时妥协。在2019年法国大罢工中,由于法国政府在退休改革方案中取消“特殊退休制”,引发公交、能源等行业工会的示威。以法国总工会为代表的强硬派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等改革派相互对峙,导致交通长期瘫痪,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第三,欧工联面临欧盟东扩后构建欧洲认同的难题。首先,随着捷克、爱沙尼亚等东欧国家工会陆续加入,欧工联需要消化东扩压力、扩展资金来源,协调东西欧、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工会间的复杂关系,增强政策影响力,并加强与欧洲以外地区工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其次,欧工联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形成欧洲认同。陈志敏曾表示欧工联本身是东西欧结束分裂和意识形态淡化的结果,⑥陈志敏:《欧工联的机遇与挑战》,载《欧洲》,1993年第1期,第47-50页。作为欧洲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欧工联主张实现欧洲范围内的民主、自由与平等。然而,欧工联参与政治活动背后的理论渊源是合作主义,但由于缺乏欧洲认同,合作主义存在民主赤字危机。⑦张尚:《欧洲社会模式下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0页。换言之,欧工联与欧盟共同面临如何实现一体化的难题,不仅需要实现建立劳工层面的欧洲认同,还需要推动雇主和政府层面的联合行动。
对福利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随着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欧工联与欧洲雇主协会将在协调欧洲劳资关系、增进欧洲福利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二是为福利制度转型提供超越国别的思路,即欧工联从强调工会的竞争性转向加强吸纳整合的功能,从分散的工会斗争转向团结合作的工会联盟,如今试图构建涵盖国内工会运动、区域工会组织、世界工会对话的蓝图。依此,欧洲国家在调整福利制度时也应当突破国家的局限,从比较和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
(二)对西方工会和福利制度的反思
从18世纪中叶英国出现最早的工会组织至今,欧洲工会走过了两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纵观战后工会发展史,在工人阶级斗争、工会与政党等多重社会力量互动之下,欧洲各国得以改革资本主义,完成向福利国家的转型。不可忽视的是,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工会在福利政治框架下的身份和意识危机。
首先是身份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会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阶级属性是工会的基本属性。工会本身是工人阶级为了加强自我保护而组建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争取工人权益。然而,西方工会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遵循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王铁军曾指出工会与资本谈判时具有“受压迫阶级领导者”与“异议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在赞同与强制之间维持平衡。①王铁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89页。奥菲也表示如何保证对其他组织的竞争力成为工会领导人关注的焦点,受结构性力量的驱使有时提出激烈的诉求。②[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在许多情况下,冲突往往产生于工会领导人之间而非国家与工会之间。事实上工会不仅无法完全反映工人的意见,其领导层还与雇主联合会、政府共同构成阶级妥协体系,不断边缘化工人阶级,将不同部门与行业劳动者争取福利的行为与采取工会保护措施联系起来,阻碍工人获取真正的福利。
其次是普遍的意识危机,更为严重的是战后长期的社会契约思想使工会失去了阶级意识和主导愿望。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下,社民党长期实施阶级妥协政策,导致工人的阶级身份逐渐被淡化、思想呈右倾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工会的基础。阿斯布约恩·沃尔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他批评欧洲的劳工运动以放弃社会主义目标为代价换取福利国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北欧、西欧福利制度的实质是将阶级妥协制度化,这种短期成就助长了工人阶级的非政治化和非激进化。③[挪]阿斯布约恩·沃尔、郭懋安:《欧洲工会运动振兴的道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2期,第26-29页。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工会和劳动阶级的议价方式无形中被资方主导,并与之趋同。
进一步分析可知,工会面临的危机实质上反映了福利国家的深层矛盾。其一是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矛盾是支持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同时,通过干预工会活动等方式使劳动力和资本不断撤出,打破宪政安排。④[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130页。工会组织被分化瓦解,有限合作的合法性和约束力十分脆弱,无法解决工人去商品化问题。其二是权力中心与主体多元化的冲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合作主义的结构变化后促进了非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⑤[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2页。非正式、不显眼和非公开的程序愈发突出,⑥[德]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63页。政治权力中心将愈发从官方制度中隐退。面对全球化浪潮,阿尔夫·斯科尔特等多元主义者进一步表示全球文明形态将超越民族国家的组织结构,提倡一般性的改良全球资本主义。①[英]安德列亚斯·比勒尔著,工力译:《欧洲工会和社会运动联合反对新自由主义(上)》,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第40-41页。
总而言之,战后欧洲工会在遵循自由、民主、妥协等原则基础上,采取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参与抗争和博弈,成为联系民众与其他组织的重要纽带,深度参与了福利制度的形成和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受到福利框架的重塑。基于竞争性、团结性和干预力方面的差异,欧洲工会可划分为北欧模式、英国模式、南欧模式和欧陆模式。不论何种模式,工会始终面临身份和意识危机,其实质反映了西方工会制度和福利制度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不断发展,福利国家的转型压力日益增大,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失灵恰好为工会重新调整三方合作关系、摆脱边缘化地位、推动市场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契机。未来,欧洲工会应重新认识自身的阶级属性,开展争取劳动质量的斗争,并发挥欧工联在组织和影响上的优势,在欧盟内部推动形成劳、资、政三方面的欧洲认同,在外部加强跨国合作与国际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