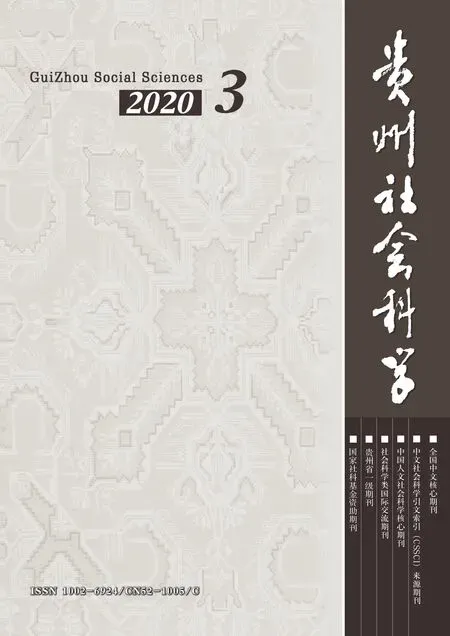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评点叙论
胡建次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一、《草堂诗余四集》版本与体例
沈际飞选评《草堂诗余四集》现存三个版本,一为明末翁少麓刊印本,二为明末万贤楼自刻本,三为明末吴门童涌泉刊印本。三种本子均为四集十七卷。其中《草堂诗余正集》六卷,《草堂诗余续集》两卷,《草堂诗余别集》四卷,《草堂诗余新集》五卷。沈际飞选评《草堂诗余四集》延续了武陵顾从敬刊刻《类编草堂诗余》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编的体例,为分调本。其“发凡”云:“《正集》裁自顾汝所手,此道当家,不容轻为去取,其附见诸词,并鳞次其中。《续集》视顾选尤精约,悉仍其旧。《别集》则余潜为排缵,自宋泝之而五代,而唐,而隋;自宋沿之而辽,而金,而元,博综《花间》、《尊前》、《花庵选》宋元名家词,以及稗官逸史,卷凡四,词凡若干首。新集钱功父始为之。恨功父搜求未广,到手即收,故玉石难陈,竽瑟互进,兹删其什之五,补其什之七,甘于操戈功父,不至续尾顾公。”[1]这里,沈际飞明确交代了《草堂诗余四集》的各自选编情况,道出了其选评目的及特点等。可见,《草堂诗余四集》是以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及钱允治所选词作为基础删改增补而成的,体现出一家之独特审美追求。
《草堂诗余正集》为“云间顾从敬类选,吴郡沈际飞评正”,总六卷,共选录词作465首。其中,卷一小令134首;卷二小令、中调97首;卷三中调57首,长调19首;卷四、卷五、卷六长调158首。《草堂诗余正集》选词以周邦彦、苏轼、秦观、欧阳修等人为多,且多为柔婉绵丽之作。如仅卷一中,所选秦观之作就有《捣练子》《如梦令》《浣溪沙》《菩萨蛮》《阮郎归》《画堂春》《海棠春》《柳梢青》《南柯子》《鹧鸪天》等,由此可见一斑。
《草堂诗余续集》分上下卷,为“毗陵长湖外史类辑,姑苏天羽居士评笺”,共选录词作187首,其中,上卷小令95首,下卷中调、长调共92首。《草堂诗余续集》延续了《草堂诗余正集》的选编风格,艺术趣味偏于婉约柔美的一面。
《草堂诗余别集》为“娄城沈际飞选评,东鲁秦士奇订定”,凡四卷,共选录词作462首。相较于《正集》《续集》对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的沿袭,沈际飞于《草堂诗余别集》中大胆突破,广选南宋人之词,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如仅蒋捷之作,《别集》中就选录38首;辛弃疾之作位居第二,选录20首,远多于其他词人。
《草堂诗余新集》乃于钱允治所选词的基础上辑编而成,为“吴群沈际飞评选,钱允治原编”,凡五卷,共选录词作524首。相较于《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其显著扩大了所选词人的范围与数量,收录明人之作相当可观,当代词坛名家诸如高启、徐渭等皆有入选。虽然,沈际飞在“发凡”中仍遗憾道:“今人之词,方云霞其蔚蒸。如升庵《填词选格》、《词林万选》、《词选增奇》、《填词玉屑》、《诗余补遗》、《古今词英》、《百琲明珠》等书,已不复见,矧宋元遗本,其饱蠹覆瓿者,不知几何矣。又如我明宋潜溪、解大绅、王阳明、王守溪、于廷益、何大复、唐荆川、杨椒山、莫廷韩、梅禹金、汤海若、黄贞父、汤嘉宾、骆象先、钟伯敬、丘毛伯、陶石篑、屠赤水、王百榖、袁中郎诸公集中无词,而陈眉公、张侗初、李本宁、冯具区、王永启、钱受之、邹臣虎、韩求仲、顾邻初、王季重、董玄宰、谭友夏、赵凡夫诸公尚未有集,坐井窥管,自分不免。”[1]针对明代一些代表性词人之作的具体留存情况,沈际飞志在有补于各种文集或词选之缺漏,尤其是对那些还没有结集的词人而言,他认为选集便更具有一定的意义。事实上,《新集》改善了彼时明人词作少有选录的状况,对后继者亦提出了“有同志者,不妨惠教,以嗣续编”的愿望,它对促进明人词作的传播接受有着显著的意义。
二、《草堂诗余四集》的主要批评观念
(一)主张以情为本
沈际飞《序草堂诗余四集》云:“通乎词者,言诗则真诗,言曲则真曲。斯为平等观欤!而又有似文者焉,有似论者焉,有似序者焉,有似箴颂者焉,呜呼,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1]这段话明确表现出沈际飞推崇情感表现的艺术观念。他论说诗词曲之体虽然其内在质性有异,在创作取向上也显示各异的特征,但它们在以情为本上是完全相通的,情感表现成为传统文体的内在本质要求。沈际飞在评周邦彦《夜飞鹤》(河桥送人处)时感慨:“今之人务为欲别不别之状,以博人欢,避人议,而真情什无二三矣!能使骅骝会意,非真情所潜格乎?物既如是,人何以堪!”[1]他遗憾于一些人漠视情感真实之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不由唏嘘,其对情感表现的推重可见一斑。
明代词坛重视情感表现者不少。如,杨慎《词品》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予友朱良矩尝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言亦有理也。”[2]467杨慎肯定词作以情感表现为本位,但他主张情感表现要更多地合乎中和的原则,要有利于养就主体心灵的宁静谐和,其在本质上与沈际飞所倡导情感表现是有所差异的。
沈际飞大力肯定词作表现男女之情。他在《序草堂诗余四集》中云:“虽其镌镂脂粉,意专闺襜,安在乎好色而不淫?而我师尼氏删国风,逮《仲子》、《狡童》之作, 则不忍抹去。曰:‘人之情, 至男女乃极。’未有不笃于男女之情,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间,反有钟吾情者。”[1]沈际飞认为,男女之情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因此,他肯定那些描写个人情感生活之作,重申其“不忍抹去”之意,将张扬人的情感作为词的创作的重要原则。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四集》中收录众多儿女情怀之作并予以大力肯定。如其评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云:“人之情至少游而极。”[1]感慨秦观在词中描述的“蓬莱往事”、吟诵的消魂离情感人至深。其评曹云宠《如梦令》(门外绿阴千顷)云:“‘不胜情’三字包裹前后。”[1]评赵德鳞《锦堂春》时,直言“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一句,“反其指而用之,情思缠绵动人”。[1]如此等等。
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别集小序》中描述了人之纷繁复杂的情感状态。其云:“块然中处,喜则心气乘之,怒则肝气乘之,思则脾气乘之,恐则肾气乘之,悲忧则肺气乘之,惊则五脏之气乘之。人流转于七情,而《别集》中怜合万状,触目生芽,怒然而思,侠然而惊,哑然而笑,澜然而泣,嗷然而哭,捶击肺肠,镂刻心肾,年千世百,无智愚皆知,有别欤无别欤?”[1]沈际飞认为,人的各异情感的产生是与其身体的不同器脏紧密联系的。人生而有七情六欲,正是因此而使人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状态,引人投身与沉入。《草堂诗余别集》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地抒写出人的多样情感意绪,形象地表现出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从而触动人心。沈际飞充分肯定选集中的词作对人情感表现的细致,认为这样的抒情写意是有着其艺术魅力的。如他在评朱敦儒《鹧鸪天》(检尽历头冬又残)时,赞其“奇趣豪情”。[1]评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时,言“燕然未勒”句,“悲愤郁勃,穷塞主安得有之”。[1]可见,在沈际飞看来,词作所表现不只是男女相思别离困苦之情,同样也有忧国患民之情、忧愤不平之情甚至各种奇情异趣等。人生而有情,其情生于心而需发抒于外,以词传情自然是合乎人之本真的。沈际飞把情感抒发作为评判词之高下的首要标准,这道出了词之艺术表现的本质所在。他于《序草堂诗余四集》中感叹:“故诗余之传,非传诗也,传情也,传其纵古横今体莫备于斯也!”[1]沈际飞将情感表现概括为各种文学之体共通的表现内涵,此论很好地道出了词的本质便在于抒发情感的功能。
(二)强调由丽入雅
明人词学评点有着自身的特色,形成独特的话语系统。在明代词学评点中,诸如“妖”、“娇”、“媚”、“俊”等字出现频率较高。如卓人月、徐士俊所选《古今词统》评紫竹《踏莎行》(醉柳迷莺,懒风熨草)云:“起八字何其娇腻。”[3]317评董斯张《减字木兰花》(谁能消受)云:“遐周所得六朝镜铭,未及此词妖丽。”[3]151作为批评家的沈际飞,其选评词作也呈现出这样的倾向。如评刘过《沁园春》(洛浦凌波)时,赞“‘载不起’句妖治”。[1]评贺铸《摊破浣溪沙》(锦鞯朱弦瑟瑟徽)时,夸其“娇艳。好模好样”。[1]在《草堂诗余续集》中,沈际飞评杜安世《渔家傲》(疏雨才收淡苎天)时,直言其“媚极,不媚不怨”。[1]类似的字眼,在评黄庭坚《水调歌头》、秦观《海棠春》、辛弃疾《祝英台近》、王世懋《解语花》、韩文璞《南乡子》、高观国《玉蝴蝶》、王世贞《望江南》等篇什中皆有出现,可见,沈际飞深受时代文化的影响,讲究词的创作具有婉丽动人艺术面貌及表现效果。
但是,沈际飞在追求词之柔美的同时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主张词当有雅致之性。他在《序草堂诗余四集》中认为,“词吸三唐以前之液,孕胜国以后之胎,斟量推按,有为古歌谣辞者焉;有为骚赋、乐府者焉;有为五、七言古者焉;有为近体、歌行者焉;有为五、七言律者焉;有为五、七言绝者焉。”[1]沈际飞主张词乃博采众体的产物,而不少人仅以“艳科”视之,所以提高词品甚为关键,而要提高词之品格,去俗复雅乃必由之路。因而,他在《草堂诗余四集》中尤为强调词之雅质的重要性。如其评周邦彦《蝶恋花》时云:“美成能为景语,不能为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价微劣于柳。”[1]直接表明了所持雅之质性优于华丽之象的态度,把词之雅质放在甚为重要的位置。无独有偶,其评贺铸《浣溪沙》时亦道:“俗化雅,更简远。”[1]沈际飞称扬贺铸能巧妙地化俗为雅,有效地拓展了艺术表现之道。其评欧阳炯《菩萨蛮》时,还云:“没情雅,此《花间》不如《草堂》处。”[1]强调情感表现的入雅避俗乃《草堂诗余》的独特优长之处。
然则何谓“雅”?“雅”源于《诗经》中的音乐分类,与“俗”、“郑”相对。当“雅”与“俗”相对时,雅取“高雅”之意;与“郑”相对时,取“雅正”之意。虽如此,不同文人对词之雅义亦有各异的理解。沈际飞的词雅观念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主张以情感表现作为区分词之雅俗的准则。他认为:“词以弄月嘲风为主,声复出莺吭燕舌之间,不近乎情,不可邻于郑卫,则甚景而带情,骚而存雅不在兹乎?委婉深厚,不忍随口念过,汉魏遗意。”[1]在他看来,情感的真挚与否是十分关键的,它从内在影响着词的雅俗之面貌。如其评李煜《菩萨蛮》时云:“俚言也,诚言也。”[1]对李煜词中运用俚俗之语表现真挚之情甚为称扬。他在评周邦彦《蝶恋花》时,亦为周氏“能为景语,不能为情语”感到遗憾。可见,沈际飞眼中的雅词,即为感怀于心而抒发之外的真情之作。
那么,怎样才能创作出具有雅之质性的词作呢?在沈际飞看来,创作者的艺术功力是甚为关键的。首先,他认为,词一旦质实,则难有雅趣。如其评姜夔《琵琶仙》(双浆来时)云:“词大忌质实,白石道人《探春慢》、《一萼红》、《扬州慢》、《暗想》、《疏影》、《淡黄柳》诸曲,多清空骚雅,惜难备录。”[1]而至于词之用语,则不必拘泥,灵活使用即可。其评张先《系裙腰》云:“末句即诗之杂体,如双声叠韵、离合回文,及五色四时,药名县名于类,一时活计也,在诗可憎,词原有可取。”[1]可见,沈际飞认为雅言俚语皆可入乎词中,真正区分词之雅俗的,是其是否发乎于内并展现真情实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沈际飞认为,无论雅言抑或俚语,经过艺术提炼皆可成为雅词,然而雅俗同篇是不可取的。其评方俊《鹊桥仙》(草头八尺)时,即毫不讳言:“词作俚语必极俚,不许入一雅句。如征仲《鹊桥仙》:‘看取金茎,入手和气,东瀛祥光南极。德庆无涯,寿星方照’等语不雅不俗,厌睹删之。”[1]沈际飞感慨不同风格的字语混杂于一篇作品之中,会严重影响其审美表现效果,势必拉低了词作的艺术价值。
综上可见,沈际飞推崇词之雅性的实质是其“情至”观念合乎逻辑的延展,是主张以情为本的具体落实,与“情至”审美理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与张炎所主张“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役,则失其雅正之音”[2]266不同,沈际飞所论之雅,更偏向于一种艺术特色,至于词之思想内容,如吟诵爱国之情,抒发相思之怨,抑或琐忆山间闲趣,凡此种种,他认为皆能呈现出雅致的特征。可以说,在沈际飞的词学观念中,“雅”的涵括范围被大大扩展了,其所生发的内容也被有意更新了,这对于词的发展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三)推崇自然生动
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四集》中还体现出重自然、反雕饰的批评倾向。明词创作多有尘俗纤绮之弊。陆蓥《问花楼词话》曾云:“人有恒言,唐诗、宋词、元曲三者,就其极盛言之。风气所开,遂成绝诣。明以时文取士,作者辈出,诗学殊逊唐、宋。即如填词,虽刘诚意之雄略,夏少师之警悟,坊间所传二公开元乐、浣溪沙诸阕,犹恒人耳。王元美艺苑卮言,辨晰词旨,而所为小令,颇近雕琢。”[2]2544这里,陆蓥在称扬刘基之词雄迈放旷,夏言之作警悟启人的同时,批评王世贞所作词流于修饰雕琢。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亦道:“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4]255王国维感慨明人词作虽有不少佳言妙句,但始终存在雕琢字句的弊端,致使词作局促委顿、难成大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沈际飞倡导重自然、反雕饰的审美观念。
他在评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时,赞其“古词妙处,只是天然无雕饰”,[1]将唐五代词之妙定位在自然无雕饰的基点之上。其评刘过《唐多令》(芦叶满汀洲)时,又道:“情畅,语俊,韵协,音调,不见扭造,此改之得意之笔。”[1]从情感表现、语言运用、韵律协调等角度肯定刘词的自然本色特征。他也对万俟雅言《长相思》(短长亭)大为称赞,认为:“此词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工而平,丽而雅。要字新刺。”[1]可见,沈际飞认为,词人的独特思致惟有在自然状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运行。
但沈际飞所追求的自然,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朴素质朴,其所倡自然,是经过精心构思而呈现的自然流动,是遵循旨法而又不拘于格套,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不觉其妙而自妙”的浑成状态。如其评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时,便赞“高手作文,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当限以绳墨”。[1]此外,沈际飞还认为,词的自然在于它与情思的浑融涌现。若无情而为,所作之词势必缺少自然之感。因而,自然之词当“心与景会,落笔即是,着意即非”。当然,词的自然离不开字语的天机自运,自然之语能让读者于具体字句中跳脱而出,深入词作的意境之中。正如沈际飞在《草堂诗余正集》中评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时所云:“读他文字精灵,尚在文字里面,坡老只见精灵,不见文字。”[1]称扬苏轼善于以自然之语而表现灵动之意致。其评方俊《鹊桥仙》(草头八尺)时即赞道:“韵脚天然。”可见,沈际飞倡导的重自然、反雕饰是有着多层次内涵的,惟有在多维度中都把握好“自然”,方可创造出生机充蕴之佳作。
(四)倡导翻新出奇
宋代词人队伍之壮观,作品之璀璨,让人望之兴叹。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曾云:“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2]618刘体仁指出,明初词人并非不想超越前人,造成他们与宋人相差甚远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艺术上缺乏自身之独特创造。面对难以逾越的高峰,明代一些有识之士是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四集》中明确表现出倡导翻新出奇的批评观念。其评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云:“‘宠柳娇花’又是易安奇句,后人窃其影似犹惊目。真声也,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能通于人。”[1]评苏轼《菩萨蛮》时亦道:“以孟公仿述古,今成滥套。”[1]可见,沈际飞对明人流于模仿、难以创新现状的不满。他格外留意词的翻新出彩之处。其评秦观《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云:“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少游翻之,文人之心浚于不竭。”[1]评苏轼《浣溪沙》(风压轻云贴水飞)时,赞“首句化腐为新”。[1]评陆游《卜算子》(驿外断桥边)时,夸其“排涤陈言,太为梅誉”。[1]等等。沈际飞对苏轼、陆游等人善于活化前人之功表现出十分称赏的态度。
由上可见,沈际飞并非否定学习前人,他注重的是,词的创作不能止步于效仿,而要在学习前人的同时注重激活创新,形成自身独特的面貌。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翻新出奇呢?沈际飞主张,首先,词人应当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其评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时云:“七夕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1]沈际飞认为,世人皆言聚少离多之苦,秦观却能从另一角度立意,生发出独特的主题表现。其次,翻新出奇需要词人自身丰富的想象。他评欧阳修《浪淘沙》(帘外五更风)时云:“‘吹梦’奇。幻想异姿。”[1]评黄升《南乡子》(万籁寂无声)时,赞其“幻思,幻调”。[1]词的创作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优秀的作品离不开瑰丽多彩的想象。因而,要做到翻新出奇,能以寻常之景构非凡之思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立新意,抑或利用自身的积累与想象创造佳句都对词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而,沈际飞又退而求其次,认为词人可以“援引古事”,但应注意的是“不为古用”。如其评秦观《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时云:“末用李词,古人爱句,不嫌相袭。”[1]秦观虽然袭用前人词句,但不为古人之意所拘限,形成“脱胎换骨”的艺术效果,这就是翻新出奇了。
总之,虽然历代文论家多有倡导翻陈出新之言,但在词学领域,沈际飞对该艺术观念的着意强调,可谓对词的创作大胆创新的切实鼓励与导引,蕴含着他对明代词坛变化的细心眷注与深切关怀。
(五)讲究章法格韵
沈际飞所追求的自然并不等于粗鄙质朴,他追求的是在艺术创造后形成的自然流动。因而,创作方法对于一首佳作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沈际飞在所选评《草堂诗余四集》中展现了其对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的重视。
他认为,巧妙选取合适的字语,可让整首词更加精彩动人。其评周邦彦《宴清都》(地僻无钟鼓)时云:“‘千俦万侣’上用个‘算’字妙。”[1]认为一个“算”字为词作增色许多。评张先《生查子》(含羞整翠鬟)时,亦赞:“‘锁’字入此处致甚。”[1]评秦观《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时云:‘乍雨乍晴’句妙,不在‘叶’字,而在‘乍’字。”[1]评苏轼《虞美人》(持杯遥劝天边月)时云:“奇于‘劝’字、‘愿’字。”[1]可见,沈际飞格外留意词作炼字炼意的精彩生动之处。
此外,沈际飞认为,对于重复用字当持以谨慎的态度,勿因重复用字而损伤词之面貌。其评毛泽民《于飞乐》时,便道其“‘记’字犯重”。[1]评田不伐《南歌子》(团玉梅稍重)时,亦指出用字重复的问题,言其“‘扇’、‘风’二字犯重”。[1]当然,沈际飞对于重复用字并不一概反对。如他对詹天游在《多丽》(晚云归)中的用字重复现象,就表示“意承前,不嫌字复”[1]。可见,字语是否重复,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应谨慎使用又不一概而论。
但是,在沈际飞看来,仅仅注重字语的使用还是不够的,优秀的词人应将佳字妙句与谋篇布局结合起来。其评史邦卿《绮罗香》云:“一曲之中,句句高妙者少,但相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处用工取胜。”[1]这正表现了他注重谋篇布局的整体观念。沈际飞认为,词的起句与结句十分重要。优秀的开头与结尾有利于营造整体的艺术表现效果。其评何籀《点绛唇》(莺踏花翻)云:“起句结句俱难得,填词每以此取胜。”[1]整首词皆为佳句是十分困难的,因而词人应当格外注重起结之句的精妙,这样,即便中间部分相对普通些,也能使整首词显示出艺术魅力。其评晁补之《洞仙歌》(青烟幕处)还云:“凡作诗词,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青烟幕处’至‘卧桂影’固已佳矣;后段‘都将许多明,付与金搏’至‘素秋千顷’,可谓善救首尾者也。”[1]除此之外,沈际飞还主张作词应当曲径通幽,有所转折起伏,反对过分袒露有失新意。其评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时云:“转转折折,忤合万状,清风朗月,陡化为楚雨巫云,阿阁洞房,立变成离亭别墅,至之也。”[1]无独有偶,在对秦观《桃源忆故人》(碧纱影弄东风晓)的评点中,他对秦词也大为赞赏,言其“‘海棠开了’下转出‘啼莺妆点’,趣意不窘”。[1]可见,沈际飞主张,作诗填词有所转折往往可收到奇特的艺术表现效果。
当然,词的格调韵律也尤为关键。元明之际,北曲流行,词韵与曲韵相混现象突出,沈际飞认为,这种现象迫切需要得到遏制与纠正。他在《草堂诗余四集·发凡》中即感慨道:“钱塘胡文焕有《文会堂词韵》,似乎开眼,乃平、上、去三声用曲韵,入声用诗韵,居然大盲。世不复考,将词韵不亡于无,而亡于有,可深叹也。愿另为一编正之。”[1]可见,沈际飞对词作声律表现抱有极大的忧虑。与杨慎等人不同,他认为,词韵与曲韵不可混同,“上古有韵无书,至五七言体成而有诗韵,至元人乐府出而有曲韵。诗韵严而琐,在词当并其独用为通用者綦多,曲韵近矣。然以上支、纸、置分作支思韵,下支、纸、置分作齐微韵,上麻、马、祃分作家麻韵,下麻、马、祃分作车遮韵,而入声隶之平上去三声,则曲韵不可以为词韵矣。”[1]因而,在《草堂诗余四集》中,沈际飞格外关注词的格调韵律问题,对于作者所犯韵律之误,他都一一指出。
沈际飞在评叶梦得《念奴娇》(洞庭波冷)时道:“下句大意不差,但换韵换字岂以《念奴娇》仄调耶!然《忆秦娥》调仄而孙夫人独平,《柳梢青》调平而贺方回独仄。调无相似者,平仄者不妨耳。‘破’字‘过’字换韵误。”[1]此论指出了叶梦得用韵换调的失误之处。其评苏轼《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时,亦云:“或以‘歇’字似趁韵,非也。”[1]沈际飞对词作用韵的评点,在《草堂诗余四集》中还有多处。如其评张仲宗《渔家傲》(楼外天寒山欲暮)时云:“杨升庵以否与主同叶,呼否为府,实闽音也。曹元宠梅词亦以否为府,皆非。及考《中原音韵》却宜同叶,升庵之论不可尽信。”[1]沈际飞坦言,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一书中,主张“否”与“主”协音,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其评黄庭坚《阮郎归》(烹茶留客驻雕鞍)时,还云:“一字自相为韵,出于汤铭盘而韵上日字亦韵,四韵皆‘山’。前句四韵亦叶盘铭之□□。”[1]足见他对词之格调韵律表现的重视。严格区分词韵与曲韵,主张用韵换调皆需慎严,这是沈际飞对词的创作提出的基本要求,《草堂诗余四集》中的评点正体现了其艺术原则与审美理想。
三、《草堂诗余四集》的选评价值
《草堂诗余四集》作为“草堂”系列中的一种,不论从选词范围、审美取向还是批评观念来看,都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显示出独特的选评价值。
首先,从选词风格来看,它择取包容了多样的词作,呈现出丰富的艺术面貌。北宋以来,时人多尚委婉柔美之作,沈际飞虽在所选《草堂诗余四集》中收录婉约之词数目可观,但又并不拘于婉约一体,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趣味。如他在评辛弃疾《水龙吟》(夜来风雨匆匆)时云:“人指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不知曲者曲也,固当委曲为体,徒狙于风情婉要,则亦致厌。回视稼轩,岂不易目翻恨。”[1]可见,沈际飞对辛弃疾刚柔兼济的词作艺术表现的推赏。此外,他还称扬洪瑹之词“垒句滔滔然”。[1]称赞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云:“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1]可见,沈际飞并不限于关注婉约柔美之作,对于其他词作风格呈现亦多有推赏。《草堂诗余四集》这种兼容并包的选评态度,一定程度上对偏重婉约之词予以了破解,是显示出积极意义的。当然,从总体而言,沈际飞选评仍以婉约之作为主。其主张在对胡浩然《东风齐着力》(残腊收寒)的评点里便可见一斑。其云:“词贵香而弱,雄放者次之,况麤鄙如许乎!”[1]沈际飞直言绮丽柔媚之词最为本色可贵,雄放之作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可见他仍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的批评观念。
其次,《草堂诗余四集》广泛收录当代人佳作,这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在相当长时期,明代选家对本朝词作多有忽视,评价并不高。如,陈霆《渚山堂词话》云:“予尝妄谓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蕴藉,不多见也。”[2]378陈霆从情感内涵、音律表现、语言运用、风格呈现等方面,对明词予以了批评指责。这种现象直到钱允治选编《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才有所改善。沈际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选录当世佳作,删改增补,这对提高明词的社会地位、促进明词的传播有着不小的意义。就《草堂诗余新集》来看,其收录明代词人和词作数量都相当可观。它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的基础上增选词人47家,增补词作196首,明初至明末词人皆有入选,包括边贡、林鸿、刘基、高启、徐渭、陈继儒、杨慎、王微等人。在《草堂诗余四集》中,沈际飞对本朝词人也多有赞誉。如其评王世贞《怨王孙》(愁似中酒)云:“看当代词,伯温、纯叔辈圆厚朴老,元美、征仲辈法无不尽,情无不出,俨然初盛之分。秦公庸先生首肯曰:‘近日君子何以自处。”[1]评丘琼台《满庭芳》(岁岁年年)云:“自李易安‘寻寻觅觅’连下十四个叠字,创意出奇,琼台通篇叠字,无輧无辏,无接无续,奇之又奇。”[1]沈际飞从情感表现、字语运用、法则彰显、意旨生发等角度予以评说,足见其对明代优秀词人词作的充分肯定与推扬。
此外,沈际飞广选南宋人佳作,显著扩大了词源,突破了一些人评词多以唐五代北宋为尊尚的局限。在《草堂诗余别集》中,选录7首以上者有11人,其中,除苏轼(17首)、黄庭坚(7首)以外,其余诸如蒋捷(38首)、辛弃疾(20首)、刘克庄(13首)、陆游(11首)、黄升(10首)、刘过(10首)、史达祖(10首)、姜夔(7首)、严仁(7首),皆为南宋人,可见南宋词占了绝大多数。沈际飞在选词上大胆突破,体现出不为时趋所拘束的特点。同时,他在《草堂诗余四集》中对所选之作多有独特之论。如云:“人皆称柳、秦、张、周为词祖,而不推蒋竹山,何耶?”[1]对传统词坛定位之论予以反思。又如,评及刘过《小桃红》(晓入纱窗静)一词,沈际飞赞其“言趣至到,过绝于人”。[1]沈际飞大量选录南宋之词并予以称扬的做法,对扩大南宋词的历史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沈际飞在所选评《草堂诗余四集》中花费不少笔墨推尊词体,为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草堂诗余四集·发凡》中,他驳斥历代“词为诗余”、“词为乐府之变”的持论,指出词乃独立文体,并非诗的附庸或变体。他格外留意辨分词与其他文体之联系及别异。如云:“词中名多本乐府,然而去乐府远矣。”[1]在具体评价中,沈际飞推崇词体的观念多有体现。如其评苏轼《南乡子》(寒玉细凝肤)云:“是词非诗而实诗,尊诗贬词者合作何解?”[1]评王世贞《满江红》云:“石田端烈,衡山精细,凤洲谐刻,维持天地间君臣大义也,词于是续经史矣。”[1]他认为明代词人中的优秀之作同样可具有补于经史之功效,它们在对不同艺术个性的张扬中,小中寓大,其社会价值功能显著。彼时,时人仍多以词为“小道”、“卑体”。如,陈霆《渚山堂词话》云:“词曲于道末矣。纤言丽语,大雅是病。”[2]347俞彦《爱园词话》云:“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2]399在不少人仍轻抑词体的背景下,沈际飞努力推尊词体,为词的创作发展铺就道路,这也为清人词体之尊潮流的出现注入了丰富的养料,铺就了先在的根基。
总之,作为一位富于个性的词评家,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四集》中表现出多样的批评观念与审美原则。其主要包括:一是主张以情为本,以抒发情性作为评判词之高下的首要标准;二是强调词之雅性,以情感真挚与否作为区分词之雅俗的重要准则;三是重视自然,反对雕饰,讲究情感抒写、结构行文、语言运用都要天机自运;四是倡导翻新出奇,反对简单仿拟,提倡在衍化中创新;五是讲究字句章法,注重格调韵律,反对词韵与曲韵混用。沈际飞的这些批评观念,较为典型地反映出明人词学批评的关注焦点,很大程度上展示出明人关于词之创作与欣赏的多维度思考,为后世词集选评及词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