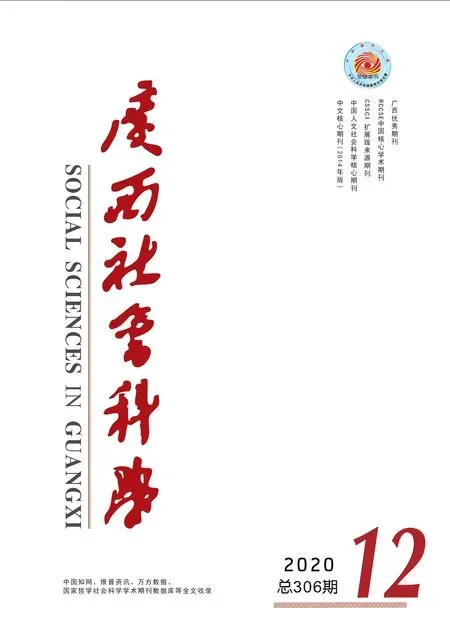“真理的发现”与现代国家想象
——论中国文学史编纂中的进化论思想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虽然进化论与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关系已得到较多关注,但已有研究仍有诸多不足,如忽略进化论在文学史著作中所发挥的“真理的发现”与现代国家想象,尤其忽略了进化论在古代文学史著作中发挥的作用。进化论认为宇宙和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这种以宇宙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进化论思想是进化文学史观念形成的基础。进化论对晚清以后的中国启蒙运动甚至革命运动,对文学史理论建构与文学史书写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话语类型。最早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和黄人《中国文学史》等内含进化论的痕迹,尤其是胡适于1922年3月为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被学者认为“二三十年代写作的诸多文学史,都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胡适这篇文章所描绘的新旧文学转型的图景”[1]。在本文看来,“任何历史书写者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2],文学史书写也不例外,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进程中,进化论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音、人的精神和革命等“真理的发现”,即语言进化论促进声音的发现、历史进化论促进人的精神的发现、社会进化论促进革命的发现。实际上,“真理的发现”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真理的发现”与现代国家想象是相互统一的。
一、语言进化论与声音的发现
在20世纪以前,中国文字与声音一直处于分离状态,胡适甚至认为言语与文字的分离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因此,言文分离成为晚清改良主义和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对象,也成为文学史著作的批判对象。1897年,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指出:“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3]裘廷梁认为声音是语言文字的根源,由声音而生成语言,由语言再生成文字。他从维新变法的实用主义角度突出文言中心主义的害处,激烈批判言文不一的弊端,同时揭示白话的长处,反对模仿古人言语。王照也发现了声音在语言文字变革中的作用,他主张实行拼音文字改革、文学应该随语言变迁,在《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中揭示语言和文学的变迁规律,批判语言与文字不通的弊端。在黄遵宪、裘廷梁和王照等人的基础上,梁启超把进化论与言文一致运动相结合,推演出语言进化观,并提出“俗语之文学”的观点。在梁启超看来,古语文学向俗语文学的进化是文学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语言进化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俗语文学是先秦文学和宋朝以后文学发达的根本原因。刘师培也从进化论角度阐释了“俗语之文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907年,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描述古文衰亡的趋势,揭示日本文体的输入促使中国文学发生变革。1917年,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讲义》描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该著作是刘师培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实践。刘师培坚持以阮元“《文选》为代表的美文传统”[4],褒扬六朝文学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史地位,虽然他没有把俗语文学纳入文学史,但是其以六朝古文反抗桐城派的文学观念,尤其是他对六朝文学“声律”的重视,对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影响。1915年,曾毅在《中国文学史》中专门分析中国文字与文学的关系,认为只有实现文字与言语、思想的统一,才能做到道贯古今、治被中外。1920年,朱希祖为北京大学文科一年级撰写的参考书《中国文学史要略》铅印出版,他大力倡导白话文,并为教育部起草国语注音字母方案。朱希祖的文学史著作虽然简略,但却明确表达了他要求语言与文字统一的主张。热尔内在《中国,文字的心理方面与心理功能》中指出,虽然中国文字从未对语言进行语音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口语在古代达不到与文字相同的效果,口语力量很可能是因为文字的出现而被压抑了。柄谷行人在《民族与美学》中从语言和美学角度考察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他认为“世界语言”是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拉丁语、汉字、阿拉伯文字、斯拉夫文字等文字语言都是“世界语言”,同时“声音语言作为俗语则遭到轻视”[5]。在柄谷行人看来,现代社会对感性和感情的重视与对作为声音语言的俗语遥相呼应,如果把声音语言摆在优先位置,世界帝国的文字语言就相应降低了位置,而俗语就会被当作民族语言而使地位得到提升。或许刘师培和曾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现了俗语在声音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以声音对抗文字中心主义是文学史著述的重要传统,中国文学史著述首先也是在“声音的发现”中而发展起来。
“五四”时期,虽然“俗语之文学”被“白话文学”取代,但是梁启超和刘师培等人倡导的“俗字俗语”仍然被这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继承,“俗语文学”和“白话文学”实质上都是强调文学创作的语言变革,都是要求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统一。然而与晚清时期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从进化论出发,把“白话文学”树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大大提高了白话的价值与地位。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描述了从1872年至1922年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他利用白话文学史观抨击古文,揭示曾国藩以后古文的衰亡趋势。胡适洞察了中国文字的历史和缺陷,他强调古文的共同缺点是不能与人生交涉,他宣告古文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死文字,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一千年来白话文学始终没有断绝,将来的文学非白话不可。1921年,胡适为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写《国语文学史》讲义,后由黎锦熙交给文化学社印行。黎锦熙认为《国语文学史》的编写在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文学史无“语”的历史。黎锦煕指出“所谓中国文学史,只让‘文’的一方面独占了二千多年,‘语’的一方面的文学,简直无人齿及,所以有特编《国‘语’文学史》之必要”[6]。后来,胡适把《国语文学史》讲义进行修订,以《白话文学史》为书名重新出版。在胡适看来,中国文体与语体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不一致,由于中国的统一帝国和科举制度的维持,古文又延续了二千年,中国古文可谓是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教育子孙的工具。然而,国语文学仍然突破了政府的权力、科第的诱惑和文人的毁誉,实现了国语文学的自由进化,国语文学的进化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进化。国语文学是一千多年历史进化的产儿,若没有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进化,就没有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胡适认为,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与国语文学相对的就是贵族文学,而贵族文学是死的文学,没有价值的文学;国语文学史是创造的文学史,也是活文学的历史,国语文学种下了中国文学革命的种子。1923年,凌独见出版了《新著国语文学史》。凌独见曾是国语讲习所的学员,他的著作深受胡适的影响;凌独见强调研究国语文学史的目的是建设新文学,他认为专制政体是国语文学的“死对头”,科举制度则是国语文学的“死冤家”。在胡适和凌独见等人看来,国语的进化具有突破帝国权力和科举制度控制的意识形态内涵,也具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诉求,国语文学史的撰写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以来的言文一致运动受到了日本明治时期言文一致运动和欧洲国家的文学革命的影响。黄遵宪倡导言文一致运动与他在日本期间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日本发现了作为声音语言的俗语的解放力量,也希望中国实现文字语言与声音语言的统一。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考察了日本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运动,他把这一时期的“戏剧改良”“诗歌改良”和“小说改良”都包含进言文一致运动之中。虽然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时间上不一致,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宏大目标:“言文一致是为建立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事项”[7]。柄谷行人认为言文一致运动的根本在于“文字改革和对汉字的否定”,因为声音语言比文字语言具有无可比拟的“经济性、直接性和民主性”[8]。在汉字文化圈,作为文字语言的文言文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统治性甚至是压迫性,因此,作为声音语言(口头语言)的白话(俗语)只能被无限地贬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倡导文字改革,否定作为文字语言的汉字,努力实现日语的声音文字化,这也可以说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整体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来说,声音性文字是西欧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汉字的优越性地位在日本遭到了根本性颠覆。对黄遵宪、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也遇到了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相同的情况,试图颠覆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的优越性地位,便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借鉴“欧西文思”来改革中国的语言体系,试图实现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试图实现声音语言与文字语言的统一。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考察声音与文字的关系,提出要发出“现代的声音”的主张。在鲁迅看来,中国人虽然能够说话,结果也等于无声,中国虽然有文字,但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德里达意识到“发音的退化与政治堕落不可分割”,“文字反映了融为一体的民族分崩离析的过程并且是其奴役的开端”[9];鲁迅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意识到“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语言是民族的财富,也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语言的统一也是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因此,鲁迅号召青年“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他强调“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0]。依据德里达的观点来说,文字包含着多种形式的暴力,比如原始文字的暴力、差别的暴力、分类的暴力和名称系统的暴力,文字在本质上“是人对人的剥削”[11],文字最初是建立在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并且把这种剥削和压迫长期固定起来,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纯洁的没有压迫的文字。鲁迅深刻洞察了古文的暴力和剥削本质,他认识到古文是封建贵族阶层的暴力和压迫工具,因此在文章结尾明确指出只有推翻古文才能获得民族新生。对晚清以前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深受作为文字语言(书面语言)的文言文的熏陶或压抑,在西方声音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发现了作为声音语言(口头语言)的白话(俗语)的解放力量和颠覆作用,因此他们把声音语言建构为一种现代性意识形态,建构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国语文学史》、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等文学史著述通过对“声音语言”的发现,从而承载了相同的历史使命。
二、历史进化论与内面的发现
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历史进化论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指导思想,使“文学的进化”和“内面的发现”成为文学史著作的重要内涵。所谓“内面的发现”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真理的发现”[12]。自从严复引入进化论以后,进化论首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在最早出现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林传甲和黄人都把文学进化观念作为普遍规律来看待,比如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到文学进化观念的普遍规律性,认为文学进化即使是在退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发生,“凡此可见退化之国亦可进化也”[13];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文学进化是“螺旋形”扩大的过程[14],强调进化是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力,认为中国秦汉以后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文学的进化过程。进化论思想在林传甲和黄人的文学史书写中都有重要体现,相较林传甲只是提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黄人则更加明确运用进化论分析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为文学的历史进化论建构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林传甲和黄人只是运用进化论研究文学史的演变历史,那么胡适则明确提出文学史的历史进化观念。1919年,胡适把历史进化观念运用到诗歌史研究,他在《谈新诗》中指出,如果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歌的历史变迁,就可以看出自《三百篇》以来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15]。胡适描述了诗体解放的历程,强调四次诗体大解放都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进化趋势。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中都自觉运用了历史进化的理论与方法。陈国球指出,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描述的“平民的文学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继续发展”“民间的文学渐渐起来”“白话小说可进步了”等语句,“都是由‘进化论’的角度立说的”[16]。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揭示白话文学自然演进的趋势,即白话文学经历由汉朝的平民文学到现在的白话文学的进化过程。
在林传甲和黄人的文学史著述之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开创了中国戏曲史书写的先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开篇第一句话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7],他认为楚骚、汉赋、六代骈文、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没能继续这样的文学形式,同时强调戏曲代表了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元戏曲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戏剧进化史,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多次引用王国维对进化论的理解和运用。王国维是戏曲专史著述的开创者,而鲁迅是小说史著述的开创者。1923年,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讲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尤其提到进化规律在小说代际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8]。鲁迅详述小说在唐代的演变,揭示唐传奇兴起的原因,他把进化规律运用于从上古神话传说一直到清末谴责小说的演进过程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实质上是一部中国小说的进化史。1924年,鲁迅在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把小说历史与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相类比,认为人类历史的进化规律也适应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艺的历史变迁;他描述从神话到神仙传再到六朝志怪志人、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历史变迁,简述中国小说的进化历程。在鲁迅看来,中国历史的进化有其独特的规律,它可能反复,也可能羼杂,但是进化的趋势却不会改变,中国文艺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也遵循这种规律。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并且编写了讲义,前三篇名为“中国文学史略”,第四至第十篇名为“汉文学史纲要”,在这个讲义中,鲁迅提到伏羲神农氏“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19],他还简述由文字到文章的进化历程。郑宾于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中也借鉴进化论,认为“文学流变”指的是文学的源流派别的变迁和因革,强调文学的变迁和因革都是时代的创造。用郑宾于的话来说,文学的历史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创造,诗演变成赋,演变为律,再变为宋词、元曲,散文的各家各派的古文、杂文、小说的演变,都是文学的创造。郑宾于强调文学史应该描述文学在历史上的趋势和其现象变化之迹,描述各时代文学的兴替和沿革,要特别表彰各时代文学的创造。谭正璧著有《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进化史》和《中国小说发达史》等文学史著作。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谭正璧描述中国文学自太古到现代的变迁大势,依据进化论分析将来文学的发展趋势。他借鉴梁启超对“历史”概念的界定,认为“文学史”的定义是:“叙述文学进化的历程,和探索其沿革变迁的前因后果,使后来的文学家知道今后文学的趋势,以定建设的方针。”[20]谭正璧所理解的“文学进化的历程”指的是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文学随时代而变迁,因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描述中国文学的进化历程,比如诗三百进化为古诗,古诗进化为词令,词令进化为曲,曲进化为京戏。谭正璧还认为进化论可以作为判断“文学史”好坏的重要标准,符合进化规律的就是优秀的作品。不难发现,从黄人、林传甲到胡适、王国维、鲁迅再到郑宾于、谭正璧等学者的文学史著作中,进化论都发挥了难以替代的思想指导作用。
进化论内在包含对历史进步和文学进步的观念,这也成为文学史著作的重要内容。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人的文学》,他通过把“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进行对立,揭示“内面的发现”是新文学进步的根本特征。周作人认为欧洲在15世纪就已出现“‘人’的真理的发见”,他把“人的真理的发见”建立在进化论理论基础上,他强调“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阐释人的“内面生活”这个概念,指出人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21],也就是说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基础,但人的“内面生活”与动物相远,最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在周作人看来,人的“内面生活”也就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所谓“灵”指的是人的灵魂,也就是神性的发端,而人生的目的就在发展这种神性。胡适曾经认为“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是文学革命的两大成就,周作人把“文学革命”的核心观点建构在进化哲学基础上,集中体现了进化论对文学革命运动的重要影响。从进化论推导出“人的真理的发见”并不是周作人的发明,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人之历史》中由进化论演绎人类种族的发生发展,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又由进化论演绎出“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第一义也”[22]。后来,陈长衡由进化论演绎出人文之进化和人种之进化。1923年,东方杂志社编纂、陈长衡和成长合著的《进化论与善种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长衡在《进化之真象》中认为宇宙之进化可分为两种:“天演之进化(nature evolution)”和“人演之进化(human evolution or progress)”[23]。陈长衡批评当时国内流行的四种关于进化的观点,尤其批评章太炎关于善恶并进的观点,认为宇宙进化包括天演(自然)之进化和人演之进化,人演之进化又包括人文之进化和人种之进化。其进化观念综合了达尔文、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论以及马尔沙斯的人口原理和近代善种学观点,揭示了宇宙和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基本原理,以及人类精神与种族不断进化的道理。“五四”时期,由于胡适和周作人等启蒙思想家的宣传和介绍,“‘人’的真理的发见”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后来,周作人把这种观点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1932年,周作人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到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批评吴汝伦在序文中的保守看法,强调《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24],所谓“言志”也就是表现“‘人’的真理”。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能够看到“内面的发现”,尤其是王国维对浪漫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强调,以及鲁迅对反封建思想的重视。
三、社会进化论与革命的发现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宣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优胜劣汰说;1898年,严复解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从翻译到出版《天演论》,历时四年(即1895至1898年)。这几年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无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此时,严复综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赫胥黎的伦理进化论,并密切联系中国处于亡国灭种危机的实际情况,在《天演论》提出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口号:“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25]。该口号正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天演论》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在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化过程中,“进化”和“启蒙”两个词语甚至可以等而视之。西方传教士对进化论的宣传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启蒙效果,严复第一次在主观上把进化论当作“开启民智”提出来。严复在《原强》中介绍进化论思想,就明确提出要用进化论来“开启民智”的想法,“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要务”[26]。可以说,晚清以后的知识分子都把进化论作为启蒙工具来看待,《天演论》出版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热烈反响,以及在中国思想界产生的重大影响,都体现了进化论的启蒙效应。从严复编译《天演论》到《新青年》宣传介绍进化论,再到1927年《科学》杂志出版“进化论专号”,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进化论思潮,最终形成了进化世界观体系。以胡适的观点来说,中国在屡次战败之后,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进化公理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巨大刺激,他们把“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看作金科玉律,把进化论看作救国救民的真理。进化思想点燃了中国青年的心和血,促使他们走上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从晚清到“五四”时期,进化学说不仅成为研究语言和历史发展的方法论,也成为分析社会变革的方法论。1930年,陆一远编著的《社会进化史大纲》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作者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中国社会的进化过程,描述中国从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历程。社会进化论影响深远,在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著述中都有鲜明体现,社会进化论也就被看作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从社会进化论出发,陈独秀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并由此发现了改变中国的途径,提出了“革命”口号。陈独秀以革命的眼光观察分析文学史的变迁,1915年,他在《青年杂志》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勾画了欧洲文艺思想的历史变迁。在陈独秀看来,欧洲文学艺术的变迁顺应社会潮流,社会变化是文艺变迁的背景,文艺发展也影响政治社会之革新。
强调文学进化深受时代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影响,成为文学史编纂的重要模式。1915年,曾毅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曾毅在书中提到文学史变迁与时代精神和政治制度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学之变迁升降,当与其时代精神相表里。学术为文学之根祇,思想为文学之源泉,政治为文学之滋补品。”[27]在曾毅看来,文学随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而不断进化发展,文学发展代有特质、代有变迁,因此,他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与时代状况紧密结合,比如讲唐朝文学时,专门用两个章节描述唐朝的文化思潮;在讲宋朝文学时,又专门以两个章节分别讲述宋朝学术、政治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关于文学史上的时代区划,他认为文学史之时代观并不一定与学术界之时代观相一致。1915年,张之纯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出要使语言与文字相联系,以顺应国家的进化发展。中国语言的进化程度与希腊相伯仲,而文学的进化则秩序井然,为了开通民智,俗辞俗谚剧本山谣都可以入文学,才能适应社会的进化发展。张之纯把文学的进化与时代的进化紧密联系,在文学史著作中分析时代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比如在描述黄帝时代文学之进化时,他详细讲述黄帝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认为黄帝“立六相、设史官、制陈法、立占天官、作甲子、作蓋天、定算数、造律吕、作咸池之乐、典章制度炳蔚可观”[28],这些都为文学的进化创造了条件。
由进化而革命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主张,也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模式。在胡适看来,文学进化观念是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进化包括自然进化和人为促进两种形式,有意地鼓吹和人为促进的进化就是革命,革命潮流是天演进化的必然规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集中体现了这种由进化而革命的观念,并解释了进化与革命的关系。中国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种子,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长期历史进化的必然结果,因此白话文学代表了文学革命的成果。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的文学,也是最能代表时代的文学,白话文学史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学史。谭正璧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他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中把胡适《白话文学史》列为参考书,也对胡适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谭正璧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时代的痛苦不断地压迫中国人的心坎,丧权失地以及各种耻辱滔滔不绝而来,中华民族由不觉醒到开始寻求生路,“‘维新’,‘革命’,都是应了这种要求而产生的,果然曾一度维新过,又起了屡次的革命;在文学上,也曾经过一度‘维新’化的改良,而最后也走进了前趋不息的革命的领域,造成了文学史一个崭新的扩大的有新生命的伟大的时代”[29]。他强调新时代文学产生的经过情形与当时的政治变化如出一辙,无论何种革命运动,革命者都是满腔热血一往直前,但反对者绝不会坐看革命的成功,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
四、结语
进化论对19世纪的欧洲文学史理论与编纂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泰纳《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朗松《法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都是以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同时进化论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遭遇了反思和批判的声音。比如韦勒克认为“必须抛弃在文学的发展和从生到死的封闭进化过程之间作生物学的类比的观点”[30]。又如德国学者绍伊尔在《文学史写作问题》中反思进化论文学史观,认为进化论建立在一种因果性和必然性思维上,但历史发展在关键时刻完全是开放的,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历史便体现出连续性,又呈现出断裂”,他主张抛弃一元论、必然化的进化论,而应当用“必然与自由的二元论观点”来分析文学史的发展进程[31]。窦警凡在《历朝文学史》中也抨击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适应于异域文学但不一定适应于中国文学,中国学者在借鉴进化论时也可能操之过急或者失之过偏。1930年,鲁迅在《〈进化和退化〉小引》中提到进化学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终成为一个空泛的名词。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正面作用和积极意义,同时也有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32],因此,反思进化论在文学史编纂中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