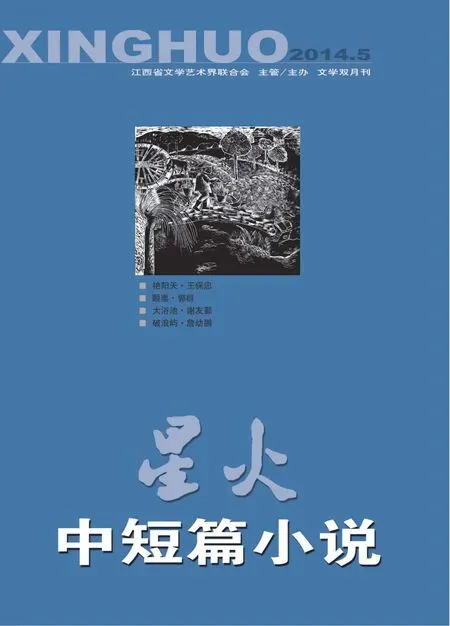鲁院同学曹多勇
○武歆
2004 年,在北京八里庄认识了来自安徽的小说家曹多勇。后来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52 名写作者,在写作道路上也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鲁三届”。正是因为这个共有的身份,让我们这些“鲁三”同学十多年来互相关注,只要见面必定兴高采烈,只要到了某个同学所在的城市,不管什么事情,一个电话打过去,肯定会受到同学的热情招待。
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新的客观洞察、新的生活方式无疑成为整合创造商业生态、全面重构商业关系,从而全新定义未来生活的场景源泉。
我一直喊他多勇。过去是,现在也是。
在我持久的印象中,多勇是不事张扬的实力派。几十年来,他始终专注地写作,很少顾及、经营写作以外的事情,坚定地用作品彰显自己的存在。他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诚实的人。我从心里喜欢诚实的人,与这样的人交往,心里特别踏实。
16 年前认识多勇的时候,他已经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还有书写淮南风情的长篇小说,在全国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重要文学刊物上的常客。我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但因为整个九十年代完全中断创作,2000 年才又开始重新写作小说,所以在心里非常羡慕多勇。那时候即使在“鲁院”学习期间,他也是埋头创作。那时候,我就特别佩服他旺盛的创作力。
记得前年我去合肥,因为报到那天中午我才从国外回来,回到家里简单收拾后,立刻乘坐傍晚时分“高铁”前往合肥,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参会人员,到宾馆时已经晚上十二点多了。可是作为东道主的多勇,还在大厅静静等候,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必须等我同学呀,多晚都要等”,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们俩当即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很多年之后的这次相见,感觉他除了依旧勤奋创作之外,还有着对历史的深层次思考。那一天,参观完一处历史遗迹,我们俩站在外面聊天,谈中国历史,后来不知道哪个话题,说到了楚国历史。多勇说他正在研究这段历史。他说了好多研究感受,其中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楚国后来衰败,整个国家的女人都生不出男孩子。他感慨道,当一个国家进入衰败期的时候,一切都走下坡路,甚至与生育相关联。
我们都属于性格内向的人,因为我还喝点酒,所以经常呈现性格外向的假象。不喝酒的多勇,偶尔举杯,也是点到而已,非常理智。因此我们在八里庄四个半月学习期间,一起“玩”的时间并不多。那时与我经常在一起“玩”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有些酒量的。记得那几个月里只要与他见面,无论楼道里还是院子里,他第一句话就是“昨晚你又喝酒了吧”,搞得我特别不好意思。
我们曾经在天津见过面,也在合肥见过面,还在外地文学活动中相遇。每次相遇都会热烈交谈,谈创作倒是不太多,谈的都是对生活的看法,也有对历史的认真分析。
如今仔细回味我和多勇离开“鲁院”后的诸多联系,每一次都是充满美好记忆的。
同样因为开启状态的麦克风,两人这段本不对外开放的双边会谈得以向媒体“直播”。当时,外界把奥巴马的话解读为,他不愿意和内塔尼亚胡打交道。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鲁院”学习期间我们来往不多,之后却是来往频繁,或电话,或相见,都很愉快。多勇的特点是开门见山,接听他的电话,基本上没有寒暄,上来说事,说完就放下电话,干脆利落。与这样性格的人打交道,非常轻松,没有任何压力。
在“鲁院”时与曹多勇交流不多,但却留下很好印象,刚才说过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但也有性格,有时也会对看不惯的社会现象说出自己的意见。
大约是2009 年,曹多勇接到湖南《文学界》杂志邀请,要做三个作家作品合辑,于是他邀请我,还有我们共同的“鲁三”同学胡学文,做了一期图文并茂的作品专辑。我和胡学文比较轻松,把作品、评论、印象记等一并交给曹多勇处理,之后什么都不管了,多勇则是任劳任怨地来回沟通,仔细核对,也不知道他电话打了多少遍。那期《文学界》杂志封面,我们三个“鲁院”同学的头像赫然并列,感觉特别好。
我和安徽作家朋友都很熟悉,说起来有意思,只要见面,立刻就能成为好朋友。譬如前作协主席、敦厚善良的老大哥季宇;现在的作协主席、曾经一起出访过的许春樵。还有做大生意、创作和酒量都不错的钱玉贵,再加上之前的“鲁三”同学潘小平、徐迅,以及当年《清明》编辑部的众多编辑……因为有那么多的朋友相识,所以从心里感觉对安徽有着特别的亲切感。
式中:为开口管桩在土塞不完全闭塞条件下的单桩承载力;为开口管桩在土塞完全闭塞条件下的单桩承载力;为桩外侧摩阻力;为桩内侧摩阻力;为桩环底端阻力;为桩土塞阻力;为土塞自重。
我记得,那时候经常与他在一起的有同样来自安徽的潘小平,还有身在北京同样也是安徽人的徐迅。由此我在内心推定,曹多勇喜欢与非常熟悉的人在一起,不轻易、不主动去结识新朋友。
传统文论关于“正读”已经积累了系统化的理论,然而随着文学及阐释的多元化倾向的日益明显,新出现的文学创作及批评现象中,误读取代正读成为阅读的代名词,传统追求确定意义的阅读观念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型的文学研究现象。文学的更新发展需要意义的不断增殖,也需要理论的“反躬自省”,误读理论这种批评方法需要有一个“元批评”(metacriticism)[20]的视角,也就是说对误读本身进行误读,对误读的原则方法进行批判辩论,这样才能永葆理论批判的生命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的角度对“误读理论”进行关照,目的是考察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出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之间应时刻保持适度的张力。
还有最主要一点,天津与安徽之间有历史渊源。这个话题说起来,那就太长了,在这里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历史,非常容易了解天津与安徽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些渊源,天津、安徽作家之间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至今“天津话”和“安徽话”之间还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一句话的尾音儿,有着极大的相似。2004 年是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之前的2003 年我们天津作家还曾经到安徽固镇去寻访,记得听一位八十多岁固镇老人说话,那就是纯正的“天津话”。
前年、去年,因为在合肥、太原召开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所以两次与多勇见面。一次多勇是东道主,一次是他跟许春樵共同赴会。
我不想谈他的创作,让评论家去谈吧,那是他们的责任。我只想说说十多年来与他交往的点滴往事。
研究者指出,有许多潜在变量能够预测工作场所侵犯行为,包括社会的、组织的、身体的、认知的、人格的、态度的等因素。Neuman、Baron等(1998)[9]研究提出了一个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模型,该模型后来被称为侵犯行为通用情感模型(The General Affective Aggression Model,GAAM),认为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主要预测变量来源于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两方面。个人因素方面,核心预测变量是人格特征(如A型人格)、情绪状态(如被激怒、受挫等)和侵犯经验(如敌意归因倾向)等。组织方面的核心变量是组织公平、组织气氛或文化等。
我始终认为,一个写作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开始停下来思考历史。这会通常意味着他的创作将会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我从心里欣赏这种“可怕”。
去年在太原又一次见面。那几天,我和多勇、许春樵,经常凑在一起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
假如说见面也有遗憾的话,那就是那年多勇、潘小平来天津,正好赶上我重感冒。本来我想带着他俩多走走、看看,但是吃过一顿饭后,实在支持不下去了,难受得起不来床,也就没有好好陪伴他们,至今还过意不去,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我记得给多勇、潘小平打电话,他们说还有见面的机会。
是的,有的是机会。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基本国策。40年来,我省积极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原料型向产品型转变,实现了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科学利用,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源支撑和保障。
毕竟我们拥有共同的身份证明——鲁三届。这个共同的身份,将会永远伴随我们成为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