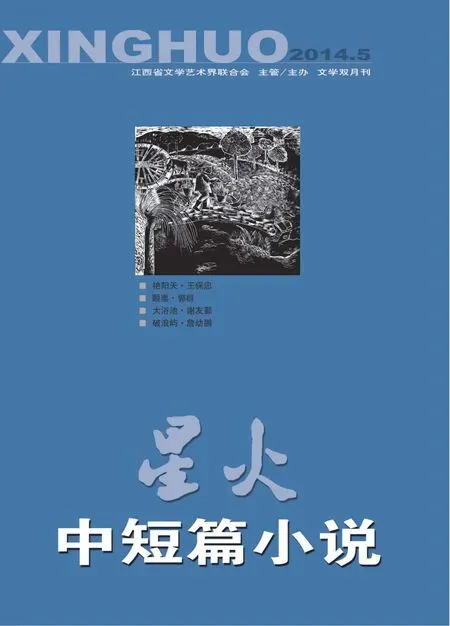五奶的城市生活
○陈天佑
五奶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说是心口子疼。五奶一哼唧,整个屋子都暗下来了,屋子里的桌子呀床呀什么的全都噤了声。五奶一哼唧,就要五爷给她揉揉。五奶年轻时就这样,一生气就犯病,心口那儿疼,就要五爷给她揉。其实五奶在很多事情上都爱折腾一下五爷,说不清是什么想法和动机,反正想一出是一出,而且,稍不如意,就不高兴,就给五爷甩脸子看,五爷早已习以为常。
五奶生气是吃晚饭的时候,儿媳妇先是嫌她没有把床单洗干净,接着又嫌她做的饭菜盐淡了,菜也炒得太软了。老两口牙齿都不怎么好,因而饭菜都要做得软活,老两口才能轻松咀嚼。但儿子儿媳妇不喜欢,儿子呢,不说,儿媳妇就不行,装不住,说了几次了。这一次,吃了一小口桌上的饭菜,皱了皱眉头,索性把碗一推,说是胃不舒服,不吃了,回去睡觉了,身后带着一股子罡风,呼呼呼地像扫把迎面朝五奶脸上扫过来。
五奶哪里受过这等气,刚开始的时候,还想摆一摆婆婆的威风,但几个回合下来,她就知道,她不是儿媳妇的对手,这个儿媳妇三两招,就把她拿住了。
儿媳妇的招确实很管用,她从不和五奶正面较量,只和她男人闹,直闹得男人灰头土脸,精神倦怠。五奶心疼儿子,只好忍个肚儿疼。
遇到对手了。也许是自己种下的因,才会有今天的果。自己刚进家门时,不也是和婆婆事事明争暗斗么。五奶常常暗自思忖。
五奶的儿媳妇叫王冬梅,是县医院的牙科大夫,最擅长的就是拔牙。当初,王冬梅与儿子润生恋爱的时候,润生刚从乡里考到了县文化局,对冬梅,五奶是满心欢喜的,冬梅长冬梅短的。五奶对旁人讲,她可是把冬梅当自己的姑娘看待的。冬梅心里也暖得仿佛怀里一直揣着个热水袋,上街的时候,总是挽着五奶的膀子,不知道的人看了,还真以为是母女俩呢。现在,当初的融洽就如春天溪边的薄冰融化在了草丛中,藏进了各自层层叠叠的皱纹里。
对于王冬梅来说,现在,婆婆柔软的胳膊变成了一条蟒蛇,再也无法想象相挽的样子。婆婆在她眼里,成了一个爱唠叨,只顾自己感受的自私的人。最让她可笑又可恨的是,婆婆居然自不量力地一心想按照对待公公的办法改造她,简直可笑透顶!她们融洽关系的打破,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与此同时,王冬梅听到了关于婆婆在当地的一些事,这加剧了她对婆婆的本能对抗。天下的婆媳关系,可能都有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五奶年轻时,可是远近闻名的厉害主。公公性子软,家里的事,自然都是五奶作主,公公只是点个头表示赞同而已。在外面,五奶依然表现强势,像头随时准备向侵犯者发起攻击的狮子。那时候,为了给家里分上好地,为了给窝囊的五爷出气,为了争这争那,五奶随时都可以豁出去,简直就是一颗装在炮膛里随时准备射出去的炮弹。多年后,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还常常提及五奶当年为了争一口气,喝了农药,拉到医院洗胃的惊心动魄的事。
这样反复斗争的结果,就是五奶赢得了没有人敢随便惹的名声。
五奶躺在那儿,那只猫温顺地卧在她的臂弯。五爷揉了一阵,五奶说好些了,不揉了,让五爷给她买瓶酸奶去,她想喝。五奶仍然躺在床上,她穿着一件紫红的罩衣,深蓝裤子,灯光下,紫色肆无忌惮地流淌下来,和蓝色混在了一起,映着一种混沌的色调。五奶打年轻时,穿衣就穿那种深色的,很少见她穿过浅色的衣服,里面贴身穿的,也是非红即紫,周身时时铺张着一种喧闹的充满争斗的气息。五爷起身到楼下小卖部,买了酸奶,五奶爱喝的那种,酸得倒牙,但五奶爱喝,觉得只有这种才过瘾。五奶是个追求过瘾的人。楼下的小亭子里,几个老汉老婆子坐那儿纳凉,像泥塑的佛一样,各自枯坐着。旁边一伙人围在那儿下象棋,几个人坐着,更多的撅着沟子看。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吵起来了,有人掀翻了棋盘,棋子儿像打碎的干粮散了一地,结果不欢而散。
这个小区是县城最大的一个小区,住户大部分是近年搬下来的乡下人。这两年时兴进城,离城远的乡里人都在城里买了楼房。五奶也是去年才进城的,村子里八成的人都进了城,不进不行了。乡里没几个人了,小卖部也没了,住乡里,不方便不说,最主要的是会让人看不起。五奶又是好强的人,岂有落后于人的道理,于是就下来了。五奶下来,比别的人更有道理,儿子在城里工作,不下来反而让人说三道四,有些人还不知道怎么猜测呢。
别人还在城里没地落脚的时候,五奶因为儿子的关系,往城里跑就是小趟儿,来了一住就是好几天。五奶觉得,要说生活的方便,还是城里好,再说,城里也热闹。五奶喜欢热闹。
说起热闹,五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乡里安静,听见的,无非是鸡鸣狗吠,鸟雀的叫声,牛羊的叫声;到了城里,车的声音,喇叭的声音,人的声音,到处都是声音的海洋。别的人说起城里的热闹来,仿佛都受不了,简直就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而五奶呢,表面是抗拒的,内心却又是欢喜的。抗拒是意识里的随大流,喜欢却是潜意识的真实感受。热闹有什么不好呢?刚下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一下子还不大适应城里的生活,到了傍晚,还喜欢东家串西家走,又都装修了房子,新置办了家具,互相看的愿望都很强烈,少不了相互比一比。这个时候,大家喜欢谈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到底乡里好还是城里好。讨论基本分成了两派,这当中,城里有人工作的,都说还是城里好,城里没人的,都说还是乡下好。两派都能说出些各自的好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五奶打心眼里觉得城里好,旁人再和她说起受不了城里闹哄哄的时候,她就说,你是城里来得少,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在乡下人看来,城里的诸多不好中,最让人不堪的,就是没个人说话。在乡下,哪个村子里能没有白话台呢?哪个地方没有一两处墙皮被磨得光溜溜的南墙根?那里永远是传播新闻的地方,东家的猫儿西家的狗儿,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杨树下、井台边、屋檐下,抽烟的爷们、打毛衣的女人、打闹的孩子,哪里没有流淌的浓浓的乡音?在乡里,可以对牛说,对羊说,对鸡说,对着自家长长的墙说,在城里,你对着马路说对着空气说,马路空气又不是你的,不会理你的茬。
五奶因为厉害,和她交心交肺的人就少。村子里少得可怜,亲戚们当中,大多领教过她的厉害,也都断了和她的交往。时间越长,就越发生疏了。五爷又是个没嘴的葫芦,和五奶能说话的,实在没有几个。那个人,张皮匠,早已经走了。真正想起来,那个人也不是和她说话的人,不过是懂得她的心而已,不认为她多么厉害。五奶记得,那个人曾经给她说过,她其实是世上最孤单最软弱的人,你越是厉害,越说明你孤单软弱。五奶嘴上不承认,心里却暗暗惊奇这人眼光的毒。后来他们就偷上了,她给他讲她的内心,他听着,接她的话茬,给她讲外面的趣闻。过后,五奶又后悔给他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把自己暴露给了他。但下次完事儿的时候,她睡在他的胳弯里,却忍不住再一次地重复她的内心。
五奶再一次生气,是一月后的一个周日。这次,她生的是儿子的气。这一个月当中,润生一次都没有来看过他们老两口,只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问他们见他手机充电器没有,一次是问一个老亲的电话号码。问电话号码的时候,五奶忍不住问了句,你要他的号码有啥事吗?问完就后悔了,果然那边说,你问的干啥?五奶最喜欢听儿子说新闻了,可惜儿子只有和别人说的时候,才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好像天南海北,知道挺多。和他们老两口在一起的时候,连个响屁都不放。有时候他们绕上弯子问,润生总是淡淡一句,要么是不知道,要么一句,你们打听那些干什么。这么一来,老两口就不怎么主动向儿子打听那些社会新闻了。但儿子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却支着耳朵听,然后,再把儿子喧的喧给别人听,哪怕只是换取别人的感叹也好。
后来和五奶能说话的,村上就两个,一个是村南的强奶,一个是村北厉二家的。强奶是心脏病,今年春上走了;厉二家的领孙子,半年见不上一次面。
强奶和五奶能说话,是因为多年前五奶帮过强奶的腔。强家在村子里是独户,势单力薄,难免受到各种欺负。强奶年轻的时候偏又有几分姿色,队里的干部都找各种机会下手,强奶的男人因此不是被派去修水库,就是派去下煤窑。强奶先是不依,但队长有的是办法,给她派最重最脏的活,记的却是低工分,鸡蛋里头挑骨头,到处抠她的疤,软刀刀,细绳绳,强奶最终只能就范。后来,村上的保管也对强奶蠢蠢欲动,要用五张上好的羊羔皮子换一次,强奶将这事告诉了队长。不几日,保管就被队长借故换了。羊肉没有吃上,反倒惹了一身骚,保管就在她的男人跟前吹风。就在强奶的男人和强奶扭打在一起的时候,五奶帮强奶解了围。五奶喝住了她男人,拍着胸脯为强奶作保。五奶眼里揉不得沙子,她说话人信。五奶为强奶遮住了丑。
强奶挺感激五奶的,自此两人无话不谈。五奶锅上好,做饭蒸馍都是一把好手,油糕炸得尤其好,酥软适口。强奶把队长送她的清油送五奶,五奶炸了油糕和强奶一起吃,强奶偶尔也拿给队长吃。强奶知道了五奶和张皮匠的事,两人说到了一起。强奶说,也不是说喜欢不喜欢哪个,也不是喜欢钱财,男人都一样,裤子一提就认不得人了,但女人离了男人,还是受不了那个寂寞。你怪五爷是个没有嘴的葫芦,我们那个,也是个木头,又长期不在家,就是在家,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队长吧,挺会说话的,知道的也多。几天不听他说话,还怪寂寞的。两人有时聊起来,都把男人喧的谎喧给对方听。五奶呢,喧得多的都是哪个公公爬灰,与儿媳妇有一腿,谁的姑娘就出嫁呢,却怀上了野种;强奶喧的呢,多是今年队里准备买几头牛,过年的时候要分几斤肉,明天公社里有个啥领导要来,等等。但不论怎么喧,结束时的话题是一样的,总会喧到两个男人身上。有时,两人少不了相互揶揄一番,相互笑话对方,但内心是欢喜的。
晚饭的时候,润生两口子回来了,王冬梅一进门就打开窗户,说一股什么气味。润生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王冬梅坐沙发另一端,拿了手机看。五奶看一眼润生,问,今儿个啥风把你给刮来了?润生愣着头瞪大眼睛盯着母亲看,不明白母亲的意思。王冬梅抬起头来,道,你们也要管管你们儿子哩,这些天,天天往外跑,不是加班就是喝酒玩牌,家里倒像个旅馆了。王冬梅数落了一顿润生的不是,又对比别的男人的好,越说越来气,脸涨得通红,胸脯那儿一起一伏。这样的数落基本上过一段就有一回,次数一多,老两口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谁愿意别人这样说自己的儿子。两老口都没有说话,心里的气却像火上热锅里的汽一样升腾起来。过了一会,五爷叹口气,悄声说,我就不知道手机里面有个啥看头,一进门就拿个手机看,也不说搭个手做饭,哪里像个过日子的女人!
本来是生儿子的气,现在,五奶开始生儿媳妇的气了。
现在想起来,自从这个儿媳妇进了家门,五奶就没有舒心过几天。好多事情和她意见不合不说,更让五奶无法释怀的是,自从有了她,自己在儿子身上就使不上什么劲了;偏偏自己又处处看不上她对待儿子的一举一动,看哪儿都不妥帖。儿子似乎本能地离他们老两口远了,儿子天天和她睡一个被窝里,与他们那种亲密感自此就隔了一层。这种疏远呢,又说不清楚,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让人想起春天玉米种子上的包衣,让人想起月光照在树杈间的光带。五奶觉得,儿子不来看他们,主要是由于王冬梅,没有王冬梅,儿子天天都会和他们在一起。她对王冬梅的时时的那种恨,主要是因为这个—她从她身边沾走了儿子与她的那种天然亲近的气息。她甚至暗自捉摸,总是王冬梅说了什么话,使了什么招,儿子才这样的,这个货!
老两口开始做饭,五爷择菜、洗菜,剥葱、剥蒜,五奶开始炒菜,五爷知道,只要儿子来,五奶做饭,一切依儿子的喜好来,别的人是全然不考虑的。菜,一个是酸辣土豆丝,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是酸菜粉条肉,外加一个麻婆豆腐,饭是灰碱面。盐使得比平时大,菜也不能炒太软。
吃饭的时候,王冬梅说她最近给县上一个重要局的头儿看牙,拔了两颗牙了,听说那个局长挺厉害的,县上的领导都不敢轻易惹,但那个局长的牙却不行,大牙基本都不行了,得种牙。过了一会儿,又说,那个局长还委托她给他的儿子找个对象呢,说了几次了,他儿子在人社局工作,年龄快三十了。我打听了一下,条件相当好,有两套房子,最重要的是他家原是城里人,现在那块地方要拆迁,听说可以补好几个铺面呢。那地方的铺面一个就值几十万。王冬梅一脸的羡慕,恨不能自己立即嫁过去。她接着说,将来局长去世了,就都成了儿子的了,局长只有一个儿子。家底子不一样,日子差距大了,我们一个同事,公公婆婆去世得早,没有负担,现在人家在海南都买了房子了。
公公不说话,眨巴着眼睛望着五奶,五奶一筷头饭刚吃嘴里,差点儿吐出来。窗台上落的一只麻雀听不下去了,扑棱棱飞走了。润生呢,装作没听懂,边看手机边吃饭,一声不吭。这样的场景仿佛已经演绎过多次了,这不过是多次之后的又一次。五奶气得脸色发青,但她很快又平静了。她知道,这样的事,闹,怎么闹?哭,吃药,还是上吊?在别人那儿的好手段,一样都用不上。闹出去,一来丢人得很,二来也是和儿子过不去,让儿子难为,总不能让儿子和她离了吧。
一想到儿子,五奶立即英雄气短。想当年,自己也是说一不二的主,现在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是五奶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五爷有时笑着问五奶,你不是厉害吗?现在脾气跑哪儿了?我看啊,你也就是在我跟前使性子行。五奶长长叹一口气,那气都流到门外去了。五奶说,现在处处靠人家,总得看儿子的脸吧。许是自己年轻时太强势,老天爷要罚我哩吧,老古人说,廊檐水下来窝窝里掉,一点儿都不差啊。
五奶进卧室拿件衣服,见儿媳妇在床上,呵呵地睡着了,嘴巴洞开,像随时准备攻击的蛇,嘴角拉着一丝涎水。窗外的阳光从格子里射进来,映在王冬梅的身上,那些线条像潮水一样层层漫向五奶,一股悔意从五奶心里撞出来,心却像坠着个石头往下沉。她怎么也看不上这个儿媳妇。这种感觉,她其实早就有了,这一次,不过是又强化了她的看法,这个儿媳妇,确实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五奶想不起来,从啥时起,她们就基本不在一起上街了,偶尔有事一起出去,也是老两口走一起,小两口走一起。王冬梅再也没有了当初小心地收着臀,小步轻脚的样子。走在街上,总是大步流星,胯扭得很夸张。五奶看在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人一旦看不上一个人,就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一声叹息砸得肚子咚咚响。她觉得真的是上了当了,是她们老两口子这一辈子上的最大的一次当,仿佛花了大价钱,一不小心,买回了一件低劣的赝品。
这天晚上,五奶心口子疼的毛病又犯了,让五爷给揉了半晚上才睡。刚迷糊,五奶又说,刚才梦见厉二家的了,梦见厉二家的说自己先走了,活不下去了,自己在人世间孤零零没个人可怜,急得找自己的老汉去。五奶醒来后心口那儿跳得厉害,她叹道,听说厉二家的早和儿媳妇过不到一起去,那霉鬼总不会寻短见吧。厉二家的男人本来给一个搞建筑的远亲看料场,一个月给两千块钱,前年夏天出门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偏偏司机是个穷鬼,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亲戚呢,说他是自己出门撞死的,又没有死在自己料场,只给了几千块,就这,还是看在亲戚的份上。老汉就这样白白死了。大儿子在新疆打工,年前家也搬过去了,不打算回来了。她和二儿子生活在一起,二儿子在城里打工,生了二胎,她主要带孙子。儿媳妇也是个厉害的主儿,三天两头闹一次,把个厉二家的整得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厉二家的前段时间来,和五奶喧了半日,只说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五爷睡意正浓,没有心情听五奶的,又不敢直接拗五奶,只劝她,别胡思乱想了,好好睡吧。
第二日一大早,就传来了厉二家的死了的消息,说是吃了耗子药没救过来。五奶想起厉二家的曾经给自己说过,自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孙子呢,太小。别的人给孙子讲故事,她没有故事讲给孙子听,她只有一肚子的怨恨。她把怨恨讲给孙子听,孙子听不懂,她就开始咒骂他的娘。骂着骂着,孙子看着她怨恨的表情,哇哇地哭起来,孙子哭,她依然说,依然骂。骂过之后,心情就会好一些。
尽管厉二家的每次都会给孙子洗脸,但无论洗多么干净,儿媳妇每天回来,都会从儿子脸上发现他哭过的痕迹,她的眼睛像显微镜,能窥测到她孩子的每个毛孔。她就变本加厉对待婆婆,不给她吃饭,不准她睡觉。厉二家的又不敢给儿子说,只能自己默默忍受。五奶每次去,厉二家的都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舍不得让五奶走,给她没完没了地喧儿媳妇是如何变着法子虐待她的,让五奶想想办法。五奶有什么办法呢,老的办法,年轻的时候用过的,怕是早派不上用场了。五奶也早没那个心劲了,自然出不了什么主意。后来想起一个来,跑去找厉二家的,让她养只猫,和自己作个伴。厉二家的没那个心劲,说她连自己都养不活。有好几次,厉二家的对五奶说,只待孙子再大一点,能离开怀了,她就不活了,这日子,她过得够够的了。五奶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管不了厉二家的事。厉二家的感叹,五奶你是多么厉害的人,都没有办法,看来我只有死这一条路了。
五奶只当厉二家的说说,没承想那老霉鬼真寻了短见。本来,厉二家的是很迷信的一个人,相信寻了短见是要下地狱的。五奶赶紧去看厉二家的,人很多,因为是寻了短见,屋里就充满了一种灰蒙蒙的怪异的气氛。人的表情也各异,阳光射进屋子来,飘荡的尘土像群魔乱舞。有愤怒的,有悲伤的。厉二家的娘家没有什么人为她作主,几个兄弟都是软柿子,不敢说话。其他人呢,只能叹息。在乱哄哄的屋子里,五奶看见了蜷曲在炕上的猫,猫儿也许知道主人不在了,半眯着眼睛,很无助很害怕也很悲伤的样子。五奶突然说,猫怕是几天没吃东西了,给喂点吃的吧。很快有人拿来了吃的,但那猫只是嗅了嗅,伸出舌头洗洗脸,眯上眼睛打瞌睡。
五奶出来的时候,带走了那只猫,她答应过村子里另一个没地方说话的人,要给她找只猫作伴的。
五奶再一次生大气,是秋后。说好五爷回老家去一趟,最多三天就下来。五爷回去,一是今年秋雨多,回去看一下屋子漏雨了没有,二是园子里的苹果成熟了,摘些拿下来吃。五爷到了老家后,每天都会通过手机给五奶报告当日的见闻和情况,五奶最爱听那些了。五爷说,院子里草长满了,我花了半天时间才铲了。五奶笑笑说,有牲口的时候没处寻草去,害得你经常要到山上去割草。五爷说,西屋漏雨了。五奶忙问,哪儿漏了?五爷说,就贡桌上头那块,不厉害,贡桌上溅了点泥水,我已经收拾好了。五奶如释重负,说,那就好,你再检查一下灶房漏了没有。五爷说,好。五奶又问,还有啥没有?五爷说,老队长的孙子考上四川大学了。五奶“哦”一声,强奶的影子在眼前闪了一下。顿了顿,说,没想到他倒命好,孙子一个一个都出去了。五奶叹一口气,又道,四川的大学好是好,就是那地方听说热得了不得,还经常地动。
第四天,五爷一天都没打电话来,五奶打过去,也不接,五奶就生气了。五奶想肯定是谁喊上喝酒去了,老头子就喜欢那口。一会儿又想,肯定是到谁家喧谎去了,在城里没地方喧谎,憋得慌慌的了。一会儿又想,可能是和泥干活呢,老头子干活从来都不马虎。五奶爱这样捉摸,越捉摸越生气,再怎么也不能不打个电话回来啊。到了晚上打,还是没人接。五奶的心就揪到嗓子眼上了。她慌忙给儿子打电话,又打电话让村上的人去看。一会儿消息就来了,五爷躺在院子里,好像是从墙上掉下来的,人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们找车往县医院送,让他们赶紧找医生。
这边就忙起来了,打电话问情况的问情况,找人的找人,润生一边安顿一边准备往医院里赶。
五奶双眼通红,紧张得双手微微发抖,嘴唇也抖。她突然想起来了,本来先前是想让润生去的,正好王冬梅娘家有事,润生就没去成,才让老头子去的。
五奶就开始在心里恨王冬梅,就她娘家的屁事多,要是她娘家没事,润生就去了,润生去了,老头子就不去了,也就不会出事了。润生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眼睛上拴着个绳子,睫毛那儿抿在一起,眼睛就显得格外大。她跟在润生身后一次次抱怨王冬梅,抱怨她的娘家,反复那几句话。润生安慰母亲,这会儿抱怨有啥用,老子不会有事的,医院那边,王冬梅都已经说好了。五奶这才缓过神来,想起五爷要住院,赶忙准备衣服、床单、饭盒、毛巾、卫生纸等。
王冬梅也回来了,她担心公公这次凶多吉少,平日对他们老两口的不好,让她不安,心里自是过意不去,又迷信公公真要是去了,对自己不好。赶忙帮忙准备东西,左一声妈又一声妈,显得格外亲切。她看见五奶准备的饭盒盖儿破了,说,快扔了,妈。一面问润生,家里那个新饭盒在哪儿?我去取。五奶心里一热,泪水就下来了,王冬梅拿了餐巾纸,一边擦婆婆的泪水,一边劝,妈,你不要担心,公公那么好的人,一定会看好的,有我和润生呢,你别担心。我已给神经外科的主任打了电话,那儿还有我几个同学,都是骨干,我给他们都说了,没问题,你放心好了。五奶听了,感激地望着王冬梅,心想,咋说也是一家人。
一行人赶到医院,发现来早了,送人的车才到半路。王冬梅就让大家先到自己的办公室,给大家倒茶。楼道里到处是人,大多像无头的苍蝇乱撞,几拨人探进头来,要么找人要么问地方。冬梅索性关了门,再来人问,她就让问导诊台去。五奶看在眼里,热在心里,觉得家里有个医生真好,心里又生出一丝对冬梅的好感来。冬梅穿着白大褂,下面露出半截圆润的腿肚子,从前面可以看见她穿着一件湖蓝红花的连衣裙,五奶突然觉得,冬梅挺洋气的。五奶的心里突然生出一丝愧意,觉得自己平日对冬梅是不是苛了点。她站起来,让冬梅坐一坐,她说她坐久了,想站一站。
送五爷的车到了后,医院赶忙安排检查,王冬梅的几个同学都来了,一面帮忙作CT,做各种检查,一面安排办住院手续,一路顺利。冬梅跑上跑下,又要解决难题,又要照顾婆婆,妈长妈短的,当着外人的面,五奶心里真的热乎乎的,她的眼泪都下来了,觉得自己真的是对不起冬梅。别人以为她仅仅是因为担心,纷纷又劝她。
检查的结果是颅内出血,住院手续早已办好,很快就住进了病房,安排治疗。几个人认真地看了片子,看了各项检查,又和主治大夫商量治疗方案。五爷像睡着了一样,身体上一下子多了很多管子。五奶嘴凑在五爷耳边轻声喊了几声,大家都看见五爷没有任何动静,五奶却说,她分明看见五爷的眼睛动了一下,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一切安排妥当,大伙劝五奶回去,不要担心。王冬梅掏了毛巾,给五爷擦手臂和脸。润生和大家说着话,询问村里来人当时的情况,老子果然就是上房去看房顶时从院墙上掉下来的。五奶后悔让老头子回去,对冬梅和她娘家的恨意早消失了,只一迭声地说,不回去啥事都没有,又抱怨老头子一辈子啥都放不下,就那么个破毡袄都要放梁上,啥用都没有。别人劝道,别抱怨了,抱怨也没用,世上的事,哪能知道呢,要是事先知道,就不会出事了。冬梅过来挽住五奶的膀子,劝五奶回去。多年之后再次挽这个熟悉的膀子,仿佛触摸老屋贡台上的神柱。婆婆的胳膊感觉比以前更松弛了,两人都有点不自然,冬梅脸也红了。
五奶回到了家里,心神不定,本来是想倒杯水喝,却到了卧室,打开了柜子,找出了五爷的一件呢子大衣。这件呢子大衣是润生结婚时两口子特意给五爷买的,五爷一直舍不得穿。五奶展开来,抖了几下衣服,没想到从中掉下几片黄表纸。五奶拿起来一看,纸上画了很多古怪的图案,像道家先生画的那种鬼符。有片纸上,好像写的是字,但五奶一个也不认得。五奶站在那儿,半晌才回过神来,老头子这是在干啥,从来没有给自己说过。
刚回过神来,五奶觉得口干舌燥。要是老汉在,只一句话,给我倒杯水,老头子屁颠屁颠就倒了,要是烫,还要用碗来回倒几次。这会儿没人使唤了,只能自己倒。就在这当儿,电话响了,是一个亲戚知道了,打来问情况,事无巨细。五奶不知道怎么回答,应付了几句,挂了电话,自言自语,又帮不上什么忙,啰啰嗦嗦的。却又忘了喝水,拿起一块抹布擦起了桌子。擦了一会儿,又想起刚才没有拿老汉的掌中宝放音机,老汉没有别的爱好,就爱听秦腔,说是听,其实就是听那个调,至于唱的是啥,并不关心。平日里,无论多么疲乏,只要秦腔的声音一出来,老汉立马就有了精神。
那个掌中宝,五爷喜爱得很,看掌中宝的眼神就如看自己的小儿子。操作起来像女人绣花一样小心,别人动都不让动。老汉曾经对五奶说过,要是自己走在她的前面,掌中宝就是他的伴。那时五奶还为老汉这话不高兴呢,这会儿想起来,心生悲哀。人一老,更孤单,老汉的话,虽说是玩笑,可也是心里话。老汉一听秦腔,说不定就醒了,电视里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吗?五奶这样一想,越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一时时都不能耽误,她甚至有点兴奋,拿了掌中宝就往医院里赶。
到了医院,五奶说了自己的想法,医生笑了,说,病人需要安静,哪能吵呢,再说,他也听不见,你啊,是电视看多了。润生两口子也出来阻止,就是听,也得好了才能听。五奶有些失望,只好把掌中宝放进衣兜里。但五奶坚信自己的想法,万一呢?别人不在的时候,她还是把掌中宝悄悄放在了老汉的枕头下,她坚信老汉能够感觉得到掌中宝的存在,掌中宝早把它来了的信息传递给老汉了,他们的心相通哩。放上后,她再观察老汉的表情,竟然觉得老汉的表情舒展了些,仿佛正沉浸在秦腔高亢的唱腔中。
下午,五奶让其他人回去休息,她来照顾老头子。儿子儿媳妇已经累得够呛,就回去了。五奶捋了捋老头子的头发,坐床边,抓住五爷的手,想起那几张奇异的黄表纸来,突然觉得老头子可怜,自己也孤独,不觉悲从中来,眼泪索索地从脸上流下来。看着老头子苍老的脸,握着那粗糙的大手,她竟然发现她对老头子其实陌生得很。平日里老是责怪老头子不如她的意,总觉得他像木头一样,不会说话,没有别的男人花翻,也不会来事,干啥都按部就班,也不懂得机巧,甚至,连个玩笑也不会开,但这会儿,想起厉二家的来,想起那些一辈子活在男人生活里的人,她心生愧疚。她发现,和老头子生活了几十年,老头子的耳朵里面,竟然长着几根毛,下巴下面还长着一颗痣,自己都不知道。本来,五奶觉得,她对老头子太了解了,他哪儿有个啥,她闭上眼睛都知道,他心里想的啥,她一眼就能看穿,她比他肚子里的蛔虫都了解他。但实际上,她对他感到陌生。
五奶坐床边,给五爷搓手。也没啥能干的,只能搓搓手,让血液流畅,头上的淤血也许会流开,他的病就会好起来。五奶一有这个想法,便觉得理应这样,带着这样的希望,她搓得很卖劲。搓了一阵,她向外面望望,悄悄摸出掌中宝来,打开秦腔,声音放小,咚咚呛,再放枕头下,然后,又开始搓。她觉得,心诚则灵,这么做,五爷一定会睁开眼睛的。这么想着,她突然觉得,五爷的手指好像动了一下,这让五奶兴奋异常,甚至开始感动起来,老头子还是对自己有感应的。
整个一下午,五奶都没有挪窝,一直搓五爷的手,五爷的手让她搓得滚烫。儿子、儿媳妇换她回去吃饭,她执意不去,她怕她走了后,就没人给老头子好好搓手了,不搓血液就不流畅,老头子的病就不会好。但她不告诉儿子儿媳这些道理,她知道,他们不会相信她说的。
手术是第二天做的,医生们都说,做得很成功。但到了晚上,老头子的病情开始反复,先是血不凝结,后来多个器官有了问题,到了第六天,终究还是没有醒过来,永久地睡着了。只不过,他睡着的时候,五奶发现,他的头微微倾向放掌中宝的这一边,和他晚上放枕头边听的姿势一模一样,很享受的样子。
发送老头子的时候,他穿过的衣服照例是全部要烧掉的,但那件大衣,五奶没让烧,盖在了五爷的身上。拿大衣的时候,五奶流着泪悄悄地把那些黄表纸拿给润生看,问,你看你老子画的这是啥?润生看了,也不懂,那些字符,他一个也不认识,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来是哪儿见过。润生看的时候,也是一脸的惊诧,老子是个简单纯粹的人,从来没有过这些举动,怎么会突然间画了这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呢?五奶坐床上,抹一把泪,悠悠地说,说明你老子心里有事,没地儿说,才这么做的。
那些黄表纸,润生也拿去,同衣服一起悄悄地烧了。
但这件事,使润生心生不安,他的脑海里,时时飘荡着那一撂黄表纸,飘来飘去,就幻化成父亲去世前金黄的脸。那些字符,也像一个个长着尖爪的怪物,时时挠着他的心。平日里,只知道让他们吃好,喝好,觉得只要有吃有喝,穿暖没病,就好了,很少关注他们的想法。父亲去世后,润生想起来,自己自从工作以后,都没有和父亲酣畅淋漓地好好聊过一次天,他和别人动不动海阔天空,张家的猫儿李家的狗儿,张天子李霸王,喧头多得不得了,可到了父亲那儿,总是没有话说,总是吃完饭就走。父亲有时候带着一种巴巴的表情,希望他说些什么,父亲最爱听他说外面发生的事儿了,但他仿佛故意抵抗一样,偏不说,他的心底里生出一股拗劲来。小时候就是那样子,父亲让他干啥,他就偏偏不干,父亲让他这样做,他偏就那样做,这股拗劲,每每让他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来。他给自己的提示是,你一个农民,听那些干什么。这个提示,仿佛是合理的,因而,润生也不觉得有什么。这个家,仿佛就是他们歇脚的一个店,他们像候鸟,来去匆匆。父亲留给他的印象,越是自己小时候的,越深刻,越往后,越模糊。
事情过后不久,一切按事物的规律回归原位。
所不同的是,润生再回家看母亲的时候,发现,家里冷清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变得热闹起来。总有人,有时候是原来村子的熟人,有时候是某个亲戚,有时候,是邻村他并不熟悉的人,也有好久不怎么往来的老亲,不知怎么,都突然上他家的门来了。润生有些感动,到底是亲戚。润生想,也许是父亲不在了,亲戚邻里们来看母亲的。母亲喜欢热闹,家里一来人,母亲表现得很高兴,像小孩子一样欢天喜地,她拿出他们两口子给她买的衣服让他们看,拿出好吃的让他们吃。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对于家里的来人,不论是谁,五奶都顽固地不让走。只要人来了,她就会想方设法地留下来,让他们住在家里。那次润生的舅母来,润生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景,舅母执意要走,说是她不在,家就背走了,家里的猪啊狗啊的都没人喂。五奶立即说,她给舅母的邻居某某某打个电话,让她帮忙照看几天。舅母又说,还要给上中学的孙子带鞋子回去呢。五奶马上说,楼下就有卖鞋子的,她掏钱买上,带班车上。舅母见五奶这样,不好意思再拒绝,先是答应了,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要走,站起来拿了包就准备走。五奶见了,急了,死拉住包,把包抢过来,放里屋里,一迭声地说,你快快坐下,今儿个你不能走,说啥也不能走。我还要和你好好喧喧呢,下午我们包饺子吃,我这就称肉去,你不能走,不能走,你走了,我可要留心了。这边舅母宁要走,这边五奶像母鸡斗老鹰一样伸开膀子拦着不让走,你推我搡,来来回回,直到俩人都筋疲力尽。
五奶奇怪地生了一种走人恐惧症。家里只要来人,她就生怕那些人走。她赔着笑脸,不断地和他们说话,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他们,惟恐怠慢;她早早准备做饭,拉开不让走的架势,仿佛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有时候,人家宁要走,说出一个理由来,五奶立即就会反驳,说出几个解决的办法来,她的办法很多,甚至不惜把人家的事情揽在自己头上,她给润生打电话,让他想办法解决。
五奶的这种离奇表现在外面都有了名声,这种名声,当然先是在亲戚们间传播,很快就传了出去。王冬梅听到了,气乎乎地对润生说,你妈天天学雷锋做好事你知道吗?润生惊讶地问,做了什么好事?王冬梅告诉他,有人看见,五奶天天拿了油糕等在车站,看见认识的人,便给人家油糕吃,然后拉着说上半天话,再拉家里,管吃管住,家里都快成车马店了。王冬梅哼一声,又说,人家都说,婆婆家就是你们村的办事处。这下好了,你妈有了好名声!
润生这才想起,母亲家的油这段时间用得非常费,他都买了好几次了,他还纳闷呢,多几个人,也不至于这么费油。自己当时也没多想,这会儿一想,对呀,母亲家里,经常有股油炸的气味。
润生去了母亲那儿,她正在和几个村里下来的人聊天,拿了自己新买的衣服给他们看,桌子上堆满了果核、瓜子皮,中间放着一个碟子,却没有东西,碟底儿油汪汪的。桌子上面的餐巾纸,黄黄的,油浸开来,几朵黄花绽开一样。
润生一一问候过,坐下。母亲笑着说,还想给你打电话呢,你就来了,来了正好,你牛叔要给你牛婶看病,今儿下来查了一下,明天准备住院,本来他们要回去取些用的东西的,来去花钱不说,麻烦的,就不回去了,床单呀、饭盒呀,洗脸盆、卫生纸什么的,我这儿都有,你老子病了的时候备下的,他们拿去用就行了,你呢,让王冬梅给他们医院的领导说一下,找个好大夫给你婶看病。润生表面应着,脸却僵僵的、红红的。
润生回去后,母亲的电话紧沟子就跟来了,她问,冬梅给医院领导说了吗?大夫找了吗?润生生气,说,妈,你以为谁的事都可以麻烦人家吗?自己老子的事,那是没办法,别人的事麻烦人家,人家会说的。你不知道,那些医生天天不是这个找就是那个找,最烦熟人找了。母亲的呼吸急促起来,突然压低了声音说,那你想想办法啊?
润生挂了电话。
晚上,母亲的电话又打过来了,润生没好声气地喂了一声,那边却半天没有声音。好久传过来的是那个牛叔的声音,牛叔说,五奶病了,下午还好好的,不知怎么突然就不对了,浑身抽搐,眼仁往上翻,身上热一阵,冷一阵,好像是感冒了,你们过来看看。
润生赶忙赶过去,走路上,他想,要是父亲在,肯定会给母亲揉,母亲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父亲呢,很卖力地给她揉。
润生想着,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