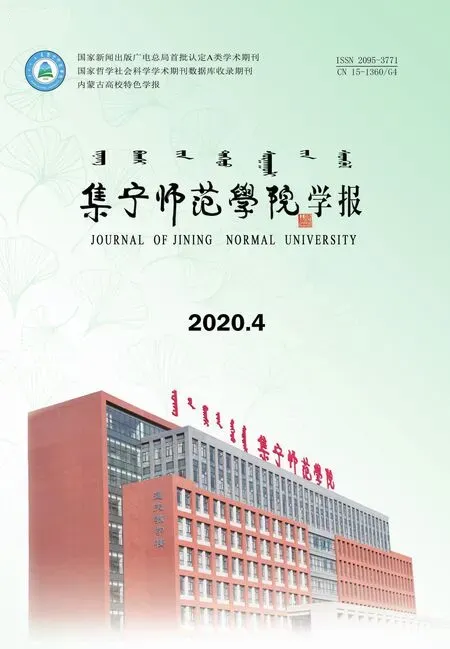先秦散文的语篇隐喻研究
高杨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教育部,河南 郑州 450064)
隐喻不仅是语言和思维的,也是交际的。隐喻在语篇话语的交际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先秦散文中,词汇、句式层面充满了隐喻意义和隐喻表达,对语篇理解和人物的思想交际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隐喻相关单词的识别、隐喻相关命题的识别、非隐喻相关单词唤起目标域概念、隐喻相关单词唤起源域概念和相关命题、蓄意隐喻的语篇效果等[1],而不同语境又对词汇、句式和话语层面的隐喻产生限制和指导作用。
一、词汇隐喻在先秦散文语篇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现代人阅读古文,会对词义理解产生歧义,歧义词汇产生隐喻。隐喻形成的一词多义是产生歧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词多义产生和发展于共时和历时中,受话者或读者必须了解词汇的历时演变意义,不同时代词汇意义在语篇中唤起共时性,达到关联合成,促进语篇理解。
(一)祭祀词汇的隐喻意义
祭祀代表着中国礼文化的发端,现代人根据隐喻词源学追溯隐喻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根据语篇背景理解古代意义和现代意义,或根据范畴解歧理解古代祭祀词汇。
例一: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左传·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解析:“币”原义:古代把捆扎的丝织物作为祭品或馈赠的礼物,后来把贡献的玉、马、皮、帛(丝织物)等物品,都叫做币,现代成为商品交易的媒介,如人民币、欧元、英镑等。现代人认为“币”原义是隐喻意义,理解“币”原义要追溯古代历史文化。中国崇尚礼仪文化,开始于先秦,为后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礼初始于祭祀文化,强调“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在于祭祀与武力。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敬神和祭拜先祖祈求获得丰收。所以祭祀的物品也被当作礼物珍惜。随着社会发展,物质丰富,玉、马、皮、帛(丝织物)等祭祀进贡的贵重物品,都叫做币。现代社会,币已经抽象为购买商品的“钱”。“币”从实体物质转移为抽象物质“钱”,从物质特点到作用的发展,词义有联系。理解古代“币”需要勾连起各个时期的意义,了解隐喻意义的形成原因,才能更加深刻理解当时古文的背景知识、历史文化发展及人们思维特征的变化。
例二:赐女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国语·鲁语上·展禽使乙喜以膏沫犒师》)
解析:“牺牲”原义是供奉祭祀、立誓或筵宴用的牲畜,作名词。现代指为了正义目标或事业舍弃生命,作动词。古代意义和现代意义有联系,牲畜作为祭品,庄严隆重,牺牲被杀死,隐喻延伸到为崇高信仰献出生命。
例三: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礼记·王制》)
解析:“太牢”和“少牢”隐喻义有等级性,彰显了古代礼仪严格性,等级不同祭祀用品不同。“牢”是圈养牲畜的栅栏,转喻为作为祭品的牛、羊或猪。“少牢”转喻祭祀用的猪和羊。
(二)词性转换产生的隐喻意义
古代汉语的许多动词随着历史发展,隐喻延伸为现代汉语的名词。
例一:范宣子为政,诸侯币之重。郑人病之。(《左传·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解析:“病”现代义指“疾病”,作名词,古义释为“忧虑”,作动词。“忧虑”成“疾”,隐喻延伸为“疾病”。
例二: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
解析:“丧人”的“丧”原义是“丢掉,失去”,作动词,隐喻延伸为“失位而逃亡他国的人”,作名词。
例三: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楚辞·九章·惜诵》)
解析:“贰”为动词,含义“一分为二”,延伸“叛变,背叛”。历史发展,词汇的词性变化,意义也随之改变,是隐喻作用的结果。
(三)听觉词汇的隐喻意义
声音和意义之间关系可以通过像似性(iconicity)连接,其在语篇中的互动可以通过听觉分析研究。象声词(onomatopoeia)多出现在特殊词汇中,声音象征(sound-symbolism)多出现在词汇和特殊声音中。声音象征特设声音的倾向,通常与包括声音的单词的意义相关,能够投射到文本中不同的空间[2]。
例一: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庄子·养生主》)
解析:“砉(huà)”,象声词。厨师了解牛的机体构造,厨刀所到关节之处,发出“砉砉”声响。“騞(huō)”,象声词,进刀解牛的声音,大于“砉”声音。象声词不仅表现了描述的声音,而且整个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象声词形象地展现了庖丁解牛的娴熟技能,一气呵成。隐喻经过不断实践操作,掌握事物规律性,做事运用自如,体现了艺术魅力和语篇的真实性。
例二: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解析:形式范畴(form category):“渊、泱泱、沨沨、熙熙”象征乐音的特征(sound shape)与源域 (sounds of different music)互相投射,源域(sounds of different music)同时与目标域(百姓忧伤不困顿、象征东海的大国之风、完美婉转而险要变化、委婉曲折而又正直)互相投射形成隐喻合成域(blending):(魏康叔和卫武公的教化、国运未可限量的太公的国家、贤德相辅佐的明君、周文王盛德)。
二、句式结构在先秦散文中产生的语篇隐喻效果
词汇的语义特征或音位特征具有隐喻意义,而句式结构也能够促进语篇隐喻效果。
(一)下位范畴的源域与上位范畴的目标域反向对比
例一: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 《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左传·周郑交质》)
解析:语篇中的隐喻更多融入在语篇目的转换中,而不是一对一的单个语篇和单个隐喻策略的对应。有时源域延展原型范畴,建立新的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category),上位范畴包括源域和目标域。这种对应策略适应概念划分的语篇目的,因为抽象和不熟悉的实体结构通过类比或关系焦点与具体的更熟悉的源域相连。自然界中属于下位范畴的具体种类的野菜、野草、积水、死水和生活中的简陋用器可以进献鬼神和王公,而上位范畴交换人质却无信用的观念事件。卑陋的物品与尊贵身份的人质形成反向对比,突出语篇主题,形成隐喻合成域(物不在于轻重,而在与双方心诚)。对话结构隐喻体现在先秦散文的语篇中。
(二)上位范畴喻体与具体事例补充融合
例一: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左传·臧僖伯谏观鱼》)
解析:从劝阻公观鱼,引出话题,上位范畴的喻体(器用条件、轨和物的抽象定义)抽象不易理解,举出具体事例:四季农闲时进行畋猎活动;讲习军事活动车马、服饰、旌旗的等级制;鸟兽肉不能放在祭祀器具里,皮革、牙齿、骨角和毛羽不能制作军事器物等,围绕“礼”展开劝谏,隐喻映射了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轨不物,就会“乱政”。
(三)定义连排句式对隐喻效果的烘托效应
定义连排句式虽没有明显隐喻词汇,但是隐喻表达的频率和密度高,为语篇提供了线索,提高了隐喻力量指数,强化隐喻效果,朗朗上口,提高了教化的趣味度和情感呼吁,使隐喻成为有效的劝说工具,
例一: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左传·石碏谏宠州吁》)
解析:六逆和六顺的定义排比烘托庄公宠爱公子州吁,离开顺理事去做逆理事会招致祸害的隐喻效果。
例二: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左传·臧哀伯谏纳郜鼎》)
解析:节俭、等级制度、礼数、文采、物各有其用、动辄有声、光明的定义连排句式批评了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烘托了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性,起到了隐喻效果。
例三: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左传·宫之奇谏假道》)
解析:鬼神依从有德行的人、上天保佑有德行的人、美的才芳香、有德行的人的祭品是真正祭品的连排句式突出了古人尚德的教化。
三、蓄意隐喻在语篇中的作用
先秦散文充满了对话语篇,话语主题有时不明显,源域的解释和变化或视角对源域的注意对话题意义和目的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说者和听者交流目的实现。蓄意隐喻在突出源域注意和话题意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蓄意隐喻(deliberate metaphor)与非蓄意隐喻(no-deliberate metaphor)的不同点是蓄意隐喻使受话者把源域作为独立的概念域而被注意,再引导考虑目标域。蓄意隐喻不仅是语言和思维事件,而且通过说话者唤起或指导受话者在语篇的心理表征中建立交际功能的跨域映射,达到事物参照实现。蓄意隐喻在不同语篇中有不同修辞和交际目的,文学和会话中的趣味性(divertive)、新闻和科学中的信息性(informative)和教育中的指导性(instructive)等。
例一: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共叔段做事僭越了臣子的本分,导致兄弟间争斗。庄公嫌怨母亲,将其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死就不再见面!”过些时候,庄公后悔。颍考叔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解析:通过范畴化和解歧,颍考叔使得“君之羹遗之母”(源域1)映射“孝顺母亲”(目标域1),属于常规隐喻和间接隐喻,含有蓄意义。隐喻意义在语境中近一步发展,生成了“君之羹遗之母”的“孝顺母亲”的话语事件(源域2),引起受话者注意,改变受话者看待话语主题的视角,与庄公幽禁母亲的不孝行为和后悔心情(目标域2)框架存在可观察的差别,源域2和目标域2被分别唤起且隐喻性和本体域相异的直接对应表达,属于蓄意的直接隐喻(直接隐喻体现在隐喻比较中的源域的直接表达,使受话者没有选择的对源域清晰的注意,蓄意唤起相异的概念域,相异概念域为隐喻比较提供了基础,如,Juliet as the sun),源域和目标域分属不同语域,但在同一话语中,起到了交际目的,最终教化了庄公而恢复母子关系。颍考叔不直接通过语言教化,而是通过转换设计(turning device)帮助说话者唤起在线对话的隐喻解释,从常规隐喻原始支配维度转变到蓄意新隐喻的新维度,从间接隐喻过渡到直接隐喻,直接隐喻越延伸,标记越突出,目标域也越突出,施加在意识隐喻思维中的机会越大,更加促进唤醒意识思维,激起受话者共鸣,具有话语策略,教育和劝说意义深刻[4]。
常规隐喻也有蓄意性,如体现在报纸标题的双关语(punning)和幽默(humor)等引起注意,起到了独特的修辞效果。《郑伯克段于鄢》的标题解析为:共叔段不义,不称为弟弟,庄公为“郑伯”(意为大哥),但失教于弟弟,是讥讽他驱赶共叔段的本意,不写共叔段主动出逃,而用“克”字,体现了史官对庄公的讥讽责难的蓄意含义。
例二: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毋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礼记·杜蒉扬觯》)
解析:知悼子死,还没有下葬。平公作乐饮酒,师旷和李调侍奉左右。杜蒉纳谏,如果直面平公不是,平公未必承认过失。于是在师旷、李调和自己吃了三杯罚酒后,快步离席,引起平公困惑而追问,杜蒉才讲出原因,平公也就爽然接受过错。杜蒉的怪异行动具有蓄意隐喻导向作用,蓄意隐喻产生陌生突兀感,使接受者印象更加深刻,可以创建新的意义,不是简单的运输意义,而是潜在的改变思想。
蓄意隐喻关注目的性的交互主观的信息传输。非蓄意隐喻没有特殊交际目的改变语篇事件当前局部主题中受话者/接收者的视角。蓄意隐喻不是隐喻的修辞功能复兴,并没有否定或放弃概念隐喻理论,而是对概念隐喻理论忽视的意识的重新认识,是概念隐喻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蓄意隐喻是说话者/发出者蓄意唤起受话者/接收者转移视角,离开语篇的目标域转向相异的源域[5]。蓄意隐喻与常规隐喻不矛盾,相当部分常规隐喻也有蓄意性。蓄意隐喻是实现教育或特殊目的,常规隐喻则是日常话语范围。蓄意隐喻对听者而言新颖和陌生,对其原有思维方式产生碰撞而转化观念。蓄意规约隐喻加强和拓展原有概念。语言创造性是从最常规和可预测到最新颖陌生和不可预测的阶段层次的语言现象,常规隐喻拓展和延伸是蓄意隐喻[6]。蓄意隐喻的作用是使受话者意识到它的意图交际作用,就是改变视角,指导受话者不断地选择其他参照框架和观点,再考虑局部主题。蓄意隐喻的主要预测是注意:当隐喻的结构表示接受者必须从话语或短语的目标域到与隐喻相关表达的源域注意力转移,是关于源域的注意力高度具体化:集中在作为话语处理情景模式的源域的指令表征。在语用术语中,隐喻的源域概念需要设置话语表征中的源域指称时,被认为是蓄意使用的。当隐喻展示特殊的语言、概念或交际特征,如延伸或新奇时,源域的指称在情景模式中将会被设置[7]。
四、语境对隐喻效果的指导和限制作用
例一: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礼记·曾子易箦》)
解析:曾子病危卧床。曾子的弟子子春坐于床边,曾元和曾申坐于床脚旁,童仆手执蜡烛坐在角落。童仆说:“美丽和干净,是大夫级别使用的竹席啊!”子春说:“住嘴!”曾子听见这话,惊惧地说:“啊!”童仆又说:“美丽和干净,是大夫级别使用的竹席啊!”侍疾的人物所处不同场景位置隐喻表达了礼的等级分明,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隐喻表达要遵守礼制,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病重之际坚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直至在竹席更换中死去,表现了曾子坚守礼法的执拗信念,体现了儒家崇尚礼法的思想,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语篇主题不是暴露“礼”的崩坏,而是以具体事例隐喻讲解礼法高于生命,曾参是以身护礼的榜样。对于当代人或许认为曾子思想囿于迂腐而不开化,但抛开曾参守“礼”,他的自律和知错必改的精神,是令人感动和值得学习的。
例二: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惠子相梁》)
解析:语篇场景内容设置为讲故事,起因是惠子为相,庄子看望,惠子受人挑拨,搜捕庄子。庄子从容往见。语篇情节出乎意料,祝贺朋友,不喜却疑,搜捕在即,不躲自迎。庄子泰然相答,委婉相叙,一针见血以奇鸟之喻,描摹生动传神,如见其形,如闻其声:鹓鶵比喻志向高尚纯洁的人,鸱比喻贪图功名富裕的人,腐鼠比喻功名利禄,梧桐等比喻高洁的志向,勾连讽刺惠子无情无义。庄子清高自守,机智幽默。语篇情景内容使人意料之外,富有趣味性,庄子没有直面斥责惠子,蓄意映射表明自己见解立场和志向,暗含讽刺惠子,使惠子惭愧,起到了既痛快斥责又回味不尽的隐喻效果。(注:文章例子出自《古文观止》[8])
五、结语
先秦散文处于中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散文充满了丰富多彩的隐喻。隐喻对散文的说理文结构、形象具体的说理方式和语言艺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散文思想体系有着深远影响。先秦散文的语篇隐喻研究从单词、短语、小句和段落层次分析语言事件和语境中的语言表达。语篇隐喻在人们互动交际、语篇安排和说话者如何构建协商新的理解的语篇空间中起了重要作用。分析先秦散文语篇隐喻对认识散文的主题和意义、古人的思维特征和现代文章如何给予人们直达心底,令人彻服的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