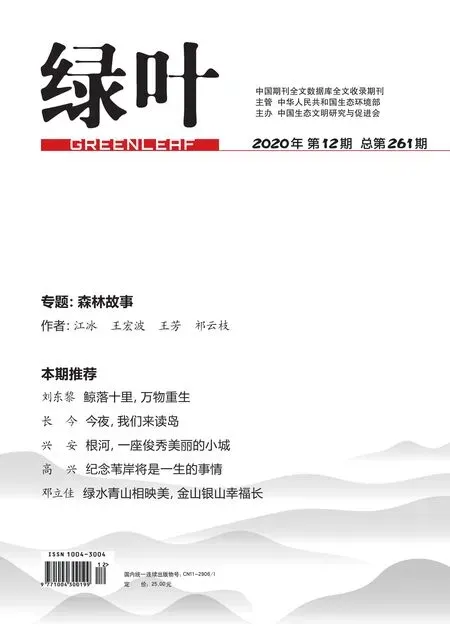以树的名义
◎王芳
飞旋在山西的天空,绿色盈盈。心,是愉悦的,右玉、芮城、沁源,分居晋之北之南之东南,以“久久为功”的气魄,为我们刻下生态的丰碑。山是眼波横,水是眉峰聚,我们本就该去往那眉眼盈盈处。当我们真正到达的时候,我没想到,我是以树的名义。化身为树,我愿永远地驰骋于这块土地。
站成右玉的一棵树
不入右玉,怎知春色如许?怎知绿色如许?从东西南北各处潜入右玉,人,瞬间消失的人的形体,而成为树的造型、树的倒影、树的绿意葱茏,倔傲地站立。
这是右玉后天修炼的功能,绝妙如磐且无可替代。
若在地图上寻找右玉,它很小,小到用铅笔标不出它的形状,画不出它的身形妖娆,但它却顽强地挺立。它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与时光博弈,与天地交换生存密码,以至于成为人们心口中的一粒朱砂痣。
这场生命的交换,是可歌可泣的,是感天动地的。
十九任县委书记以一把铁锹做链接,链成时间之矢,站在右玉的土地上。风吹来,沙袭来,寒冷、饥饿、困难、挫折等小兽排山倒海地奔涌过来,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的身后慢慢地滋生出人墙,人墙的脸上表情各异,惋惜、感叹、痛苦、欢乐、咒骂、倔强、盼望、梦想、遗憾次第交织,表情万千,但眼神是相同的,只有一种表达:坚定。是的,是坚定,在这里,生存与毁灭不是问题,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隆重而有硬度的抗争过后,天地对他们露出欣慰的笑靥,于是几十年来,那十九位县委书记,那扛着铁锹的人墙,都把自己种成了右玉的一棵树,一半儿埋在土里,一半儿向着阳光,长大长壮,握紧苍凉,背上安详。
多少年,江山如画,如同北宋王希孟一点点画出的《千里江山图》,青绿山水是渐变的,找不到时间界限,也逐渐衍变出树的特质。当我走近时,也发现自己已站成一棵树,一棵普通的小老杨,春天里伸出绿叶,与天地同呼吸;秋天里,骄傲地华丽转身成一片一片的金黄。
金黄,是金黄,金子一样的黄,高贵、浓艳、热烈,绝代风姿,虽是苍老而嶙峋的树干,却用尽全身力气,盛放。
这样的小老杨,曾经是右玉最早的救命树,就那么两三棵,就那么瘦瘦小小的、可怜巴巴的,长在泥土里,长在苍头河旁,把根深深地扎下去、扎下去,不喊苦,不说痛,把繁衍当成使命,竟然挣扎出更多的绿色和金黄。这金黄是绿色的升华和质地,以绝美的风姿呈现最后的飞翔,落下去,等待第二年的卷土重来。这样的生命轨迹也让右玉改变了模样,风,渐渐收敛羽翼;沙,渐渐臣服于氧气的浓度,一池春水托出绿色的右玉。
越来越多的树木、灌木、乔木在右玉安家,小老杨缩小自己的扩张,只因自己比其他树更需要水分,便选择了退避三舍,让给更多木质的生物生长。它在自己曾经的疆域内,安静地呼吸。
松树来了,浓荫蔽日,长成松涛园的样子。立在园内,松涛便与自然和鸣,那是世间最美的合唱,绿了心肺,涤了愁肠,大地之上有另一个世界,我们浸入其中,看不见彼此。
如果可以选择,我就是一棵小老杨,站在高高的牛心山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俯视大地。右玉就在脚下,与我相伴的,除了树木,还有太多叫不出名字的草木。我与草木在一枯一荣间成为知音,相同的频率呼吸着,劫后又重生,我们生生世世纠缠在一起。
也或者,我会长在苍头河旁,以小老杨的挺拔,等待着风毛菊、啤酒花、铁线莲柔软无骨地攀爬过来,我是它们的依靠,它们是我的精神伴侣,为它们的绽放和飞翔,我可以奉献出自己。雾柳、沙棘与我并肩,那都是我的异姓兄弟。苍头河是我们的江湖。河,流了亿万年,从南向北,树木伴随着河流历经了千万劫数;从小到大,倔强着。这都是右玉人的特质,也是右玉的特质。这样的特质,构筑出右玉的森林版图,这样的版图扩张到千山万壑,连一丝缝隙都不曾留下,绿,铺天盖地而来了。
我不是旁观者,我是见证者。
站成一棵树,历史却纷至沓来,多少年多少代,这里是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刀兵箭镞的塞北高寒之地。那些兵将戎装而来,建长城,修烽堠,与朔风一起征战,金戈铁马踏响时空,朝代更迭成为一幅模糊的背景。花草凋零了,兵将们化为尘土,长眠于这些沙土之下,为各自皇帝的宝座献祭。时光飞逝,右玉长出许多土质城堡。
曾经,生存成为挑战,人们越过杀虎口,背井离乡,唱出一曲《走西口》,去口外谋生也经商,这里驼铃繁忙,谋生的意义远大于自己的精神原乡。
等我赶来,站成右玉的一棵树时,却只能在书本上寻找这些历史,万千棵树木早已变成右玉的卫士,世世代代的右玉人种下一棵树,也是种下自己。他们手搭凉棚回望时,历史在退缩,缩入线装书里,化成铅字千行,铁马秋风或风沙满天,只是尘缘间的一线微笑。
微笑可以持续,站在右玉粮仓里,全国的画家背着画板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们坐在风里,吸着氧气,心翻绿浪,把右玉的树印在他们永恒的画作里。画布里的树,每一棵都是世上最美的风景,这些风景又拥拥挤挤地簇成一次次展览。从生到死,从动到静,右玉的树成为王者,扶大厦于将倾,而那个默默奉献的郭虎站在树的斑驳暗影里,傻傻地笑,心怀悲悯。他把自己燃烧了,正在化入右玉的万物里。总有一些人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倾尽所有就是他们干预世界的方式。
站在右玉的每个地方都是可以的啊,绿色如许,沉醉地呼吸,与天地同在,枕万物安眠,每个人都无可替代,不是吗?
绘事后素,我的黄河树
你是黄河!
你从巴颜喀拉山出生,一路行走,一路茁壮,在大地上、山涧中奔流的时候,有了脾气,有了性格。他们赞美你,他们征服你,他们自诩是你的儿女。可我知道,千万年来,你还是你自己,可以被暂时改造,却永不会被超越。
而我只想端详你的容颜。于是,我在有限的年华,踏足宁夏草滩,涉足阿拉善磴口古渡,在碛口古渡流连忘返……我见你总是在宽阔的河道上不停地奔流,仿佛一停下,就辜负了岁月。
这一回,我在芮城等你。
头枕着中条山,脚蹬着你的身躯,不知睡了多久,等许多作家赶来,把我唤醒。
于是记忆如纷飞的柳絮,飘扬在古魏大地上。
不知谁递来一支画笔,也好,绘事后素,此刻,山川做纸,天做书房,地做案,你是我的洗墨池。
我来画下你吧,毕竟已经注视良久。
你的沧桑,你的气势,我竟然画不出,于是我拢袍袖,抻皓腕,便俘虏了你,只稍稍这么一提,便把你拖入我的纸张。
你的波涛汹涌在纸上恍如树干,如此履痕斑驳,树干之下,根系竟然隐隐约约游龙惊鸿般回溯到青海去了,我窃喜。
我想画上一座城。
一座古魏城,松柏森然,立在如今的芮城城外,土质城墙隆起如山峦,在松柏的滋养中,丝丝缕缕地递送着幽古之情。我在幽静中,画出西周的青铜质地,画出周朝定鼎时分封诸侯的盛况,画出魏芮争战,画出城内人民的生死递嬗。城内,人人忙碌,种植,交易,他们自有光与火的追逐。可我也得画上城垣的建立和毁圮。城,残缺了,人们不知去向,我在唇齿间发出一声叹息,美的事物从来残缺不全。
我想画上一个渡口。
大禹曾在这里开始治水的步履,后人在塬上塑了大禹石像,可我不画大禹。我只画后人于1970年10月1日开工的水利灌溉工程,多少芮城人日夜穿梭在工地上,风餐露宿,冬寒夏暑,挖土排沙浇注,他们的人生只与动词有关,有人在沙土中死去,这一工程,竟然持续了几十年。一级站移动式泵车提水,沉沙地两厢交替运行,二级站一次扬高193.2米,三大技术创新,开辟了时代水利先河。我要画上芮城人的喜悦,画上那株千年神柏扑簌簌的喜悦。
看到活生生的生命埋藏在工地上,我想问问黄河,你能不能少点脾气,他们就能少点周折?黄河沉默。
我想画上一个人。
一个82岁的老人,他叫高文毓,我想画出他苍老的面容和倔强的身躯。虎神山上走过他少年的足迹,记下他退休后回归乡梓植树的心雄万夫,我要画下他以及他的家人,一锹一坑的辛劳,画下他风吹过的皱纹,画下他火烧树林后的伤痛,画下他家人遭遇不测后的老泪。树多了,绿来了,他老了,我笔下的黄河也有了泪。
我想画上一座湖。
碧水共长天一色,那便是圣天湖。层层折叠的土崖下,湖水湛蓝地横陈着,我的画笔就这么大肆涂抹,便是一座湖,我又轻轻地点染上丛丛蒹葭,水深处成湖,水浅处成湿地,水鸟低迴鸣唱,我的心也氤氲起来,我的天用湖蓝色,擎出几朵白云,蓝白映衬之下,湖水满载着美的吟唱。
黄河,你在这里,稍微一调皮,渗出一座湖,我不责备你了,你在这里温情脉脉,把曾经的宣叙变作咏叹,送我“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诗意,也送我“横素波,干青云”的豪情。
我想画上一首歌。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古魏人唱着歌儿在稼穑在渔猎,一声声的伐檀声都写成了诗,即使满眼愤怒,那也是正正经经的思无邪。这歌,唱出生活的破碎,化作匕首,刺向我们看不见的人群。我听着这歌,满腹悲悯,我画下伐檀的余韵,锵锵然千年不息。我想画上一把火。
这把大火在西侯度,举世瞩目的西侯度。火光中,裴文中、贾兰坡、王建、王益人等人在西侯度穿梭,文化层一点一点被剖开,石器、骨头一个一个被分离出来,他们殚精竭虑,他们小心翼翼为我展开一幅长卷。180万年前,西侯度还是一片草原,树林茂密,溪流潺湲,巨河鲤、羚羊、古中国野牛、山西披毛犀、中华长鼻三趾马、野猪、兔、鬣狗、剑齿象、三门马等动物在这里悠然来去。忽然,一丛火在雷声过后从天而降,地面骤燃,吓坏了西侯度人。他们在大惊失色之后,却发现了食物的香味,于是这把火成了他们的神祇。在这样的长卷中,西侯度人驾驭火之后,野兽远去,食性改变,加速了猿到人的进化,他们的笑容随着火光一起迷离在旧石器时代。那些草原和动物不再进入我的画笔,那些关于遗址的纷争也远去,我只画下这绝世的笑容。此刻,我不是向古代逃逸,而是对人类历史有更高的期许。
我想画上一幅图。
一幅空前绝后的华丽庄严的《朝元图》。其实哪能画呢?珠玉在前,我只能是临摹。站在永乐宫外,我获得内心的桃源。恍如隔世啊,即使人声鼎沸,我却获得无上的宁静。
元始天尊安坐,众神朝拜。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后,有民间的工匠画下这峨冠博带的神群。他们衣袂飘然,神色庄严,朝拜进中国和世界艺术史。
握着画笔,屏神静气地临摹,那高出尘世的神众,气象如此宏大。是谁在这里挥手风雷落笔华章呢?却原来,题壁赫然标注,这《朝元图》出自马君祥,还是有名有姓的,仿佛看见这位并不著名的洛阳画师注视着我,神情偏冷,气韵天成,而我手中的画笔也是他曾经所用。
一座城一个渡口一个人一座湖一首歌一把火一幅图,零落附就,成为我的树枝。
树干已成,树枝也好,仔细观看,还要画上树叶。芮城内所有乔木、灌木、骄杨柔柳、野草闲花都被一点点填入画布,于是,枝繁叶茂了。芮城原来如此地绿,山川河流都有碧翠的朦胧。我的大树已成,那些图歌湖渡城都是黄河上长出来的,不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没有黄河,便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了我的树。
这是我的黄河树,我心满意足,把画笔交还给马君祥。我把黄河掸掸,抖落颜料的尘灰,交还给河道。我与黄河作别,黄河头也不回,只顾东流去。目送黄河远行,我知道,这世间,人和事都是要还予天地间的。我该走了,如吴带当风一般长袖舒笼,卷起我的画图,我只留下一个羽檄交驰、悠远亦蹒跚的背影。
此一去,云山万里,冷月长风,万事如海一身藏,纵使尘满面鬓如霜,我也会记得芮城,记得芮城绿,记得绘事后素,我曾经画下一棵黄河树。也许得遍体鳞伤地笑傲万夫,我也不虚此生。
树·世界
穿花破碧,从并州动身,跃上葱茏四百旋,抵达灵空之巅。
如此,昊天广宇,便可以逡巡沁源,睥睨天下。
灵空山的风,在秋阳的照拂下并不激烈,温柔亦多情。轻风中,万树列阵,自成树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板中,我,渐渐消失肉身存在,而被同化为一棵树,可以选择任意的一棵树比邻而居,成为树世界的子民。
可以是一棵松,万古长青而常在,代表幽静和出世,与隐士的态度相仿,好似已经历过太多的人世沧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却从不说话。可以是一株柏,执松之手,与松偕老。可以是一株枫,万山红遍时,也不会缺失了自己的树影。可以是一棵柳,弱柳扶风,春天先来,秋天迟走,一个物事的柔弱却总是显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是一杆竹,从这稀疏的瘦美中体会到林下之风,还能体会到从清瘦美到气节美的哲学和情怀的转变。可以是一株槲,娑婆蓬然,终生向着阳光。可以是一株桃,人面桃花相映红,前度刘郎今又来。可以成为任意一棵树,脚踩着大地,背负着青天,除了生长,再不问世界,只要天不倾、地不震、火不烧、雷不劈,那么便云淡、风轻。
最想站在“九杆旗”身边吧。这株阔大的油松,吸日月之精华,天地有正气,灵秀复清明,即使分身为九,也要穿云向上,与天空对话,与飞鸟追逐,与白云嬉戏,与风雨相搏,如此,便可以庇佑着身下身边的众生,动如金猴,静如药草,大到人群,小到蚂蚁。自己把根扎向岩层,长成自己的王国,站在“九杆旗”身边,除了肃然起敬,再泛不出应有的思绪,被雄壮所染,我有了几分婀娜。
灵空之外,万树依然列阵,长在路旁,长在河边,长在饭桌外,长在人群中,任意排列生长,不需演练,不需布阵,随意而潇洒。三棵名为“福禄寿”的古槐,穿越过丛丛迷雾,与“九杆旗”对望着,传递出不一样的情思。雷霆雨露,俱是天恩,谁更久远这个命题已不再重要。古槐吸收世间风水,避过一场场风雨霜雪,千年生长,呈现龙腾虎跃的态势。既如此,便如此!它不会讲出“福禄寿”的寓意,因为那不是它的语言,但它已飞升成仙,满含慈悲,愿意送给人“福禄寿”的美好祈愿。
列阵的万树之下,有花草。
花,万紫千红,江山开遍,一花一世界,枯荣自有涯,开在每一个可以盛开的角落,追不上树的轮回,便做好自己吧。属于我的时节,我是花,不是我的光影,我是草。离离原上生,高山草甸上长,安定了尘土,也安慰了流离的灵魂。从不招摇过市,却又傲骨巍然,时不时地从花叶间穿过刀剑的铮铮之鸣。从不过问世间俗务,却从未忘了刺探自己的内心:万年与瞬间,在另一个维度上,它是一样的。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药草。
连翘芳香袭人,青绿的嫩黄的,人们二次采撷,它两次贡献自己的躯体,变成两种成药,在中医的铜秤间称斤论两。而它的叶竟然在茶的车间里,晾干过,烘焙过,成为茶杯里的叶子,一点点在开水的拥抱中,忍痛舒卷自己的身子,人们在舌尖上透出更多的芬芳来。世间事,哪一件事不经过轮回与阵痛呢?党参花如风铃状,喜凉又防风,补中益气,和胃生津。黄芪花成串,黄艳艳的,那样好看,性味甘,保肝降压治气虚。柴胡、芍药、车前草、防风、黑药、鱼腥草、枸杞、茯苓、地骨皮、管仲、半夏、益母草、黄连、甘草、天地星、山楂、藜芦、款冬花、百合、地椒、酸枣仁……那么多的药草,组成中药世界,那是万物的悲悯,相生相克,相依相傍,可医众生的根骨,在须臾的变幻中,人们已经再世为人。
列阵的万树下,流出一条河。
那是沁河之源,如龙盘伏山间,如龙腾伏百里过沁源。河里倒映着树的翩翩风度,掺杂着临水照花人。水波动时,树与花荡漾着破碎的笑声,河水接纳这一切,又努力让自己的身躯渗入万物。流水无声,只知道,成为树世界的滋润者时,那不是施恩,而是奉献,奉献了自己的躯体,成就了别物的繁荣和盛放。给予不是灭绝,河流自己,嘘气成云,飞沫为雨,自己给自己补给,亿万年的给予,便有了亿万年的“源”“源”不绝,而这也许是“生活在别处”的意义。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鸟。
千万年间,沧海桑田,造化高山大川,古地中海渐渐消失,青藏高原隆起,有了如今的山河版图,树生草长,有凤来仪。鸟便栖息了,喜鹊报喜,布谷报春,燕南飞,雁北归,各自有使命。而灵空内外有许多许多的鸟,飞来飞去。天鹅来了,苍鹭来了,黑鹳来了,褐马鸡成群了,鸟语啾啾,鸟鸣如弦歌,各自有雅意,它们在沁源的天地间,同呼吸共成长,繁衍生息。人们救下它们时,它们知道一步三回顾,记得自己的恩人。鸟的世界,干净亦温暖。褐马鸡活着时,便要被人取走尾翎,扎于戏曲盔头之上。翎羽旋转、抖动、挺立、摇摆,穿插着舞台人物的悲喜,台上的百无禁忌,台下的迷恋渴望,浑然一体,可人们却极少知道褐马鸡有一刻眨着迷茫亦疼痛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树外的世界。
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鸟的世界浩大空悬。如有唢呐,此刻适合奏一曲《百鸟朝凤》。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时尚。
沁源地形特殊,众山环绕,人居其中,在这环绕的大山万树中,人们却没有忘记追随时尚。一座古桥边,一处土台畔,有流水长亭,有圆荷风举,有古屋风雅,有诗画落户,可食可住可行可体验,人们创造着自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不是南山,是太岳山,是雄壮如树叶盘桓地图的太岳山,是生长原始森林的太岳山,是带着血与火洗礼过的太岳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还有太岳山。
列阵的万树之下,有煤。
那是另一个树的世界,万年前,树之身埋入地下,渐渐化成乌金,变了颜色,没有变了易燃的体质。一日日长埋在地下等待,等待人们把它挖出来,重见天日的时候,也是粉身碎骨的时候。它燃烧起来,驱散了万年前人类对兽群和未知世界的恐惧,也让千百年后的人们在冬天取一取暖。这个树的世界,炫目温暖却有尽头,当我们向千万年前的造化借款的时候,我们却支付不起庞大的利息,只有重建另一个树的世界,弃黑取绿,营救自己的蓝天。
列阵的万树之间,有乐。
那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呜呜咽咽的,诉说着沧桑变迁。那是夏代的石磬之音,清脆悦耳,诉说着田园牧歌。那更是生长在沁源人骨子里的沁源秧歌,欢宴时,悲伤时,婚丧嫁娶时,便唱起它,唱出生老病死,唱出人情世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族危难时,也唱起它,声如匕首,心如刀剑,风雷身上过,气节世间留。这乐,丝丝缕缕,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管管弦弦,吟唱在山河之间,与树的风涛鸾凤和鸣,一唱就是几千年。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神迹。
琴高乘鲤飞翔,树林之中留下他的身影,仙班有他,而人间不再。圣寿寺高卧于灵空山中,李侃坐化,已成佛影,尘世与佛陀,不过是两件暂且容身的袈裟。道佛相融,这是神的世界,而神的工作与人的工作是相同的,都是在荒凉的地方种一些树。
在沁源,无论是灵空山内,还是世外,都有不同的世界,又都是树的世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山、河、树、花、药、鸟、乐,都是满目雄浑的一部分,万物各自为政,又随遇而安,“莫听穿林打叶声”,那是生长的声音。世界在身边,繁盛了,而人隐于树之后,成为树的一部分。沁源人说,树,不是树,而是我们的亲人,它们受伤,我们会疼。却原来,在这里,树与自然是高于人群的,人与它们和谐共生,经过时光淘洗,羽化为精神、梦想和美。
虽是尘土衣冠,却不妨碍我有江湖心量。此刻,前有千古远,后有几万年,葱茏如是,绿意如是,万里江山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