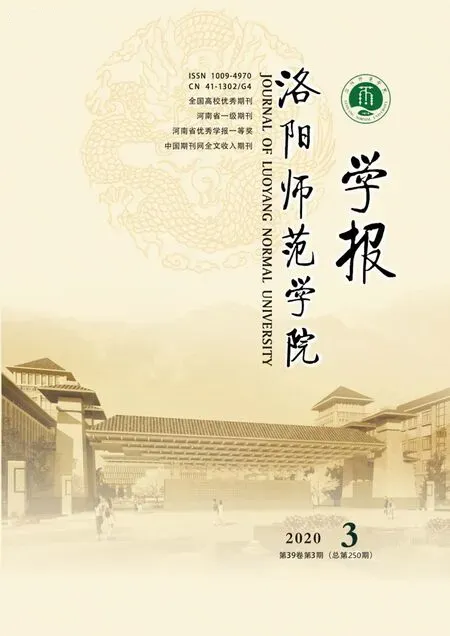融媒体背景下的地域文化译介策略
郑东方,陈德用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文化软实力是对经济发展的有益补充。中华文化的海纳百川不仅体现在包括饮食、汉字、建筑、国画等有形表现,又包含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相处模式、生产方式在内的无形表现。[1]中国地域广大,各族各地文化习俗不尽相同,如何将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翻译并传播至海外,亦需商榷。
随着融媒体的发展,文化交流已不仅限于传统的报纸传播和电视媒体,新型的互联网数字化传媒有力地促进着各国文化的融合。专业学者的参与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直播平台等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改变着地域文化的传播途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有机融合正变得日益普及。但由于融媒体在传播理念和融合度等方面还呈现出若干不确定性因素,地域文化的译介也因此需要一些建设性的参照和建言。
一、融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有机整合
“融媒体”一词最早出现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强调新闻传播与科技信息的融合。这种融合狭义上讲是传播活动的时空交汇,广义上则指传播渠道、介质与技术标准和行业术语甚至文化范畴的集合。
2003年美国新闻学家谢因波曼提出了自媒体(WeMedia),即参与式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这种媒体以网络论坛(BBS)、博客(Blog)、即时通信(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等为主要传播途径形式,采用电子化、数字化的通信手段,进行身边新闻的自主化传播。2004年美国弗吉尼亚媒体中心的沙尼·伯曼就预言,到2021年普通大众将生产50%的新闻内容,主流媒体必将接受这种新闻传播形式并对之妥协。[2]2007年图灵奖获得者、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吉姆·格雷提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基于数据密集型计算的科学研究范式。这意味着基于融媒体和大数据的文化译介传播正在引发新的热潮。2014年英国企鹅出版公司执行总裁亚历克斯姆指出中国文化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仍然十分陌生,一位中国作家通常得拿到诺贝尔奖才能在西方被认知。[3]
国内对“融媒体”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阶段。早期研究重点集中于宏观层面,侧重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栾轶玫和尹章池等人提出创新是融媒体时代的发展理念,为传统媒体向融媒体的转型指明了发展方向。2013年后,国内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微观层面的新闻实务研究。扈长举和王长涛从受众为本、多重工具、故事驱动和专业主义四个方面阐述了融媒时代新闻报道的理念和方法。这是对记者的传统价值和报道技巧的重新挖掘和再次补充。丁敬梓探讨了主流媒体对网络言论进行正确引导的迫切性。[4]近年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传统媒体与融媒体之间的过渡和融合。张小玲通过传统文化的“旧”和融媒体的“新”的结合,探讨了通过融媒体传播传统文化的一些方式。[5]
由此可见,融媒体的发展尚在探索阶段,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尝试探索融媒体的新型传播路径,针对融媒体背景下的地域文化译介鲜有研究。而西方人更是对中国地域文化深感兴趣,地域文化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民族特征,是一个地域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智慧财富和物质财富。因此,地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就成了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
二、地域文化译介的桎梏
(一)文化偏见
中国地域文化的海外传播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以文字为主要载体,而根据西方出版制度,中国文学需要西方的汉学家以及翻译出版发行机构等多方审核后才能向海外推广和发行。这种译介模式无形中偏向和讨好了西方读者,适应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偏好,但不利于异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有种“曲意逢迎”的意味。因而,中国文化未能在海外产生应有的影响力,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不够全面和客观。如果说西方媒体的版权制度是传统媒体时代的弊端,那么西方读者长期形成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强势心态就促成了中国地域文化的“边缘化”。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失衡导致了中国地域文化在西方被误读乃至扭曲。有些西方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印象还停留于“停滞封闭的乡村、政治迫害或扭曲性爱”。[6]
(二)翻译策略的一边倒
在传统媒体时代,多数地域文化的传播是通过文字的记载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海外传播的。因此,代表中华文化的文学作品就成为“向世界说明中国,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7]。而译者处理文学作品时,考虑到英美读者对中国地域文化的不熟悉,尽量将其以“归化”手法处理。这样英美读者读到的译文就俨然成了“地道”的“本土作品”。首先这不利于跨文化交际和传播,中国特色文化并未被西方人所认知,西方读者因此会误读,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差别不大。其次,译者这种“讨好”英美读者的做法只会让他们保持对自己本国文化的优越感,而无视甚至歧视中国地域特色文化。以林纾的翻译为例,林纾谙熟中国文化,文笔不凡,但不懂外文,他的外译中作品无不充斥着“归化”的翻译手法,将西方描述成和中国一样的状态。
(三)译介活动的单一性
一方面,过于集中的中国文学传播让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形式单一,如《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一直都是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纸质媒介,但2002年《中国文学》的停刊以及“熊猫丛书”的停办成为传统译介的重创。西方人本就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所抵触,过多的官方宣传会加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成见。汉学家蓝诗玲认为中国文学缺乏人文关怀,几乎所有小说都被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签,充其量是“中国的宣传教育资料”。[8]同时,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集中于官方参与和支持,如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等的开展,但多数都集中在杂技、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引介。法国驻华外交官Alexandre Ziegler(亚力山大·齐安杰)曾表示,希望能带来最新、最有代表意义和创新性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像文化遗产一样的节目。[9]
我们在努力传播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同时,应当拓展译介的取材范围,更多地推广一些反映中国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的人文思想,让西方读者摆脱过时、传统的视野。另一方面要拓宽译介渠道,不受限于传统媒体渠道,及时采用最新媒体技术,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三、地域文化译介策略
(一)文化学者与专业译者的共融
在传统的译介传播中,译者的传播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介传播的译作风格走向和议题进程。而在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上,专业学者和专职译者依旧是开展地域文化译介传播的中流砥柱。可以说,这二者的相互影响和兼容共生构建了融媒体时代的译者主体。[10]
以滁州地区所在的江淮文化为例,滁州本地学者的研究侧重在传统历史文化名人在滁州的生活,如欧阳修和韦应物等文人的诗歌典故,以及滁州地区的旅游文化研究等。而滁州地区以外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江苏盐城创刊的《江淮文化》杂志,蚌埠学院和合肥学院各自创建的江淮文化研究所。上述研究均立足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强调地域文化的历史性和时代性,鲜有涉及地域文化的译介和推广。而传统译介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文学这种“具体实质”的文字记载,对于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如琅琊庙会、滁州竹编、凤阳花鼓等的译介关注较少。这些文化资源具有历史性、独特性和地域性,凸显了滁州的地方特征,成为滁州特色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资源优势。但目前市场上的地域文化产品只停留在文字或图案装饰等低层次的呈现,未能使滁州的地域文化与产品紧密结合。[11]
不仅江淮文化如此,与其相邻的桐城派文化中的文学典籍译介活动也未能得到专业学者和译者的“合作”,而真正实现译介主体的兼容性构建。这种不对称的双向研究很难让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和融媒体时代的机遇中脱颖而出。因而借助融媒体的资源整合,将专业文化学者和专业译者结合起来,二者共同承担地域文化译介主体的职能,从而实现地域文化的“走出去”。
(二)陌生化翻译策略
“陌生化”这一概念是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这位形式主义大师认为作者应采用特殊的创作手段来将日常熟悉事物“陌生化”,使其脱离原物的形象,让读者的阅读时间和空间延长,产生新的认知体验,从而增加文学作品的美感,最终读者可以在习以为常的语境中感获新认知。[12]那么在地域文化的译介中,为满足目的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认知需求,译者就需要采用独特的陌生化翻译策略让读者对异域文化产生“陌生感”,进而激发读者的认知欲望并满足其猎奇心理。莫言作品中的山东高密地域文化,姜戎的草原地域文化,以及王安忆的海派文化在海外大放异彩,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这些译作的成功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译者的陌生化翻译策略,其将中国的地域文化“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
在融媒体时代,数字媒体为地域文化的译介提供了新途径。传统纸质书籍可以通过电子书如kindle等方式随时随地阅读。除了以文字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可以在数字媒体平台传播外,一些非文字形式的地域文化如饮食、服饰和建筑等也有了全新的译介形式。通过如抖音等手机APP,一些当下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热词和新词,以及新生事物可以更快地通过文字、声频和视频更加形象生动地传播。通过“文字+图片”和“文字+视频”的传播模式,采用陌生化译法,让英美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地域文化,从而树立地域文化的海外形象,有利于跨文化交际,进而做到文化重塑和文化自信。
(三)拓宽译介渠道
首先,如果地域文化的译介仅仅限制在学术圈和文学圈,被动等待国家政策主导,这将无法适应融媒体时代的传播走向。借助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尝试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团体参与的机制,地域文化译介传播也相应有了制度和资金保障。完善与西方出版发行方和文化传播公司的合作和互动,特别是与国外主流媒体的良性互动,并及时解决译介传播和推广的难题。但也应注意不要以西方价值观为取向,应保持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学者郭建宁指出: “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要注意是‘走出去’,而不仅仅是‘送出去,所谓‘送出去’就是以‘送’为目的,而不大顾及别人的接受方式和文化习惯,往往是政府买单,组织华人和留学生观看,而对国外主流社会没有什么影响。”[13]一方面要注意保留中国地域文化的民族性和陌生感,这样有助于西方读者体验中国地域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另一方面要避免强加于人的“硬性推销”,通过对西方文化准则的了解,尝试探索中西译介的新型传播途径。
其次,开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包括网络、微博、手机APP等多种新技术平台都可与地域文化产生互动。多种媒介传播意味着多样化的接受渠道和接受环境,有利于中国地域文化的良性推广。如1988年由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后,莫言的小说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汉学家和西方读者开始关注中国山东高密地区的地域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类似的推广活动仍然太少,在融媒体时代的今天,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可以成为地域文化译介的新途径。时下自媒体也是地域文化译介的新型途径,自媒体具有典型的“草根性”,更接地气,通俗易懂,更具有地域文化的代表性。但这种“草根性”在信息发布者的自律性和外界对信息真实性的鉴别方面有待提升,因此,也应加大对自媒体的监管力度。
再次,加强信息技术与专业翻译兼备的优秀译者本土化培养。当下中国地域文化的译介主体是汉学家,优秀的本土译者严重匮乏。如果长期被动依赖“外援”,中国地域文化的传播依旧步履维艰。在融媒体成为主流的当下,掌握翻译信息技术的本土译者的优势不仅在于更了解中国的地域风土人情,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为国家文化建设培养生力军。
中国地域文化需要借助融媒体的全方位多平台的传播渠道更好地传播和发扬。中国地域文化译介遭遇的发展瓶颈不仅有国内外环境的“人为”因素,也有传播途径的“技术”因素。在融媒体的文化“助力”下,加强译介主体的“兼容性”; 拓宽译介渠道,开拓多元化的传播途径; 并着力培养信息技术与专业翻译素养兼具的本土译才,紧紧抓住时下融媒体的开放和技术性特征,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传承发扬,建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