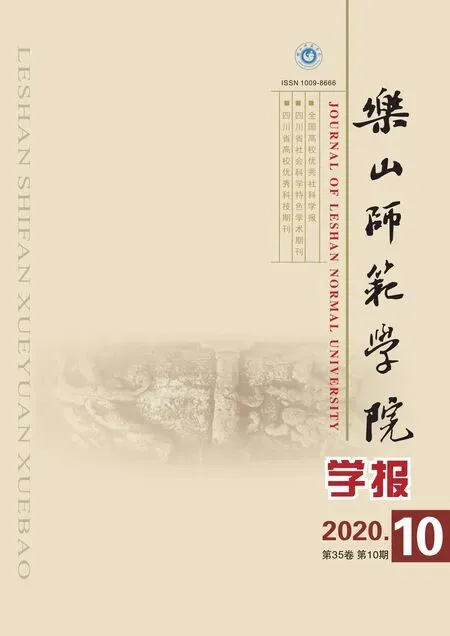赵元任语法学思想接受研究
刘宗保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学术史研究离不开“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接受研究是指从读者(接受者)角度分析其对相关作品及其作者思想等的接受情况,凸显读者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一关系中的中心地位,要义在于研究读者对相关作品及作者思想等的阐释、发展,展现相关作品或作者对后世研究的影响程度,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接受研究源于文艺美学界,语言学界首先注意到接受学的是谭学纯等[1]的研究。该文主要从共时的修辞接受者角度研究修辞活动,构建了“接受修辞学”框架。此后鲁国尧[2]针对语言学界对接受学研究的现状,呼吁中国语言学接受“接受学”。张楚[3]则对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地接受史研究。但在语言学的接受学研究中尚未见到与汉语语法学研究相关的接受研究。为此,本文尝试以赵元任的语法研究为个案,从接受的角度探讨其研究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程度,以期学界更好地认识赵元任语法学思想在当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理论价值。
一、接受对象与接受度
(一)接受对象
对赵元任语法思想的接受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其作品的译介和结集出版等,可称为版本接受。我们认为相关学者的著作或作品出版后被不同程度的译介、再版重印等,也反映了学界对其作品思想的接受程度。二是对其作品内容的接受,可称为文本接受,这是接受研究的核心内容。版本接受是在文本接受基础上实现的,同时相关版本不断地译介也会扩大文本的影响。
(二)接受度
文本接受有程度之分,即有强接受和弱接受。强接受是指作者提出的理论思想得到学界的显著接受。当然,这种显著接受可能并非完全接受,而是存在一定争议,但争议本身也说明学界的重视程度。强接受又可分为集体强接受和个体强接受。集体强接受侧重相关思想被学界普遍接受形成了一定共识,或者说是学界的一种集体接受。个体强接受侧重学者个体挖掘并重新审视相关理论观点的过程。这两种接受可以相互转化,集体强接受中的某些理论观点可能会在学者个体研究中重新审视接受,挖掘出新的理论价值。同样,个体强接受的内容也可能会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集体共识。弱接受则是不完全或非显著接受,是对相关的理论分析提出一些质疑或否定,这种接受可能是部分接受,或者是对其他学者对其思想观点接受有误基础上的的再接受。但其本质都是对相关思想观点的重新认识。
二、版本接受
版本接受主要包括其语法著作版本的接受和相关论文集对其语法论著收录的接受。
(一)专著版本接受
赵元任的语法著作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为《中国话的文法》。同时,因为该著作是在《国语入门》基础上的拓展,因此本部分版本接受重点是对这两本专著的接受过程作一梳理。
1.《国语入门》版本的接受
《国语入门》(MadarinPrimer:AnIntensiveCourseinSpokenchinese)是赵元任先生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粤语入门》(CantonesePrimer)基础上扩充而来的。该著作从版本接受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层面:
一是从版本的译介来看,主要是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翻译版:一个版本为台湾出版的由斐溥言释述、董同龢校阅的《国语语法大纲》;第二个版本为李荣翻译的《北京口语语法》,于1952年在开明书店出版,195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李荣先生在编译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章节调整,同时也将《粤语入门》一书中的相关部分纳入其中。
二是作为后来相关著作的直接参考体系。丁声树[4]等出版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深受该书翻译版的《北京口语语法》的影响,周法高[5]认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
2.《中国话的文法》版本的接受
赵元任先生1968年在美国伯克莱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描写汉语语法的专著AGrammarofSpokenChinese,1970年出版第二版。该书出版后在汉语学界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分为中译本和原文再版两类。
(1)中译本的接受
该书的中译本分为节译本和全译本两类。节译本为吕叔湘1979年翻译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口语语法》,此后又多次再版发行。此外,台湾学海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国语语法-中国话的文法》版本,从目录来看,该版本是吕叔湘版本的再版,基本术语和章节完全一致。
全译本为丁邦新先生于1980年翻译的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该版1982年再版,2002年出增订本。1996年,该版本又被收入由刘梦溪主编、胡明杨等编校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
(2)英文原版的接受
英文原版也有两个版本:一是收录在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元任全集》(第3卷)中。该全集依类成卷,共计20卷,在该全集中收录的即为该书的英文原版。二是于2011年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该次出版的为平装本。201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年纪念)精装本,《中国话的文法》英文版是为其一。
从《中国话的文法》由原版到中译本的接受来看,两岸三地的汉语学界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版相应的中译本,这反映了当时该著作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从翻译的版本内容来看,有全译和节译之分,这也说明不同学者在接受其内容时的取舍之分。其中节译本翻译时,吕叔湘先生认为“原书是供英语读者用的……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斟酌情况,重要的地方全译,多数地方删繁就简,少数地方从略。但是就内容说,没有实质性的削减。”同时该书翻译时也根据了两个版本,“本书前半部分是根据初印本(1968)翻译的,后半部是根据第二版(1970)翻译的”[6]。 正如赵元任所言:“把应该对中国人说的话都准确的译了,把不必对中国人说的话跟例子都删去了。”[7]也就是说节译本和全译本的区别主要在于受众之分,但其实质性的学术内容并无分别。
从时间跨度及出版频次来说,两个中译本及英文原版在后来的不同时间多次再版重印,或者收入不同的文集中,也说明了该著作的学术价值不断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肯定。
从版本阅读的角度来看,学者更多地是对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中的口语用例或者术语表达上的问题提出看法。张志公认为,赵元任先生写《中国话的文法》这本书时,因为离开中国时间很长,“书中的用例,显得有点过时了”[8]。郭良夫则认为,《中国话的文法》还需要全译本,因为“这两版都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大陆的读者不容易见到。再说丁译有些用语跟我们常用的也不大一样。”[9]文中还举例指出如果不全译出来,书中有些话还是不容易明白,有些有启发价值的思想未能充分得到体现。
(二)论文集版本接受
国内最早对赵元任语言学论文进行译介和收录的当为1985年由叶蜚声翻译、伍铁平校对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该论文集主要译介了4篇论文,但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涉及音位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的相关内容。
之后有正式的语法学相关的论文集当为1992年(赵元任诞辰100年)由袁毓林主编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该书收录论文共计16篇,其中与汉语语法(包括方言语法)相关的论文有5篇,分别为《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汉语语法与逻辑杂谈》《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汉语中的歧义现象》和《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
此后,赵新娜与吴宗济于2002年(赵元任诞辰110年)合编了《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论文集分中英文两卷,中文卷为赵元任用中文发表的及部分翻译的论文译文,英文卷为未经翻译的英文原文及译文列为中文卷的英文原文,因此从译文来看两者是有重合的。就中文卷而言,该论文集共收录论文63篇,其中语法相关论文8篇,除了之前袁毓林编选论文集中的5篇外,另外三篇分别是《国语的语法和词汇问题》《中国语法图解两例》和《“俩”“仨”“四呃”“阿”》。
从收录论文来看,语法方面主要是集中在前述5篇中,这也是后来学界经常引用和讨论的文献,对后来的研究影响相当深远。本文后面讨论的文本接受很多都是源自这5篇文献的接受。
三、文本接受
(一)强接受
赵元任语法学思想中被学界“集体强接受”的主要集中在其《国语入门》《中国话的文法》及相关论文中。其中前两本著作“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从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10]。
具体而言,据刘宗保[11]梳理,朱林清等[12]、龚千炎[13]、邵敬敏[14]、陈保亚[15]、李葆嘉[16]、安华林[17]、林玉山[18]、李宇明等[19]对赵元任的语法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括,这些也是学界普遍接受的,主要包括:语言观上区分了同代与异代、描写性文法与规范性文法、分类性文法与结构性文法;研究对象上,注重汉语口语研究;研究方法上,首先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汉语,如第一次系统使用鉴定字等;具体的语法体系建构上,创建了“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并以此结构建立了汉语构词法体系;在句法范畴问题的探索和解决上,认为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根据句内位置确定主宾语;提出了“整句”和“零句”概念;等等。
这些语法思想在不同时期被相关学者提出,并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同时,有的思想观点在当时的理论价值与现时重新认识价值可能发生变化,而这正是需要我们从接受的角度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个体强接受”强调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为解决新问题或进行反思等过程中,相关学者挖掘的一些具有当代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的过程,这些问题可能是系统性的,也可能是相关个案。
1.语音与语法研究互动观点接受
赵元任特别重视口语研究,因而语音或与之相关的韵律节奏等作用在整个语法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黄灵红[20]根据补译吕叔湘翻译的《中国话的文法》相关内容,阐释了对赵元任语言研究中语音形式与语法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刘平[21]和戴军明[22]通过分析《汉语口语语法》,指出了该书中蕴含着语法与韵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思想,认为语法研究必须重视与语音的结合。
具体到赵元任关于语音和语法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在研究中的接受主要有两方面:
(1)“那级单位”的接受问题
汉语研究的本位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如何解决汉语中的词的大小与离合以及语言结构的本位等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赵元任指出,“综合考虑韵律成分、形式类和同形替代等几个方面,也许会产生出一个跟其他语言的word很相似的概念”“为什么非要在汉语里找出其他语言中存在的实体呢? 更有成效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是确定介乎音节词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23]239-240。这一认识对后来的汉语本位问题多有启发,比较突出的是“字本位”理论和“韵律词”概念的提出。
1)“字本位”理论对“那级单位”的接受
关于汉语的本位是词还是词组或字等一直是语言学界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一讨论中的代表之一即为“字本位”理论。徐通锵[24]认为赵元任对汉语的字和英文的word概念的认识与“字本位”的汉语语法研究理念有契合之处。赵元任认为,印欧系语言中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23]233。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23]248“人们不要在汉语里去寻找在其他语言中存在的实体,更有成效地进一步研究是确定介乎‘字’(音节词)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23]239-240。
徐文认为赵元任对汉语“字”的性质的认识是当时最为精确和科学的。在徐氏看来,“字”是中心主题即意味汉语的结构以“字”为本位,应该以“字”为基础进行句法结构的研究,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字本位”的理论体系。不过后来冯胜利[25]9认为,字本位如果要成为一个具有语言学意义上的术语的话,那么它就是“音节词”的代名词—是词,而不是字,也即从音节的角度来定性“那级单位”。
2)“韵律词”概念对“那级单位”的接受
汉语中关于“词”的大小边界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讨论。冯胜利[26]161-174认为应该从多维性角度来看待汉语“词”在句法、词法和韵律等界面的特征。冯文认为,赵元任所提出的介于音节词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不可能是词,也不可能是短语[26]164,“赵元任所谓的‘那级单位',不是别的,正是音步,正是由音步决定的韵律词”[26]165。它是句法、词法和韵律之间交互作用的枢纽。冯胜利后来也再次指出,“赵元任找的那级单位除‘韵律词’而莫属。”[25]7因而尚新等[27]指出,冯胜利先生对韵律词的论述均表明了其来源得益于赵氏的韵律思想。
不过关于冯胜利认为韵律词这个单位是赵元任讨论的“那级单位”,沈家煊等认为,其实赵先生说的是“介乎音节词和句子之间的‘那些单位’,而不是‘那级单位’”[28]69。
当然这是不同学者的认识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赵元任先生关于“那级单位”对“韵律词”概念的提出及其后来韵律语言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关于汉语音节和节奏认识的接受
音节相关的节奏问题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愈发受到重视,是语法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界面。沈家煊[28]47-73在讨论汉语的音节和节奏问题时,就从赵元任的相关研究中受到启发,提出了相当深刻的见解。赵元任认为汉语“单音节是非常活跃、具有意义、变化不大的单位”,又“由于大多数音节有完整的声调”,“音节与音节的长度和响度跟其他许多语言相比变化小”,所以汉语“连续话话的节奏呈高度的单音调”[23]246。沈家煊[28]50根据赵元任的这一论述对英、汉语的节奏进行了区别定性,即英语的节奏属于“重音定时”型,轻重控制松紧,轻重为本;而汉语的节奏属于“音节计数”或“音节定时”型,是松紧控制轻重,松紧为本。
此外,沈家煊[28]52还在赵元任[23]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汉语节奏伸缩性的特点,并进一步申述认为汉语的节奏单位要区分“基本单位”和“强势单位”,单音节是基本单位,而双音节是强势单位。
沈文这一研究进加深了对汉语相关单位和结构的重音形式以及与意义松紧关系的认识,同时也说明了赵元任关于汉语音节节奏问题的分析还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值得重新审视。
2.“汉语主语是话题”认识的接受
汉语主语和话题关系问题是汉语学界热门问题,赵元任认为“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是动作者和动作的关系。但在汉语里,这种句子的比例是不大的,也许比50%大不了多少。因此,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较比合适。”[29]45这一特点被称学界称为“汉语式话题”。这一认识对后续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有诸多方面,本文着重分析与该观点相关的三个方面的接受情况:一是关于汉语自由容纳非论元句法成分(主语)认识的接受,二是汉语谓语动词方向模糊性认识的接受,三是“零句是根本”认识的接受。
(1)汉语自由容纳非论元句法成分(主语)认识的接受
论元成分与句法位置之间的约束关系在学界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对非论元成分在受约束的句法位置上出现有不同分析。张伯江[30]认为,汉语中非论元性成分在受约束的句法主语上位置上出现非常普遍,表现为自主/非自主动词类主语、施受同辞类主语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在赵元任[31]中都有讨论。张文认为赵元任是最早意识到汉语可以比较自由地容纳非论元性的句法成分的。赵元任主张用语用概念“话题”和“说明”来确认汉语的主语和谓语。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汉语语法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依赖论元结构的支撑,汉语基本句法事实是句法成分形式上的说明性的并置关系。
(2)汉语谓语动作方向模糊性认识的接受
汉语主语看作话题还涉及到谓语动作的方向性问题。赵元任认为:“把主语看作主题的话,可以得到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谓语里动作动词的方向不一定能够是从主语到宾语”,“但是,有好些动词,从动作本身性质来看就没有明确的方向”。[31]41这一认识实际上隐含了对汉语句法格局的理解。赵先生举了相关例句来说明,其中“叫”字句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例子。张伯江[32]则沿着赵元任对“我叫张老三”认识的思路,即不是来自被动化的语法变化,进一步探讨了现代汉语“称说”义动词所构成的句式的来历。在此基础上,张文把这一发现延伸到对其他动词的观察上,力图说明汉语话题结构在汉语语法中的决定性作用。张文认为“叫”字句个案反映了汉语的基本句法格局就是话题句。动词谓语的方向之所以不明确,就是因为汉语谓语的根本特点在于说明性。
(3)“零句是根本”的接受
“零句(minor sentence)”是赵元任先生在《中国话的文法》中提出的概念,“零句没有主语-谓语形式。”[29]42。“一个整句是一个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29]51这一概念自提出来之后,在汉语语法学界没有被充分地重视和挖掘。沈家煊[33]一文对“零句说”及其相关的汉语“流水句”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赵元任先生的“零句说”是从整体上、根本上揭示了汉语语法特点的重要学说。沈文认为,对“零句是根本”的忽视是很多人对汉语主语和话题的关系认识有偏误的原因。而主谓结构可以做谓语也是从“零句是根本”这一认识推导而来的。沈文还在零句说的基础上,阐述了流水句的“并置性”和“指称性”,而这两个特性对语法理论中句法递归性和名动分立的普适性提出挑战。
对“零句是根本”的认识也关涉到对汉语逻辑特点的分析。沈家煊[34]通过对《汉语语法与逻辑杂谈》[35]和《汉语的逻辑如何运作》[36]等论著的解读,对汉语逻辑的特点作了详细的阐释,并结合其提出的“名动包含说”和“用体包含说”进一步申述了作者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如汉语里主语和话题的关系不是分立的关系,而是“话题包含主语”的包含关系;汉语多采用并置的方式和松散的话题说明句等。作者认为,这些都跟“零句是根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述三个方面的接受都和赵元任关于汉语主语和话题关系的认识相关,有的是从其直接推导而来,有的是与之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相关结论。也说明赵元任关于主语和话题关系的认识对汉语语法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
3.其他语法研究的个体接受
赵元任的语法思想除了上面几类接受之外,也有其他语法研究课题逐渐挖掘并重新审视。
(1)汉语语气词研究的接受
赵元任在《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37]等论著中有相关语气词的研究,其中有的分析对当代汉语语气词的研究也有一定启发。
赵春利等[38]在研究句末助词“嘛”的认知与情感的关联性研究时就受到了赵文相关研究的启发。赵元任[37]890-891将“末”(即“嘛”)的认知语义界定为“应知未知”,即表示的是“你应当知道、记得或懂,但我想或我怕你实在不知道,不记得或不懂”。后来,赵元任[29]357进一步从“固执味道的肯定”中揭示出“你应该知道、你怎么不明白”的内涵,赵文认为赵元任提出的“应知未知说”为系统地揭示“嘛”认知、情感及其关联性铺设了桥梁。此外,赵春利等[38]35在分析陈述句与“嘛”之间的选择关系时认为,赵元任揭示了“末”字陈述句在人际交流层面所隐含的“应知”义。而“嘛”字陈述句具有的“命题确信性”和“对方应知性”两个语义特征在赵元任的论述中已有所提及。也就是说,赵元任对汉语语气词的相关分析对当代语气词研究中仍然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
(2)在古汉语研究中的接受
赵元任相关语法思想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薛凤生[39]即在赵元任语法研究思想的启发下,将汉语的句法归纳为八个特色:高度的“口语风格”、主语和谓语的含义为话题与说明、语气词具有标示句式的功能、语法词常有省略、所谓“词类活用”、“词序”决定词类之语法功能、谓语形式多样和“零句”极普遍。这八个特色是作者在赵元任相关语法思想基础上得出的,包括汉语的主语和谓语就是话题和说明关系、句子有“零句”和“整句”之别、“零句”是汉语口语的常态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将这些句式特色运用到对古汉语句法的分析有很大裨益,甚至有的效果是赵元任没有提到的,如对所谓“主谓结构”和“被动式”的讨论。可以得知,赵元任的汉语语法思想对古汉语研究也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二)弱接受
对赵元任语法研究中相关问题的分析有学者也存在一定的质疑,这种质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赵元任本身研究相关结论提出的不同看法,是部分接受;另一方面是有学者在接受赵元任相关分析时可能存在理解不准确的地方,后来学者对其的解读指出质疑,是再接受。
1.部分接受-汉语主宾语的有定无定问题的接受
关于汉语主宾语有定和无定问题,赵元任指出:“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主语所指事物是有定的,宾语所指事物是无定的。”[29]46这一判断分为前后两部分,即主语是有定的和宾语是无定的两方面。根据王红旗[40],学界对这一观点基本是接受的,如刘月华等[41]、徐通锵[42]、李艳惠等[43]。同时也有学者针对前部分或后部分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范继淹[44]针对前半部分提岀“无定NP主语句是汉语的一种句式,并不罕见,也不特殊”。黄南松[45]针对后半部分,提出宾语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定的”。王红旗认为,“赵元任只看到了无定成分倾向于作宾语,但没看到有定成分作主语和宾语都是自由的”[40]86。因而这个观点的前半部分(即汉语主语的绝大部分是有定的)符合事实,而后半部分(即宾语绝大部分是无定的)不符合事实。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信息传递原则与经济原则在主语位置上不竞争,绝大多数主语是有定的;信息传递原则与经济原则在宾语位置上竞争,大多数宾语也是有定的,但数量低于主语。
2.再接受
(1)提出“羡余”汉语术语的接受
“羡余”在英文中称redundancy。在汉语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赵元任是提出汉语“羡余”术语并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如曹婧一[46]、王进文[47]、潘先军[48]等。据宋定宇[49],他们是依据赵元任的论文“Formal and Semantic Discrepancies between DifferentLevels of Chinese Structure”(《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的中译版中用了“羡余”来翻译进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但根据宋定宇[49]78的考证,从1836年至1968年赵元任等多名中西学者有关汉语研究的中英文献中,发现此期间从较早的汉学家郭实腊到较晚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等至少10名学者都谈到过汉语的“羡余”现象,并有西方汉学家明确提出了“羡余”的早期汉语术语。也就是说赵元任先生并不是最开始关注这一语言现象并使用“羡余”的第一人。
宋文[49]83还认为,在赵元任用汉语撰写的文献中并未发现“羡余”一词。并进一步认为,朱德熙[50]在讨论“差一点+VP”结构时已经使用了“羡余”(redundant)一词来描写某种语境下该结构中的否定词“没”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此宋文认为,朱德熙先生应该是提出汉语“羡余”术语的第一人。
(2)关于“越来越……”中“来”性质的接受
关于赵元任是否把“越来越……”中的“来”定性为“代动词”在相关研究中有不同接受。龙国富[51]在分析“越来越……”这一结构时,根据赵元任[29]290的分析,认为这里的“来”在句中表示为一般化的用法,是以代动词( pro-verb) 的身份出现,指代前面已经出现的动词。马楠[52]则认为,赵元任[29]70谈到“越来越……”结构时,并没有说其中的“来”是代动词,只说它同“过”或“变”一样,是在“找不到一个动词(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的情况下,用来“填空的动词”。“填空的动词”并不等于“代动词”,否则“过”或“变”也要被视为“代动词”。而赵元任在谈“来”的代动词用法时,所举用例中并没有“越来越……”结构。所以作者认为,“越来越……”中“来”是代动词这个观点,不能看作是赵元任的观点。
弱接受无论是部分接受还是再接受都是在对赵元任语法思想挖掘基础上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学界更准确地认识相关思想内涵,是对赵元任语法思想研究的重要补充。
接受研究可有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纵向研究是从动态历时的角度展现某个作品的理论观点被读者接受的过程,横向研究是从静态的角度展现相关作品被读者接受的现状或者结果,两者是相互补充的。赵元任语法学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从辞态角度举例式的分析了比较典型的接受研究案例,并未充分展现某一语法思想在学界研究接受的脉络,目的在于提出语法接受研究框架以抛砖引玉。后续研究可以就本研究中某个具体的语法思想更深入地分析其接受历程,也可以继续发掘其他理论观点在学界的接受情况进一步研究,从而可以从点和面的角度更系统地分析赵元任语法学思想的接受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