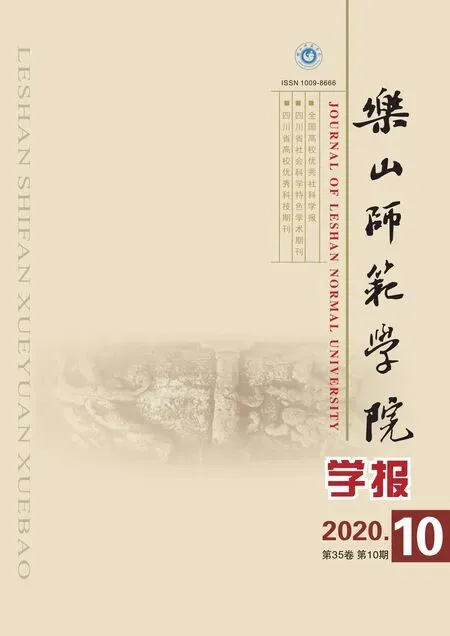从《计算之星》看STEM领域女性职业困境
廖全宇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在大众刻板印象中,科幻小说界是由男性主导的领域。然而女性作家实际却一直是科幻文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科幻作家布莱恩·阿尔迪斯认为近代意义上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是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1]5,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加拿大女作家玛丽·艾特伍德的作品在当代科幻小说文坛有着重要地位。自2016年起,素有科幻界奥斯卡之称的雨果奖的重要奖项几乎都授予了女性作家,如2016至2018年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都由黑人女作家N·K·杰米辛(代表作《方尖碑之门》《巨石苍穹》)斩获,2016年中国女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当年度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她们的作品从女性作家的视角对性别、种族、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赋予了当代科幻文学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一种进步的话语体系,大胆质疑现状,探索着各类富有争议性的话题[2]127。
2019年,美国女作家玛丽·罗比尼特·柯瓦(Mary Robinette Kowal)凭借小说《计算之星》(TheCalculatingStars)一举包揽科幻界三大重要奖项的最高荣誉,包括雨果奖的最佳小说奖、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和轨迹奖最佳科幻长篇小说奖。《计算之星》讲述了女科学家艾尔玛·约克(Elma York)克服多重阻力成为一名宇航员的故事。在1952年的平行世界,华盛顿特区毁于一场彗星撞击,科学家们发现地球50年后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于是全球开始了宇宙殖民计划。科学家艾尔玛·约克发现来自社会和体制的歧视使女性无法成为宇航员,于是踏上了努力和抗争的道路。
在传统观念中,理工行业或STEM领域(即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mathematics的缩写)是以男性从业者为主的领域,但在今天这一领域的性别分工和构成随着性别平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被打破。柯瓦在小说中,对政治、种族、性别以及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她尤其关注到女性在航空领域这一传统理工行业的职业发展问题,这与当代女性职业发展现状息息相关。但对于她的作品的研究,尤其是从女性主义角度的解读在学术界还存在大量空白。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或然历史小说呈现出的女性在理工科领域的职业发展的困境、出路和现实意义。
一、走回现实的或然历史
《计算之星》的每个章节都以一段简短的新闻报道开头,交代故事进程中的时间和世界局势。初读小说,会让人产生强烈的以假乱真的感觉,读者实际很快就会随着故事展开发现小说和真实历史的偏差,即所有故事都构想于一个平行世界的框架中。这种文类在科幻小说中被称为“或然历史”小说。在19世纪末,作家们对历史做出虚拟式推想[3]112,创造出“或然历史”这个文类。或然历史小说基于某个历史分岔点探索,即让历史“在某个岔路口走向不同方向”[3]113,导致后续历史与我们所知的历史产生偏差,产生“夸张而且常常是讽刺的效果”[4]209,并且“基于对偏离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审视和思考”[5]78。例如希莱尔·贝洛克和G·K·切斯特顿等作者在早期或然历史作品集《如果事情不是这样》(1931)中,推想了重大历史事件所可能会产生的不同后果和结局[3]113。
那么《计算之星》与真实世界的历史分岔点在哪里呢?小说开头的彗星撞击看似是与现实最明显的分歧。发生于1952年3月3日的该事件将整个华盛顿特区夷为平地,充满了戏剧性,美国随后陷入水深火热的灾后自救和重建。但并不是所有或然历史小说的作者都会以在故事最初的事件作为真正历史分岔点。实际上,在故事开头,读者已“身处一个不同的世界”[4]210,在跟着主人公体验“那个瞬间后的很多年”[4]210,在小说进程中才去渐渐发现“会发生什么”和“已经发生了什么”[4]210。据作者在全书后记的“历史笔记”中所述,从托马斯·E·杜威(Thomas.E.Dewey)击败杜鲁门当选美国第33任总统开始,历史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点读者从第一章开头“摘录”的新闻标题“杜威总统祝贺NACA成功发射卫星”[6]1已经可以窥见端倪。这是小说中美国成功发射的第三颗卫星,而现实中,美国直到1958年10月才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直至1983年,萨利·莱德(Sally Ride)才成为飞入太空的第一位女性[7]。因为需要“一位能够更早一点开始太空项目的执政总统”[6]310,在杜威替代杜鲁门执政的这个美国,航天科技方面有更早的发展,而美国因为天灾并没有将国力耗费在马歇尔计划和越战上。虽然小说中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脱离我们所知的“既定世界”的常识。社会的其他方面,诸如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思想理念和读者所知的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并无不同。性别和种族歧视依然盛行,女性和有色人种也在抗争和寻求平等。
那么《计算之星》仅仅是一个灾后的人类重生和宇宙探索叙事吗?如同多数探索末日主题的科幻小说,《计算之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人类对“灾难后恢复正常秩序还存有坚定信念”[3]115这个话题。但或然历史小说的存在价值并非是仅仅编造出新奇的情节,而是在于帮助读者另辟蹊径地理解当代社会,因为这样的叙事终究会回到读者的当下[3]113,通过虚构审视现实,反映出“作者在文化上甚至意识形态上的考量”[5]76,甚至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作者通过文本或叙事所投射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5]78。《计算之星》翔实还原了航空航天业的日常工作,还更多落笔于以艾尔玛·约克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在职场、社会上的奋斗经历。包裹在“硬”科幻外壳里的内核是职场女性对突破职业玻璃天花板和职场玻璃笼子的尝试,以及对工业社会中性别分工的平等问题的反思。
二、STEM领域的女性困境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由于大量男性走上战场,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开始工作,填补短缺的劳动力。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提高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已走入各行各业。小说中,女主角艾尔玛在二战期间作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服役于美国空军。灾难发生后,她凭借其数学和物理的博士学位,就职于小说中虚构的国际航空航天联盟(International Aerospace Coalition,以下简称IAC)的计算部门。小说同时也塑造了一群拥有高学历的女性科学家、女飞行员和其他职场女性的形象:收留艾尔玛的全职主妇莫特尔·林德霍姆,因有数学相关学位,灾后在IAC就职于计算部门;女计算师海伦·刘在小说后期也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其他女性宇航员候选人也活跃于情节推进中,比如前运输机飞行员妮可·瓦尔金,以及记者贝蒂·拉尔兹等。
女性在职场上的活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社会运动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8]65,众多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和法案兴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开始于1984年的WiSE(Wome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运动。WiSE运动旨在鼓励更多女性投身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9]199。类似的社会运动还有于2005年兴起的Athena-SWAN运动,在传统STEM领域基础上,增加了医药领域,并且在2015年把工作扩展到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领域[10]。
Henwood在其研究中指出,虽然决策者和从业人员对女性投身科技行业普遍持肯定态度,但WiSE运动成效有限[9]199-200,印证了“女性在STEM领域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女性理工科人才稀缺成为一种全球现象”[11]89这一观点。性别主义倾向在社会中仍然是显而易见的。STEM领域中女性所陷入的困境是多方面的,不仅局限于职场,更能见诸于校园与媒体,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女性在STEM行业中的求学和就职意愿。《计算之星》所涉及1952—1958年这7年历史,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且时代远早于当今,却真实印证了当今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教育、职场和社会舆论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女性在STEM领域求学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教师和同学的影响。女主人公艾尔玛早早就展现出在理科方面的才华,十一岁考入高中,十四岁时考入斯坦福,但她一直以来都是数学课班级中唯一的女性,并且成绩拔尖。这让其他男同学对她抱有巨大敌意,表现出更加有攻击性的情绪,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男性优越感(sense of gender superiority)”受到了破坏[12]41。而教授们则经常让艾尔玛向全班解释数学问题,以刺激男生的自尊心,迫使他们因为羞愧更加努力,因为男生们“不能忍受一个小女孩竟然能懂他们不懂的东西”[6]180,这更让艾尔玛受到同学的孤立和敌对。然而这种教学模式是建立在性别二元主义、性别对立化的思维之上,是基于数学学习能力上男性一定优于女性的前提,因此会让男性在看到女性在理工领域表现出和自己相似的能力时,感受到威胁[12]42。这一思维模式会让男性认为理工科是自己的专属领域,并进一步把这种思维模式带入到日后的工作中,在职业领域严格划分出性别鸿沟,以捍卫自己的“利益”。
因此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和负面导向更加明显。STEM类行业是传统意义上男性为主的领域,对女性来说是非传统的就业选择,作为少数派的女性往往面临着多重的阻挠和困境。在STEM类职场中,即使在具有同等资质和能力的情况下,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女性的自然性别属性,并以此作为女性无法胜任的理由。IAC即使后期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女性职员,这种情况也没有改观。在有相同学位和资质的前提下,男性的职位均是工程师,而女性只能成为“计算员(computer)”处理数据运算这样的基础工作。这种不平衡也直观地反映在性别比例的悬殊上,计算员的数量屈指可数,淹没在工程师的“男性声音”中[6]66,如同7名女宇航员候选人完全“消失”在35名男宇航员候选人中一样[6]242。《圣经》将女性被视为“更软弱的器皿”(彼前3:7)[13]404,在父权主义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女性自古就被视为“第二性”,因此在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中,女人不能且不应从事“危险”的工作。艾尔玛多次申请成为宇航员时,IAC主任克莱蒙兹认为太空探索任务如同“哥伦布探险发现”[6]79,反复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由,多次拒绝艾尔玛的申请,并在媒体上公开回应不考虑让女性成为宇航员,原因是“男性更加胜任那项工作”[6]90。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女性的职场地位远低于男性,因此在工作中受到语言上贬低,以及遭受性骚扰也不足为奇。比如在IAC内部出现工程师勒罗伊·普拉科特性骚扰女性职员的事件,以及外号“泡泡”的工程师波比恩斯基故意造出阴性形式的“computress”[6]128一词称呼计算员(computer),刻意强调计算员的女性身份,引发了所有计算员的强烈反感。
边缘化了的女性在STEM领域往往成为象征性的存在,因此在真正实现抱负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迫于社会舆论,IAC后期招收了一批女性宇航员候选人,实际上主要为对外宣传服务,尤其是在对媒体开放的训练时只要求“走走过场”[6]250。艾尔玛曾在电视节目《魔术师先生》中因获得了“宇航员女士”的外号而全国闻名,因此IAC多次利用这点进行航空航天项目宣传。来自巴西的宇航员候选人杰西拉·帕兹-维沃罗斯称,自己在巴西两名候选人中胜出是因自己还曾获得过选美小姐称号。在看似平等的表象下,艾尔玛和其他候选人承受着巨大的挫败感,因为“科学并不是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6]252,获得社会支持和平息舆论风波才是以IAC主任克莱蒙兹为代表的既有体制所希望得到的,而以艾尔玛为代表的女性候选人愈发边缘化。
在这样的宣传口径下,媒体也为制造性别歧视助纣为虐。新闻媒体在公共话语体系中使用性别歧视化的字眼,挑起性别冲突,进而深化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当IAC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披露了艾尔玛将成为宇航员时,一位男记者向她提问成为宇航员的感受时,并没有使用“astronaut”一词,而是使用了“astronette”[6]235,以强调其女性身份,以及和其他(男)宇航员的区别。1958年7月20日的新闻报道标题为“两名宇航员与一名女宇航员准备登月(TWO ASTRONAUTS AND AN ASTRONETTE PREPARE FOR THE MOON)”[6]294,此标题继续沿用了“astronette”这一生造词,以强调性别区别。另一场记者发布会的提问也充分展现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例如记者刻意提问“为什么你们都想要打败男性登月”[6]243即是故意在制造男女的对立,而实际是女性并非是要和男性对立,正如妮可·瓦尔金所答,“女性想要登月的原因和男性一样,女性可以在太空中做一份有用的工作”[6]243。除了制造性别二元对立之外,对女性传统的刻板印象也体现在媒体的提问中。例如新闻发布会上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你们打算在太空中做什么饭”[6]244。这个问题仍然带有男性沙文主义色彩,因为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女性更多担任了家庭主妇的角色,主要家务之一就是在厨房做饭,因此更多地在空间上与“厨房”有更紧密的联系。而记者有意将“厨房”这一概念强行赋予踏入太空探索的女宇航员,是对其“科学家”或“宇航员”这一中性色彩的职业身份的抹杀,并强调了她们身为“女性”和“主妇”的属性。
19世纪前,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把女性塑造成“天使和妖妇”两个极端,在这种困境背后隐藏的是父权社会背后的性别二元对立思想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压抑[14]292。灾后艾尔玛向帕克上校提出志愿作为飞行员去营救难民时,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这确实不是女人该呆的地方”,而更适合她的是看护工作,因为那是他心目中“对女性来说的一份好工作”[6]38。同时小说中前纳粹火箭专家冯·布朗则把带给纳粹德国“毁灭性”打击的苏联女飞行员们称为“夜间女巫”(Night Witches)[6]185。无论温顺的“家中天使”还是“妖女恶魔”,都是“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14]292在作祟。因此不消解固有的性别二元主义,女性就没有办法找到出路。
三、探寻女性出路
诚然,男性和女性之间存有巨大差异,在STEM领域里做出杰出成就者往往以男性居多。有研究指出,非但两者没有优劣之分,更不能以性别作为STEM领域去留的单一准绳,应该给予男女平等的话语权[11]90。女性在STEM领域能见度低、代表性低的现象成因固然是源于二元化的性别主义倾向,然而想要改善和推动女性在理工科领域的劣势,则需要横跨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寻求方法。因此,要改善这样的状况,既需要女性个体的不懈奋斗,也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高威等学者指出,社会、家庭和自我这三方面是导致女性脱离STEM领域的重要原因[11]91,因此要想冲破女性在STEM领域的困境,也必须从这三方面着手。柯瓦在小说中借助艾尔玛的经历对此进行了大胆探讨和假设。艾尔玛之所以能圆梦太空,除了她对梦想的执着和个人的努力,来自家庭与社会对她的帮助和支持,乃至体制性的改革都不可或缺。
家庭是艾尔玛的启蒙和最坚实的支持来源。作为美国空军将军的女儿,艾尔玛曾回忆自己两岁时就首次随父亲乘坐战斗机飞行,并由父亲亲自教授如何驾驶飞机。因此当问及她成为宇航员的动机时,她表示“不记得有什么时候飞行不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6]219。正是幼年时期父亲对她的飞行启蒙埋下了种子,让她能够在今后种种逆境中也保持这种热切渴望。艾尔玛的哥哥赫希尔与她一同就读大学,当艾尔玛遭到同学欺凌时,他全力予以了支持和保护,因此让艾尔玛能够在充满攻击性的环境中顺利完成学业。婚后,艾尔玛的丈夫纳撒尼尔·约克(Nathaniel York)对她的事业全力支持理解。艾尔玛最初在争取平等权力受挫时,一度想过放弃。虽然她知道无论自己做出什么选择都会得到支持,但想到丈夫一直以自己的成功为骄傲,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如纳撒尼尔对艾尔玛工作的态度:“她喜欢工作,那么我就会努力确保她有她所喜欢的东西。”[6]221也正是纳撒尼尔在克莱蒙兹主任为难艾尔玛时极力维护自己的妻子。同时,他的名字是对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中人物的互文。《火星编年史》中的纳撒尼尔·约克上校首次带领人类登陆火星,在《计算之星》中纳撒尼尔担任的是太空殖民计划的总工程师一职。作为一个幕后角色,同时也是艾尔玛的坚实后盾,纳撒尼尔这个人物寄予了作者的希望,即实现STEM领域性别平权需要男性对女性的理解与支持。
同样,体制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机构组织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也对促进女性在STEM领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一个传统的分层组织机构中,对具体工作的固定性别分工会限制女性的职业流动性[15]4,如同“玻璃笼子”一样成为女性发展的体制化障碍[16]3。因此艾尔玛虽然有理科博士学位,但只能成为计算员,因为IAC安排给女性的只有计算员和秘书这样的辅助性工作,这样边缘化的处境也切断了女性职业成长的路径。而相反,同伴协作关系的组织更利于增加女性的可见性,减少刻板印象[16]6。艾尔玛通过和飞行俱乐部的女飞行员们合作,一同扩大舆论效应,才争取到招收女性宇航员的机会。同样,在一次太空任务中,机械故障让两名远在月球表面的宇航员性命岌岌可危,是艾尔玛凭借优秀的计算能力、对宇航项目全面的掌握以及冷静果断的判断在控制中心化解了危机。通过此事件,克莱蒙兹完全认可了艾尔玛的实力,认识到了计算员在太空任务中的重要性,并且对女性参与航天项目的态度有了巨大转变。他决定改变以往宇航员的方式,让艾尔玛从计算员中大量推选培养新宇航员的候选人进行培养,以更完备地应对复杂危险的航天探索任务。最终,艾尔玛不仅成功参加了1958年7月20日的登月任务,成为一名真正的宇航员,而且间接地改造了IAC遴选宇航员的制度,让更多女性与男性一样能够公平地在项目中竞争。
艾尔玛对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更是建立在社会层面的符号学意义上的成功。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代表人物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女性应该基于对自身特性的认知,发挥对符号象征态的双重作用,使自己发展为一种符号象征态,产生并遵守新发展出的秩序,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对符号象征态的社会,即既定社会中的性别二元论的颠覆作用[17]131,从而赋予符号学“解构父权男女二元对立女权主义的意义”[14]295。艾尔玛在任职计算员期间,多次在少儿科普节目《魔法师先生》中担任嘉宾,重点对航空领域专业知识进行科普,广受全国电视观众好评,并获得了“宇航员女士(Lady Astronaut)”的昵称。她作为“宇航员女士”在电视节目和社会活动中的活跃,不仅赢得大众的青睐,还引发了公众对宇航员遴选的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使得IAC迫于舆论压力和对资金支持的考量,宣布征收女性宇航员。这些努力大幅推动了在航空领域的平权运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艾尔玛通过电视节目超越了“艾尔玛·约克”和“约克夫人”的个体属性,成功把自己符号化为“宇航员女士”和“约克博士”,成为了理工科高知女性的代表。研究指出,男性的自我效能感信息主要依靠过往的成功经历,而女性不同,她们在科学领域中自我效能感信念更多来源于社会信念和间接经历,即得到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支持与对他人成功体验的观察[18]117。艾尔玛通过言行给女孩们树立了榜样,告诉她们女性也可以成为博士、飞行员和宇航员,让众多女孩燃起对理工科的兴趣,让民众对航空领域的了解和兴趣也大为增加。同时她对社会中对女性的既定职业刻板印象和性别分工规则进行了消解,建立起全新的性别分工观念。这些努力终于推动首位女宇航员杰西拉·帕兹-维维罗兹在1957年12月飞入太空,艾尔玛自己也在次年成为第二名飞入太空的女宇航员。
李峰指出,“基于想象的或然历史小说,无论多么天马行空,都只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社会困境所做的历史文化回应”[5]82。《计算之星》既是一段虚构的航空航天业界的女性个人奋斗史,又是对当代理工科领域长期存在的性别主义倾向的影射。小说挖掘出在教育、相关业界乃至社会舆论体系中的性别壁垒的根源,即父权制度下的性别二元主义,以虚构的历史来书写真实的现在,以圆满的过去寄寓对未来的美好愿望。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女性在各个领域中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各自领域中的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多元化的社会里也有更多力量在参与着体制和思想观念上的变革,让女性在各个行业里都发挥出自己的本领。然而,要大幅改善STEM领域乃至全行业中的女性低能见度、低代表性的现状,不仅需要女性自身对现状进行深层的审视,更需要发动整个社会在行为和观念的层面上,以及在校园、职场和社会话语体系中,消解和超越性别二元主义。作者柯瓦把小说的故事舞台放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正是隐喻职场性别平权运动如同《绿野仙踪》的龙卷风,温柔而强大的草原之风不会上把房子撕裂,变革的暴风眼会把女性带入彩虹尽头的新世界,在“或然历史”的黄砖路上找到超越父权二元主义的翡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