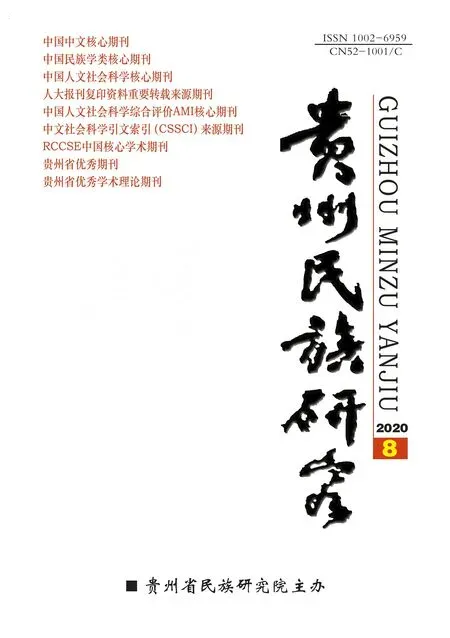清代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交替
——以湘西永顺地区为例
张 凯 成臻铭
(1.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81;2. 吉首大学,湖南·吉首 416000)
标蓝的地方改为:“改土归流”标志着土司制度在土司区的消亡,但是土司制度的残余力却依然影响着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在改土归流地区亦希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以将“国家”的概念灌输到地方社会。这就使得清政府会通过一系列手段在地方扶植新的“国家”代言人,以消除土司制度残余力的影响。如此一来,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就成为了各地方群体迎合国家政策,角逐地方控制权的“战场”,地方控制权也由此在不同群体中发生着交替。本文将通过考证清代改土归流后某一区域具有一定时间维度与延续性的碑刻、族谱等材料,说明改土归流后国家政策在地方社会的推行状况。并以此为基点,重新观察地方社会新崛起的势力是如何通过国家政策一步步取代原有的权力群体,从而成为地方权力新的控制者。
一、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与土目群体的权力冲突与和解
(一) 清政府与土目群体的权力争夺
“土目”是各地土司为了更好地管理庞大的土司基层社会而设立的自署职官。由于土司基层社会的事务随着土司区的发展日益繁杂,所以“土目”群体也逐渐壮大,成为了土司时期仅次于土司群体的第二大群体。清代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诸多土司地区掌握实权的在职土司以及其后代被安插至内地生活。如永顺宣慰司使彭肇槐及其后代就被雍正帝发往江西安插[1]。这一方面使得改土归流后的土司群体彻底失去了他们在当地掌握数百年的地方控制权;另一方面也使得留守在改土归流地区的土目群体有机会继承当地残留的“土司权威”,以此与“国家”进行权力角逐。
在改土归流后的地区,清政府会在当地建立地方政府,派遣流官管理。在内地的基层社会,地方政府依靠乡里制度进行管理。这一制度在内地有着长期的发展过程,至清代已臻于完善[2]。保甲制度是清代乡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而又十分有效的管理乡村社会的制度。所以在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清政府也引入了保甲制度进行管理[3]。
不过,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状况往往十分复杂。以永顺地区为例,新设的永顺地方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忠心的乡里势力帮助自己管理地方社会。这就使得他们只能任用土司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土目群体为保长、里正[4]。地方政府这样布政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其积极的一面是,土目群体在土司时期长期管理基层社会,十分熟悉当地的状况,能够很好地维护地方秩序;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是,土目群体管理地方社会的权力基础是“土司权威”,基层土民将对土司的敬畏转移到了他们身上。这就使得土司时期曾经存在的诸多“积弊”在改土归流之后依然盛行于地方社会[5]。后者显然与清政府设立保甲制度的初衷相矛盾。正因如此,改土归流后的永顺社会成为了以“国家权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和以“土司权威”为基础的土目群体产生强烈碰撞的“战场”,“田尔根事件”由此爆发。“田尔根事件”的结果是,清政府通过“小案重判”的方式将一大批不服地方政府管理的强硬土目分别“以斩、绞、军、流、徒、杖分别发落”[6],“国家权威”在与“地方势力”的交锋中取得了一次大胜。而后,永顺地方官员以“田尔根事件”为由头,开始趁热打铁对当地的保甲制度进行了改革,使之基本与内地无异。同一时间,永顺地方政府还对当地社会所遗存的土司“陋习”进行全盘的清理,基本禁绝了永顺社会的“土司积弊”[7]。
在刚完成改土归流的地方社会,无不上演着这样“国家”与土目群体角逐地方权力的“大戏”。多地的土目群体因为这种权力斗争失去了地方社会的控制权,使得他们需要跳出“土司权威”的影响,与国家建立起新的联系,以避免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 达成和解:土目群体的宗族重建运动——以内塔卧彭氏为例
在土司时期,有不少势力庞大的土司在当地仿照汉人的宗族制度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宗族组织系统。这一系统对内便于加强土司群体的凝聚力,提高土司进行社会管理的行政效率;对外又能将当地话语与“国家”话语进行对接,拉近与“国家”的关系。其中,尤以明代永顺宣慰司使彭氏所建立宗族组织的特点最为鲜明。
从明正德年间到明万历年间,历任永顺宣慰使曾在他们的辖区内仿造内地的宗族组织形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宗族运作模式。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国家的战乱导致永顺地区社会动荡,当地不少建筑遭到严重破坏。顺治四年(1647年) 和顺治八年(1651年),永顺老司城周边连续被逃兵洗劫,永顺彭氏宗祠也在洗劫中付之一炬[5]。虽然之后彭氏土司一直有重修宗祠的意向,但随之而来的苗疆开辟运动和改土归流运动使得他们尚未行动便失去了在当地世代生活的权利。不过,改土归流后被强制迁出永顺地区的仅仅是彭氏的直系子孙,旁系的彭氏仍然在当地生活,他们也是土目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他们面对“土司权威”的影响逐渐在永顺社会消退的状况后,便将重建彭氏宗族组织的行动提上了日程,他们寄希望以这种方式重新获得在当地的控制权。在土司时期,彭氏的直系子孙为了在当地树立权威,采取了积极修谱、建造彭氏祠堂等多种手段[8]。这就给改土归流之后的彭氏旁系提供了重建宗族组织的优秀范本。
改土归流后,内塔卧彭氏是生活在永顺地区最大的彭氏旁系之一,他们也是最早开始对彭氏宗族组织进行重建的群体之一(注:“内塔卧”为永顺地区的传统地名。“塔卧”土家语意为“田螺”,因当地版图形似田螺而得名。“内塔卧”即为田螺地形的内部平地,与“外塔卧”相对。新中国成立后,内、外塔卧合并成塔卧乡,属永顺县地)。他们首先号召当地的彭氏族人“每家照丁多寡,每丁捐钱三百三十□□收齐,以购义田”,并选择了有威望者做族长,主持宗族事务。到了乾隆初年,他们还在族长的主持下,开始定期在祠堂中进行了祭社活动[9]。根据陆群、蒋欢宜的研究,改土归流后永顺内塔卧彭氏祭社活动的过程和礼仪表现基本与汉人宗族无异[10],这就说明了内塔卧彭氏有意模仿了汉人的祭社活动,以强化自己的汉人身份。
另一方面,内塔卧彭氏开始将土司时期所流传下来的《历代稽勋录》进行了续修。《历代稽勋录》在土司时期被彭氏子孙认为是有与汉地族谱一样性质的谱书,但它只记载了彭氏直系一脉的传承,所以更应该被认为是家谱而不是族谱[11]。而内塔卧彭氏在续修《历代稽勋录》时,增添了很多旁系的资料,并加入了更为详细的瓜藤图,完善了谱书结构,使之成为了真正的彭氏族谱,强化了重建后永顺地区彭氏宗族的凝聚力。此外,执笔的彭氏子孙极其认同该书上所述的彭氏为江西汉人后裔的说法,并在之后各代《彭氏族谱》的新修过程中,均将“江西迁来说”写入了谱中,以强调自身汉人身份的真实性[11]。
在彭氏族学的重建上,内塔卧彭氏也费尽了心思。由于在改土归流之后,彭氏土司所修建的族学——若云书院被永顺地方政府征用改为了永顺府学,彭氏子孙便在内塔卧重新修建了一所新的学校以充当彭氏的族学[9]。在该族学外,竖立着一块卧碑,该碑上写道:
吾等既为圣世汉民,即当躬圣人至教用,是捐钱粮建立儒学。延师彭义才等,教以诗书,多刷圣谕广训,分布任领,令馆师,日则教子弟在馆熟读,夜则令子弟在家温习。庶几子弟之父兄辈,亦得闻作孝之大端,立行事之根本。久久习惯,人心正,风俗厚,而礼义可兴矣[9]。
在此碑文中,永顺彭氏自认为是“汉民”,并通过日夜诵读儒家经典这一手段,使得整个彭氏宗族的内部成员耳濡目染儒家文化。这一行为体现了当地彭氏极力维护自己汉人身份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彭氏族人日夜诵读的经典之一是《圣谕广训》,该典籍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传统的儒家经典,而是雍正二年(1724年) 国家所颁行的,以康熙皇帝教导臣民行为准则的《圣谕十六条》为蓝本的官修典籍。当时的清政府不但在内地儒学广推这一典籍,还将其列入了科举必考书目之中。内塔卧彭氏显然明白《圣谕十六条》在当时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十分重视这一典籍在彭氏宗族内部的普及,以体现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认同。
乾隆年间,时任永顺知府李拔在亲自考察内塔卧彭氏族学之时,即兴为彭氏族人题写了千余言的《劝学箴》。文中的内容充满了对彭氏兴办族学的赞美,但也严格要求学生忠君、尊孔,接受儒教伦理。最为重要的是,该文反复强调学生不得妄议国政和校务,更不准离经叛道,发表狂言怪论[5]。可见,当时的永顺地方官员一方面对彭氏兴办族学主动重建与“国家”关系表示肯定;一方面又提醒永顺彭氏应加强儒学教育,主动培养他们后代忠君爱国的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杜绝他们作乱的可能,以长久维护当地的社会安定。
内塔卧彭氏的宗族重建行为在永顺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彭氏宗族的势力由此在当地迅速蔓延开来。直到现在,永顺县的塔卧镇有些老人在描述当地大族的时候还说道“彭两千,吼一吼,塔卧抖三抖;向五百,跳一跳,房瓦要震掉。”[12]其意思是当地以彭、向两姓为大族,其中彭氏势力最大,族人有两千之多,可见内塔卧彭氏在当时发展规模之大。并且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内塔卧彭氏族人重修的族谱来看,他们的宗族建构已十分完备,从底层逐步叠加,形成了“个人—独立家庭—联合家庭—小支—大支—各房—宗族”的严密等级结构[9],这些特点均与汉人宗族组织基本无异。
最为重要的是,永顺彭氏至此在自身与国家之间再次构建起了新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以“土司权威”为基础,而是以宗族组织为基础。这展现了永顺彭氏对汉人文化的“向化”之心。更进一步的是,这种“向化”行为使得土目群体的身份开始发生了转变,他们由“土司权威”的继承者逐渐变为“国家”主流文化的传播者,就此缓解了他们与“国家”紧张的关系,得以继续把持着永顺社会的地方权力。
总而言之,在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地方势力在经历了与“国家”的抗衡后,急需重新与国家建立起联系,借此延续自身在地方社会的权力与利益。一般而言,这种新的联系应是一种基于汉文化的行为模式,这就使得宗族重建运动在地方社会发展起来。不过,各地方社会和解行为也并不是都以宗族重建为手段。如广西浔州府的地方势力在改土归流后就是运用将地方神国家化的方式与国家建立起新的文化联系,并借此成为了国家在地方上的文化代言人[13]。虽然手段各不相同,但是地方势力的目的均是以文化互动的方式与国家达成和解。这样的行为,有利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构。
二、改土归流后土籍士绅群体对地方控制权的掌握
通过宗族重建,土目群体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进行了重建。但是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土地,仍然牢牢掌握在土目群体手中,这让清政府又开始着手改革地方社会的土地政策,以期收回地方社会土地资源的控制权与分配权。
以永顺地区为例,雍正八年(1730年) 三月,雍正皇帝正式下令在永顺府进行土地重勘运动,规定“将永顺一府秋粮豁免一年,令有产之家自行开报,准其永远为业”[3]。这一条令展现了清政府强力打击被土目群体私占土地行为的决心,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次土地重勘不仅使得永顺土民逐渐摆脱了与土目群体的人身依附关系,还使得他们开始通过赋役制度与“国家”建立起直接联系,“国家”的概念就此进入永顺土民的经济生活之中[7]。清政府对永顺土民“额以赋税”之后,也相应地使他们获得了科举的权利。
其实,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 清政府就规定,永顺地区凡是编户纳税之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15]。但是,由于此时的土地重勘才刚刚起步,所以永顺土民几乎没有自主的耕地,科举权利牢牢掌握在土目群体手中。到了土地重勘完成之后,绝大多数的永顺土民获得了土地,开始向国家承担赋税义务,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能够与土目群体一同进行科举考试。
不过,土目群体在土司时期就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本身就有一定的儒学积淀[16],所以在应付以儒学为宗的科举考试时,他们较一般土民获取功名的机会就更大。尤其在土目群体对宗族系统进行重建后,宗族内部的族学体制较之前更为完善,而底层土民只是初识儒教,土目群体的族人与土民们一起科举应试,无疑是土目族人中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虽然永顺地方政府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在当地确立科举制度后开始兴修府学、义学和书院,并就近设置考棚,加大科举制度的普及程度[14]。但是永顺地方政府的行政预算实在拮据,并不像内地州县一样能给在校的儒生发放足够的廪食,这使得很多穷苦的土民根本不可能让自己的子弟在政府所办的学校内读书,从而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永顺府的官学入学率十分之低[5]。反观土目群体,不但拥有自己的族学,还为族学配置了一定的学田,这样每年学田的收入能给族人子弟创造优良的学习条件,这就让他们在当地的科举考试中仍然极具竞争力。以内塔卧彭氏为例,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 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 间,彭氏科甲出身的族人有秀才21人,举人9人,进士3 人,成绩十分不错[9]。
如此一来,土目群体的族人因为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为了报答宗族对自己学业的支持,往往会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继续支持宗族的发展。这使得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宗族势力日益壮大。而有功名的族人们由于所在宗族势力的扩大,也随之在永顺地区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土籍士绅群体由此在当地形成。正如乾隆初年永顺知县李瑾对当地土籍士绅群体的赞美之言:“服勤力穑以供赋税;诵诗读书以为国华。”[15]这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对他们的肯定。
从土地改革到“纳粮当差”再到获取科举资格,当地大姓族人最终通过科举制度获取新的士绅身份,如此的发展模式普遍存在于改土归流之后的地方社会之中。如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土目群体在改土归流之后就因为当地土地所有权的变更,科举文教的兴起而开始发生了变动。当地黄氏宗族的崛起开始强烈冲击当地原有的势力格局,并与中央王朝建立了新的联系[16]。由此可见,虽然地方势力的主体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他们通过对国家新政策的解读和迎合,开启了与国家新的、友好的互动模式,并使得自身身份发生了较大转变。
三、客籍士绅群体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争夺
(一) 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的移民概况
在乾隆时期,我国人口数量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之下,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成为了内地人口最好的移民目标,也成为了他们进行土地开荒、商贸活动以及兴办文教的最好对象。以永顺地区为例。根据史料记载,永顺府从乾隆初到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 新增人口21 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17]。
永顺社会短时间内会有如此庞大移民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土地重勘后,清政府对永顺社会的土民进行了重新土地划分和编户,使得当地的民政制度与内地趋同。这也使得土司时期“蛮地”与“汉地”的划分失去了依据。土司时期“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口号就此成为了空谈[18]。再加上土司区原籍土民数量十分稀少,这就使得当地在重新划拨土地所有权后出现了大量的荒山荒地无人认领。所以,当地官府在改土归流后便提出了“任民自由占田”的政策[19],以借此发展当地较为落后的农业。这一政策的执行必然导致内地大量无田之人涌入永顺地区进行开垦荒地的占地行为,也为永顺社会带来了第一批大规模的移民。
其二是商贸利益的驱使。如改土归流后龙山县的移民“多长、衡、常、辰各府及江西、贵州各省者。其先服贾而来,或独身持幞被入境”[20]。而在永顺县,其迁入的客民“在他省则江西为多,而湖北次之,福建、浙江又次之。在本省则沅陵为多,而芷江次之,常德、宝庆又次之”[21]。可见当时永顺地区因为商机而趋于此的移民之多。
除了开山占田与商贸利益的驱动,当地移民潮的第三大动因在于土民参加科举考试的优惠政策。永顺地区施行科举制度后,当地政府考虑到土民文教水平较低,便规定当地科举中第的名额按“土三客一”划定,以示公平[14]。这本可使得土籍考生科举中第的机会大大高于客籍考生,但是一大批汉人看到了政策的漏洞,开始蜂拥至永顺地区占地或者买地入籍,“争冒考嗣”。这就使得清政府“科举公平”的愿望落空,还使得当地低廉的土地价格飞升。如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永顺知府骆为香就因为汉人在当地乱抬田价,导致“田土价较前昂贵已不啻倍蓰”而下令“禁汉人买土地”[22]。针对这些负面效果,清政府紧急出台了“在前朝入籍为土,在本朝入籍为客”[23]的规定,以期彻底杜绝这种“喧宾夺主”的科举乱象,但是此时永顺地区的科举移民已有一定的规模。
正是以上三个动因,使得永顺地区吸纳了大量的移民,成为了当地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永顺地区的社会事务,逐渐在永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主角。
(二) 反客为主:客籍移民身份的转变——以龙山县黄氏宗族为例
在改土归流后,虽然土目群体与地方政府发生过不小的权力冲突,但凭借着自身的调试,使得他们仍然能够以新的“土籍士绅”的身份继续掌握着地方控制权。如在永顺府的龙山县地区,当地乾隆年间建造、修缮公共设施的表彰行文中,均有彭姓、向姓、田姓等人员慷慨的捐赠行为,批准立碑者也多为历任龙山知县[23],可见当地政府对他们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行为的高度肯定。在土司时期,龙山县境内的彭姓、向姓和田姓便是颇有势力的土目大姓[24]。改土归流之后,龙山县地的彭、向、田这三大姓氏的后人开始通过配合地方政府做慈善事务重新确立了在当地的权威。更进一步的是,他们以这种方式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在地方官员心目中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与国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但是,随着当地移民的不断增多,客民凭借着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积累了雄厚的经济财富。在物质生活不断充实的同时,客民们开始迫切地期望参与当地社会事务并有效地掌握地方权力。仍以龙山县为例,道光至同治年间该地区公共设施的建造、修缮行为无一例外由黄姓一族的“善士”出资完成[25]。可见,在清末的龙山县地,黄氏宗族已经替代土籍的大姓宗族,在当地士绅群体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龙山黄氏的始迁祖为黄鸿祀,于乾隆年间由省城长沙举家迁往龙山开荒和经商,是当地改土归流后较早的移民之一。与当地其他客民一样,黄鸿祀很快因为开拓荒地和商贸活动拥有了大量的财富。暴富之后,黄鸿祀开始有意识地参与龙山当地的社会活动,以凸显自己之于当地社会的重要性。如嘉庆初年,龙山县爆发白莲教起义,黄鸿祀自掏腰包“募乡勇,捍卫城池”,为打退“教匪”立下很大的功勋。除此之外,黄鸿祀还在思想品质上树立了道德的标杆。他“年未及壮”便丧偶成单,却“鳏居五十余”,终身未再娶。声称“吾虽能给饘粥,固未忘搀菜作饭人也”。黄鸿祀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在他去世后,因为生前的义举和德行,被当地官府“请祀乡贤”,黄氏家族在当地的地位逐渐发生了改变[26]。
而让龙山黄氏开始获得当地控制权的关键事件是黄鸿祀之孙黄大镇的科举中第。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黄大镇通过科举考试中得进士,任职柳州通判,此为龙山黄氏入仕之首[27]。黄大镇任官后,龙山黄氏随之由富及贵。黄大镇的祖父黄鸿祀和父亲黄之翰由此得封奉直大夫,其长兄黄大钟得封承德郎[27]。黄氏家族能够集体封官加爵除了黄大镇的科举功勋之外,还在于之前黄鸿祀的所作所为为黄氏家族在当地奠定的民间威望。由此,清政府才会以黄大镇进士及第为契机,给予了黄氏家族丰厚的赏赐,以期树立一个能够忠于“国家”的地方势力。果不其然,得到封赏后的龙山黄氏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的处理,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得力助手[28]。到了嘉庆年间,“历三世,丁渐繁”的黄氏家族看到时机成熟,便将修建黄氏宗祠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黄鸿祀病逝后,其长子黄之翰成为了家中决策人。他从两方面认定修建黄氏宗祠的重要性:其一是龙山黄氏每次长途跋涉回长沙祭祖十分麻烦,费时费力;另一方面又认为要在龙山县更加突出黄氏家族的影响力,应在当地修建新的黄氏祠堂,即可遥敬“远溯所自出之祖”,又可供奉“始迁之祖”,还可团聚永顺府的黄氏族人,以发展成当地的大姓宗族[29]。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黄氏宗祠在黄之翰的主持下在龙山县修建完毕[29]。黄氏宗祠的修建,一则标志着移民而至的黄氏家族就此发展为龙山黄氏宗族;二则预示着客民身份的黄氏家族开始朝着地方士绅的身份发生转变。到了道光年间,龙山黄氏宗族已发展为当地最大的宗族之一,黄氏族人也由此能够通过科举制度不断获取功名,光耀门楣,充实着黄氏宗族在当地的权力基础[30]。
与当地土籍宗族势力不同的是,客籍宗族势力与“国家”是直接通过科举制度建立的关系,这也让地方政府更能够接受他们的崛起与壮大。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三月,黄之翰三子黄大钺以举人身份邀请前龙山县令徐瑃撰写《中南黄氏宗祠记》,徐瑃欣然挥笔成帖,并将此碑刻立于龙山黄氏宗祠正门侧[30],以示地方政府对黄氏宗族的肯定。光绪三年(1877年),龙山地方政府开始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 《龙山县志》的基础上编纂新的县志。新版县志与旧版县志相比,只有两处不同。其一是续写了近六十年来的大事记;其二就是编者在新版县志的“人物传”和“贤妇传”两条目下,花了很大篇幅补入了黄氏族人的社会功绩以及他们夫人的忠贞事迹[31]。以上事实均表明,经过数年的经营,黄氏宗族在龙山地方官员的心目中已成为地方领袖和道德楷模,是当地“国家权威”的代言人之一。此时的龙山黄氏宗族的身份已完全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只富不贵的客籍移民群体,而是在当地有着绝对权威的士绅群体。龙山黄氏宗族就此成为了当地社会控制权的掌握者之一。
四、两大士绅群体的“冲突”与“制衡”——以龙山县为例
在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虽然控制权在土籍士绅群体和客籍士绅群体中进行着交替,但是地方政府不会一味地任凭一方势力无限坐大,以酿成尾大不掉之害。所以在两大势力的权力“冲突”中,地方政府往往扮演着“制衡者”的角色,以维持当地社会权力分配的合理性。
以龙山地区为例。在清道光年间以后,当地并非黄氏一枝独秀,仍有其他颇具影响的土籍宗族势力,如向氏宗族。改土归流后的龙山向氏宗族继承了祖上在土司时期所积累的丰厚田产,十分富有。改土归流后,他们的族人又通过科举制度获取了功名,重新建立了与国家的联系[32]。但是,向氏宗族所积累的财富数量以及获取科举功名的族人数并不及黄氏,所以在当地的影响力只能屈于黄氏宗族之后。
不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绝不允许某一宗族势力在区域社会一枝独秀,即使这一势力较土籍宗族群体更加便于驾驭。地方政府深知,过于强大而又没有制约的宗族势力极有可能发展成与他们对抗的地方权力,极不利于“国家”的概念在当地的推行。所以说,当黄氏宗族势力过于强大时,地方官员便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有意地进行制约。
道光五年(1825年),龙山黄氏宗族黄大钟(黄之翰长子) 被人告官。诉状指出,身为保约的黄大钟伙同其他地方小吏在采买塘汛兵丁的军粮时,“藉公滋扰,滥派里夫,大为民累”。面对这一“莫须有”的控告,时任永顺知府吴传绮在只有口供的情况下认定黄大钟等人罪名成立。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吴传绮并未对黄大钟等人进行严厉的惩罚,而只是对这种行为“禁革在案”[33]。可见,当地官员也并不认为有真凭实据可以处理黄大钟等人,只是寻求通过这一事件对黄氏家族进行打压。
这一诉讼所引发的另一事件是,龙山向氏宗族提出将此次诉讼的前因后果刻碑立于县邑之中,明示于龙山县民。向氏宗族的提议明显是对黄氏宗族窘境的落井下石,但是竟然很快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批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十一月,就在《中南黄氏宗祠记》碑于黄氏宗祠前竖立的八个月之后,《龙山插堤采买兵谷及重修神庙柱碑》也于龙山卸甲祖神庙门前落成。该碑由时任永顺知府黄宅中颁示,向氏族人出资兴修[34]。“卸甲祖神庙”为乾隆时期土司后人彭氏所出资修建,供奉历代彭氏土司,每逢三月十五,便有土目后人聚集于此进行庆典[34]。随后,由于清政府有意消除“土司权威”的影响,该神庙逐渐荒废。而借由此次立碑事件,该神庙被向氏族人出资重修,这一行为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龙山插堤采买兵谷及重修神庙柱碑》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构成,其一是龙山县所承担兵粮的具体额数,其二是黄大钟等人“滥派”案件的前因后果,其三是亦有对历代永顺彭氏土司的歌功颂德之言[33]。可见无论哪一部分的内容,都标示着永顺政府对黄氏宗族的故意打压和对向氏宗族的有意扶持。
根据永顺地区相关地方志、碑刻以及族谱等材料的记载,除了龙山县,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土、客宗族相争的事件。而在这些事件中,地方政府一般都会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他们会根据当时的地方局势,有意地偏袒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以借此使得诸多地方势力的权力分配达到平衡,从而有利于“国家”概念在地方社会渗透。
五、结语
研究改土归流后的永顺社会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拥有地方控制权的主体势力是不断变动的。不同的群体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能够借助国家不同的制度与政策,通过文化、经济、政治等手段来塑造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以达到掌控区域社会的目的。其实,从永顺社会内部权力交替现象可以窥见出西南地区在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所呈现出的变迁样态。改土归流后的土目群体,以及中晚清时期的土、客士绅群体,其身份属性大相径庭。但是仔细研究,又能发现他们的联系。土目群体在土司时期是土司群体的附庸。改土归流后,土司群体被清政府强制迁往内地,土目群体由此接替土司群体把控了地方权力。但是土司群体继任者的身份显然不会被“国家”所接受,清政府便开始出台一系列制度与政策致力于消除“土司权威”在当地的影响。如此一来,土目群体开始通过自身的努力转变身份,希望与“国家”重新建立联系,继续把持地方权力。其结果是,土目群体转变为了清政府可以接受的土籍“士绅群体”。另一方面,在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的移民逐渐增多,“占田”和“通商”使得客民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也使得他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参与地方事务的机会。而“士绅群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使得他们能够以经济资本、科举制度等要素转变身份。最终,晚清地方社会发展为了由多个土、客籍的“士绅群体”分享地方权力的区域社会。而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在诸多大姓宗族之间起到了调和关系、平衡权力的作用,地方社会由此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