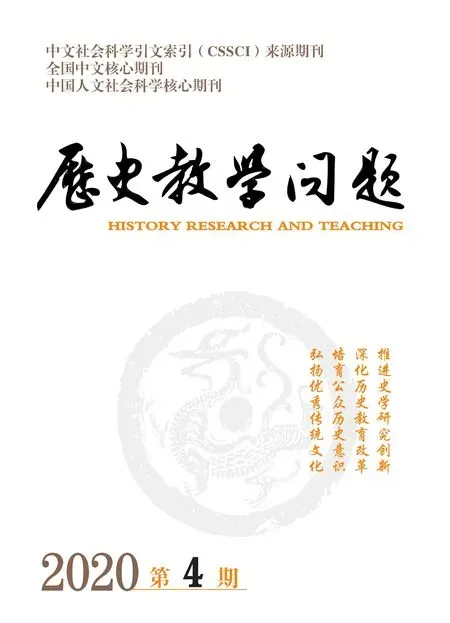布瓦索纳德与牡丹社事件
刘 丹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加速“脱亚入欧”,提升国际地位,推进了多项海外计划。除派遣岩仓使节团赴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促成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外,还策划实施了令东亚华夷秩序逐步解体的“牡丹社事件”。①1871 年10 月,66 名琉球人遇海难后,误入台湾东部生蕃地界,54 人惨遭当地土人杀害。1874 年5 月,西乡从道无视日本政府命令,以“保民”名义率兵登陆台湾岛,向牡丹社等蕃民复仇,引发了近代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外交争端——“牡丹社事件”(又称“台湾出兵”)。日本的侵台行为不仅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抗议,连英、美等西方国家也表示反对。一意孤行的西乡从道在达成“复仇”目的后,又继续在生蕃地区勘察地形、修筑道路、建造房屋,拖宕推诿拒绝撤兵。与此同时,中日围绕琉球人是否为日本属民、台湾生蕃地区是否为“无主之地”等关键问题持论不决。为化解外交僵局,大久保利通亲赴北京与总理衙门展开激辩,在此过程中,担任其随行法律顾问的布瓦索纳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智囊作用。②布瓦索纳德(Gustave émile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法国人,毕业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1852 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专业为民法,曾获得大学颁发的最具价值金牌。
近年来,关注“牡丹社事件”的学者逐渐增多,围绕事件的历史定位、日本出兵的真实目的、中日谈判的过程、生蕃杀人的原因和动机等,做了一些研究。③关于“牡丹社事件”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 纐纈厚:《台湾出兵の位置と帝国日本の成立》,《植民地文化研究》(东京)2005 年第4 期;2.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 期;3.李祖基:《“牡丹社”事件——1874 年日本出兵侵台始末》,《台湾历史研究》2015 年;4.高加馨:《从Sinvaudjan 看牡丹社事件(上、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纪要》(冲绳)总第72、73 期,2008 年。主要观点包括:1.“牡丹社事件”是日本近代海外军事扩张的第一步,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远因,具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特征。2.日本使用“障眼法”,在谈判中表面上质疑台湾所属,实际上是觊觎琉球主权。3.台湾原住民被动卷入近代国家关系,其族群文化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应构建历史话语权为自己正名。这些研究从事件主体(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台湾原住民)角度切入的较多,而从第三方视角出发的甚少。本文以《布瓦索纳德台湾事务建议书》(Consultations de M.G.Boissonade sur les Affaires de Formose)为基础史料,④《布瓦索纳德台湾事务建议书》成书于1874 年,共两卷,由布瓦索纳德以法语撰写,主要记载了其跟随大久保利通赴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的活动内容,内含19 份谈判建议书,现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本馆内。从法国法律学者布瓦索纳德对中日分歧的解释、对谈判走向的引导以及对和解条约的建言三个维度,探究其在协助解决中日纠纷过程中所持的基本态度和发挥的主要作用。
一、布瓦索纳德对中日分歧的解释
在大久保利通之前,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曾与总理衙门进行过交涉。日本主张琉球早已成为萨摩藩之附属,琉球人为日本属民,为保护属民发兵理所应当;依万国公法,台湾生蕃地区应属“孤立化外之地”,日军登陆此地并未侵犯中国利益;生蕃地区之所以被视为“无主”,关键在于中国未对该地进行实效管辖。与此相反,清政府认为琉球为中国朝贡国,其人被害与日本无关;万国公法是西方之法,不适用于东方;清政府已在台湾设置台湾府,全岛均属中国领地,这是不争的事实。布瓦索纳德作为日方雇员,给出了符合日本利益的解释。
(一)日本出兵何以属正当行为
布瓦索纳德根据萨摩藩对琉球长达200 多年的实际控制和琉球向日本朝贡的事实,给出三点建议:第一,琉球向中国朝贡的同时也向日本朝贡,即使琉球不能被视为日本不可缺少之领土,至少还有一种直接的依赖关系。琉球藩王每年都向日本朝贡,反过来日本对琉球人应负有保护义务。第二,虽琉球也向中国朝贡,可中国并未尽到保护义务,而日本作为真正的保护者完全具备自行出兵的资格。第三,琉球人遭杀后,选择了向日本求救,并未向中国求援,这也是日本出兵的正当理由。①参见大久保泰甫:《ボワソナードと国際法—台湾出兵事件の透視図》,東京:岩波書店,2016 年,第240 页。
笔者认为,日本出兵是否正当,取决于琉球与中日两国到底有何关联,特别是日琉之间是否存在公法意义上的从属或依附关系。中琉之间的封贡关系确立于明朝,发展于清朝。琉球之所以向中国朝贡,既有作为弱国“欲借天威以壮其国”的安全考量,也有以封贡贸易获取巨额利润的经济目的。然而,日琉关系的发端却与此有着明显不同。1609 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俘虏了尚宁王,并割占琉球五地(大岛、喜界岛、德岛、冲永良部岛和与论岛),岛津家以武力控制了琉球。琉球的历史由此进入“两属时期”,一方面继续坚持作为封贡体制下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另一方面被强行纳入近世日本幕藩体制,成为萨摩藩的“家臣”。②徐勇、汤重南主编:《琉球史论》,中华书局,2016 年,第107—108 页。1872 年9 月,完成了废藩置县的明治政府在琉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一等官),列入日本华族,将“琉球国”强行改为“琉球藩”,进而又从财政、税收、人事和外交上实行了所谓的“内治化”政策。不难看出,琉球对中国的依附是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作出的自愿选择,非但未受到任何外力压迫,还获得了远超所贡方物价值的“实惠”。琉球对日本的屈服,则先后经历了萨摩藩和明治政府的武力威吓,既被迫朝贡,又要俯首称臣。
事实上,琉球此前未因任何公法意义上的“协约”成为日本的附庸,“琉球国”被降为“琉球藩”,也只不过是迫于日本强势的无奈之举。正因如此,布瓦索纳德才未认定琉球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只是强调了日琉之间的朝贡关系。换言之,在他的公法概念中,日本出兵的目的只能是道义上的“礼尚往来”,谈不上“保国”或“保民”。此外,《万国公法》中载:“进贡之国并藩邦,公法就其所存主权多寡,而定其自主之分。即如欧罗巴滨海诸国,前进贡于巴巴里时,于其自立、自主之权并无所碍。七百年来,那不勒斯王尚有屏藩罗马教皇之名,……然不因其屏藩罗马,遂谓非自立自主之国也。”③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20 页。这里的“自立”和“自主”,既指被朝贡国不能对朝贡国加以干涉和侵犯,也包含朝贡国与他国之事应由其独立解决。琉球人遭害是琉球本国之事,琉球是否真的求助日本为其复仇尚不可断,即便如此,如何处理也应凭其自主,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无权妄加干预。更何况,中方由始至终都不知生蕃杀害琉球人一事,根本无从下手。正如总理衙门在照会中所言:“贵国外务省文书……未提及受害,地方官即无可办理。”④《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39 页,第230 页。
(二)生蕃地区何以为无主之地
以文祥为代表的总理衙门大臣对日本以万国公法为依据讨论中日纠纷,一直相当抵触,因为它不符合东亚地区长久以来遵循的“华夷秩序”。在第三次谈判中,当大久保利通再次要求中方用公法证明中国对生蕃的治理之实时,文祥明确重申“万国公法为近来西洋国家编成,未载我国之事,固不可用于辩论,而应以正理商谈”,⑤《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39 页,第230 页。坚决拒绝承认公法的普遍适用性。然而,布瓦索纳德解释称:“欧美之国际法并非法典,而是包括理性和正义在内的自然性原则的集合,只不过是在成文法规出现以前,用来约束国家间关系的自然规则,中国不会不知。战争中,西方诸国都会承认自然法的规范和原则,如果交战国违反这一法则,就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责难。公法是西方国家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的经验成果,也可为东方国家(Orient)所用。”①《布瓦索纳德台湾事务建议书》上卷,1874 年,处番书类档案2A-033-06-545,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第44 页。布瓦索纳德还特别指出,清政府曾翻译过瓦泰尔(Emer de Vattel)著的《各国律例》和惠顿(Henry Wheaton)著的《万国公法》,以证明中国对万国公法早有研究,两国可以公法为基础进行交涉。为此,他还专门整理了法国、英国、德国等国际法学者的有关学说,形成《公法汇抄》:
发得耳氏(法兰西国人)曰:一国新占旷地,非实力占有,即就其地建设馆司而获实益,公法不认其主权。
麻尔丹氏(英吉利国人)曰:占有者,须有占有之实。又曰:一国徒宣告占有意向者,不足以为占有。虽寻觅一岛,固属创获,非有实力掌管之迹,不足以为占有。
叶非德耳氏(独逸国人)曰:凡有掌管地土之意向者,必要继以实力占有,又证以永远制治之措置。
貌龙西利氏(独逸国人)曰:凡称占有者,寻觅新域,已有占据之意向,而施以实政之谓也。又曰:各国得有权兼并无人之境及蛮夷之地者,必由开疆辟土,教化其民,创造其政。凡国之主权,非施于实地,则无得焉。又曰:……若一国广略蛮土,自称执主权,而其实不能开拓管理者,已非生聚之谊,而又阻他国使不得开其地也。凡非有实力永久施行者,不得正真占有之权。若初占后遗,或止虚张表识,谓之惟假其权可也。故一国虽有掌管邦土之名而无其实者,他国取之,不为犯公法。②《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45 页,第225 页,第228—229 页,第235 页,第235页。
很显然,布瓦索纳德有针对性地摘录了诸如“实力占有”“占有之实”“实力掌管”“施以实政”等内容,着重强调“实效管辖”(占其地、理其政、征其税)才是“某国领有某地”的必要条件。若某国仅声称占有某地,而未进行实际管理,则可视其为“无主之地”。事实上,“无主之地”原本指“无人居住之地”。19 世纪以后,西方国家为使占领行为合理化,有意曲解了无主之地的概念,近代万国公法更是将其解释为“虽有人居住,但所属尚不明确之地”。③参见井上清:《新版「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東京:第三書館,2012 年,第52—53 页。这样一来,诸如台湾生蕃这样原本由土人自居自管的地区,其所属权就有了可以被重新讨论的可能。
大久保利通在第一次谈判中就开门见山质问总理衙门:“贵国既以生蕃之地谓为在版图内,然则何以迄今未曾开化蕃民?夫谓一国版图之地,不得不由其主设官化导,不识贵国于该生蕃,果施几许政教乎?”④《日本 外交文 書》第 七巻,東京:日本国 際協会,1939 年,第245 页,第225 页,第228—229 页,第235 页,第235页。看得出,大久保利通意在确认清政府对生蕃地方和当地土人到底采取过哪些具体管理措施。第二次谈判中,总理衙门回复称:“查台湾生蕃地方,中国宜其风俗,听其生聚,其力能输饷者,则岁纳社饷,其质较秀良者,则遴入社学,即宽大之政,以寓教养之意,各归就近厅州县分辖,并非不设官也。特中国政教由渐而施,毫无勉强急遽之心。”⑤《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45 页,第225 页,第228—229 页,第235 页,第235页。首先,关于“宜其风俗,听其生聚”。布瓦索纳德认为,“风俗”毕竟不同与“法律”,对一处地方无碍于纲纪的风俗,可以不加干涉,这正体现了管理者施政之宽仁。但若涉及到惩凶诉讼,就要依靠国家的法律。风俗为“私”,而法律为“公”,两者属性有着根本的区别。法律的实行是属地的重要特征,若清政府对生蕃未施加有效惩治,就不能证明法律效力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生蕃地区并不属于中国。其次,关于“其力能输饷者,则岁纳社饷”。布瓦索纳德认为,“天下无有教而不化之民,其教养土蕃之法,行于实际者,果有多少,何其狼心久而不化耶?”⑥《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45 页,第225 页,第228—229 页,第235 页,第235页。若清政府对生蕃进行过教化,就不应该发生肆意杀人的恶劣行为。此外,若受教化规模太小,人数过少或辐射面不够广,也不能证明进行过有效管理。再次,关于“各归就近厅州县分辖,并非不设官也”。布瓦索纳德认为,“今之府县遥为分辖者,果足以理讼狱制凶残也与?……今使遥辖人跡不到之地,尚得谓之设官之实乎?”⑦《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45 页,第225 页,第228—229 页,第235 页,第235页。从官衙的所设位置来看,应采取就近原则,便于对居民的管理。反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就等于没有管辖之实。最后,关于“中国政教由渐而施,毫无勉强急遽之心”。布瓦索纳德认为,“凡征服邦土名之为义者,必须继以政教,……政教由渐而施者,其开导必有端可见,今台湾建设府县以来……山内山后之民,未见开导之端”。①《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35 页,第247 页,第247 页,第240、308 页。自台湾府设立(1684 年),清政府就应在台湾全岛普及法令,虽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应拖延200 年之久。面对日方的咄咄逼人和出言不逊,文祥虽甚为不悦,但也只能以“各国所属邦土,不得以臆度之词任意猜疑,各国政教禁令亦不得以旁观意有不足径相诘难”勉强驳之。②《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35 页,第247 页,第247 页,第240、308 页。
辩论一开局,清政府就被拉入公法的讨论范围。布瓦索纳德发挥其法律专家的优势,针对总理衙门答复中的“漏洞”,接连抛出令人难以招架的“公法之问”,致使文祥最后不得不发出“夫台湾地方,本属中国不待辩谕,久为中外所共知”,③《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35 页,第247 页,第247 页,第240、308 页。这看似强硬实则无奈的愤懑。布瓦索纳德无视“华夷秩序”在维系东亚国家关系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将西方公法生搬硬套在东方国家身上,自然也没有考虑到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以不治治之论”和适用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实效管辖领有论”二者之间的区别。④参见張啓雄:《〈以不治治之論〉対〈実効管轄領有論〉:1874 年北京交渉会議から見た日中間国際秩序原理の衝突》,《社会システム研究》(東京)第32 巻,2016 年3 月,第127—173 页。这也正是文祥等清朝大臣拒绝遵循公法的根本原因。
二、布瓦索纳德对谈判走向的引导
中日谈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节点:一是谈判之初中国“华夷观”和日本“公法观”的针锋相对,二是谈判期间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主动调停,三是谈判破局后大久保利通企图对清宣战。布瓦索纳德从理性和人道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了以“赔款”换“撤兵”、以“调节”代“仲裁”和以“止战”替“开战”的建议。
(一)以“赔款”换“撤兵”
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后不久,针对中日僵持不下,布瓦索纳德和李仙得⑤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美国人,1872 年受雇于日本政府,曾协助副岛种臣策划出兵台湾计划,是主战派代表人物。联合提出了四个与清交涉的备选方案:“一是日本继续对台湾生蕃地区进行军事占领;二是日本从清政府获得赔偿后撤兵;三是中日两国承认台湾独立,生蕃地区由日本保护;四是确保生蕃地区中立,由中日两国共同保护。”⑥大久保泰甫:《ボワソナードと国際法—台湾出兵事件の透視図》,東京:岩波書店,2016 年,第201 页。要如何选择,取决于当时的形势。首先,西乡从道率兵登岛已成事实,虽“仇”已报,但所耗人力和财力无人补偿,让生蕃土人承担显然不现实。要么让清政府承认生蕃地区非中国领地,将其作为“战利品”据为己有,要么承认生蕃地区是中国领地,进而向清政府索求赔款。其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台湾全岛皆属中国。对此,英国公使威妥玛曾有过两次明确表态。⑦《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235 页,第247 页,第247 页,第240、308 页。若日本选择诉诸武力,势必损害西方国家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商贸利益,不仅会招致各国联合干涉,还将毁坏日本的国际声誉。再次,日本国内此时正推行“殖产兴业”,发动战争会导致财政困难,强国计划将受到影响。最后,台湾夏季天气炎热,流行病泛滥,岛上日军死伤众多,战斗力已大为削减,恐难以应付大规模战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布瓦索纳德认为“主和避战”的第二个方案既能维护日本的国际尊严又能保障国家利益,是首选之计。
(二)以“调节”代“仲裁”
大久保利通与总理衙门交涉期间,威妥玛向日本提出可参考“阿拉巴马号索赔案”,⑧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虽正式声明中立,却暗中为美利坚邦联联盟国(南军)制造了一艘巡洋舰“阿拉巴马号”。联盟国用它攻击摧毁了68 艘联邦合众国(北军)的船只。1863 年10 月,美驻英大使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提出抗议,要求英国赔偿一切损失,并表示愿将此案交付国际仲裁。1871 年,由美、英、瑞士、意大利、巴西等多方代表在日内瓦组成委员会进行裁决,最终签订“华盛顿条约”(Treaty of Washington),英国正式向美国道歉,并赔偿美国1550 万美元。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中日问题。对此,布瓦索纳德坚决反对。他表示,若中日两国发生武力冲突,势必会严重威胁到西方国家在东亚的利益。各列强为阻止利益受损,联合施压的可能性极大。他们或以仲裁强迫中日停战,或逼迫中日已开放港口保持局外中立。总之,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招致列强的介入,这将严重损害中日两国的独立性和国际尊严。⑨《布瓦索纳德台湾事务建议书》上卷,1874 年,处番书类档案2A-033-06-545,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第25 页。19 世纪后,国际法规定解决国际争端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斡旋、调停和国际仲裁。斡旋和调停都是由第三方(个人、组织或国家)出面,或提出解决方案,或在当事国之间周旋以化解矛盾,当事国可在事后否定调节方案。国际仲裁则是由多方或多人组成仲裁机构进行裁断,结果表现为条约的签署,当事国必须服从仲裁结果。不难想象,诉诸国际仲裁一定会优先有利于西方国家,中日两国作为弱国必然失去主动权和话语权,而无论仲裁结果如何两国都必须接受,极具不确定性。大久保利通在10 月11 日和10 月14 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对英公使所言之仲裁)吾已告之并无诉诸仲裁之意,惟忧国内情实危急迫切,人心难押,势不可御。”①《大久保利通日記》下巻,東京:日本史籍協会,1927 年,第320 页,第323 页,第331—332 页。“英公使望吾国诉以国际仲裁,且委其为中间人。此举必妨害我独立之权,考量日本内情迫切,据今日僵持之态势,告之吾将归国。”②《大久保利通日記》下巻,東京:日本史籍協会,1927 年,第320 页,第323 页,第331—332 页。可见,大久保利通在权衡利弊后,接受了布瓦索纳德的建议,决定放弃国际仲裁。即便如此,威妥玛仍旧积极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如活塞一般奔走于中日之间。对此,大久保利通在10 月25 日的日记中提到:“若英公使介入,我国势必遭受非难,我方迄今未有丝毫委托之意。然,总理衙门已接受英公使之调节,并托其传话予我,我方仅就其问以照会答复而已。”③《大久保利通日記》下巻,東京:日本史籍協会,1927 年,第320 页,第323 页,第331—332 页。大久保利通虽不接受仲裁,但并未拒绝威妥玛的“居中调停”。
(三)以“止战”替“开战”
第四次谈判中,因双方始终固执己见,谈判破局。大久保利通一方面接受英国调停,一方面与布瓦索纳德探讨对中国开战的可行性。对此,布瓦索纳德的态度十分明朗——日本不具备开战资格。日本出兵台湾的前提是“生蕃地区为无主之地”,既然视其无主,就没有向清政府兴兵问罪的前提。相反,清政府视生蕃地区为自己属地,日本出兵侵犯了中国的利益,清政府是可以出兵干预的。如果日本非要为开战找理由,恐怕也只有三个环节存在可能性。一是关于此前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提出谒见同治皇帝,遭到清政府拒绝一事。布瓦索纳德认为,拒绝来使求见属于礼节问题,清政府这样做即便不妥,至多算是没有给予应有的外交礼遇,并不能成为开战的理由。二是清政府责难日本侵犯中国领土一事。中方主张台湾为其领地,只是一种“理论主张”,并没有对日本构成侮辱性行为。对于清政府提出的“领土侵犯”的说法,可通过对话、仲裁和战争解决,即便对话和仲裁都达不到目的,最后有资格诉诸战争的,应该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一方——中国。三是清政府拒绝接受大久保利通提出和解方案一事。布瓦索纳德表示,这仅仅是交涉不畅的表现而已,根本构不成宣战的理由。④《布瓦索纳德台湾事务建议书》上卷,1874 年,处番书类档案2A-033-06-545,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第169 页。
以上可见,布瓦索纳德对局势的判断较为客观,对西方列强惯于“以公法之名行霸权之实”的伎俩非常了解,对日本无宣战理由的分析也甚为合理。他之所以要努力避免战争,与其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19世纪中叶,法国二月革命后,欧洲浪漫主义盛行。在此基础上,法律构建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和人本主义,而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不以征服为目的,不企图发动战争,不诉诸武力”等人道主义思想被明确写入法国宪法。⑤大久保泰甫:《ボワソナードと国際法—台湾出兵事件の透視図》,東京:岩波書店,2016 年,第38 页。作为思想受过洗礼的法律学者,布瓦索纳德理应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这就决定了他能从较为理性和人道的角度看待当时的国家关系,并积极引导中日纷争朝和解的方向发展。
三、布瓦索纳德对和解条约的建言
鉴于布瓦索纳德的理性分析和威妥玛的往复周旋,日本最终选择了与清政府达成和解。在条约的执行细节和内容解释上,布瓦索纳德做了较为周密的考虑。首先,关于补偿金的交付,若清政府不肯在撤兵前支付,就需要以正式文书的形式确定下来,包括补偿金额、支付地点和支付时间。他建议支付地点选在山东芝罘或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要避开运输风险和冬季冰冻期),支付时间不能迟于日军正式从台湾撤兵三日后。其次,支付给被害人的补偿金不能冠以清朝皇帝恩赐的名义,这样会有损日本的尊严。他认为,既然清政府主张对生蕃地区的领有权,就应当对其臣民的杀人行为负责。而这个责任的承担者应当是由诸大臣组成的政府,而不是皇帝个人。比如1870 年的“天津教案”,最终支付给法国的赔偿金就是出自政府的名义,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恩赐。再次,日本可允许补偿金在名义上被看作“抚恤金”,也可与清政府另立条约标明具体金额,但必须要将支付补偿金一事明确载入正式文书中,否则日本将一无所获,这关乎到日本的尊严。最后,在条约中应标明,为保障今后航海人员的安全,清政府应派驻军坚守日军在台湾已建造的各个据点。否则,日方此前一直声称的“为保护今后航海者安全而出兵”的正义性就不复存在。布瓦索纳德所指的正式文书就是双方签署的《北京专条》,而另立的条约就是《互换凭单》。
《北京专条》内容:“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蕃,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①《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317 页,第317—318 页。
《互换凭单》内容:“台蕃一事,现在业经英国威大臣同两国议明,并本日互立办法文据。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又日本退兵,在台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亦经议定。准于中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全行退兵,中国全数付给,均不得愆期。日本国兵未经全数退尽之时,中国银两亦不全数付给。立此为据,彼此各执一纸存照。”②《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巻,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9 年,第317 页,第317—318 页。
布瓦索纳德亲历整个谈判过程,将日本在这场较量中的表现总结为三点:“第一,大久保利通试图通过对话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谈判到达极限时选择了退让。第二,在清政府愿意补偿与日本出兵所花等额费用的前提下,日本同意从台湾撤兵。第三,日本同意把对出兵费用的补偿以抚恤琉球受害人的方式支付。”③《布瓦索纳德台湾事务建议书》下卷,1874 年,处番书类档案2A-033-06-546,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第235 页。
从条约内容可以看出,布瓦索纳德的建议在条约内容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日本所得赔款数额虽仅有50 万两白银,或许还不能与所花军费相抵,可换来的却是日本的国家尊严、国际声誉和有利于国内改革发展的大环境。清政府虽然暂时保住了台湾,但在名义上却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统辖权,这就意味着中琉间的朝贡关系已被切断。后来的史实证明,正是以此次清政府的外交失败为发端,日本才不断扩大野心,攻朝鲜、吞琉球、割台湾,发动了一系列对东亚各国的侵略战争。
结 语
中日北京谈判是“牡丹社事件”的关键一环。这场“华夷观”与“公法观”的对战,决定了近代东亚国家关系的基本走向。日本借助所聘外国人的专业知识,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成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论战过程中,日方表面上的交涉人是大久保利通,其实背后真正的策划者和主导者是布瓦索纳德。因受雇于日本政府,他很难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作出判断,他对万国公法“实效统辖”概念的过分强调和对被曲解的“无主之地”概念的完整继承,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同时,他也提出了引导中日之争走向和解的建设性意见,避免了两国因武力对抗而两败俱伤。客观理性分析布瓦索纳德的观点和行为,对于研究西方知识人群体在东亚近代格局变迁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