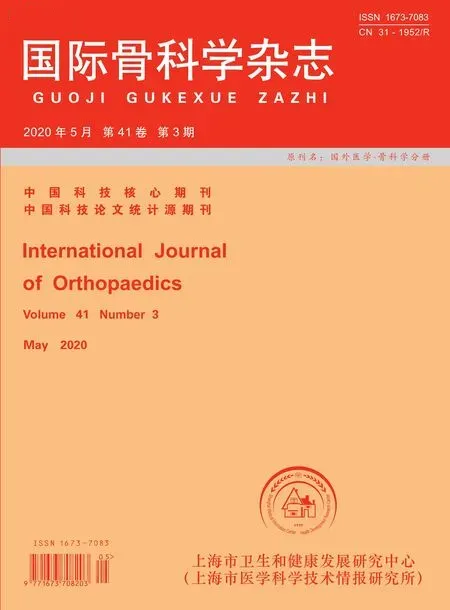肺癌骨转移分子机制及相关分子标志物临床意义的研究进展
滕小艳 魏丽荣 夏前林 杜玉珍
骨是肺癌远处转移常见靶组织之一[1]。骨转移灶的形成对患者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易导致骨相关事件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
肺癌骨转移的形成过程复杂。肺癌细胞离开原发肿瘤后随血液循环迁移至骨组织定植,或进入休眠状态,或与造血干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相互作用获得骨微环境的某些特征,继而发生增殖[3]。肺癌细胞在骨组织中生长可破坏骨形成与骨吸收的平衡,进而形成大的骨转移灶,此时患者只能接受姑息治疗[4]。
我们回顾国内外文献,对肺癌骨转移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对参与其中的血清分子标志物的临床意义进行探讨。
1 肺癌骨转移形成的分子机制
肺癌骨转移的形成是一个多步骤过程。第一步,播散的肿瘤细胞(DTC)在骨髓微环境中定植;第二步,涉及DTC的生存和休眠;第三步,涉及少数休眠DTC的激活和发展,形成微转移灶;最后,DTC进入增殖生长期并使骨微环境改变,随后其逐步降低对骨微环境生存信号的依赖,最后独立于骨微环境,并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大的骨转移灶[5]。
1.1 肿瘤细胞的休眠
肿瘤细胞可随血液循环迁移至局部骨组织。为了在骨组织中建立癌转移灶,定植的DTC根据其位置可立即生长或进入休眠期。休眠使DTC能够适应骨微环境,继续生存和增殖,同时也能使其不受免疫系统和不同治疗的影响[6]。骨微环境中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基质细胞、成纤维细胞等对骨组织中DTC生存和休眠的维持至关重要[6]。
为了在骨微环境中适应、生存和生长,癌细胞必须表达通常由成骨细胞或破骨细胞表达的因子,以此模仿骨细胞,逃避细胞毒性治疗和免疫反应。例如,骨转移癌细胞可表达组织蛋白酶K、骨保护素(OPG)、骨桥蛋白(OPN)和钙调神经磷酸酶(CaN)等[6]。此外,一些实验研究表明,癌细胞可与巨噬细胞融合,或通过与破骨细胞前体融合诱导多核巨细胞,形成具有破骨细胞特性的癌细胞[7]。肿瘤细胞可表达多种破骨因子,如甲状旁腺激素相关蛋白(PTHrP)、白细胞介素(IL)-6、肿瘤坏死因子(TNF)-α、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这些分子的表达可能在逃避免疫监测或形成骨髓定植中为其提供生存优势[5]。
1.2 休眠肿瘤细胞再激活
骨微环境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能够使休眠的肿瘤细胞再激活。
1.2.1 破骨细胞的激活作用
休眠肿瘤细胞再激活可能是在非肿瘤细胞控制下进行的,即外部因素的作用。当肿瘤细胞与骨内膜表面的骨衬细胞结合时可导致肿瘤细胞长期休眠,而破骨细胞介导的内皮细胞重建可去除骨衬细胞,从而释放休眠肿瘤细胞,使其重新激活和增殖,并形成微转移,然后增生,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形成大的骨转移灶[5]。
休眠肿瘤细胞激活过程中,只有少数细胞可通过表达整合素和趋化因子受体(CXCR)4成功地与骨髓基质中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发生相互作用[6],特别是整合素αvβ3和αvβ5,它们能够识别并结合骨基质蛋白。而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可识别肿瘤基质细胞表达的整合素α4β1并与之结合,促进破骨细胞祖细胞募集,导致肿瘤细胞再激活[8]。同时,CAF可通过高表达CXCR1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来启动骨转移,通过内皮祖细胞募集促进肿瘤的生长、增殖和血管生成,进一步加重骨转移的级联反应[9]。
有文献报道,骨微环境中一些细胞外基质蛋白能够重新激活休眠的DTC,尤其是Ⅰ型胶原、Ⅳ型胶原、OPN、骨涎蛋白(BSP)和降钙素,这些蛋白还可促进血循环中的肿瘤细胞在骨髓定植[10-11]。
1.2.2 肿瘤细胞的自主激活
肿瘤细胞再激活也可能在其自主控制下进行,即内部因素的作用。
骨代谢平衡依靠破骨细胞引发的骨吸收与成骨细胞引发的骨形成之间达成的动态平衡来维持。核因子κB 受体活化因子(RANK)/核因子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OPG信号转导通路是维持骨稳态的重要机制,也是调节破骨细胞形成和成熟的关键途径[12]。具有破骨特性的肿瘤细胞的发育可通过以上信号转导通路改变骨内平衡,触发干细胞信号的释放,刺激转移性生长[13]。因此,DTC重新激活还取决于肿瘤细胞需获得癌干细胞样特性,允许其进行自我更新。
一旦肿瘤细胞开始增殖,它们在骨微环境中可分泌多种可溶性细胞因子,包括PTHrP、IL-6、TNF-α、M-CSF、基质金属蛋白酶、CXCR4、CXCR12和OPN等,这些因子可促进破骨细胞的分化、增殖和活化,增强破骨细胞的骨吸收作用,促使溶骨性骨转移发生[14-15]。有学者认为,肿瘤细胞通过上调RANKL,产生并释放促肿瘤生长的骨结合分子,包括转化生长因子(TGF)-β和PTHrP,从而刺激骨吸收发生。同时,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既能刺激破骨细胞的骨吸收作用,又能从骨微环境动员骨髓源细胞[16]。
成骨细胞也可以通过生成CaN、OPG、PTHrP、IL-6和前列腺素E2来调节破骨细胞的形成[16]。同时,骨微环境可释放多种储存的活化生长因子,包括TGF-β、IGF、BSP和骨形成蛋白等,它们又会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并支持其生存[17]。而不断生长的肿瘤细胞会分泌许多溶骨性前体因子,发生进一步的溶骨,并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在骨组织局部形成肿瘤微转移灶[18]。
此外,肿瘤细胞还可分泌微RNA以及外泌体样小囊泡,显著促进骨转移的发生[19]。肿瘤细胞产生的组织蛋白酶K,可增加肿瘤细胞的侵袭性,并有助于骨降解[11]。肿瘤细胞还可释放干扰正常骨吸收的因子,包括成骨细胞分化抑制剂,如分泌性蛋白 Dickkopf-1和硬化素[18]。
1.3 骨转换失衡与肺癌骨转移
成骨细胞介导的骨形成与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构成骨代谢反馈环路,维持骨转换的动态平衡,保持骨完整性。
破骨细胞通过分泌H+和酶[如抗酒石酸盐酸性磷酸酶异构体5b(TRACP-5b)],发挥骨吸收作用。Ⅰ型胶原被组织蛋白酶K降解,其降解后释放的N末端和C末端片段可在血液和尿液中被检测到。同时,破骨细胞生成促破骨细胞因子(如IL-6、M-CSF)能力增强,成骨细胞也能分泌骨基质矿化所必需的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 (BALP)[20]。
RANK/RANKL/OPG轴的关键分子有助于调节骨转换。受体RANK由破骨细胞前体表达,配体RANKL由成骨细胞和基质细胞产生,通过与受体RANK的相互作用来刺激破骨细胞的分化和成熟。OPG是一种由成骨细胞及骨髓基质细胞等分泌的可溶性蛋白,同时它又是一种诱饵受体,可以防止过度骨吸收。许多促破骨细胞生成因子(如IL-6 和M-CSF)和抗破骨细胞生成因子(如β干扰素)均有助于调节破骨与成骨之间的平衡[21]。
肺癌细胞转移到骨后可释放PTHrP等多种可溶性介质,激活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抑制成骨细胞OPG的表达,从而促进骨吸收。破骨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又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分泌促骨溶解的介质,造成溶骨性病理改变。而骨吸收时从骨基质中释放的TGF-β 等生长因子又会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使转移瘤不断浸润扩展,骨吸收作用不断增强,进一步破坏骨组织。当骨质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致使骨形成和骨吸收的微妙动态平衡被打破,骨代谢产物增加,释放入血,血液中可检测到骨转换标志物异常升高[20]。
2 骨转移相关血清分子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价值
肺癌骨转移时,早期骨骼病变通常无法被检测到,故其早期诊断一直是临床难题。由前文可知,骨微环境中的多种因子及骨转换均与肺癌骨转移的形成相关。研究发现,骨转移标志物的血清水平异常一般早于骨转移的影像学异常,且其测定操作简单,价格低廉,创伤小,可广泛开展并进行动态监测[14]。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将骨转移血清标志物的变化与肺癌骨转移的临床应用联系起来,特别是在早期诊断、病情进展监测以及预后评估等方面[15]。
2.1 血清骨微环境细胞因子
骨微环境中的细胞因子在肺癌骨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但其在肺癌骨转移中的临床应用研究还较少,目前主要涉及 CaN、OPG、PTHrP和IL-6 等。
CaN可调节T细胞核因子1的活化,后者是破骨细胞基因的关键转录因子,在破骨细胞分化中有重要作用;同时,CaN可协同细胞外的Ca2+参与激活休眠的肿瘤细胞[18]。一项纳入223例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表明,患者肿瘤组织中的CaN表达升高,且与肿瘤的病理分型、分化级别等相关[22]。也有研究发现,肺癌骨转移患者的血清CaN水平明显高于无转移患者[23]。
肺癌细胞分泌PTHrP后可与成骨细胞表面的相应受体结合,促进破骨细胞的分化成熟,最终导致溶骨性骨转移发生[24]。有研究证实,在大多数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体内,PTHrP表达升高,PTHrP阳性者更易发生骨转移[25]。一项纳入1 149例高钙血症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血清PTHrP高于150 pmol/L时与高钙血症的存在呈显著正相关,并且较高的PTHrP水平与骨转移发生率增高和中位生存期降低均显著相关[26]。有研究发现,在肺癌患者中,抑制PTHrP抑制剂MiR33a的表达可以促进骨转移发生,提示PTHrP可能成为预测肺癌骨转移的血清标志物[27]。
对RANK/RANKL/OPG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发现,溶骨性破坏或成骨性破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均有 OPG 等因子的参与[13]。一项纳入1 279例肺癌患者的meta分析研究显示,血清OPG与骨病变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肺癌骨转移患者的血清OPG水平明显高于没有骨病变的患者,提示血清OPG水平可作为肺癌骨转移鉴别诊断的有效评估指标[28]。
细胞因子IL-6可调节骨吸收与骨形成之间的代谢平衡。一项对330例Ⅳ期原发肺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高IL-6水平与骨转移发展有显著相关性[29]。但IL-6生物学作用的多效性导致其在骨转移的诊断和监测中受到较多因素干扰,其临床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0]。
2.2 血清骨转换标志物
骨形成和骨吸收均与阶段特异性骨转换标志物的生理释放有关,它们在血液或尿液中的水平可反映骨转换过程,被称为潜在的骨转移标志物[14]。在肿瘤骨转移发生中,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活性均显著增加,呈高水平骨转换状态[31]。
当成骨细胞合成增加时,反映骨形成的血清骨转换标志物均升高,如总Ⅰ型前胶原N-端前肽(tP1NP)、Ⅰ型前胶原C-端前肽和BALP[32]。当破骨细胞活性增强时,体现骨吸收状态的标志物则大量释放入血,如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特殊序列(β-CTx)和TRACP-5b[4]。有研究发现,骨形成标志物 tP1NP、BALP及骨吸收标志物β-CTx、TRACP-5b的血清水平在肿瘤骨转移组中明显高于非骨转移组[33-34]。
BALP在骨钙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反映骨形成的指标[14]。一项对238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高水平血清BALP与骨骼事件、疾病进展和死亡的风险增加均相关[35]。但是,由于其他影响骨代谢的疾病也可引起血清BALP 升高,且其检测也更困难[36],故血清BALP尚不能作为肺癌骨转移的特异性标志物。
3 结语
综上所述,血清分子标志物在肺癌骨转移的诊断、病情进展监测及预后评估等方面具有重要临床价值,但是其临床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一些因素阻碍了其临床应用[37]。此外,由于血清骨转移标志物的不稳定性以及研究样本量不足等问题,其临床应用价值受到限制。
近年,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数据挖掘方法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学研究中,特别是智能预测模型的应用[38-39]。以多目标优化为理论基础,并以反传人工神经网络为模型,通过多目标神经网络模型学习[40],对骨转移血清分子标志物进行整合,建立“最优分子标志物群”,构建基于肺癌骨转移的智能诊断血清模型,可能有助于提高对肺癌骨转移的早期诊断和进展监测,对改善肺癌患者生存质量,实现肺癌的慢病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