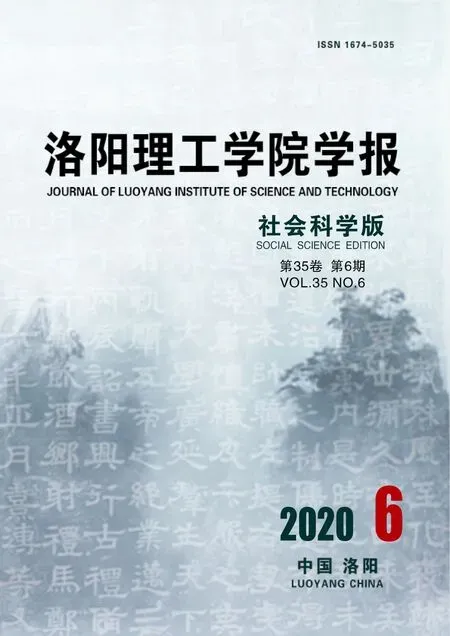中国的威廉·华兹华斯研究
马 伊 林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威廉·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桂冠诗人”,柯勒律治与阿诺德均将其誉为继莎士比亚、弥尔顿之后最伟大的作家。华兹华斯一生创作900余首诗歌、一部诗剧(《边界人》)和一部游记(《湖区指南》)。1801年,《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出版令其成为颇有影响力的诗人。次年,弗朗西斯·杰弗里在《爱丁堡评论》刊发的评介《抒情歌谣集》的文章揭开了西方华兹华斯研究的序幕。随着西方学者对华兹华斯的持续关注,西方华兹华斯研究在19世纪后半叶已达到小型产业的规模[1]。遗憾的是,中国关于华兹华斯研究在起步时间上比西方学界晚了近一个世纪,自20世纪90年代才走向成熟。本研究将按照1990年前后两个阶段考察国内华兹华斯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审视该研究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可探讨的空间。
一、初始阶段:1900~1990年
国内关于华兹华斯研究的初始阶段包括三个时期,即1949年之前的开拓期、1949~1978年的停滞期和1978~1990年拨乱反正的复苏期。这一阶段研究论文数量较少,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水平不高,主要以介绍性、总论性文章为主,论文作者多为学术功底深厚的资深学者。
(一)开拓期
梁启超在《清议文》所刊载的《慧观》一文可以看作是中国华兹华斯研究的滥觞。梁启超把华兹华斯比作“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的“善观者”,肯定诗人“常以其已知推其所未知”“见造化之微妙”的体察万物的超卓能力。令人遗憾的是,梁文并未评析华兹华斯的任何一首诗作。继梁启超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诗歌的自然主题与诗论。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盛赞《丁登寺》第35~49行的诗句所体现出的回归自然的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赋予真正的中国人无法言表的温顺的那种平静而受到庇护的心态[2]。此外,郑振铎在《小说月报》连载的《文学大纲》中讴歌了华兹华斯对自然的热忱。1947年,李祁的《华兹华斯及其序曲》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文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华兹华斯的生平,还探讨了华兹华斯自然诗的构成以及意义,并宣称华兹华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诗人。胡适和陈瘦竹是国内最早关注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两位学者。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引证华兹华斯所倡导的反古典主义的语言观来为中国文学革命提供指引[3]294。1932年,陈瘦竹的《Wordsworth的诗论》一文推介了诗论中的情感、想象等思想。以上学者对华兹华斯代表性诗歌的自然主题和诗论的介绍、总体把握以及积极接受,为国内读者初步了解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打开了一扇窗口。
(二)停滞期
1949~1978年近30年间,由于历史和政治形态的影响,西方作家被标以资本主义的标签,其作品被排除在阅读的视野之外,只有少数被认为是革命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受到重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在此期间受到冷遇与曲解。
1949年,卞之琳在《文艺报》所刊载的《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指出华兹华斯虽然要求自由但是却离自由甚远、愈成熟愈疏离年轻时候的理想,他不再指望以反抗争自由,反而悠然地回到自然之中[4]。在卞之琳看来,华兹华斯走的是一条脱离现实的道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像雪莱、拜伦参与革命与斗争,没有发挥诗人的先锋作用与普世情怀,反而隐居英国湖区,将目光聚焦于生活和个人情感,甚至在晚年宣扬宗教思想,由此,他自然而然被化作消极逃避现实的一派。卞之琳从政治革命层面对于华兹华斯的否定态度也不自觉地引领学界的走向。无独有偶,苏联学界对于华兹华斯的态度同卞之琳的观点本无二致。1953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研究所编写《英国文学史》把湖畔派诗人归入消极的浪漫主义者行列,只因他们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态度,这一观点也代表了苏联学界对于华兹华斯较为一致的看法。国内学者以译介的方式照搬苏联的研究思路。1956年,《文史译丛》创刊号刊载《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英国文学概要》译文,文中把湖畔派诗人当作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典型。1959年,阿尼克斯特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纲》作为该时期高等院校英国文学史课程的教材,书中把《抒情歌谣集·序言》看作反动与保守的浪漫主义宣言。此外,晴空的《我们需要浪漫主义》也把矛头直指华兹华斯等人。文中指出这些诗人站在与历史发展相悖的进程中,他们过于迷恋过往的生活,这是消极的浪漫主义态度,而他们的作品对我们时代没有任何价值。晴空的论述也同范存忠的《论拜伦和雪莱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的观点如出一辙。在范忠存看来,华兹华斯的消极情怀背离了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精神,因此也必定被时代所摒弃。
(三)复苏期
1978年11月,杨周翰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会议的发言标志着学界对外国文学的重新认识。会议上,他特意提出要对华兹华斯实行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他对文学界的贡献[5]5。在具体实践方面,王佐良、郑敏等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学界重估华兹华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一文中,王佐良肯定了华兹华斯在英国文学史上一流大诗人的地位,文中对《抒情歌谣集》以及《序曲》的哲思感悟、自然观、想象观等进行了简要评价,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篇分量极重的中肯评述。郑敏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再评价》高度赞扬华兹华斯诗歌对于贫苦民众刻画的现实性,并且审视了华兹华斯对英国现代诗和诗论发展的影响。伴随着两位资深学者对华兹华斯重估的积极风气,不少青年学者纷纷为华兹华斯正言。刘彪在《华兹华斯简论》中纠正了学界的华兹华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想日趋保守的错误认知,肯定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十年间的诗歌创作的价值。此外,苏卓兴的《试论华兹华斯的美学原则与创作实践》、王淼龙的《谈谈华兹华斯及其〈抒情歌谣集·序言〉》、汪剑鸣的《谈谈关于华兹华斯的评价问题》、茅于美的《英国桂冠诗人》、王忠详《谈谈湖畔派诗人》以及傅修延《关于华兹华斯的几种评价的思考》等,同样为恢复诗人积极的浪漫主义身份作了正本清源的努力。
二、成熟阶段:1990年至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始在较深层面挖掘华兹华斯诗歌与诗学的魅力。这一阶段的成果多为专题研究型论文,论文作者比较年轻,有相当一部分论文是在硕士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此外,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除诸多不为人熟知的抒情短诗,比如《采坚果》《永生颂》《西敏寺桥上》等外,《远游》《塌毁的茅舍》《索尔兹伯里平原》《坎伯兰的老乞丐》《退伍的士兵》《有一个男孩》《感恩节颂歌》等一些长诗、叙事诗和颂歌也陆续进入学者视野。
作为国内华兹华斯研究的深化期,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为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的研究虽集中在前人有所涉足的自然观、想象观、情理观等领域,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表现出较强的问题意识。段孝洁的《从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看其哲学思想》把诗人的自然观置于西方哲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其思想中的复杂性被揭示。章燕的《自然颂歌中的不和谐之音——浅析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我否定倾向》挖掘了华兹华斯在自然世界中对人生的百味体察与精神重压,使其诗歌在自然视域下透露出不和谐的色调。王捷的《华兹华斯自然诗创作溯源》和孙婧的《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诗意建构》也是关乎相关主题的较有见解的文章。此外,聂珍钊的《华兹华斯论想象和幻想》探究了诗论中的想象与幻想的联系问题,该文为较为深入地理解华兹华斯的艺术创作提供指引。苏文菁的《情与理的平衡——对华兹华斯诗论的反思》指出华兹华斯的沉思是个人情感向艺术情感转化的过滤器。不仅如此,兰菲刊发在《东西方文化评论》的《华兹华斯与陶渊明》还把华兹华斯同中国古代诗人进行比较研究。兰文通过“退隐田园与回归自然”“自然之道与宇宙精神”“天人合一与主体移转”“哲学诗人及其艺术境界”等四个角度,审视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在以上学者努力之下,华兹华斯的形象在读者心中已成为具有复杂思想的哲性诗人。
进入新世纪,关于华兹华斯研究迈向更高的台阶。中国知网(CNKI)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00~2017年期刊论文数量有1 300余篇,博士论文7篇,出版的学术专著以及评传性著作4部,华兹华斯研究已达燎原之势。受到西方思潮和研究偏好的影响,这时期代表性较强、影响较大的成果呈现出与西方学界较为一致的多元化特征。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空间理论、生命哲学、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等西方理论和哲学思想成为研读华兹华斯作品的支撑,而西方学界所热衷的城市研究和教育理念研究也助推了国内学者对华兹华斯作品中的城市书写与教育思想的探究。此外,诗学思想和自然主题研究也取得高水平的发展。
(一)女性主义研究
胡鹏在《〈序曲〉的崇高与秀美》一文中比较了《序曲》的美学构成与同时代的艾德蒙·布克美学观点的契合和背离,指出女性化的自然虽主导着崇高与秀美,但诗人却利用女性自然将两者融合,与此同时侵占女性自然的权力进而改变自然的性别,最终形成并建构有别于布克美学的华兹华斯式的超卓[6]。孙晓安的《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矛盾女性观》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既表现出对女性的同情、赞美和认可,又表现出一定的男权意识,但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英国,华兹华斯对女性的这种矛盾态度却是积极的和进步的,标志着男性开始思考女性的身份和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女性主义组成部分的生态女性主义也成为探究华兹华斯作品中性别话语的重要理论支撑。梁路璐和邱德伟在《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华兹华斯诗歌的自然观》一文中依据该理论探究《露西组诗》中自然与女性的联系,文中指出两者在幻境中交融并汇作梦幻中的他者得以呈现。张智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华氏兄妹创作》运用同样的视角审视了《丁登寺》中自然和多萝茜的文化利用问题。此外,有学者从“双性同体”的视角分析了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二)叙事学与空间理论研究
申丹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解读叙事》等专著或译著为国内学界了解西方叙事学并把西方叙事学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提供指引和参照。近年来,学界以叙事学视角切入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而非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后现代叙事作品,华兹华斯的诗歌也成为考察的重点。陆梅华的《“后经典语境下”华兹华斯诗歌的叙事艺术研究》从诗歌的叙述者、诗歌的叙事序列、诗歌戏剧性叙事、诗歌跳跃性叙事、诗歌音乐化叙事等方面,对具有华兹华斯典型叙事艺术特点的多首抒情诗进行解读。该文较好地打破华兹华斯诗歌叙事研究拘泥于叙事诗研究的局面,验证了诗歌叙事学批评的可行性和效度。同样,李增的《论华兹华斯〈捣毁的茅舍〉中的主题与叙事技巧的统一》运用叙事学理论中指涉主题的叙事行动以及控制读者情感发展的叙事节奏[7],对《捣毁的茅舍》中叙述者的心路历程进行较为扎实的探讨,这同时也是国内学者对该叙事诗的首次评析。
不仅如此,空间理论视角也成为关于华兹华斯研究中较为瞩目的一支。较有代表性的是周美兰的《华兹华斯诗歌的空间艺术》。周文借用苏贾的“三种空间”辩证法分析华兹华斯诗歌所建构的乡村空间、城市空间与开放空间,并挖掘三重空间之下的政治文化。此外,在《诗魂探幽——从心理空间理论析〈孤独的割麦女〉的诗人创作灵源》一文中,李睿和赵嘏以福科尼耶(Gilles 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为支撑分析《孤独的割麦女》,指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建立心理空间并发生空间概念的整合,而其诗作便是诗人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对其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的过程的还原。该解读视角较为新颖,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三)生命哲学、宗教思想等哲学思想研究
华兹华斯童年时期父母的离世以及青年时期弟弟约翰的海难令其常常思索生命存在的意义,这在其诸多作品中也有较好地映现。20世纪开始,国外学者就较多地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切入华兹华斯的作品。近年来,张彬、吕冰等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在《立体的生命观:华兹华斯生命哲学阐释》一文中,张彬通过对华兹华斯的诗人、评论家与基督教徒等三重身份的考察,展现华兹华斯分别对于生活之道、生命形态以及生命价值的多层次的生命意识。吕冰的《从〈水仙〉看海德格尔存在哲学观照下的浪漫主义本真生存》一文中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探究《水仙花》所体现出的人类本真生存的分裂性和救赎性。此外,叶蔚芳的博士论文《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原初创伤的剖析》借助阿塞吉奥里和弗曼的原初创伤理论审视华兹华斯对于生命的态度。文中指出,华兹华斯在《索尔兹伯里平原》《黄昏漫步》等诗歌中的“恐惧”与“混乱”,《塌毁的茅舍》《永生颂》等诗歌中的“救赎”与“痊愈”,以及《远游》《哀歌》等诗歌中的“幻灭”与“皈依”,较好表现出人类生存本质的不同阶段。作者在结尾部分带给读者较为深刻的哲思:“如果说饱受创伤的华兹华斯曾寄望于那匹奔跑在莱斯顿荒野上、带有神性之光的无暇白鹿的慰藉,那么受启蒙大潮冲刷后,以祛神去魅为己任的现代人类又该‘伤’归何处?探问至此,华兹华斯终其一生对原初创伤的吟念也可成为人类反躬自身的永恒路标。”[8]
与此同时,华兹华斯诗歌的宗教思想也得到系统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光旭的专著《华兹华斯“化身”诗学研究》。赵著借用宗教中的“化身”概念,运用现代阐释学的方法探究“化身”在《序曲》中的映现。书中还探讨了诗人的宗教情感论、神学语言观等问题。李增和裴云的《选民意识·先知声音·预言诗人》也同样对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两位作者较为详尽地分析《序曲》中“选民意识”的具体表现形式,指出“‘选民意识’是华兹华斯追求预言诗人地位的思想动因,也是其用来摆脱影响的焦虑、超越前辈诗人的精神力量”[9]。
(四)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现使相关批评成为国外华兹华斯研究中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为西方学界华兹华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该理论视角方面同西方接轨。
王苹在国内开启了运用后殖民主义解读华兹华斯的诗作的先河,为国内读者理解浪漫主义同时代话语的联系提供指引。她的《告诉我她在唱什么:〈孤独的割麦女〉的后殖民解读》剖析了《孤独的割麦女》中的战争暴力、历史纠葛与文化冲突。文中指出,华兹华斯对殖民主义批判的同时又持有英格兰性,同帝国保持既共谋又斗争关系[10]。除涉及《孤独的割麦女》,王苹在另一文《“水仙化”与“踢水仙”》中考察了《水仙花》的殖民话语以及在不列颠文化殖民主义的浪潮中殖民地所肩负的使命,该文作者同时也论及了加勒比文学中对《水仙花》的书写以及对儿童的“水仙化”教育。与此同时,李增在《政治与审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东方书写研究》一书中的第一章也同样考察了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帝国话语。书中指出:《序曲》的“中国园林”片段是对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不快的访华经历的较好回应,表征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此外,宋慧岩的《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运用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的“颠覆”与“抑制”理论评析了《丁登寺》《伦敦,1802》以及《世事让我们过分劳心》的意识形态,但由于篇幅原因,论证略显单薄。
不仅如此,国内在华兹华斯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知名学者针对国外学界的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较热的研究现状发出不同声音。章燕在《对英国浪漫主义形式研究转向的思考》中以《丁登寺》为例审视了新历史主义研究视角的利与弊。张旭春在《没有丁登寺的〈丁登寺〉》中提出了华兹华斯研究中不该“滥用”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论点,认为那些拘泥于边角料的“小史”并不能支撑其还原“大历史”的壮举[11]。同样,丁宏为在《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一书中以一定的篇幅考察学界政治话语视域下的华兹华斯研究状况,指出华兹华斯诗歌的殖民话语解读会破坏诗歌的本意与审美趣味。
(五)城市书写研究
国内学界在华兹华斯城市书写研究领域通过借鉴诸如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都市漫游者”等研究范式和思路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谢海长的博士论文《现代城市体验:华兹华斯诗学及作品研究》探究华兹华斯的剑桥、伦敦、巴黎等城市体验与他早期诗歌人生道路选择、成熟期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外,作者还审视《序曲》《家在格拉斯米尔》等诗歌中所表现的同乡村生活大相径庭的城市居民异化、共同体瓦解以及大众文学艺术泛滥等现象。如此系统且扎实的研究实属不易。此外,有学者把华兹华斯的伦敦体验放在帝国的视域下进行考量。在《美学沉沦、否定批判与隐喻剧场——论华兹华斯〈寄居伦敦〉中的都市漫游者与伦敦形象》中,张鑫认为“都市漫游者”的华兹华斯在寄居伦敦的过程中承担了叙事者、阐释者和中介者角色,诗人的伦敦印象也由前期的美学沉沦转向思虑成熟时期具有矛盾心态的否定批判,巨城伦敦也构成了一座帝国中心的怪物嘉年华与隐喻剧场[12]。同样,余君伟的《都市意象、空间与现代性:试论浪漫时期至维多利亚前期几位作家的伦敦游记》也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华兹华斯的伦敦漫游体验对种族的考量、帝国中心的认知等问题。
(六)教育理念研究
国外关于华兹华斯教育理念的研究已相当成熟,不少论文或专著涉及华兹华斯对卢梭的教育理念的矛盾态度、对文学书籍启发心智的赞扬以及对理性和功利教育的批判等问题。国内在该视角领域虽刚刚起步,但起点并不低。作为国内较早关注华兹华斯长诗《远游》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徐红霞的《华兹华斯的〈远游〉与十九世纪英国国民教育》首次触及了诗人对英国国民教育的看法。该文在梳理英国国民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诗人借漫游者之口呼吁政府建立国民教育的初衷,反映其教育理想与英国教育实践的张力[13]。此外,王茜的《在大自然中读好书》中探究了《序曲》中“阿拉伯之梦”的教育问题。文中指出,诗歌中所体现的自然教化塑造了诗人对待知识的通达气质和良好直感,“在大自然中读好书”也成为诗人在自然中接受精神升华的体现[14]124-129。袁宪军在《自然的意义:解读华兹华斯“丁登寺”诗》一文中以《丁登寺》为切入点,考察了华兹华斯在诗中所传达的自然在人性与道德培养、神性启迪、审美情感、透视真理、人类沟通等教育方面所产生的意义[15]。实际上,王茜和袁宪军的研究是对华兹华斯自然观的一种在教育维度上的深化。
(七)诗论研究与自然主题研究
自从20世纪初就一直受到中国学者关注的诗学思想和自然主题领域的研究在这期间得到较为系统的发展,呈现出以专著或博士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
苏文菁的《华兹华斯诗学》对华兹华斯诗学思想形成的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涉及内容包括语言观、想象观、情理观、创作观等。作为国内第一部华兹华斯诗学研究专著,它对华兹华斯的诗学研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除了苏著的宏观考察,一些学者聚焦以往学者所忽视的诗学某个要素。赵光旭的《华兹华斯“瞬间”诗学观念的现代性特征》把华兹华斯的诗学观念“瞬间”与现代主义诗学概念“顿悟”进行对比,认为“瞬间”在其客观机制、叙事手法和感官意象方面都具有现代性特征。刘晓晖也同样注意到华兹华斯的“瞬间”思想,他在《反讽与华兹华斯的“时光瞬间”》一文中从浪漫主义反讽的角度分析了“瞬间”的认识论内涵。除“瞬间”之外,徐永峰的《灵视——华兹华斯诗艺建构的核心》还审视了“灵视”的内涵。徐文指出:“灵视”是诗人探索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它成功展示那沉静而永在的人性的悲曲中所渗透的人性的崇高。此外,陈清芳的《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把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等都归因于“快乐”原则,并指出“快乐”是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
除了在诗论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绩,王萍、杨丽和张秀梅各自的博士论文也表明了学界在自然主题研究领域达到一定高度。在《凝视自然的心灵书写——华兹华斯诗歌研究》中,王萍从“凝视”这一视觉隐喻的启发下照看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理论与自然的关系。文中较为全面地探讨了诗人对待自然的态度、自然观的文化之根、自然观的形成、书写自然时表现何种心灵感悟等问题。杨丽的《华兹华斯与英国湖区浪漫化》以文化地理学和风景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把华兹华斯所居住的湖区看作一个典型的“空间/地方/风景”复合体:既是一个被当地人实践和活动的具体地方,又是一片风景,还是各种权力话语交锋的空间。文中选取构成湖区风景的四大元素“水、石、木、建筑”为考察对象,审视华兹华斯对湖区的“情感投射”“想象升华”与“诗意萃取”[16]。张秀梅的《抗拒现代:生态后现代视域下的华兹华斯研究》把华兹华斯的诗歌放在生态后现代视域下进行解读,通过探讨华兹华斯对工业社会、宇宙机械模式、现代意识形态以及单一因果论等的四重抗拒,展现华兹华斯的多元化的生态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学者还从感官角度考察华兹华斯的诗歌。朱玉的《华兹华斯与“视觉专制”》《倾听:一种敏感性的形成》《“远居内陆……却听到强大的水声”——华兹华斯《序曲》第1卷的意义与影响》等系列论文探讨了听觉对华兹华斯洞察事物背后永久价值的重要意义,文章颇见功力;其专著《作为听者的华兹华斯》更是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难能可贵的是,朱著还在附录部分添加《家在格拉斯米尔》的中译本,这是继丁宏为1999年翻译的《序曲》后的另一首长诗的译作,它为国内学者探究这首长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结 语
国内华兹华斯研究始于1900年,经历1900~1949年的开拓期、1949~1978年的停滞期以及1978年后的复苏期,自1991年走向成熟。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论和成果的影响,国内研究无论在选题范围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较好地同国外研究接轨,形成多元化蓬勃发展态势,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读者深刻认识这位伟大的诗人做出重要贡献。但也应该承认,在此期间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研究中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对文本、对具体分析论证不够扎实和细致。一些研究者借助于西方理论对华兹华斯作品阐释的过程,不自觉地遵循理论至上的批评方式,直接把某部诗作标以某种理论的标签。再譬如,从国内研究成果的参考文献来看,研究较少引用针对具体问题表述的观点,反而在理论专著中对原理的论述居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可以归为研究者对理论的过于迷信,又可以归为其并未吃透理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非是摒弃理论,而是加强理论建设,提高理论修养,提高思辨能力和分析论证水平,同时也要以恰当的方式看待理论,加强问题意识,注重文本细读[17]。
其次,研究成果存在低水平的重复现象。就拿中国知网上以“华兹华斯”“自然”“丁登寺”为主题的30余篇论文来说,大多数篇目虽采取相似论述视角,但彼此之间并无任何“交流”,行文中也鲜有涉及早先对《丁登寺》中自然问题有过深入探讨的章燕和袁宪军的文章的蛛丝马迹。实际上,加强国内同行之间的对话,是避免重复的较好举措。对于前人的成果,都应该持尊重的态度。有些学者为了人为地成果创新而消极地对待前人的努力,造成非主观故意的重复,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此外,有些研究看似新颖,但却亦步亦趋跟随国外学者的思路与叙述模式,甚至在文中出现语言欧化的现象以及语法和逻辑漏洞。
最后,整体研究有待加强。一方面,应更多关注华兹华斯不同作品之间的互文联系,避免将作品割裂进行研究,这同时也对我国学者的研读范围提出更高的要求,《莱尔斯顿的白母鹿》《命名地方组诗》《边界人》《湖区指南》等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长诗、组诗或非诗学作品应该引起关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华兹华斯的诗歌对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借鉴以及对同时代诗人济慈、骚赛的影响,这为华兹华斯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探索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