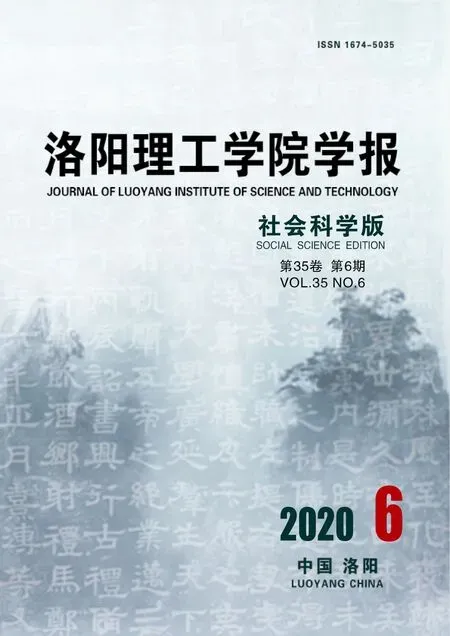论杨杏佛的救国思想及实践变迁
孙 阳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杨铨(公元1893~公元1933年),字宏甫,号杏佛,江西清江(今江西省樟树市)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和民族革命战士。面对清末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杨杏佛开始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杨杏佛一生经历了革命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二次革命救国、中间路线等阶段,贯穿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重大历史时期,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殚精竭虑,做出了卓越贡献。“纵观杨杏佛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一条由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步走上或接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清末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具有代表性”[1]1。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杨杏佛的救国思想及其实践演变进行分析,全面展现其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光辉历程。
一、革命救国思想的初步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难,清廷当局政治腐败,对内镇压,对外卖国,这深深刺激着少年的杨杏佛,他逐渐养成关心社会和现实的习惯,“自十二岁起,就开始读《申报》,并经常以时事为内容与兄妹交谈”[2]1,久而久之,心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种子在其心中生根发芽。
1908年,杨杏佛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入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这所中学民主和革命氛围十分浓厚,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公学中的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都是革命党人,他们思想开放,心系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并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经常在校“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进化论观点,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宣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3]。在这些新思潮的影响下,杨杏佛不仅喜爱看《民报》,经常与同窗朱蒂煌、李骏、张奚若、任鸿隽等人探讨时事,流露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还广泛结交校内外的革命党人,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10年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8月,杨杏佛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又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继续求学。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国振奋,各地同盟会员纷纷响应。在这种情况下,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的杨杏佛同裘荣奔赴武汉,投身革命[3]。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杨杏佛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处秘书,负责收发组工作,他以高度的热情认真工作。对于新政府的成立,杨杏佛十分高兴,曾高唱:“博浪推空,嬴秦朝换。”[2]5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联合执政,内部矛盾重重,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掌权的立宪派企图通过南北议和来实现共和。作为坚定的革命派,杨杏佛坚决反对议和,但由于其力量微弱,不能阻止议和进行。南北议和后,新任总理唐绍仪到南京接收秘书处并宣布:“愿意继续为官的,可随同北上任职。”[3]37当时的杨杏佛对新政府持怀疑态度,认为恶势力实力强大,便决定放弃为官。此期的杨杏佛虽然在政治上失意,但是救国救民、报效祖国的初衷并未改变。在革命救国方案失败后,杨杏佛决定到海外留学,继续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二、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
1912年11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杨杏佛、任鸿隽等11人从上海乘“蒙古号”海轮赴美留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系统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以便将来服务于国家建设,从而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
杨杏佛当时主张科学救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受国内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科学救国思潮在中国由来已久。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开展的洋务运动,使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的重要作用。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更加重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各地创办报刊,建立学会,不断呼吁向西方学习,科学救国思潮一时之间在国内蔚然成风。在此影响下,国内出现了一些科学技术团体,如中国工业会、中华工程师会等。杨杏佛也深受这种思潮影响,认为这是一条新的救国道路。第二,国外的亲身经历。杨杏佛到达美国后,深刻认识到科技乃强国之道。他说:“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恩赐为多。世界强国,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辛焉。”[4]312反观当时的中国,科学十分落后,“国人失学之日久矣,不独治生苦寙,退比野人。即数千年来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荡然若无……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矧其在今之世耶”[4]313。中外科学的巨大反差深深刺痛了杨杏佛,他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科技,中国才能独立富强。杨杏佛说:“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4]313第三,国际形势的影响。杨杏佛到美国1年后,国际局势空前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当时他担心“一旦战事爆发,世界上的头等强国,都会把他们多年积蓄的力量拿出来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性作用。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5]2。杨杏佛认为必须将科学引入中国,并使其开花结果。
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救国”之志,1915年1月,杨杏佛与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任鸿隽等人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在美国出版《科学》月刊杂志。在创刊的第一年里,杨杏佛就先后发表《伽利略传》《牛顿传》《电学略史》《战争与科学》《学会与科学》《电灯》《瓦特传》《人事之效率》《东西厄灵辟克运动会与中国之前途》等文章,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3]38。杂志发行后不久,“社中同人便感觉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5]4。杨杏佛也认为:“忧世之士欲图学术之昌明者,其以学会为当务之急乎。”[6]由此,《科学》杂志董事会经过考虑和社员商量,于191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成立后,杨杏佛担任《科学》期刊编辑部部长,负责日常的编撰工作。杨杏佛以高度的热情和严谨认真的态度支持着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发展,为在中国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科学救国实践的不断深入,杨杏佛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宣传科学知识是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如果要彻底使中国摆脱落后的面貌,还必须大力开展实业建设,将科学知识和技术与发展实业相结合。由此,杨杏佛在思想上由单纯的科学救国变为主张实业救国,在探索救国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从科学救国到实业救国
科学与实业是相辅相成的。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杨杏佛逐渐认识到科学与实业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了能够使科学与实业真正结合,以期回国后能在发展实业方面为国效力,实现自己的实业救国之志,1916年夏,杨杏佛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在学习期间,杨杏佛十分关心国内实业的发展状况,并对国内实业进行了全面考察。针对国内实业状况,杨杏佛说:“二十年来朝野呼号,莫不以实业为救亡之本;然漏戽日甚,外货充市,旧长之商品日蹙,而新式之实业旷焉无闻。叩商人以所业损耗之轻重不能对,询当局以实业失败多寡不可得。中国将以穷蹙亡,三尺之童子能言之。欲其不亡,必振兴实业,欲振兴实业必先知过去失败之地位。”[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振兴国内实业,杨杏佛刻苦钻研,阅读了大量有关工商管理、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书籍,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提出了诸多促进国内实业发展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第一,科学、工业和商业同时发展。杨杏佛指出:“在当今世界,商业被强者恃作亡人之国的武器,要发展商业,不但要大力发展工业,而且要讲求科学的经营方法。三者具,始可称霸商业。”[2]16第二,以解决民生为根本目的。杨杏佛认为:“发展实业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办实业,就是要使人获得金钱与温饱。金钱与温饱,并不是恶物,区别仅在于是为小己,还是为国家社会。我们办实业,就是要赚钱,为民解决生计之路,使民温饱。”[2]17第三,加强宏观调控。杨杏佛强调:“发展实业,光有机械、资金不行,重要的在于加强经营管理。经营管理分为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两部分,所谓微观管理就是指厂内生产的计划性与合理调度,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或社会对整个社会的均衡原则。”[2]18第四,注重把握时机。杨杏佛十分重视发展实业的时机,他说:“读者或且以常识小之,不知吾人生计竭蹶实业之失败多由不明时间之利害……其间指挥进退枢纽成败者实此招之不来挥之不去之光阴。嗟乎!得时者昌,失时者亡,时乎!时乎!时乎云乎哉。”[8]第五,实行保护政策。杨杏佛认为实行保护政策是促进中国实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对此,他指出:“保护政策实为发达中国实业之纽而中国关税权已归外人掌握,吾人虽欲奋发恐不免为纸上空谈。曰不然,开税不过为庚子赔款之抵押品。欧战告终吾人果能屹立不辱,则收回关税权当非难事。即或不能实行保护政策,果政府人民并力以赴实业,以全国之力经营之,列强虽能充货吾市,不能强吾人买之也,一言以蔽之,中国实业而欲以独作时代兴也,必实行保护政策为闭门修养之计。”[9]
1918年夏,杨杏佛在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正式毕业。1918年10月,怀着实业救国之梦,杨杏佛同赵志道、任鸿隽等人一起回国。回国后,杨杏佛为了尽快将自己的实业救国之志付诸实践,决定与任鸿隽、周仁等人合资创办工厂,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未能如愿。同年11月,杨杏佛在上海青年会干事徐可叔的介绍下,准备到汉阳铁厂工作。他认为到汉阳铁厂工作既可以解决生计需要,同时又可以将自己多年的实业救国之志付诸实践。杨杏佛乐观地认为,只要认真研究中国的旧实业和劳动者的现状,然后再改善经营管理,中国的实业一定可以振兴。但是现实的状况与他心中所想大相径庭。在汉阳铁厂工作期间,杨杏佛经历了遭人猜忌与排挤,感受到了工业界上层领导人道德的沦丧,目睹了因铁轨常年失修、铁厂工人缺乏机械知识和安全意识而造成人员伤亡的惨剧。残酷的现实不断冲击着杨杏佛,使其对中国实业的实际状况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经过对中国实业现实状况的全面考察,杨杏佛认为其发展艰难同三个方面因素密切相关。第一,实业学生之预备难。第二,实业界之人事难。主要包括“资本与人才不相联络、新旧实业相隔膜、兴实业者重感情不重实业、实业界依赖名流太重”[10]等。第三,实业界的境地难。具体表现为“政治不宁、政治时以实业借债、军人与盗贼蹂踊、外人竞争剧烈,无国家保护、无统计事业以及原料机械难得”[10]等。在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中,杨杏佛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缺乏实业人才。对此,杨杏佛指出,仅仅依靠留学归来没有充分实践的学生,中国的实业是不会振兴的,只有培养中国自己的实业人才,摆脱靠外国培养的老路,中国的实业才能迅速发展。杨杏佛说:“吾国实业界未尝一日栽培陶其实业学生,徒恃学生数年异国教育便望其建业成功,难矣。”[10]
残酷的现实使杨杏佛多年的实业救国之梦化为泡影,在全面反思的同时,他又深刻认识到培养本国实业人才的重要性。由此,杨杏佛在思想上逐渐向教育救国转变,在救国道路上再一次实现了重大转折。
四、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
1919年8月,杨杏佛辞去汉阳铁厂会计处副处长之职,9月,在郭秉文的邀请下,到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担任商科教授,正式开始了长达5年的教学实践。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改为东南大学,杨杏佛又先后担任商科主任和工科教授。
在5年的教学生涯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之志,杨杏佛以“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为工作中心,专心致志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就“如何利用教育达到救国”这个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具特色的见解。首先,要进行教育改革。杨杏佛对民国以来的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指出当时的教育界浮夸之风盛行,教育家将学生人数和教学经费的多寡作为衡量教育发展好坏的标准,表现出强烈的商业化特征。对此,杨杏佛说:“学校之人数俞多,而人格越低,学校之经费俞增而学术思想之成绩俞劣。民国十四年以来教育界所造就者何物,新绅阀新市侩新游民而已。”[11]100杨杏佛还认为教育发展的好坏对政治和学术影响甚大,强调:“今日政治之混乱其原因首在缺乏高洁之人格,而造成此高洁人格之责任,惟超然于利禄竞争之教育界能之。苟教育界亦惟势利是逐,师徒日熏陶捧督拜金主义,风气所趋不廉夫顽者鲜矣。故今之教育苟不改革,则中国之政治与学术,必皆商业化,昔人所鄙薄之市侩且将为中国之惟一模范矣。”[11]102因此,必须“从教育革命始,惟民众化与学者化之教育乃可产生高洁之公民与学者”[11]103。其次,整顿学风和教风。杨杏佛进入教育界后,感受到学风和教风的败坏。对于学风,他说:“今之学风,浮嚣鄙陋,苟且依赖。势力所在,甘为私人之走狗,暴力可凭,污辱师长如狱囚,认富贵为道德,以谄媚为才能。在校则百计猎学分,乞文凭。出校则百计谋饭碗固地盘,而美其名曰奔走社会,注重职业。”[11]105-106这样的学风使在校大学生“思想竟不能自主,行动需人监视,乃至区区请人讲演之别力亦无之”[11]106。杨杏佛指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学生,而在自命人师负百年树人大任之教职员——校董校长与一切教职员”[11]106-107。当时的教职员“闻学生之不幸而有得色,甚且乘其创痛之余,为劫持报复之计”[11]107。因此,“欲整顿学风,当先从整顿教风始”[11]109。对于如何整顿教风,杨杏佛提出了三种方法:“第一,为师者当确立主张,予学生与社会与共见;第二,当言行始终一致,不因人我利害而异;第三,当以廉洁刻苦之生活,不屈不挠之气节,立力学为人之基础。”[11]110-111为了从根本上达到整顿之效果,杨杏佛呼吁:“世之为父兄师长者,亦有念国事之日非,青年告,起而努力整顿教风,改造教育,为国家留一线生机,为社会留一份正气者乎。”[11]111-112最后,普及工业教育。在多年的实业实践中,杨杏佛深刻认识到对工人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虽然有工业教育,但是“其数极少,其效极微”[11]121。杨杏佛认为长此以往,必定会对国家带来巨大危害。他说:“工寙陋则出品安得精良?成本安得轻减?直接受其影响者,工人自身与工业,而间接受其影响者,则全国之人也……其影响所及:从积极言,聚无教育之民,必不能成富强之国,而种且日以退化;从消极言,生活艰辛,则无生趣,怨恨之心以生,堕落之行不免,一旦有事,或且流于盗贼遇激之途,其影响不仅及于工人自身也。”[11]123因此,杨杏佛极力主张“工人教育不能忽视”,但普及工人教育不能依靠政府,最好的方式是向工业界寻求帮助。杨杏佛认为工业界“若出资以训练其本厂之工人,则凡具有远大眼光之资本家,必愿为之,此可乐观者也”[11]127。此外,杨杏佛还介绍了训练工人的5种方法并制定了成人工业教育计划15条,详细说明了普及工人教育的方法。杨杏佛坚信:“教育今日之工人,收效即在目前。果使工人教育普及,则渥温之自治工厂,摩吕斯之文雅工人不难实现于中国。吾方梦此境,亦愿吾国之工业家同为此梦。语云有志者事竟成,是在吾工业先觉与教育家之努力为之耳。”[11]136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杨杏佛不仅关注教育,还热衷于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杨杏佛多次在公开场合宣传社会改造思想,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与共产党人密切交往,这些都引起了当时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强烈不满,他与杨杏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1924年夏,郭秉文以江苏省财政困难、学校经费不足为由,在没有征得工科主任茅以升同意的情况下,下令停办工科,迫使杨杏佛离校。多年的教育救国实践收效甚微,杨杏佛反思后认为,仅仅依靠教育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杨杏佛说:“故就今日之中国情势言,多一教育家,即多一寄生虫,徒增农工界之负担,而无补于国事。”[12]2教育救国之所以收效甚微,杨杏佛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与政治相分离。他指出:“今之投身教育实业者,大抵皆一国最优秀之分子,其志则鄙政治而不为,又不愿任改革之责,其力则藉教育实业为保障,足以糊口安心,武人政客之黠者知其不能为祸,且足以消磨反抗人材,亦虚与委蛇以博贤名,而教育实业遂成为中国超治乱无是非之特殊社会……而此中立之教育与实业,且作壁上观,中华民国之祸乱,又安得而不延长至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哉?”[12]9由此,杨杏佛认为要想救国,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以良政府为先”[12]10。但是,当时的中国军阀当政,南北分裂,从现实国情出发,杨杏佛认为要想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必须首先推翻军阀政府,恢复秩序。他强调:“今日救亡之最急者莫过恢复秩序,欲恢复秩序当首去军阀,然去军阀而以武力,当其进行,人民以不胜蹂躏之苦,幸而成功又不免以暴易暴之患,况中国之大,外人干涉之严,武力统一殆无幸成之理。”[12]12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杨杏佛“抛弃苟全乱世之教读生活,恢复十年前之国民革命之生活”[3]。
五、再次回归革命救国
1924年10月,杨杏佛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再次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到达广州之初,杨杏佛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于11月随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孙中山逝世后,杨杏佛毫不动摇地继续着孙中山未完成的事业,为推动国民大革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这一时期,杨杏佛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自己之前的实践经历,对“如何实现革命救国”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就革命救国的具体实现路径,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第一,实行国共合作。杨杏佛始终坚持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杨杏佛认为实行国共合作是挽救国家和民族的良方,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强大力量。对此,他指出:“由于国共合作,全上海人民团结起来了,全国人民也开始大团结,这样,北伐战争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胜利。不久,不但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可以实现,而且人民可以享和平、民主与幸福的生活。”[13]125第二,广泛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在长期的实践中,杨杏佛深刻认识到要想取得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在国内,要发动全国民众。杨杏佛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是分散的。国民革命的成功,惟有全国民众参加方能实现。”[14]37在国际上,要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他指出:“中国是国际的,中国革命也是国际的,我们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力量有限,如何能不联络其他被压迫民族与同情于民族解放的各国革命分子呢?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政府和人民固然是我们的好友,帝国主义的国家中被压迫阶级与革命份子也是我们的好友。”[14]41为了联合这些力量,杨杏佛呼吁:“一切被压迫的省民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14]41第三,加强对革命者的道德和人格修养。杨杏佛不仅强调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还认识到革命者的道德人格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我们国内的知识界有的人没有人格。他们是富贵可淫,贫贱可移,威武可屈。他们对于农工阶级,都不把他们当成人看待。一个人材,应该是思想、身体、道德完全的人材。一面要有真正的学问,一面要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假如我们四万万人都有人格,有知识,齐喊一声取消不平等条约,他们外国人敢持异议么!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加倍用功读书,加倍用功救国,把自己造成完善的人才来为社会服务。”[2]59第四,科学与革命相结合。科学救国是杨杏佛曾经实践过的救国途径,但多年的实践并未收到成效。到国民大革命时期,随着杨杏佛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入,逐渐认识到科学之所以未在中国开花结果,主要“是因为科学家与革命家分道扬镳的缘故”[15]69。杨杏佛强调:“改革社会,为人类谋幸福,不仅是革命问题,必须有科学知识,看出社会的弊病,搜集人类的切身问题,经过几番的研究,精细的考虑,再依照自然的程序去改革,才可得着最后的好果。”[15]74由此,杨杏佛主张惟有科学与革命合作才是救国的正确方法,即“革命家须有科学的知识,科学家须有革命的精神,用科学的知识,革命的精神,精细的研究来计划一个理想的中国,这个理想的中国,要适合世界的潮流。那么依照所定的步骤,怎样去打倒军阀,怎样去打倒帝国主义,庶几可以达到最后之目的”[15]76-77。
对于这些革命救国主张,杨杏佛将其付诸实践。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杏佛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其目的是“以孙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为国人之柞鼓晨钟明灯木铎”[16]191。在报刊社论中,杨杏佛猛烈抨击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号召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民族日报》的创办,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9月,上海总工会纪念“九七国耻”,杨杏佛上台演讲,号召“民众牢记24年前清政府屈服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的耻辱,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3]。为了救济在五卅运动中牺牲的民众家属及其受伤者,杨杏佛与沈泽民、沈雁冰、张闻天等共产党员发起中国济难会,后又当选为该会的审查委员,并说明该会成立的宗旨在于“同情于为民族解放之人,而予意尤当注意农工”[3]。1926年1月,国共合作建立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杨杏佛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担任执行委员并兼任宣传委员,具体负责对北伐军的策应工作。北伐期间,为了配合北伐军,秘密传送情报,杨杏佛在孙中山葬事筹备处设立电台。由于被孙传芳侦破,杨杏佛被逮捕,在好友郑毓秀的解救下才幸免于难。被释放后,杨杏佛又在法租界华龙路法国公园建立电台与北伐军继续联系。1927年1月,北伐军攻入浙江后,为了配合其夺取上海,杨杏佛主动联系中共上海区委,要求与工人纠察队一同行动。192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杨杏佛作为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代表参加起义前召开的国共联席会议,并对这次起义给予全力支持。起义胜利后,杨杏佛当选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委员。杨杏佛这种鲜明的革命立场和为国民大革命做出的贡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高度赞扬。巴黎《救国时报》发表评论说:“杨杏佛先生在当时协调国共关系上尽很大努力,实为有功于上海起义之人物。这样效忠于民族解放的实业,效忠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不畏强暴,不畏牺牲的精神,真可谓一切民族革命者的楷模。”[3]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以及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的建立,给杨杏佛以巨大鼓舞,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前途乐观,在不久的将来,自己的革命救国之志便会实现。但是现实的情况与他的所想截然相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量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被杀害。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杨杏佛以中国济难会的名义积极营救被捕的革命者。但他的这一系列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憎恨。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陈立夫和陈果夫到上海主持党政,他们罢免了杨杏佛在上海市党部的职务并将其逮捕准备枪决,后在好友郭泰祺的营救下才幸免于难。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使杨杏佛多年的革命救国之梦再度破灭,其心情异常苦闷。在经历了短暂的挫折之后,杨杏佛又重新振作,一面为孙中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奋斗,一面继续探索行之有效的救国救民之道。
六、从革命救国到中间路线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杨杏佛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革命的前途现在依然是很黑暗,中国民众仍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切做官发财谋事吃饭的机会虽然日日减少,但是革命牺牲杀身成仁的机会却日日增多。”[17]49在杨杏佛看来,救国救民依然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但是,当时的杨杏佛由于受阶级立场、党派利益的限制以及蒋介石反共宣传的影响,在思想上逐渐右倾,在救国救民上逐渐转向短暂的反动,将合作多年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并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走上了扶蒋反共的道路。杨杏佛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认为真正能够救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杨杏佛热衷于国共合作,认为当时容共“是想共产党加入本党信仰三民主义,使他们知道本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党,而放弃共产的思想”[18]。然而,现实的发展与杨杏佛所想大相径庭,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被国民党同化,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并对国民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杨杏佛一度认为:“共党在本党阴谋捣乱破坏本党,破坏国民革命,我们的反共,也是一点都不错的……现在本党虽然已经把共党分子清除出去,但是清党的工作,是没有终止的,我们要一期一期的清党,才能保持本党的青年性,才不至趋于腐化。”[18]因此,无论从阶级立场出发,还是从党派利益来看,杨杏佛选择扶蒋反共都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使国民党腐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清党只是保持国民党纯洁性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杨杏佛认为还要将国民党内的投机腐化分子清除,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党内的团结,激发每一个党员的革命性,继续着孙中山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才能彻底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从而到达救国救民的目的。
这时的杨杏佛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寄予很高的期望,期待着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但是,残酷的现实再一次与他的期盼截然相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蒋介石政权不但妥协退让,还镇压国内民众的反帝抗日宣传运动,大肆迫害革命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为了加强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在党内排除异己,不断发动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和反共战争,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31年6月,杨杏佛随蒋介石到江西对红军的真实状况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国内各个党派的不同政见与民族存亡的问题相比,均为小事,各个党派应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蒋氏政权的作为和对红军的考察使杨杏佛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并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逐渐认识到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失去了革命性,成了为蒋氏个人独裁服务的私人政党。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暗杀于上海,这使杨杏佛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政权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质,并最终抛弃对蒋介石政府的幻想,重新思考救国救民之路。杨杏佛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政体的愿望与当时国内中间路线思想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由此,杨杏佛便逐渐走上了国共以外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
杨杏佛走上第三条道路后,积极联合宋庆龄、蔡元培、史量才等社会知名人士,为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争取国内民主和自由,营救被捕革命者和政治犯,动员国内民众抗日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7月,杨杏佛与宋庆龄、斯诺等人组织营救牛兰夫妇委员会,积极营救被国民政府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而逮捕的牛兰夫妇,在他们的努力和担保下,牛兰夫妇才被允许就医进食。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杨杏佛、蔡元培、林语堂等人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对其进行释放。为了使营救革命者、争取民主和自由等工作更加系统化,杨杏佛、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在上海联合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和执行委员,并负责同盟中的实际工作。同盟成立后,杨杏佛以顽强的精神和卓越的组织能力,领导同盟成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33年1月,杨杏佛代表同盟总部在北平建立分会,并积极营救被关押在北平的政治犯。3月,同盟联合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等团体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杨杏佛作为代表阐述了“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以及释放政治犯联合的重要性。”会后,他还积极为自救会购买武器,以实际行动支持自救会的工作。1933年4月,杨杏佛、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杨杏佛到南京同汪精卫等人谈判,要求释放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藻英等革命者。5月,杨杏佛、蔡元培和宋庆龄又亲自到上海德国领事馆抗议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他们指出:“本同盟认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动,不特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自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2]93此举表面是在抗议德国的法西斯专政,实则是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抨击。他们还联名致电汪精卫和罗文干,要求释放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作家丁玲、潘梓年等人。
杨杏佛的这一系列行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和践踏人权的罪行。对于进步力量来说,给予他们以重大鼓舞,对于反动当局来说,则引起了他们的仇恨。为了阻止杨杏佛的活动,蒋介石多次派特务对其威胁恐吓,但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以顽强的精神继续斗争。1933年6月15日,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发出秘密通告,派遣特务暗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杨杏佛、鲁迅等均在此名单之列”[19]。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于“中央研究院”附近,年仅40岁的他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杨杏佛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大历史阶段,面对近代中国日益严重的国难,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担当积极投入到救亡第一线,将自己的所学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救国思想,并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将其发展完善,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将其付诸实践。虽然受阶级属性和党派利益的局限,杨杏佛的各种救国方案并未真正实现,他的思想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现了短暂倒退,但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坚信民主和科学,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同进步力量团结协作,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