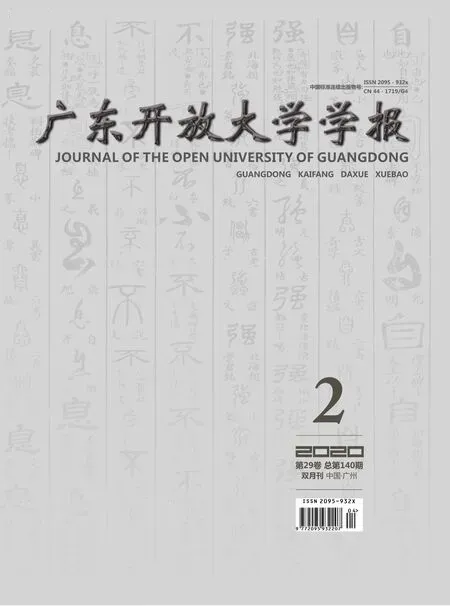论唐五代小说中表文的类型及其功能
何亮 陈丹丹
(1.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10333;2.广东开放大学,广东广州,510091)
表作为公牍文的一大类,常采取以情动人的方式写作,“表以陈情”,表现出较强的文学性特征。表文有特定的功能,主要用于下级向上级进言。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曰:“下言于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1]关于其缘起,较为复杂。《文选·卷三十七·表上》李善注曰:“三王已前,谓之敷奏。故《尚书》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为表。总有四品:一曰章,谢恩曰章;二曰表,陈事曰表;三曰奏,劾验政事曰奏;四曰驳,推覆平论,有异事进之曰驳。六国及秦、汉兼谓之上书,行此五事。至汉、魏以来,都曰表。进之天子称表,进诸候称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2]秦朝以前,献上之言统称“敷奏”。秦朝建立后,改称为“表”。正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所言:“三代以前,谓之敷奏。秦改曰表。汉因之。”[3]汉魏六朝、秦时,下级进呈给上级的公文还可称“上书”。汉魏以后,进献给天子的公文才称为表,进献给诸侯的则称之为“上疏”,“表”用于帝王的专属身份得以确立。表根据使用的场合和目的,可分成进献表、庆贺表、谢恩表、请求表、谏论表、遗表与陈情表等多种类别。且其功能随着时代发展,有一定变化①表文始于汉代,是大臣向皇帝陈述事情的文书。唐宋以来,仅限于陈谢、庆贺、进献所用。元代时,庆贺表文称为表章,每遇皇帝生日、元旦,五品以上官员皆上表章进贺。明代庆贺文书除表文以外,增加笺文一项,表针对皇帝和皇太后,笺针对皇后。清代表文制度沿袭明制。清代表文有两项功能:一作庆贺之用。遇有庆典,如登基、传位、册立皇后、上尊号等,王公百官均上表庆贺。二作进献修史之用。史书修成,须由总裁官具表进呈;当年考取的文武进士,也要呈表谢恩。此外,属国表文是清代表文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贡上行文书中的主要体裁,主要功能为庆贺、请封、谢恩、进贡等。(见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4页。)可见,表文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融入唐五代小说中的表文,类型相对简单,主要有请求表、陈政表和谢表三种;使用功能却比较丰富,可以自荐、推荐他人,也可以陈政、申诉冤情、请求官职、说情。表文渗入唐五代小说,一方面增强了其文学性特征,另一方面与政治、现实相结合,扩大了题材范围,使作品表现出“有补世用”的世俗性和功利性。
一、请求表:自荐、推荐他人或说情
唐五代时期,随着《大唐开元礼》的编撰、颁布,以及公文自身发展的进一步完善,公务文书的格式也更加规范,更加符合礼制。当臣子有所请求时,用合乎典制的表文将下情上达。此类型的表文可称之为请求表。《全唐文》汇集了诸多相关表文。如卷一百六十九狄仁杰写给武则天的“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臣欲闻奏,似为逆人论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非其本心,愿矜其诖误”[4],虽寥寥数语,恳求则天皇帝饶恕因李冲叛乱事遭受牵连的六百名无辜百姓的意图却十分明晰,充分展示了狄仁杰为官的风范,以及高超的文字艺术技巧。唐五代小说中也出现了不少请求表,主要作用为自荐、推荐他人或说情。
自荐的文化传统古已有之。战国时期,毛遂在赵国风雨飘摇且人才匮乏之际主动请缨,帮助赵国成功突围,成为历史上的美谈;西汉时期,东方朔深知汉武帝继位之初,急需招纳有才之士,凭《上书自荐》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5],“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6]。唐五代小说中自荐的表文,不是为自己谋求官职,而是代人受过,为其鸣冤,与用于政治现实的表文截然不同。如康骈《剧谈录》卷下“刘相国宅”,萧相为蒙受不公正待遇的刘相国鸣不平,请求外派代替相国出镇荆南。小说只截取了表文部分内容,“正人吞声而扼腕,百姓掩泪于道途”[7],百姓、正义之士对刘相国调任深表愤懑。表文以自荐的形式变相为刘相国申诉。小说中的刘相国为历史上的清廉名臣刘瞻。史书关于其一心为国的记载颇多。康骈《剧谈录》中的表文从侧面烘托了他在当时民间、官场的政绩和声誉。
除了自荐,有才之士获得赏识的另一重要途径就是由他人代为举荐。举荐才士是朝廷选拔、任用人才的途径之一。大历年间,皇帝颁布了“令州府观察等表荐贤才诏”,希望各级官员举荐才士,“内外文武官,及前资官六品已下……仰所在州府观察牧宰,精求表荐”[8]。《全唐文》载录了举荐他人的表文,如柳宗元“为王户部荐李谅表”、“奏荐从事表”等。唐五代小说中也有不少篇目涉及推荐他人的题材,故事人物以表这种形式“推销自己赏识之人”。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条,张祜与令狐文公交好,曾经将平时撰写的新旧诗歌三百首与自荐表一起进献,表文内容如下:“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9]张祜上表文采平淡,没有突出自己所献诗歌的特点,也没有阐述自己的政治远见。元稹对其评价不高,最后以失败告终。张祜是有真才实学的。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对张祜进行了介绍:“张祜,字承吉,南阳人,来寓姑苏。乐高尚,称处士。骚情雅思,凡知己者悉当时英杰,然不业程文。”[10]张祜不善于程式化的公案文章,不被有些官员看重自在情理之中。
表文可以举荐,也可以对被举荐之人提出反对意见。唐五代时期的士子,即使才华满腹,掌握其命运的,还是那些政治家。小说对决定士子前途表文内容的披露,从另一层面展现了唐代科举制度以及官场的风貌。
表文还可以请求皇帝委派得力助手,协助处理政事。如《南柯太守传》,南柯上表请求天帝赏赐辅佐的大臣,“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11]。南柯慧眼识英才,与诸位贤臣将南柯郡治理得有声有色,由此而任太守二十余年,甚有政绩,大受宠任。
唐五代小说中的表文可用于臣子与现实中的皇帝,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也可以用于凡人与神仙世界的天帝、仙臣与天帝王,如《南柯太守传》。天界一如人间,典章制度以及行文规范通用。神仙世界只是人间世界的缩影,是小说家以“曲笔”创设出来的另一个人间。唐五代小说中向皇帝请求的表文,撰写人的态度都谦虚、恭敬,文风畅达、凝练,时时刻刻考虑到了皇帝与臣子应该讲究的礼仪。相较于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文,举荐他人的表文较多。举荐人为官必须实事求是,朝廷也有相关程序、规定,不能因个人情感、喜好胡乱举荐。周广顺元年夏五月曾下诏“禁滥荐敕”,“朝廷设爵命官,求贤取士……是以国无幸民,士无滥进”[12],身处朝堂,举荐人才都十分小心,因此,流传于世的举荐表相对较少,亡人逝后要求追赠官职的却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为,替逝者追赠官职符合朝廷典制,举荐人相对来说风险较小。而小说中举荐他人,纯属小说家的主观意愿,对现实并不造成任何影响,因此,唐五代小说中频频出现请求举荐官职的表文。另外,小说中的表文受小说家本人的文学素养,及公文撰写水平影响,表文的质量良莠不齐。而在现实中臣子给皇帝的上表,都经过深思熟虑,艺术成熟,思考问题更为缜密。要知道,表文写得不好,惹恼了帝王,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历史上因上表不称皇帝心意而被杀头的大有人在。整体而言,唐五代小说中的请求表,在艺术价值有限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中,篇幅简短,语言质朴,而传奇小说中则语辞繁富、华赡,讲究韵律之美,表现出骈偶化倾向。
二、陈政表:陈述政见或申诉冤情
上表事关士子、官员仕途,甚至性命,符合皇帝心意,就可能获得官职的升迁,否则将招来杀身之祸。朝堂上,面对皇帝质疑,及国家面临的困境,不置可否虽能守住官位,毕竟在其位食其禄得奉其事。许多公正廉明、忠心为国的大臣写下了不少表达政见,解决治国弊端的表文。如《全唐文》“论时事表”,李纲上表唐高祖,无所顾忌地指责其骄奢淫逸,并列出朝政的腐败,“臣伏见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负太平……而陛下不悟政教日颓,在内不许论事,当朝略无谏者”[13]。家人蒙受冤屈,无奈之下,只能诉诸权利的最高主宰皇帝。如《全唐文》卷二百六十“请代父死表”,父亲被人诬陷,儿子为父亲鸣冤代为受过,“臣闻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恩,昊天罔极。臣父文成充使特置严刑,罪小责深,不胜冤苦……即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不任酷裂之至,冒死投匦以闻”[14]。陈政表文学色彩突出,情感鲜明,撰写人以质朴的语言表达真挚的情愫,打动人心。其文学性特征与唐五代小说刚好相契合,唐五代小说移植此类表文于作品,以之或劝诫皇帝,或申诉冤情,或传达对其他官宦的看法。
天庭可掌管世间芸芸众生。当人世纷争时,天上的官员向王母陈述了处理的策略。如李玫《纂异记·嵩岳嫁女》,李君上表汇报了处理歼灭逆党的办法,“某县某,克构丕华,德洽兆庶……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氓,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15],李君平定战乱的方式为“以暴制暴”,让天降灾祸扰乱人间,人间大乱,逆党自然就容易清除。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令人不得不深思人命在统治者心中的意义。他们关注的只是镇压逆贼,老百姓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小说通过天上神仙李君上表解决人间战乱之事,影射当时统治者的草菅人命。
唐五代时期,因相对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出现了许多敢于批龙鳞、逆圣听的臣子。他们一身正气,指陈时弊。这一情况,在唐五代小说中也有体现。唐五代小说中的表文,言辞更加激切、尖锐,臣子的耿直也更加凸显。如《王氏见闻录》,此书的作者王仁裕历仕五代。“王承休”为其中篇幅最长的作品,融入的表文等公牍文数量也比较多。在这篇小说中,忠臣蒲禹卿针对蜀国出游一事,用表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展现了那段时期朝政的内外交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戒慎之靼……今去洛京不远,复闻大驾重来,若彼预有计谋,此则便颏征讨。况凤翔久为进敌,必贮奸谋;切虑妄构妖词,致生衅隙。”[16]上表陈述政见,起笔喜欢将古往今来的明君与当朝国君进行比较,蒲禹卿也遵从了惯例。接着,追溯先帝创业立国的艰辛,言外之意,蜀君王衍应该励精图治,守住先帝建立的基业。接着表文从正面阐释上表的意图,王衍不能东巡。最后,以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为证,告诫后主应勤于自励。最后,结尾之处再次请求蜀主放弃东巡之举。全文气势磅礴,针对王衍东巡一事,正反对比论证,言辞恳切,为表文中的上乘之作,被《全唐文》卷一百四十、《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收录。通过这篇表文,形象、生动地刻画了蒲禹卿的忠臣形象,为了解那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可贵资料,尤其是关于古蜀国的研究资料。又如张鷟《朝野佥载》卷六,王求礼对武则天宠幸的冯小宝经常出入宫闱深表不满,为严肃宫规,上表提出解决之策:“太宗时,罗黑能弹琵琶,遂阉为给使,以教宫人。今陛下要怀义入内,臣请阉之,庶宫闱不乱。”[17]求礼以太宗为留住宠臣将之阉割旧事,建议武则天让薛怀义变成阉人。武则天宠爱男色,《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八有记载:“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18],右补阙朱敬的谏言就提及薛怀义:“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19]。武则天男宠过多,以致大臣上言讽谏。武则天丑事暴露,为留住接纳忠言的美名、笼络人心,厚赏朱敬。小说对此段宫廷事件的记载,与正史有一定区别。史书中的谏言,相对比较委婉,而小说中的就比较尖锐。王求礼明明知道武则天宠幸冯小宝的真正原因,反而要求将之变成阉人,此情节也只能出现于小说了。
表文陈述政见的另一形式,就是为民或者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官员申诉冤情。《桂林风土记》“张鷟”条,姚元崇担任宰相时,诬陷张鷟曾经在江南受贿。张鷟的儿子、黄门侍郎张廷珪、刑部尚书李白等正义之士,纷纷上表为其鸣冤:“其子上表,请代父死。黄门侍郎张廷珪、刑部尚书李白等连表称冤”[20],鸣冤虽然起了效果,张鷟减去了死罪,但仍然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关于此事,张鷟《陈情表》可印证:“臣忝朝班,幸蒙驱策,不了一使,罪应至死。”[21]《桂林风土记》所言张鷟流岭南事当真实可信。通过小说的记载,被称为“青钱学士”、享誉海内外的张鷟,也会受人陷害下狱,宦海风波的险恶由此可见。
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指出:“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22]表用于实际的本来意义,即臣子将内心的想法准确、得体地传达给皇帝。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指出:“表者,标也,明也。标著事绪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23]表的语意必须清晰,用词准确、措辞明了,才能将下情有效上达。“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24]表是下级进呈给上级的文字,注重礼仪之邦的中国古代,文字的运用对此也要有所体现。唐五代小说中陈述政见的表文,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一点。有些表文虽不见于当时史料之记载,与史书中的其他事件可相互印证,有助于对史实的进一步考证。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很多人物、事件,都是无可查询的。相应地,小说中的表文有可能只是小说家满腔报国之志的抒发,也有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时效性不强,对现实的意义有限。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上呈给皇帝的表文,如权德舆“论旱灾表”,从稳定封建统治的角度及时提出解决旱灾的5条建议;崔行功“论时政表”,劝阻皇帝让后宫干预政事,都是针对朝廷所面临的窘迫问题生发,关涉面很广。表文的长短,以及所言之事,由朝政的需要所决定。而唐五代小说中的表文,更多的是出于小说叙述故事的需要,其时效性及对实际的意义并不是小说家所关注的重心。
三、谢表:祝贺、致谢或辞谢
皇帝虽位居高位,剥去威严的面纱,也只是凡人。皇家也有婚姻嫁娶、生辰寿诞等喜庆之事。作为天子的大臣,皇家举办喜宴,是表白忠心的绝佳时机,皇帝也通过此方式笼络大臣,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天下出现所谓的祥瑞之兆或者国泰民安时,大臣也纷纷上表,向皇帝道贺。不过,由于皇帝的身份特殊,贺表多是溢美之词。如陈元光“漳州刺史谢表”,“伏奉垂拱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制……展驽骀之力,申鹰犬之劳,庶荒陬蛮僚,尽沐皇风;率土生灵,尽闻斯庆。臣无任感恩,不胜陨越之至。谨奉表以闻”[25],对皇帝的知遇之恩表示感谢。久处政治的漩涡,深感不安,借生病之际辞官,如许远“辞疾让官表”:“臣自去月十七日旧疾发动,有加无瘳。至今月五日,臣自量气力,恐至不起,谨忍死口占,陈露上闻……并令恭守所职,伏听进止。仰天沥恳,诚切气微,免首呜咽,申吐不尽。不胜哀迫痛恋之至。”[26]唐五代小说中也有此类表文,上表的用意、行文方式、语言等与史传的表文相似。
如《杨太真外传》①有些研究者将《杨太真外传》归入宋代,而《全唐五代小说》将之归属为五代,本文从其说。,开元年间,唐玄宗将江陵进贡的柑子移植到蓬莱宫种植,没想到不仅成熟,而且硕果累累。玄宗赏赐给大臣,宰臣上表道贺:“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旷古所无者,乃可谓非常之感。是知圣人御物,以元气布和……故兹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佳实。绿蒂含霜,芳流绮殿,金衣烂日,色丽彤庭。云矣。”表文用四六相间的骈体,阿谀唐玄宗的圣明让本不能在北方种植的柑子开花结果。
佚名《灯下闲谈·梦与神交》,采用志怪小说常见的“梦幻题材”,以“入梦”的形式将冥间、现实世界相连,落第书生史松代冥王撰写了一份感谢天帝的表:“右臣闻生为国珍,殁当庙食,前文备载,往哲所标。苟非正直以流芳,曷得蒸尝而受享。臣名传史籍,威袭遐陬,佐汉之功业炳然,在楚之明灵著矣……中谢臣谨者别行阴鸷,围护封陲。使一州无鼠窃狗偷,保三楚常风调雨顺,遇过乞而专行戮剿,逢公忠而敦固行藏。自然上答穹灵,不负封册,云云。”[27]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虽然为贫寒士子提供了仕进之路,考中科举的人却很少。根据徐松《登科记考》等史料文献记载,每年录取的也就几十名,其中托关系、说情、请人代考等现象时常发生,世家大族子弟占录取人数较大比重。史松的表文引经据典,其实恢弘,词藻华美。即使才华横溢,深得冥王、天帝赏识,却未能通过科考。《梦与神交》以幻笔描写现实,便于叙说不能直接言说的内容,同时也给接受者留下思考、再创造的空间。
不愿接受皇帝赏赐,臣民可以表谢绝。李玫《纂异记·徐玄之》马知玄的儿子蜓诣宫门进表,“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千之忠贞,有魏中尉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已,昧于知人……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冒国家之宠荣。报平王既非本心,劝伯禹亦非素志。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蜓上表是为了辞谢,为了避免惹怒皇帝,以“伏奉恩制云”起首,格式规范。升官本是一件喜事,蜓却加以拒绝。他的理由很充分,亡父一身正气,不能以亡父的冤死获得官位。另从天象来看,国家即将倾覆,官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后来,蚍蜉国的命运果如表文所预言。
综上所述,表作为一种上行公文,风格典雅,写作格式严谨、规范。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上表,表文必须清晰明白地体现自己的意图。东汉蔡邕《独断》详述了表的写作格式、文体功用:“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口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囊盛。”[28]表文不像奏、章等公文,形式相对自由。内容可长可短,视言说内容而定。如果涉及事件比较机密,为防止泄密,必须用帛囊密封。李充《翰林论》现存辑佚涉及“表”时特别指出:“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29]表文无需华丽的辞藻,实用性置于首位。而刘勰《文心雕龙》却强调文采对于表文的重要性:“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30]表进呈给皇帝,吐露心声、阐述政见时,既需要展示个人才华,也要体现个人风骨。“骨”、“采”兼顾的观念,影响了唐五代时期表文的制作。唐五代小说中的表文,很多都为士子精心结撰之作,即使从小说文本独立,也是一篇精美绝伦的佳作。《全唐文》中收录的不少表文,就源自唐五代小说。表文融入唐五代小说,呈现出阶段性严谨特征。唐初小说的表文数量较少,文字相对质朴;中晚唐,尤其是五代,表文数量逐渐增多,篇幅也明显变长。与此时期国家陷于危难动荡,政治题材不断涌现相关。唐五代小说家很多为朝廷官员,有些甚至身居要职。他们以小说描写现实,“补史之阙”,希望给统治者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