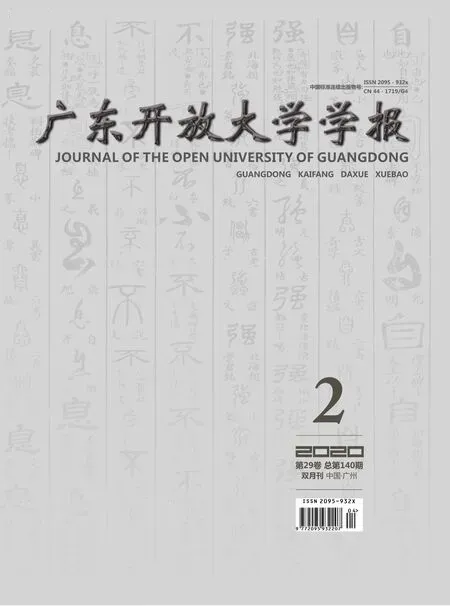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的女性叙事研究
朱立华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134)
“艺术修女”(Nun of Art)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勃朗宁夫人、乔治·艾略特、爱米丽·勃朗蒂、菲莉西亚·赫曼斯、迈克尔·菲尔德、罗莎蒙德·华生、阿德莱德·普罗克特、弗吉尼亚·缪以及伊丽莎白·西德尔等一样,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诗坛的主要女性诗人,也是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诗人的主要成员,其诗歌之中体现出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怀、女性的“现代性焦虑”以及女性的自律、反省和救赎等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创作诗歌的时候,女性主义初露端倪,因此她算不上一位女性主义作家或女性主义理论家。然而,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克里斯蒂娜开始关注女性问题,她的诗歌之中已体现出女性主义特征,或女性问题意识。克里斯蒂娜所创作的千余首诗歌中大概有两百多首,是以女性作为叙事对象,或建构以女性为创作对象的女性形象,或分析女性传统角色定位和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形象扁平化、边缘化的状态,或描述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女性勇敢反抗男权的女性形象,或讲述女性对于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即女性的“性自主权”,或揭示女性在叙事中处于“被描写”的状态等,通过女性叙事模式,表达克里斯蒂娜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和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道德的关注,其诗歌体现出女性主义的诗学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几首女性叙事诗《小妖集市》《王子的历程》《爱情三重唱》和《少女之歌》等,通过女性书写来表达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一、女性叙事的理论缘起与流变
20世纪末,苏珊·兰瑟(Susan Lancer)等学者将女性主义批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了女性叙事理论与女性叙事模式。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叙事)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随着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兴起和叙事学的发轫,兰瑟等学者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关联。由于接受了女性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兰瑟在1981年出版了其著作《叙事行为:散文性小说视角》(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探讨了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批评实践。1986年她又在《文体》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该论文首次使用“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narratology)这一术语,提出该理论模式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结合起来研究,奠定了女性叙事的基础。之后,兰瑟又出版了著作《虚构的权威》,进一步阐述了女性叙事或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1]。此外,布鲁尔、沃霍尔等发表了论文《放开说话:从叙事经济到女性写作》和《建构有关吸引型叙述者的理论》,将女性主义、性别政治与叙事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美国学者纳什在《女性主义叙事伦理》中,借鉴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关于性别与叙事策略关系的总体思想,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一些现代作家的代表作进行解读,促进了女性叙事的发展。之后近二十年间,一些西方学者聚焦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关注她们在运用叙述策略时的特殊表现,以社会历史语境为参照,探究暗含在叙述声音、情节结构、话语方式等形式中的性别意蕴。至新世纪初,女性主义叙事学得到广泛认可,被学界定名为“关注性别差异、对故事与话语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流派[2]。
二、克里斯蒂娜诗歌的女性叙事
克里斯蒂娜与女性主义存在影响关系。首先,克里斯蒂娜作为“拉斐尔前派姐妹会”(模仿“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而建立)的成员,接受了女性主义的影响,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她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人文关怀。“拉斐尔前派姐妹会”,主张女性应该具有和男性平等的话语权、接受教育权,消除女性歧视,女性应该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她们的这些主张和当时刚刚兴起的女性主义存在很多共性。其次,拉斐尔前派(即“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表面上看似乎和女性主义者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拉斐尔前派成立于1848年,而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标志着女性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虽然只是时间的巧合,但它们都诞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相同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他们对于女性道德问题,女性的地位、话语权等问题的关注,存在共同之处。克里斯蒂娜同样作为拉斐尔前派诗人的成员,接受了女性主义的影响,其美学思想和艺术主张与女性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其诗歌之中(如短诗《如果我是女皇》)蕴涵着某些女性主义的诗学特征,显示了诗人的女性主义声音和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克里斯蒂娜生活的时代正是女性主义兴起的时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他者”,逐渐走向男性主宰的世界,开始意识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女性问题”,同时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她们意识到女性只有通过意识觉醒,才能对父权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抗,才能构建全新的女性形象,才能拥有话语权和独立的身份认知,才能消除歧视、获得平等地位,进而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
第一,女性“性自主权”意识。“性自主权”意识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聚焦之一。克里斯蒂娜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个“假正经”的时代,但是女性主义像春风一样使死寂的“禁欲主义”泛起了涟漪,正如凯特·米勒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所论,“历史上第一次把伦理和性的双重标准,还有把娼妓制度作为两性不平等的问题提出来。因此,在维多利亚后期,就出现了比较宽松的自由性欲的风气”[3],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问题”开始得到关注,文学作品中发出了女性主义的声音,再加弗洛伊德的“性是人类行为的本能冲动”观点、避孕和堕胎技术的发展,女性得到更多的性自主权。克里斯蒂娜在其短诗《微笑与叹息》中,提出“……爱,创造和发掘它的财富;爱,是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叹息是因为白昼的漫长,漫长的日子在叹息中消磨,心灵的重负使歌声哀婉忧伤,时光拖慢本应飞逝的脚步,我们活着却注定会死亡。”她认为诗歌中可以听到女性的发声,听到对宗教禁锢女性的叹息,“禁欲主义”下女性缺乏性自主权的凄婉的哀怨,而这种叹息、哀怨有时比呐喊、疾呼更能撼动人性,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对性自主权的渴望,渴望男女平等的性关系。
第二,女性的话语权与“身体”意识。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男权社会的时代,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处于集体失语状态。例如,《王子的历程》中,贯穿全诗的都是王子的声音,从未听到新娘的声音,她处于失语状态。即使涉及新娘,也是第三者外聚焦式的叙述,侧面描述了新娘的端庄仪态,忧郁神情。自始至终,新娘从未发声,完全处于失语状态。即使女性作家所使用的语言本质上也是男性语言,是男权意识的载体,承载着男权价值观。在男性语言里,女性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及其具体的传达形式。女性身体上,会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暴虐与侵犯。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女性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问题,以及自身的问题,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二) 女性形象的赞美与崇拜
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中提出,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形成两个极端,不是仙女就是恶魔。天使天真、美丽、可爱、无私,恶魔丑陋、自私、蛮横;有时男性作家描写天使外表,魔鬼内心,表现出男性文学的厌女症和对女性的文学虐待,体现出男性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性政治倾向[4],所幸拉斐尔前派中性政治倾向并不明确,他们多表现出热爱女性或崇拜女性的女性主义特征。
女性形象的赞美、女性形象的崇拜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聚焦之一。克里斯蒂娜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下,女性形象的传统角色定位和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形象边缘化的状态,女性不总是第二性的“他者”,不总处于“失语”状态,而是重构的全新的、敢于追求爱情且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新形象。这些形象充满对女性形象的赞美和崇拜,通过女性叙事,表达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这些形象包括姐妹形象,如《小妖集市》中反抗小妖的姐妹莉齐和劳拉、《少女之歌》中山间快乐的三姐妹形象;新娘形象,如《新娘歌》中的公主和《莫德·克莱尔》中的新娘;圣母形象,如《圣诞颂歌》中亲吻耶稣的圣母;天使形象,如《基督徒和犹太人》中的大天使与小天使;平民女性形象,如《王子的历程》挤奶女工、侍女,以及《两次》中皈依上帝的虔诚女孩等。
第一,姐妹情深形象。克里斯蒂娜作为“拉斐尔前派姐妹会”的一员,在其女性叙事诗歌之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姐妹情深的女性形象。在《小妖集市》中,克里斯蒂娜塑造了美丽的劳拉姐妹的天使形象,赞美了姐姐为了拯救妹妹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像两朵鲜花恋在一个梗上,/像两片雪花刚刚飘降,/像两条嫩枝,象牙雕妆,/金黄的枝尖像威严的君王。”她们仪态端庄,清纯甜美,为了不去惊扰她们休憩,连“笨拙的猫头鹰忍着不再疾飞,蝙蝠也不再往复鼓翼”。克里斯蒂娜赞美了莉齐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为了拯救因受小妖象征的男性世界的诱惑而偷食禁果的妹妹劳拉,她遭到小妖的虐打但坚贞不屈,最后那帮邪恶的家伙,被她的抵抗整得疲惫不堪,而狼狈逃窜,有的钻入地底,有的潜入小溪,有的消逝在远处不见踪影。
在《少女之歌》中,诗人成功塑造了气质“高贵典雅”、“温婉大方”、“甜美清纯”、“宛若女王”、“像太阳一样明亮”的女性形象,高挑的个头,高雅的仪态,闪动的眼波、秀丽的面颊、激情的香唇、飘逸的金发、扬起的圆颈、轻盈的步态,神态逼真、形象鲜明,成功塑造了天生丽质的女性形象,通过表现女性的真实面貌而非男性的幻想,表达了对女性形象的赞美,体现出女性主义情怀。克里斯蒂娜同时也塑造了牧牛人、牧羊人和国王三个男性形象,通过男性对于女性的跪拜,表达诗人自己的女性崇拜和女性关怀意识。首先牧牛人坐在梅根的脚下,目不转睛,充满敬畏,温情地倾听她的歌声;其次,牧羊人直勾勾跪在梅面前,忘记了一切,不管东西南北,不顾幸福伤悲;最后那个国王,不顾自己的尊贵身份,拜倒在玛格丽特膝下,尊贵的国王,躬身向她表达仰慕之情。在男性主宰的父权社会中,女性不再失语,而是拥有话语权,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第二,平民女性形象。虽然克里斯蒂娜因宗教失去爱情,精神上受到打击,疾病使肉体受到折磨,诗歌中总幻想死亡与天堂生活,但她并未悲戚、绝望。相反,其死亡书写持有明亮乐观的态度,生活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其诗歌之中也塑造了一些生活中的平民女性形象,赞美女性的勤劳与质朴,显示出她的平民情怀。在《王子的历程》中,王子在迎娶新娘的历程中,由于不断受到各种诱惑和艰难险阻,耽误了日期,导致了新娘郁郁而终。其中挤奶女工和侍女的叙事中,诗人塑造了一个可爱、俏皮而又大胆表白爱情的平民女性形象:她很直爽地提供了奶茶,但又索要报酬,不要黄金珠宝,不要丝绒外套,只要普通的白围巾和一天的陪伴,赞赏女孩不贪钱财的美德,表达了自己对于平民女性的人文关怀。
在《新娘歌》中,诗人对于侍女的形象的赞美主要表现在侍女对于主人的忠诚和深厚感情,对于女主人真爱难得,郁郁而终的伤痛以及对于爱情不忠的谴责与质问:为什么不及时迎娶公主呢?为什么在她升天之后,你才徒然泣涕涟涟?我们不稀罕你那妖艳的玫瑰,我们纪念她,在她卷发上洒白色罂粟花,不是为你存留一丝念想,你根本不配。这种情感也是对男性社会的抗争与谴责。关于新娘的形象,可以说是克里斯蒂娜自传式的虚幻爱情书写。诗人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失去真爱之后,经常产生虚幻的爱情,发出真爱难得、真爱易逝的叹息。她笔下的新娘“倒下还那么妩媚”,她“曾经多么美丽,即使作女皇,她也配得上任何高贵的国王,她仪态端庄,从未听她语气急躁,从未听她语调烦扰,言行自已,举止得体,滚滚红尘的喧嚣,无法搅扰她内心的静谧。手不曾慌,脚不曾忙,不曾欣喜若狂,不曾遇事慌张。”
第三,皈依上帝的虔诚女性形象。克里斯蒂娜受家庭的影响而皈依上帝,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将自己的理想、信仰,寄托在自己塑造的皈依上帝的虔诚女性形象身上。例如,在其宗教叙事诗《两次》中,两次将自己的心捧在手里,想要奉献给上帝,第一次,不管叫我倒地或站立,还是让我活着或死去,不管遭遇多少艰难,都要把心奉献出去,而第一次心还没熟,却已破碎,但一心向主,从不退缩。第二次将心捧在手里,恳求上帝的评判,来“里里外外仔细察看:淬炼它的成色,涤除它的浮渣,将它置于你的掌控之下,以免别人摘走它。”将自己的心捧在手里,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上帝,通过皈依上帝的虔诚女性叙事,赞美了一个诚心向主的基督教徒。
此外,在《莫德·克莱尔》中克里斯蒂娜还塑造了一个美丽的莫德·克莱尔与一个“邻家妹妹”的形象:“她跟着他们走出教堂,/步履盈盈,仪态大方,/他的新娘像乡村姑娘,/莫德克莱尔则像女王。”
(三)女性爱情的悲剧式书写
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也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聚焦之一。爱情是女性作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作为感性动物,女性能够强烈地体悟到自我的感情向往和微妙的爱欲冲动,往往追求情与性相统一的“灵肉合致”的爱情,追求爱情自主和婚姻自由。克里斯蒂娜诗歌的爱情书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所面临的爱情与婚姻的困境,克里斯蒂娜对于爱情的书写,表现出女诗人的爱情悲剧意识与爱情观,主要体现在《王子的历程》和《爱已死亡》等爱情叙事诗歌之中。《王子的历程》,悲剧式的爱情书写,是克里斯蒂娜借用《天路历程》的叙事结构,以戏仿的手法改写自《睡美人》,讲述了公主新娘苦苦等待王子来迎娶自己,然而,王子在迎亲的历程中,遭遇了种种诱惑,如挤奶女工的邂逅与挽留,鲜奶的诱惑;洞中老怪物邀请留宿,神药的诱惑;漫漫河水的阻隔,温柔的诱惑;又过了长河,翻越了高山,最后终于到达王宫,然而一切都太晚了,“太晚,爱情已逝;太晚,欢娱难留,太晚,太晚!你在路上耽延太久”,“受蛊的公主在她的塔楼”像“受蛊的鸽子立于枝头,孤独死去,没有配偶”。新娘等不得王子的到来郁郁而终:“沉睡,安息于格栅窗后,她内心充满渴求,你害她苦等没盼头”。通过悲剧式的爱情叙事,书写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爱情悲剧,表达了诗人对于女性爱情、婚姻的人文关怀。在《爱已死亡》之中,女诗人将爱情与死亡这两个文化意象并置,表达了其爱情悲剧诗学观:“爱已死亡,尽管它坚强如死亡,/来吧,在凋谢的花丛中,/让我们给它布置安息的地方。/……爱诞生于春天,/却夭折在收割之前;在最后一个温暖的夏日里,/它毅然离我们而去,/不忍目睹秋日黄昏的灰暗与凄凉。/我们坐在它的墓旁,/哀叹它的死亡……”
第二,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摆脱困境、颠覆传统女性道德标准、解构传统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女性叙事,如《少女之歌》《小妖集市》《爱情三重唱》等。对于克里斯蒂娜爱情观的传统研究,大多聚焦于前者,即女诗人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所面临的爱情与婚姻的困境,对于真爱难觅的叹息,对于“灵肉合致”唯美爱情的企盼;而忽略了其诗歌之中觉醒的女性形象——她们冲破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严苛的双重道德标准,大胆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也忽略了其诗歌之中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诗学观。《少女之歌》中赢得牧牛人、牧羊人和国王的爱情的三个女孩就是觉醒了的女性形象。而与此“三女”形象相似,克里斯蒂娜在《爱情三重唱》还塑造了另外“三女”形象:大胆追求爱情,不拘泥于传统道德禁锢,一个寻求不到爱情而心情郁闷,因爱的重负而痛苦得哼哼;一个因爱而蒙羞;一个对爱情渴望得要死,但真爱难觅而逐渐变成慵懒粗俗的主妇。
三、结语
在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分析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诗学观,及其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发现克里斯蒂娜塑造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女性主义诗学观:其一,女性时常面临来自男性世界的诱惑;其二,女性作为“他者”或“第二性”,没有平等话语权,虽然其所发出的声音比较弱,但至少已经发声,开始扮演女性该有的角色,初步确立了女性自我身份的认知。其三,“身体”关系不对称。其四,女性抗争的必胜信念,赢得了女性的尊严,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克里斯蒂娜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其五,克里斯蒂娜诗歌也体现出女性不平等的经济地位,维多利亚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之中,生儿育女,无经济地位,这也算是一个“女性问题”。
当然,有关克里斯蒂娜诗歌中的女性声音,还存在另外一些“声音”,包括“女同志论”和“女性觉醒与上帝崇拜矛盾论”等。例如,有学者采用“女同志理论”来分析《小妖集市》中两姐妹之间的亲昵举动,如“像两只鸽子偎在同一巢,翅膀相挽相抱”,“面贴着面,胸抵着胸,她们蜗居于同一窠巢”等,观点虽新颖,但那只是贴了一个“女同志理论”的标签,尚不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克里斯蒂娜对于女性的关怀和对上帝的虔诚具有矛盾性:她既渴望女性能像男性那样受到教育又怕教育会使女性思想自由而不顺从上帝。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共创作包括抒情、叙事和伦理诗歌近千首,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其诗歌进行了译介,但是其诗歌翻译数量有限,文本分析所需语料尚需补充(作者也只翻译了百余首)。虽然除“女性叙事”外,我们也对女诗人的“原型叙事”、“互文叙事”、“唯美叙事”、“爱情叙事”、“死亡叙事”以及“意象叙事”等进行了研究[5],但是对于克里斯蒂娜的“现代性的焦虑”,诸如人类精神家园的沦陷、人类灵魂的自律、反省和救赎问题;克里斯蒂娜的“动物、人类和上帝享有平等关系”的生态美学思想及其反对奴隶制度与殖民主义等民主思想[6],还需在美学乃至哲学的高度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