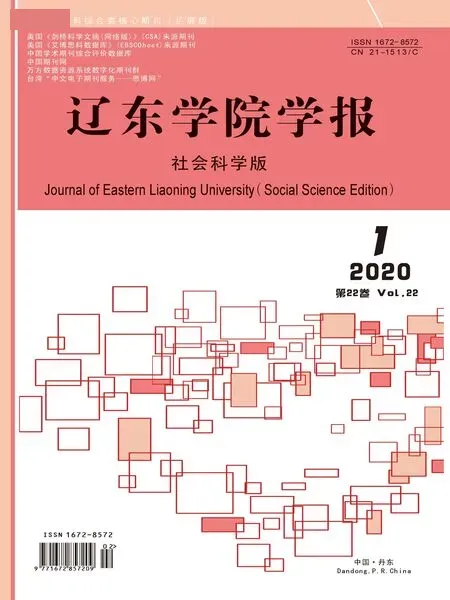细雨中的香椿树街
——苏童与余华小说中的少年形象对比
姜 雪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一、 苏童小说中的少年形象
“香椿树街”是苏童小说中标志性的空间坐标,关于这个地名,苏童自己曾说:“其实不是我触及那两个地方就有灵感, 而是一旦写得满意了, 忍不住地把故事强加在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头上。”[1]2苏童的笔以南方湿润的土壤为墨水,致力于将全世界有同样精神困苦的人都搬到这条街上来。他倾心所讲述的主要是女性的宿命性悲剧和少年的血色青春。其中少年们成了香椿树街上最为张扬、热烈、明艳的一抹色彩。从1989年发表在《钟山》上的《舒农或者南方的生活》,到1992年发表在《作家》上的《回力牌球鞋》,1993年《作家》上的《刺青时代》,《小说家》上的《游泳池》,1993年、1994年连载在《钟山》上的《城北地带》,再到1999年发表在《作家》上的《古巴刀》,发表在《大家》上的《独立纵队》,2003年发表在《钟山》上的《骑兵》,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的《河岸》再到201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雀记》,苏童笔下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的少年形象,舒农、舒工、鲁鲁、陶、小拐、孙红旗、达生、叙德、陈辉、小堂、库东亮、保润、柳生……这些少年生长背景大多相同,生活在无爱的家庭中,父母爱、兄弟情淡化,成人世界混乱肮脏的一面冲击着少年的心理,导致他们的性格出现异化。这些少年一方面心底里仍保留着孩童的纯真的向往,另一方面行为和思想方式却已经出现自我角色混乱。他们好奇的窥探着成人的世界,却对随之而来的肮脏无力消化。他们对无爱家庭感到痛恨同时也无能为力,压抑到极点的少年甚至产生弑父、逃亡、纵火等极端行为。“香椿树街”涌现的一批批边缘少年形象的塑造不仅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也对青少年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二、余华小说中的少年形象
余华的少年时期是伴随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和动荡的时代风云变幻成长的,加之此后短暂的牙医生涯,这使得他面对笔下的人物时有着超乎想象的客观冷静,也使得他塑造的人物呈现出了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他笔下的少年形象与苏童笔下的略有不同,其中暗藏的性格本质性不同是前者面对精神困顿、希望破灭后整个人便灰暗委顿下来,后者则在困境中或努力生存下来或获得了永久的解脱。余华1987年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十八岁出门远行》、1993年出版的《在细雨中呼喊》以及2004年出版的《我胆小如鼠》、2008年出版的《兄弟》,使得孙光林、孙光平、苏杭、苏宇、国庆、鲁鲁、李光头、宋刚……这些有着不同性格经历却同样内心孤独、凄惶无助的少年走进我们的视线。余华将少年世界和成人世界对立起来,少年试探性介入成人世界,见证了苦难、荒淫、冷漠和死亡,感受到绝望进而开始逃离,最终却以悲剧收场。余华通过还原本真的感觉的方式还原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生活真实[2]20。这种真实使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情不自禁地便将自己与他们相提并论了,少年时代的那种孤独、凄惶、无助的记忆超越时间,独自来到。
三、同工之美
(一)风雨中成长的青春
苏童和余华小说中的所有少年的成长背景无一是幸福的。首先是母爱的缺失。《刺青时代》中男孩小拐出生没几天他母亲就死了;《骑兵》里左林的母亲被运煤的卡车撞死,像飞鸟一样飞走了;《香椿树街故事》中鲁鲁的母亲是一个对他没有半点关爱的妓女;《在细雨中呼喊》里国庆被父亲抛弃后,只能靠反复回忆母亲而获得一点温情;孙光林的母亲唯唯诺诺毫无主见;《河岸》中库东亮的母亲只是把他当作和他父亲一样的麻烦;《黄雀记》中柳生母亲的絮叨像一只闹钟“你的快乐是捡来的,夹着尾巴做人吧”[3]119,母爱的缺失使得这些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身心健康发展受到阻碍。
其次是父亲的荒唐。《河岸》中库东亮的父亲库文轩对他采取监禁式的教育;《舒家兄弟》中这样描述舒农的少年生活:“就这样舒农迎来了他少年时代最难忘的夜晚。他记得他被黑布蒙住眼睛被绳子绑住手脚被棉花团塞住耳朵的那些夜晚,父亲和邱美玉就在他身边做爱”[4]27;《在细雨中呼喊》里这种荒唐在孙光林、孙光平的父亲孙广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光明正大的和寡妇偷情,还将家中的财物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寡妇家,他以“过过眼”为借口,在和孙光平相亲的姑娘胸上“摸了一把”,后来更因为猥亵儿媳妇被儿子砍掉了耳朵;《兄弟》中李光头的父亲偷看女人屁股时掉进粪池淹死,使得李光头和他有了一样的癖好;《骑兵》里左林的父亲为了化解纠纷,跪在大街上给傻子当马骑。父亲的荒唐是导致这些少年悲剧性宿命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父亲的伤害使得他们更加孤独,进而衍生出羞耻、暴力和逃离。所以舒农烧了自己的家;库东亮多次想踏上那辆开往幸福的车;孙光平拿斧子割去了父亲的耳朵。少年那种“走进现实世界时的懵懂、冲动、敏感、孤独甚至不知所措”, 那种“成长途中与那个时代芜杂、零乱、荒唐的成人世界的隔膜与猜忌”[1]2,是少年们悲惨命运的开始。
(二)生理教育的匮乏
亲情的缺失加上农民根深蒂固的粗糙使得少年们无法在青春期接受正确的生理知识教育以及心理引导。他们的生理知识完全来自对成人世界的好奇与窥视,进而进行模仿这一过程。《舒农》里的两兄弟舒农和舒工就是最好的例子。舒农除了偷看父亲和苏美玉偷情,还将他们扔到河里的避孕套收藏起来。舒工学着父亲和楼上的苏美玉女儿谈恋爱,还模仿父亲对舒农进行暴力;《在细雨中呼喊》里苏宇的性启蒙是他父母藏起来的黄书以及父亲和寡妇光明正大的调情,他便认为那是正确的,如郑亮父亲说的那句“农民嘛,都这样”,所以对女性的渴望使他在胡同里猥亵了陌生女人,成了人人厌恶的流氓犯;同样一个家庭出来的苏杭则表现为拿小镜子在厕所偷窥女同学,性侵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黄雀记》里的柳生更是在水塔强暴了仙女,嫁祸给保润,使得三个人的人生完全葬送。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里曾借孙光林之口为少年的性冲动做了解释:“我当初对厕所的选择让我看到了自己无处藏身的少年,这样的选择是现实强加于我,而非出于自愿”[5]80。青春年龄的少年们对生理上的变化既恐惧、又享受隐秘的欢愉。因为缺少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他们只能任由生理的欲望,悄悄主持自己的一部分言行。
(三)性格呈现两极分化走向
苏童和余华笔下的少年性格大多呈两极分化走向:一种是由于自身的自卑而衍生出对暴力和权力的病态向往;另一种畏畏葸葸地走在路的最边缘,内心却滋生着很多阴暗的想法。前者如《桑园留念》里的肖弟、毛头到小拐到后来的猫头,豁子、红旗、小堂、陈辉、达生、孙光平,他们由于自身生理缺陷而感到自卑进而产生英雄梦。他们渴望着得到少年中的权利,通过成立帮派、打架斗殴来解决问题。《刺青时代》中描写过这些少年的斗殴:“拿着刀你捅我,我劈你,五十一名少年在垃圾瓦砾堆上的浴血之战”[6]131,这些少年追逐的是自己已经丧失的尊严,所以他们竭尽全力,他们歇斯底里,认知的扭曲导致他们的性格乖张、行为暴力。后者如库东亮、舒农、孙光林、苏宇以及《我胆小如鼠》中的“我”。这类少年主要的性格特征则表现为阴郁,带着仇恨和压抑惶惶不可终日,被成人和同龄人两个世界同时抛弃。《舒家兄弟》中描写舒农“喜欢朝人多的地方走,站在人群外侧张望一会儿,然后离开”[4]270;《我胆小如鼠》中的“我”的父亲在世时,经常对母亲说:“杨高这孩子胆子太小了,他六岁的时候还不敢和别人说话,到了八岁还不敢一个人睡觉”[7]7;《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光林的自述揭示了这群惯于沉默的少年的内心,“孤单是为了维护自尊,交朋友只是为了故作镇静和虚张声势。”这些落单的少年被别人叫作“空屁”“小阴谋家”“叛徒”“孬种”……这些胆小自卑的少年是很多青少年的缩影。
四、异曲之妙
(一)清晰的精神寄托
香椿树街和细雨中呼喊的这些少年经历的同样都是内心的成长,那是恐惧、迷惘、心旌飘摇的历程。但对比苏童笔下的少年形象和余华笔下的可以清晰地看出,苏童笔下的少年几乎都有很明确的精神寄托,而余华笔下的少年则很少有。例如《城北地带》中小拐因为自身的残疾而将全部精神寄托在复兴野猪帮上,他想用他自认为的英雄似的荣耀感来和内心的自卑抗衡;和小拐有着相似经历的左林亦是如此,《骑兵》中的左林因为罗圈腿被嘲笑,所以他“独来独往,心中怀着一个焦灼而令人费解的秘密。连我都觉察出左林对骑兵生活的疯狂的妄想”;《独立纵队》中的小堂对加入独立纵队这一帮派有着难以想象的执念;《游泳池》里的达生为了在游泳池里游出一个漂亮的蝶泳,将想驱逐他的管理员歪脖老朱溺毙在水池里;《舒家兄弟》中的舒农因为无爱家庭的束缚想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猫;《黄雀记》中的保润近乎疯狂的纠缠仙女要跟她跳小拉;《回力牌球鞋》中陶执着于回力鞋,最后鞋被收破烂的老头收走了,他便走到哪里都喜欢观察别人的鞋。在肮脏、混乱的生活环境以及粗俗、猥琐的精神环境影响下,困顿、压抑、恐惧挥之不去,少年们不免产生了逃亡的心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自己的梦想中去,而这一逃亡事实上是一个陷阱,是在追求希望的过程中迅速地绝望。于是,逃亡最终成了一种无望的挣扎。
(二)残存的少年心性
这些并未得到世界温柔对待的少年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凶狠的还击着世界。在这样不利于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空间里,少年们过早的成熟,他们模仿成人的那套生存规则,变得色情、暴躁、疯狂、冷漠。这种早熟,苏童和余华笔下的少年都具备,但是就少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言,不难发现苏童笔下的少年仍残存着些许少年心性。例如《古巴刀》中的陈辉因为想加入帮派而给三霸送各种各样的刀,陈辉的送礼还停留在孩童似的讨好层面;《黄雀记》中擅长捆人的保润,当柳生请他捆自己发疯的姐姐时,保润像个老成的手艺人一样抠了下鼻孔说:“我从来不捆女人”,但当柳生说给他送一篮猪爪子,因为喜欢吃,保润马上打破了自己伪装的成熟,同意把她带过来捆,十足的小孩儿心性;《河岸》中父母离婚后,权衡利弊选择了父亲的库东亮清晰的为他和母亲的关系下了结论:“我是我母亲的客人”以及“不是她灭亡,就是我疯狂;不是她疯狂,就是我灭亡”[8]57。但是他还是会偷偷看母亲,在她工作的粮油加工站对面的电线杆上写下一个幼稚的报复性标语“打倒乔丽敏”。苏童笔下的少年是一种伪装的成熟,他们举手投足之间仍有少年的稚气,苏童用这种残存的稚气完成了对成人黑暗世界的拷问。
余华笔下的少年则表现为心理的成熟、行事的圆滑、话语的老练,少年心性已经被磨砺得所剩无几。《兄弟》中十五岁的李光头就已经学会用林红屁股的秘密耐心细致的和男人们讨价还价,换取三鲜面吃,文中写道:“他半年里美滋滋了五十六次”[9]20。这些男人们都说他比很多圆滑的成年人还要精明世故;《在细雨中呼喊》里的鲁鲁是一个很小的少年,他已经会很好的掩藏自己的情绪,鲁鲁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投其所好的送礼方式,他用母亲留下的钱买了两根大前门香烟,想以此来“贿赂”司机,求其在七桥停一下车;国庆则是以自己的诚实和精干计算,十三岁便击败了在卖煤这个职业里干了二十多年的同行,同是这一年,国庆竟然买了一瓶酒和一条烟前往十一岁的女孩慧兰家提亲。余华笔下的少年是一种内心的老成、世故、圆滑,他们为人处世已经如同成人一般面面俱到了。这些一如成人一般的少年,使人心生怜悯的同时生出反思。
结 语
苏童和余华的作品中,作者成功塑造了一系列风雨中飘摇的少年,这些少年使其作品大放异彩。对比二者笔下少年的形象,不难发现这些少年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苏童笔下的少年面对成长困境,表现出的是少年佯装的成熟,他们有着清晰的精神寄托。余华笔下的少年面对成长困境,表现出的是心理上的早熟,他们适应成人世界的规则且善于利用规则。无论是苏童还是余华,这一群生活在黑暗中,习惯于游走在人群边缘的少年形象都为当今青少年教育问题提供了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