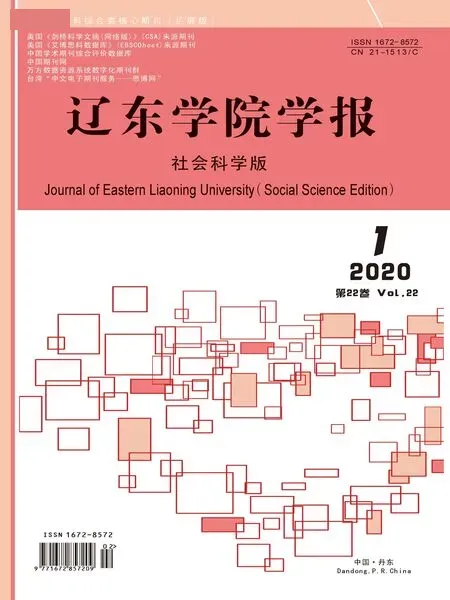拓展中国文学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读后
王以兴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据董乃斌等所著《中国文学史学史》一书的著录统计,自20世纪至今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学者编撰的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超过一千部,数量不可谓不大。因此,对这百余年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历程进行学术史回顾和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且重要了。当今学界关于建构“文学史学史”学科和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愈发高涨,就是这种学术反思的直接结果。当然,学术反思的精深程度和最终的结果如何,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是否能够站在文学史编撰者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彼时创作的历史实情,以对文学史著作给以理解的同情和科学的批判。温庆新所著《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一书,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该书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及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等三部代表性文学史著作为例,对1900—1910年间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整体情形加以探究,视野开阔,新见迭出。尤其是,该书坚持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旨趣及其变化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述与总结,为我们更宏观且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史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
一、研究时限的界定与学术视野的通达
该书将研究时限限定于20世纪初期的第一个十年,即1900—1910年之间,这也是中国文学史的艰难初创期。如此选择的背后,正是作者温庆新通达、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做支撑。
通读此书不难发现,该书最根本的意图是要在中国文学史百年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对这十年间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情形加以整体观照,从而为当下及未来重写文学史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事实依据和学理判断。当然,整体观照离不开对具体文学史论著和编纂者的微观透视。为此,该书选取了这十年间三部代表性的文学史论著,就他们各自的书写特征、学术渊源及价值追求,进行个案分析和梳理。正如该书所言:“这三部文学史著述分别代表20世纪初期教会所办大学的中国文学教学选择、朝廷官方意志重要体现的大学堂中国文学教学选择、中学堂一线教学人员的中国文学教学选择等三大不同类型,对彼时社会转型、学术变迁、学制改革及‘中西交通’背景的不同回应,以便尝试就上述所言彼时治文学史的编纂选择等问题而展开申说。”从中可以看出,黄人等三部论著的学术旨趣虽各有不同,然从中国文学史学的纵向发展来看,他们又不自觉地具备了属于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共性特征,即文学概念不清晰、标准不统一的过渡性。于此可清晰的窥视到:彼时学者在中西学术交通的背景下,虽受启发于西方诸如“进化论”、民主自由等思潮而进行中国文学史的编纂,然而编纂思路和书写主体则完全以传统学术为主导,努力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试图以此发扬传统的“固有之学”和维系人伦道德。这种学术追求和编纂意图,迥别于1910年之后严格按照西方文艺理论视野下的“纯文学”概念进行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操作模式。
因此,比较而言,该书有助于学界对中国文学史学百年发展脉络,进行更为完整清晰的把握和深入透辟的理解。关于20世纪初期头十年间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当今学界重点围绕黄人《中国文学史》及其相关问题展开,比如黄霖先生《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一文。虽说也有如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曾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整体情形做过探讨,然而,限于篇幅和侧重史迹勾勒的研究思路,故于“知其所以然”的角度进行的论述,则略有欠缺,稍显薄弱。而温庆新所著则细致且充分地挖掘了20世纪初期三部代表性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与彼时社会转型、学术变迁、学制改革及“中西交通”诸多方面的内在关联,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同时,这十年间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时代意义,也得以凸显出来。正如该书所言:“正是经过1900年至1910年这代治文学史者的努力——编纂中国文学史所面临的问题及可取之路,才有可能使后来治文学史者规避编纂过程中的某些问题。”
据此亦可见及,某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能否将之纳入当下学术研究的大格局与大视野中,对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予以填补、延展和纠正,从而为学界提供更多的或深、或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温庆新所著,显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二、还原视角下实证主义方法的灵活运用
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研究者敏锐地发现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点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加以周密论证和翔实阐述。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温庆新所著对此类方法的运用,显然是非常熟悉且自觉的。正如该书所云:“采用还原视角梳理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历程,以还原历史为切入点,结合实证主义方法去关注历史的客观存在及其背景,以梳理文学史的精神及文化价值为主,无疑是消除研究中存在偏见的一种可取方式。”在笔者看来,所谓还原视角和实证主义方法的结合,也即意味着该书试图回归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语境中,去具体考察当时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学术发展等诸多层面之于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的书写内容、学术立场和为学诉求等方面的内在影响与直接表现。
该书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内容分为五章,前四章分别梳理和剖析了“近代学术之变迁”“古典目录学”“‘外来经验’、古典目录学的杂糅”与“‘中国’想象”等四个方面,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具体影响。第五章则重点讨论编纂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追求和个人经历而在上述四个方面影响下所形成的彼此有别的文学史书写旨趣。比如,在晚清革新自强、救亡图存的社会情势和时代背景下,彼时学校教育积极推行的学制改革和“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具有强烈的“致用”意图,即维持人伦道德和社会稳定。那么,“中国文学门”文学课程中设有“说文学”“音韵学”等门类,不仅是因为小学知识系治经学的入门之径,可为彼时学制变革者借助儒家经义维持“圣教”与巩固清廷统治的基础工具,而且还另有一层考虑:“实现因废除科举而致学子无所适从之情形,向维持社会稳定过渡的一种安抚性措施。”据此而言,作为彼时大学文学教员的林传甲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时,严格按照当时朝廷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等旨意而为,也就容易理解了。于此,反映出时人对于文学史学科性质的矛盾和困惑心态,学界亦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如《中国文学史学史》即云:“林传甲的这部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章程》中有关文学研究规定的教材,充分表现出在文学学科设立初期,人们对这门新兴学科的范围、内容和手段的认识,多少有些介乎中西、古今之间的摇摆和含糊:既要照顾被模仿被汲取的西方学理,又要迁就传统的中国学术思维的定势。”[2]至于黄人《中国文学史》与各《章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则罕见学界涉及。而该书敏锐地洞察到了黄人学术思想之中西杂糅交汇的一面,从而对其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诸多实情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并加以概括道:“以《章程》为原则指导,以西方价值观为理论引导,所论多系黄人的自我发挥。”可见,林传甲、黄人等学人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仅是对彼时官方意志的自觉靠拢,更是彼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有志之士由其固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激发而来的一种学术自律行为。此种情形与1910年以降编纂者们从历代文学史内部的学科经验进行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做法,确有本质的区别。
再者,“外来经验”之于彼时中国文学史编纂过程中的具体影响和细微过程,该书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查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精湛的思辨力,对此做了带有辩证意味的历史还原。例如,因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严格恪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并反复征引《四库全书总目》以之为编纂文学史的指导思想,故学界多视为保守顽固,鄙薄待之;至于其中缘由,则几无深究。而该书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近代学制改革的时事背景,指出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完全是在教育致用和政治致用的学术意识的支配下,坚持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目录学为根本,并积极借鉴和吸纳诸如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远藤隆吉《中国哲学史》等“外来经验”,以及西方的宗教、科技、政治等学识来重新组织和阐释中国文学史的意图。从中即可清楚看出林传甲所具备的中西交融的知识结构,以及一定程度的比较视野。当然,该书对林传甲在编纂中国文学史过程中比较视野的运用,并非单纯的褒或贬,而是下语谨慎且客观。其言:“从某种意义讲,林传甲亦是中西融通之人,《中国文学史》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及编纂实践,足以证明之。”这样一来,不仅极大地纠正了时下学界在评价林传甲及其文学史编纂时过于武断或简单的倾向,而且有助于避免某些学者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偏爱”而任意给予不实之虚誉的主观化做派。
可以说,该书熟练、灵活的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实情进行了全面的历史还原,揭示出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或被忽略或被遮蔽的逻辑细节和事实隐情。从阐释思路、论证方法及诸多观点的新颖程度讲,此书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真可谓是“熏然耳目开,颇觉聪明入”(杜甫《送率府程录事还乡》)。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三、对当下学术史研究的多重启发
正是由于温庆新通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采取还原视角下的实证主义方法,使得该书在学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多重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今天来看,百年中国文学史的艰难发展和不断探索,可视为中国学者试图将西方学术视野下的“纯文学”概念及文学史书写模式与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下的文学创作进行对接和交融的过程。而该书的研究,使我们从历史源头的角度深刻理解和认识到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实在没有必要生搬硬套西方的文艺理论。因为早在20世纪初期,黄人、林传甲等学人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就是在西学的启发下,并积极借鉴和参考西方,尤其是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经验而编纂的,但林传甲、黄人等编纂者仍以中国传统学术为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只有立足本国传统,从实际出发,对西方各种学识和文艺理论进行批判式吸纳和融会贯通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真正对中国文学史学科内部发展规律进行深入考察,从而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意识的产生过程作出客观评判。
其次,从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看,该书对当下的文学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术史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众所周知,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还原历史实情,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以便在细致梳理和认真总结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和利弊优劣的基础上,多角度、多层次地阐释其间的各种主客观成因。而实践此类意图的最有效阐释途径,就是实证主义的客观合理运用。可以说,该书目光如炬般地窥探到在20世纪初期民族危亡的时代局势下,教育革新、学术变迁及以目录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各种学识思潮的交流,其间所形成的纵横交织、纷繁复杂的文化背景与彼时中国文学史编纂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种文化背景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文学史编纂者的主动迎合和参与。故而,以黄人、林传甲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士人出于启蒙革新和教育“致用”的目的,借鉴西方包括文学观念在内的各种学识思想来讨论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形,试图为晚清政府培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伦道德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可用之才。这种“中体西用”的学术思维就造了彼时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比如,沿袭甚至照搬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传统目录学的评价体系、标准及具体内容;又如,“小学”知识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另类”存在。同时,文学史编纂者在人生经历、学术累积和为学诉求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性,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编纂旨趣。因此,从整体思路和阐述方式上看,该书就自然而然地做到了现象与本质、特殊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科学化论证。而这恰是学术史研究所必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素养。
最后,该书从源头角度展开学术史建构的论述视角,使我们清楚认识到:不同时期的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二者不可偏废。自从20世纪前后西方文艺理论视野下的“纯文学”观念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后,本土学人受其启发且以之为参照,从而对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规律进行了积极探索。此举背后,则是文学史编纂者对古代文学自觉意识的酝酿、萌发以至成熟之历程的梳理。此外,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坚持文学本位,立足于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之两维,希望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阐释评介能够潜移默化地给予读者在政治、道德、人格、性情等方面,以真、善、美的濡染和熏陶。此可谓百年文学史学发展的共性特征。而所谓个性,有两个含义:一是,任何文学史著作的编纂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避免地贴上独特的时代标签;二是,因编纂者在学术素养、思想意识和为学诉求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导致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书写形态和表述方式上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编纂旨趣。而这一切我们从该书的第五章论述中,即可得到此类追根溯源式解释的合理运用方式及其范式意义。
概言之,通达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得该书敏锐洞察到20世纪初期头十年的中国文学史编撰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而本着“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诉求,该书采取还原视角下的实证主义方法,翔实缜密地考察了此期间三部代表性文学史著作的共性特征、个性旨趣及其主客观成因。因此,在研究范式与具体方法的运用上,该书对于包括中国文学史学在内的学术史书写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该书在行文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对话姿态,从不盲从学界的主流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地指出学术名家的某些研究纰漏和缺憾。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当下学界,尤其青年学子所缺乏且值得镜鉴的学术勇气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