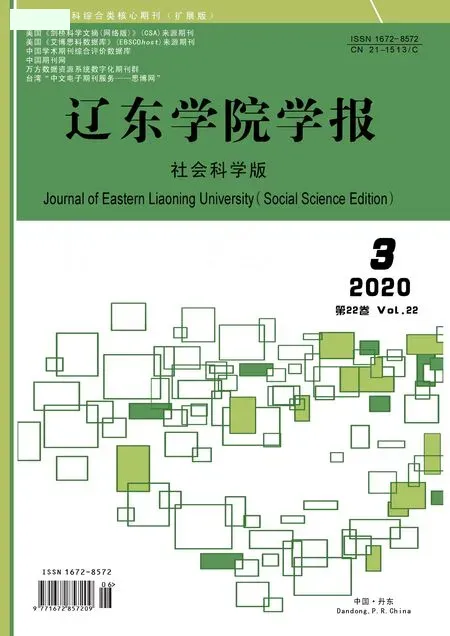《金枝》中的过渡礼仪与国王形象探析
王小雨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人类学学者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边缘——过渡——融合”理论,意在强调“礼仪”对早期社会日常生活的重大影响。在作者看来,人生就是阶段性地层层推进,礼仪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纵览国内外诸多有关早期社会面貌的田野调查实录,举凡经济、社交、信仰、亲族、灾害、死亡,总是能窥见几分礼仪的投影。弗雷泽代表作《金枝》中,国王的特殊身份使他不得不直面个体与集体的双重仪式过渡,由仪式生,由仪式死,由仪式确立价值,一言以蔽之,早期社会国王的生命历程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浓厚的仪式感。
一、过渡期与巫术礼仪
纵观早期巫术行为的发生背景和行巫目的,无一例外都与“转折”牵连。日常生活生产的理性经验保证早期初民对传种营养的基本需要。马林诺夫斯基曾多次为原始社会辩解,它不是现代文明人眼中蛮荒、无组织秩序的一盘散沙,无论从房屋搭建、节日庆典、早期艺术品的花纹图样还是内部人际关系,早期社会反而呈现更为严密复杂的运行机制,“任何原始社会都有很多知识宝藏,是以经验为依据,而被理性所修正的”[1]15。在纷繁芜杂的原生态意识团里,巫术显然是最为神秘诱人的一块。经验操控下的日常生产并不能保证时时刻刻的等量回报,人常为经验与科学背叛,无法预料的天灾、突如其来的恶疾或者一场不太顺利的狩猎都有亡族灭种的可能。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巫术应运而生,它由咒语、仪式、施行者的条件三部分组成。集体性的巫术仪式多见于事关部落生死的转折时期。仪式过程中,巫师口念咒语,手舞足蹈,陷入癫狂痴迷的神灵附体状态,此时,人神合一,巫师依靠独一无二的通灵技能传达民众需要,恳求神灵庇佑保护。于是,早期巫术仪式带有明显的实用目的性,生育巫术基于繁衍传种、气象巫术针对洪涝干旱、土地巫术事关农业种植,特罗布里恩群岛上为库拉打造的独木舟,从建造到试水航行,巫术不离始终。
一场成功的巫术仪式的关键,与巫术前后人与物生存状态的差异大小挂钩。由衰转胜、由无到有、由佳境走向更佳是对巫师职能的肯定,黑巫术亦是如此。于是,巫术仪式成为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之间的过渡期,巫师是神灵与普通民众间的摆渡人,他们共同组成两个世界互通往来的唯一关卡,通晓个人集体命运,手握过去未来,《金枝》中国王同时也是能够“绝地天通”的部落巫师。从这一层面看,早期社会于理性经验所不能解释的意外为原始巫术提供了现实动力,而巫术横亘于两种情境之间的特殊处境使其顺理成章地担任“渡”者的角色。国王参与的任何部落教仪都有固定的实践模式,求雨仪式表现为:大旱——国王求雨——雨(有/无);生产仪式为:无子——国王求子——妊娠(有/无);狩猎仪式为:国王求猎物——打猎——打猎结果(好/坏)等。佐证早期国王选举实为期望国王打破眼下的生存境况,挽救族人不满情绪的衍生。巫术过渡的概念不仅是早期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还与群体心理紧密相关。梦境与现实的混沌,主客不分的思维现状使“泛灵论”占据初民信仰的核心地位,生病和死亡被解释为灵魂受阻和离体,当原始人笃信自己的灵魂已被黑巫术迫害驱逐,便立马陷入颓然等死的状态。因此,那些掌握与神灵沟通秘诀的巫师成了唤灵、招魂的主角,在咒语的辅助下,四处游荡、行走不定的灵魂回归肉体,患者重获新生。由此,人们对巫术总是抱有崇敬和畏惧两种情感态度,精神涣散的人巫术后神采奕奕,体格健壮的遭遇黑巫术后萎靡不振,这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案例是原始人世界观宇宙观的真实心理写照。原始巫术正是通过对个体灵魂的安慰、集体灵魂的崇拜从而稳定部落上下的情绪,以此角度,巫术在早期社会的“攻心”力可见一斑。
原始部落日常生活的阶段性特征将一切行为现象很自然地分成前中后三个部分,个人与事件的“前”“后”顺利过渡倚靠巫术发挥媒介力量。它既是早期灵肉信仰的视觉呈现,也是部落心理状态的客观反映。过渡期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集体的命运走向,这也使得巫师一职长期处于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的特殊处境。
二、国王形象的多重过渡
弗雷泽认为,早期社会国王一身多用,同时兼任部落的巫师祭司。母系社会的大前提决定部落头领的位置不可能通过世袭代代相传,反而多由平民群体中擅长“绝地天通”的能者担任,换言之,酋长的儿子永远是平民。《金枝》里,国王任期时长与个体衰老程度相关,早期社会国王与神灵合二为一,一旦出现精力衰退、性欲削减等有损神灵能量的征兆,国王即刻赴死,在体内神力遭受损害之前将它转移到另一个年轻且精力充沛的寄体中。因此,每一个国王的一生都会经历两次重要的身份变更,从世俗世界走向神圣世界再走下神坛,完成“人——人神——祭品”的双层转变。
(一)国王加冕:世俗——神圣
《金枝》中,加冕与献祭犹如两道门,是划分国王不同人生阶段的重要界限,门前门后,普通民众获得实权成为国王,任期结束为天神献祭。范热内普提出每一种身份转换都历经分隔、边缘与聚合三种状态,因而延伸出分隔礼仪、边缘礼仪与聚合礼仪的概念。以国王加冕仪式为例,仪式前国王与神灵各不相关(分隔期),仪式过程中随着加冕步骤推进国王逐渐圣化(边缘期),最后以桂冠或其他象征物完成身份的转变(聚合期),去魅过程亦然。“从一状态到另一状态之过渡是庄严一步,如果不特别谨慎,就无法完成”[2]183,相关礼仪前前后后不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每一个时间点与动作都经过周密考量计算。杀王仪式里,人们倾巢而出,杀鸡宰牛,饮酒高歌,处死国王的手法和尸体处理方式各有讲究,初民对集体仪式总是怀有极大的热忱,“每一个体总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之多个群体。为从一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2]188
只需对人类学仪式理论稍作了解,便可窥见“许多仪式与信仰底核心都是人生底生理时期,特别是转变时期,如受孕、怀妊、生产、春机发动、结婚、死亡等时期。”[1]28任何原始人的一生,均可按时间点划分为诞生、少年、成年、老年、死亡。不仅原人如此,翻开任何文明人的履历,也都是以成年、婚姻、生子、死亡作为一生的概述。这一系列人生阶段的层层转变并不单纯依赖个体的实际年龄,而是由相关教仪做主要凭据。不少部落中,新生儿诞生之初是没有灵魂的,直至成长到一定阶段,经由巫师的洗礼,才可被称为人,而未经葬礼的则永远不能进入亡者世界,与那里的祖先社会聚合。“过渡礼仪模式”的界定前提是“礼仪”“仪式”,即有宗教性、巫术性、象征性、过渡性的人类行为。在每一阶段的人生仪式中,“他们必须停止、等待、通过、进入,最后被聚合”[2]33。对任何部落而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未开化民族中也会引起神秘的敬畏感,往往被视为黑巫术的携带者,他们常由村长接待,因为较之旁人,部落的头领拥有更强的免疫力。即便如此,任何外来人进村都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从村外到村内,慢慢进入直至被部落接纳,这些过渡仪式的根本就在于“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2]5。
对民众、国王、神灵三者关系而言,民众在身体机能方面处于劣势,这意味着多数情况下,教仪都是围绕民众“求取”与神灵“赐予”这一主题呈现。以干旱为例,经年不雨造成的颗粒无收使国王履行求雨职责,在渴求神灵赐福的同时许诺相应的回馈。至今中国不少边远地区仍有还愿一说,一旦心愿达成,便如数实现许愿时的承诺,否则便是亵渎神灵权威,容易招致祸患。早期社会,国王与神灵有着类似契约的微妙联系,灵力将国王从平凡世界聚合入神圣世界,通过满足群体需要巩固国王地位,这类恩赐也将由国王赴死来完成回礼义务。
总体而言,国王的加冕仪式的最主要目的是俗民的圣化,其特殊身份使之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道天然屏障。“禁忌”一词同时针对神灵与恶灵,由于“这种神人既是造福也是降祸的根源,对他不仅要加以保护,同时也要予以防卫”[3]306,不洁与神圣构成“禁忌”一词的两个方面。早期社会对于月经初潮的女孩、产妇、杀人者、悼亡者都有一系列具体的禁忌条例。在某些部落中,国王在任期间脚不能沾地,防止灵魂与地面接触造成灵力受损,日本早期国王的一生几乎都困在椅子上,不得自由。传统理念认为,任何携带圣洁之气的人或物都不得与地面接触,地下是鬼魂真正的藏身之所,时常会到地面游荡侵袭。在弗雷泽著名的交感巫术理论中,根据接触律原则,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互相作用,于是国王的名字、头发指甲等附属物对国王之外的其他人构成禁忌,与此同时,国王也需与俗民保持距离。因此,国王与平民之间实际存在两组禁忌圈,双方各行其是,互不干扰。
综上,个体身份的成功转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必经的分隔期、边缘期与聚合期同部落转危为安的过程大致吻合,其中巫术仪式成为此彼转换的节点。所不同的是,国王身份转换仪式的主要对象是集体神灵,人们渴望通过娱神进一步拉近人神距离,索取丰厚回报。个体身份转换仅是针对每个人自身的灵魂,从一年龄到另一年龄,一职业到另一职责,便于人生阶段的划分和评介。
(二)国王葬礼:死亡——复活
有关学者在对早期丧葬仪式的调查中,提出了二次埋葬的概念。二次埋葬与临时埋葬相对,当部落中有人去世,族人通常将尸首停放一段时间,等到皮肉腐烂,再捡取死者的骨骼入殓,或者将尸首埋在较浅的土层中,待腐烂之后,再将骨骼挖出二次埋葬。此种做法的现实依据是人们认为刚死的尸体是不洁的,将处于污染状态的死者就地埋葬不利于灵魂的净化,只有通过停尸使之自行腐烂消解。实际上,早期民众对生与死的概念与现代人大相径庭。死亡并不是一个能在瞬息之间完成的行为,机体的生理现象并不能构成死亡的全部。人死后,个体的灵魂便立刻面临两个世界的尴尬处境,肉体的不洁使他不能贸然地与阴间祖先社会聚合,停留在阳间又会被视为恶灵,给活人带来危险。因此,从停尸到彻底消解的时间间隔正好给肉体与灵魂提供从一个阶段迈入另一阶段的缓冲期,在肉体洁净的同时保证灵魂能平安到达死者的世界,进入新一轮的转世再造。于是,“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它也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它在转变的同时也在再生;在毁掉旧身体的同时也在形成新身体”[4]35,在一些必要仪式的辅助下,灵魂与洁净后的新身体结合甚至会产生比过去更高级的存在形式。
“无论对个体或群体,生命本身意味着分隔与重合,改变形势与条件,死亡以及再生。其过程是发生动作、停止动作、等待、歇息、再重新以不同方式发出行动”[2]188-189,当我们再度审视早期生与死的关系时,发现葬礼的存在不单纯是生者与死者的告别,更多的是死者通过净化重获生命的过程。《金枝》中,国王的献祭礼不难发现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欢庆场面,刽子手将国王皮肉宰割分食,群众饮国王的鲜血,这些残酷骇人的举动实质上加速了国王尸首的净化,同时促进神力的再次聚能。所谓“神人”,正是一个通过他的神圣死亡成功地战胜了死亡并将他的信徒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形象,死亡获得了生命被排斥与整合的双重含义。因此,献祭仪式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杀戮,恰是灵魂取得对死亡的绝对胜利,迎接另一段纯净美好生活的开端。
(三)权力更替:神权——政权
摩罗在《国王的起源》中就《金枝》中的国王制度给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评介——无人愿意染指的王冠。从国王出现早衰就必须赴死这一事实来看,公众所加给国王的责任,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由于部落领袖的主要功能乃是通过祭祀活动与神灵沟通,谋取赐福,因此,国王的权力并不是建立在暴力与玩弄权术的基础上,而是确确实实为老百姓谋求利益福祉,“只有在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指挥自然进程、为臣民谋福利的情况下,他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5]258列维·施特劳斯对早期社会的酋长制度有独特的见解,“酋长是被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愿意组成一个群体而存在的理由所在,而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群体觉得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而制造个酋长出来”[5]401,于是早期国王掌握的权力与后世君主手中的政权大相径庭,能否得到族人认可、一以贯之地满足成员们的物质需要、时刻精力充沛从而保证神灵力量的强大成为原始国王集权与丧权的现实标杆,“权力来自同意,权力靠同意来维持其合法性”[5]402。
从早期经济状况来看,部落首领拥有比常人更为可观的财富,以“库拉”仪式为例,那些能够代表所有者地位的臂镯项链,多是在首领圈内相互流通。但是这种所有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关系,任何人都不会选择长期占有库拉宝物,对物品暂时的所有权的主要目的是增加部落头领的声誉。与“库拉”仪式相对的则是“夸富宴”,又称竞技式呈献,经济实力雄厚的部落大摆宴席、席间刻意破坏珍贵艺术品,通过炫耀财富确定人际或人群间的等级高低。“强大的主要表征是富裕,而富裕的主要表征是慷慨”[6]144。实际上,当部落头领的财富累积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他常会主动分发财物,与亲族分享,等级愈高,维持部落经济水平一致的责任就越大。在原始观念中,占有恰恰是为了赠予,通过将财富送出而积极地享受占有财富的快乐。更有甚者,头领的财富常被族人洗劫一空,而头领却无处申冤,抢劫成了原始部落正常的生财之道。就此,早期国王头衔并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反而因为注定的悲剧命运令人敬而远之,他享受到的特权源于民众需要一位神气饱满、身强体壮的领袖帮他们参透天机,因此当国王日渐年迈、气息奄奄,民众便以强烈不满、极其冷漠的态度表达对国王的零容忍。由此可见,早期的首领制度更倾向于文明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
与此同时,民众同时扮演着国王的仰慕者和刽子手,这种相互融合又二元对立的微妙关系使得历史发展进程中上层阶级与底层人民的隔阂有迹可循。“杀王仪式”随着时代推进渐趋和缓,国王可通过出让、拍卖王位寻找替死鬼,或以死囚代替,甚至国王不需要真正赴死,只用在刑场上配合演出糊弄天神。人类文明的发展彻底颠覆国王的命运,国王凭借巫术将权力变质,成为一家一姓的专属,将一个民主制度更迭为一个君权制度,或者说更迭为一个元老寡头统治,国王由早期神灵代言人转以君权神授,喻示着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宗教领袖向政治领袖的双重过渡。以中国封建君主为例,他们同样坚信苍天庇护,相信天象的出现源于天神的情感好恶,皇帝更是以天子自居。流星、地震常被认为是异端,皇帝常通过祭祀、罪己诏等形式反省功过,但绝不可能为讨好神灵献祭。彼时,天神只是名义上的万物之主,更多的实权掌握在人间的国王手中。如果说民众与神王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那么君王与民众则以统治与被统治区分阶层。神权甚至为政权粉饰,保证君主正统地位,成为特定姓氏家庭的护身符。
通过对早期国王身份的辩证探析,原始国王经历了由人到神人再到祭品的重重转变,身份更替同时伴随着从世俗到神圣,从死亡向永生的迈进,早期国王的产生和献祭都基于部落民众的现实需要之上,没有政治意义上的国王,只有“呼风唤雨”的国王。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也为国王提供了摆脱献祭命运的救命符,凭借巫术礼仪的辅助,国王从天神的背后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世俗权力的独裁。
三、人、王、神空间秩序的维持
以加冕、献祭为程式的过渡礼仪是部落某个体由平民转为国王(圣化)再由国王成为祭品(去魅)的平行位移,同时构成人、王、神三者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垂直过渡。普通人经由加冕仪式获得国王身份,原先游离的“电子”,位于边缘化模棱两可的新人通过相应的举止行为,如宣誓、舞蹈、唱歌、接受信物等,在仪式中反复强调、强化新的“自我”意识,与旧我渐次脱节。换言之,从这个仪式开始,父母、姐妹兄弟、好友等文化符号所代表的含义都在慢慢虚化、淡化,而神、禁忌、权利与义务则越来越近,清晰地呈现于日常生活中,不断左右新人的生活。
就“人——王——神”三者空间结构上看,人神沟通是目的,王是中介。民众担心个人诉求无法抵达神的耳边,于是创造出王,借王的口、手代替民的口、手。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王催生了过渡礼仪,也不是王一开始就在维护该秩序,而是民众灵魂信仰的成型过程中,产生了王,王的身份是民众确定的,是民众经过选择之后赋予某某的身份。于是,加冕强调的是一位新人将要进入的阈限、匿名状态和封闭性的、遵循与服从的生活方式。因此,献祭的内涵便逃不开国王在享受一定的特权之后对民众的“反哺”“报恩”,《金枝》中,国王赴死的同时也带走了部落民众在世间的一切罪恶,王以个人的血肉之躯为集体净化,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替罪羊”的角色。但是,献祭的诱因仍然归结于神灵的“不死论”“青春论”,一任又一任国王前赴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仍是神灵长生不老观的代价,由此观之,国王在讨好民众之后,依然继续为神灵服役。在“人——王——神”体系中,人为下,神为上,国王由下方诞生,按时按质替下方传送讯息,又及时为上方反馈,在某个时间点又被上下方合而诛之。反观《金枝》开篇中那则内米湖畔的神话,一位逃亡的奴隶心惊胆战地守卫圣树,随时有丧命的可能,早期国王以个人前途的悲观消极确保着“人——王——神”体系的安定稳固。当国王权力进一步膨胀,义务性角色转为指挥性角色,神权一跃而为集权,三足鼎立的格局沦为二元对立、强制命令与绝对服从。王不再是人神沟通的转接点,他开始发声、指挥、决定、制裁。可以说,在经历了千百年的沉寂之后,他用王冠代替桂冠,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加冕,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必须承认的是,以政治国王为领导的社会依然安定稳固,如果说早期神王的维稳手段是“讨好”“自戕”,那么新王则以更高水准的法律、军队、官僚完成长治久安、和谐太平。
结 语
早期社会的阶段性特征表明个体与事件都是在无数次转折中实现各自的圆满,从好到坏、从无到有的进程是以仪式作为关键节点,同样,原人的生命也是由具体仪式来完成人生阶段的过渡,这被范热内普以形象的“跨越门槛”(threshold)指称。《金枝》中,加冕与献祭是国王身份转变的关键教仪,在身份更替的背后,更牵扯到早期宗教信仰、权力更迭乃至初民的生死观,而神王到政王的转变更是“人——王——神”空间秩序既破又立的再定位。于是由人到神,由神到祭品的程式,实际上是早期社会原生态意识团的真实反映,过渡礼仪虽然是线性的进程模式,但它同时亦是多层次的,在每个阶段仍可以划分出更小的过渡礼仪,可从中窥察其核心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