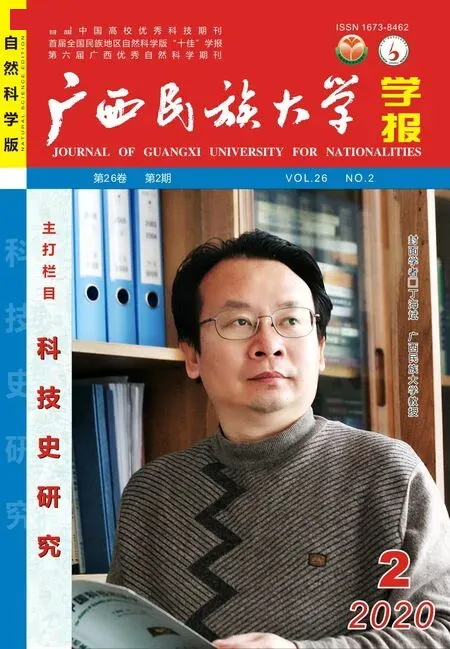跨学科的科技史家*
——丁海斌教授访谈录
万辅彬/问,丁海斌/答
万辅彬(以下简称“万”):海斌老师,您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相识的吗?
丁海斌(以下简称“丁”):永远难忘! 人生是由很多偶然组成的必然.如果没有那次与您的偶然相遇,如今我们也就无法坐在一起饮茗论学.那天,您作为前辈、领导来参加科技史的学术会议,本应住单间,但您不肯搞“特殊化”,所以才有了与我这个睌辈、后生(当时我的确还很年轻)共居双人间的特殊经历.那天您还送我一本您的铜鼓研究方面的著作,至今记忆犹新.另外,由于会议期间和您同住一室,我们的房间陆续有学者来访,因此我也有幸结识了不少科技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您论学兴致颇高,我们曾谈起“李约瑟之问”等诸多学术话题,很是尽兴.如今回首过往,真是心向往之.
万: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一直相互关注对方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后来我发现您不仅在档案学领域做出了很大成就,而且在科技史和历史学两个领域都有骄人的成就.
丁:独特的学术环境、特殊的学术机缘、广泛的个人兴趣和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再加上近40年来在学术研究上从不敢懈怠,偶然间竟造就了今天我这样一个跨学科学者.我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档案学——主要学术方向是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哲学)、档案史(普通档案史与科技档案史)、档案历史语言学、电子档案管理;历史学——中国古代陪都学、沈阳地方史;科技史——科技文献研究、“官科技”研究(可以扩展为“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社会组织形态”研究)等.其中,多数研究方向都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外,我还发表过一些文化杂文.
档案学是我的本学科,也是我学术研究的母学科.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科技档案管理学,是它让我进入科技史界;因研究清代盛京档案,我由此进入中国古代陪都研究领域.
20世纪90年代因我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开展相关研究,从而进入文史哲的研究领域.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就必然研究档案史,而从档案史到历史学,这具有学术上的必然性;研究科技档案必然研究科技文献,而科技文献恰恰是科技史研究的基础,所以随着科技文献学的建构便自然而然地进入科技史学科之中.近20年来,我与科技史界、历史学界的交流相对多些,当然这也是各种机缘使然.
万:您的36本著作,260多篇学术论文,横跨档案学、科技史和历史学三个学科,说明您是精力充沛、成果涌流的跨学科学者.
丁:“成果涌流”不敢说,但我的确是一个努力治学的学者.努力+机缘=今天的我.当然,今天的我并不是最好的我.我经常说,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不懈地追求学术真谛,永远奔跑在追求学术之路上,不因种种诱惑而停下自己的脚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尽管我也曾因那些诱惑而左顾右盼,但所幸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这是我人生最幸运的地方.
万:听说最初一些师友十分不理解,以为你是在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实际上您是抓住机遇,在几个方向都做到了“做深做细,做大做强!”
丁:是的.具体而言,我是档案学专业出身,又是科技哲学的博士.从1985-2020年,大约34年的时间,横跨了几个学科,近20年来我先后担任过档案学、中国古代史、中国科技史、法律史、民族学这几个学科的导师.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1)档案基础理论(档案哲学);(2)中国科技档案史;(3)档案历史语言学;(4)中国古代陪都学;(5)中国古代科技文献;(6)电子档案管理研究;(7)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社会形态研究(以“官科技”研究为主);(8)沈阳地方史.
我的思维比较活跃,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一旦发现“新大陆”,我就会立马深挖下去,在一段时间内会不遗余力,尽可能地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体系.在上述前5个研究方向上,学术体系都已趋于成型,有一种蔚然成林的感觉.我自己也颇感安慰,后来熟悉我的朋友慢慢也就理解了.
万:我知道您在每个方面都写了几部书、数十篇文章.
丁:其余3 个方面,由于力所不逮,尚未建成体系.其中,“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社会形态研究”我是想继续做下去的,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逐渐构成较成型的理论体系.
在沈阳地方史研究领域中,我参与了《沈阳通史》《沈阳文化史》《沈阳城市发展史》《沈阳工业史》等书的编写工作.其中,与科技史关系最为密切的《沈阳工业史》三卷都是由我主持编写的.
万:从您的成果看,您在科技文献学和科技文献史方面做出的成就又好又快,让很多以科技史为专业的人士都感到汗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丁:“又好又快”不敢当.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是科技档案史的研究使我走进了科技史学科.我进入高校后,最早讲授的课程是“科技档案管理学”和“科技文件材料学”.当我开始讲授这两门课程时,惊讶地发现:当时的《科技档案管理学》竟然没有“史”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科技档案、科技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学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件巨大的缺憾.就像一个孩子是捡来的,我们既不知道他从何而来? 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谁? 也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这个孩子站在那里,我们除了他的外貌之外,对他一无所知.这就非常尴尬! 没有历史,事物的完整性和清晰性就大打折扣.没有“科技档案史”的《科技档案管理学》是极不完整的学科.
鉴于此,那时候我立志要解决这个问题.实话实说,科技档案史作为档案史里面的一个比较专门的领域,比较难.但是问题越难,最后的收获就越多,最后的成果也越丰硕.事实上,我在科技史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都来源于科技档案史的研究,而且还远远没有收获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我出了一本《中国科技档案史纲》;2007年我将其完善成为《中国科技档案史》;到了2011年,又出了一本《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研究》.这几部书把这个体系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它是我在中国档案界的第一个具有个人特征的“标签”,也是我进入科技史界的入门券.
万:科技档案史的研究对您后期的研究影响非常大,您后来又从科技档案史发展到科技文献史.
丁:我今年刚刚出版了《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就是从科技档案史的研究上发展而来的.此前还出版过《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并且从古代科技档案史又发展出了“官科技”和古代科技机构、科技制度方面的研究.这些方向的研究与科技档案史的研究关系非常密切.我刚开始做科技档案史研究的时候还很年轻,如果我现在再做的话,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做了.
万:怎么做呢?
丁:我会把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史、中国古代科技机构史和中国古代科技制度史三方面并在一起做.我称其为同步套裁.
万:为什么要一起做呢?
丁:因为在研究科技档案史的时候,一定会涉及机构的问题.如果没有机构的话,又何来档案之说呢?它是从机构来的,而且还一定和某些制度相互关联.我当初在研究科技档案史的时候,其实把科技机构的问题、科技制度的问题都密切接触到了,所以如果现在来做的话,我会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做.
万: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您的研究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领域逐渐扩大.
丁:确实如此.通过科技档案史的研究,后来逐步延伸到文献史、机构史、制度史.
万:在科技档案史的研究中,您对哪些部分的印象最为深刻?
丁:在科技档案史的研究中,地图档案、天文档案、医药档案、工程档案等方面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它们的史料挖掘最初都很艰难,都让我印象深刻.但最深刻的还是对《周礼》的科技档案史研究.
万:《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您是怎样研究这部典籍的呢?
丁: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20多岁且丝毫没有先秦史研究经验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史学前辈的指点:著名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指点我去看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和郑玄的《周礼注疏》.我在辽宁大学图书馆古旧阅览室枯坐了整整3个月,方才啃下这两部书及王安石《周礼新义》等《周礼》注疏与研究作品.在发表了《〈周礼〉中记载的科技档案与科技档案工作》一文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二十篇论文.但是,《周礼》的相关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很多未解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解决.
万:我很期待您对《周礼》的进一步研究.
丁:在这里,我要批评一种学术研究的浮躁态度.有许多学者研究《周礼》,使用《周礼》的内容作为史料,但认真读过《周礼》的学者似乎不多.在中国知网,我用《周礼》做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出文章数为926条;而使用《周礼》进行全文检索,得出来的数字竟高达198,963.也就是说,有这么多学者在文章中提到《周礼》,难道他们都了解《周礼》是什么样的一部书吗? 事实上,《周礼》作为史料,被误读、误用的情况极为普遍,其中也包括科技史界.
万:能再深入地谈一谈您对《周礼》的研究吗?
丁:《周礼》无疑是科技史研究中的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我重点谈以下几点.
第一,《周礼》本名《周官》,它是讲官制的.所以它主要与科技制度史有关,是研究先秦科技制度的重要史料,其“天、地、春、夏、秋”各篇都包含有科技制度方面的内容.佚失的《冬官·百工篇》与科技史的关系更为密切,应是主要记载手工业制度方面的内容.后人补代之以《考工记》,但其体例与《周礼·冬官·百工》并不一致,所以其缺憾是难以弥补的.
第二,不可将《周礼》所记简单地作为西周的史实.《周礼》并不是纪实性作品,而是一种创造性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为西周及春秋战国的历史史实,也有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设计与设想.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西周或春秋战国的历史史实,要区分历史史实的年代——西周或春秋、战国,也要区分史实与作者自己的设计与设想.在这个方面,我做了一点工作,通过寻找旁证的方法,基于目前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周礼》中的文档词汇做了初步的区分,将研究成果《〈周礼〉文档名词再研究》一文发表在了《档案学通讯》上.如果时间许可,我希望可以对《周礼》全书的主要内容做一个初步的考证.
万:在中国科技史界,您的中国科技文献研究很有影响.请问:您研究中国古典科技文献,除了因研究科技档案史而打下了相应的学术基础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动机呢?
丁:我进入科技史界之后,发现科技史学科的教学活动中似乎没有专门的科技历史文献学.我曾经问过一个权威的科技史研究机构:有没有开设科技历史文献学的课? 怎么上的? 谁来上的? 他们回答:这门课实际上是他们机构里的一位历史学背景的博士后在上,内容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学,并不是我们专业的科技历史文献学.后来发现即使个别高校开设了科技历史文献学这门课,但也缺乏专业性、系统性.实话实说,我们的科技史研究生这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很不够.
针对这一情况,我就立志去做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研究.把完成《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和《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作为我的学术使命.现在,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这项使命.换句话讲,也算是不辱使命.
万:能仔细谈谈您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研究的基本情况吗?
丁:目前主要成果有两部:《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和《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第一部书是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通史,第二部书则是较完整且专业的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著作.这两部书可以搭建起中国科技历史文献学一个大的框架,它们可以担负起中国古代科技史学科文献学教材的使命.
当然,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还有一些分门类的、细致的东西需要做.现在,我开始做数据库方面的工作,正在和科学出版社合作.同时也感谢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学科有这个条件能够支持我部分经费.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说.科技史前辈张秉伦先生曾经跟我通信探讨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学的教材建设问题,当时我与张先生素未谋面,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张先生主动联系我,其真诚溢于言表,实在是晚辈学者学习的榜样.可惜我们未及深入沟通,先生即驾鹤西去,没有达成我们之间的合作.惜哉惜哉! 愿先生天堂安好!
当然,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还需要开展更多的深入研究.另外,中国科技史学科还需要开展《中国科技史史料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当然,有《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作为基础,《中国科技史史料学》的出现也就为期不远了.
万:在中国科技历史文献方面,您还有一些其他后续的想法吗?
丁:首先,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研究与教学要有一支专业队伍.目前各高校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还很少,应该加紧培养.我现在正在带一些高校的中青年学者进行古代、近代科技文献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人员较少且缺乏机制上的保障.广西民大科技史学科如果开始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工作,让我做一点以老带新的工作,应该会有一些成效.
万:在考察您学术研究经历的过程中,我发现您具有很明显的发散性思维的特点.那么,从科技档案史的研究中,您的发散思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又取得了哪些意外的收获?
丁:研究科技档案史的时候,我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都发现了一些相关问题,并开始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这些领域上.
纵向上,科技档案是科技文献的一部分,研究科技档案史必然会研究科技文献史.所以在我研究科技档案史20年后,便又转向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和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的研究工作.
横向上,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科技档案主要产生于官方科技活动中,而且是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主体.于是,我又转而进入中国古代“官科技”的研究领域(后来我更明确为“科技活动的社会组织形态史——国家科技、民间科技、宗教科技的历史研究”).
万:您使用中国古代“官科技”这个名词是不是受“官文化”等名词的启发?
丁:是的.要想了解古代科技档案的产生、内容、形态等问题,不清楚古代科技活动的社会形态、制度是不行的.这些科技档案产生于当时的科技活动实践,科技活动实践是它们的本体.“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1991年发表于《学术界》的《论“官科技”及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万:您的中国古代“官科技”研究让人印象深刻,能展开来说说这个问题吗?
丁:中国古代的科技档案主要来源于官方的科技机构.有没有来源于民间的呢? 有,但是民间的多数不能够保存下来,不成规模.所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主要是官方的,即“官科技”.
我觉得中国古代“官科技”的研究我只是起了个头,比如说要做一个“中国‘官科技’(国家科技)发展史”,从古代、近代到当代,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目前,我在这个方向上的著作主要有两部:第一部是《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这是我的博士论文,于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部是今年正在出版过程中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官方、民间、宗教三大作者群体研究》,这个可以算是一部古代通史.上述研究还不能说已经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科技群体的研究框架.
万:您在《学术界》发表了文章之后,似乎在“官科技”的研究方面中断了一段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重新进行了这个课题的研究呢?
丁:“官科技”的研究最初的确是我的“业余”研究.所以,在1991年《学术界》上发表《论“官科技”及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一文以后,停止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2004年我“带艺投师”跟随陈凡教授读科技哲学博士,又开始对“官科技”接续研究.
与陈凡教授结缘大约是在2004年,我与陈凡老师等十几位大陆学者受邀访问台湾高校.期间,我与陈凡教授一见如故,并因对中国科技史的共同关注而终生结缘.我原本是打算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的,当时,我正因工作上难以脱身无法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而苦恼(当时我已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工作上不允许我长期离开岗位去北京读博),而与陈教授的相遇使我得到了在沈阳读博的机会.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如果没有读科技哲学博士的这段经历,我不可能在中国科技史领域走得这么远.
在读科技哲学博士期间及其后,我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古代“官科技”的文章:《李约瑟现象的“官科技”解读》《论清代科举与“官科技”》《清代“官科技”体系中的高层群体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官科技”的——《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也正因如此,陈凡教授更是成了我终生的良师益友.
万:每个人在他的学术道路上都会遇到贵人指点,恩师提携.
丁: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件学术往事.1991年我的《论“官科技”及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一文的责任编辑是王光照先生.在发表我的文章之前,王先生特意寄书信于我,大气磅礴的书法,让我印象深刻,信中充满了对年轻人的期许与鼓励之情.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多次与一些前辈学者通信,他们表现出来的学者气度令我终生难忘.前辈学者们的鼓励、期许,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成为我前进的重要动力.在这里,我借这个机会,向王光照、吴宝康、王传宇、陈智为、邓绍兴、王渝生、孙文良、张秉伦、陈凡、王雅轩、胡玉海、王海晨,还有万老师您等前辈谨致谢忱.
万:在“官科技”研究的问题上,您还有其他的打算或规划吗?
丁:从“官科技”问题出发,我将此问题扩展为“人类科技活动的社会组织形态”研究,即对“国家科技、民间科技、宗教科技”这三种科技活动的社会形态进行研究.我的中国古代“官科技”研究,实际上是这三个视角里面的一部分.“官科技”这个名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征.如果在更大范围内讲这个问题,应该用“国家科技”这个名词,它是指体制内的.当代中国的科技群体,主要是体制内的,少量是企业的(我将其归到“民间科技群体”).第三部分是宗教的.当代“宗教科技”的力量弱了一些,但从历史上看,宗教这样一个群体在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按照这三大群体去研究科技史的发展,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科技史的研究视角,非常重要.就像现在我们在高校做老师,一定会受到高校的体制影响,而且影响非常大.我们要不停地填表,为什么填表呢? 因为需要对国家有个交代.国家、民间、宗教,实际上它代表的是科技体制.
科技史,本质上是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既然是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而科技活动又是一种人类的社会活动,就必然存在着人类科技活动的社会组织形态问题.既是如此,必然涉及人类科技活动在什么样的空间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这决定着人类科技活动主体的存在方式,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目的、目标、方式与归宿.这是古今中外的人类科技活动都存在着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涉及人类科技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它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科技发展.当然,它是一个科技史的问题,也是科技哲学和科技社会学的问题.同时,它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科技史界有责任对这个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
关于以上问题的研究,我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该问题主旨宏大,内涵极其丰富,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希望得到科技史界同仁的关注!
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且很庞大的科研计划,您觉得要实现它需要什么条件?
丁:我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将来有条件时,首先做一个“中国科技活动社会形态史”,希望能贯通古今.有条件的学者可以做一做国外的,特别是欧美的“科技活动社会形态史”.当然,除通史类研究外,一些断代的、专题的甚至是更细致而微的研究也是重要的.
在这里,我也谈谈科技史学科的某些特殊性问题.科技史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类型和不同的研究思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这个学科的人员队伍比较复杂,不是一种单纯范式的学科.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要谈谈科技史研究范式特殊性的问题.科技史研究,它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自然科学的范式,一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有一些纯自然科学出身的人,他们受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影响比较多,他自然而然把这种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带入到科技史的研究中来;另一部分人,比如说我,纯文科出身,虽然接触科技方面的知识比较主动一点、热情一点,但毕竟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所以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特征.从我的作品中大家可以看得很明显,我的中国古代“官科技”研究就具有明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特征.所以在科技史界,实际上有这么两种不太相同的研究范式,然后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角度和方法都有一定的不同.
万:这种不同是好事情,多元的研究角度、多样化的研究队伍,对学科本身的发展、完整性和研究内涵的丰富都是有好处的.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您在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并在科技历史语言学方面已经有所涉猎,在这个方面您有什么计划吗?
丁:我在历史语言学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也有一部书计划出版.其中涉及了一些与科技史相关的内容,如“地图”“图籍”等词汇.我本人并没有多少精力进行科技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但有中青年学者跟我合作,以他们为主开展相关研究,如沈阳建筑大学的吴哲副教授(工程哲学博士)在工程史方面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我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使用了文献学、计量语言学、数字人文等方面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进行专业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可以作为科技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借鉴.进行科技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也是科技史研究深化的一种表现.
万: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者,您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有哪些感受呢?
丁:中国高校的现行体制不适合跨学科研究,因为学者早早地就被钉死在某个学科上了.学科评估、专业评估、学位点申报、项目申报、学者评价等一系列学科建设、学术评价活动都划定了严格的学科界限,高校只需要“某一学科”的学者,而不是跨学科的学者.在资源分配上,也是具有很强的学科壁垒.某某学科的学者要申请其他学科的项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如果要做一个跨学科学者,首先要少一点功利心.如果从功利出发,就不要做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自然发生的,是纯学术的,一般与功利目的无关.这是我个人的切身体会.
其实,跨学科本来是学术研究的常态.学术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是跨学科的.古今中外所有大学者几乎都是跨学科的.试想:有哪个学科与哲学、历史、语言、数学不无关系呢? 学科之间本就是相通的,相通是正常的,跨学科也是正常的,封闭是不正常的.但现在的学术机制把它反过来了,跨学科变成不正常的了,跨学科学者变成了稀有动物,起码现行学术环境是不利于跨学科学术研究的.
就我个人而言,除功利性淡些之外,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我做学问的方式都是从问题出发的,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学科.学术思维到哪里,我的研究就到哪里,从不考虑学科界限.但学者总是有职业的,有从事的、学习的和专业的,所以这些问题往往围绕着自己的职业、专业展开.我本人是从档案学专业(我的职业与我学习的第一专业)出发的,也受科技哲学(我学习的第二专业)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从问题出发.
在学术界,有些人学术界限观念很强.我见过一些学者,研究辽史的要和研究金史的明确分开,研究清前史的与研究晚清史的分开.界限要分清,不分清楚就会被人笑话.我曾经也是一些人私下里讲笑的对象,但现在很少有人笑话我了.因为我的几个体系日趋成形,也得到了相关学科学者的认可,大家自然无话可说了.但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你要挺过来才行.研究的问题多,自然花费的时间就多.35年过去了,我研究的几个学科体系还在构建中,虽然说学无止境,任何研究都是没有止境的,但多个体系的建设还是要比单一体系的建设艰难一些.我并不是一个“聪明人”,因为“聪明人”在这个功利社会中是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我是一个透明的人,是一个执着的人,是一个不管别人怎么说只管做自己的事的人.现在有点做成的样子了,就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了.
万:您在历史学方面也颇有成就,特别是在中国古代陪都学和沈阳地方史研究中成就卓著,能简要谈谈您是怎样切入中国古代陪都学研究的吗?
丁:由于地缘的关系,我早年研究过清代故宫档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清代沈阳的历史,其关键是它作为清朝陪都的历史.当时我担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学院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东北地方史、清史.为了带动学院的老师们研究东北地方史和清史,也出于我个人的学术旨趣,我主动承担了“清代陪都盛京研究”的课题.课题设立之初,我只是把它作为清代的特殊现象来对待.但深入研究之后,让我大开眼界,发现陪都现象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学术界此前并没有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这激发了我新的研究兴趣.在《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一书里,我对中国古代陪都现象做了简单的描述,这部书成为我研究中国古代陪都学的滥觞之作.
万:后来您在中国古代陪都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丁:截至目前,我在中国古代陪都学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完成了中国古代陪都研究方面的第一部断代史——《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二是完成了第一部中国古代陪都通史——《中国古代陪都史》,把中国古代陪都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具有标志性意义;三是目前我正在进行《中国古代陪都制度研究》(暂定名)的撰写工作;四是关于主辅(首都与陪都)关系的研究,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历史现象.除以上提到的著作外,这个方向上我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中国古代陪都学的研究还涉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问题,我发现了“多京制”的问题、京都“主辅摇摆”问题.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值得我去继续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加到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来.
万:能再谈谈您的沈阳地方史的研究吗?
丁:我的沈阳地方史的研究也是从《清代陪都盛京研究》这部书开始的.这部书出版后,我得到了沈阳地方史界同仁的认可,被他们“强拉”进沈阳地方史的研究工作中.后又陆续收到《沈阳文化史》《沈阳城市发展史》前辈主编的邀请,我无法拒绝,所以我又参加了这两套书的编写工作.后续又主持完成《沈阳工业史(三卷本)》的编写工作.
万:除以上研究外,您觉得您还会在哪些方面继续进行跨学科研究呢?
丁:我思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对新问题特别敏感,善于发现问题,我经常说我的最大缺点就是“停不下来”.
万:这哪里是缺点,问题意识强是优点!
丁:在我当下的研究计划里,等待完成的著作类选题大约还有20个,文章类选题更多一些.它们包括档案学、历史学、历史语言学、科技史、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档案学、科技史、历史语言学与当前的工作关系较大;哲学也是从档案学延伸而来,目前在做的是经验哲学,是从档案哲学研究中扩展而来的,也是最近一两年要做的事;文学的计划主要是长篇小说和长篇杂文,也都有了思路,并各自有了几万字的初稿,但真正写它们可能要到退休以后了.
万:您作为一个跨学科学者,能谈谈您和科技史界的关系吗?
丁:相比较而言,除了我的本学科——档案学之外,我进入比较深的学术领域是科技史.所以关注并参加科技史的学术活动也相对多一些.当然,我的科技哲学博士的学习背景也是我加入科技史圈子的有利条件.跨学科研究者在科技史界比较多,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科技史学科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科技史界的学术包容性强,像我这样的跨学科科技史研究者也比较多,并没有太多局外人的感觉.事实上,我也受到了科技史界的关注和青睐,有多次正式加入科技史专业团队的机遇,东北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学科、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学科、山西大学科技史学科等国内多所高校科技史学科都曾对我青眼有加,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入职.像我这样跨学科的学者,对高校学科方面的要求与众不同.如果一个高校只有科技史学科,没有档案学、历史学等相应学科,我是很难加入进去的,而广西民族大学恰好科技史、档案学、历史学三者皆有,而且科技史学科、档案学科都有很好的学术积淀,这给我入职广西民族大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于是,在万老师您的邀请下,我欣然来到南宁.如今我已是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团队的正式成员,有一种归属感.
万:在科技史学术研究上,您觉得还有什么遗憾吗?
丁:在科技史学术研究上,我有许多遗憾.最为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能够带一个科技史的博士和博士后,我的几个学术研究方向都还没有很好的学术传承人.我希望在退休前的这些年中,能够在档案学、科技史、中国古代陪都学等方向上,培养出几个好的学术传承人来.
到目前为止,我做的与科技史有关的科技档案史和科技文献史要多一些.而科技制度、机构、群体、科技历史语言学等方面,做的相对少一些.在这些领域中,我只是拓荒者之一吧,给大家开个头.可惜的是,在科技史领域中这几个方向上目前做的人还很少.我个人认为它们在科技史领域中的意义是重大的.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成果本身无疑是重要的,但我认为它是最基础的,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为什么如此发展? 它发展的过程有什么经验教训?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本身,它有什么样的实践规律? 有什么样的活动机制? 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空间中活动的? 等等.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才能最终解释古人做了什么.希望我的工作,能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完整性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