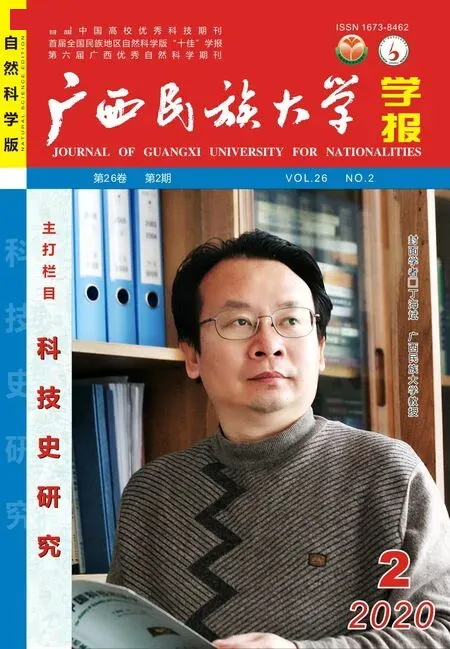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田 宇梁宏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西 南宁 530028)
0 引言
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根据《公约》第三章第十二条:“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订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1]这里所指的清单,在中国是指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①以下如无特殊情况,简称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经过十多来年的实践摸索,广西也基本构建起符合区情的非遗名录体系.如今,非遗工作已全面进入“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巩固抢救保护成果,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推动非遗事业可持续发展”②2017年文化部原副部长项兆伦同志在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的后申遗时代.在此背景下,通过对现有名录体系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补充和完善,是进一步做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
1 广西非遗名录体系建设的意义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各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非遗资源.这些珍贵的遗产是各族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是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激励广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截至2019年12月底,广西共有国家级非遗52项,自治区级非遗762项,市级非遗1406项,县级非遗4052项.实践证明,名录制度对遗产项目及所在社区都将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1.1 抢救、挖掘与保护非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遗主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各民族千百年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2]然而,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生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亡”的局面,一些依靠口传心授和行为传承的非遗正在不断消失.因此,在非遗工作的早期阶段,中国秉承“濒危优先”的保护理念,将一大批亟须保护的传统文化纳入非遗名录中.短短十多来年,通过政府、专家、社区民众等群体的共同努力,广西也构建起完备的名录体系.“非遗”从一个陌生、新鲜的外来词汇变成了受社会关注、认可的热门文化事项.实践证明,政府主导下采取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措施对于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是行之有效的.名录体系的建构无疑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抢救和复兴竖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
1.2 消解了社会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认识上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
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存在简单、粗暴的二元划分误区,即官方的与民间的、精英的与大众的、精华的与糟粕的、科学的与愚昧的,等等.甚至不少与宗教相关的文化事项被贴上“封建迷信”等污名化的标签,一度被禁止.这种狭隘的文化观认为,只有官方的、精英的才值得被保护和传承,而普通民众的文化是粗俗的、底层的,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进入国家管理的场所,成为国家认可的文化.[3]非遗的理念和内在机制正是对这一狭隘文化观的反思与批判.通过名录建设,大量原本不被认可的民族、民间文化得以正名,并且经政府批准而以此进入官方的文化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的桂剧、壮剧、邕剧、彩调、桂南采茶戏等地方戏剧得以与京剧、昆曲等,壮族织锦技艺与云锦织造技艺、苏绣、蜀绣等一道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曾经一度被禁止的毛南族肥套、京族哈节、壮族三月三等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一道被列为国家级民俗类非遗项目,成为今天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名片.
将遗产申报及其进入名录体系的过程,也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再研究、再认识、再理解,最终实现文化自觉.高丙中先生认为,它开启了新的社会进程,以文化共生的生态观念和相互承认的文化机制终结中国近百年的“文化革命”.[4]
1.3 使非遗保护更为规范、科学、有序
中国在名录设计上实行的是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自上而下的四级名录体系的架构.而在申报实践中,中国施行的是自下而上的申报制度,即由县级到市级,市级到自治区级,再由自治区级申报国家级.首先,它保障了不同民族或族群都有申报遗产列入名录的平等机会和权利.申报主体或群体可以从自身文化中选择代表性的项目进行申报,由此保证众多民族文化能得到相对平衡的申报与保护.[5]其次,通过申报、评审、公示、申述、复议、公布等一系列规范的程序,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申报的规范性、科学性、公正性.这样的制度安排,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对非遗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证明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1.4 为各民族提供了平等、共享的交流平台
非遗名录的内在机制强调的是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它倡导不用单一或纯技术的价值标准对多元文化进行评判.而文化多样性正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如前所述,各民族都有将自身遗产申报并被列入名录的平等机会和权利.名录构建优先考虑的是该文化事项是否代表了特定族群的文化认同和该群体是否愿意被这样的文化事项所代表.[6]遗产进入名录的过程,是将地方或族群代表性的文化放置于全社会关注的视域和国家认可的文化体系中各安其位,也正是实现“私权”向“公权”让渡的共享过程.[3]因此,名录体系也为广西各民族提供了一个平等、共享的交流平台,以达到学者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的.[7]
1.5 搭建起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实现广西文化强区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
广西地处中国南疆,有三市八县与越南接壤,陆地边境线长1000多千米.不少民族与东盟国家的民族同根同源,他们在语言、服饰、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等方面十分接近.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共有55项自治区级非遗属于跨国、跨境共享项目,如京族哈节、独弦琴艺术、瑶族服饰、壮族侬峒节等.这些跨国共享非遗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重要作用.以非遗名录为载体,搭建起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的桥梁,有利于讲好广西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有利于促进民心相通,经贸往来,更使得非遗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支撑和新的亮点.[8]通过名录体系的构建,就是要促进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更加广泛地加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来,为广西文化强区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
2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非遗保护的早期阶段,名录制度在抢救、保护广西优秀文化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度尚不完善,加上地方保护理念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致使广西名录体系建设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2.1 政府包办包揽导致名录建设政绩化、商业化
当前非遗保护的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9]在非遗保护的早期阶段,由政府主导是符合国情的.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广西在非遗保护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政府主导”在不少地方往往演变成了政府包办包揽,以至于“社会参与”仅仅成了一个口号.最后只看重非遗带来的政绩和经济效益,使得名录建设逐渐政绩化和商业化,而这两者恰恰是当下非遗保护中最致命的问题.[10]
首先,在评审中,为求政绩,不少地方单纯追求入选的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导致许多并不符合非遗定义或条件的项目混入名录,使得名录鱼龙混杂.这种情况在市县级名录中尤为明显.其次,政府的包办包揽导致评审往往只从行政官员或者学者的角度去判断,而缺乏文化持有者应有的立场,最终导致遗产核心内涵被边缘化,甚至扭曲化.最后,地方政府考核往往只看重入选项目的数量,而少有人关注申遗之后的保护成效.
2.2 分层级的名录体系容易导致文化阶层化
客观而言,非遗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文化价值本身是相对的、多元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项目进入名录的过程,就是用他者的眼光和标准对项目进行价值评判的过程.而遗产一旦进入名录,就会获得政策、资金、场地等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层级越高,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就越容易受追捧.而未进入名录或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却很少有人关注.
事实上,进入名录的项目毕竟是少数.例如,广西县级以上非遗共6272项,仅占普查资源线索总量的4.66%.未进入名录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样是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适应周围环境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同样值得我们珍惜、保护和传承.同时,由于非遗具有流变性和历史性,许多遗产在传承传播过程中会有跨越族群、社区的现象.[11]而遗产进入名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经济效益,容易导致出现抢注遗产的问题.在名录建设的早期,往往谁就先申报,谁先列入.未列入名录的地区则失去了被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该地区遗产项目的萎缩,甚至消亡.
这种偏离了非遗保护初衷的做法无疑打破了乡土社会里原有文化体系的平衡,从而出现文化阶层化的问题.可见,名录体系的构建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对文化进行筛选并将其置于不同层级,尤其是将资源过于集中在进入名录的项目和更高层级的项目时,客观上就容易破坏文化的多样性.
2.3 现行的类别设计容易将完整的项目肢解
《非遗法》将非遗分为六类,①(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在名录评审中,为突出可操作性,则将非遗分为十类.②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这种细化的分类制度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分类设计的本土化实践和理论贡献.它在框架设计和制定标准时,最大程度地考虑了普适性原则,尽力寻求遗产项目在该类别文化特质上的最大公约数.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突显遗产项目某方面特征和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会忽视或舍弃其他部分的特征和价值,从而出现完整的项目被肢解的问题.
一方面,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各民族在适应周围环境的生产生活中的伟大创造.当我们将遗产从整个生境中抽离出来作为某一种艺术或文学项目套进某一类别时,客观上很容易人为地割裂遗产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大部分文化项目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往往包含多重文化属性.也就意味着,在官方的现行分类体系中,大部分项目是跨类别的.例如壮族天琴艺术,既有传统音乐的属性,也有民间文学、传统舞蹈,甚至包含祈福仪式的内容,很难说哪一部分的文化属性更为重要.类似的项目还有壮族末伦(包含民间文学、曲艺、民俗三重属性)、侗族多耶(包含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三重属性)等.当为了符合某一类别的申报标准和要求时,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突显该遗产某一部分的价值和文化属性,而隐去了该遗产其他的文化价值和天然属性.这种特质上的“显”与“隐”很容易将完整的文化项目肢解.
2.4 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严重偏少,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
截至2019年12月底,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项国家级非遗.而广西国家级非遗子项目只有52项,仅占全国总量的3.79%,远远低于全国100 项的平均值,也远低于西部省区87项的平均水平.而与广西相邻的贵州省为140项,云南省为122项.贵州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就有国家级非遗72项.显然,国家级项目数量明显偏少,无法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关于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边境地区倾斜的政策.同时直接影响着广西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报及对中央非遗保护支持经费的争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广西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不利于民族文化强区的建设和民族自信心的树立.
2.5 项目定位不准确影响向更高层级的申报
在市、县级非遗名录中,部分项目在定名、类别归属等方面定位不准确,容易出现错误的价值导向,也直接影响了遗产往上一层级的申报.具体表现在:
(1)不少地区为突显项目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独特性,在定名时往往采取“民族的某一支系+项目本体”或是“申报地区+民族+项目本体”的方式.如白裤瑶打陀螺、白裤瑶年街、那坡彝族跳弓节、兴安瑶族刺绣等.然而,在中国官方公布的五十六个民族中并不包括支系,且在项目前冠以“申报地区+民族”的做法,容易将项目碎片化、行政化,既无法准确地反映项目存续和流布状况,也不符合非遗规律.
(2)部分项目类别定位不准确.如前所述,在中国现行的名录分类体系中,很多项目具有跨类别的文化属性,项目归类是申报和审批中的普遍难题.例如“梧州龟苓膏配置技艺”是第一批区级非遗项目,申报时主要考虑龟苓膏具有防治热毒、湿毒的功效,因此将其归为传统医药类.但医药行业并不将龟苓膏作为一种传统药方或药剂来使用.尽管其具有一定的药用功能,但该项目更侧重配置方面的技艺,因此放在传统技艺类更合适.
(3)部分市县甚至将物质遗产混入了非遗名录中,更是混淆了物遗和非遗之间的界限.
3 完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的对策
名录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的文化事业.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广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可通过以下措施可加以应对.
3.1 正确处理多元行动方的关系,保障民众在名录建设中的文化主体地位
根据《公约》关于非遗的定义可知,社区民众才是“文化”的持有者,是“文化”的真正主人.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民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应该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民众主导转换.政府在非遗工作中的主要作用应该是组织、参与或引导,专家主要负责咨询.两者都不应该越俎代庖,包办包揽.只有恰当处理多元行动方的关系,实现文化主客位的正常化,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名录体系建设的政绩化、商业化.
此外,要避免“社会参与”的口号化、民众文化主体的虚无化,必须在法律法规的层面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在名录构建过程中,不仅要获得社区民众的授权,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保障文化持有者的参与权、话语权和监督权.实现遗产申报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换,最终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12]
3.2 从自治区级层面做好非遗名录体系的顶层设计
(1)要从各级层面尤其是自治区级层面控制入选名录的项目数量.应依据非遗的定义和入选条件,从源头把控名录的门槛,提高入选质量,确保名录的价值导向.应避免为盲目追求入选项目的数量和层级,将遗产拆解或将伪遗产混入名录的做法.项目入选名录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应该是地方政府和文化持有者向全社会做出即将担负起遗产保护责任的公开承诺.
(2)在名录评审中,应改变“谁先申报,谁先列入”的做法.尤其在处理跨民族或跨地区的同类非遗申报时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以避免抢注遗产情况的发生.
一是对于在形式、内涵上均保持相对独立、完整的同类项目,均可列入名录.例如同是“打油茶”,但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在油茶配料、工具、制作流程、相关习俗都有各自的民族特点,是当地民众适应周围环境的经验总结和长期形成的民俗.因此,可以同时列入名录.
二是对于形式、内涵上大体一致的同类项目,可采取列入扩展名录的做法.例如“壮族打榔舞”是壮族民众以农具榔、杵为舞具模拟稻作生产的一种传统舞蹈.广泛流布于南宁市马山县;崇左市天等县;百色市田阳县、平果县等壮族聚居区.各地的打榔舞在舞具、舞蹈形式、内容上大体一致,因此可以将各地整合作为申报地区以扩展项目的形式列入名录.
三是对于明显以某地为核心,其他地区为辐射区域的项目,可以采取以核心区域为申报地和保护单位,但同时应公布项目的流布区域.项目保护单位也不仅仅只承担本地区的项目保护职责,还应作为牵头单位负责全区其他流布区域该遗产的保护.
(3)建立自治区级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过去的十多年来,自治区本级可用于非遗保护的经费十分有限,非遗长期处于“洒面粉”式的保护阶段,导致非遗保护工作缺乏重点,保护成效不明显.有些急需保护的项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因此,可以设立自治区级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针对性的采取“抢救性保护”.此外,建议设立自治区级优秀实践名册,主要侧重于遗产保护成效的示范性和推广性,为其他地市提供借鉴、参考.
3.3 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树立整体性保护理念
整体性保护的理念早已是国际社会和学界的共识.正如刘魁立先生指出的:世界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以全方位、多层次和非简化的方式来反映并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只要是能体现人类在特定时空内的文化形态及其创造力的,都应该给予关注、研究并注意保护.[13]
在名录建设中要贯彻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应当至少从三个层面来考虑:
(1)应着眼于名录体系外整个传统民族文化全局性的保护,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少数、特殊遗产的保护.例如,如果壮语消亡了,那么以壮语为载体的众多遗产如壮剧、壮族三声部民歌、壮族铜鼓习俗等都将失去生命之源,其传承发展更无从谈起.
(2)注重项目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歌,没有无缘无故的舞.”[14]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有其生存的、特定的文化土壤.因此,在遗产保护中,既要保护非遗,也要保护其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
(3)注重与非遗相关联的“物遗”的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恰如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前者是其载体或具体表现形式,后者是内涵和精髓,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例如壮族天琴艺术,天琴的制作、弹奏、曲谱谱写、仪式等是非遗本体,但如果没有了曲谱、家屋、圩场等,天琴艺术也终将失去依托,最终走向消亡.
3.4 聚焦于遗产具有的多重文化属性,建立更为科学的分类制度
鉴于遗产文化属性与名录文化属性上的冲突,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归到《公约》关于非遗分类的认识和思考上来,并在分析、总结现行分类制度的优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为科学的分类制度.
如前所述,过于细化的分类容易将具有多重属性的遗产肢解.而《公约》开放的划分体系和可以跨类别申报的制度设计恰恰弥补了这一点.例如2009年,中国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遗产——“藏戏”,在中国名录分类中属于传统戏剧,但在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藏戏”所属类别中则同时包含了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显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了考虑“藏戏”所具有传统戏剧的文化属性外,还充分考虑了其具有的民间文学、仪式、禁忌、民俗等方面内容.
因此,有必要借鉴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建设的经验,充分考虑遗产具有的多重属性,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更为科学的分类制度.不应为了符合某一类别的申报标准,而舍弃了遗产其他方面的文化属性.例如壮族天琴艺术,在公布类别时不应只是传统音乐,还应该包括民间文学、传统舞蹈和民俗的文化属性.
3.5 加大国家非遗项目的申报,提升广西非遗的可见度及影响力
广西作为非遗资源大省,有着大量与东南亚国家共享的跨国跨境项目.只要做到科学谋划、合理部署,就能逐步缩短与全国的差距.
首先,应当及早谋划,可以从现有的762项区级项目中筛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项目,以设立广西的国家级非遗申报预备清单,甚至是人类非遗代表作申报预备清单.其次,应当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力量,加大科学研究.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申报同时也是对非遗项目再认识、再挖掘、再研究的过程.这需要借助专家学者的力量,做好非遗项目基本内容、分布区域、地理环境、历史渊源、重要价值、主要特征等基础性综合研究,为遗产在更高层级体现项目可见度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再次,应当准确把握国家级非遗项目申报的导向,扎实做好国家级非遗项目申报材料.
3.6 打破“名录”终身制,实施动态的评估、监督和管理机制
为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重申报、轻保护”的错误理念,有必要打破“名录”终身制,实施动态的评估、监督和管理机制.2011年8月,文化部公布了《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监督检查,实施国家级代表性项目的动态管理.建立完善的非遗保护效果评价机制,既是对当前非遗保护名录制度的一个有效补充和完善,更是将有关非遗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15]
从自治区层面采讲,关键是如何将这一制度细化落实,形成长效机制.首先,应将各级名录中不符合非遗定义的项目,尤其是伪遗产“清出”名录,确保正确的价值导向.其次,将定名、定位不准确的遗产项目进行调整.再次,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对不具备保护资质,无法履行保护职能的项目保护单位采取警告、摘牌或调整等措施.为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可以依托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等作为保护单位,充分发挥文化持有者自身的力量.例如民间文学类项目可以依托文联,传统音乐可以依托山歌协会,传统美食类项目可以依托食品协会,医药类项目可以依托医院、医药联合会等更为灵活多样的项目保护单位.
4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非遗保护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系统工程.非遗名录体系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关键核心的重要作用.当然名录体系只是一个工具或通道,最终我们需要回归到对《公约》精神和非遗保护的理念的再认识、再理解上来.在更加注重保护的后申遗时代,我们更应尊重社区民众文化主体地位,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树立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建立更为科学的分类体系等,并且恰当处理多元行动方的关系,形成合力,才能有效保障非遗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