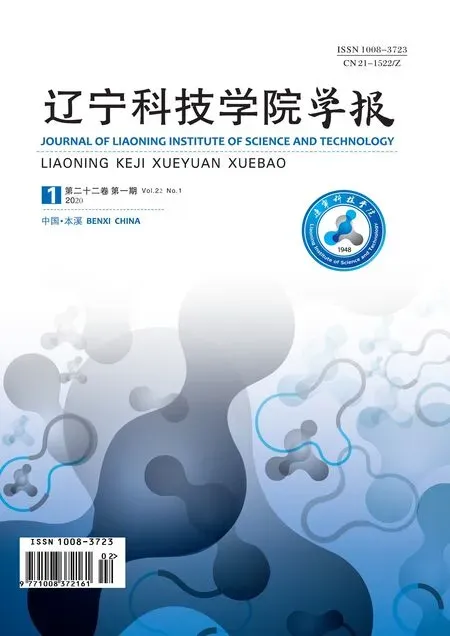校企合作中外政策制度比较研究
王妙婷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山西 太原 030009)
伴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校企合作问题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而校企合作涉及部门、单位、企业、学校等多个主体,想要取得长效发展还需要国家完善的政策制度的支持。在校企合作政策制度体系建立方面,西方国家发展相对成熟,因此应加强校企合作中外政策制度比较分析,探索出有助于国内校企合作工作开展的政策制度发展建议。
1 校企合作中外政策制度
1.1 国外政策制度
从国外校企合作政策制度发展情况来看,美国起步时间较早,在1862年就通过了首个职业教育法案《莫雷尔法案》,要求学校发挥社会服务职能,鼓励农业工学院培养专业人员,以更好的帮助农民和农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美国先制定了法律法规,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规定进行工读课程开设,要求各州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合作,随后通过了《合作训练法案》、《就业培训合作法》等各种法案,由联邦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发挥协调、资助作用,通过完善职业教育资格鉴定制度等政策制度推动校企合作开展〔1〕。结合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美国不断进行法律规范完善、细化和调整,建立了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相较于美国,德国在职业教育法律方面贡献更加突出,从1182年颁布《克隆车工章程》开始建立师徒制,1869年颁布《企业章程》,对企业职业培训义务进行了规定,随后推出了《强迫职业实习教育》、《工业法典》、《行业条例法》、《职业教育法》等多项法规,为现代企业职业教育“基本法”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校企合作方面,德国还颁布了数百种单项法规、相关条例,形成了注重徒工培训,并以企业培训为主、学校教学为辅的职业教育模式,即“双元制”,实现职业能力培训教育与企业岗位需求协调。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引进“双元制”后,衍生出了“现代学徒制”,出台了《职业教育法》、《培训保障法》等政策制度,实现全日制教育结构与学徒制以及培训生制的全面整合,形成了多元校企合作机制。
1.2 中国政策制度
中国校企合作政策制度出台时间相对较晚,在国家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提出系列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育人的法律法规。1983年,国家颁布《教育部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提出了国家办学与部门、企事业单位办学并举的方针政策。1991年,在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文件中,强调通过政策制定促进行业、企事业单位与各方面联合办学,在政府统筹下推动产教结合和工学结合。随后,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法规政策,强调持续推动职业教育人才模式转变,使校企合作得到加强,从以学校为中心向工学结合方向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从理论上推动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发展外,国家也颁布了相关政策加强校企合作资金投入。201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对以政府为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进行建立健全,推动校企合作政策法规的制度化发展。在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文件中,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义务进行了明确,并加快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现校企联合招生和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2〕。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联合颁布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推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在加强校企合作规划的同时,完善配套政策制度,使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得到深化。
2 校企合作中外政策制度比较分析
2.1 顶层设计比较分析
在校企合作政策制度建立上,西方国家注重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如美国、德国都从国家法律层面提出政策制度的建设要求,能够实现政策制度的总体设计。在国外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学校、企业等单位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责任、义务进行了明确,为推动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较而言,国内主要进行校企合作政策条例和规范制度的出台,法律层面的总体设计发展滞后。对2010年之前颁布的各项政策法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出台的政策文件多具有宏观性,包含了大量的原则性规定和倡导性条款。在顶层设计方面,仅出台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并且只对校企合作做出了笼统规定,要求企业、学校履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义务。2018年颁布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企业、学校、政府、行业等做出了相对具体的规定,但因出台主体级别有限,且“促进办法”的约束力相较法律有很大差别,因此不能代替法律制度对国家校企合作工作的发展进行规制。缺乏对校企合作主体行为和关系的顶层设计,导致了国家对各主体的约束不足,难以为相关政策制度的建立提供充足法律依据,造成了校企合作开端不佳。
2.2 组织协调比较分析
校企合作属于跨界教育模式,国外为推动合作的开展,规定由专门组织协调部门进行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规划监督和考核管理,如德国在州一级设立了行业协会进行校企合作统筹管理,美国成立了全国合作教育委员会进行政府、企业和学校关系的协调。为增强政策制度权威性,德国出台了《职业训练条例》等规定,由政府对违反规定的单位进行经济处罚。在组织协调方面,我国从进入21世纪以来开始颁布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政策,提出加强政府统筹协调,建立行业与教育对接协作机制。在2018年颁布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中规定校企合作综合协调与宏观管理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会同开展相关工作。实际在政策制度落实上,依然需要依靠教育机构和企业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缺乏专业组织协调机制。在监督管理上,规定由各级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及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具体的权、责、利不明,且该办法与相关法规制度,如《劳动合同法》、《保险法》等没有对接,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造成政策制度落实效果不佳。
2.3 配套机制比较分析
在配套机制建立上,国外侧重从财政投入、职业资格管理等方面完成校企合作运行政策制度的设计,促使校企合作项目得以规范开展。如美国出台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确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运行机制,德国开发了数千个职业标准。我国在校企合作配套机制建立上,从融资信贷、资源要素开发等方面进行了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建立了校企合作融资平台来吸收社会资金,并运用多家联合培训机制实现合作成果分享,以符合国情的方式对校企合作项目运行进行约束和规范。但受经费制约,同时相关职业证书难以得到市场认可,近年来国家尽管一直在出台校企合作激励政策制度,取得的成效却并不理想。
3 完善我国校企合作政策制度的建议
3.1 完善我国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
与国外校企合作政策制度比较后发现,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校企合作法律制度的制定,对本国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统领规划的作用。我国应该借鉴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制定《校企合作法》,明确规定学校、企业、政府、行业等相关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完善我国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目前,包含江苏、吉林等在内的一些地区,参考六部颁布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相关规定,开始从地方立法层面进行校企合作政策制度顶层设计,以完成国家校企合作立法问题的初步探索。而未来国家在政策制度发展中,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政策与立法的结合,明确合作主体权、责、利关系,为相关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提供指导。
3.2 理顺我国校企合作协调组织机构
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组织协调监管机构众多且管理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各机构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法律制度不同,而这些制度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导致校企合作工作开展不顺畅。针对这种现状,首先应根据《校企合作法》的规定,依法在中央到地方建立完善的校企合作多层次协调组织机构,明确相关主体权、责、利,在此基础上,以《校企合作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进一步修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保险法》、《民法》等法律的相关内容,加强法律之间的统一协调性,明确各校企合作机构的职责和权限范围,疏通开展校企合作的障碍,开展跨部门合作。
3.3 完善我国校企合作的配套激励机制
为保证校企合作政策制度能取得良好执行效果,我国应对西方国家建立激励机制方面的先进经验进行汲取,结合实际需要完成地方校企合作专项资金建立,采取政府投资、行业资助和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提供资金支持〔3〕,确保经费足够吸引相关主体投身于校企合作事业中来。在职业教育管理上,还应对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制度进行完善,规范职业资格等级标准,加强职业教育与校企合作工作的融合,促使校企合作主体参与合作项目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4 结论
综上所述,相较于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中国在校企合作政策制度建立方面的起步时间较晚,相关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尚未得到完善,在组织协调政策制度和配套机制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建设,同时结合国家实际情况出台有效政策加强校企合作组织协调,并完善配套机制保证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