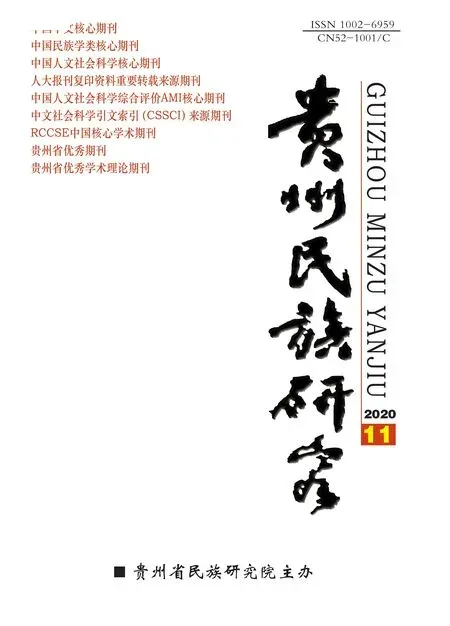百川归海:百越文化融汇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图景
李富强 卫彦雄 吕 洁
(1.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06;2. 广西民族大学 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越人是中国上古时期至汉代活动于中国南方的一个土著族群。“越”作为一个族称,大概始于商周时期。《逸周书·卷七·王会解》:“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遇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其人玄贝,海阳大蟹……禽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锺,锺牛。蛮杨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鰂之酱,鲛瞂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其中有“东越”和“越沤”之族称。 《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019年) “于越来宾”。其中有“于越”之族称。
将越人称为“百越”,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此后,《汉书·地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仅记录了“百越”的分布状况: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而且说明了称为“百越”的原因: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根据史籍记载,这些“各有种姓”的百越族群大致包括了“句吴”“于越”“东瓯”“西瓯”“闽越”“南越”“骆越”“滇越”“山越”等不同支系,它们都先后建立了割据于中原王朝之外的“王国”文明。
东汉之后,越人逐渐少见于史籍记载,尽管在闽、浙、皖、赣之交仍有称为“山越”之人,但却是比较零星、分散的人群了。总的来说,百越族群或逐渐消融于华夏-汉族之中,或在与华夏汉族的互动中逐渐演变为壮侗语民族。不论是演变为汉族,还是演变为壮侗语民族,其后裔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百越文化也融汇于中华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犹如《淮南子·氾论训》所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这是百越民族文化的一个历史图景,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的一个片断和侧影。
一、百川异源:百越文化是发源和成长于中国南方的独特文化
“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各有地望。据老一辈学者罗香林考证,百越各支分布如下[1](P39-100):
于越,初以会稽为中心,及勾践初年,北起今浙江崇德,东至浙江定海,南达闽浙交界,西及鄱阳湖东岸。
瓯越(亦称东瓯),以今浙江南部之瓯江流域为中心。
闽越,以今闽江流域为中心,东及今台湾澎湖列岛,西达赣东北。
扬越,今汉水流域。
南越,东及闽越地,南尽海南岛等地,西达广西、越南,北至衡阳。
西瓯,今广西柳江以东,湖南衡阳西南,下至苍梧封川,北达黔桂界上。
骆越,东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达越南东北部和中部。
滇越,今云南滇池一带。
罗香林对于百越的考证和研究,一直被学术界奉为经典。现在学术界对于百越各支系分布地的观点大多与罗香林的观点大同小异。如按照胡绍华的观点,百越各支系分布如下:
句吴,大致分布在今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带地区;
于越,大致分布在今浙江的杭嘉湖平原一带、宁绍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带;
东瓯,大致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
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省及赣东部分地区;
南越,主要分布在今广东省及广西部分地区;
西瓯,大致分布在今广西桂江流域河西江中游一带;
骆越,大致分布在今广西左江流域、海南省和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
滇越,分布在今云南省西南部地区及缅甸北部地区[2](P292-293)。
“各有种姓”的“百越”虽然各支系的文化各有差异,但亦有共同特征,自成体系。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罗香林归纳为:“擅于制造和使用钺和铜剑、善于制作舟楫和行舟、精于制造和使用铜鼓、好纹身习俗。”[1](P127-156)
林惠祥概括为:“断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语言、使舟及水战、铜器。”[3](P112-115)
凌纯声总结为:“祖先崇拜、家谱、洗骨葬、铜鼓、干栏、龙船、凿齿、文身、食人与猎首、洪水传说。”[4](P389-408)
陈国强等人归纳为以下特征:“水稻种植、喜食蛇蛤等小动物、发达的葛麻纺织业、大量使用石锛,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有极其精良的铸剑术、善于用舟,习于水战、营住干栏房屋、大量烧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操鲜明特点的语言、流行断发文身及拔牙风俗、留有浓厚的原始婚俗、崇拜鬼神、迷信鸡卜、实行崖葬、崇拜蛇、鸟图腾。”[5](P32-70)
胡绍华归纳为:“相同的语言——越语,共同的农耕经济生活——稻作农业,共同的宗教信仰——崇拜鬼神、迷信鸡卜,相同的生活方式,文身断发习俗,不落夫家习俗,打牙习俗,行船棺葬及悬棺习俗,使用铜鼓的共同习俗。”[2](P293-297)
吴春明则归纳为:“拥有海洋人文的价值取向——舟楫,特殊的聚落形态——干栏居和洞居,特殊而多样的丧葬形式,特殊多样的装饰艺术,复杂的自然崇拜,广谱的经济活动以及南岛底层方言系统。”[6](P79-86)
还有不少学者对百越文化的特点做过归纳和阐述。尽管观点不尽一致,但大多认为,百越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百越文化自成系统,是一种迥异于中原华夏文化的独特的文化体系。
独特的百越文化是中国南方的土著文化。尽管《史记》 《尚书》 《淮南子》 《越绝书》 《吴越春秋》等中国古籍常将越人的根源追溯到大禹,谓之为“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7],相当一些老一辈学者如罗香林等也据此认为“越族源出于夏民族”[1](P1-8),但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种观点不过是由根深蒂固的华夏—汉人中心主义立场带来的偏见和误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骐就曾将百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百越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认定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先越文化”[8]。现如今,考古发现,在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新石器时代曾广泛存在以几何印纹陶和有肩石器、有段石锛共存的众多遗址,这些遗址的遗物遗迹透露出其主人的许多文化特征,如干栏建筑、善于用舟、稻作农业、断发纹身、凿齿拔牙、蛇崇拜、悬棺葬或崖洞葬等,这些正是百越人独有的文化特征。日益丰富的证据表明,百越族群实际上就是由当地史前人类演变而来,百越文化就是当地土著文化。从“先越文化”到“百越文化”、从“先越民族”到“百越民族”,其间无论从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考察,都有一个继承、发展和变化的过程[9](P10)。
二、百川朝海:百越文化融汇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写照
汉代焦赣《易林·谦之无妄》 云:“百川朝海,流行不止,道虽辽远,无不到者。”这正是百越文化融汇于中华文化历史过程的写照。
百越文化融汇于中华文化是“先越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交流的继续。据有关学者研究,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序列中即有中原北方的文化因素传入与融合。旧、中石器时代,有细、小石器工业群的介入;新石器时代,来自北方的新石器、早期青铜文化的影响接踵而至,尤其是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强劲影响,尽管从整体上来说,这类影响只是局部的和短暂的,没有形成扩展和持续之势,没有改变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土著传统,具有鲜明本土传统的器群组合仍是东南新石器文化的主流[6](P273-290)。而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原北方文化影响南方的势头持续加强。夏商时期是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初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夏商王朝将青铜文化传播、影响到南方。两周时期,中原华夏文明传播和影响到了整个南方地区。
中原华夏文明与百越文化的交流可能自东而西有早晚强弱的不同。东部的“句吴”“于越”等融汇于华夏的步伐最快。从考古发现来看,太湖至宁绍平原的湖熟文化、马桥文化、高祭台类型和赣鄱流域的吴城文化和万年类型,都表现出浓厚的夏商青铜文化特征。可见,在龙山文化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东南北部的湖网平原地区的土著文化已经受到夏商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初步的“华夏化”态势[6](P345)。西周时期,华夏族群可能已经成规模地迁徙到了江南湖网平原地区。《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7]这一记载可能反映了华夏族群迁徙至东南北部的事实。与之相印证的是,在从苏皖南至浙赣地带的吴、越土墩墓文化中,中原华夏文化因素多见,如绳纹陶系的鼎、袋足甗、鬲和青铜礼器类的鼎、鬲、簋、尊、卣、盘及成套的青铜兵器等,代表中原华夏文化的器物成套出现。由于“句吴”在“于越”之北,其与华夏交流更早、更甚,也更多地接受了华夏文化。《史记·吴太伯世家》曾载:“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7]公元前544年,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出使鲁国,已能从华夏文化的角度审视诗三百,并逐一评论之。此后,季札又游历齐、卫、郑、晋等中原诸国,带回了许多华夏文化,使吴国逐渐华夏化。“句吴”之民并入越国也进一步推动了“于越”的华夏化。
“于越”与华夏交往交流的起点自然也是十分遥远的。据研究,“先越文化”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良渚文化的创造者与夏商周时代的人们在宗教信仰上一脉相承,夏商周文明中的宗教信仰来源于良渚文化;商的青铜文化对越国有强烈的影响,周文化则通过吴国而影响越国[10](P1-10)。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说明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末,于越已与中原王朝交往交流。此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与中原各国争霸,文化交融随着交往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发生,越地出土的青铜礼器,尊、鼎、爵等,越来越具有中原华夏文化特征,越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沿袭、仿效商周旧制的色彩越来越明显。华夏化明显的“句吴”并入越国无疑加速了越国人“于越”的华夏化。越灭吴后,勾践为了争霸中原,于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 迁都琅琊,这也是于越民族的一次大迁徙,于越从此更加接近中原华夏人,交往交流更加便利。虽然此后越王翳因国势衰弱难以立足北方而南返于吴都,越王无疆败于楚之后回走越人基地——“南山”,即会稽山和四明山一带的南部山地,但越国之民不可尽返,滞留北方者当不在少数。公元前306年,即楚怀王二十三年,楚国联合齐国灭了越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7]。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7]。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为防止越人重新聚集以倾覆秦王朝,秦始皇为“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彰。因徙天下有罪适(谪) 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11]。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于越大部被华夏化,只有小部分逃入高山丛林之中的成为“山越”,逃往海外诸岛的成为“外越”。
“百越”的其他支系,如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虽然自夏商以来即与中原华夏交往、交流不断,但华夏文化对它们的影响远逊于对“句吴”“于越”的影响。
闽越,主要分布在闽江流域。先秦时期,受中原华夏文化影响不深。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在闽越之地设闽中郡。秦末,闽越王无诸助汉灭秦,汉王朝以羁縻制治之,以无诸为闽越王。到汉武帝时,闽越坐大,汉武帝遂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 派兵攻打,杀闽越王余善,结束了地理格局中的闽越国局面,并“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7]。被迁徙至江淮的闽越此后逐渐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
东瓯,主要分布在瓯江流域。秦时,臣服于秦王朝。秦以羁縻制实行统治,利用东瓯王摇统治东瓯旧部。秦末,诸侯叛秦,东瓯王摇“从诸侯灭秦”,并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不附楚”,而“率越人佐汉”,故在汉初被汉王朝封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12]。但随着汉王朝政权的巩固,刘邦开始消除异姓王,东瓯遂与中央王朝发生矛盾,及至汉景帝时参加了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但“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7]。汉武帝接到东瓯的求援,“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尽管“未至,闽越引兵而去”[7],但东瓯与闽越从此结怨,东瓯王为求自保,便请求归附汉朝。汉武帝接受了东瓯王的请求,将东瓯迁至江淮间与汉民杂处。东瓯也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汉化,成为了汉人。
南越,主要分布在今广东省及广西东部部分地区。据研究,其在商周时期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较闽越深刻,在岭南地区石峡上层类型的夔纹陶文化中,发现有闽越地区没有的青铜盉、鼎、钟等周式礼器[6](P346)。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 派尉屠睢率50万大军,挥戈南下,略取岭南,虽遭遇顽强抵抗,损失惨重,但历经艰难,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统一了岭南,即于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尽管秦统一岭南后不久便亡,实际上对岭南没有多少直接的治理,但秦始皇先后5次强行迁徙各色“中县之民”或“中县人”至岭南,“与越杂处”,强迫越人同化[13](P52-53)。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行南海郡事的赵佗建南越国,都番禺。他一方面“和辑百粤”,依从越人风俗,任用越人为官,另一方面又坚持汉族文化,实行秦汉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和礼制,推广汉族的语言文字,倡行越汉通婚,使汉文化得到了全面而广泛的传播,为越汉两族的融合奠定了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基础。及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由于南越国不用汉法,丞相吕嘉谋反,攻杀南越王兴及太后和汉使者等,汉武帝发兵10万,分5路直指南越国。翌年冬,平南越国,于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岭南重新置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虽然其间或有“以其故俗治”等统治政策,但终究从此在岭南与中央王朝间更无阻梗,两地间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至东汉末年,广东境内番禺、广信等地越汉融合的结果,越已不复为越,而形成了一个操粤方言的群体,这就是汉族广府民系的先民[13](P100-101)。
西瓯、骆越,大致分布在今广西境内。由于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有时单称瓯或西瓯,有时单称骆或骆越,有时又连称瓯骆,致使后人对于西瓯和骆越到底是两支不同的越人,还是同一支越人的问题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西瓯和骆越是同族异称;有人则认为,西瓯和骆越是不同的两支越人。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未有共识。但不管西瓯、骆越是一族还是两族,他们与南越一样,自秦汉以来,经历了一个与汉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然而,或许是广西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的缘故,西瓯、骆越的主体并没有演变成为汉人,而是在东汉之后演变成为乌浒、俚、僚,到宋、明之时,演变成为壮、布依、黎、侗、仫佬、毛南、仡佬、水等民族。
滇越,大致分布于今云南西南地区一带。《史记·大宛列传》曰:“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7]可见当时滇越与中原汉人已有往来。但时至东汉,滇越之名消逝,而“掸”之名出现。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掸在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而逐渐演变为傣(泰)族[14](P192-196)。
总体来看,百越文化在融汇于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两种形态或结果:
第一,越人汉化为汉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灭亡,历秦始皇统一岭南,至汉武帝平闽越和南越,为汉人族群大规模南迁进入百越地区,越汉文化的交融奠定了基础。至秦汉时期,百越地区汉民人口大幅度增加,汉文化传播势头强劲,区域文化达到了高度的汉化:战国前后,句吴、于越已完全融合于华夏族,其所操语言亦融合成华夏语(汉语) 的方言之一——吴越语。东瓯、闽越被迁至江淮间的,旋即被汉化,留在原地的也在与汉人的互动中于东汉中晚期融合成为汉族的一支——潮汕民系[13](P107-108)。
第二,越人演变为壮侗语各民族。未汉化的越人,亦在与汉人交往交流交融中,演变成为新的族群——(乌浒) 俚、僚。两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为逃避战乱,汉人持续大量南渡,规模化移民高潮迭起,百越地区人口骤增,汉文化成为了主体和主流文化。至唐宋之后,越汉文化交融的结果,一是大量的俚、僚被汉化,成为了汉人;二是部分俚、僚在宋元明时期演变成为壮、侗、黎、布依、仫佬、毛南、水族、仡佬、傣、京等少数民族。
三、长留风雨在江东:百越余韵为中华文化增色添彩
“一自百川归海后,长留风雨在江东。”[15]清代毛奇龄的诗句形象地反映了百越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原华夏-汉人与边疆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过程。一方面,中原华夏-汉文化在同化百越民族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百越民族的文化成分,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汉文化;另一方面,一些未汉化的百越族群后裔在经受了华夏-汉文化的洗礼之后,也以少数民族群体的身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论如何,总的来说,百越文化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海洋,百越文化的积淀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百越文化的余韵为中华文化平添色彩。
(一) 百越故地的汉文化包含着丰厚的百越文化积淀
百越故地的汉人,不论是南来的汉人,还是汉化了的越人,都经历过越文化的浸染、熏陶,因而具有越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了百越故地汉文化的特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百越故地的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话等汉语方言,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百越先民的语言成分。罗美珍认为,客家话中的古越语成分不能看作“南岛语底层”,只能看作是汉语受古越语的影响,这是一种借代关系,而闽、粤、吴方言中的古越语成分是“南岛语底层”[16]。
第二,汉唐以来,特别是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合浦、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的兴起及海外贸易的昌盛,是百越民族“便于舟楫”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合浦港曾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极盛一时。由于两汉时期,中原与岭南交往十分频繁,中原的产品蜀锦、丝绸、瓷器等经南流江从水路大量涌入合浦,而合浦的珠玑、犀、象、农产品也大量销往中原一带,随着对外贸易的频繁,印度及东南亚商人多从合浦港登陆,然后经合浦港沿南流江前往中原,因而合浦港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高峰期,直至唐宋之后,才让位于广州、扬州、泉州等大港口。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合浦发现有大批的汉墓,说明汉人已大量进入该地,而从出土的遗物来看,这些人显然受到当地越文化的影响。如大量出土的建筑模型,就有干栏建筑的风格。受越人“便于舟楫”文化的影响,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而合浦不仅是连中原、抵交趾等地的中转港,同时还是以盛产珍珠(南珠)而闻名的商港。长期以来,合浦沿海居民“赖以采珠为活”,这是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17]的继承。唐宋之后,广州、扬州、泉州等大港口的兴起,海外贸易的兴盛,也是百越民族“便于舟楫”文化基因的遗传。
第三,百越故地汉人的干栏式建筑、喜食水产、嚼槟榔、不落夫家、镶牙、崖洞葬、船棺等日常社会生活习俗是百越文化的继承。如百越的干栏式建筑自新石器时代便已发源,河姆渡遗址[18]、广东高要茅岗遗址[19]都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存。这个传统大概在汉代就已为当地的部分汉人所接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汉墓发现了不少的干栏式建筑模型,说明干栏式建筑在当时汉人社会中也很流行。又如,南方汉人自古以来喜食水产,这也应是受“越人美赢蚌”[20]影响的结果。而至今南方汉人常见的二次葬习俗以及崖洞葬、船棺葬等习俗亦是源自于越人。
第四,百越故地汉人对妈祖、蛇神等的崇拜,是百越民族原始宗教的传承与延续。据研究,中国东南汉人所信仰的妈祖是越人的后代[21];华南汉人的蛇神崇拜源于越人的蛇图腾文化。华南汉人对“妈祖”和“蛇神”等的崇拜,不但凸显了华南土著文化的传承与基层特征,更透露出华南汉民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不管华南汉民是越人的汉化还是越化的汉人,他们身上浓重的妈祖崇拜和崇蛇文化,表明他们并不是中原汉民简单的“衣冠南渡”,而体现了华南文化史上汉越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混杂局面[6](P401)。
(二) 百越后裔民族文化传承着百越文化基因
作为百越后裔的壮侗语各民族传承着百越文化的基因,最显著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1. 语言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壮语与亻良语相似,民国《天河县志》云:“俍语与僮略同,而声音略劲”。而“俍”与“僚”有嬗递关系,“俍”乃由“僚”演变而来[22]。俚僚语,柳宗元说是“殊音”,周去非亦“不可晓”,异于汉语无疑,但俚僚呼其所尊者曰“都老”或“倒老”,与壮族无异,直至解放前,壮族仍称“寨老”“乡老”为“都老”,称年长的男人为“都斋”,年长的妇女为“迷都”或“都伯”,“都”有“人”的含义,乃人称冠词,说明俚僚语与壮语相似。不仅如此,我国学者将今壮语拿来同古代“越人歌”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证明今壮语同古越语基本一致[23]。
据《广西通志》引《庆远府志》记载僚人语言的基本词汇,用来与侗语基本词汇进行比较,是基本相同的。例如,僚人称母亲为“乃”,侗族也叫“乃”,有的则叫“埋”,僚语称兄为“怀”,侗语则叫“吠”。弟,还有许多基本词汇完全相同。如,僚语和侗语都称弟为“侬”、穿衣为“登苦”、吃饭为“谊欧”、饮酒为“该考”、吃肉为“谊难”等。往上追溯,有学者将西汉刘向《说苑·说善》 中的《越人歌》 与侗语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侗语似比壮语更接近于《越人歌》原意”[24];或“似可认定这首《越人歌》是古人侗歌”[25];或“《越人歌》 是古代百越支系的民歌,它与侗族早期民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26]。这充分说明了侗语与古越语的亲缘关系。
仫佬族语保留的伶族称,是对僚、俚、骆越、西瓯族群称谓的记录和诠释。仫佬族地名峒、骆(罗、乐),与骆越的骆有关。仫佬族称“我们”为“饶”,正是古“西瓯”切音。仫佬族自称“伶”难详其义,但其音却是“僚”失去m韵尾的语音,“僚”复原m韵尾,即是“伶”,其语音可以追溯到古骆越民族的源头。仫佬语与俚语、僚语是相通的,俚人、僚人的一些称谓可用仫佬语来破解。如俚人的“倒老”,仫佬语称为“冬老”,是“寨老”的意思。又如“郎火”,《炎徽纪闻》载:“撩人,古称天竺……无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长有智者,役属之,号曰郎火。”“郎火”即“头人”“首领”的意思,现在仫佬族仍称“头人”为“郎火”。仫佬族语与壮语、侗语也很是接近。范宏贵在比较了壮、侗和仫佬族语言后,认为仫佬语是壮语和侗语之间的一个过渡。
毛南族的语言与紧邻的黔南水语很接近,与侗语、仫佬语有半数基本词汇相通,也与壮、布依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
水语与同语族中的侗语、毛南语、仫佬语、布依语、壮语有亲缘关系,尤其与侗语的关系最为密切[27]。
而李锦芳通过研究发现,仡佬语属于侗台语四大语支(台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仡央语支) 之仡央语支。侗台语言起源于广西一带,黎、仡央两语支是较早迁出的部分。仡央各支系与古夜郎关系密切,西汉夜郎国降汉之后,其地置牂牁郡。牂牁系仓吾之延续,因其地多原仓吾越人,遂称牂牁。上古音仓吾与牂牁相通。仓吾系最古老的越人部族之一,商周时期是越人的强盛部落。仓吾在今桂东北一带,夜郎可能是其向西扩张的后裔。仡央语支与古越语关系密切。仡央先民当是与其他侗台先民共居岭南,后来才西进贵州高原,建夜郎国,至汉代他们仍与同种同言的南越保持密切联系。仡央语支与相距遥远的黎、临高语有许多同源词,有的与侗水语支同源而与台语支不同,说明双方仡央先民在黎、临高人迁离大陆以前具有密切关系,他们共同生活的地区可能在桂东粤西,即古仓吾部及其以南地区[28](P45-56)。
2. 习俗
如越人居住干栏的习俗,在壮侗语民族中得以传承。继越人之后,僚人亦住“干栏”房屋。《北史·僚传》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唐书·南平僚》则更进一步说:“南平僚者……部落四千余户,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楼而上,号曰干栏。”僚人的“干栏”比越人的“干栏”有很大进步,已明确人住楼上,必须“登梯而上”。继僚之后壮侗语各族的房屋也是“干栏”。直至现代,在壮侗语民族地区的农村里,这种楼上住人,楼下养家畜和置放农具的“干栏”式房屋,仍到处可见。
越人有“椎髻”“凿齿”之俗,于古籍记载颇多。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说:“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载:南越王赵佗也行“椎髻箕踞”之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也说:“凡交趾所统……项髻,徙跣,以布贯头而著之。”近年在湖南、广东、广西出土的越墓中,都有“椎髻”发形。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越人“断发”和“椎髻”是并存的。“凿齿”又称“打牙”,就是拔去一、二颗牙齿。《淮南子·坠形训》说:“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凿齿民。”《战国策·赵策》也说:“黑齿雕题,鳗冠林缝,大吴之国也。”所谓“凿齿”“黑齿”都是拔牙的习俗。“椎髻”“凿齿”之俗被僚人继承了下来。《博物志·异俗篇》说:“荆州极西至蜀,诸蛮曰僚子……既长,皆拔出上齿各一,加狗牙各以为华饰。” 《太平寰宇记》 载:“蛮僚之类……椎髻、凿齿、穿耳。”在壮侗语民族的妇女中,长期盛行椎髻发型。乾隆《柳州府志》 载:“……峒人,椎髻,首饰雉尾,卉衣。” 《老学庵笔记》 称:“在辰、沅、靖州等地,有仡伶、有仡榄,男未婚者,以金鸡羽插髻。”至于“打牙”,在1950年前,有些青年男女,喜将一二颗门牙镶成“金牙”或“银牙”以为华饰。还有的壮侗语民族地区在人死后,如果牙齿尚齐全,必须敲掉一颗门牙以后,才能入棺埋葬。
越人笃信鬼神、盛行鸡卜的习俗,在壮侗语民族文化中有所体现。 《史记·封神书》 记载:“是时既灭南越……乃令越巫立越祝词,安台无坛,以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汉书·郊祀志》也有粤人信鬼,“而以鸡卜”的记载。汉代以后,鸡卜之俗仍在越人后裔中流行。唐代柳宗元《柳州峒岷》 诗云:“鹅毛御腊缝山厕,鸡骨卜年拜水神。”宋人周去非《岭南代答》对鸡卜的方法有具体的记载:“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未孽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祈祷,所占而卜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号,伴两腿骨相背于竹挺之端,执挺再祷。”“乃视两骨之则,所有细穴,以细竹挺长寸余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以鸡卜定吉凶的习俗,从越人至僚人一直流传到现代壮侗语民族。《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记载:“洞人病不服药,惟于古木水边祭鬼,以鸡以卜吉凶”。《平乐县志》说:侗僚“婚葬用五行,以鸡骨卜吉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壮侗语民族地区,尚能见到“鸡卜”与“蛋卜”的活动。
3. 宗教信仰
体现越人生活在水网地区、从事稻作农业等特征的宗教信仰在壮侗语民族中得以传承。
(1) 太阳崇拜。左江流域岩画中,体现越人太阳崇拜的遗迹主要有3处:一处是宁明花山第二区第二组岩画,这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及其下方3 个顶礼膜拜虔诚歌舞的图像[29](P39);一处是崇左银山第二处第二组岩画[29](P144-145),画面上方是一个太阳图像,下方为一群举手歌舞的膜拜者图像;一处是扶绥县吞平山第一组岩画,画面上有2个正面人像,其中一人身躯高大,另一人较矮小,其左上方有一太阳图像,可见7道光芒线条[29](P183)。太阳崇拜一直在越人后裔中传承。北齐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苍梧乃广西东北部,东君便是太阳神。屈大均《广东新语》亦曰:“盖南人最事日,以日为天神之主,炎州所司命,故凡处出山者,登罗浮(山)以宾日;处海者,临扶胥以浴日,所谓戴日之人也。又日之所中,在其首上,故日戴。”在壮侗语民族所铸造的象征财富和权力的宝贵重器铜鼓上,无一不铸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30](P115-119)。直至现代,太阳崇拜的现象仍可见于左右江地区。如在南部方言的壮族普遍认为太阳是天的眼睛,日蚀时,人们要打锣,把扫帚往天上捅,以防狗把太阳吃掉。云南西畴革机屯的壮族,每年春节期间都要由族长带领族人到一固定的小山头上祭拜太阳。大年初一清早,族长带领族人到山头上,在一块大石上摆上供品,朝太阳升起的地方朝拜。太阳升起的时候,族长带领族人,绕着大石头转圈,祈求一年的平安、丰收。
(2) 月亮崇拜。据分析,左江岩画上的圆形图像第一型第一形、第十一形,第二型第一形、第九形,第三型第一形及第四型各形有可能属于天体图像[31](P168)。这反映出越人除了太阳崇拜外,还有月亮崇拜。崇拜月亮的习俗在左右江流域至今流传。如桂西的靖西、德保、那坡、大新、天等一带,流行一种祭月请神活动。这一活动当地俗语称为“请囊亥”,翻译成汉语即请月姑娘之意[32](P1698-1701)。分析祭月请神活动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虽然掺入了不少巫、道的成分,但其本质无疑是源于自然崇拜之一——对月亮的崇拜。
(3) 铜鼓崇拜。《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水经注·温水》载:“……盖籍度铜鼓,即骆越也。有铜鼓,因得其名。”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百越地区出土铜鼓甚多,在左江流域岩画中铜鼓图像也甚为常见。铜鼓在越人后裔心目中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隋书·地理志》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扣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太平御览》:“有鼓者,极为豪强。”《续资治通鉴长编》:“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谈迁《国榷》卷六九:“藏鼓二三,即雄长诸蛮。”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四:“藏(铜鼓) 二三面者,即得僭号为寨主矣。”《明史·刘显传》也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晋书·食货志》:“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曹学铨《蜀中广记》引《上南志》:“铜鼓,有剥蚀,声响者为上,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递有差等。”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二:“仲家,范铜为鼓,其制类鼓,无底。遇死丧,待宾客,击以为乐。相传诸葛武侯之所铸者,价值牛马或以百计,富者倾产市之,不惜也。”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中载:仲家“俗尚铜鼓,击以为娱,土人或掘地得鼓,即夸张言诸葛武侯所载者,富家争购,即百牛不惜也”。明邝露《赤雅》:“铜鼓,……重赀求购,多至千牛。”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六载:“琼州有黎金,似铜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脐,黎人击之以为号,此即铛也。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以铜为器,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时至现代,铜鼓在壮侗语民族中依然是神圣之物,据不完全统计,广西河池市现藏传世铜鼓1400余面,崇左市和百色市几乎每个壮族村落都有,逢有重大节日庆典,可拿出来使用。更重要的是,在左、右江地区很多有关铜鼓来源的神话传说依然流传,铜鼓的平时管理有制度,铜鼓的启用及收藏有一定的仪式和风俗,铜鼓依然发挥着娱乐、神器、重器和集众的功能[33](P12-22,206-220)。
(4) 雷神崇拜。在古代文献中,有越人及其后裔祭祀雷神的记载很多。如《太平广记》 云:“唐罗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为海康郡,……其事雷畏最甚谨,每具酒肴奠焉。”《铁围山丛书》曰:“独五岭之南,俚俗犹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岭外代答》卷十亦曰:“广右教事雷神,谓之天神,其祭曰祭天。盖州有雷庙,威灵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钦人尤畏。圃中一木枯死,野处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许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则又甚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丰,末年盛祭。每祭,则养牲三年而后克盛祭。其祭也极谨,虽同里巷,亦有惧心。一或不祭,而家中偶有疾病官事,则邻里亲戚众忧之,以为天神实之灾。”对雷神的顶礼摸拜,在唐宋朝的时候,似是广南西路人们的地区性行为。宋朝广南西路,包括今广西、广东高州县以南的粤西南及海南省。在这些地区内,越人后裔广建雷庙或雷王庙。比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四三三《梧州府祠庙考》载:“雷神祠,本邑各乡俱有,每三年用特牲祭。”唐朝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雷塘庙开祭之日,也到庙中读祷雨文,祈求雷神叨念民艰,降下雨水急民之急[34]。左江流域岩画众多的铜鼓图像充分说明《蛮司合志》所说的“是鼓有神”,因为它是通神之器。此神即为雷神。《广东新语》称铜鼓“雷人辄击之,以享雷神,亦号之为雷鼓之。雷,天鼓也。……以鼓象其声,以金发其气,故以铜鼓为雷鼓。”在出土的众多铜鼓上,多饰有云雷纹,按照“雷取其奋豫,云取其濡泽”的记载,云雷纹与风云雷雨有关。因此,铜鼓的出现和使用是雷神崇拜的反映。而在壮族神话中,雷神被尊为壮人早期四大神(雷公、布洛陀、蛟龙、虎)之首。雷王的生动形象:雷王住在天上,有一副青蓝色的脸,灯笼般的眼睛,鸟类的嘴,并长着一对翅膀;他左手可以招风,右手可以招雨,凶恶威严;他主宰着人间风雨,生死祸福,既可使人间风调雨顺,又可使天旱地裂或洪水滔天[35]。在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壮侗语民族中也有雷神崇拜的现象[36]。
(5) 水神崇拜。由于越人及其后裔生活于河流纵横的江南地区,他们“仰潮水上下”而垦食“骆田”[7],或“射翠取毛,割蚌求珠”[37],因而“陆事寡而水事众[17]”。大量贝丘遗址表明,百越先民大多背山靠水而居,渔猎一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们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中有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而水又可以给他们带来灾难,因此对水的崇拜在越人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纹于铜鼓之上的龙舟竞渡习俗,至今仍流传于我国南方各地。龙舟竞渡虽系托“救屈原以为俗”,其实早在屈原之前的春秋时期便已存在于越人之中,其原始的性质就是祭水神的礼仪节目。正如闻一多在《端午的历史教育》中指出,端午节是断发纹身的越人,为祈求生命得到安全保障而举行的祭节,所进行的龙舟竞渡,便是这种祭祀中的娱乐节目。有人认为,左江流域岩画与水神祭祀有密切的关系,整个岩画就是祭祀水神的生动画卷[38]。越人祭水神的习俗薪火相传。唐柳宗元《柳州峒氓》咏道:“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温庭筠《河渎神词》曰:“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水村江浦过风雷,楚山如画烟开。”孙光宪《菩萨蛮》云:“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许浑《送客南归》诗亦云:“瓦樽留海客,铜鼓赛江神。”这些材料都描绘了当时骆越后裔祭水神的盛举。直至近现代,壮族人还认为有一种叫“图额”的神,住在水深的河弯或深潭中,因而他们在戽水捉鱼时,要对“图额”烧香、礼拜和上供[35]。所谓“图额”,就是鳄鱼,是壮族先民及壮族心目中水神的具体形象。在壮侗语民族心目中也有自己的水神崇拜。
(6) 蛇崇拜。百越民族蛇崇拜的文化特点十分突出。《说文解字·虫部》曰:“南蛮,蛇种。”《说文解字·闽》:“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百越地区普遍发现几何印纹陶,据研究,其纹饰是蛇形、蛇皮鳞纹的简化,起源于古越人的蛇图腾崇拜[39]。华南、东南和云贵高原越系青铜文化中,蛇形、蛇纹的青铜器也很多见。这种崇蛇文化在壮侗语民族中传承,表现为壮侗语民族的“蛇祖”“龙母”“蛇母”崇拜[6](P373-391)。
(7) 青蛙崇拜。在左江崖壁画中,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叉开双脚,两手拱起,手指和脚趾叉开[31](P158-162),分明是在模仿青蛙的造型。这是骆越人崇拜青蛙的反映。反映越人青蛙崇拜的材料很多。首先,反映在族称上,据研究,越人之“越”为“雩”的同音变异,而“雩”为古越语谓“蛙”之音。所以,“越人”其实就是“蛙之人”的意思[40]。反映在考古发现上,越人及其后裔铸造和使用的铜鼓的鼓面大多饰有立体青蛙,有的是单蛙,有的是迭蛙,数量从1只、4只至6只不等[30](P81)。这包含有深刻的信念内容。人们之所以在铜鼓上铸造青蛙是因为他们相信青蛙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给他们以帮助和庇护。青蛙崇拜流传至今。特别是在左右江流域壮族文化中,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壮族的民间文学以听觉的形式表现了壮族对青蛙的崇拜之情。壮族关于青蛙的神话很多,如《蚂虫另歌》[41]《祭青蛙》[42]等,都把青蛙说成是上天下来的神物,具有非凡的本领。一些地区的壮族还相信日蚀、月蚀的发生是由于蛤蟆吞食日月所致[43](P24)。另外,《蚂虫另仔成亲》[44]《青蛙姑娘》[45]和《蟾蜍的故事》[46]等神话故事还描述了蛙蝇变成人与人类结亲的情节和内容。不仅如此,东兰、凤山和南丹一带的壮族至今流行一个规模盛大的祭蛙节日——蚂虫另节。蚂虫另节又称“蛙婆节”或“埋蚂虫另”,这是一个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典礼。
(8) 犬崇拜。古代越、僚人对狗非常尊宠。《国语》卷二十《越语上》载:越国君王勾践为了鼓励生育,增强国力,曾下令:“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以狗奖励生男孩,以猪奖励生女孩,可见狗在当时越人心目中的分量。 《太平御览》 卷七八〇《叙东夷》 引《临海水土志》说,“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临海水土志》是三国时代沈莹所撰,安家之民就是当时居住于今闽、浙之界的越人。他们杀狗祭祀死去的父母,逝去的父母可以得到慰藉,灵魂可以因狗而逸升天际。直至近现代,广西崇左一带的壮侗语民族,春节时仍结草为狗像,并在其身上披挂彩带而立于村口供奉;有的地方则凿石为狗,立于村口供奉,以期驱鬼禳灾,保佑村寨平安。
(9) 鸟崇拜。广西左江崖壁画的扶绥岜赖山第一处、后底山第二处和龙州沉香角第一组,共有4 只鸟类图案。其中除龙州沉香角一只位于正身人像的旁侧外,其余3只均处于正身人像的头顶上[31](P164)。虽然这几只鸟的特征不很明显,但左江崖壁画作为骆越巫术文化的遗迹,画上这几只鸟是有深刻含义的。它很可能是传说中的“雒鸟”,是骆越人所崇拜的图腾。越人的鸟崇拜在其先民的神话传说中有所表现。 《越绝书》 卷八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其何故也?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因病亡死,葬会稽……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吴越春秋》 《水经注》 《博物志》等书,也录有这则东南越人“鸟田”的神话故事。而中南的骆越同有“骆田”的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47]按照《说文解字》 的解释,“骆田”即“雒田”,“雒”为“鹆其鸟”,意为“小雁”,因而“雒田”这个词本身已包含着一个“鸟田”的传说[48]。正因如此,骆越因鸟得名“骆人”,即“鸟人”之意。越人铜鼓上的纹饰以实物的形式直观地反映了骆越的鸟图腾崇拜。广西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上,身饰羽毛、头著羽冠的羽人图像比比皆是。如贵县罗泊湾铜鼓[49]和西林普驮铜鼓[50]的腰部都有羽人图案。这与古代文献中称我国南方有“羽民国”的记载是一致的。《山海经·海外南经》曰:“海外自西南陬又至东南者……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同书《大荒南经》又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淮南子》卷四亦言南方有“羽民”国。其实,“羽人”是所谓“人的拟兽化”。它显然是源对与鸟认同的心理,即鸟的图腾崇拜。因为在广西出土的铜鼓上,鸟的形象十分常见。贵县罗泊湾铜鼓羽人图案的上空有鸟口中刁鱼、展翅飞翔,船头还立有衔鱼的鸟[49]。这种鸟是一种生活在海边的水鸟或候鸟。《淮南子·本经训》云:南方人“龙舟益鸟首”。高诱释曰:“益鸟,水鸟也。画其像著船首,以御水患。”这种水鸟就是传说中的雒鸟,正是铜鼓主人骆越的图腾鸟[51](P131)。越人的鸟崇拜在壮侗语民族中得到了传承。在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的神话中,他们共同的始祖母被称为“姆六甲”,始祖公被称为“布洛陀”,这两个名字分别是“六甲鸟之母”和“鸟首领”之意。此外,他们崇拜的布洛陀的兄弟雷王,也按鸟的形象来塑造:人身、鸟喙、鸟翼、禽爪[52]。壮族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人死后变成鸟的传说。如民间故事《秧姑鸟》说,立夏前后,殷勤叫唤“勒谷勒啊”,提醒农民耙田插秧的秧姑鸟,是由美丽的壮族少女变成的[53]。《救哇鸟》[46](P164)《杜鹃鸟的故事》[54](P258-259)等也是此类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与图腾崇拜中人与图腾同类的观念是有关的。
(10) 田(地) 神崇拜。广西宁明花山第一区第6 组岩画中有一对男女在性交,其下排列着谷粒状的点,旁边还有铜鼓和人祭图像。这是骆越人通过巫术将人的生产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祈求农业丰收的一个仪式场面。这个仪式场面祭祀的神是田(地) 神。对田(地) 神的崇拜在左、右江骆越后裔中一直得以传承。由于壮侗语民族是稻作农业民族,田(地) 神崇拜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壮族十分常见社公祭祀,他们认为社公是全村的“主人”,主宰全村的祸福,因而各地都举行一些仪式祭祀。
(11) 鬼神崇拜。关于越人及其后裔信巫祀鬼,古籍早有记载。 《史记·封禅书》 云:“是时,既灭两越……乃令越巫立越祝词,安台立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史记》正义云:“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此法也。”《北史·僚传》:“僚人……喜则群聚……俗畏鬼神,尤尚淫祀,至有卖其昆季孥尽者,乃自卖以祭祀焉。”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云:“横州专信巫鬼,其地家无大小,岁七、八月间,量力厚薄,具牛马羊豕诸牲物,罗列室中,召所谓鬼童者五、六人,携之楮造绘画面具,上各画鬼神名号,以次列桌上。以陶杖鼓,大小皮鼓铜锣击之,杂以土歌,远闻可听,一人或三、二人各带面具,衣短红衫,执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清陆祚蕃《粤西偶记》载:“鬼鱼似鳄,壮人仇杀取此鱼祀鬼,舆人食之辄死,觉之请蛮人咒之立苏。”现在壮侗语民族农历七月十四日这个节日之所以名为“鬼节”,其源则起于越人及其后裔在这一天“祠厉”,即焚香烛、化衣,祭祀饿鬼、野鬼。农历七月十四正是稻谷将熟不熟,青黄不接之时。鬼人相通。所以,“禾黄鬼出”[55],以及“十月禾黄鬼上村”[56]。鬼之所以活跃起来,是因为它们饿了,衣敝了,便上村来寻吃找穿。它们作祟于人,便出现了“稻田黄,睡满床”的景况。为免除灾难,人们便以七月十四日为鬼节,给饿鬼、野鬼们祭祀、化衣,满足它们的要求,祈求它们不要伤害阳间的人群,送它们离开村子,由于七月十四日这一天,饿鬼、野鬼窜村入市,非常活跃,所以这一天人们便停止一切作业,不走村入市,连牛也关在家里不放养,唯恐撞上鬼。
以上论述,挂一漏万,取直就简,不论是百越故地汉文化,还是百越后裔的民族文化,其中不仅包含了百越文化的遗传和底层特征,而且在传承的过程中,汉文化与百越文化相互碰撞,其形态和内涵也在改造和整合中交融,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便是这样形成的。也正因为中华文化是海纳百川形成的一体多元的对立统一体,才使得其始终生机勃勃,一直延绵不断。通过百越文化融汇于中华文化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