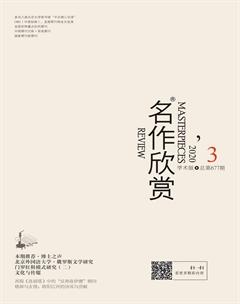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田园诗歌意象差异解析
摘 要:华兹华斯与陶渊明是中英诗坛上杰出的田园诗人,二人均因不满社会、理想破灭而归隐田园。他们的田园诗都充斥着冲淡恬然、物我相融之意。本文拟从诗歌意象角度入手,纵观二人的田园诗创作,从意象选择和意象组合方面分析差异,探寻其背后隐含的中西文化与哲学差异。
关键词:华兹华斯 陶渊明 田园诗歌意象 差异
东晋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增添了田园诗这一新的题材,他的这部分田园诗均写归田后躬耕之甘苦,在简朴、恬美的田园生活中泯去世俗熏染、悠然自得的心境。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产生幻灭感后便蛰居到英国西北湖区,在被人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美学宣言的《抒情歌谣集·序言》里,他主张“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为单纯的状态之下”,因此他最有造诣、成就最高的便是热情讴歌大自然的诗歌,他认为大自然能够启迪人性中的博爱与善良,融合在自然之中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
从意境上看,这两位使人创作的诗歌意境是颇为相像的,他们以敏锐的感悟力怡情山水田园,在物我交融回归自然中使自己的心胸升华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而纵观两位诗人的经历,陶渊明为避开晋室混乱不安的时局不愿和社会现实认同而归隐田园,华兹华斯则因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恐怖政策遭到早年梦想的毁灭而寄情田园,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他创作了大量欣悦愉快并具有鲜明色彩的田园诗。这种借自然景物的慰藉作用逃避浊世的心理倾向则是二位诗人创作的相通之处。但是由于历史、地域、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观念的不同,其二人的田园诗歌意象从比较诗学以及平行研究的角度来看,又存在较大差异。
一、象征性意象与现实意象折射出的文化差异
英国琼·哈格斯特龙的《姊妹艺术·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一文中指出,华兹华斯的“诗作中缺少‘诗画同源的风格”,诗集中并无多少严格意义上的绘画诗,他自己脑海中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想象博物馆”a。 哈格斯特龙认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视觉意象都是笼统的、放大的、具有音乐感的,并非具体的视觉意象,灵魂就像一个星星,而太阳也只是一个泛泛的意象”b。例如在華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作《水仙花》中,水仙花被写成了可以表达欢乐、愉快(“glee”“jocund”)的一个群体(“a crowd”“a host”)。这首诗歌的意象水仙花便被赋予了无限种解读的可能性。如诗歌末尾,华兹华斯写道:“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孤独之中的福;于是我的心便装满幸福,如水仙一同翩翩起舞)诗中的水仙花意象不再是一种植物,它可以象征着内心的欢乐,却也引导着诗人寻找到自己的灵魂,富有神秘色彩又具有象征哲理含义。再比如华兹华斯的在他三十二岁所做的《彩虹》一诗中,彩虹(rainbow)就不仅仅指自然界当中的彩虹了,它可以是华兹华斯渴求回归自然,在对美好自然的追求中收获纯净的心灵,也可以“蕴含一定的宗教情怀”c,即“用耶和华的标志……使他的诗歌才能有赖于回复他童年来自于自然中的欢乐”d。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田园诗是从陶渊明开始的,田园画的出现要略早于田园诗,田园景物成为创作的意象已显示出当时上层文人的审美趣味已不仅局限于政治教化和理论清谈的范围。从创作和作品理论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与画论便有相通之处。陆机《言论》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因此同华兹华斯“缺少诗画同源”风格不同,“言与画”并举这种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文人来说是一种共识。因此陶渊明的田园诗作中呈现给我们的便是“普通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生活场景,乃至更具有感知的审美对象。不仅是可以看到、想到的,而且是可以接触甚至是嗅到的事物”e。“山涤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慢慢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再如《归园田居(其一)》中,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人人可见,普普通通的诗歌意象一切如实说来,并未有奇特隐喻之意,却表达出了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
华兹华斯田园诗歌中象征性的诗歌意象与陶渊明田园诗歌中现实主义的诗歌意象,即像田园画般的平常景物的还原,二者的差异在于西方田园诗人受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影响浓厚,而中国的田园诗人则受儒道二教思想影响深远。华兹华斯的田园诗歌中隐秘的上帝或隐或现,因为“在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中,自然更是神性的表现。人与自然都是从上帝的源头涌出的”f。他认为只有在工业文明尚未浸透的大自然才能使得他遭受毁灭的政治信念与个人情感得到救赎。因此,华兹华斯和其他湖畔派诗作的最大特点便是歌唱自然,崇拜自然神。比如华兹华斯有一首《致杜鹃》的诗,全诗并没有描写杜鹃的形体,而是它飘忽的声音和这种声音带给人心灵的震荡。他的诗以及西方田园诗歌并没有像中国田园诗那样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反而会令人时刻领悟到神秘力量支配万物和对上帝顶礼膜拜的虔诚。这种表现便是华兹华斯的田园诗歌意象充满了隐喻的象征意味。纵然,陶诗中也有酒、鸟、菊松等出现频率较高的主要意象,象征着诗人作为一个躬耕士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但这些意象象征意义明确,没有华兹华斯浪漫主义田园诗歌意象呈现出的混合了人性、神性、理性三位一体。陶渊明深谙儒学,当身处乱世,无法实现弘道济世的理想时,他便到老庄崇尚自然的哲学中寻找归宿,从退隐避世返回自然中获得慰藉。因此,白描般的田园景物意象使他的诗读起来就像一幅田园写生画,色彩、线条实物实景,不论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还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都十分逼真。陶渊明的审美便是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从客观描摹田园生活中,从极为平凡的景物、极为平常的生活细节中发现自然美和领会其中的自然意趣。
二、发散式的意象组合与平行并列意象组合之差别
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外国诗歌,无论长短,每首诗中都不是单个意象的孤立呈示,必然有意象的组合。克莱夫·贝尔认为,意象的组合不仅是为了意象的作用得到确认,而是实现比各部分相加之和大得多的整体价值的最终手段。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人与自然根本互相适应,人的心灵能映照出自然界中最美最有趣的东西……一种想象力的色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之面前。”基于这样的诗歌创作理论,华兹华斯田园诗歌的意象体系具有繁复性的美感,呈现为发散式的意象组合方式。 因此他的田园诗歌意象的组合既有客观物象的铺陈,也有因其本人意念情感联想和想象的产物。如其《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中写到水仙花“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我一眼看见了一万朵,在欢笑之中起伏颠簸,粼粼波光也在跳着舞”,由一个主导意象“水仙花”裂变出其他意象“银河”“波光”,呈现出动态美。在著名的《丁登寺》这首诗中,华兹华斯则写道:“我又一次看到树篱蒿,或许那并非树篱,而是一行行顽皮的树精在野跑。”发散式的意象组合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一缕一缕的意象似乎不断地来到你眼前”g,这除了与其联想的丰富性、审美的独特性有关,也来自于其自然天成的美学思想。
“意象”一词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一贯有之,从《周易·系辞下》中“近取诸身,远取諸物”至刘勰将其带入艺术创作和审美领域,意象更成为中国古代的基本审美形态之一。纵观陶渊明田园诗的意象群体,他无意模山范水,也没有华兹华斯田园诗中以一个意象辐辏其他意象的组合,一诗中的所有意象都是从自然界客观物体取象,追求对外物表象直觉式把握,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递进关系,若干个别意象只是作为一幅完整画面的局部景点呈现。《和郭主簿二首》中,蔼蔼林荫、清凉凯风、悠悠白云、书声琅琅、悠悠琴韵,并列形成群体意象,以意贯之。《已酉岁九月九日》诗中,风露、哀蝉、丛雁、蔓草、园木、秋空等意象构成完美结合体,创造出一幅意蕴深远的暮秋时感图,这不是某个孤立意象能承载的起的,而是通过意象并列,构筑起意味不尽的意象世界,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与陶渊明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哲学密切相关,老庄哲学崇尚自然,强调天人合一,因此中国民族思维传统便是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与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自然观,他的田园诗歌中多是同一时空或同一逻辑起点上多个意象的平行组合。
ab 杨乃乔:《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第74页。
cd 李肖锐:《李白焦山望松廖山、华兹华斯我心雀跃中“彩虹”意象对比研究》,《大众文艺》2013年第16期。
e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f 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g 邹建军:《论华兹华斯诗歌的意象形态》,《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60页。
作 者: 朱林,硕士,山西工程职业学院基础部高职语文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