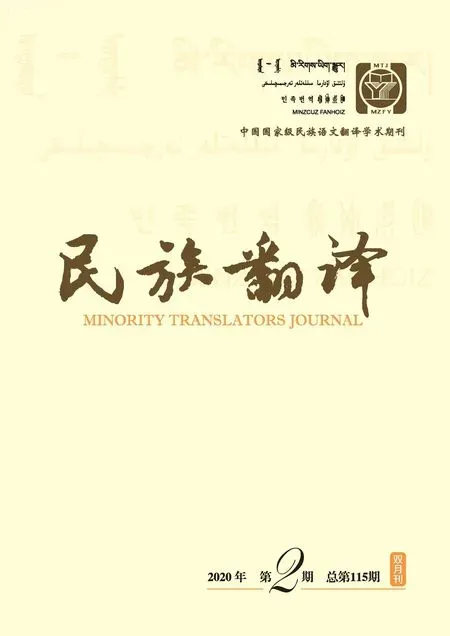互文性视阈下《蒙古秘史》之翻译探究
⊙ 张锁军 田振江
(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一、引言
互文性又名“文本间性”,“互文性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1],其最早出现于20世纪后期,由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次提出,她认为“互文性指的是任何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拼接而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改造。”[2]即明确了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任何文本都不是“原创”,其理解都离不开“互文性”的作用。她认为的“互文性”并非单纯指文本内上下文之间的语境关联,而更多地关注文本外不同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往来,他们彼此相互参照、相互引用、相互指代,形成了宏大的开放体系。这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创作、语言及文体学分析、翻译教学与研究、语言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缔造了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新视角。其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的结合对于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增加了新的视角,形成了新的方向,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文选取《蒙古秘史校勘本》和阿尔达扎布译《新译集注〈蒙古秘史〉》为底本,从内容互文性、语体互文性和副文本互文性三个维度扼要分析互文性在其中的应用及其翻译效果。
二、互文性视角下的翻译思辨
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之间的对话,认为任何文本都要共时、历时地再现并接受一切外来文本信息,这些文本共同交织在一起形成庞大的体系,任何新文本的产生都要在这个庞大体系中与各方对话,这与翻译活动及其研究有着天然共性,为二者的结合缔造了基础。
互文性与翻译研究的开放性。互文性视角下的文本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即对外开放性,或曰,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拼接,是对其他文本的再创作。学者们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到翻译领域,这打破了传统翻译的局限性,凸显了文本的开放性以及互动性,“翻译活动不是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3]因此,译者不能只将自己的翻译活动局限于狭义的文本,翻译文本是开放的,其生成亦是吸收或引用其他文本信息,在与其他文本互动对话中实现的。所有文本都在其所构成的庞大体系中不断运动,是动态地相互影响着的。
互文性与翻译研究的多元性。互文性理论的提出,其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敢于挑战原创,认为没有所谓的“原创”,翻译研究也因此不再局限于源语作者的绝对权威性,即打破了翻译活动的一元性,而更多地关注翻译活动的过程性研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看似是源语和译语的桥梁,实则是译者的身份发生着复杂变化——读者、阐释者、译者、创作者,并且还需将这几种不同身份做自然的对接。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解码源语文本,并结合自己所习得、掌握的知识对其进行阐释和改造,再结合译语习惯将其进行编码,译成译语文本。译者不仅要熟悉和了解源语和译语语言知识,更要主动寻求文本的相关知识,如:社会背景、文化视野、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改写,从而实现翻译活动的一元到多元的跨越。
互文性与翻译研究的再创造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对原文本进行再创作,即互文性转换过程。译者不仅自身身份在不同阶段发生着变化,还要与不同身份的人对话,不仅要与作者对话,还要与读者对话,要全面、多方位、立体地展开翻译活动。值得关注的是,译者基于自身已有知识体系和文本信息去理解和接受周围世界更庞大的文本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自我意识的再创造,即不仅要书写自我,更要书写他人。可见,为了还原源语语言与文化全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所寻求的互文性转换需充分考虑语体、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副文本等多重动态因素,并将其进行互文信息结合,只有做到这一点,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才能在“理解—阐释—转化—表达”中真正传递源语信息,并再造出符合译语读者群体习惯的译文。
翻译活动不是两种语言符号文本的简单转换,互文性视角下的翻译活动涉及对原文本的解构与建构,文本与文本间的阅读、阐释以及再创造,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历史的庞大本文体系中加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翻译活动的全貌和本质,找寻翻译活动的策略。
三、《蒙古秘史》汉译本之互文性
《蒙古秘史》共12卷,282节,记述了蒙古族近500年的历史。其语言形式独特、草原气息浓厚、符号资源充沛、互文信息明显,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专家们的关注。虽然原文本无法找寻,但一直以来相关研究却并未止步,各类相关主题的文章与著作均不鲜见。自清朝末年传播至国外,《蒙古秘史》被译成多种语言而存在,“包括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中文、俄语、匈牙利语和波兰语”[4],仅就《蒙古秘史》现存版本而言,“目前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有375个版本的《蒙古秘史》。”[5]
就中文版本而言,历史上就出现过顾广圻的“顾氏本”、钱大昕的“钱氏本”和叶德辉的“叶氏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阿尔达扎布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中,不仅译出了现代汉语译文,《蒙古秘史校勘本》原文也被附在其后。故此,笔者将其用作底本,探究互文性理论在此文本中如何在开放性、多元性和再创造性三个方面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并以此来分析译本中运用的翻译策略。
(一)内容互文性(Content Intertextuality)
内容互文性是互文性理论在各类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任何文本内容都是对其他文本的拼接或引用。要理解《蒙古秘史》这样一部文化气息浓厚的著作就必须要了解蒙古族文化,特别是语言表达方式和风土人情,充分了解互文信息才能更好地进行品读和欣赏。
《蒙古秘史》中包含了丰富的谚语,互文性理论体现得比较明显。从符号转换角度来看,文中所选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内容表述大体一致。但由于不同版本目的语读者不同,作者在翻译文化色彩浓厚的谚语时,均采用了不同的语言文字符号来表述,即符号形式发生转变,符号信息内容未变化,这样的翻译属于典型的直译,保留了蒙古语原有的文化气息。如:
例1:
校勘本原文音译为:孛可列因孛薛圖兒,扯客列因 扯额只圖兒。[6]559
中文译作:放在髀石背面的臀部,放在髀石心面的胸部。[6]178
从内容上看,髀石并非真正的石头,它类似于人类的膝关节,多指动物腿部连接上下骨骼的关节。髀石分心面和背面,两面都有凸起的部分,看起来像它的臀部和胸部,蒙古语源语的表述极具蒙古游牧民族文化特色,是蒙古族常用的谚语,即将重要的人或事放在髀石凸起之处,用于表示牢记在心,不会忘记之意。以往的很多译本将其译作“放在腰子的尖里,胸膈的腔子里”或意译为“绝不会忘记”,虽大致传递了意思,却不够精准。根据互文性开放性特点,任何文本与其他文本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话,译语文本需要开放性地寻找恰当的文本进行吸收,而在这里阿尔达扎布的译本直接引用了传统的蒙古谚语,在语言形式和内容上忠实于原文本,原汁原味地复制了原文信息。符号形式虽有转变,但符号信息内容未变,互文性作用明显,既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元素,又为蒙古族文化的传播贡献了力量。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据笔者统计,整部《蒙古秘史》汉译本中内容互文性运用达35处之多,再如:
例2:
校勘本原文音译为:阿米秃 古兀捏 不 客列列[6]548
中文译作:对活人不要讲![6]146
这段故事发生在成吉思汗小时候遭敌人追杀,被沉白和赤老温所救,将其藏在羊毛车上,并告知女儿合答安“对活人不要讲!”以往这句话多被译成“不要对任何人讲!”这其实也没有错,准确传递了源语信息。但考虑到语言文化习惯,蒙古族常年生活在草原,以骑马放牧为主要活动,思维习惯直来直去,说话方式淳朴自然,不加修饰,阿尔达扎布的译文草原色彩清晰,更符合内容语境。
总的来说,内容互文性在这里体现明显,是文本信息顺利传递的必要所在。译者在理解原文本的有形符号到译为自己思想中的无形符号,并将思想中的无形符号译为目的语的有形符号的整个翻译过程中,符号转换频繁,过程较为繁琐,译者如何开放性地选择较为合适的方式进行符号翻译至关重要。从互文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再创造性角度看,译者不仅在对话作者,更在对话读者,为了将文本信息进行最佳传递,在此过程中译者身份发生众多变化,在对源文解码和译文编码中,译者开放性地充分考虑了蒙古文化元素和语言习惯,对原文本进行多元性的再创造翻译活动,以期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并实现与译语读者更好欣赏《蒙古秘史》的目的。
(二)语体互文性(Genre Intertextuality)
语体是民族语言的功能变体,“当一个语篇跨越单一的语体边界,融汇多种语体的表达特点,呈现出一种多体混成的状态时,就是语体互文。”[7]语体与语篇关系密切,一种语体应具有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或特点,而语体特点的体现要借助于语篇功能来生成。
《蒙古秘史》语体较为特别,它以记史的形式记载了黄金家族近500年的兴衰存亡,所谓“秘史”,应是皇帝命人撰写,以供黄金家族内部阅读和参考。虽为史书类著作,但《蒙古秘史》语言风格淳朴,自然天成,并未采用许多的技巧,为“白话文”作品,其主要语体为口语语体。此外,《蒙古秘史》不单单记载史实资料,其中更包含了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多方面的描写,以类似于百科全书的形式记载了当时蒙古社会的诸多事宜,这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提升了文本的审美功能,更是当时社会文明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当时人们所喜欢并乐于接受的形式,故此其次要语体应为文学语体。如:
例3:
校勘本原文音译为:迭額列腾格理額扯 札牙阿秃脱列先 孛兒帖·赤那 阿主兀。格兒該 亦訥豁埃·馬闌阿只埃。騰汲客秃周亦列罷。斡難·沐漣訥 贴里兀捏 不峏罕·哈合敦納 嫩秃剌周 脱列先 巴塔赤·罕 阿主兀。[6]523
中文译作:孛儿帖·赤那奉上天之名而生。他的妻子是豁埃·马阑勒。他们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峏罕合勒敦山,驻扎下来。生下儿子,名叫巴塔赤·罕。[6]1
例4:
校勘本原文音译为:雪你不里。超堅失剌 古温格侖 額魯格 朶脱合因 格格額兒 斡羅周客額里 米訥 必里周。格格延 亦訥 客額里突兒 米訥 升格古 不列額。合魯侖納闌 撒剌因 乞里耶兒。失剌 那孩篾圖 拭察班札周 合兒忽 不列額。[6]527
中文译作:每夜,有个明亮的黄色的人,循着天窗或门额射入的光芒而进来,抚摸着我的肚子,使其光芒透进我的肚里。出去时,在日月的光照下,如同黄狗一般,摇摆着悄悄的溜走。[6]48
例3出现在《蒙古秘史》第1节,其语体风格简单纯朴,以作者独有的口语语体记述了蒙古族祖先的姓氏,发源地以及辈分关系等信息,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的描写和修饰语言,颇有“记史”印记;而例4出现在《蒙古秘史》第21节,阿阑·豁阿的两个儿子猜忌父亲及叔父们死后,后面的三个儿子是母亲和谁所生。阿阑·豁阿作为母亲向自己的儿子们讲述自己“感光生子”这样极具神话色彩的故事,其语体风格截然不同。文学语体的运用增强了神话故事的叙事效果,描写细致入微,使得神话故事听起来更自然可信,以实现说话者特殊的语用目的:让儿子们相信自己,并确保自己在儿子们心中的地位不受动摇。
从互文性角度来看,译者开放地吸收不同语体的不同文本并将其拼接和再创造,所译出的新文本将不同语体自然地交织在一起,语体互文性明显。不同的语体风格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主要语体与次要语体相互配合,为故事情节的展开以及趣味性、可读性的提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蒙古文译到中文,符号形式发生了变化,但符号信息基本未变,语体互文性的运用充斥在两个文本中,语体互文转化高达153次之多。译者在语体转换中对文本的再创造能力值得赞叹,不同语体的自然衔接提升了译文的质量,旨在最大限度传递源语信息的同时更关注了源语信息的方式,从而实现翻译的最佳效果。
(三)副文本互文性(Paratextual Intertextuality)
克里斯蒂娃倡导的互文性需与解构主义批判相结合,倾向于对其做模糊的解释。与此不同,热奈特(Genette)所提倡的互文性更为精准,使其成为可以进行描述的工具。他在《羊皮纸:二级文学》(1982)提出跨文本性概念,并界定了5种不同类型的跨文本关系: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uality),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和广文本性(architextuality)。[8]这5种跨文本关系中,副文本的概念和价值得到了广泛关注。副文本由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构成,主要包括标题、章节标题、前言、序言、注释、后记等。
《蒙古秘史》为畏兀儿字母书写的蒙古文,语言晦涩难懂,而勘本是将其进行汉字标音转写出来的。无论是哪种形式都不方便阅读,语言和文化所造成的障碍对于一般汉语使用者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汉语译本中,为实现最佳的理解效果,许多译者采用多种形式的注释对文本加以解释说明,副文本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阿尔达扎布翻译的《蒙古秘史》中副文本信息极其丰富,主要表现为5种形式:一是前言,作者为此书做了6页的前言,不仅介绍了《蒙古秘史》的由来以及传承过程,更举例说明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重要或者有争议的符号信息,乃至于编写体例等详细信息,起到了很好的导读作用;二是章节提要,概括总结本卷或者本节的主要内容,辅助读者对文本信息进行整体把控;三是明代总译,此为明朝初期翰林院议员们将每个词进行了注释,并对每节大致内容进行汉译,形成了独特的形式。此部分的添加有助于将古文和现代文进行比对,分析符号信息转变或增减的原因,来探究汉译本的优与劣;四是注释,正文中以注释形式对重要词条加以辅助说明,以便读者了解更多的原文信息。很多时候都是译文仅有一页,而注释却有几页甚至十几页之多,总注释多达1160多个词条,主要对重要历史人物、事件以及蒙古族风俗习惯等进行详解说明。此点最为重要,所占篇幅也最多,注释频繁引用他人见解并进行分析说明文本信息及翻译策略,更直接引用古人言语或经典著作来解释说明蒙古文化特色词汇及习俗等;五是索引,书后做了详尽的索引,可用于检索正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部族名,值得一提的是,此部分为多种语言符号进行编写,可满足不同语言使用者理解词义的不同需求。
副文本互文性属于典型的增译手法,使得符号信息成倍增加,但蒙汉民族在语言、习俗以及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若不能理解《蒙古秘史》中文化色彩浓厚的词汇以及历史事件,则有碍把握其全貌。从互文性视角分析,译本中副文本的使用体现了其开放性,即译文中吸收了许多与原文本相关联的其他文本,主要包括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文本,以此来对原文信息进行辅助说明,“副文本元素从属于它的文本。”[8]这既是对原文本的再创造,亦是译者考虑源语作者、译语读者、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多元翻译产物。表面看虽增加了读者理解和记忆的负担,实则却换来读者对文本理解程度的提升,更对于《蒙古秘史》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结论
互文性理论进入语言学领域对文本阐释以及语篇分析大有裨益,且成为影响翻译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以互文性理论为视角,对《蒙古秘史》蒙文校勘本和中文译本进行解读,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蒙古秘史》这部民族历史巨著,更可以对互文性理论的研究起到助推作用。通过内容互文性、语体互文性和副文本互文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看到符号资源丰富的《蒙古秘史》中存在大量互文性信息,其表现形式多样,却均服务于作者或译者写作或翻译意图。译者将翻译策略与互文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再创造性密切结合,使之在这部历史巨作撰写及翻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探究这些互文符号的翻译策略,为今后传统历史著作、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