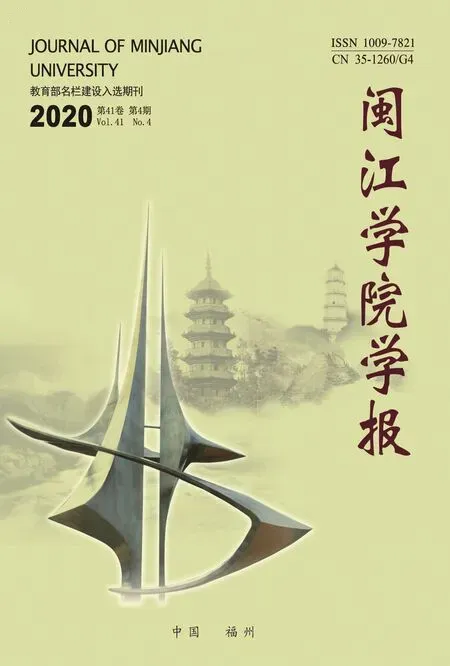陈普咏史诗之自注研究
阎震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陈普(1244—1315),字尚德,别号惧斋,福建宁德石堂人士,世称石堂先生。宋末元初理学家、文学家。师承韩翼甫,为朱熹三传弟子。其生平散见于《宋元学案》《宋季忠义录》《东越文苑》等,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传世。《石堂先生遗集》中存咏史诗二卷,共370首,别题为《咏史诗断》,体裁上采用七言绝句,以一人一题的形式对上至尧舜、下至南宋的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品评,诗后自注多达280条,占比巨大。分析陈普的咏史诗,需要精准把握其诗后的自注,点明其特点、作用,剖析诗歌与自注之间的关系,从而清晰呈现诗人的创作意图,揭示其咏史诗背后的思想内涵。
一、诗歌自注的源流
出于探究文学作品本意的目的,围绕文本展开的阐释在将目光对准文本本身的同时,亦应关注附属文本的功能和意义。自注是附属文本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中国的注疏之学起源甚早,经学家往往以“注”“疏”“笺”等方式解读经典,郑玄遍注古文经便是一例,文学家亦对文学作品进行注释,如王逸作《楚辞章句》,此皆为他注。自注的源起可追溯到《史记》,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在自己的著作中交代背景、解释词语、发表评论,开自注之先河。诚如章学诚所言:“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自注”[1]。此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部著作皆保留了自注这一形式。
降至南北朝,自注实现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迁移,谢灵运《山居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皆有自注。目前可考的诗人中,鲍照最早对诗歌作自注,其《学陶彭泽体》《喜雨》《侍宴覆舟山二首》皆有题下注,从此自注进入诗歌这一体裁中。中唐以来,诗歌中的自注明显增多,尤以元稹、白居易为典型代表。二人对自己的作品大量做注,种类丰富,形式繁多,以位置论有题注、夹注、尾注等,以功能而言有音注、人名注、措辞注等。往往一首诗歌便带有多条注释,如白居易《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一诗,题注以“昔予为尹日创造之”[2]828交代创作时间,诗后注“自予罢后,至中丞,凡十一尹也”[2]828交代现状,中间还有夹注解释用词。在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注释的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有标明出处、补充背景、解释目的等,可谓无所不包。如同样是题注,白居易《逸老》一诗解释了诗题的典故出自庄子,而《过裴令公宅二绝句》则叙述了与友人的过往。
两宋承唐而来,诗歌自注于数量、方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苏碧铨《论王禹偁诗歌自注的文学功能与文献价值》一文统计王禹偁现存640余首诗歌中自注数量近300条,占比为宋人第一[3]。《施注苏诗》中保存有520余条苏轼自注。欧阳修留存的38首古体诗中自注内容颇丰[4]。黄庭坚、王安石等人作品中亦有大量形式各异的自注。
就诗歌而言,宋诗中的自注有其特殊之处。基于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反思以及诗歌服务于学术、政治等原因,宋人在诗歌创作上开辟了新的路径,提出了新的诗学理论。周裕锴以“四端”概括宋人对诗的认识:“一是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诗是天地元气的体现;二是从艺术本质着眼,认为诗是文章精华的结晶;三是从心理角度来讨论,认为诗是人格精神的体现;四是从哲学角度来考虑,认为诗是伦理道德的余绪。”[5]秉持着此种诗学认知,宋代诗歌一反唐代“丰腴华贵”的气象,走入了“富有理趣”的世界。“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6],宋人以才学的积累替代天赋的挥洒,本着深厚的知识储备,凭借以理入诗的方式创作诗歌,形成了“学问化”的特点。作为诗歌附属文本的“自注”,亦在文本的影响下,走向了“知识化” “理性化”。宋诗的自注集中于解释字词、阐明典故,注重为读者提供相应的知识背景,较少言说个人经历,或抒发一己之情的叙述性内容。
活跃于宋季的陈普,在宋代诗歌自注风格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带有自注的咏史诗,其自注带有宋诗自注的一般性特点,亦有其特殊之处。这些自注作为架构于诗歌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为我们理解陈普的咏史诗,感受诗人的史论观念、儒学思维、思想感情提供了一条捷径。
二、陈普咏史诗自注的特点
(一)篇幅较长,种类单一
陈普所作的370首咏史诗中,留存自注多达280条。若仅就咏史诗而论,陈普诗中自注的占比较王禹偁而言亦不落下风,可谓体量巨大。其自注篇幅灵活,长短不一,诗人根据诗歌的不同情况为其做出合适的注解,详实之处论述完备,简略之处言简意赅,最短的仅有4字,最长为《鲁肃》一诗,达1 033字。考其自注全貌,总体而言篇幅较长的居多,诗后自注达百字以上的比比皆是,如《朱文公》《慕容垂》等。作为对比,同为宋人的黄庭坚105条自注中最长的仅43字。较前人而言,陈普诗后的自注可谓“长篇巨制”。
不同于白居易、元稹等诗人,陈普咏史诗的自注内容单一,几乎不针对诗歌的音节、措辞进行自注,也没有与自我相关的抒情性或叙事性内容,就形式而言亦仅诗后注一种,无夹注、题注等。陈普的自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为诗歌提供背景知识、相关材料,如《廉颇蔺相如》一诗自注“长平丧师时,廉蔺皆在”[7]5;二是对诗歌内容做出的史论、史断,如《季札》自注言“事之失正者,皆足以乱天下,亡国败家”[7]3。两种类型往往融合在一起。
陈普自注篇幅较长,种类单一的特点,与咏史诗内涵丰富、适合评述的特性息息相关。诗歌短小的体制决定其无法将复杂的历史充分铺陈,诗人对历史的评判亦无法浓缩在三言两语之中,或注于诗题之下、诗句之间,因而陈普采用了尾注的形式,以较长的篇幅交代事件、补充细节,同时亦借助大篇幅给予的广阔空间挥洒笔墨,淋漓尽致地倾泻自己的思想。诗歌的特性和诗人的创作意图得到了和谐的融汇。
(二)知识化
“文本的陈述丝毫不是凝固的,只有作者或读者的陈述才必定是确定的东西。”[8]为了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好地扩散个人经验,作者有必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释。这是自注最为直接、普遍的目的。“自注”是“由作者直接担当阐释者”[9]。陈普咏史诗后的自注,对诗歌内容进行大量的资料补充,或解释疑难之处,其目的亦是为了全面、客观地还原史实,准确地传达作者的思想,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论断,避免误差。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大量援引经典,其自注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典型宋人诗歌自注“知识化”“学问化”的特点。
第一,陈普诗歌中的自注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对诗歌做了细致的补充性说明。如《蜀先主》(其三)自注云:“汉末群雄各得一州,而又有际会岁月……初得徐州,而为袁绍、吕布所害。再得徐州,而为曹操所苦……末年急计,不得已取刘璋。”[10]1从地理角度切入,将刘备所占、所经地盘以时间顺序一一排列。这些地域上的细节使得刘备一生“北投南走若穷猿”[10]1的窘境生动了起来,让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而使诗歌实现具象化,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观点。自注提供给诗歌的地理、历史细节从另一方面亦佐证了诗人论述的准确性。
第二,陈普的自注把握了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往往将知识从一点引申至另一点,使自注的知识立体化、结构化。如开篇的《有虞氏》,诗的着眼点乃舜的品德,然在自注中,诗人不仅仅以舜与其父亲瞽叟、兄弟象之间的事例来阐述儒家的忠孝之义、兄弟之亲,更进一步发散开去,通过周文王、颜回的遭遇探讨面对穷达、生死的方法,以伯夷、叔齐的高义为切入点论述“天地之常经”[7]1,将诸多历史人物联结在一起,拓宽了自注覆盖的知识面,以之丰富诗歌内涵,深化诗人论断。《齐桓公》二首于自注中言霸道之弊,亦由齐桓推至秦皇。
(三)论述化
知识化的自注具有补充性质,其功能是拓宽诗歌文本,为读者提供解释性的材料。除此之外,陈普亦将自己对历史的观点通过自注来表达,使自注知识化的同时亦带有了强烈的议论性,形成了第三种特点——论述化。不同于知识化,论述化的核心在于阐述作者自身的观点,而非为文本添加材料或为读者提供辅助。陈普通过诗后自注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点,分析、引援具体史实支撑自己的论断,甚至采用假设性的论据,时有别出机杼的史论。其论述化的自注与诗歌互相生发,完善了诗歌的表达功能,将作者的思想和诗歌的内容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诗注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以《鲁肃》一诗为例,陈普在自注中举出部分史实作为证据,之后划分论点,展开了其独到的论述。第一,陈普认为刘备占有荆州是时势所逼,形势比人强,且早在其谋划之中,“刘表未死……已以荆、益为囊中物,非夺之也,事势然也”[10]12,因而不能归罪其失信,为蜀汉政权开脱;其次,陈普认为赤壁之战时周瑜的兵马和关羽、刘锜的军队数量相当,双方投入的力量不分伯仲,因而功劳相当,且刘备集团事后又再次战胜了曹操,论功荆州应归刘备所有,“乌林之役,周瑜水军三万,关羽与刘锜亦二、三万”[10]12;第三,周瑜不仅想要夺回荆州,甚至想进一步由荆襄攻取益州,侵占刘备谋划内的地盘,置其于绝境,是为不义,“是欲置玄德于无立锥之地”[10]12。陈普以此三点为刘备集团占据荆州提供了依据,从而证明鲁肃欲将荆州赋予蜀国这一政治行为从道义而言所具有的正确性,“始是当年子敬心”[10]12,称赞了鲁肃作为一个政治家所秉持的道德和大局观,指出周瑜的错误。抛开论断的准确与否,陈普的自注论点鲜明,论据详实,诗歌和自注互为表里,议论性强,诗人对自身的论断相当自信,其论述化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自注的论述化使陈普的咏史诗上升到新的高度。
三、自注中体现的思想内核
陈普咏史诗后的自注,于诗歌文本而言,是补充材料的存放之所,亦是诗人发表议论的舞台,然其意义并非仅限于阐释学。史料与论述的背后,是诗人作为一个理学家所秉持的、一以贯之其生命的儒学思想。陈普以儒学的纲常伦理为绳墨,衡量古今人物,评判历朝事件,形成了强烈的道德史观,于其自注中流露出来,集中表现为明正统、贬簒逆的思想、先德后功的评判标准、批判异端邪说及天命思想四方面。
(一)明正统、贬篡逆
正统观念,由来已久,孔子论“华夷之辨”,已从中原王朝与周边部落关系的角度涉及了这一问题。汉代秦而来,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继周寻求理论支持,亦是明统序之正。陈寿著《三国志》,以魏、晋承汉,开后世正统之辩的争端。同为晋人的习凿齿便反对陈寿之说,以蜀承汉,而以晋代蜀。降至两宋,论争更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秉持“正闰之际,非敢所知,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11]的态度记录历史,遇分裂混战时期,便选一朝为主,平等地叙述各个政权。南宋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一反司马光的标准,依照《春秋》条例,以儒学的道德伦理作为主要依据,重新树立正统谱系。作为考亭的三传弟子,陈普的史论继承了朱熹的正统观念,于自注中鲜明可见。
朱熹与司马光关于正统的论争,主要分歧在于三国时期,司马光以魏为正统,朱熹则以蜀汉为王道,“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12]3 459,针对蜀汉未能一统中原的结果,朱熹甚至创立了“正统之余”这一说法,来为蜀汉寻求统系上的合理性。“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13]“蜀汉是正统之余,如东晋,亦是正统之余也。”[12]3 459陈普接受了其师的理论,将蜀汉置于正统地位,以魏、吴为僭国,以达到“示训”的目的。如《荀彧》(其一)自注云“曹操作西园校尉及屯酸枣时,其所志愿未必不正”,“以文若之才略……而复日闻道德之言……逆乱之心,老死不发矣”[10]10。陈普以荀彧这一曹操的重要谋士为切入点,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论证曹操篡逆行为的不正当性。在诗人的眼中,曹操应当始终怀抱其“暮年当作汉征西”[10]10的志向,遵守人臣之义,尽心辅佐王室,而非从英雄转变为奸雄。诗人以诸葛亮为对照,将曹操的篡权行为归结于其身边谋士未能导之以德,暂且不论这一论断的合理性,但对于曹操的越统篡夺的批判,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正统观念于《蜀先主》(十二)一诗的自注中表达得更为明显,诗后自注云“建安十八年,操立为魏公,杀皇后伏氏”[10]3,“后主建兴七年,孙权称帝于武昌”[10]3,对于魏、吴等割据政权的统治者,陈普从君臣大义的角度出发,罗列其失德之举,批判其人的叛逆行径,对他们做出否定的评价。但同时,对于刘备这一正统的继承者,从“贬篡逆”的角度而言,诗人亦有微词:“辛丑年,蜀中传献帝被害……费诗谏勿称王,不悦,左迁之,遂继帝位于武担之南。”[10]4就统系而言,陈普承认刘备继承汉朝建立蜀汉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但彼时汉献帝仍未死,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刘备不顾费诗的劝谏,即刻登上王位,从“臣事君以忠”[14]的角度而言,亦有不当之处,因而诗人称其“幸自无颇辟”[10]3,没有落入“无君”者的行列。
陈普通过其自注,对正统与非正统做了明确的划分,于评判中寓褒贬,以期达到“明顺逆、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的目的,其正统思想于儒学道德史观的驱使下,从自注中强烈地表达出来,可证其儒学思想之一端。
(二)先德后功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5]从儒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人物的考量,最为普遍、也最为重要的两个判定标准,便是德行与功业。但一个人的德行和功业往往并非是一致的,当二者发生错位时,就儒学的伦理道德而言,“德行”会被置于“功业”之前。陈普的史论吸收了这一准则,以“先德后功”的尺度衡量历史人物,做出儒学思维下的论断。
《齐桓公》二首围绕儒家的“王霸利义”之辩展开,批判齐桓公及以其为代表的霸道政治。第一首自注云:“霸始齐桓,极于始皇,二人之死,皆不得棺敛。”[7]2先从结果上印证“霸道”的错误性。第二首自注点明“内不修德而外有骄色”[7]3乃齐桓公失败的原因,将霸道的失败归于德治的缺失。“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16]105,孟子从行仁的方式上将王道与霸道区分开来,并将王道置于霸道之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6]105王道、霸道的比较,其实质是对于德行、功业的考量。儒家在政治上推崇“仁政”和“德治”的思想,功业的达成要以道德的建立为前提,纯粹出于事功的霸道不符合儒学的伦理道德。陈普于自注中推“王义”,反“霸利”,正是本于“先德后功”的原则。“不修德则无本”[7]3,对于齐桓公这类无德,不凭借仁义立国的君主,纵有功业,亦难入诗人法眼。
庞统与诸葛亮并称凤雏、卧龙,乃刘备的重要谋士,为攻占西川做出重要贡献。然陈普《庞士元》一诗对其趋利负义的行径做了批判,自注云:“士元之于仁义如此,凤雏之称,得无过乎?”[10]6作者认为刘璋善意邀请刘备入川,刘备初亦无负刘璋之意,而庞统定谋划计,急欲刘备吞并刘璋,非仁人所当为,甚至将其中箭而亡归于“岂所谓趋利而蹶者欤”[10]7。晋人习凿齿亦云:“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17]在谋划西川这一事件中,庞统为了一时之功绩劝其主背信弃义,于仁义之害甚大,相较而言,庞统取得的功业已无足轻重。《羊祜》(其二)高度评价了羊祜“尺鲤何曾到贾充”的行为,自注云:“祜预同谋伐吴,祜在襄阳,不附中朝权贵……杜预继之,数饷遗洛中贵要。”[10]24陈普将羊祜与杜预做对比,认为羊祜纵使被抑,亦不以利益结交权贵,换取事功,虽然未能完成伐吴之业,但能全其一己之义,不以功名废仁义,无愧于心,“平吴之功宁为祜而不为预矣”[10]24。陈普依据儒学政治理论,将“德行”“功业”划分先后主次,以“先德后功”的标准考量历史人物,肯定道德的至高地位,否认缺乏仁义支撑的事功,其“德治史观”可见一斑。
(三)批判异端邪说
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提倡而被设立为官方正统思想,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然在由汉到宋的千百年间,多次遭到以释氏、老氏为代表的其他学说的冲击。唐代大量的道教徒得以进用,“开元中……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虽汉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18]。宋继五代十国,连绵的战争造成了礼纪伦常的崩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19],“异端邪说”盛行,在思想层面上与儒学夺权。宋太宗在位时佛道并重:“上素崇尚释教,即召见天息灾等”[20],“召华山道士丁少微”[21]58。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伙同丁谓制造祥瑞,进行封禅,以致于“一国君臣如病狂”[21]172的程度,道教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崇奉。宋徽宗对于道教的热衷有过之而无不及,“夏四月庚申,帝讽道箓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21]396。针对这一情况,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们竭尽全力重塑道统,发明儒学义理,以重新证明其地位的合理性、合法性,相当重要的一环便是对“异端邪说”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
陈普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人,自然承担起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使命。其咏史诗对佛、老等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何晏》一诗从“清谈”这一行为入手,对根植其背后的老庄思想进行攻讦,自注云:“盖吾道之所不容者”“其罪浮于桀纣”[10]18,何晏终日清谈,沉溺于老庄的玄言之中,不修身正性,其服食、行散等行为背弃礼法,与名教相去甚远,遭到作者的强烈批判。陈普还称“近世以其所解《论语》行天下,是未尝读书也”[10]18,将何晏所著《论语集解》与其人一同否定。信仰老庄之人难免以道家思想浸染《论语》,有悖孔门正道,难现其中精义,因而为诗人所不耻。《老子》则将矛头直接对准了道家、道教的思想源头。其自注称:“老子其流之弊,至于书符咒水”[7]3,诗人考量道家的流变史,认为老子“玄之又玄”的哲学理念最终必然走入宗教的范畴,以致于终日画符祈神,于世教无益,徒祸害心性。
《宪宗》一诗通过自注揭示了佛教对唐代政治的负面作用,“宪宗元和十三年迎佛骨,韩愈以谏贬……人谓佛骨之不祥也”,“懿宗咸通十四年再迎佛骨,百倍元和之奢……四月佛骨至京师,七月殂”[10]41。唐宪宗、唐懿宗等君王信奉佛教,崇浮屠之说,以至于蔽塞耳目,迷惑心性,耗费财力,不恤民生,诗人揭露了释氏于家国天下之危害。
(四)天命思想
天命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陈普的咏史诗对天人关系多有探讨,对于“天命”这一至高无上的终极概念,诗人表达了认同,认为天伦与人伦,二者是紧密结合的,天命不可抗拒。
首先,陈普在自注中多次表达了对某些历史片段无可挽回的遗憾,尤其是部分事件中的主人公德行俱佳,却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一类人物,或者说事件,诗人往往无法解释,只能将其归为“天命”。以曹操为例,其以臣犯君,不施仁义,就儒学的道德标准而言,“仁、德”等成功的基本要素皆不具备,却安全渡过诸多危难,一统北方。对其成就的功业,诗人只能归结于天命,“孙策以部署死,天也。不死则许危而袁绍未败”[10]9,天命选择曹操,人力无法抗拒。反观刘备,汉室宗亲,一代仁君,却最终难以避免失败,陈普认为也是天命使然。《蜀先主》(其一)自注云:“老而后跨荆益,天也。”[10]1作者将刘备少年织鞋贩履,老来方才开创基业归结于天意,认为天要汉祚于此终结,因而不让英雄人物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地点。
其次,陈普亦从天命的角度论证部分政权灭亡的必然性。如《秦皇》(其二)自注称:“地上宫室焚于项羽,地下百司宫观尽于牧羊者,是造物欲灭其迹,不使留于天地间。”[7]7陈普以鬼神之怒佐证嬴政的无道,借造物主的意志否定秦朝的统治,此即董仲舒“灾异谴告”理论的具体显现。对于西晋的迅速沦亡,陈普亦将其置于天命的视域下观照。《晋武帝》(其三)自注云:“岂天欲假手南风,为魏报仇,而夺其神明乎?”[10]23诗人将司马炎皇位无人可托付的结局归结于“天教炽业谢芳髦”,认为是天对篡夺魏国政权、残害曹氏的司马氏的惩治。
再次,天命论在陈普的咏史诗中,还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即五行相继之说。自汉以来,阴阳五行之说成为了天命论的一部分,儒者以此来解释政权更替,也用之制约人君,维持政治秩序。陈普的咏史诗中,五行相继作为天命论的标志清晰可见,《邹衍》一诗是最直接的证据,其自注云:“邹衍始为五运之说,秦乘之为水德,色尚黑,用法刻急”[7]8,诗人认为居于水德的秦以刑法易德法治国,注定招致失败,“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皆上黑……事皆决于法”[7]8。《史记索隐》云“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22]。《司马宣王》(其四)一诗的自注引用《洪范》的话,说明司马氏正因为没有“积善”,才导致子孙无法“逢吉”,最终不能得天,亦是诗人信奉五行相继说的体现。
陈普其师祖朱熹撰写《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对历代兴亡的原因有自己的观点,比如“治—乱—治”的历史循环论,但有时朱熹也无法理清历史变迁的真正原因,亦将其归结于天命论,《朱子语类》中就有“废兴存亡惟天命”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陈普于朱熹的一脉相承。
陈普咏史诗的自注在继承先辈诗人的基础上,受宋代诗歌学问化的影响,形成了篇幅长、种类少,带有知识化和强烈论述性的特点。在这些特点的背后,是诗人借以安身立命的儒学思想。陈普采用以理入史的方式,通过自注,将儒学的道德观念蕴藉于史论之中,集中表现为明顺贬逆的正统思想、先德后功的道德评判准则、批判佛老思想以及天命思想。通过对陈普咏史诗自注的分析,可以实现诗歌文本与附属文本的沟通,完成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解读其咏史诗,把握诗歌的思想内核,以至对诗人的精神世界有更为深刻的理解。陈普咏史诗自注的价值绝不仅于此,还体现在诸如文献学等多方面,以俟下次再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