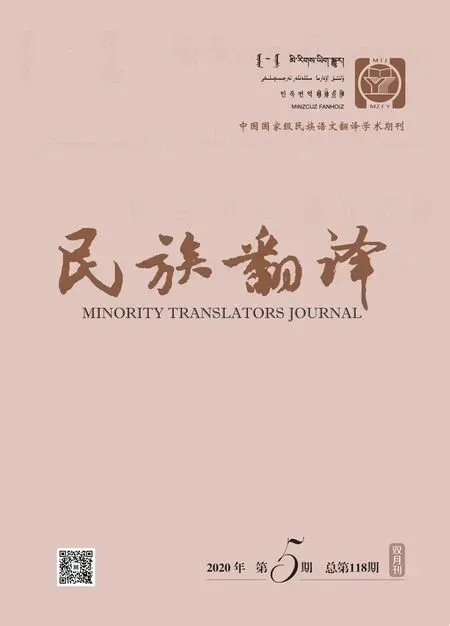诗性智慧与深度翻译*
——史诗《格萨尔》科恩曼英译本探赜
⊙ 臧学运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引言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藏族活形态史诗《格萨尔》的千年传唱,头顶着“藏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世界第一长诗”等各项桂冠,跨民族、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地从青藏高原经中亚大陆走向世界。如果说1771年俄国人帕拉斯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是史诗《格萨尔》在国外的首次译介[1],到今年《格萨尔》的域外翻译传播已达250年之久,已被翻译成了俄、德、法、日、英等十几种语言文字,流布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史诗英译最为耀眼。这与英语作为重要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和其世界通用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随着《格萨尔》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史诗英译从零星状态达到了燎原之势。
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从1905年到2020年,《格萨尔》的英译本已经多达15本,期间历经南亚印度、欧陆英伦、北美大陆、中华本土,最后到21世纪全球化视野下多点开花、竞相绽放。通过梳理史诗的英译发展史,笔者对《格萨尔》的英译行为进行全景图谱考察,经对比发现史诗的英译本大都是“变了味”的翻译,主要呈现了译者对《格萨尔》的编译、述译、节译与创译,而藏英对照、以诗译诗的传统翻译却是凤毛麟角。史诗的第一个英译本是德国摩拉维亚的传教士——A.H.弗兰克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的《格萨尔传奇:一个下拉达克版本》(ALowerLadakhiVersionofKesarSaga)。此译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英译本,因为书中关于史诗的说唱内容仍然是藏文原文,并没有翻译成英文,仅包含英文内容摘要、英文注释、英文词汇以及英文附录;被西方译者奉为圭臬的法国女作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儿译本《岭·格萨尔王的超人一生》(TheSuperhumanLifeofGesarofLing)是章回体的编译本;在北美大陆出现的第一个英译本是艾达·泽特琳的《格斯尔可汗:一个西藏传说》(GessarKhan:ALegendofTibet),这是一个故事述译本,从译本封面上的“TOLD BY IDA ZEITLIN”而不是“TANSLATED BY IDA ZEITLIN”就可以看出;美国道格拉斯·潘尼克的《格萨尔王战歌》(TheWarriorSongofKingGesar)是一个面向舞台、歌剧化的节译本;由中国本土译者王国振主译的《格萨尔王》(KingGesar)是一个汉语中介的转译本。除此之外,史诗的英译本还有儿童读物本、动漫绘制本、小说本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现代译论认为,翻译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改造、变形或再创造。”[2]从这一角度可以把史诗《格萨尔》的编译、述译、节译、创译等版本形式归属于英译系列。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对史诗《格萨尔》生命在海外的延伸具有积极作用。正如弋睿仙所说,“只有作品被成功译介进入新的环境中,才有可能滋生新的读者群体,并培育接受环境。”[3]这些非传统的史诗译介本正是发挥了如此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满足了读者对藏族文化的理解,培育了部分史诗爱好者。她进而又指出“待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后,呼唤忠实于原作内容风格展现原作精神及其代表的民族文化的全译本的时机也将到来。”[3]
在广大读者的期待中,由罗宾·科恩曼、喇嘛召南、桑杰·康卓联合翻译的《史诗岭·格萨尔:神奇诞生、少年时期与加冕称王》(The Epic of Gesar of Ling:Gesar’s Magical Birth,Early Years and Coronation as King)(以下简称“科恩曼英译本”)于2011年由美国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s)正式出版,并迅速走进了大众视野。它在后现代时期人们普遍崇尚“快餐文化”“碎片式”的浅阅读时代,以史诗的藏文源本为底本、“以诗译诗”为风格特征、原汁原味“大块头”的方式呈现,不能不引起学界的关注。目前已有学者对《格萨尔》的相关英译本展开了研究,比如,对艾达·泽特琳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4]、达维·妮儿英译本的民族志阐释[5]、道格拉斯英译本的跨文化传播[6]、葛浩文英译本的特点[7]等译本展开了相关论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对科恩曼英译本仅在个别文章中作为举例对象有所提及[8],并未展开译本本体研究。科恩曼英译本出版算起来已经接近十年了,作为当前唯一一部藏英对照的学术译本,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为何至今没有走进学者的视野而成为研究对象?译者在选择藏文源本的考量是什么?译者采取的诗化风格之动机是什么?译本有怎样的翻译特色?《格萨尔》英译发展趋势有怎样的变化?本文运用文献研究与考证、文本细读与比较的翻译学、历史学研究方法,首次对《格萨尔》的科恩曼英译本展开全景研究,分析源本传承与价值,总结译本特色,结合当下民族志的深厚翻译理论(Thick Translation)、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打造《格萨尔》史诗英译的理想范本。这不仅为藏族活态史诗《格萨尔》的英译指明发展方向,助力当前方兴未艾的格萨尔学研究,还为我国丰富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对外传播提供理论范式,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可资借鉴的途径。
一、合作翻译之典范:译人译事
史诗不仅是活形态的,具有异文传承的特点,又是融藏族社会、文化、宗教于一体的集大成者,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科恩曼译本另辟蹊径,走上了合作翻译之路,由罗宾·科恩曼、喇嘛召南、桑杰康卓三人主译,简·霍斯协助翻译。
罗宾·科恩曼(1947—2007)出生在美国的新奥尔良,本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是邱阳创巴仁波切的得意门生,也是由创巴仁波切在美国创建的第一个闭关修行中心的心灵导师。同时他还参与创办了那烂陀藏英翻译中心,有大量的藏传佛教经典著作译自他的笔下。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那诺巴大学教书时,他重回校园读书,最终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早在1991年,在法国格萨尔学专家石泰安(R.A.Stein)的启发下,科恩曼就开始了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其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岭·格萨尔史诗》的比较研究。为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科恩曼就着手于史诗的第一部,即《格萨尔的神奇诞生》的翻译,并成为论文的一部分。1993年,他获得了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为期三年的研究员职位,从此开启了学术生涯,用尽毕生精力投入到了他为之追求的格萨尔翻译事业。1995年,他在哈利法克斯遇到桑杰康卓女士,就开始了包括喇嘛召南在内的三人合作翻译,时间长达6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还兼任藏语教师,其一位名叫简·霍斯的学生对三人的史诗翻译提供了较大帮助。
译本的另外一名译者喇嘛召南于1964年出生在史诗盛行之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他14岁时就出家为僧,跟随寺院堪布芒塞尔修习藏传佛教之法。1990年,喇嘛召南离开藏区,开启了自己的朝圣之旅,先后参观访问了印度、尼泊尔等地,后来只身来到美国弘扬佛法。他从小就聆听艺人的《格萨尔》演唱,对史诗耳濡目染,是他一生的兴趣所在。1999年,他和史诗的第三位译者桑杰康卓女士在美国创建了毗卢遮那之光翻译中心,开始从事藏传佛教经典之作的英译工作。
桑杰康卓女士早在1971年就旅居印度,修习藏传佛教。在她到达达兰萨拉后不久,藏族作品与档案图书馆就面向西方人士开放了。在接下来的7年中,她一边在印度、尼泊尔等地旅游,一边广泛地学习藏文佛法,不仅深谙教义并能熟练进行藏英口译。1977年,她遇到了嘉初仁波切,开始与其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地合作创建一些佛教修行中心,并亲自为修行人员担任藏英口译员。
科恩曼、桑杰康卓的英语背景及其藏传佛教徒的身份,喇嘛召南的藏语底色及其多年旅居美国的经历,加之三人都成立了藏英翻译中心,常年从事藏族文化、宗教、文学作品的翻译,经验丰富,以上种种使得两种语言与文化在他们的笔尖之下游刃有余,似乎三人进行史诗《格萨尔》的英译是天作之合。事实也的确如此,历史上首次以藏语源本为底本进行史诗英译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三人密切合作翻译《格萨尔》主要集中在1994-2000年的6年间。在翻译时,首先要大声地朗读藏语,字斟句酌,生怕误漏信息;同时整个翻译过程全程用摄像机进行录制,其态度严谨,可见一斑。因为藏文源本中有很多果洛方言词语,出生于此地的喇嘛召南的作用就发挥到极致了。从2000年开始,科恩曼开始着手译本的编辑,但直至2007年病逝,译本未能面世。出于对完成这一项目的内心渴望以及为完成科恩曼的遗愿,喇嘛召南、桑杰康卓及上文提到的简·霍斯集合在一起审阅并重新翻译了史诗前三部中的大部分译文。史诗《格萨尔》科恩曼英译本终于在2011年正式出版,历经20年,众望所归。之后,喇嘛召南等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史诗《格萨尔》第四部的翻译了。这次他们选取的是史诗主人公格萨尔北方降魔之部,我们期待其能尽快进入公众视野。
二、大器晚成之经典:译本爬梳
从1905年第一个英译本出版算起,100多年后,科恩曼英译本才于2011年在美国波士顿首次出版,后经2013年、2015年再版(硬皮精装、共656页)可谓之大器晚成。译本包含了序言(Forward)、前言(Preface)、历史回顾(Historical Introduction)、译者导言(Translator’s Introduction)、致谢(Acknowledgments)、正文三部(Three Volumes)、注释(Notes)、术语表(Glossary of terms)、人名表(Glossary of names)、参考文献(Bibliography)等10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翻译文本。除正文外,还有大量的副文本(Paratext),这些“零部件”是译著不可缺少的部分,体现了译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活态史诗翻译的艰难、译本的“厚重”及其巨大文化价值吸引了土登尼玛(阿拉桑嘎仁波切)、萨姜米庞仁波切分别为其作序,皆中肯地评价了史诗英译的成就,表达了对社会的关切,即:我们的世界正经历着仁心缺失、气候变化、灾难频出的大环境,此时更加需要慈悲、智慧、超能的格萨尔,其唤醒人心向善的精神与能量,能够面对世上混杂与迷茫。序言符合两位的僧伽身份,也使译本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佛教氛围。正如土登尼玛在序言中引用的一句话所说的那样,“Except for the enemies of the Buddha’s doctrine and those who bring harm to sentient beings,I,Gesar,have no enemies.”[9]x(格萨尔征战四方的敌人都是有悖于佛教教义之徒,除此之外,再无敌人。)在前言中,译者交代了译本底本的选择、译本风格的取舍、文本编辑体例的说明等,以期为读者奉上质量上乘的英文译本,通过对细微差异的处理,体验史诗所承载的文化魅力。
科恩曼译本的巧妙之处在于有两处“导言”,分别是大卫·夏皮罗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译者自己撰写的Translator’s Introduction。两处导言内容相互补充,联手为读者奉献了能够深刻理解史诗内涵与主题的阐释性解读。夏皮罗先生的导言堪称一篇学术论文,首先把《格萨尔》置身于世界史诗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指出史诗具备的“九大文学特征”,分析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能够引发民众共鸣的情感体验;其次把《格萨尔》置身于历史语境中,考察史诗产生的文化土壤之“佛苯之争”,从而把史诗完全带入到佛教氛围,而格萨尔则成为佛国“代言人”,拯救并开悟处于“魔”统治下的人民,带领他们走向“香巴拉”。然而在这一部分中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夏皮罗对所谓“看不见的世界”(Invisible World)、“转世化身”(Reincarnation)等进行细致描述,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增加史诗的可读性,吸引读者,但这更反映出一个佛教徒对史诗的解读,阅读时需要读者加以甄别。而在主要由喇嘛召南执笔的“译者导言”部分,译者表达了史诗翻译成英语会对西方世界有所贡献的信心,正如译者指出“From the outset of this project, I have been fully confident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stories of the enlightened,compassionate warrior Gesar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will contribute to a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basic human goodness and dignity.”[9]xxiii作为虔诚的佛教徒,译者对当代社会中失去本真的现象给予关照,希望能够唤醒人们的向善之心,宗教的说理倾向昭然若揭。这与三位译者佛教徒身份相吻合,也与藏传佛教中的普世佛理相契合。“译者导言”篇幅较长,共35页,对史诗的文体风格、主题宗旨、世袭血统进行了简单概括;对史诗中的主要人物,如格萨尔、生身父母、皇后王妃、兄弟大臣、叔父总管等8人进行了详细刻画,特别指出史诗主人公格萨尔是佛国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手菩萨)在人世间的“代言人”,融智慧、慈悲与力量于一身;同时还是莲花生大师在尘世间的化身,以肉身降临人间,担负着拯救人们脱离苦海的使命。导言中还有大量的篇幅以部本章节为线索梳理概括了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结构严谨、语言简单,不仅为不熟悉史诗的读者提供了较好的导言作用,还解决了可能会因史诗译本重在说唱而忽略故事情节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两处导言运用人类学中经常采用的深度描写(Thick Depiction)手法,呈现出研究性特点,具有浓郁的学术气息,是整个译本的有益补充。
在作者致谢(Acknowledgments)部分中,因译本的主要译者罗宾·科恩曼在其出版之前病逝,因此译者用词恳切,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科恩曼惋惜与怀念,对科恩曼生前的亲朋好友、本尊上师、出版编辑进行了诚恳致谢,指出没有科恩曼对史诗格萨尔的执念、本真与追求,就不可能有20年后译本的诞生。译者特别感谢了邱阳创巴仁波切。作为科恩曼的依止上师,正是创巴仁波切开启了他的智慧法门,得益于正确指导与背后力量的源泉,译本才能在二十年后付梓出版。译者还特别感谢了法国学者石泰安,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与生前所给予的启发,科恩曼在他的基础上以德格林葱三部木刻本中第一部为研究对象,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与译文初稿。这不仅说明了译本源本的来源,还说明了西方藏学家学术研究的一脉相承,本译本中或多或少地也参考了石泰安的法译本。
正文以部本(Volumes)的形式,涵盖了德格林葱三部木刻本的主干内容,与《天界卜筮》《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的主要情节相对应。每一部包含不同数目的章节,对史诗的前三部进行了源本对照式的翻译。译者在翻译每一部本的题目时,采取了归化策略,分别译为TheEventsleadingtoGesar’sIncarnationintheLandofLing,Gesar’sBirthandChildhoodintheLandofLing,GesarWinstheHorseRaceandBecomestheKingofLing。这样做的目的正如译者所言“to change the title of the volumes to make the English more descriptive of the narrative.”[9]xiii(改变部本题目是为了使得译文在叙事中更具描述力。——笔者译)译文中的另一个特色是在每一章节之前,译者都会用诗体形式的四句话对本章出现的主要内容进行“预示”(Foreshadow),高度凝练,提纲挈领,引人入胜。
译本文末出现了67页注释(Notes)、33页术语表(Glossary of Terms)、12页人名表(Glossary of Names)以及16个参考文献。这些副文本对译本同样重要,尤其是对不甚了解藏族文化风俗习惯的西方人士来说,不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更显示出译作的学术风范与严谨。在160个注释中,关于藏传佛教的相关阐释却是极少,这是译者的选择,认为藏传佛教术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化中,对西方读者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以至于译者认为在史诗的翻译中也就无须赘述了。
整个译本装订精致,内容翔实,目录齐全,错落有致,布局合理,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是一个融文学翻译、学术研究于一体的译文文本。译本中体现的翻译策略与藏传佛教在北美大陆的广泛传播与影响是分不开的;同时,作为佛教徒的三位译者,借史诗翻译进行宗教说理的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诗性智慧之体现:译本特色
科恩曼译本由三人合作翻译,历经20年才得以完成。译者的学术素养、严谨态度、旅居经历、佛教徒本质保证了译本的质量与特色,10年内出版三次,足以说明译本在英语世界受到的欢迎与重视。译本语言地道自然,文笔清新、华丽细腻,虽然有浓厚的佛教文学色彩,但又不失民间文学特点和史诗风格。通过文本细读与译本比较,可以用“源本对照,历史首次;以诗译诗,韵律再现;深度翻译,文化补偿”等几个鲜明特点来概括。
(一)源本对照,历史首次
如上文所述,15个英译本大都属于编译、节译、创译、转译,虽然属于广义上的翻译,且对于延长史诗生命的域外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创造性的叛逆”毕竟和传统的源本对照翻译相去甚远,就像我们不能把阿来创作的汉语小说《格萨尔王》说成是作者对藏语本史诗《格萨尔》的翻译一样。这种翻译方式想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史诗味道,恐怕还做不到。敏锐的嗅觉、学术的追求让科恩曼牢牢抓住了时间节点与空间维度上的契机,开启了历史上首次对《格萨尔》进行藏语源本可对照的、回归传统的英译。
《格萨尔》作为活态史诗,传唱千年,语境变迁,形成了口传、文本、电子等多种介质同时并存的现象,加之互文性,导致异文本的传承繁多。到底选择何种文本作为翻译的底本才能更好地体现史诗的本来面貌呢?科恩曼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据扎西东珠考证,“1946—1949年,法国巴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石泰安(R.A.Stein)教授受法国远东学院派遣来中国考察。期间,他通过王光壁先生从康区什拉布手中获得《天岭》《诞生》《赛马》三部林葱土司木刻本,然后他以拉丁文转写藏文成书,再逐字逐句翻译,与1956年在巴黎出版了《岭地喇嘛教版藏族〈格萨尔王传〉译本》。”[10]林葱木刻本的法文翻译在西方引起了较大的轰动,科恩曼受其影响也选择了以德格林葱三部木刻本(Woodblock Carved)为底本作为对照进行英译。事实上,根据笔者通过电话采访兰却加教授(《格萨尔文库》藏文通稿副主编)得知,1996年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文库》第一卷第一册《英雄成长》中的《天界篇》《诞生篇》和《赛马篇》也是以林葱木刻本为蓝本的(这一点在《文库》前言、后记中没有提及)。显然国内外重要的学术译本都不约而同地参照了德格林葱木刻本,这与木刻本是早期史诗的主要载体是分不开的,它更能体现史诗的原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机缘巧合”。据译本《前言》和《导言》介绍,科恩曼译本参照的是林葱木刻本的印刷体文本。而这个藏文印刷本首先由居·米庞(1846—1912)的弟子居麦土登嘉木样扎巴(Gyurmed Thubten Jamyang Dragpa)编撰,后来又在土登尼玛(阿拉桑嘎仁波切:本英译本序言作者之一)及其他高僧的指导下进行了整理与编辑。科恩曼的依止上师邱阳创巴仁波切自称是史诗岭国穆布董(Mukpo)氏族血统后代,他的儿子萨姜米庞仁波切(本译本的另外一名序言作者)号称居·米庞的转世化身。在上师的鼓励下,科恩曼从1991年就开始了以藏文源本为蓝本的史诗《格萨尔》英译工作,这在所有的英译本中尚属首次,开启了历史先河,成为敢于涉足庄严史诗英译的先行者,具有开创意义。
(二)以诗译诗,韵律再现
史诗,从体裁上来说是民间长篇叙事诗,用诗歌的形式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难、抵御外侮的斗争及其英雄事迹。”[11]史诗《格萨尔》就是这样一部散韵结合、诗体为主、说唱交替的“歌诗”。如何将原作中的文化性、民族性给予关照,同时把握史诗的文学风格与艺术形式,避免述、编、创的手法,是每一个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众多的翻译论中,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说”,抛开“宁信而不顺”或是“宁顺而不信”的提法,都指向了“雅”。窃以为“雅”就是要求译文的风格要向原作的艺术审美靠拢。因此在翻译中,根据史诗的自身体裁与内容的特殊要求,译文应具有诗的特征,诗的审美,诗化历史,再现诗性智慧。所以《格萨尔》翻译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运用符合原著风格的文学语言,准确地再现原著的艺术形象,忠实地传达原著的思想内容。”[12]科恩曼译者就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在底本确定后开始了“以诗译诗,韵律再现”的《格萨尔》英译。译本《前言》中提到“We have taken great care to ensure that this translation is faithful in form and meaning to the original Tibetan.”[9]xiii,译者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在形式和内容上做到对藏文源本的“雅”与“信”。在《格萨尔》的众多英译本中,极少有译者敢于尝试诗化翻译,即使有,也是数量极少或者干脆将其转换成歌剧的形式进行。史诗《格萨尔》中集中呈现了藏族诗歌格律的各种形式,比如年阿体、格言体、鲁体、多段回环等,使得史诗极富音乐性和自然韵律,节奏鲜明、和谐悠扬。鉴于藏英两种语言分属完全不同的语系,要想充分体现史诗的音韵之美,是很难的。为此,科恩曼译本采取了“折中”的翻译方法。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英语中常常使用的自由体诗歌的形式,遵循能押韵时就押韵,不能押韵时也不做强求的原则,要求不能因韵而丧失意义。尽管如此,译文读起来也没有“翻译腔”,就像读英文诗歌一样,朗朗上口。在自由体的诗歌翻译中,译者尽量做到了行文简单,内容不走样,形式贴原文,为史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三)深度翻译,文化补偿
作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博物馆”,《格萨尔》具有藏民族文化特质,是民间信仰文化的载体,成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如何描绘一幅高原藏民族精神面貌的蓝图,让他者走进藏族人的心灵世界,是每个译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尽量保证艺术审美的前提下,译者应该运用巧妙的方法对藏民族特有文化现象,比如宗教术语、民俗事项、生态文化等,进行恰当的阐释,既要使译文不失藏族特色,又要帮助译入语读者把握史诗内蕴。科恩曼英译本中,译者通过使用译文导读、脚注夹注、文末注释等多种翻译方式进行文化阐释,达到了准确传递原作中的文化因素,并向世界人民展示藏族文化全貌的目的。例如:
The divine arrow that knows human language
Is the thick glottal click of the dralas.[9]508
何为“thick glottal click of the dralas”?译者没有对dralas做出单独的解释,因为即使把其解释为“War god”,西方人也不能理解什么是“战神”,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空缺现象;而是将其在文末注释为“This is a palatal click,quite loud,that Gologs make to indicate determination.It is made after a good meal,or when you bravely determine to do something.Or when you are angry and about to fight.”[9]570原来这是果洛人表达“毅然决定”时从喉咙处发出的一种响声,可能是饱餐一顿后,或者是下定决心做某事的时候,或者是表达生气要决一死战之时,都会发出的一种声门上腭音。在注释中,还引用了喇嘛召南的进一步解释,“这种世俗的声音在寺院里是被禁止的。如果年轻僧人不经意间发出这种声音,会受到惩罚,因为这似乎具有骂人的意味。”[9]570类似的文化阐释有160处,再加上文中夹注、底端脚注,形式不一,数不胜数。另外,译本导言中,译者还单列一节,详细地描述了史诗中的“神与魔”,再加上文末的“术语表”,读者对于来自异域的文化就不会那么陌生了。通过这些方式,使得陌生文化语境化,特别是通过提供言语行为的有关时间、地点、民族文化和心理因素等搭建阐释空间,得以圆满解决。事实上,这种通过导言、文末附录、注释等多种副文本的方式再现原作意义的做法是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惯用手法。
深度翻译或厚翻译,也称为厚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中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理论对翻译所具有的理解性和阐释性的描述。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将其定义为“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现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13]显然,深度翻译追求的是把语言的转换置于语境中,是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化空缺或者文化欠额现象进行文化补偿的一种策略。科恩曼英译本将这种深度描写运用到了极致,重构历史语境,还原社会文化,展示藏族全貌,帮助译入语读者掌握文化本真。
结语
在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上,由于一直缺乏懂民族语言与外语的双语人才,不得已采取了经汉语中介转译为外语的“曲线救国”之计。虽然在特定时期内对民族文化“走出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民族语言在译为汉语时就已经经过了文化过滤,然后再经汉语转译外语,从而引起“文化走样”,就可想而知了。根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本德尔教授所提出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译介最理想的方式为“直接从语言A到语言B的翻译”[14]来看,这里的A就是藏语,而B就是英语,中间没有其他任何介质,再借助于民族志的深度描写,呈现文本语境与文化因素,从而使得翻译理想化。可以说,在史诗《格萨尔》的百年英译历程中,只有科恩曼译本采取了融“源本对照、以诗译诗、深度翻译”于一体的方式,多个“历史首次”,使得译本走向了史诗英译巅峰。当然,作为口传史诗,《格萨尔》的最大特点是“活态性”,是说唱艺人通过知识储备、特定程式的现场“表演”。如何把表演过程展示给读者成为当下译者的重要考量。
文本化的译本使得史诗的口头表演特征消失殆尽,导致了只有通过表演才能展示的史诗特定语境下的文化内涵不能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读者。而如何体现艺人的表演等“活态”特征,科恩曼译本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期待通过借鉴当代美国民俗学与人类学中的“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寻找两者的理论共通点,从而促进我们重新认识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是“如何从认识论上将其对外翻译仅仅看作是不同文本之间的语言翻译上升扩大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翻译,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对外翻译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向度。”[15]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把国外史诗英译的“接力棒”重新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并结合我国2018年实施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从理论到实践,打造《格萨尔》史诗英译的理想范本,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借鉴,从而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好声音”。这对推动中国文化繁荣兴盛,推进世界多元文化合作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必将成为格萨尔学研究历程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