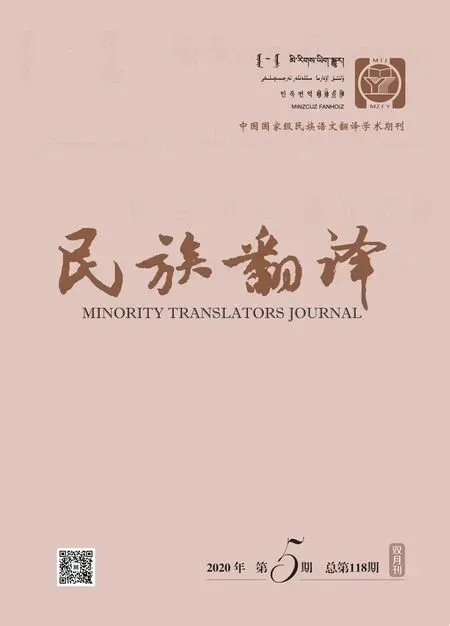彝文经籍长诗汉译文本《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一瞥
⊙ 罗 曲 余 华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文史馆,四川 成都 610041;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北京 100089)
由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翻译和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从2006年开始出版第一辑,至2018年共出版了10辑,每一辑中包括若干卷,有的“卷”还包括若干章节。
从篇章内容看,《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主要选自操彝族北部方言的四川彝区毕摩经典,在选编及其呈现方面,对比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至2012年陆续出版的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以古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的“四行对照”形式,《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突出“辑”的特点:所载文本有的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规范彝文和汉语文译文文本对照的方式呈现,有的则是直接对过去汉译本的辑用。
一、内容概述
目前出版的10辑《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译丛”)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传统文学作品
操彝语北部方言的四川彝族,其传统文学主要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有的口头传承文学作品记录于毕摩经书之中,具有“写本”的特点。在已经出版的10辑《中国彝文典籍译丛》中,第一辑和第二辑主要是这类“写本”作品,其篇目有刊载于第一辑的第一卷《勒俄特衣》、第二卷《物种的起源》、第三卷《玛牧特衣》、第四卷《彝族尔比选》,刊载于第二辑的有第五卷《妈妈的女儿》、第六卷《幺表妹》、第七卷《甘嫫阿妞》、第八卷《姿子妮乍》、第九卷《彝族克智选》、第十卷《彝族过年歌》、第十一卷《彝族挽歌选》。
彝族传统文学的传播在历史上有两条渠道,一是民间口头渠道,二是古彝文写本渠道。历史上四川彝族中能运用彝文者,是祭司毕摩群体和个别有条件学习运用彝文者(如土司土目阶层中的部分人士),他们是古彝文写本渠道的传播主体。“译丛”第一辑和第二辑里的传统文学作品也是如此,由他们通过相关民俗文化活动或其他方式,使“定格”写录的作品得以传播。
除了以上所例示的文学作品题名外,还有的文学作品融会于毕摩祭祀经文之中,如“译丛”第四辑第二卷《祭祀缘由经》中的《祭祖的缘由》一章,载有《石尔俄特》传说;“译丛”第四辑第三卷中的《献祭驮马经》中,关于马的起源以及不同马的品种的描述是文学作品,其内容与第一辑中第二卷中《骏马的起源》雷同。
(二)祭神祈福
“译丛”第三辑至第十辑,其内容都是关于彝族先民的精神信仰及其对生活的追求,从多个角度表现了彝族先民祈求平安福运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相关的俗信文化。
1.灵物崇拜下的愿望
“译丛”中的某些经文,标题题名或是祭神的,或是驱鬼的,或是祭魂招魂的,其内容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祈愿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比如“译丛”第三辑第二卷《请魂祭神经》,据编译者前言称:“该经主要是用于祭祀家宅神仪式或举行防护礼仪式。旨在招请和安抚主人的家宅神灵,让它们忠于职守,各司其职,护佑整个家庭,让各家庭成员和谐共处、事业兴旺、安居乐业、健康长寿。”[1]21-22该卷的《祭祀佑神经》中说:“恩木兹吉禄,乃是众贤人;恩木莫吉禄,乃是众群星……吉禄莫反叛,吉禄莫背主,祭之降临主人家。”[1]23-24在四川彝族传统文化观念中,“吉禄”是护佑神之意,其物质载体可是任何一种物质,可意译为“吉祥神灵”,是灵物崇拜的表现。
除了反映彝族先民祭祀神灵祈求平安的愿望之外,还有请毕摩念诵相关经文,以获得长寿的愿望。这在“译丛”第三辑第二卷《请魂祭神经》中的《长寿吉禄》表现明显。
2.祈求神灵“护法”
“译丛”中的某些经文题名有“护法”一词,如第三辑第四卷《毕祖护法经》《护法快神经》等。据称《护法快神经》的使用频率很高,内容涉及彝族神话传说中的支格阿龙射日月并治理人间后,因行祭祀而使人神和谐之事,请天地、山川、河流、森林等神灵前来护法,并协助毕摩驱逐有关的死神和病魔。在这类经文里,将神灵视为是一种按自然规律翻滚旋转之物,而且速度快,所以称为“旋转快神”。从经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看,就是祈求神灵在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保佑人们平安,并赐福于人。[1]67-68类似的文本还有《纳布纳威快神》《截击快神》《鹫鹰快神》等。
(三)防病治病经
1.对疾病及生与死的认识
彝族先民在历史长河里,在其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生存食物的同时,也不断地探索如何应对自然界对其生存的影响和威胁。对人类生存威胁最大的莫过于疾病,反映彝族先民对疾病源的探索以及防病治病和表达生死观的文本,在“译丛”中相当丰富,主要分布于第三辑、第九辑、第十辑之中。如“译丛”第三辑第十卷《死因病由经》中的《死因》篇,表达了彝族先民的生死观:
自古世事难预料,秋季雷声震,巨雷震寰宇,秋雷闷沉沉。冬来雪花飘,冰雪连天际,压毁松柏枝,捣毁雁鹅巢。早春三月里,牛羊撒牧场,牧场不安全,畜命丧牧场。秋季三月里,山坡牧牛马,山坡不安全,时有坠崖命丧者。夏季三月里,沼泽牧猪群,沼泽不安全,时有命丧狼口者。自古人类栖身在世间,世间并非安全处,生生息息永循环。[1]151-152
生老病死虽然是大自然的规律,但人们对于疾病还是要积极防治的。“译丛”第三辑第十三卷《献药疗疾经》,包括《驱逐病魔》《堵塞病源》《疗疾》三部分。其中的《驱逐病魔》说:毕摩举行仪式驱逐病魔斩病根,主要是驱逐降自苍天鬼界的病菌,驱逐来自鬼界的十二类疾病。对于人的疾病,不是人本身自带而得的,而是自然界传播的,所以驱逐病魔时要将之驱逐到病魔的来源之处[1]174-178。
过去曾视这样的经文为落后“迷信”,没有对彝族先民关于疾病的认识从保健和疾病防控的视角加以审视。在现代医学视野下,尤其是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和危害的背景下,这篇关于驱逐病魔的毕摩经文蕴含的信息量很大,现在看来最为突出的,是关于疾病传染的描述,对于当下预防疾病也有其“文化力”的价值。
“译丛”第三辑第十三卷《献药疗疾经》强调“巫医并举”,在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信仰语境中多次提到药物治病。文卷在毕摩举行祭祖仪式,通过给祖先亡灵祛除疾病的语境下,表达了药物治病的理念[1]179-181。
从祭祀鬼神精怪以祈求平安吉祥到以药物治疗疾病的行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发展历程中往往表现出原始的“巫医”特性,所以在古彝文经典中,有关寻找药物治病的内容往往融汇于原始宗教信仰文化很浓厚的祭词类经文中。
2.对几种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认识
痢疾在过去的凉山彝区被视为最为恐怖的疾病之一,有一句咒骂人的话就是“你得了痢疾了吧”。“译丛”第三辑第十五卷中所载,在祭祖送灵仪式上也要念诵的《痢疾起源经》,其内容反映了彝族先民对痢疾的认识,其中的《序经》描述了痢疾病魔的严重性和毕摩念经咒痢疾病魔鬼的浩大声势。紧接《序经》后的《痢鬼的来源》,以先民当时的认识水平,在其观念意识里塑造了“痢疾鬼”这个角色,认为痢疾由三种食人魔怪带到人间。虽然字里行间仍充斥着万物有灵论,把痢疾视为鬼灵精怪,但从认识论的视角,这里的“带”结合上下文可视为是一种“传播”或“传染”,且将痢疾作了分类,反映了彝族先民对痢疾的种类有所认识,且对其传染性也有所了解。关于痢疾的预防,“译丛”第三辑第十六卷《防痢经》的记述也较详细。
“译丛”中关于防治痢疾伤寒疾病的内容,还见于第九辑第九卷《防痢卸伤寒》。该经主要用于痢疾伤寒流行时的预防仪式或送灵归祖的“尼木措毕”仪式中的葬送痢疾仪程。除此之外,还用于给因痢疾伤寒致死之人的亡灵祛秽仪式上。
麻风俗称“癞子”,在人们的心里甚至比痢疾及相关传染病还恐怖。有关防治麻风疾病的经文及其仪式活动也倍受重视。“译丛”第九辑第十卷《预防麻风经》,是了解和研究彝族传统社会里人们对麻风疾病的认知和防治的重要文献。
“译丛”第九辑第十一卷的《预防神疾怪病符咒》,内容是借助神灵防治各种疾病。第四辑第五卷《镇病魔经》,可视为是彝族先民的一种治病措施和行为。该经所载内容,是邀请毕摩的护法神和天神地祗前来并协助毕摩,驱逐病魔,并对病魔进行镇压。
传统社会里,四川彝族的婚姻除了门当户对等要素外,还有不成文的禁忌:禁与有传染病史、狐臭病、麻风病的人家通婚。这是出于彝族传统社会对这些疾病无可奈何的原因。不过人们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即借助人们信仰的神灵加以镇压消除之。如“译丛”第四辑第七卷《祛除狐臭经》,表现了彝族先民对狐臭的憎恶和预防祛除措施。
在彝族传统社会里,疯癫症、神经病、狂犬病等对人们的生活威胁也是极为严重的。对于这类疑难杂症,彝族先民用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解释,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些带有历史特别印记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渗透着鬼灵精怪的信仰,但其中仍闪烁着彝族先民探索世界的精神光芒,表现了彝族先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相关文献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如“译丛”第八辑第五卷《驱疯经》里,将疯癫疾病拟人化、神灵化并重点描述了疯癫疾病的传播及其表现形状。《疯癫起源》则对疯癫疾病的起源进行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认知:疯癫也是传播传染的。[1]149-150
“译丛”第十辑第一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所载内容,也是关于防治疾病的。
(四)灵魂崇拜经
彝族传统社会盛行万物有灵论,灵魂崇拜是其一大特色,这在人们的生活祈愿、平安求吉、孝亲敬老等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处于生病或身体不适状态时,都要从人的魂上寻找答案,并通过与人的所谓灵魂的“互动”作用,来祛病恢复健康。毕摩经文里关于招魂、拽魂之类的经文极为丰富。生病或精神状态不好时,被认为是魂被鬼怪缠住的原因,如果人死了,则认为是魂永远离开了人的躯体的原因。所以在传统日常生活中,除了为活着的病人招魂、唤魂、拽魂外,还有在逝者老人丧葬仪礼上的祭词挽歌中进行相关招魂、唤魂、拽魂。
“译丛”第一辑、第二辑为传统文学作品,但第二辑第十卷的《彝族挽歌选》,从其二级标题看,灵魂崇拜贯彻始终。第三辑第一卷为《魂路拽魂经》,是彝语“莫嘎以宪”的意译,意为“拽住走向亡魂路的活人之魂”。彝族的传统信仰中,人死后其灵魂归祖先生活之处,所以该经中所描述的“拽魂”路线,是从祖界一站一站地将游魂拽回到仪式主人家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彝族先民进入凉山时的迁徙路线,对于研究彝族的历史地理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有学者据此将之视为《指路经》的姊妹篇。
(五)丧葬祭祖中的祖灵崇拜
彝族先民的灵魂崇拜,在丧葬仪礼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译丛”中几乎每一辑都有丧葬仪礼或祭祖仪礼中所表现的灵魂崇拜。如“译丛”第三辑第十二卷的《招引亡灵经》、第十七卷的《拽灵重祭经》。
《招引亡灵经》是彝语“尼核尼果”的意译,意为“为受祭者指引亡魂”。其主要内容为通过劝导受祭者的亡灵切勿变化和躲藏,迅速前来依附于灵竹根和羊毛麻皮上,以便制作成祖灵筒(签)类祖灵替代符号加以祭供。
“译丛”第三辑第十七卷的《拽灵重祭经》,是彝语“尼木俄宪”的意译,意为“祭祖送灵,拽取亡灵”。
(六)除秽求平安经
在彝族先民观念里,污秽无时无处不存在着,而污秽的存在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导致人生病;在祭祖送灵仪式中,如果毕摩的灵签和家中神物等具有灵性的物品被污染了,就会失去灵性而致病于主人。在彝族传统社会,每个家庭每年都会在一定的时间举行去污秽的仪式。进行任何宗教仪式,去污秽仪式也是必须的。在去污秽的仪式里念诵的相关经文,统称为“祛污除秽经”。
在重视祛除污秽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对之加以预防,使之不出现或少出现,使生活环境保持一种“洁净”极为重要,这在“译丛”第三辑第十四卷《祛污除秽经》中的《防污秽》一章中有详细描述[1]186-187。
除了专门针对毕摩的祛污除秽经文外,更多是针对具体事物、具体场景的祛污除秽。这方面的经文极为丰富。如“译丛”第三辑第十四卷中用了十八章内容进行详述,此外还有第十八卷的《祓除火秽经》,第十九卷的《扫除尸秽经》等。
避灾祸、求吉祥,是人类的共同心理行为,但其表现带有民族或地域特色。载于“译丛”第四辑第一卷的《避祸躲灾经》,彝语为“茨则久则”。“茨则”意为“一对”或“一双”,“久”有“循环”“运转”“运行”“行走”等意,“则”有“躲过”“躲避”“错开”“让过”等意。该经是彝族传统社会中请毕摩进行除污祓秽仪式时使用的重要经文之一,包括《活祸的源流》《祛污除灾》两章,以彝族先民在当时的认知,描述了污秽的产生过程[2]。
(七)祭祖献祭求吉祥
彝族传统社会盛行万物有灵论,相应的仪式相当频繁。仪式的主角是祭司毕摩,相关经文里,请毕摩或请历代毕摩神灵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译丛”第四辑第二卷《祭祀缘由经》,包括《请毕摩》和《祭祖的缘由》两章。
彝族的祖先崇拜为最突出,对祭祀祖先的仪礼特别重视,表现为祭祀仪礼的规模以及祭祀仪礼中的“祭献”。载于“译丛”第四辑第三卷的《莫弥库伙》,意译为汉语即《献祭经》,对祭献内容的表现记述最为详细,经文篇幅也最长,其表现形式为优美的彝文长诗,是彝族传统社会祭祖送灵仪式上专用的经文之一,也是一部典型的祭祀长诗作品。
“译丛”中除以上所列各门类外,还有大量表现对疾病预防为主要理念的“避灾祸求吉祥经(防治置卫经)”类经文。
二、文本特点简述
“译丛”的文本源自彝族民间祭司毕摩的经书,其母语原文的文体为彝文诗体形式,节奏感强,在音律上表现出与彝语“声母多、韵母少”的语言特点相适合的押“音节”特色。这种音律特色,在译文中得到了尽可能的体现。比如第九辑:
鲁朵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斯乃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木阶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此此护毕摩,毕摩前来护主人,护卫主人此一家。[3]78
在这段译文里,保留了原文中押音节的音律特点,分别有规律地押“毕摩”“主人”“此一家”等音节。又如:
烧肉热茶一置卫,烧肉热茶来护卫;曲味酒香来置卫,曲味酒香来护卫;粮食粉面来置卫,粮食粉面来护卫。[3]149
在这段文本中,分别押“置卫”音节和“护卫”音节。①
从体量上看,篇幅都较长,所以本文称之为“经籍长诗”②。因为“译丛”各辑不是严格按内容逻辑排列的,比如防治疾病的文本,从第三辑到第十辑都有分布,所以从整体而言,可将“译丛”视为“经籍长诗辑”。从大的方面看,作为“经籍长诗辑”的“译丛”,可分为“一般文学作品”与“信仰文化经籍诗”两部分。到目前为止,“译丛”共出版了10辑,文学部分还有不少优秀之作未收入其中,如《哈一迭古》《惹底索夫》《阿苏史惹》《勒革史惹》《勒俄特依公史篇》等,以及曾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中出现过的咒语长诗《狐仙三姊妹》等。这些优秀之作,应该会出现在第10辑之后的某一“辑”或某些“辑”之中。否则,作为凉山州政府的一个翻译文化工程,就是一大遗憾。
从“译丛”所包括的“一般文学作品”与“信仰文化经籍诗”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态性”。与《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相比较,“译丛”的原生态性首先表现在反映民间俗信文化方面,完全是彝族历史上的本土自然信仰文化,未见从外输入的信仰文化内容,更未见人文宗教文化内容。在已出版的10辑“译丛”中所载的“大众文学作品”,从题材到内容到表现手法,表现出完全的彝族特色。而《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所载的《董永记》《凤凰记》《丁兰刻木》之类的翻译作品在“译丛”中未见,更未见以汉文化题材为对象的彝文创作作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化的发生发展一是取决于自然环境,二是取决于社会环境。“译丛”的这种原生态特性,一方面反映了凉山彝族历史上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交通不便,限制了与外界的往来交流。另一方面反映了凉山彝族历史上的社会,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彝族社会自身的发展特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循环系统”,从而影响到与外界文化交流。所以,在1949年前的毕摩经文中,没有见到外来文化内容。而在近年发现的毕摩经书中,则出现了彝族信仰文化中镇压病魔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龙手握手枪的插图。在凉山甘洛县,由于岭光电土司自小接触汉文化,并在外地学习时接触了新知识,当时经过他整理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衣》中,出现了“欧罗巴”之类的新内容,但是增加了此类新内容的《玛牧特衣》,肯定没有进入毕摩经书之中,因为与岭光电同时代的凉山毕摩们,没有条件接触外界的相关文化知识。
“译丛”的原生态性特点,对于研究彝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重要的参照。这种原生态性如实地展现了彝族历史上受制于自然地理及社会环境的认知特点,以及由这种认知所影响下的彝族历史上的文明发展特性。比如,在彝族传统社会,生产力落后,医药文化更为落后,一些现在看来不是很难治疗的疾病,在当时却是严重威胁人们生命的“鬼怪”,要靠祭司毕摩诵经预防和驱病鬼,以求得健康平安,突出了疾病是传染的和应预防的认知。在相关仪式上念诵的防治痢疾的长篇经文,正是反映出人们对于预防疾病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生活充满着热望,在方法上现在看来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仅从文本而言,在作品的翻译上有的地方值得斟酌,比如在祭祀祖先时对祖先称呼为“你”,作为汉语表达,用尊称“您”似乎更妥当些。另外在《祭酒还债经》译本中,有“三神主三域”一句,但是在阐述中,却出现了一神主高原、一神主宰姻亲戚、一神主宰社居地、一神主鬼域等内容,表明的是“四神主四域”,存在着形式逻辑上的“种属”不相等的情况。当然,诸如此类的情形,和“译丛”整体价值相比较,瑕不掩瑜。
注 释:
① 关于彝族传统母语诗歌音律中的“押音”或“押音节”的民族特色,本文作者在相关学术刊物分别发表了《彝族古代文论中的“押音”》《彝族古代文论“押音”的表现模式》《彝族母语传统诗歌的“音律”》《彝族母语诗歌的比兴和音律》《彝文文献长诗中的“韵律”》等研究成果。
②这里的“经”是毕摩经书之意,“籍”则有书籍、彝文古籍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