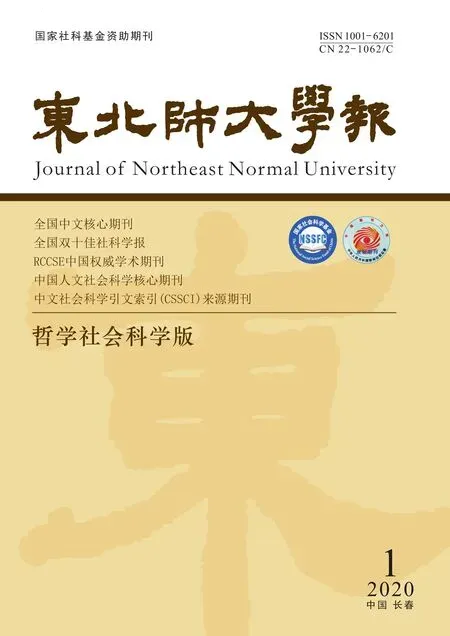古埃及那尔迈调色板的社会记忆功能
郭 子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 100006)
那尔迈调色板是19世纪末年的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经研究,它是古埃及前王朝(约公元前5300—前3000年)[1]末期的物件。调色板两面铭刻着清晰完整的浮雕,学者们对其做出了各种解释。一种解释最引人注目、广为流传,即调色板浮雕记载了那尔迈统一上下埃及、建立地域王国的丰功伟绩。根据这种解释,那尔迈调色板成为古埃及统一国家和文明形成的标志物,古埃及文明的形成时间也因此被定格在公元前3100年或公元前3000年[1-2]。
然而,那尔迈调色板没有铭文准确无误地说明这种观点。或者说,此种观点仅仅是以调色板浮雕和古埃及历史上相关浮雕肖像为基础的学术推测。恰因如此,一些学者在对那尔迈调色板浮雕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了很多不同观点。不同观点大大丰富了学界对那尔迈调色板的认识,也对调色板的史学价值提出挑战。
由于史料的局限,论争诸方在对调色板浮雕进行阐释时,越来越多地以古埃及历史时期的相关浮雕铭文和文化现象为根据,对调色板同时代和之前时代的考量则越来越少。本文希望在梳理和回顾诸家观点的基础上,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依据,对那尔迈调色板浮雕进行综合考察,进而对其内涵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探析。
一、考古环境缺失下的不同阐释
古埃及的几份王名表简单记录了最早的人王美尼斯及其继承人的事迹[3]。公元前3世纪早期,埃及本土祭司马涅托在其著作《埃及史》中,将美尼斯视作统一上下埃及的第一位人间之王,将美尼斯之前的历史分为神王朝、半神王朝、死者的精灵王朝[4]。美尼斯之前的岁月仅限于传说,确切的历史无从谈起。19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考古发现的年代早于第3王朝[5]。对这段空白的填补始于1894年末至1895年初的考古季。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W.M.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和他的同事奎贝尔(J.E.Quibell,1867—1935年)等人,在上埃及涅迦达及其附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坟墓和无数陪葬品[6]。他们继续在上埃及其他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其中1898年在希拉康坡里斯的发掘收获甚丰。这些考古发掘为古埃及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提供了一手材料。那尔迈调色板恰恰位于这些重要考古发现之列。
1898年,在上埃及希拉康坡里斯一个古代神庙遗址里,奎贝尔发现了一个“大宝藏”。大宝藏出土的文物种类很多,包括象牙雕像、象牙滚筒印章、石质权标头、燧石刀、石头器皿、象牙雕刻品、石头雕像和石碑等;文物数量也很可观,总数达2 000多件[7-8]。一般认为,这些文物是在古王国(约公元前2686—前2160年)或中王国(约公元前2055—前1650年)时期埋葬的,但大多数文物属于前王朝至早王朝(约公元前3000—前2686年)时期[9]。奎贝尔在发掘大宝藏的过程中,发现了那尔迈调色板。
奎贝尔和格林(F.W.Green,1869—1949年)限于早期考古学记录方法和考古发掘技术的限制,没有准确而详细地记录所有出土文物的具体地层和文物之间的层位关系。皮特里早在1900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7]。在1900年的考古报告中,皮特里和奎贝尔称那尔迈调色板源自大宝藏[7],且大宝藏可能是中王国时期埋葬的。格林在1902年的记录中指出,那尔迈调色板发现于大宝藏附近一米或两米远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地层年代早于埃及统一10年或20年[10]。如果格林的记录是真实的,那么调色板一定是那尔迈王本人奉献给神的纪念物。如果皮特里和奎贝尔的记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调色板在最终进入大宝藏之前经历了怎样的事情[6]。正是基于那尔迈调色板准确出土地层的混乱或缺失,学者们在对它进行深入阐释时,提出了各种不同见解。
奎贝尔无暇出版大宝藏的出土文物。1898年,皮特里简略地描述了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只有寥寥数语[11]。1900年,皮特里在奎贝尔等人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部分重要文物做注解,详细解说了那尔迈调色板。他认为调色板的主人那尔迈是前王朝的国王,他进而把那尔迈所在的时期定名为“0王朝”。皮特里认为“国王那尔迈的调色板是对美纳(Mena,即美尼斯)之前的时代最完整、最重要的记录”,“与同时代巨大燧石刀、权标头一样,是记录历史的传统工具。”[7]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皮特里对那尔迈调色板浮雕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在调色板正面,高大形象的国王左手抓着敌人的头,右手握着权标头,高高举过头顶,准备捶打敌人。在国王后面是他的贴身仆人。他前面是国王的隼鹰,握着一条穿过俘虏嘴唇的绳子。隼鹰脚下的植物是表示6000的象形文字符号,表明了俘虏的数量。俘虏下方是两个象形文字符号,读作瓦什(Washe),可能是一个单词,最好翻译为“独一无二者”或“湖之地的统治者”,或许是法尤姆的统治者。在这组符号下面是两个被杀死的敌人,他们的名字符号在各自身体上方。正面浮雕里面关于国王肌肉的刻画很值得关注。在国王围腰带上装饰着四个哈托尔女神的头,哈托尔的头也在调色板两面的最顶端刻画出来。这表明女神哈托尔在当时人们的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每一面顶部两个哈托尔头像中间是国王的名字那尔迈,名字铭刻在一个房屋或坟墓状的方框里。这些方框与后来的坟墓墓道很像。
在调色板反面,一个国王率领的胜利队伍正前往“大门”处,或许是去神庙里。他似乎是通过水路而来,因为“独一无二的荷鲁斯”站在船上。游行队伍由四个诺姆的首领组成,他们都扛着军旗,还有高级祭司塞特、国王那尔迈和国王的仆人们。他们似乎来自一个名为戴伯(deb)的建筑物。游行队伍前面是敌人的尸体,都捆绑着,头被砍掉并置于两腿之间,都有胡须。在这个场景下面是两个神秘的动物,脖子缠绕在一起,形成调色板的调色碟。每个动物的脖子上有一条绳子,分别由一个人在动物的头后侧拉着,这个拉绳子的人的头部形象与国王很像。这或许象征着对某个部落的征服。在下面的空间里,一头公牛攻入一个设防的围墙里,砖块散落在它面前;公牛在践踏敌人。这无疑是将国王与强大的公牛等同起来。城镇的名字铭刻在围墙内部[7]。皮特里的解释将那尔迈调色板与国家统一和文明起源的话题紧密结合起来了。
皮特里将这项考古发现和他关于那尔迈调色板的解释写入自己的著作《埃及史》里面[12]。那尔迈调色板和希拉康坡里斯其他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在短期内就引起了关注。美国埃及学家布列斯特德稍晚后几年也用那尔迈权标头和调色板等作为重要考古证据,阐释埃及统一国家的建立,将美尼斯与那尔迈等同起来[13]。20世纪30年代,汤普森和柴尔德等人都将那尔迈调色板反映的情况吸收进相关研究当中[14-15]。20世纪40年代,弗兰克福特在《王权与神祇》一书中,描述了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认为那尔迈可能就是美尼斯,整个浮雕表达的是上埃及国王那尔迈征服下埃及并最终统一埃及的过程[16]。20世纪50年代,柴尔德在阐述近东文明起源的时候,接受了皮特里的阐释,将那尔迈视作埃及第一位法老[17]。到20世纪60年代,皮特里关于那尔迈调色板的解释进一步被学界接受,很多学者继续将那尔迈与马涅托笔下的美尼斯等同起来,将其视作古埃及上下埃及统一王国的建立者[18-19]。20世纪70年代,霍夫曼在阐述法老之前的埃及时,详细介绍了奎贝尔和格林在希拉康坡里斯的考古发掘,对那尔迈调色板也有所阐述,基本认同皮特里的阐释[6]。今日,很多学者仍坚持这种观点[1-2]。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对皮特里的观点提出挑战。埃莫里基本认可皮特里关于那尔迈调色板反映那尔迈国王统一上下埃及的阐释,但并不认为那尔迈就是美尼斯[20]。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在基本认可皮特里关于那尔迈调色板浮雕解释的同时,对于那尔迈是否为第一个统一埃及的国王提出了质疑,认为第一个统一埃及的可能是比那尔迈早很久的蝎子王Ⅱ;那尔迈只是对埃及北部地区叛乱的征服,而非对那里的首次征服[5]。凯姆普在论及古埃及早期国家的文化基础时,也认为那尔迈调色板纪念的是国王那尔迈对北方敌人的一场胜利,调色板的浮雕包含了埃及王权的很多因素,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其表达的意识形态功能[21]。瑞德福德认为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场面体现了那尔迈时代埃及人的历史意识[22]。玛丽·怀特认为那尔迈调色板浮雕描绘的是国王那尔迈通过与埃及的敌人进行战斗,将邪恶力量挡在埃及之外,从而达到维持宇宙秩序平衡的作用[23]。21世纪初年,凯瑟瑞·A.巴尔德重点强调那尔迈调色板浮雕反映了战争在埃及统一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4]。中国学者郭丹彤认为“那尔迈调色板展示了埃及统治者对利比亚人的征服,是对相同主题的更早版本的复制”[25]。尽管这些观点对皮特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但仍坚持国王那尔迈的战争行为,没有否定调色板反映国王战争胜利的功能。

另一种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与调色板的用途有关。早在1900年,皮特里就已经注意到那尔迈调色板是国王的献祭物,而非实用物[7],因为它高达63厘米,宽约42厘米,不具有实用性[23]。布列斯特德也强调了那尔迈调色板的仪式性,认为它是在纪念那尔迈战胜三角洲地区叛乱者的胜利仪式[13]。正如前面所述,瑞德福德和凯瑟瑞·A.巴尔德等人都已经更多地弱化调色板对于埃及文明起源的决定意义。约翰·贝恩斯认为诸如那尔迈调色板这样的前王朝末期物件“不可能记录那些下令制作它们的统治者们的具体功绩,而是表达了对统治权的渴望和遵从”。也就是说,那尔迈调色板更具象征意义[27]。
1878年,清末洋务派的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唐山创办开平矿务局(开滦矿务局前身)。此后,开平矿务局周边工业和资本日益聚集壮大,使唐山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第一张股票……。短短百年,唐山开创了无数个全国历史先河,唐山也因此成为一座妇孺尽知的城市。
沿着那尔迈调色板具有象征意义这个思路前进的是大卫·欧康纳。他认为,从那尔迈调色板浮雕里面那尔迈和其随从都赤脚前行来看,这是在神庙里举行仪式。“调色板所有肖像符号记录的是一般化的仪式,而非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录。”具体而言,调色板正反两面上部的母牛形象描绘的是天,而下部描绘的是地,中间的大人物通过王冠和服装等表现出来的是太阳神拉的追随者之一或拉本身,两面肖像场面描绘的是太阳神拉或拉的追随者那尔迈代替拉神举行仪式,纪念太阳神打败敌人并实现每日早上升起的循环;调色板上的各种符号都是表达这些仪式的象征物[28]。
尽管学者们就那尔迈调色板浮雕提出了若干种学说,但总体上看无非集中在两个方面:战争和仪式。关于那尔迈调色板浮雕描述了战争的观点,大多强调调色板对国王那尔迈或那尔迈的将军进行胜利战争的记录,这实际上是主张那尔迈调色板的历史记忆功能。关于那尔迈调色板浮雕具有象征意义,甚至是描述神话仪式的观点,大多强调调色板是统治者用来向神献祭的奉献物,不具有历史记忆功能。前一类观点强调调色板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后一类观点突出调色板的献祭用途。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那尔迈调色板及其浮雕?
二、考古环境中的前王朝战争与仪式
既然前述诸家观点主要围绕战争和仪式展开,那么本文这里首先从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入手,考察那尔迈调色板及其浮雕与战争和仪式的关系。
从考古发现来看,埃及最早的暴力行为发生于距今1.2万年以前。考古学家在西沙漠的萨哈巴(Sahaba)山发现了大约距今1.2万年的一个墓地,出土了59具骨骸。其中,24具骨骸的头骨和身体骨骼具有明显的刀伤痕迹,或许是激烈暴力事件造成的[1]。暴力事件至少是古埃及史前社会逐渐复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关于前王朝时期战争的证据,直到涅迦达文化I时期(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才出现。
莫斯科普希金优秀艺术博物馆收藏了涅迦达文化I时期的一个容器。在容器上,一个人左手握弓,右手控制四只绑缚在一起的灰狗。这个人物应该是猎人。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也有一个容器,是涅伽达文化I时期的。这个容器上描绘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高大的男性,另一个是性别不明显的小人物;大人物牵引着被绑缚起来的小人物,甚至有捶打小人物的举动。布鲁塞尔博物馆也有一个铭刻着类似图案的容器。这些容器上的大人物或许是征服者,被绑缚起来的小人物或许是被征服者[1]。无论这些场景是否描述真实的战争,但肖像画显然表达了征服与被征服的含义。
到涅迦达文化Ⅱ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3200年),上埃及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长方形坟墓。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占地面积达8平方米,出土了30多件陪葬品。根据坟墓的规模、结构和随葬品等情况,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某位国王的坟墓[6,29-30]。大约公元前3400年,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的部分墙壁上装饰着彩色壁画,因此得名“画墓”[10]。绘画保存很好,色彩鲜艳,栩栩如生。一部分绘画描绘的是几艘船只和人们互相打斗的场面。这个场面很可能记载的是埃及人对外来入侵者的一次胜利反击。另一部分绘画描绘了高大形象的人物在举行祭祀活动。此外,也是值得注意的,在画面一个明显的角落位置,有一个高大形象的人物,他左手抓着跪在他面前的三个俘虏的头,右手高高举起权标,准备捶打俘虏[7]。这是埃及历史时期表达国王打击战俘的传统艺术手法。从这些断断续续的绘画场面来看,画墓的主人以国王的身份,率领军队抵抗外来入侵,获得胜利,并在战争前后举行祭祀仪式。当然,这种所谓的外来入侵或许仅仅是另一个地方国家对希拉康坡里斯地方国家的攻击。这是涅迦达文化Ⅱ时期埃及社会存在战争和仪式活动的突出事例。
到涅迦达文化Ⅲ时期(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关于狩猎、战争和仪式的浮雕越来越多。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一个名为凯拜尔·阿拉克的河马牙刀柄两面铭刻了精美浮雕。在刀柄一侧,一个西亚形象的人物正在驯狮子,下面是狩猎场面;人驯狮子的场面与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壁画上的同类形象很相似,这或许是对军事首领或国王能力的表述方式。在刀柄另一面,两行人物呈连续战斗状态,他们下面是几艘飘荡在河上的船只,船里面是战死之人[16]。刀柄上的浮雕或许描绘的是亚洲人的狩猎行为和埃及人与亚洲人的战斗。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涅迦达文化Ⅲ时期的调色板,呈盾型,雕刻了很多大型动物,其中两只鸟头动物和两只土狼形象最引人注目。这个调色板高42厘米,宽22厘米[31],应该是向神献祭用的祭品,大型动物或许是对国王的描绘,也可能是对某种神祇的刻画。调色板本身表明涅迦达文化Ⅲ时期的社会举行很多仪式。
在埃及开罗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城市调色板”残片,目前仅存三分之一,高约19厘米,宽22厘米。在调色板的一面有三行动物,还有一个表达“利比亚”的符号,所以也称“利比亚调色板”。在调色板的另一面,有七个城池,名字被书写在城池里面,城池的上方是各种动物在用鹤嘴锄攻击城池[31]。这个调色板的浮雕表达的或许是一些城市对另一些城市的进攻。大英博物馆和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了一个调色板的两个残片,属于涅迦达文化Ⅲ时期。大英博物馆残片比较大,浮雕描绘的是一只巨大的狮子正在攻击逃跑的敌人。阿什莫林博物馆残片比较小,正好是大英博物馆残片的上面部分,浮雕描绘的是两个被俘虏的人物以及他们所属的王旗。浮雕表明这是一个战场,该调色板也因此被称为“战场调色板”[31-32]。哈里斯在文章里面提到了第三块残片,上面是胜利的狼对敌人的践踏,狼也是国王的化身[33]。
那尔迈权标头浮雕比较完整。在场面的中心位置,头戴红冠的国王坐在凉亭里,后面是国王名字那尔迈;国王名字下面是一个高级祭司,名为切特;高级祭司下面是国王的仆从,手持拖鞋和水瓮;他们后面是仪仗队。凉亭上方是希拉康坡里斯的兀鹰女神,保护着国王。国王面前分为三栏:上栏一个牛圈后面有四个军旗,显然是不同诺姆的军旗,代表军事联盟;中栏的一个轿子里面坐着一个任务,其性别和身份不详,轿子后面三个人在跳舞,与古王国时期那些表达国王在塞德节期间绕墙跑动的场面很像,从而这个栏目表达的或许是国王在举行塞德节;下栏的形象和象形文字放在一起,意思是40万头公牛、142.2万头羊和12万俘虏,这或许是国王获得的战利品。在这三栏后面是一只朱露和一个羊圈[7]。权标头描绘了国王的军事联盟首领身份,也表达国王的战争胜利,更展现国王主持重要仪式。
无独有偶,蝎子王权标头和那尔迈权标头的浮雕都同时描绘了战争和仪式。实际上,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浮雕也同时描绘了战争和仪式。例如,在那尔迈调色板正面从上往下第二栏里,国王头戴红冠、手持权标而立,面前是王名那尔迈的象形文字,身后是手持拖鞋和水瓮的仆人,身前是高级祭司切特;在切特前面是四个军人,他们手持军旗,旗帜上方雕刻着胎盘、豺狼和隼鹰的形象;军旗前方是十个被斩首的人,脑袋在他们的两脚中间放着。这个场面表明国王那尔迈以下埃及国王的身份,作为军事联盟的首领,在臣子的带领下,前往观看俘虏被斩首的场面。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胜利之后的仪式,或许是在神庙里面举行,因为国王和其他人物都赤脚前行,赤脚前行是埃及祭司在神庙里举行仪式时的做法。在那尔迈调色板反面中栏,一个高大形象的国王,头戴白冠,右手紧握权标,将其高高举起,左手紧握一个跪在他面前的三角洲地区俘虏的头发,准备捶打之;国王后面是一个手持拖鞋和水瓮的仆人;国王面前是一只隼鹰将三角洲地方的俘虏带来,交给国王。这个场面是古埃及历史时期描绘国王征服并打击敌人的标准主题[32]。
不可否认,前王朝时期的这些物件上的浮雕确定无疑地表明,战争和仪式是当时社会的重要方面。这些浮雕或者描绘战争,或者展现仪式,或者同时描述战争和仪式。涅迦达文化Ⅰ时期的浮雕还仅仅表达一个方面,即战争。涅迦达文化Ⅱ时期的壁画则同时描绘了战争和仪式,只是场面比较分散。到涅迦达文化Ⅲ时期,几个权标头和调色板的浮雕比较集中地同时展现了战争和仪式。可见,这种对战争和仪式进行描绘的浮雕艺术,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完善的发展过程,那尔迈调色板是这个过程的高峰,将战争和仪式紧密而完美地结合起来。另外,前王朝这些物件上的浮雕对人物和国王的描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涅迦达文化Ⅰ时期的身份模糊,到涅迦达文化Ⅱ时期的国王身份比较确定,再到涅迦达文化Ⅲ时期的准确显明。那尔迈调色板浮雕对国王形象的描绘达到了顶峰,将上埃及和下埃及国王的身份同时描绘出来。这样,那尔迈调色板描绘的战争和仪式与国王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关于国王具有战争和仪式两种职能的完整叙事。进一步讲,那尔迈调色板浮雕既是关于战争和仪式的浮雕艺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前王朝时期战争和仪式的历时性记录,甚至是对王权发展演变结果的记载。
三、那尔迈调色板的历时性社会记忆
除了战争和仪式,那尔迈调色板及其浮雕还蕴含着更广泛的内容。
首先,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浮雕肖像和文字具有更为深层的含义。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符号都非常简化,具有古风埃及文字的写作特点,往往缺乏明确的限定符,甚至表音符与限定符很难区分开来。这就使得那尔迈调色板浮雕中的很多符号的读音和含义存在不确定性。例如,皮特里认为那尔迈是对调色板中大人物面前和调色板顶部中间两个符号的读音,一个符号是鲶鱼,读作nar;另一个符号是凿子,读作mr[7]。然而,菲尔塞维斯认为这两个符号都不应该这样解读。菲尔塞维斯认为第一个符号与埃及历史上使用的鲶鱼符号不一致,更像是对牛头形象的扭曲表述,意在传达某种震撼效果,从而应该翻译为“追赶敌人的公牛”[36]。第二个符号也不是smr(朋友)那个单词里面的mr,应该是表达“强大”之含义的单词mnkh的限定符。菲尔塞维斯便将这两个符号理解为“追赶敌人的强大公牛”。菲尔塞维斯进而对那尔迈调色板浮雕里面的62组符号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每个符号都具有文字的含义,甚至可以连缀为语句[26]。菲尔塞维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皮特里和加德纳等人传统观点的一种颠覆。2000年,T.A.H.威尔金森也对那尔迈调色板上的那尔迈之名提出了质疑,认为鲶鱼只是一种象征国王强大控制力的象征物,不具有表意符的含义,真正的发音符号是凿子[37]。关于那尔迈的名字,还有很多其他解释[38]。这充分体现了那尔迈调色板浮雕铭文语义的不确定性。
那尔迈调色板浮雕铭文语义的不确定性与古埃及文字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特点有关。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前王朝早期的公元前5千纪,上埃及的人们用各种小雕像来表达个人的社会地位,并逐渐用化妆、小珠子装饰物、大头针、木梳和手镯等物品表现人与人的关系和差别。到公元前4千纪,这种方式逐渐往下埃及传播[39]。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肖像通常被期望发挥更广泛的社会功能”[40]。从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来看,到涅迦达文化I的时候,古埃及人已经在一些器物上铭刻简化的动物和人物形象,并用某些动作表达深刻的含义,展现社会关系。公元前3400年,涅迦达文化Ⅱ时期的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的彩色壁画最能说明这点。到涅迦达文化Ⅲ时期,一些调色板和权标头上继续用动物和人物以及其他物件相结合的方式,表达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然而,到涅迦达文化Ⅲ时期,这些物件上除了有表达某种含义的图像,还出现了文字,就像城市调色板那样。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古埃及的文字也确实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产生了。在阿拜多斯乌姆卡伯墓地的U-j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125件粘土容器和碎片、160个小型骨头和象牙标签,这些物件上都有刻画符号,刻画符号上用墨水涂抹,以突显颜色。学者们认为这些符号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是古埃及最早的一批文字,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200年[41-42]。从涅迦达文化Ⅲ时期的调色板和权标头上的浮雕铭文来看,文字的比重越来越大,其表达的含义也相对早期更明确了一些。可以说,埃及文字是脱胎于具象化的实物的,经历了从具体实物到用实物形象描述社会关系的转变,即图像文字。最后,图像文字逐渐发展为能够发声表意的真正字母文字。在浮雕当中,文字既能表达相对准确的含义,又具有装饰性效果[43],从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广泛使用。当然,到那尔迈调色板雕刻时期,古埃及文字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从而浮雕仍需要大量既能写实又能传意的肖像。那尔迈调色板就是前王朝末期文字发展基础上出现的象形文字与图像描述相结合的产物[44]。这样,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是埃及前王朝文字发展的结晶,甚至是对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集中记录。
其次,那尔迈调色板浮雕中的动物形象也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在调色板的正反两面的上部,各有两个牛头。皮特里和法国学者范迪尔认为它们是女神哈托尔的形象[7,45],弗兰克福特和埃莫里等人都接受了这种观点[46,20]。菲尔塞维斯持反对意见,认为调色板两面的牛形象不太一样,而且牛角特别大,应该是水牛的牛角,与埃及历史时期女神哈托尔的化身普通母牛的形象差别较大[26]。本文更倾向于皮特里和范迪尔的观点。尽管考古工作尚未找到前王朝时期关于女神哈托尔的描绘,但这并不等于前王朝时期的古埃及人对女神哈托尔没有崇拜;调色板反面最下面的公牛的牛角也非常大,或许前王朝时期关于牛的描绘的确是以水牛为原型的,这样女神哈托尔以母水牛头部的形象出现也就正常了。如果往前追寻,我们可以在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的壁画中找到蛛丝马迹。在坟墓壁画的一个部分,有一只倾倒的、不完整的牛,这个牛的牛角就非常大,与那尔迈调色板上的牛角和牛头很像[29]。那尔迈调色板上头戴王冠的人物,身后拖着一条牛尾,这或许表明国王与牛有关,或者国王具有牛的强大力量。这头牛出现在坟墓壁画上,至少表明,这种形态的牛受到前王朝时期古埃及人重视,国王将其铭刻在坟墓壁画上必定赋予其一定含义。也就是说,那尔迈调色板顶部的四个牛头应该是古埃及人关于牛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应该是前王朝时期人们赋予哈托尔女神的古朴形象。
调色板中关于隼鹰的描绘和刻画却早在那尔迈调色板之前的几百年里就出现了。考古学家在希拉康坡里斯墓地发现了一个孔雀石制作的隼鹰雕像,是涅迦达文化Ⅱ早期的物件。学者们认为,这是目前发现的埃及最早的隼鹰雕像,是对荷鲁斯神的刻画[47]。在城市调色板上,也出现了隼鹰手持鹤嘴锄攻击其他城市的场面,这里的隼鹰应该也是荷鲁斯。那尔迈调色板上,国王面前、抓着俘虏头、脚踩六支荷花的隼鹰也应该是荷鲁斯神。这里的荷鲁斯神应该是国王的保护神。这个荷鲁斯神是前王朝时期古埃及人关于隼鹰崇拜的发展结果。考古学家不仅在那尔迈调色板中发现了写在serekh里的那尔迈名,他们还在西亚阿拉德等地发现了同样写在serekh里面的王名[48-49]。那尔迈采用荷鲁斯站在serekh上的做法确立了一种新的方式,是对之前荷鲁斯神崇拜的总结。
在调色板另一面,有两个高大的动物,它们的长脖子扭在一起,形成一个调色碟。每个动物后面都有一个男人,用绳子拉着它们。一般认为,这两个动物的形态表达的是上下埃及的统一,那两个人物是同一个人,是国王本人。这样,这个场面表达的是国王统一了上下埃及。当然,这个场面也表达了国王恢复埃及的和平和宇宙的平衡。在前王朝时期,古埃及人认为某些大型动物(例如眼镜蛇、河马等)代表的是邪恶力量,是对宇宙秩序的颠覆力量[50];国王对大型动物的征服和控制意味着国王对邪恶力量的胜利,意味着正义战胜了邪恶,是对宇宙秩序的恢复。在这个场面的下方是公牛在攻击一个城市,脚上踩着逃跑的敌人,这是对国王强大形象的描绘。这种用公牛表达国王形象的事例在前王朝的其他调色板和权标头上也有体现[51]。T.A.H.威尔金森认为,在那尔迈调色板上,把国王对动物的掌控作为展现王权的做法,是对之前各种类似主题的总结,甚至是终结,之后的历史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37]。
如此看来,那尔迈调色板中的动物形象体现了古埃及人宗教信仰的发展,也展现了古埃及人关于宇宙中正义和邪恶力量的二元对抗和平衡,更体现了古埃及人认为国王具备统一上下埃及和恢复社会秩序能力的王权观念。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那尔迈调色板上,是前王朝时期埃及人文化观念逐渐发展演变的结果。
此外,那尔迈调色板的艺术表现水平达到了一定境界,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那尔迈调色板用砂岩制作而成,打磨的非常精细。调色板浮雕中的每个细节都非常细腻,文字符号的细部、人物和动物的面部表情以及眼睛,甚至人物服装的纹路、人物用力时绷起的筋骨都清晰可见。在前王朝时期,古埃及人用来雕刻调色板的工具以更为坚硬的石头工具为主,可见生产那尔迈调色板需要非常精湛的技术和较大量的人力。这种生产技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至少从涅迦达文化I时期开始,埃及人就开始制作各种陶器、石器、象牙和骨头制品,甚至金属器、纺织品等,这些人工制品大大锻炼了埃及人的手工技艺,也不断地使社会走向复杂化[52]。学者们通过对前王朝时期墓葬的考察发现,随着墓葬的发展,国王和其他社会精英会赞助人工制品的制作,国王尤其如此。很多手工制品都是为那些拥有相当财富的社会精英制作的,诸如精美陶器、调色板和权标头这样的物件,大多是社会精英和国王使用的。据研究,制作这样的物件需要很多工匠长时间劳动,从而当时有些工匠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制作。至少到涅迦达文化Ⅱ时期,专业化的工匠已经从事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使社会进一步向着复杂化发展[53]。尽管涅迦达文化Ⅱ和涅迦达文化Ⅲ时期的陶器、权标头和调色板浮雕刻画都比较精美,但那尔迈调色板上面的浮雕最为精美和细致,从而那尔迈调色板也是古埃及前王朝时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突出物件,是对前王朝时期长时间手工业发展的概括。
最后,那尔迈调色板浮雕中的很多因素体现了调色板的主旨。在调色板反面,两个长脖子的动物被认为是对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模仿,这种主题也出现在之前的凯拜尔·阿拉克刀柄、城市调色板上面。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雕刻这些物件的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37]。也有可能是埃及国王借用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传统做法。无论哪种可能性能够成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前王朝时期,尤其在公元前4千纪,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交往始终存在。考古发现证明,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埃及就与西亚的黎凡特南部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考古学家在南黎凡特发现了前王朝各个文化阶段的埃及文物和王名[54]。考古学家也在阿拜多斯的U-j墓发现了大量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文物,包括400多件从巴勒斯坦进口的坛子[1,55]。20世纪60年代,那尔迈进攻埃及北部,缺乏确凿证据[56]。到20世纪90年代,考古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考古学家在以色列纳盖夫北部考古遗址哈立夫台地发现了一个埃及人的储藏地,还发现了一个带有那尔迈serekh的陶片。这些证据表明,那尔迈为首的王室与迦南南部存在贸易关系。实际上,在以色列考古中发现的十几个铭刻着serekh的陶片或物件当中,只有这个遗址出土的那尔迈陶片的考古环境是确定而准确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陶片的材料源自埃及尼罗河,这确定无疑地表明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存在贸易关系。这也进一步证明,在那尔迈统治末期,埃及与迦南南部的贸易和管理网络更复杂,是在那尔迈完成了对下埃及和迦南南部的统治之后出现的[57]。这些考古发现可以补充那尔迈调色板本身希望表达的内涵,即那尔迈统治时期,甚至之前很久的时候,上下埃及已经统一起来[13,58-62]。也就是说,在那尔迈调色板上,国王分别佩戴着上下埃及的王冠,并且捶打下埃及俘虏,可能是表达那尔迈本人和之前一段时间里出身于上埃及的国王对下埃及三角洲地区的叛乱进行的讨伐活动。这种讨伐活动很可能是零王朝时期的常见现象,因为零王朝时期的统一国家或许并没有后来那么稳固,至少三角洲地区的政治势力还有很强张力[63]。如此看来,那尔迈调色板是对前王朝时期一个较长时段里埃及对外交往和统一上下埃及等主题的记忆性描述,旨在宣传有关王权的意识形态[64]。
通过对那尔迈调色板本身和其浮雕的细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那尔迈调色板本身体现了前王朝时期手工艺技术的发展,也表明了古埃及文字的发展,更展现了古埃及人关于王权的文化观念。当然,那尔迈调色板的核心还是在表达前王朝末期统一的埃及国家的不稳固状态。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内容都是长时段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尔迈调色板和浮雕是对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历时性社会记忆。
由于考古环境的混乱或缺失,那尔迈调色板浮雕的内容存在很多解读可能。当我们将那尔迈调色板放入前王朝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时,它便不再是单独的文物,而是对这个长时段社会发展进程的历时性记忆。它不仅是对前王朝时期战争和仪式的概念化描述和展现,还是对前王朝社会很多方面的集中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