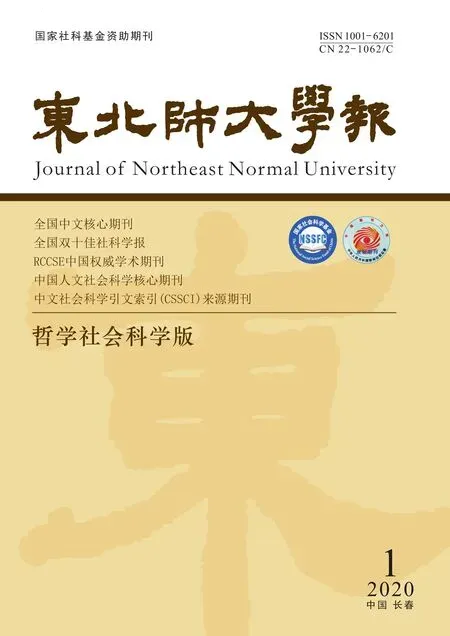《穆天子传》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
刘 伏 玲
(江西师范大学 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2)
当今学界对宋代《穆天子传》版本情况并未作完整的梳理,且对文献的考订亦存在不足,故文献梳理显得尤为重要。《穆天子传》在北宋广为流传,至南宋不多见。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言:“阅读过去的重要文学作品的人不但获得了作品的传统,而且获得了解释作品的附属传统。”[1]该书在传播过程中就形成了儒、道、释三个阐释传统[2]。阐释让《穆天子传》的正史地位遭到质疑,如苏轼就曾讶其“虚诞”。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下面从版本情况、传播方式、传播区域、接受情况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穆天子传》版本情况与传播方式
宋本《穆天子传》的序言、整理者、卷数、字数、校订记录等版本情况首次见载于宋人目录、笔记中,故这时期的版本信息是重点考察对象。
(一)版本情况
《穆天子传》主要以六卷本行于世,如王尧臣《崇文总目》、欧阳修《新唐书》、郑樵《通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骙《中兴书目》、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等,俱言“六卷”。亦有一卷本(1)高似孙《史略》云:“《穆天子传》。(一卷,《竹书》内书。李氏《邯郸书目》云‘六卷’,必是字误。)”《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13页。。字数则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第九卷所载为“八千五百一十四字”[3]。卷数与字数已是定论。在此,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宋本是否有“荀序”和“结衔五行”(2)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提及整理队伍的名单,列有结衔五行:《穆天子传》(旧钞本),前有荀勖序,序前首有结衔五行云: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勖(一行)领中书令议郎上蔡伯臣峤言部(二行)秘书主书令谴 给(三行)秘书校书中郎张宙(四行)郎中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已讫谨并第录(五行)。,二是《穆天子传》是否有别名。解决这两个问题有助于版本的考定。
1.荀序与结衔五行
宋本《穆天子传》是有“荀序”的。据赵明诚(1081—1129)《晋太公碑》言“荀勖校《穆天子传》,其《叙》亦云‘太康二年’”[4],其言“太康二年”与今本《穆天子传》“荀序”合。按赵明诚所言时人所见应是荀勖本。这是最早提到宋本有“荀序”的文献。与赵明诚同时代的姚宽(?—1162)和其后的陈骙亦持此种观点。姚宽在注释《陶潜〈读山海经〉诗》时说:“‘泛览《周王传》’,乃《周穆天子传》,荀勖校定本是也。”[5]陈骙《中兴书目》(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八《艺文》引)云:“六卷。晋太康二年,汲郡民发古冢得之,其书言穆王游行之事,侍中荀勖等校正,郭璞为之注。《序》曰:‘谨以一尺书纸写上,请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诏荀勖、和峤等以隶字写之’,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6]赵明诚《金石录》、姚宽《西溪丛语》、陈骙《中兴书目》俱未提及结衔五行以及其他整理人员。
另外,张邦基家和曾旼家亦藏有《穆天子传》。我们从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中的记载也没有找到结衔五行的线索。
曾皈(当为旼)彦和,博学之士。予先君有此书,彦和借往讐校,乃题其后,云:“晋中书监令荀公曾、和峤所上古文《穆天子传》六卷,即太康二年汲冢人准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也。”[7]99
曾旼(一写作旻),字彦和,龙溪(今福建漳州)人,事迹见《宋诗纪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应麟《玉海》。他不仅是宋代饱学之士,还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据陈骙《南宋馆阁录 续录》载曾旼之子上献图书数目:“曾旼家藏书二千六百七十八卷,未经校正。”[8]可见其家藏书之丰。曾旼借张邦基先父所藏讐校后,在张本后题字指出《穆天子传》的校者与来源。因此张本既无结衔五行又无“荀序”,否则曾旼题字实有画蛇添足之嫌。今本“荀序”署名为“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勖”,序言第一行为“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曾旼所题与“荀序”内容符合,曾旼本可能有“荀序”或者见过有“荀序”本,但有五行结衔的可能性很小。从人情往来上讲,曾旼本如有结衔五行定会誊在张邦基家本之上,或者与之交流。
张邦基提到的另一信息非常重要,他说:“今汲冢中竹书唯此书及《师春》行于世,余如《纪年》《瓒语》之类,复已亡逸。”[7]99也就是说汲冢书七十五篇流传至南宋时期只有《穆天子传》《师春》存于世。可见《穆天子传》的珍贵性。
基于此,清人所见本有结衔五行者,大概是藏书者和抄书者根据它书自行添加的。
2.篇名
在宋元文献中,此书多以《穆天子传》为名传世,亦有名《周王传》《周穆天子传》《穆王传》《周王游行记》《穆满传》者。陶潜《读山海经》在宋人中广为流传,“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句中的《周王传》指汲冢书《穆天子传》为宋人姚宽等人引用。王应麟在《玉海》第五十八卷“艺文”中将《周王传》与《穆天子传》并列作为题名,正文部分介绍的是《穆天子传》。《玉海》卷四十八又言“周穆天子传”,可见书名的传写有些随意,此篇名还出现在姚宽《西溪丛语》中。《穆王传》之称见于史容、史季温父子所作《山谷外集诗注》,云:“郭璞《山海经序》云:‘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穆王见西王母,取其玉石珍瑰之器、金膏银烛之宝。’今考之《穆王传》则云‘天子之宝,玉果璇珠烛银’。”[9]《周王游行记》则见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前已引。考其内容与《穆天子传》相合,应是同书异名。《穆满传》者出自葛胜仲《寄题长安谭损之遐观阁》“时读《穆满传》,乍观山海图”[10]。为避抄袭陶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之嫌,葛胜仲改《周王传》为《穆满传》。
宋人所言《周穆王传》者指《列子·周穆王》。如李昉《太平御览》第五百七十四卷云:“《周穆王传》曰:有偃师者,缚草作人,以五采衣之,使舞。”[11]又:李昉《太平广记》卷五十六言:“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事,具《周穆王传》。”[12]吴淑《事类赋》卷十一云:“周穆尝骇于束刍”条自注亦同。李昉《太平御览》引用书目《经史图书纲目》有《周穆王传》《穆天子传》两书。虽然《太平御览》援引比较随意,相同的一句话在不同卷数引用常有微异之处,如,在第五十三卷言:《穆天子传》曰:天子南还升于长松之坂。郭璞注曰:坂有长松。而在第九百五十三卷则云:《穆天子传》曰:天子升长松之磴(山有长松也)。又将“盛姬”之“盛”写作“成”,将“钓于流水”之“流”有时写成“氵不”,“与井公博”写成“过并公博”,“饮于枝时”为“饮于枝诗”。不过第三十八卷“钟山”下言“《穆天子传》曰:自密山以至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多怪兽奇鱼”则是《山海经》的窜文。援引随意的缺点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但凡出自《穆天子传》者皆注为《穆天子传》,凡出自《列子·周穆王》的皆言《周穆王传》,可见编撰者规范统一了书名。再者,笔者从未见过两晋南北朝的学者将两书混淆过的案例。唐朝除了张铣注《文选》时言陶潜所读“《周王传》谓《周穆王传》”外,余者概莫见也。据此笔者认为顾实所言“则晋宋以来,又似以《周穆王传》《穆天子传》二名称并行矣。《太平御览》一书,本据前代之《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纂合而成。故其引用书目,亦因仍前代,并录《周穆王传》与《穆天子传》也”[13],这一推断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宋本是有“荀序”而无“结衔五行”;多以《穆天子传》为名,曾用名为《周王传》《周穆天子传》《穆王传》《周王游行记》《穆满传》,而《周穆王传》特指《列子·周穆王》。
(二)传播方式与区域
在动乱频发的宋朝,家族相传、师门相继是此书能得以保全的最根本原因。如参与《太平御览》编撰的徐铉(916—991)藏《穆天子传》,其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征引此书9次,女婿吴淑《事类赋》引33次。另外徐铉弟子陈彭年修撰《重修广韵》《重修玉篇》时各征引2次。《崇文总目》的编写者李淑,其家藏《邯郸书目》有此书的记载,其子李德刍参与编撰《元丰九域志》时亦征引3次。馆阁大臣编写《太平御览》《崇文总目》时有交流讨论。王洙将讨论的结果记载在《王氏谈录》上,其言:“《穆天子传》,左右史之书。起居注始于汉世,乃有遗法也。故今《崇文书目》以《穆传》首记注之列。”[14]宋代馆阁大臣文名俱扬,天下仰慕者众,其诗文对时人影响甚巨。在名人光晕效应下,《穆天子传》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因此他们是此书重要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此书的传播者。另外,普通士人亦家藏此书。其家庭人员亦多在其著作中著录、征引,如福州陈祥道、陈晹两兄弟,济州巨野晁补之、晁公武两叔侄,江西宜黄黄希、黄鹤两父子。值得一提的是素以藏书丰富而著名的济州巨野晁家。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提到家藏有《穆天子传》。其叔父晁补之在《鸡肋集》2处引征《穆天子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提到曾祖父秘阁公晁仲衍为白居易“六帖”作注的一事。检“六帖”小注征引《穆天子传》13条,因此其曾祖父藏有此书是确定的。

宋代《穆天子传》传播地域主要集中在河南、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山东、江苏一带。这个数据是笔者对现有文献梳理的结果。如何考查《穆天子传》传播地域?笔者认为从宋书著录、征引、摘录(诗歌引典不计)的作者的籍贯、著作的成书时间和成书地点来考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然隋唐以来,《穆天子传》的典故流传甚广,接受者可通过《穆天子传》的文本、文人的著作、官私类书等途径接受其中的典故,这给我们带来识别上的困难。基于此,本文有效样本仅限含有《穆天子传》的作品,作品来源为《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样本为宋代大部分资料,能反映宋代时期《穆天子传》传播的大概面貌。据统计,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的文人学者对《穆天子传》有浓厚的兴趣,而南宋时期私人藏书家重视对《穆天子传》的收藏。至于《穆天子传》流布情况,从作者的籍贯和成书地点进行综合考查,据统计两宋约有96位学者著录、征引此书,他们的籍贯分布是:浙江19人、福建18人、江西11人、四川8人、山东7人、河南8人、江苏7人、湖南4人、安徽4人、河北3人、陕西2人、山西2人、籍贯不详者3人。其中前六地的学者约占74%。而结合作者的生平和刻书时间则发现,居前八的成书地点为:河南(集中在开封一带)、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江苏、安徽,其中前四位成书地点占有82%。综合两数据我们得出《穆天子传》传播主要地域为浙江、河南、江西、福建、四川、山东、江苏一带。这个推断所得的地域范围与明代《穆天子传》传播地域范围相合。
为什么宋人较关注《穆天子传》呢?张邦基曾言:“此一篇也,书虽残缺不可尽读,而其所载事物,多故志之所无者,如‘世民’之吟、‘黄泽’之谣、‘黄竹’之诗,其辞皆雅驯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异闻矣。”[7]4-5其辞可喜,其地理名、物名可博见闻,张邦基可谓道尽历代文人对《穆天子传》接受心理。然“博见闻、资政用”的君王、政客与追求美、善于想象、重情感的诗人接受此书的兴趣点是不同的,体现在对此书的“用”又有所区别,下面分而述之。
二、资政用:廷前应对、劝诱与警诫
宋代皇帝信道尊道,而经道门不遗余力地鼓吹,周穆王在南北朝已成了道教神仙,成了人间帝王求仙的典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三书多载有此事。宋代皇帝为了“博见闻、资政用”,暇余之时便会阅览,所以《穆天子传》与其衍生的故事亦被皇帝知晓是肯定的。
宋太宗赵光义勤奋好学,曾计划日读《太平御览》三卷。《太平御览》摘录了《穆天子传》,一年后,宋太宗完成他的读书计划时也即完成对《穆天子传》的接受。据范祖禹《帝学》载,太平兴国九年时,宋太宗对近臣谈及杜预《左氏正义》:“杜预通博,不当凭汲冢杂说特立疑义,使伊尹忠节惑于后人。”[16]“汲冢杂说”指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汲冢书。汲冢书流传至唐时仅存四部(3)据孔颖达《正义》云:“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春秋左传注疏》卷末附,中华书局,1989年,第671页),至宋时亦不会超过这四部范围。宋太宗认为这四部书是“杂说”,与李昉、吴淑等馆阁大臣将之归为史类的认识是不同的。
宋真宗花了两年半时间读完了《太平御览》。他信仰道教,据《宋史》载宋真宗信梦中神人之命在正殿建道场迎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并改年号为大中祥符,还在京城内大肆兴建道观。他将王钦若、杨亿等上呈的《历代君臣事迹》改名为《册府元龟》。其“册府”典出《穆天子传》,指帝王藏书的地方。因此宋真宗亦是了解《穆天子传》的。
虽然宋太宗不信汲冢书,但宋徽宗却是相信的,据汪藻(1079—1154)《上宰执乞道君还阙札子》所言,有小人以周穆王见西王母故事劝徽宗时远游。宋代的皇帝多信道教,其中宋徽宗最为突出,他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这种疯狂的行为前所未见。他还大肆兴建道教宫观,操办斋醮道场,建立道学制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书,命人修成《政和万寿道藏》。在皇帝的倡导下,此时期大量的仙话故事涌出。
《冲虚真经》即《列子》道家之书也得到了大肆宣传,一时间掩盖了《穆天子传》的风采。这为南宋时期读者将《穆天子传》与《列子·周穆王》篇混淆埋下了伏笔。
在此风气下,朝堂中的大臣自然受其影响,重视对《穆天子传》的接受。其主要表现在廷前应对、劝诱或者警诫。
大臣在与皇帝进行沟通交流,如上呈札子奏状、赋诗,会援引《穆天子传》中的典故。其中,常被援引的是被认为天子之诗的“黄竹诗”。“黄竹诗”为穆天子哀民之作,到了唐代则成了皇帝彰显德行的“喜雪篇”,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如徐铉《徐公文集·御制春雪诗序》有言:“昔者《白云》之唱,七萃驱驰;《黄竹》之诗,万人冻馁。”[17]田锡(940—1003)《咸平集》卷二十六奏状《谢赐御制雪诗》《进瑞雪歌》,王禹偁(954—1001)《中书试诏臣僚和御制雪诗序》《谢免和御制元日除夜诗表》皆有引。我们从王禹偁对宋太宗的雪诗的夸赞,“周满黄竹之咏、汉高大风之歌、唐太宗守岁之诗、陈叔达初年之作,义皆无取,事不足征”[18],可以窥见皇帝对《穆天子传》接受的兴趣所在。
朝堂应对常引《穆天子传》的潮流在学子间产生了较大反响。如王应麟中进士后,闭门发愤,为应博学宏词科借馆阁之书抄录整理成类书《玉海》,该书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类目录有《穆天子传》典故。王应麟还在《六经天文编》《困学纪闻》《通鉴地理通释》《姓氏急就篇》《诗考》《诗地理考》六书中征引《穆天子传》27次,在类书《小学绀珠》中引用2次,真可谓《穆天子传》接受者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在《玉海》卷第一百九十五“祥瑞”类下“瑞雪”条下,王应麟不仅摘录了《穆天子传》中的“黄竹诗”,还关注到唐宋以来之喜雪诗,这说明了王应麟意识到了“黄竹诗”对于宫廷答对的重要性。此外,其他宋代类书也大量摘录《穆天子传》典故,如:李昉《太平御览》引《穆天子传》97条,白居易、孔传《白孔六帖》17条;曾慥《类说》引21条;《锦绣万花谷》8条;叶庭珪《海录碎事》引22条;朱胜非《绀珠集》引15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正文引《穆天子传》7条,注释引12条。不过,前集卷五十道教门“冰桃碧藕”条,下注《穆天子传》,而实出《拾遗记》。
类书之用能“施之文为通儒,措于事为达政”[19],益处甚巨,故上至皇帝公卿大臣,下至闾里布衣蒙童小子,对类书有着旺盛的需求。而从宋代类书大量摘录《穆天子传》典故的情况来看,《穆天子传》应属于考试必背内容。除此之外,另有诗歌总集专收此书中的歌谣,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八十七收“黄泽辞”“白云谣”“穆天子谣”,这些都是朝堂应对常引典故。
也有人将其作为工具,鼓动最高统治者接受建议,捞取政治资本。汪藻《上宰执乞道君还阙札子》载有其事:
小人揣上皇享国之久,平时极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龙德为隘,引周穆王瑶池之故事以劝其游;陈肃宗西内之戒,以箝其返。挟此为奸,骎骎不已,则予我剑南一道之言,有时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20]238
靖康元年(1126),宋徽宗虽曾遭屈辱仍不改崇道热情,受小人所惑“仓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余日,未知还期。”[20]237朝野上下怨声四起。三月五日,汪藻上“宰执札”,乞迎徽宗还阙。汪藻,字彦章,德兴。南宋高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有《浮溪集》60卷。君王四游,劳民伤财,正如葛立方(1092?—1164)所云:“若周穆王者,劳民费财,从事于八荒之远,岂人君之美事乎?”[21]
宋人在廷前应对、劝诱或者警诫时能如此娴熟地运用《穆天子传》典故,说明该书的故事在宋代流传已广。
三、资文事:博见闻、笺注与启思
虽然宋人对此书接受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不外乎笺注、引典。
《穆天子传》是宋类书和诗歌总集采撷的来源,也是学者注释、考证援引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宋元时期,《穆天子传》主要以单篇形式传播。此外,此书部分内容多次被类书、诗歌总集摘引和收录。用此书来笺证经书、史书、地理书、乐书是常有之事,到宋时亦不例外。如郑樵《通志》征引5条、邢昺疏《尔雅注疏》征引7条、乐史《太平寰宇记》征引11条、陈晹《乐书》征引3条。从引证的数量来看,《穆天子传》主要被用于地理考证上。另宋字书对《穆天子传》中的难字进行了释音,如丁度《集韵》、司马光《类篇》、熊忠《古今韵会举要》等等。
以《穆天子传》注释它书的范围大大延展。唐代诗人如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等喜引《穆天子传》典故。其中李白、杜甫、韩愈备受宋人尊崇,学者纷纷为其诗作注。如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编》、宋黄希原本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宋方崧卿《韩集举正》、宋朱熹《原本韩集考异》、宋王伯大重编《别本韩文考异》、宋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宋吴正子注刘辰翁评《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则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诗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欢迎。宋人爱其诗也会为之作注,如李壁《王荆公诗注》、任渊《山谷内集诗注》、王十朋《东坡诗集注》、施元之《施注苏诗》。这三位诗人也曾引《穆天子传》中的典故。笺者为了弄清出处就不得不查找《穆天子传》,这就是他们接受此书的动机。
一般来说,学者大都严谨,所引出处皆清楚明白。不过,情况至南宋为之一变,大概因为战事频发,书籍损毁严重,如家藏《穆天子传》多毁于一旦。人们获得此书的途径较困难,再加上宋徽宗时期产生的仙话与南北朝以来的仙话传播广泛,难免出现讹误。例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一引赵彦材注“万里方看汗流血”云“《周穆王传》骅骝騄耳日驰三万里”[22],李壁注王安石诗“冰房玉节谩自好,欲御还休涕垂手”云“《穆天子传》‘西王母献素莲一房’”[23];陈仁子《牧莱脞语》“桃荐瑶池之冰”、《锦绣万花谷》“冰桃碧藕”下注皆云出自《穆天子传》。赵彦材注语出自《图画闻见志》,李壁所引出自《神仙传》,《锦绣万花谷》所引皆出自《拾遗记》。《续资治通鉴长编》编者李焘的儿子李壁注诗在宋时最有名,但亦有讹误,其他见识寡陋者可以想象。
引《穆天子传》典故代表非苏轼莫属,他不仅与朋友共同研读、讨论过《穆天子传》,还在诗中直接引用此书中的典故。
苏轼引用《穆天子传》典故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引用;二是化用。这也是文人常用的用典方式。苏轼承续了江淹、谢朓的用典传统,直接引用《白云谣》中的诗句,如《次前韵送刘景文》云:“白云在天不可呼,明月岂肯留庭隅。”[24]1822赵次公注言:“西王母为周穆王谣……盖别德之语也。”[25]苏轼最常用的引典方式还是化用,如“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中就化用了《黄泽辞》中的“其马喷沙”“其马喷玉”,其诗言“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24]1376,令人绝倒。从苏轼的用典来看,他的兴趣点还是在《穆天子传》中的瑶池宴以及其中的歌谣。弟弟苏辙《次韵子瞻病中大雪》“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26]也引用了《穆天子传》中“黄竹”典故。
《白云谣》不仅是苏轼最喜爱的歌谣,也是宋代文人所喜爱的。陆游《江西到任谢史丞相启》也化用“白云谣”,如“山川间之,日月逝矣”。吕祖谦《丘运使宗卿》有“山川间之,往问无由”。在宫廷的宴会上,大臣们席间作诗,“御题初认《白云谣》”(徐锴《蒙恩赐酒奉旨令醉进诗》);文人相聚,聊到求仙访道的事情亦云:“长哦白云谣,遐想紫阳真”(贺铸《三月二十日游南台》);怀念友人:“把酒屡陪高阁醉,挥毫几和《白云篇》。”(李纲《过罗畴老故居有感二首》)。僧人送人亦作“白云谣”,如大觉琏禅师赋“白云谣”以送远。
苏轼读《穆天子传》时接受了道教阐释,偏向于神仙之说。现以《戚氏词》为中心进一步说明。
首先,我们要清楚苏轼是读过《穆天子传》的。从外核资料看,他的学生、同僚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扬州同僚曾旼(曾彦和)藏有《穆天子传》,苏轼有机会获得。再者从内核资料看,据《侯鲭录》卷三载苏轼的仰慕者赵令畤曾对他吟诵《白云谣》。他还曾与人谈过穆天子事,事据吴曾(约1112—1184)《能改斋漫录》卷十七:
东坡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为《戚氏》。公方坐与客论穆天子事,颇讶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27]435。
但费衮《梁溪漫志》(成书于1192年)认为此词非苏轼所作。
予尝怪李端叔谓东坡在中山,歌者欲试东坡仓卒之才,于其侧歌《戚氏》,……东坡御风骑气,下笔真神仙语。此等鄙俚猥俗之词,殆是教坊倡优所为,虽东坡麾下老婢亦不作此语,而顾称誉若此,岂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误后人,不可以不辨[28]。
对此诗的怀疑不在少数,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言:“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2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亦言:“端叔时在幕府,目击必不诬。或言非坡作,岂不见此跋耶?今坡词多有刊去此篇者。”[30]观李之仪(约1035—1117)《姑溪居士集》前集卷三十八“跋戚氏”事由、当事者、作年皆交代清楚明白。
……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加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定州安抚使。开府延辟,多取其类,故之仪以门生从辟;而蜀人孙子发实相与俱,于是海陵滕兴公、温陵曾仲锡为定倅。一日,歌者辄于老人之侧作《戚氏》,意将索老人之才于仓卒,以检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颔之,邂逅方论穆天子事,颇谪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尔。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他辞,亦不容别进一语,临分曰:“足为中山一时盛事,前固莫与比,后来者未能继也。”方图刻石以表之,而谪去,宾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出此词于宁国庄。姑溪居士李之仪书[31]。
李之仪,字端叔,晚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山东)人,是苏轼的门生。从李之仪跋可知诗作于1093年左右,而跋出于1112年,时间相隔不远,其记事当为可信。又其跋亦是记“戚氏词”一事最早的文献,参考价值自然比晚出资料有价值。
那么戚氏词所用之典是否出自《穆天子传》呢?还是如陈振孙所言“公方观《山海经》即叙其事为题”呢?《山海经》中并无穆天子西见王母事,因此笔者认为:苏轼与客谈穆天子时应事而写,自非出《山海经》,而是出自《穆天子传》。
苏轼《戚氏词》中“穆满巡狩”“玄圃”“八马”“瑶池”“华筵”(瑶池宴)等典故[27]434-435出自《穆天子传》,其余出自《汉武内传》《汉武故事》《十洲记》。在苏轼笔下,瑶池宴成了仙乐袅袅、妙舞不断的神仙宴会,这说明苏轼接受了该书道教阐释,偏向于神仙之说。另一条证据是赵令畤的《侯鲭录》,此书记载他向苏轼吟诵过《白云谣》,苏轼点评曰“决非食肉人语”。“非食肉人语”当是仙人语。考赵令畤与苏轼交往密切时期为元祐六年(1091)八月至元祐七年(1092)二月,此时苏轼任颍州知府而赵令畴任颍州签判。因此赵令畤为苏轼诵诗的时间有可能就是1091年(4)《次前韵送刘景文》引用了白云谣,王水照先生认为此诗作于1091年。这个时间段与诵白云谣时间同年。参见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也就是说写戚氏词与听诵《白云谣》的时间是相近的。这个时间段苏轼接触《穆天子传》是肯定的。从这两例来看苏轼并不认为《穆天子传》是史实,这与苏轼少年学道,受到道教团体阐释影响有关。
在诗人眼里,瑶池是否真的存在已不重要,它不过是一个指向欢乐无忧的美丽仙境的符号。它不仅仅存在于苏轼的诗文中,也存在于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例如,夏竦(985—1051)在其《穆天子宴王母于瑶池赋》中就塑造了这一欢乐之宴:
穆天子以八骏西廵,宾于上真。宴瑶池之胜境,当甲子之良辰。人间之别馆、离宫,如遗敝屣;月际之珠珰、玉珮,自是嘉宾。当其碧落凝寒,余霞敛色。升绣毂于层路,会鱼轩于西极。天颜半掩,旗翻日月之光;凤髻遥分,扇侧鸾皇之翼。俄而翠华潜驻,彩袂相逢。择琼瑶之吉地,邀桃李之姱容。修城而美锦千两,供帐而轻绡万重。……[32]
此赋中所描的穆天子亦是神仙形象,他驾八骏西巡至上真女神王母家瑶池。夏竦展开丰富的想象向读者展示美不胜收的瑶池之景,“千两美锦修城、轻绡万重供帐”,一时仙乐飘飘,起舞翩翩。觥筹之间,宾主尽欢。从夏竦的诗中,我们也可看出他接受了道教的阐释。
综上所述,宋本《穆天子传》多以六卷本行世,有“荀序”,但无“结衔五行”,其主要传播区域为河南、浙江、江西、山东和江苏。而宋人接受此书的目的是“博见闻、资政用”。通过对苏轼等诗人的考察发现,宋代诗人往往继承了儒、道二种阐释,将《穆天子传》和其他衍生故事一并接受,这也是宋代《穆天子传》性质归属由正史向旁史、杂史转移的原因之一。此外,通过梳理《穆天子传》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我们发现两宋时期,人们对该书的记录出现讹误,尤其是类书类,因此,以宋代资料考证《穆天子传》的卷数、文本的内容以及校正时要多加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