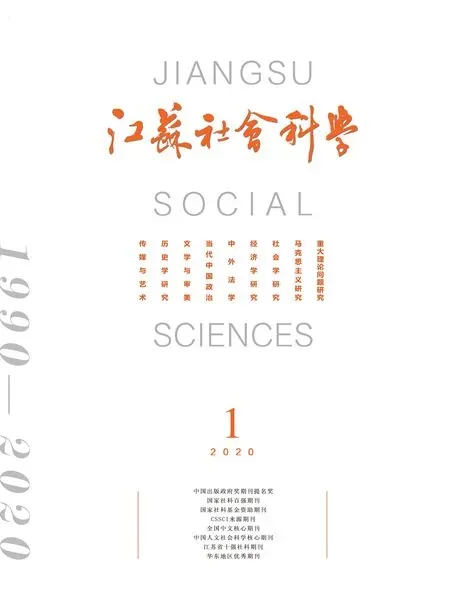当代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知行合一
姚新中 隋婷婷
内容提要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阳明心学所提出的“知行合一”既给予了实证性论证和解释,也提出了挑战,呈现出知行合一在心理结构和认知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如群体一致性压力下个体的知行背离、大脑前额叶损伤引发情感缺失所导致的知行相悖以及电车难题中情感认知双加工竞争造成的知行两难等。然而,从阳明心学“一念发动即是行”与魏格纳“白象效应”的相互佐证到阳明心学与社会心理学在情理并举层面上的所见略同,从克除不善之念、抵御外物之诱的自律与认知心理学中内驱力的对应到飞轮效应与“一万小时定律”对知行工夫的具象性推演与实证性勘测,我们发现阳明心学与社会心理学不但在思想中有诸多共鸣,其理论交叉与互补也为把握情感与认知的平衡、推动知行一致的自验期望、去除蔽染引人习行、为“知行合一”在当代社会的嵌入与施行开启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性。
当代社会心理学是一个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认知科学和哲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关注知行关系问题等。知行问题也是中国传统认识论和伦理学重点关注的问题。自孔子以降,特别是在孟子、荀子的论著中,关于学与习、习与知、知与言、言与行等的论述都从不同的方面涉及知行关系,而明代王阳明更是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该命题成为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知行合一”不仅是哲学伦理思想,代表知行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在道德自律、人际关系、境界培养等现实生活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理解知与行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在社会活动中实现个体的“知”与“行”的合一状态,走出现实中知行脱节、知易行难、知行不一等困境?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是道德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审视其研究成果如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知行关系问题,并将“知行关系”问题放在这一新学科的语境中,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探寻阳明知行观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得以实现的可能路径。
一、从哲学到社会心理学:知行困境的思考
当代社会心理学与传统哲学思辨和伦理论证有不同的研究领域,术语所指也不尽相同,但在知行问题方面却有部分重合的问题域。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知”具有认识论与伦理学的双重含义,既是认知、感知,也包含行的意念。而“行”则是落实意念之行,包含意念、意念之发动、意念之实行等,涉及心理行为、意志行为、动机启动以及从动机到身体行为的过渡。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其大致对应于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概念和行为概念。当代社会心理学通过建构各种模型,从实验数据入手,关注知行的心理机制、脑神经机制、个体与环境互动等方面,考察知行一致和不一致的内外原因。社会心理学研究揭示,个体的知与行共存于社会大环境中,不仅受个体与环境、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灵等诸多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到脑神经状态、所处境遇等多种因素的左右。社会心理学充分利用脑神经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现,提出知与行本身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主要取决于认知,但也与特殊情境和所处环境密切相关,为我们探索和思考知行困境等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方法。
1.知行背离:阿希实验与环境对行为的影响
阿希实验是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1956年进行的三垂线实验,旨在探寻社会群体环境中存在的或大脑感受到的压力是否会促使个体做出违背本身认知的行为[1]Solomon Asch,“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I.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Psycho⁃logical Monographs,1956,70(9),pp.1-70.。这一实验以大学生为受试群体,每组7人,其中1人为真受试者,其余6人为事先安排的实验合作者。实验者每次出示两张卡片,第一张画有标准长度的直线X,第二张画有三条不等长度直线A、B、C,实验者要求受试者判断ABC线中哪一条与X线长度相同,并要求每人轮流大声说出答案。
实验安排真受试者处于倒数第二个位置上。在实验的大部分时间,每人均会说出同样的正确回答,但在几次特定的问答中,实验合作者们会轮流说出同一个错误答案,这时有74%的真受试者违背了本身的认知,说出与群体回答相同的答案。阿希认为这一知行背离的状况是由于个体处在群体一致性的环境中,试图解除自身与群体之间冲突而产生的从众行为(conformity)。一方面,这种行为是个体对规范的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做出的反应,即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会天然地依从社会所接受的规则,并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2]Steven Reiss,“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Teaching of Psychology,2012,39(2),pp.152-156.。另一方面,尊重规范并不是从众行为出现的唯一原因,对信息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的反应也是个体倾向于遵守群体规范的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个体的认知范围有限,个体常需以他人为信息来源了解社会与世界各个方面,因此具有从其所属群体成员获取某些确切信息的倾向[3]Herbert Kelman,“Compliance,Identification,and Internalization 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8,2(1),pp.51-60.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受试者在从众时是内心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由于受大众影响而怀疑自己的判断。这涉及群体和情境是仅仅影响个体的行为还是同时也影响其认知的复杂问题。。
2.知行不一:盖奇案例与脑区研究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除群体施加于认知的影响外,个体情感的缺失也会导致道德领域中的知行背离。社会心理学对道德认知与行为何以脱节问题进行了很多实验。盖奇案例引发了著名的研究。美国工人盖奇在一场爆炸事故中被一根铁棒贯穿头部,经治疗康复后,他的智力、逻辑能力、道德认知、记忆力以及语言能力基本正常,但人们发现他从一个原来非常友善且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变成一个具有侵略倾向并且常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1]〔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风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第31-51页,第52-59页。。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ónio Damásio)通过对盖奇颅骨的三维图像复原发现盖奇的大脑两半球下部和内表面的前额叶皮层受到了损伤。通过研究一些与盖奇类似的前额叶受损者,达马西奥发现:他们在认知方面的能力基本正常,不但具有分辨善恶并做出正常道德判断的能力,而且在科尔伯格的三水平六阶段道德测试[2]科尔伯格根据受试者在两难情景测验中的结果将人的道德判断水准分为三水平六阶段:前习俗道德(preconven⁃tional morality)根据行为具体结果及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判断好坏是非,包括两个阶段,即惩罚服从取向阶段和相对功利取向阶段;习俗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思考道德问题,着眼于社会的希望与要求并遵守和执行社会的规范,包括两个阶段,即寻求认可取向阶段和遵守法规取向阶段;后习俗道德(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能从人类正义、良心、尊严等角度判断行为的对错,并不完全受外在的法律和权威的约束,而是力图寻求更恰当的社会规范,它也包括两个阶段,即社会契约取向阶段和普遍伦理取向阶段。达到后习俗道德水平(第五和第六阶段)的受试者具有较高的道德认知和判断能力。中也能得到优秀(即达到第五阶段)的评测结果;但是,他们无法做出符合认知的道德行为[3]〔美〕安 东 尼奥·达 马 西奥:《笛 卡 尔的 错误:情绪、推理 和 人脑》,毛 彩风 译,〔北 京〕教育 科 学出 版 社2007年版,第3页,第31-51页,第52-59页。。达马西奥认为,这是由于前额叶脑区的损伤影响了受试者在情感和共情(empathy)方面的能力,个体因而失去了使自己在道德相关事件中实现知行合一的能力[4]〔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风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第31-51页,第52-59页。。盖奇案例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更加深入地对其进行分析,也许会对身心关系、知行关系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关键是如何看待道德动机在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内在主义认为真正的道德之知必须是蕴含道德动机的,而外在主义则认为道德之知并不必然蕴含道德动机。对于盖奇是否具备真正的道德之知的问题,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3.知行两难:电车难题中情感与认知的竞争
研究者通过将思想实验与心理学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道德之知与道德选择进行了细致的区分,进一步探索情感的变化如何影响个体在道德认知和行为中的统一,如何改变个体道德认知的一贯性,如何使得个体做出不同于以往认知的判断。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他们采用电车难题(the trolley case)思想实验揭示了知行之间的复杂关系。电车难题是当代伦理学最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经典版本内容是:假设一名电车司机驾驶的电车无法刹车,前方铁轨上有五名工人。电车司机只有改变轨道,才能让这五人免于被撞死。但备用轨道上,也有一名工人。那么,是否应该改变轨道撞死一人而救下五人?在其后来的扩展版本中,有一个版本假设,救这五个人的唯一方法是把一个大胖子推到铁轨上来阻挡电车。如果以他一人死亡为代价可以拯救这五个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面对上述两难情境,大部分受试者在第一个问题上采取后果主义的认知模式,选择舍一人救五人,但在第二个问题上却没有继续采取后果主义认知模式做出选择,而是转向了义务论的认知模式,选择宁愿舍弃五人也不去杀害一人。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认为,这一认知行为差异是由两个问题造成的情感认知冲突带来的,他将道德两难困境的问题分为“亲身性”(personal)与“非亲身性”(impersonal)两类[5][5“]亲身性”与“非亲身性”是约书亚·格林为了区分道德两难问题的类型而提出的分类法,“亲身性”问题的定义有三个: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对象是一个特定的人;这种做法造成的伤害不是由转移对另一个当事人有威胁的事情而引发的。道德两难中不符合“亲身性”定义的问题则属于“非亲身性”问题。,认为电车难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是“非亲身性”的,而第二个问题是“亲身性”的。“亲身性”问题引发更多的情感变化,因此也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1]Joshua Greene,Brian Sommerville,Leigh Nystrom,John Darley and Jonathan Cohen,“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Science,2001,293(5537),pp.2105-2108,pp.2105-2108.。在之后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测验中,受试者的情绪相关脑区的活跃特征证实了格林的假设。在格林之后,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也通过道德情景实验研究了情感在道德中的作用,提出情感不仅在道德判断过程中发挥影响,而且有时会充当道德行为的动机和驱动力[2]Jonathan Haidt,“The Moral Emotions”,in R.J.Davidson,K.R.Scherer,and H.H.Goldsmith(eds.),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852-870.王觅泉、姚新中:《理性主义道德心理学批判——乔纳森·海特与社会直觉主义》,〔哈尔滨〕《学术交流》2018年第11期。。
在此基础上,格林与海特分别构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和道德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虽然两人在情感对道德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方面有一些分歧,但都认为情感的参与对人的行为特别是道德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约书亚·格林在双加工模型中强调了情感与认知的双重作用,认为人们面临道德情境时会同时激活认知和情感,这两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最终道德判断或行动的结果取决于情感和认知的竞争结果[3]Joshua Greene,Brian Sommerville,Leigh Nystrom,John Darley and Jonathan Cohen,“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Science,2001,293(5537),pp.2105-2108,pp.2105-2108.。乔纳森·海特则在社会直觉模型中将情感认知的关系比喻为“直觉之狗与理性之尾”:道德直觉是快速且自动的无意识情感过程,而道德推理是缓慢审慎的认知加工过程;道德推理过程发生于人们做出直觉道德判断之后,有意识的道德认知对直觉判断进行反思和规范,但往往很难改变由情绪驱动的道德判断和行为[4]Jonathan Haidt and Fredrik Bjorklund,“Social Intuitionists Answer Six Questions about Moral Psychology”, in W.Sin⁃nott-Armstrong(ed.), Moral Psychology, vol.2,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Morality: Inuition and Divers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8,pp.181-217.。
二、社会心理学对知行关系的探索:知行合一何以可能?
对于知行合一,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路径量化了环境与情感、情感与认知、认知与行为的研究,揭示出知行之间复杂、动态的关系,提醒我们保持知行一致的困难。这些实验同时也使诸多研究者发出“知行合一是否缺乏心理基础?”“知行合一是否可能?”等疑问。对此,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审视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与传统阳明心学对于知行合一之困难与可能性的认识。
1.知行连动:一念起即是行
知行合一何以可能?王阳明给出的答案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第3页。,指出心之本体就是知行合一。阳明心学中的知,并非限制在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其行也非仅仅是可以客观观察的物理运动。王阳明引用《大学》中的“好好色”“恶恶臭”来说明他关于知与行以及知行合一如何可能的见解:“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第3页。在王阳明那里,知与行不仅是连贯的,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他认为,意念发动就已经是行了,因此,如果发动处有不善,就要将这个不善的念头克制掉,“善念则存,恶念则去”,在行为中趋善避恶。这表明了个体意念的流动对个体行为的直接影响,也说明了知行连动在个体的心理本能中具有可开启性和可触动性。此即为知行合一之可能的先天基础。
知与行之间、意念与意念发动之间,都并非截然分离的两个领域,而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这一阳明心学的独到理解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和佐证。2003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r)在其白熊效应(也称白象效应)实验中证明了意念与心理行为的直接关系。受试者被要求在脑海中想象一只白色的熊或不要在脑海中想象一只白色的熊。实验结果显示,那些受到指示不要去想白熊的受试者,无法压抑对白熊的想象,他们所报告的脑海中浮现白熊的次数是被要求想象白熊的受试者的两倍。魏格纳认为,当个体刻意转移注意力时,思维也开始出现无意识的“自主监视”行为——监视自己是否还在想不应该想的事情,使个体反而无法从根本上放弃对事情的关注[1]Daniel Wegner and David Schneider,“The White Bear Story”,Psychological Inquiry,2003,14(3/4),pp.326-329.。社会心理学常常援引这一效应来解释由于脑海中出现的念头(通常是否定的)自发引出的行为表现。如个体想着不要紧张,却因为念头在内心的投射而引发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紧张表现;个体想着不要失眠,却使得失眠这一念头在认知过程中挥之不去,从而使个体无法正常入眠;等等。这种影响如何产生与消除也受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与关注。
2.知行合一:情感、直觉与理性
在阳明心学语境中,近似于直觉之“知”与纯粹“认知”的语义指称域不同,因为“知行合一”之知本身便是包含心之四端的良知,“所谓‘四端’者皆情也”[2]〔南宋〕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0页。。王阳明对于情感在知行合一中的重要性早有意识,其提法也与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异曲同工,认为“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3页,第5页,第35页。。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明确了情感在知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不论在约书亚·格林的双加工模型中还是在乔纳森·海特的直觉判断模型中,情感的参与都是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王阳明的情虽是良知之基,但他也提出“七情”过盛实为良知之害的观点;而在海特的直觉模型中,尽管情感被比喻为冲刺在前的猎犬,却终需理性之尾进行“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发挥其推理、辩护和检验的作用。如果单纯放任个体情感直觉的奔腾,那么,对道德事件的判断将出现无法给出理性归因的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4]Jonathan Haidt,“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2001(108),pp.814-834.。而且,直觉的判断方式与事件的情感性好恶判断重合,虽然这一判断过程在多数情况下与道德判断同步,但是很多事件无法单纯依照情感性直觉进行道德判断。在海特所举出的一些道德相关事件中,“吃掉自己的被车撞死的狗”“用美国国旗擦洗马桶”等事件能够造成受试者的直觉性的情感厌恶,而且能唤起前额叶皮层等情感脑区的激活反应。但是,若要对其进行道德解释和归因,则必须依靠理性认知的力量[5]Jonathan Haidt, Silvia Koller and Maria Dias,“Affect, Culture and Morality, or is It Wrong to Eat Your Do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ology,1993(65),pp.613-628.。格林的双加工模型对理性的作用也有强调。他提出,虽然让个体不追随情感起落并用理性约束行为只是一个不得已接受的(bullet biting)方案,但是重视推理的理性模式在很多情况下仍比单纯的自动情感模式更可靠[6]Joshua Greene,“Beyond Point-and-Shoot Morality: Why Cognitive (Neuro) Science Matter for Ethics”, in S.M.Liao(ed.),Moral Brains: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119-149.。阳明心学认为,即便是至情,“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3页,第5页,第35页。,须以天理调停适中,方能知行合一。因此,虽然社会心理学对理性有独特的定义,但是其关于直觉、情感与理性在知行合一中作用的理解与阳明心学的思路殊途同归。
3.知行互助:意志力的消磨与增强
在克除不善之念与践行良知的历程中,道德行为同时涉及道德主体在意志力层面的自控与自律。“能克己,方能成己。”[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3页,第5页,第35页。主体确定知行导向,并据此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道德意志的存在是克服抵御外物之诱、推动行动进度与延续的关键。在社会心理学中,意志力在生理层面上首先表现为一种内驱力,受大脑中巴甫洛夫系统(Pavlovian system)和目标导向系统(goal-directed sys⁃tem)的交互影响。巴甫洛夫系统代表了主体的本能与冲动的反应系统;目标导向系统则是通过有意识地对“响应-结果关联”(response-outcome association)做出反应,使主体做出行动时坚持道德规范,抵御克制巴甫洛夫系统的本能欲求。两个系统在神经递质的影响下彼此竞争,目标导向系统的胜出意味着践行良知在意志力层面的延续,而巴甫洛夫系统胜出则往往意味着主体向私欲的屈服[1]Filip Gęsiarz and Molly Crockett,“Goal-directed, Habitual and Pavlovian Prosocial Behavior”,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2015,5(9),pp.1-18.。在身体机理方面,人类的身体有一种偏爱稳定性的倾向。当行动在意志的推动下使主体迈出预先的舒适区时,身体系统会感受到压力,以至原来的体内平衡无法继续保持,身体会开始响应变化;但是,长时间踏出舒适区,往往伴随着意志力的消磨以及行动的中止。这一现象也被安德斯·艾利克森称为“新年决心效应”[2]〔美〕安德斯·艾利克森、罗伯特·普尔:《刻意练习——如何从新手到大师》,王正林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对于此类意志不坚的现象,阳明心学提倡经由持续的省察克治等修养功夫增强主体自身的意志力,若以镜喻之,便如“斑垢驳蚀之镜,经由痛刮研磨”[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1页。方可恢复光明。社会心理学认为,这一增强过程同时也是生理节奏与神经环路共同作用的结果。主体对自身不断的省察克治对应于心理学层面上不断的试错练习,本质上是一种充分利用大脑和身体适应能力发展和提升新能力的方式,可使大脑中受到磨炼的区域发生改变。通过适合生理节奏的持续性试错练习,大脑将以自身重新布线的方式适应这些挑战,构建出新的行动舒适区,减少这些挑战对意志力的消磨。这一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体的压力感受,增加了大脑双系统相关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含量,从侧面提升大脑双系统中目标导向系统(goal-directed system)胜过巴甫洛夫系统(Pavlovian system)的可能性[4]Molly Crockett,“Moral Bioenhancement: Neuroscientif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3(40), pp.370-371.。通过这一过程的不断强化巩固,主体便能逐渐增强意志,胜其习气,促进良知的践行。
4.知行协调:环境效应的双重性
知行合一的完整心体不能仅仅具有先天的内在性,必须也具有外在性,而在先天基础上的外化过程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浸染。当代社会心理学对此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从而理解知行之间的相互协调。具体行为都是个体认知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受到群体变量的影响。但是,外部刺激存在效应饱和与递减的问题,不会恒久无限,而且外部影响本身也绝非彻底的。在前述阿希实验中,74%的受试者会顺从群体选择做出与认知背离的行动,仍有26%的受试者坚持了自己既定的认知,保持了知行一致。根据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协调理论,个体保持知行一致的本能十分强烈,当认知与行动出现背离与失调时,自身会产生焦虑和不适感。为减少焦虑和不适感,寻求认知与行动的协调,个体通常会选择三种途径:①改变自身认知;②坚持自身认知;③不改变自身认知,但改变对行动结果的认知[5]IremMetin and SelinCamgoz,“The Advances in the Hist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11,1(6),pp.131-136.。
选项①以外部认知代替自身认知,归属于集体无意识状态;选项③未改变自身认知,但为了减少群体压力,采取了与外部认知一致的行动。这两种选择构成了阿希实验中的74%,也是阳明心学阐发了的知行无法合一的重要原因。知行一致是人之本能,如日月常照,但环境譬如遮蔽日月的浮云,使人丧失真知,“功夫断了,便蔽其知”[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第90-91页,第111页。,“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第90-91页,第111页。。因此,知行合一如何可能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去除“知”之昏蔽的问题,必须从内在的心性修为入手,通过发明本心,如孟子提出的那样,“求放心”,即经由内省功夫唤起“真知”“良知”的恒照,方能“致良知”,达到知行本体上的合一[3]“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同时还强调了外部环境变量对良知的正向影响。有的研究反向操作阿希实验,去除干扰遮蔽,代入对真知的认可和推崇,受试者的知行一致便自然而然,水到渠成[4]傅鑫媛、陆智远、寇彧:《陌生他人在场及其行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北京〕《心理学报》2015年第8期。。还有的研究通过行为的前置情境,唤起个体的驱动性情绪,促使个体做出符合认知中具有利他属性的亲社会行为。如艾丽丝·艾森(Alice Isen)的“一毛钱实验”,将一毛钱作为前置情境中波动情绪的变量,意外得到一毛钱的实验参与者中有九成的人会停下脚步帮忙收拾掉落的文件,而没有得到一毛钱的人中仅有一成提供帮助[5]Alice Isen and Paula Levin,“The Effect of Feeling Good on Helping: Cookies and Kind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2,21(3),pp.384-388.。这一实验表明,情绪和情境变动会对人们关于“应该”的观念产生影响,好心情或由于情境变化而导致的认知变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他人伸出援手,做出亲社会的行为。正是因为认知、行为与环境、情景有复杂的关系,当代社会心理学对情境中的气味、温度、距离、方位、洁净度等一系列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这些环境变量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认知图式和内隐情感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进一步的影响[6]彭凯平、喻丰:《道德的心理物理学:现象、机制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5.知行功夫:自验期望与飞轮效应
知行合一的习惯养成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存心养性的持久功夫。社会心理学认为,这一过程的良性发展首先始于个体对情境的知觉形成正向的自我期望或标签。自身知行一致的期望和标签具有定性导向作用,对个体认知行为的自我认同有强烈的影响,由之而引发的积极性反馈,会使个体对该情境的知觉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标签的效应,使期望变为自验的真实,如罗森塔尔实验中受到更高正向期望的学生更易将期望转化为现实[7]马欣、魏勇:《家长教育期望中的“罗森塔尔效应”循环模型探析——基于CEPS的模型检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这一转化过程不是线性且均速的。阐发飞轮效应的吉姆·科林斯(Jim Collins)将自验期望实现的过程类比为飞轮的转动。飞轮最初需要的能量是巨大的,推动飞轮也是艰难的,必须持久反复地推动。这一艰难持久的过程,便如阳明心学在推进知行合一时通过功夫再现心体的过程。王阳明曾说:“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第90-91页,第111页。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这一功夫修养的时间长度可类比为技能的练习和养成时间,其与大脑特定神经通路的形成时间同步,是促进神经纤维外层包裹上髓鞘,增加信息在神经纤维中传导的速度和精确度的过程[1]Bruce Perry,“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the Expression of Genetic Potential: What Childhood Neglect Tells Us about Nature and Nurture”,Brain and Mind,2002(3),pp.79-100.。根据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提出的“一万小时定律”,技能养成是一个长时性的过程,即便有努力的“刻意练习”,这一过程也至少需要一万小时[2]Karl Ericsson,Ralf Krampe and Clemens Tesch-Roemer,“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Psychological Review,1993,100(3),pp.363-406.。虽然技能养成需要长期的过程,但科林斯提出,随着飞轮一圈一圈转动,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飞轮的重力和冲力会成为推动力的一部分,这时,无须再费更大的力气,飞轮仍旧会快速、不停地转动[3]Timothy Kanold,“The Flywheel Effect:Educators Gain Momentum from a Model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Journal of Staff Development,2006(27),pp.16-21.。用阳明心学关于知行功夫的话来说,这便是积累日久而功夫到了的时候。
三、社会心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互补与互鉴
研究知行不一的影响因素,探寻如何使人们在日常行为中能够克服知行背离,做到知行合一、为善去恶,这是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理学所共同关心并试图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参考儒家传统,反躬自省寻求解答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而借鉴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思想、方法和路径则可以重构知行合一的话语体系,为我们重新理解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实现知行合一探索出新的路径。
“知”与“行”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两个必需要素,贯穿于个体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之说有其普遍性,虽历经世代转换,但不失其恒久价值。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针对程朱理学以降“士风衰薄”“学术不明”“知行分作两件事”之风而提出的补偏除弊之法,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语境,而其观点如“一念起便是行”“致良知”等也在现代语境中逐渐缺乏实践意义,甚至被认为是形而上的玄思,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
古老的知行合一命题亟须语境转换和重新诠释,而作为交叉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关于认知和行为机制的研究、对知行关系的探索,不仅可以为知行合一提供新解释,而且能够对其进行实验检验和科学性的论证。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和话语体系重新厘清和解释阳明心学的相关概念、观点,在当代科学论证与实验过程中对其进行扩展和话语重构,是推动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思想嵌入现代语境和社会实践,回答新时代的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此外,日新月异的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对原有的知行合一思想也提出了心理、认知、意识等层面上的种种新的疑问和思考。通过引入心理认知、环境、生理基础等变量,社会心理学可以使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在动态系统中得到重新表述和验证。这一动态系统被勒温总结为一个多变量公式:B=f(Lsp)=f(P*E)。
勒温提出,人作为一个场(field),其心理活动在一种生活空间(life space,简称Lsp)里发生。在这一生活空间中,一个人的行为(B)取决于个体(P)和他的环境(E)的相互作用(由函数f表达),随着人的心理意识与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4]Kurt Lewin,“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Concept,Method and Reality in Social Science,Social Equilibria and Social Change”,Human Relations,1947,1(1),pp.5-41.。在这一连动的系统当中,“知行合一”的过程在心理生理层面的物理广延上可被具象化。社会心理学通过评估身体构造、身体状态、感觉运动系统等生理因素对认知及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接连起认知行为与脑神经基础之间的因果同步性关系,发现认知、思维、判断、推理、情绪和行动的一体的过程,验证并细化了知行实践的具体步骤。虽然道德认知、行为以及知行合一不能简单还原为生理心理要素的相互作用,但社会心理学关于良知良行如何从一念而起,作为助力的意志在心理生理的层面如何被消磨、延续与强化,情感与理性认知如何在竞争中构建良知,环境影响的生发与其效应的饱和,知行习惯养成有怎样的时间节律,等等的研究,还是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伦理学的“知行合一”提供了系统化、数据化的实践参照,也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消除知行背离、促进知行合一提供了一定的科学论证和践行指南。
进而言之,社会心理学不仅可以为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等思想提供单向的语境重构,而且可以与阳明心学进行路径、方法、目标等方面的双向互动与交汇。如何理解和落实知行合一既是哲学问题也社会心理学问题。发明本心、自省内求是阳明心学对实现知行合一提出的理解视角和解决方案,而观察变量、证伪假设则是社会心理学的必然路径。这两者虽然在诸多方面泾渭分明,但在当代研究中不应是两条相望却不相交的平行线。寻找、分析并重新解释两者路径的交汇、视域的融合和论证的互补,不仅可以提升各自的内在价值,而且是实现创新突破的共同出路。
具体而言,当代社会心理学与阳明心学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互补、互鉴。在视角方面,实验心理学侧重于可观察、可调控、可重复的实验变量,主要以“第三人称”(the third-person)式的描述性视角计量个体知行与环境、情绪等因素的交互关系[1]Tom Froese and Shaun Gallagher,“Phenomenology and Artificial Life:Toward a Technological Supplement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Husserl Study,2010,26(2),pp.83-106.,具有基础性和可见性,可以为知行合一在个体生活中的实现提供指导和支持。但个体的内心体悟作为存于主观体验中的第一人称事件(first-person events),无法被实验视角的“第三人称”全然还原。如果借助阳明心学凝神致志、向心内求的路径,则有助于飞越人称视角的解释鸿沟,生知安行,功到自然。在研究方法方面,哲学思潮中饱含对知行合一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体悟,可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理论假设与实验思路的理论与灵感来源,有助于建构知行合一与社会群体的实践对接;而社会心理学的模型建构、数据收集、个案分析等方法则可以为知行合一的哲学论证提供数据化和具象性的支撑。在研究的目标方面,实验心理学虽然道出了阻碍知行合一的种种因素,但其目的绝非否定知行合一的可能性。很多心理学家对知行合一都抱持与王阳明同样积极的态度,认为明确行为背后的生活环境、认知情感等要素的作用是深化思考、推动个体走向知行合一的关键。有些社会心理学家明确提出,虽然人可能是生活环境、先天因素和自身生化反应操作下的木偶,“但这也意味着你有机会可以抓住缠在身上的绳索:识破思想情感的种种表象,可以让我们更加明智地度过一生”[2]〔美〕萨姆·哈里斯:《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欧阳明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多维度多层次发展为我们理解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命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进路,有助于明辨阳明心学语境中知行合一的外部烦扰之源并建构出有效的实践途径。对知行合一如何在当代语境和生活实践中得以实现的问题的回答,既是哲学思考的必然,也是促进心理健康、社会和谐的必需。传统知行合一理念由于增加当代心理学的解释而得以实质化、具象化和个体化,而社会心理学关于影响知行合一要素的量化研究则可以从阳明心学关于心身关系、天人关系、情理关系等的诸多论述中汲取灵感,从而形成哲学与心理学交融并举、互助互成的局面,为“知行合一”在当代社会的嵌入与推行增加更多空间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