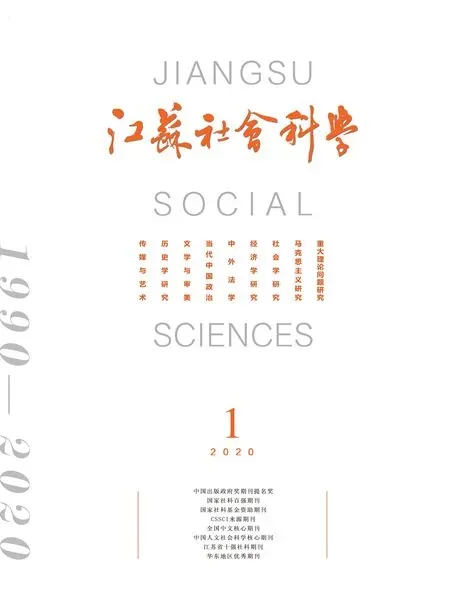中华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话语建构
——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理念与实践视角
管 宁
内容提要 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迁、拓展的,对文化遗产价值评定应遵循其内涵变迁、价值动态性等基本规律和逻辑,预判与新创文化遗产有助于更全面科学的保护与利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要与时代同步伐,遵循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进行以设计承载传统精神、提炼美学精粹、重塑传统文化的理论探索与创新。将创新理论融入现实创造,进行包括传统营造、传统家具、传统工艺等在内的整体性、行业性和跨界融合的多元化新实践,传递本土美学精神、造物理念,才能创造新时代的中国精神文化与造物文化,形成令当代世界所接受和推崇的中国话语、中国价值观乃至中国生活方式。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创造的历史遗存,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劳动与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美学精神、造物智慧和历史记忆,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文明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与灵感源泉。由于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也由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文化遗产认知历程的曲折与漫长,更导致人们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的艰辛与反复。晚近艺术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的建立,其本身就表明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英国学者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曾这样解读文化专家温迪·葛瑞斯伍德所发展的“文化菱形”思想:“艺术是由一位或一群艺术家创作而成,而不是在没有人为介入的情况下奇迹般出现的。艺术并不触及整个‘社会’,而是触及由社会体系中的个体组成的特定群体。”[1]〔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所谓“文化菱形”事实上只是种说明图,是在作者、艺术、消费者和社会这四个要素之间提供六根相互连接、类似菱形的线来表明它们所存在的复杂关系,旨在帮助人们理解文化与社会等要素存在哪些贡献,其意义在于“促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文化客体和社会世界的关联……要完全理解一个特定的文化客体,需要先理解所有四个要点和六条连接线”[2]Griswold and Wendy,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London:Pine Forge Press,1994,p.15.。葛瑞斯伍德的观点提醒我们,对于文化和文化遗产的研究应当有更加开阔和动态的视野,有意识地将文化纳入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纳入人类认知发展和实践探索之中进行考察。这是我们确立先进理念、规范保护行为、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文化遗产:认知拓展的逻辑理路
人类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走过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由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也由于人们不同历史时期所肩负使命的差异性,还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不足和偏差,导致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存在许多错误和误区,其结果是造成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和遗存被人为毁坏,留下无可挽回和难以弥补的损失。著名学者吴良镛指出:城镇化建设中古建筑遭到破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几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1]吴良镛:《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北京〕《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纵观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可以看出,导致文化遗产人为毁坏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认知的狭隘与偏差;而文化遗产被妥善保护的原因,则必然是认知的正确与科学。因此,探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认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文化遗产与“文明遗产”。通常而言,理解什么是文化遗产,只要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关于文化遗产的标准搞清楚就可以了,即可以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评价标准作为文化遗产的基本定义或评判标准。但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所创造的浩如烟海的精神与物质文化面前,仅仅依据一个简单的标准是很难作出全面概括的,也无法穷尽庞大而丰富的遗产类型。事实上,从《世界遗产名录》的6项标准本身,人们也可看出对于文化遗产认知的变化轨迹[2]即从可移动的文物到不可移动的建筑,从单一建筑到一个建筑群体,从完整的古建筑群到一定规模的古遗址,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建筑群到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再到古村镇,从古代文化遗产到近现代文化遗产,从纯粹文化领域到各领域的文明创造(如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从过往的文化遗存到现存和活着的文化遗产(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展和延伸,文化遗产的时间空间范畴不断扩大,类型和形态日益多样化。从这个现象的基本面看,与其说是文化遗产,不如说是“文明遗产”更贴切,因为文化遗产的覆盖面已经遍及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创造领域,这就需要运用广义认识论不断拓展和深化对遗产的认知,如同人们对博物馆的认识“突破了人们头脑中传统博物馆固有的拥有一定藏品和特定馆舍建筑的概念”,出现“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等一样[3]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遗产类型的不断扩展也将成为一种常态。但这不等于说只要是人类文明创造都可以成为文化遗产。那么,这就涉及到文化遗产认定的内在规律和文化遗产生成的内在逻辑。对于这种规律和逻辑的认识与把握,显然要远比了解文化遗产的标准来得更为重要。
内涵变迁与动态性价值。文化遗产界定的最基本规律和逻辑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应是那些在各个历史时代不同领域中创造并被普通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成果,包括那些历史上创造的纯粹功能性的器物与设施,以及具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发展走向与形态的机构组织所在地和承载重要历史事件的建筑(群体)等。换句话说,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变化和产生深刻影响的一切文明创造,都有可能成为文化遗产。事实上,文化遗产通常是某领域中经典性的创造,而“经典需要特殊的历史背景”,“可以认为,经典时刻描述了所谓的范式转变”[4]〔美〕彼得·埃森曼:《经典建筑》,范路、陈洁、王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导言第3页。。这表明遗产的生成往往源于某种创造范式的转变。历史地看,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是随着人们认知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动态性也体现了不同的文明创造对于人类发展的作用也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人们能够理解故宫、天坛、大雁塔可以成为文化遗产,毕竟这些建筑的恢宏与精美及其历史价值堪称经典;可是,人们或许没有想过那些在建造之时并不具有文化艺术价值的物质创造,居然在今天也可以成为文化遗产——都江堰在古代不过是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今天却因为其发挥的历史作用和独特高超的建造技艺水平而成为文化遗产;长城是冷兵器时代能够发挥重要防御作用的军事设施,并随着热兵器时代的到来而成为失去功能作用的建筑,但今天不但没有被拆除反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再比如德国的包豪斯学院,作为近现代以来改变人类造物文化发展方向(笔者以为,这种方向的改变就是一种彼得·埃森曼所说的造物范式的转变)、确立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世界第一所专业现代设计学院,因其独特的历史影响而成为遗产项目,并不因为它只有短短的十几年的存在时间[1]〔德〕包豪斯档案馆、〔德〕玛格达莱娜·德罗斯特:《包豪斯1919—1933》,丁梦月、胡一可译,〔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这就表明所谓文化遗产不仅限于狭义的文化领域,而是涉及人类所有文明创造,也表明已经逝去或仍未逝去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文明创造,都可以成为文化遗产。中国今天的超级工程如天眼、港珠澳大桥以及国家大剧院、鸟巢、空间站等,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化遗产。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产品,如手机、电脑、打印机、台灯、电视等,其各个时期生产的经典款式,也可以成为设计文化遗产。遗产的生成不仅涉及生产范式、历史时刻,还涉及诸多关联性因素,彼得·埃森曼就曾指出:“经典建筑不应该被当作自身孤立的物体,对它的研究需要关注其反映特殊时刻的能力,以及其与之前之后建筑关联性的能力。”[2]〔美〕彼得·埃森曼:《经典建筑(1950—2000)》,范路、陈洁、王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导言第5页。引入关联性视域有助于更准确评判遗产的价值。可见,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创造,其价值具有明显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决定了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持续扩展与延伸。
文化遗产:预判与新创。不难看出,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其内涵与外延随着社会历史以及人们认知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以这样一种认知态度来看待文化遗产,就能够避免人为毁坏文化遗产,妥善保护已经确定的文化遗产和未确认为文化遗产的当代创造。从这样的认知出发,我们甚至应当对可能成为文化遗产的物质创造进行预测性保护,即建立一种由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专家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预判机制,对可能成为却尚未列为文化遗产的项目进行前置性保护,给可能成为历史遗产的当代文明创造留出机会和空间,以前瞻性的思维杜绝当下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文化遗产破坏现象。正如单霁翔所言:“人们不仅要‘为今天收藏昨天’,而且还要更多地关注人类的‘今天’和‘明天’,为‘明天而收藏今天’。”[3]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在我们身边,就拥有许多值得收藏的“遗产”:如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象山校区专家接待中心(水岸山居),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就其设计文化价值而言,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化遗产,可先行进行必要的保护。而在欧美的一些当代艺术博物馆,就把如凯瑞姆·瑞席这样的顶级设计师作品作为收藏品,这不啻是对当代文化创造的认可与尊重。我们将这种文化创造称作“新传统”,而这种确认,不仅是拓展了文化遗产概念,更是确立了当代文化发展的风向标。
由于现代社会本身创造的物质与精神遗存,其更新换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和快捷,导致不太长的时期里,便有不同形态的物质文化出现。对已经过时甚至很快要消失的人类创造进行必要保护,就产生了一系列新型文化遗产:20 世纪文化遗产[4]凤凰空间·华南编辑部编:《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以及文化线路、文化环境等遗产新概念。对于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家也给予了高度重视,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使我国各类型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科学、规范和法制化轨道。但仅此还不足以对文化遗产进行全覆盖式的保护。基于前置性保护理念,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当代文化诉求和科技条件,有意识地创造各种文化精品,尤其是造物文化精品,并在创造之后加以妥善保护,使之具备成为未来文化遗产的必要品质、条件与基础。科技狂人贝佐斯在深山之中投巨资建造的“世纪时钟”,就可以作为一种有意识的“遗产”创造来看待与保护。这种“新创遗产”的意识和行为,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创造意识。
二、文化遗产:传承活化的新思想新理论
正确的认知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先进的理念能决定保护行为的科学与否;认知过程曲折而漫长,探索之路湮远而艰辛。新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良机。
新思想新战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识和精神内蕴,决定着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失去这种标识就意味着失去一个民族的根性。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唯有保护继承好文化遗产,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见中国网2014-05-05。深刻揭示了民族文化基因对确立民族根性、灵魂与标识的内在关系。在继承与发展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创新理念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313、340页。。这一系列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继承创新问题的前沿理念,阐明了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是推动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根本遵循。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和使命也发生改变:不仅要提升保护层级,还要提高继承发展水平;不仅要考虑保护的科学性,还要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建设之间关系如何协调问题,以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期望对精神生活的新期待。确立对文化遗产类型、范围的新认知,是进行科学保护的前提。国家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和类型上有许多新提法和新要求。在遗产类型上,提出加强“城市特色风貌管理”,这个概念就意味着将人们熟悉的名城名村名镇、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的保护,扩大到城市特色风貌,即将城市中富有特色的地方性建筑、区域民俗风貌也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这无疑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把握了“文化遗产”概念的深层内涵和本质属性。在保护要求上,体现出整体性、系统性、全方位的保护思路。在继承方式上,提出要融入生产生活,让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这些国家层面的新提法、新政策、新思路,不仅充分表明我国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理解越来越深入,而且表明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了许多合乎国情的新理念新战略。
设计与精神物化。探索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无疑是一个漫长而又系统的工程,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专家、设计师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理念与思路呈现不断深化和细化的特点。彼得·埃森曼的“建筑不仅仅是关于物质的存在”[3]〔美〕彼得·埃森曼:《经典建筑(1950—2000)》,范路、陈洁、王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中文版序第2页。的观点,道出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存在深刻联系。文化遗产继承转换,作为物质与精神结合体的设计及其设计文化,是一个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相形于精神文化,设计文化包含了精神理念、设计美学、工匠技艺、人机工学、人机科技、材料科学等多方面因素,是美学与工艺、文化与科技、精神与物质相互融合的产物。现代艺术设计无疑是当代文化创造乃至其他领域生产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和专业,更是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发展必须凭借的重要专业技能和途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丰富的传统文化带入当代,以实现与现代生产的融合,并让传统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平等专家深入探讨了“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这一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论题,认为现代艺术设计中民族文化元素应用的实践,可以分别从“民族文化符号与设计理念”“民族文化元素与设计风格”“民族文化精神与设计环境”三个维度进行考察。他们认为“符号真正的有益性是一种形式结构与一个正确理念的有效匹配”[1]杭海、林存真主编:《从OLYMPIK到APEC: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北京〕中国工业建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第19页。,也就是说由于符号往往内蕴着复杂的文化信息和意义指向,要使其发挥一种正能量的作用,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文化选择或理念作为支撑,当然这种支撑是建立在理念内涵与形式结构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许平等学者还从更为深层的文化心理的延续来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将民族文化精神与设计环境联系起来,认为“反映在设计中的精神取向往往是文化元素的复杂组合,它对应于所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因此包含着一个更为完整和整体的环境要求”,“设计中的精神是对外在环境的反应方式”[2]杭 海、林存 真主编:《从OLYMPIK到APEC:民族传统 文化元素 在现代艺 术设计 中的应用 研究》,〔北京〕中国工业建筑出 版社2017年版,第18页,第19页。。不难看出,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即便是提供设计来维系和传承,也需要一个来自这个民族对外在世界的基本态度,以及由这个基本态度所形成的文化倾向。通过现代艺术设计不仅要传承民族文脉,还要以具有民族特点的对待世界的态度来考量面向现实和未来的设计实践,这样才能从内在的、深刻的层面上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精髓汲取与重塑传统。设计是将造物思想和理念具体呈现出来的关键环节,其过程也是哲学、艺术、技术、工艺、环境和心理等众多元素的综合,是造物从理念到产品必不可少的过程。设计作为关乎造物的人类智性行为,我们的先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造物文化技艺、美学思想乃至哲学理念;并以设计为中介,以高超的技艺与高度的智慧将美学精神有机融入器物之中,成就了今天无数文化瑰宝。然而,“文化概念的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一个时期的艺术与当时普遍盛行的‘生活方式’存在密切的必然联系,因此审美判断、道德判断和社会判断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3]〔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一编,第七章。。传统文化作为适应以往不同时代社会生活方式的需要而产生和创造出来的精神与物质遗存,必然存在与当代生活方式的某种不相适应性,我们今天如何继承其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当下所缺失的一些审美精神、价值理念和科学的合乎人性的生活态度——成为文化专家和设计师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如果说上述专家的探索是基于传统继承及其现代性转换的理论思考,那么,另一种探索则从理论(理念)转向“设计”这一生活与现代性的“中介”来讨论传统的继承创新问题,更具有理论与实践融合特性和可操作性价值。现代设计是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尤其是在现代造物领域。传统造物和设计文化的继承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关键的问题是要全面推动现代设计文化启蒙,不仅从事造物的专业人员要系统掌握现代设计知识和设计理念,而且要让大众百姓也了解现代设计常识、提高现代设计欣赏水平。曹小欧系统回溯和梳理了中国“经由‘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的变迁因由”,“以‘设计’作为‘现代启蒙’开始,这完全超越了通常的设计史视野,而将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置于‘现代性’问题的整体之中”。他重点“讨论‘现代设计’在中国的语言方式”,以及如何“形成‘东方设计’自觉追求”[1]曹小欧:《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生活、启蒙、变迁》,〔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第220页。。但他也提醒人们:“在面对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时,经验的感性总是让人们感到亲切,进而导致我们可能会对传统工艺作出些许言过其实的溢美,而无视它在工业批量化生产目前的‘迟钝’,这种在潜移默化中滋生出来的乡土情怀,有时已经成为我们在提倡本土时‘剑走偏锋’的隐忧。重新回到‘本土’,需要对传统去粗存精的提炼,而不是一味地堆砌。”[2]曹小欧:《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生活、启蒙、变迁》,〔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第220页。这一对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乃至当代造物生产之间关系的表述,显然是建立在深入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在推崇和弘扬传统的语境中特别需要警惕和审视的。周宪从设计本身的价值功能来考察其在当代的转向与变化,认为晚近设计有三个重要的变化值得关注,那就是从功能到审美的、从一元标准化到多元个性化、从技术理性走向人文价值的转变,并指出“人性化的设计诗学乃是当代设计发展的必然逻辑”[3]周宪:《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3-242页。。这些趋向和变化,显然是人们在文化遗产的继承转化中应当给予关注并作为设计实践的重要考量。当设计诗学所需要汲取和展现的人文内涵,正是丰厚的文化遗产所能够提供时,我们必须以当代视野与精神诉求对文化遗产进行披沙炼金、去粗取精的萃取,以现代设计语言重构传统文化元素。这是再造传统文化、实现时代价值的前提,也是构建当代中国本土设计语言的基础。唯有如此,才能为当代世界文明创造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三、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新实践
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利用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关涉的领域和行业也格外广泛。从宏观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实践探索主要有整体性(综合性)项目、单一行业、跨界融合以及元素利用等类型,并在继承创新过程中突出文化心理延续、哲学思想传承、传统与现代融合、本土与世界衔接、自然与人文平衡等,尤其是探索文化基因传承与再生之方法和理念,积累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整体性转化:让传统营造穿越历史。中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建筑文化遗产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在世界建筑中独树一帜,而且区域特征鲜明且风格多样,但这类遗产也是现代化建设中受到冲击和损害最多的。过伟敏先生提出城市历史地段景观艺术设计的4个原则:即保持历史连续性、保持空间连续性、重视传统心理的延续和保护、注重景观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4]过伟敏主编:《建筑艺术遗产保护与利用》,〔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从建筑本体的历史、空间,到与建筑相关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进行系统、综合的保护理念,对于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包括福建土楼、厦门鼓浪屿、杭州南宋御街等在内,都是实践这一保护理念的成功案例。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澍则从中国绘画、江南园林设计中领悟精髓、撷取元素,他认为园林是“作为文人之间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因而造园“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5]王澍:《造房子》,〔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7页。。他创造性地将这些元素与乡村民居的建造相结合,以现代建筑设计语言,设计出象山校区专家接待中心“水岸山居”,实现在历史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穿越和衔接,实践了他构建中国本土建筑设计体系的构想。
行业性转换:道器合一的新中式。相形于传统建筑文化,古代家具文化遗产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直接体现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活理念和美学追求,而其中所蕴含与积累的丰富美学内涵,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的人居美学的精神养料。为此,众多设计师力图从古典家具中汲取美学养分,从事新中式、轻中式等各种原创当代中国家具品牌设计。古典明式家具因其熔铸了古代工匠和文人艺术家的设计智慧和美学追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不仅为世界各地博物馆所收藏,也为世界各国收藏家所青睐,甚至还成为当代著名设计师的创意灵感来源。中国当代设计师更是将明式家具作为创造当代新中式家具风格、打造相关品牌的重要摹本。这个过程艰难而曲折,许多转化和创新都是在历经挫折和失败后逐步为人们所首肯,即便是少数成功的设计也有待时日才能获得众人的欣赏和接受。设计师古奇创建的梵几品牌,从明式家具中汲取简约、静穆的美学基因,形成以明式家具为主要形态、融合日式与北欧风格的“轻中式”家具。正如陈仁毅所总结的明式家具八个核心价值之一“由安定、安静到心境过渡的文化内涵”,体现“中国家具文化中特有的‘道’‘器’合一的哲学观”[1]陈仁毅:《中国当代家具设计——从文化鉴赏到春在创新》,〔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准确把握了明式家具重要内涵一样,设计师古奇也力图传递这种精神内涵,但又灌注了自身的理解、感悟与处理方式。他将安定、安静的明式家具内涵加以转换,形成具有禅意的空灵美感,而“生长于野,安于室”的品牌诉求,则表达了对自然美的向往以及与现实之间“平衡”的价值追求。当然,不论“新中式”还是“轻中式”,其外在形态的不断美化与内在品位的逐步提升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完善,创造性转化仍在路上,也永远在路上。明式家具历经几百年才达到一种深厚永恒的美学境界,继承这些优秀的设计基因应成为中国大多数设计师的使命,同时也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接纳世界各个文明体系中的精华,创造出属于当代中国的本土设计语言与设计品牌。
跨界融合:传递内在精神的再生。源于中国本土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是一种简单的源于遗产本身的保护与利用(当然这种保护是基础和前提),甚至不是一个传统行业(非遗)的保护和利用,而是借助现代设计理念、方式、手段去提取其中的元素,包括传统造物中的符号、工艺、方法等,并根据当代生活需求,在行业自身之中以及超越行业的跨界融合中,重新创造系列的现代产品,以真正做到优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设计师张雷在杭州余杭区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的地方,与他的团队们确立了让设计回归乡土这一“还乡”概念,摒弃以往只是单纯地改良传统工艺项目的做法,在对余杭区传统工艺的深入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解构和创造。这就摆脱了沿着传统造物遗产的基本形制去进行设计的浅层次转化,而是深入到传统造物材料制作的方法与理念层面,试图传递古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环保生态的造物精神,通过材料制作的本土性达到接续传统与现代的全新设计效果。“品物流行”品牌的设计师们借助“研究、探索不同的材料,最终创造出尊重传统(应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却又颠覆传统(对传统材料和工艺进行溶解和重新组合)的设计作品”[2]沈婷、郭大泽编著:《文创品牌的秘密》,〔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第143页。。在笔者看来,这种传承方式,显然十分有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植入传统工艺的设计基因乃至设计精神,不仅更能产生创造性的设计作品,而且能在更深刻层面实现传统工艺的新生,体现出我们民族对于造物的独特理念与方式。中国民间传统竹编工艺源远流长、技艺精湛,不仅被中国设计师运用于现代日用工艺品品牌“绿竹翁”的系列产品设计,而且被国际品牌爱马仕子品牌“上下”运用于薄胎茶器之中,但“品物流行”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考虑传统竹编工艺的直接转化与创新,而是从材料学入手对竹材料进行全面的解构——将其分解为竹片、竹竿、竹板、竹皮、竹丝、竹纸和竹纤维七种状态逐一进行手工艺的研究和解构,再将解构出来的材料做成实际的样品。设计师则在这种源于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原材料基础上进行产品设计。因此,从新设计的产品形态上来看,全然没有古代造物的影子了,但其材质及其制作方式则均是源于传统的,是传统的转世投胎与再生。在这里,“尊重传统是尊重传统工艺的制作方式,尊重传统对自然敬重的精神。颠覆的是一种语言,一种表面的设计语言。我们要求设计师所做的作品,在语言、功能、视觉上都非常的当代,但制作工艺非常古老,或者采用一种非常边缘的简单工艺”[3]沈婷、郭大泽编著:《文创品牌的秘密》,〔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第143页。。这种具有创造性的传承方式,事实上已经深入到传统工艺的原始基因之中,并对这种基因进行重组和再创造,始于传统、立足当代,摒弃形制、注重精神,不仅使传统获得新的活力,而且将古老的传统以极具可塑性的方式向世界开放。鉴于“竹”在中国文化审美系统中的独特象征意味,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也创造性运用了竹片作屋顶装饰,除了以此向中国传统的抬梁式木构架屋顶致敬,建筑设计师还力图“通过建构研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哲学和精神层面上概括地表达中国的文化,而不是以具象的形式、符号、颜色等来对中国文化进行简单的描绘”[1]李丽编著:《木艺建筑——创意木结构》,〔南京〕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而王澍为威尼斯第四届国际建筑展双年展设计的中国馆,以一种极具观念性的简练表达,用来自江南民间的小青瓦建造了一个全新意识的园林——瓦园,试图唤起城市人的文化乡愁,其中支撑瓦片的框架也是由竹竿构筑的,简约而鲜明地传递了中国传统营造在材料和方式的上的独特技艺[2]王澍:《造房子》,〔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这些设计无疑都异曲同工地以内在精神的传统接续代替外在形式的传承,成为一种具有深度传承文化遗产基因的现代设计创新思路。
不难看出,王澍、张雷等设计师的探索是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的,能够既激活传统又使之重获新生并走向未来。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毅力、恒心,更需要工匠精神。很显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不论是哪一类型的实践,都必须在一个更深刻层面去理解和继承古代先辈们最可宝贵的财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远比形式、美学、技艺等的传承更为根本和本质的历史遗产。任何杰出的古代造物都是聪明才智与高超技艺结合的产物,也是一丝不苟、精工细作精神的体现。凡是杰出的造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精致”。“‘精致’,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气质,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可以多元发展的包容。因为只有充满‘精致’,才能够创造出更多不平凡的设计经典,也只有‘精致’,才可以支持一个人文辉煌的时代!”[3]陈仁毅:《中国当代家具设计——从文化鉴赏到春在创新》,〔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
此外,传统文化元素利用也是重要的实践类型。这方面西方当代世界名品的设计以善于利用各民族文化元素而赢得世界消费者青睐的经验,可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爱马仕的丝巾设计可谓创意迭出、精美无比,堪称当代丝绸美术设计的高端产品。爱马仕丝巾在工艺方面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有独特的手工技艺,其卷边工艺堪称一绝;但更令消费者青睐的是其美轮美奂的图案设计和色彩呈现。爱马仕丝巾的设计可视为一场艺术活动: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提炼和汲取元素。爱马仕经常邀请艺术家把丝巾作为画布进行创作,让丝巾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艺术元素。小小方巾承载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元素,无怪乎有那么多消费者愿意购买价格不菲的爱马仕丝巾。
结 语
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理念、新方法,呼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丰富精神食粮的新期待,顺应当代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和展示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传统、当代和未来的关系;要立足新时代,不断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方式,不断推动反映伟大时代的当代文化创造,创新文化内容表现方式,广泛运用新材料新工艺拓展传统造物文化,让中国创造携带中国文化元素、中国价值观乃至中国生活方式,成为令世人喜爱、全球推崇的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