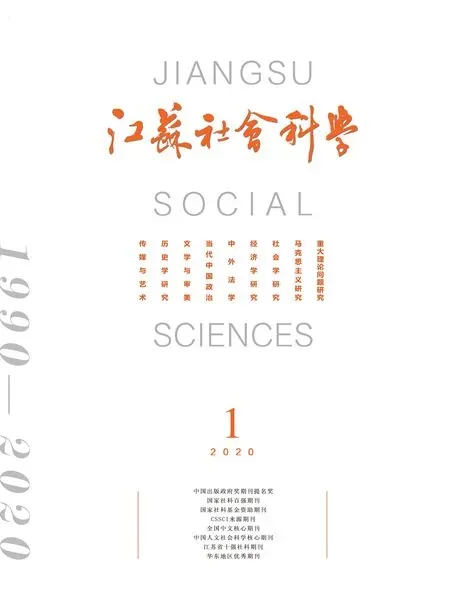阿尔都塞:社会再生产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装置
——以阿尔都塞《论再生产》为中心
张一兵
内容提要 在《论再生产》等论著中,阿尔都塞针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客观要求,新选取了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非物质条件视角,重点考察了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入门资格以及臣服于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意识形态教化机制,进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以现实存在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非强制国家装置。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成功地掩盖起自己的统治意图,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为它提供的“盾牌”后面,保障了社会再生产。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物性实践使相应的机构得以生成,而不是相反。直接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是原初的、基始性的意识形态赋型,不同于次生的意识形态。这种以家庭、学校和宗教等建构起来的非暴力意识形态装置,通过日常生活可以践行的物质活动,起到了比暴力性的国家机器重要得多的支配和控制作用。
再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也是阿尔都塞《论再生产》[1]1969年3—4月,阿尔都塞计划写一部两卷本的理论著作,第一卷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二卷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其中,《论再生产》(Sur la reproduction)是该计划的第一卷(计划中的第二卷并没有完成)。《论再生产》作为阿尔都塞最重要的遗稿之一,由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根据保存于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的两份手稿整理而编辑成书,1995年10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2011年10月被收入“今日马克思:交锋”丛书再版。此书的中译本由吴子枫翻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一书的主要讨论对象。针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客观要求,他新选取了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非物质条件视角,重点考察了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入门资格及臣服于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意识形态教化机制,进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意识形态国家装置。这种以家庭、学校和宗教等建构起来的非暴力意识形态装置,通过日常生活可以践行的物质活动,起到了比暴力性的国家机器重要得多的支配和控制作用。
一、劳动力再生产的非物质条件和资格
阿尔都塞说,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方式的分析,除了有物质生产方面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再生产。在马克思那里,这被称为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即“一种社会赋型如果在进行生产的同时不对生产的条件进行再生产,它连一年也维持不下去”[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第126页。。这是对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式中,第二个构序环节就是再生产,在那里,马克思将其指认为“生产”之后的“第二个事实”[2]〔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阿尔都塞让我们注意,马克思这里所突出指认的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es condi⁃tions de la production)。如果说,“生产过程就在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使生产力发挥作用”,那么,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就会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首先是生产力中劳动力的再生产。除去大家都知道的生产资料再生产的可见必要性,在这里,阿尔都塞重点讨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de la force de travail)问题。并且,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得到过比较详细的讨论,比如劳动力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最低保障,这也是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的直接原因。但是,阿尔都塞自己想格外强调的方面却是一个新的方面,即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再生产的非物质条件问题。他说:
事实上,为了使劳动力作为劳动力被再生产出来,仅仅保障其再生产的物质(matéri⁃elles)条件还不够。我们已经说过,后备劳动力必须是“有能力”(compétente)的,也就是说,适合在生产过程的复杂体系(système complexe)内从事工作,即在限定的劳动岗位和合作形式下从事工作。[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第126页。
这有两个方面的深刻含义:一是阿尔都塞反对将生产力中的三个方面视为抽象的对象,劳动力不是劳动者的肉身,而是他“有能力”的功能状态,即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劳作能力和工艺水平;二是揭示了一个新出现的情况,即劳动力与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关系。在阿尔都塞看来,与传统社会中的物质生产不同,甚至与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工人也不同,面对现代性机器体系和工业流水线构成的复杂生活系统,完全没有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工人是很难适应的。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讲,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一定时期由生产力历史地构成的统一体类型(type d'unité historique⁃ment constitutif),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劳动力必须(在不同的方面)是有资格的(qualifiée),并因此要以这种要求得到再生产。所谓“不同的方面”,是根据劳动的社会-技术(socialetechnique)分工的要求,对于不同“岗位”和“职业”来说的。[4]〔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6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Louis Althusser,Sur la reproduc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77。
其实,阿尔都塞在不指名地批评马克思,因为在《资本论》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讨论中,马克思没有具体分析今天资本主义新型社会技术分工中技术工人的非物质条件问题。阿尔都塞的批评并不成立:如同阿尔都塞不可能知道在他的“后天”中后工业资本主义信息产业出现的编程劳动者的非物质条件(“数字劳动”)一样,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是,阿尔都塞的提醒是对的。不同生产力水平之上,会有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再生产样态。在这里,他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再生产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再生产的差异性来说明这一观点。阿尔都塞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多样化的)的资格(qualification)的再生产怎样获得保障的呢?与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社会赋型(formations sociales esclavagistes et servagistes)中所发生的情况不同,上述的劳动力资格(qualification de la force de travail)的再生产,倾向于(这涉及某种倾向性规律)不再(在生产本身的学徒期中)“在现场”(sur le tas)而得到保障,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生产之外,通过资本主义的学校系统(système scolaire)以及其他层级和机构来实现。[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6 页,第128 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Louis Althusser,Sur la reproduc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77,p.78。
这是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可能很少会出现劳动力的生产资格(技术能力)问题,只要有体力,就能从事农活和其他体力劳动;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就会有一个是否能够胜任和完成生产任务的资格问题。并且,拉犁和打铁一类生产活动的技能的获得,通常是劳动力跟着师傅在田间地头和工场内部边干边学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资格,却是由学校系统专门培训的。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阿尔都塞讨论生产力的再生产,最后还是为了引出自己想重点讨论的核心问题——资产阶级利用教育和其他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作用问题。这里有一处不够精准的地方是,在斯密写《国富论》时面对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大部分劳动力的技能,还是在工场现场由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劳动力要通过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培训获得技术和生产资格,则是后来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其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这是《论再生产》一书的真正主题。阿尔都塞告诉我们:一方面,未来的“工人”在学校中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以获得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劳动力的资格;另一方面,还要被“内心的道德律令”(康德语)规训成为顺从者。其实,这正是让劳动者从一开始就认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合法性。这是资本主义奴役性生产关系再生产中最重要的内在保证。他说:
人们在学校还要学习良好的举止“规范”(règles),也就是说,学习劳动分工中的所有当事人依照他们“命定”(destiné)要占据的岗位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职业的首先规范和职业的良知规范;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关于尊重(respect)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说到底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l'ordre établi par la domination de classe)的规范。[2]〔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6 页,第128 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Louis Althusser,Sur la reproduc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77,p.78。
显而易见,这里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非物质条件,已经不是指与科学技术对象化为机器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知识和技术“资格”了,而是让劳动者成为进入自己命中注定的被剥削的岗位中,顺从地遵守自己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规范。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中劳动力进入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依阿尔都塞的判断,这一切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化规训,也是在资产阶级学校教育中进行的。
实际上,在学校教育中,还发生着一件可怕的事情,即资本家奴仆的规训。这一点与劳动力的非物质条件的教化是同步的。阿尔都塞说,工人接受生产技能和规训式的奴化教育,而另一些人则被训练成技术人员、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要“学习正确地‘管理工人’,实际上也就是说,(作为未来的资本家及其奴仆)学习‘恰当地使唤’(biencommander)他们”[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页。。阿尔都塞没有直接说到的是,布尔迪厄[4]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年),当代法国社会学家,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1953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1964年起任巴黎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社会学教授,1968年起接任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198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论著有:《继承人:学生和文化》(Les Héritiers.Les Etudiants et la Culture,Minu⁃it,1964)、《再生产:谈论一种关于教育体系的理论》(La Reproduction.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Minuit,1970)、《实践理论大纲》(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Droz,1972)、《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Minuit,1980)、《学术人》(Homo academicus,Minuit,1984)、《国家精英:高等学院和群体之精神》(La Noblesse d'État.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Minuit,1989)等。已经在研究资产阶级本身的接班人再生产问题。在《再生产》(La Reproduction,1970)和《国家精神》(La Noblesse d’Etat,1989)等论著中,布尔迪厄已经揭露了法国精英大学的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等级化再生产机制。
阿尔都塞分析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思想关口,即发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再生产中马克思没有充分讨论的第二方面的内容:
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资格(qualification),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遵守既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soumission à l'idéologie dominante),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有当事人再生产而出色地操纵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capacité à bien manier l'idéologie domi⁃nante),以便他们能“用词句”来保障统治阶级的统治。[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129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Louis Althusser,Sur la reproduc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78。
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非物质条件,当然首要的是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过程的资格,即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此外,阿尔都塞特别点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非物质条件中的关键,即培养无产阶级的奴化意识,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服从。同时,关键点还涉及资产阶级的新型奴仆们(工程师和经理)的再生产,他们是出色地操纵意识形态装置的专家。
最后,阿尔都塞终于不再绕圈子,他直接说,这里已经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现实:意识形态”[2]〔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页。(nouvelle réalité:l'idéologie)。这里的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中那种“上层建筑”中的观念体系,它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这就是阿尔都塞自己的新观点了。他形象地说:
所有那些从事生产、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更不用说那些“职业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语),为了要恪尽职守地(且不需要有一个宪兵跟在屁股后进行督促)完成他们的工作,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浸染”(pénétrés)在那种意识形态当中。无论他们是被剥削者(无产者)、剥削者(资本家)、剥削者的助手(auxiliaires,管理者),还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大祭司(grands prêtres,它的“官员”)等等,都是如此。[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129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Louis Althusser,Sur la reproduc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78。
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一是在生产与再生产中从事阶级镇压的人,并不一定是宪兵,而也可能是资本家的帮凶——工程师和经理,二是在生产中的劳动者、剥削者和他们的奴仆,都浸染在意识形态的现实之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的现实?它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这就是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一书中主要想讨论的东西了。
二、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
1969年,阿尔都塞从正在写作的《论再生产》手稿中精心摘要组合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Idéologie et Appareils[4]在这里,阿尔都塞没有使用法文中通常表达机器的machine一词,转而选取了福柯等人表达结构性功能的appar⁃eil。在中文翻译中,appareil概念大多被译为“机器”。可是,从appareil一词在福柯之后的后马克思思潮中的历史语境中,准确地构境之意应该是装置。我在这里区分性地保留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译法。Idéologiques d'Etat)一文[5]在《思想》杂志的编辑秘书马塞尔·科尔尼的鼓动下,阿尔都塞决定将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中的一些东西公之于众,他从这部手稿中抽出一些片段,组成了著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一文,发表在1970年6月《思想》杂志第151期上,并引起巨大反响。《论再生产》一书的编者雅克·比岱发现,这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是阿尔都塞从此手稿的第3章(“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第4章(“基础和上层建筑”)、第6章(“国家和国家装置”)、第9章(“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第12章(“论意识形态”)的摘要中选取组成的。。而正是这一文本使阿尔都塞的理论影响第一次超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依巴利巴尔的说法,
我认为可以说,这个文本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要描绘他的思想特征就必须参考的文本之一;是使用了烙有他自己名字“印记”因而可被直接辨认出来的那些概念的文本之一(在这里是“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意识形态质询”,在别处是“认识论断裂”“症状阅读”等等);最后,它铭刻进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继传统中,成为当代哲学仍在继续研究的文本之一。[1]〔法〕巴利巴尔:《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法文版序),〔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巴利巴尔的这一评价基本上是准确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一文发表之后,这一文本立刻成为阿尔都塞继《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之后最重要的经典文献,在不少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前所述,阿尔都塞现在更换了一个角度切入意识形态这一他始终关注的主题,这个新的角度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他认同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每一种社会赋型(formation)为了存在,必须在它生产的同时再生产它的生产条件,这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中,阿尔都塞更关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非物质条件问题。这个非物质条件,除了包括大机器生产所要求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劳动者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顺从。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是资产阶级统治关系再生产的绝对必要条件。现在,他更关心这一“自觉顺从”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发生的。后来,阿尔都塞对此做过一个重要补充,他将资产阶级统治的再生产看作一个整体。他说:“统治阶级必须生产它的存在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存在就意味着再生产)。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可并非单纯的复制,并非简单再生产,甚至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其自身功能确定下来的既有机构的自动的、机械的扩大再生产,它毋宁是一种斗争,争取让早先的、散碎而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在一整体中统一并复兴起来——而这个整体恰恰是通过对先前意识形态形式和新意识形态趋向的阶级斗争才得来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这场斗争是场永无完结的斗争,总是不断重新开始,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于阶级斗争。”[2]〔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装置(AIE)的说明》,孟迎登、赵文译,《美术馆》总第12 期,上海书店2008年版。
与以前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说的侧重点不同,他不再一般性地讨论与科学相对立的社会再现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探讨了作为统治工具——国家装置(l'appareil d'État)中的意识形态。依上面的讨论,阿尔都塞有些夸张地说,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保障条件中出现的新的现实。这也是齐泽克所说的从自在的意识形态(无意识观念体系)到自为的意识形态(自主国家意志)的转变。在前者中,关注的重心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自发运作机制;而在后者中,关注点则开始聚焦于国家自主地隐性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微观机制。从阿尔都塞这里的具体研究内容上可以判断,这又更集中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解析。他洋洋得意地自认为,他的作为社会新现实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后来简写为A.I.E.)的概念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补充了某些别的东西[3]〔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3页。。阿尔都塞自己专门解释道,“我们冒着理论风险把这种现实叫作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因此,理论干预的准确部位,在于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意义上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差别”[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页,第135页,第174页。。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在实践中意识到了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可是他们并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相应的理论阐述。
当然,阿尔都塞表面上认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他说,“把每个社会的结构说成为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基础,在它上面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这是一个隐喻。具体地说,这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即表示地形图(topique)的隐喻”[2]〔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57页。〔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页。。这个地形图的隐喻后来在杰姆逊等人那里得到进一步扩展延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全球化语境中发展出一种空间图绘哲学来。这两层建筑的内涵又有什么不同?一是政治法律及其附属物(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这通常被认作为一定社会统治中的国家机器[3]阿尔都塞后来对这个“镇压性国家机器”专门做过说明,他说,“(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整体即便是充满矛盾的,也仍旧要比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总体强大得多,那么(镇压性)国家机器是由什么构成的?国家机器包括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执行的工具)、军队、警察、司法系统、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监狱等)”。〔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装置(AIE)的说明》,孟迎登、赵文译,《美术馆》总第12期,上海书店2008年版。;二是整个观念性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真实想法是要突破马克思的这个外在化的隐喻。他说,“用大厦的空间隐喻来表述任何社会结构的重大缺陷在于:它显然是隐喻性的,也就是说,它仍然是描述性的”[4]〔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页,第135页,第174页。。在他这种吞吞吐吐说法中,“描述性”就带有非科学的性质。
阿尔都塞要辨识的是,被马克思描述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种观念形态,它也是一种国家装置,然而,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不同,后者是一种看不见直接暴力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对此,巴利巴尔曾经这样评论说,“他的灵感是极端-列宁主义的(ultra-léniniste),因为他并不满足于把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目标定义为‘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而是要把‘国家机器’一分为二,以便能把‘意识形态的统治’和以‘国家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表述和实践的隐性的集中化包括进来”[5]〔法〕巴利巴尔:《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吴子枫译,〔上海〕《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这与阿尔都塞先前的观念有所区别,在他看来,现在他眼中的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以现实存在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非强制国家装置。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是一些以独特和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现实”[6]〔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4页。。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阿尔都塞想着重说明,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本质恰恰在于成功地掩盖起自己的统治意图,让被统治者真的相信,阶级统治不是奴役而是合法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和自由又是通过法理来实现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就是它以一种特殊方式隐瞒阶级剥削,以致任何阶级统治的痕迹都系统地从它的语言中消失了。事实是,它本身的状况不允许任何意识形态以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出现。”[7]〔希腊〕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这是一种新历史宣判,它一把撕去了韦伯以来资产阶级法理统治的合法性面具。所以结论是,“正是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为它提供的‘盾牌’后面,保障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本身”[8]〔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页,第135页,第174页。。
三、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现实物化和实践
阿尔都塞后来承认,他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理论是“追随葛兰西”的结果,这个被称为“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东西,它指的是一整套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道德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掌握权力的阶级运用这些机构,在统一自身的同时,也成功地把它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被剥削群众,使之成为后者自己的意识形态”[1]〔法〕阿尔都塞:《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这也就是说,被指认为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包括: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各种教会体系)、教育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各种公私立的“学校”体系)、家庭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法律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包括各种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制)、工会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传播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出版、广播和电视行业等)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文学、艺术和体育等)[2]〔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第175页,第174页,第177页。。
阿尔都塞说,他这里指认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以下简称A.I.E.)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每一种A.I.E.相对应的是一些我们称作‘机构’和‘组织’(«institutions»ou«organisations»)的东西”。比如教育的A.I.E.,就会有不同层次的学校构成;政治的A.I.E.,就会有议会和政党;传播的A.I.E.,就会有报纸、广播和电视系统等等来支撑。二是“构成每一种A.I.E.的不同机构和组织都形成一个系统(système)”。它发生意识形态的作用,都不会是一个独立的现象。三是所有都不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层建筑,而是有着“真实物质支撑”(supportréel et matériel)的对象性客观现实存在[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 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第175页,第174页,第177页。。这第三点,是阿尔都塞特别突出强调的方面。在他看来,
存在于每种A.I.E.中的那些机构,它们的系统,从而每种A.I.E.本身,尽管被定义为是意识形态的,但都不能化约为没有真实物质支撑的“观念的”(d'idées)存在。我这样说的意思不仅仅是说A.I.E.的意识形态是在物质机构和物质实践(des institutions matérielles et des pra⁃tiques matérielles)中实现的,因为这很明显。我这样说有另一层意思,即那些物质实践“扎根”于非意识形态的现实(réalités non-idéologiques)中。[4]〔法〕阿尔 都 塞:《论 再生 产》,吴子 枫译,〔西安〕西北 大学 出版 社2019年版,第174页,第175页,第174页,第177页。
阿尔都塞这里想表明,他所指认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不再像原来马克思、曼海姆以及阿尔都塞自己曾经讨论的虚假的观念形态,它已经在双重构式中成为社会现实:一是所有的A.I.E.都有支撑着它存在的客观物质附属物,比如教育所依托的学校、宗教所依托的教堂等;二是所有A.I.E.发挥现实的意识形态支配作用,都会使自己对象化为非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中。这后一点是说,A.I.E.是一种在每时每刻在日常生活中物化的客观实践。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就是资产阶级市场最基础的经济实践的“消费单位”(unité de consommation)。所以,阿尔都塞明确说:
一种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就是一个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各种机构、组织和实践(pratiques)中得以实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或一部分(通常是某些要素的典型组合,combinaison typique)。在一种A.I.E.中实现了的意识形态,保障着这种A.I.E.的系统的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就在于,这种意识形态“扎根”于每种A.I.E.所固有的种种物质功能(fonctions matérielles)中。那些物质功能虽然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撑”(support),却不能化约为这种意识形态。[5]〔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第175页,第174页,第177页。
这段表述,在原文中全部使用了斜体,这恐怕是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一书中很少出现的文本现象。我推测,应该是阿尔都塞觉得这是自己此书中比较重要的原创性观点。这里的关键词,一是实践,二是物质功能,可以看出,阿尔都塞这一次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不是简单地指认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域或者类型,而是关注意识形态发挥阶级支配、镇压和统治的客观作用。这就使整个马克思-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研究传统,从观念形态第一次转向了现实生活,意识形态也有可能以社会物质生活的方式支配人。
当然,阿尔都塞也提醒我们,指认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实践和物质功能,并不是要把意识形态归属于那些可见的物性机构。阿尔都塞说,其实在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解释框架中,我们也发现有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表述,即“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机构”(l'idologie et des institutionsqui lui corre⁃spondent)[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83 页,第184-185 页,第178页。。他肯定这个说法,“不是那些机构‘生产’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一些要素‘实现于’(se réalisent dans)或‘存在于’(existent dans)相应的机构和它们的实践中”[2]〔法〕阿尔 都塞:《论 再生产》,吴子枫 译,〔西安〕西 北大学 出版社2019 年版,第183 页,第184-185 页,第178页。。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物性实践使相应的机构得以生成,而不是相反。
由此,阿尔都塞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作为原初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与亚意识形态的区别。他说:
必须把实现于并存在一定装置及其实践中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那些确定要素(élémen⁃ts déterminés)与在这个装置内部由其实践“生产”(produite)出来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为了在语言上标出这种区分,我们将第一种意识形态称为原初意识形态(première Idéologie),把第二种意识形态,初级意识形态在其中得以实现的实践的副产品,称为次级的、从属的意识形态(l'idéologie secondaire,subordonnée)。[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Louis Althusser,Sur la reproduc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114。
那些直接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是原初的、基始性的意识形态赋型,而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运行活动中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是次生的意识形态。比如,学校是国家意识形态装置,它属于原初的培养资产阶级统治接班人或者技工劳动者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型,而在学校中的教育实践中生产出来的具体一所学校的教育活动和观念,如哈佛精神和剑桥办学理念,则已经是次生的、从属于原初意识形态的东西。
四、暴力国家机器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
阿尔都塞自己解释说,之所以提出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以区别于暴力性的国家机器,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首先,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与镇压性国家机器不同,后者只有一个,而前者则为数众多,所以,“国家机器(l'Appareil d'Etat)是单数的(singulier),而我们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是复数的(pluriel)”[4]〔法〕阿尔都塞:《论再生 产》,吴 子枫译,〔西安〕西北 大学出版 社2019 年版,第183 页,第184-185 页,第178页。。其次,警察、军队等暴力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绝大多数却散布于私人领域,这是两种国家装置在发生作用领域上的不同。最后,更重要的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是‘以暴力方式’来产生作用,而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则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产生作用’”[5]〔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5页。。这是一种功能作用上的异质性。这一点,也是阿尔都塞想重点强调的差异性。也可以说,在《论再生产》和他1969年专门摘编出来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一文中,阿尔都塞所探讨的主要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的功能运作。
镇压性国家机器按照定义是一种间接或直接使用肉体暴力(violence physique)的镇压性机器,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只有在“国家装置”的意义上才能说是镇压性的,因为按照定义它们不使用肉体暴力。教会、学校、政党、新闻报刊、广播-电视、出版、各种演出、体育运动等等,在其“主顾”(clientèle)看来,都不诉诸肉体暴力而发挥作用,至少不以占统治地位的和显性可见的(dominante et visible)方式诉诸肉体暴力。[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8-179页,第192页。
当然,与可见的警察-军队镇压导致的直接肉体暴力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是“大量地和主要地以意识形态方式来产生作用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比如人们自由地去学校上学,周末到教堂参加弥撒,下班顺便买一份报纸,晚上饭后打开电视,与家人去电影院看电影,在街上看到不同的广告,阅读各种书籍,等等,意识形态国家装置都悄悄地发生自己的支配和统治作用。可是,这并不排除它也常常辅之以一定的镇压。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直接暴力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即使有镇压,“也是非常微弱的和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根本没有纯意识形态的装置这样的东西)”[2]〔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6页。。应该说,这与葛兰西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性。比岱曾经这样比较过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他说,“在这方面阿尔都塞的灵感部分来自葛兰西,后者用‘市民社会’(它与‘政治社会’相对,也就是说,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相对)这个名称来指那些(私人的和公共的)机构的整体,领导阶级的‘霸权’(该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就是通过那些机构得以实现的。但是葛兰西给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赋予了世界观、知识、文化和伦理上的宽泛意义,他认为市民社会也是正在上升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展开进步斗争的阵地,因此革命过程本身就类似于对领导权的夺取。这样看来,阿尔都塞倒转了上述理解,他把所有的机构阐释为国家装置的组成部分,而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国家装置来保障自己的统治的”[3]〔法〕比岱:《请你重读阿尔都塞——〈论再生产〉代序》,吴子枫译,〔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6期。。比如,学校和教会使用适当的惩罚、开除、选拔办法来“‘规范’它们的牧人和羊群,使它们服从纪律”,文化意识形态则通过书报检查制度实现这一功能。阿尔都塞还提醒我们注意:
在所有国家装置(无论这些机器首先是镇压性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当中以及在它们之间,镇压和意识形态化之间建立了一些非常微妙的或心照不宣的结合形式(subtiles combi⁃naisons);而这些非常微妙的结合形式(如果我们对其机制进行分析的话),可以说明在各种各样的国家装置之间建立的那些明显的契约关系和明确的(或甚至暧昧的)客观共谋(com⁃plicités objectives)关系。[4]〔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8-179页,第192页。
这是说,在统治阶级的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谋关系:意识形态装置是暴力机器的帮手;在意识形态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暴力性的镇压也会在场。
有意思的是,阿尔都塞这里的讨论直接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相对接了,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的作用机制被直指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合法统治而行使的文化霸权(hegemony)。在阿尔都塞看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就是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的传播(通过对文化的介绍和反复灌输)获得群众的同意”[5]〔法〕阿尔都塞:《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阿尔都塞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阶级若不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并在其中行使其文化霸权,就不能长时期掌握国家权力”[6]〔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7页。阿尔都塞自己说,“葛兰西是在我走的这条道路上走过一段距离的唯一的一人。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想法,即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而是像他所说的国家是包含有若干‘市民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遗憾的是,葛兰西并没有把他的思想系统化,它们停留在一种尖锐地然而零散的评论的状态中”。参见〔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04页注7。。阿尔都塞自己并没有专门论述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关系,可在他对这两个范畴的具体运用中,我觉得意识形态恰好是建构和维护文化霸权的重要途径。
阿尔都塞也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发挥作用的形式和机制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的数目较少,如在封建社会中主要是教会和家庭,而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原来教会和家庭的意识形态职能转移到其他众多新兴的意识形态形式之中,其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教育的意识形态装置。阿尔都塞认为,正是通过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所有孩子从小到大学习“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一些确定的本领,资本主义社会赋型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关系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才真正被再生产出来”[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页,第292页,第293页。。这也意味着,在阿尔都塞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中,教育的意识形态装置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觉得强调得不够:
我要说,造成这个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结果的机制,自然被一种普遍盛行的关于学校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de l'Ecole universellement régnante)掩盖和隐瞒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为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表述为没有意识形态的中立环境(milieu neutre,因为它是……世俗的)。[2]〔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页,第292页,第293页。
这一点是对的。阿尔都塞已经发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往往是被指认为价值中立的地方。这正是韦伯所确认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所谓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公开声称自己是价值中立的地方,恰恰是意识形态遮蔽最严重的盲区。在阿尔都塞的眼里,学校里的老师“用自己的忠诚本身维护了对学校的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使今天的学校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显得那样‘自然’(naturelle)、必需,甚至有益,就像几个世纪前,对于我们的祷告来说,教会也是那样的‘自然’、必需、慷慨大度”[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页,第292页,第293页。。这是说,如同过去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教会在布展意识形态的时候,总是替天行道那般天然、神圣,而今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支配,也是通过不同的学校有类别地制造出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和劳动者的后来者,这一切也是如此地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