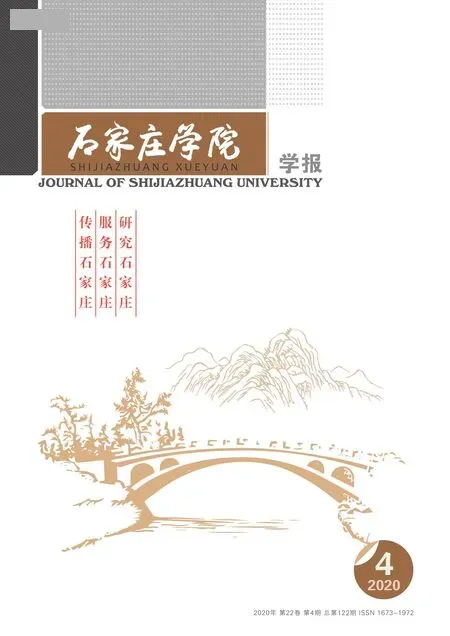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模式探析
孟英莲,彭淑庆
(1.齐鲁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2.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中国民间信仰与西方基督教是两种差异显著的宗教形态,二者分别根植于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系统。明末清初以降,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一直被贴上“洋教”标签而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排斥。特别在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的双重作用下,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在反洋教运动中展开激烈博弈,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
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突出表现为不断高涨的反洋教运动,近代反洋教运动群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一是下层民众。前者主要针对中西宗教的正邪辩论展开;后者则突破了文字辩论的范畴,借助民间宗教以暴力形式回击基督教对中国宗教传统的挑战。关于基督教与儒释道三教之比较研究,学界已有广泛深入的讨论,但对于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宗教比较少有专论。①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著相当多,其中通论性著作如杨森富著《中国风土与基督教信仰》,天启出版社1977年版;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年版;杜小安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华书局2010年版。本文以近代反洋教运动的发展为线索,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分析士大夫阶层和下层民众反洋教模式。
一、正邪之辨:近代士大夫阶层的反洋教思维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的佛道教以及祖先崇拜、民间神祗和各种信仰习俗发动了猛烈抨击,并撰写了大量宣教、护教文献。同时,一批儒士及佛教僧徒也撰写了大量“辟邪”“破邪”文献,对基督教予以严厉驳斥,其中尤以明末黄贞辑录的《破邪集》(又名《圣朝破邪集》)和清初杨光先《不得已》影响最大,这是中西宗教历史上第一次大辩论。论战双方均自视“圣教”,互斥对方为“邪”。正邪之辩是双方立论的根本宗旨和出发点。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庇护下强势向中国内地扩张,受到中国地方官绅民众的强烈抵制,双方由此展开历史上第二次论辩,并在19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反教高潮。近代士大夫阶层的论辩基本延续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首次碰撞时的“辟邪”思路,即将基督教视为邪教异端,同时还创作了大量反教文献,其中19世纪60年代初刊的《辟邪纪实》、19世纪90年代周汉所撰反教揭帖最具代表性。与明末清初相比,近代系统性的反教论著数量相对较少,但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反教文本不仅数量激增、流传甚广,而且抨击力度较明末清初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辟基督教创世说之虚妄
明末清初中西“礼仪之争”时期,封建士大夫阶层就针对“天主之有无”“万物之由来”“儒经中上帝与天主之不同”,对天主教的上帝创世说进行了一系列批驳。到了近代,反教文人们仍然对基督教“天主”之存在及其创世学说进行了严厉驳斥,论证基督教创世学说之“虚妄”。
其一,天主并不存在,乃中国上古“上帝”之托名。1861年刊布的《湖南合省公檄》云:“天一而已,以主宰言之,则曰上帝,乃变其名曰天主,即耶稣以实之。考<之>耶稣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不知元寿以前之天,果虚位以待耶?抑别有一人主之,如六朝之禅代耶?”[1]11862年刊布的《讨西洋教匪檄文》用儒家经典继续驳斥说:“洋人所供之天主,历代史书无所考,五经三传未曾闻,诸子百家亦不载……可见洋人所供之天主,乃肇造夷人之蛮子头,非肇造天地之人物也。”[1]79近代另一位反教人士林昌彝(1803-1876年)认为,《圣经》上对于耶稣神迹的记载不过和道教巫术类似,并无神奇之处,他说基督教:“然动割人肉,邪法也。又曾以七饼折为徒众三千人食,亦不过如道家搬运之术,其他别无功德,乃敢称为造天之主,谬谓天地民物皆为所造成者。”[1]407上述观点与明清之际的观点大体相同,认为“天”只有一个即儒家经典中所称的“上帝”,耶稣是一个凡人,而“天主”是洋人托名中国“上帝”虚构出来的。
既然“天主”并不存在,那么由此推理基督教的“创世说”也就不成立了。另一位反教文人王炳燮(1822-1879年)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一步批驳天主教的创世说之荒诞。他认为在洪荒开辟之初,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此对于当时的任何事情都无可稽考。“又自降生之岁至今年癸亥,为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不知西洋与中国同一天地乎?抑别一天地乎?使同一天地,则汉元帝时,中国已在近古,不知西洋何故直至此时才得天主降生?是耶稣之徒造此大谎,以神其说,使人无可质证,此之谓诬天。”[1]25王炳燮以中国历史为依据,认为《圣经》中有关“创世论”以及耶稣被“神化”纯为后来的信徒伪造。
综观近代反教文人对基督教“创世论”的批判,以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为标准,其内容、观点基本沿袭了明末清初风格,且带有明显的乾嘉考据遗风。同时,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十分浅显,多是在先入为主的思维下,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断章取义。针对中国人对上帝、天主之存在以及《圣经》与基督教历史的质疑,晚清传教士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解释与回应,他们以《圣经》为基准试图沟通中西神话历史的藩篱,竭力消除洋教的“他者”身份。
(二)维护祖先崇拜与正统神灵信仰
祖先及诸神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内涵,也是其与基督教信仰冲突的焦点。在民间信仰中,祖先被视为荫泽后世的神灵,祭祖是儒家提倡“慎终追远”的主要方式,也是民间敬拜“天地君亲师”的重要环节。不敬祖先、亵渎神灵是近代封建官绅和民众批判基督教的首要“罪状”。
1861年出现的《湖南合省公檄》列举了基督教“最恶而毒者十害”,其中第一条即“该教不敬祖宗及诸神灵”,入教时“必先毁其祖考神主,以示归心”[1]3。王炳燮也批判“耶稣不认其母,犬羊不如”,“灭绝祖宗,不如豺狼”[1]26-27,“夫四海之大,人物之众,王法所不及治者,幸有神道默助至教。今天主教抹去神道,使人心无忌惮,而惟彼教之是从,与诸邪教实出一辙,此其居心安可问乎?是欲鼓众,先以毁神”[1]26。王炳燮从儒家的神灵观出发,指出民间信仰对“神道设教”的重要作用,批判天主教亵渎神灵,与邪教无异。儒教卫道士们还试图以强制推行民间信仰的办法来防范和打击基督教在华传播,规定在每一县城设立防邪总局,并在各乡里设分局,“其局即就近地祠庙,不必另造”,“无论官绅士庶人家,堂中必设神龛,供天地君亲师五字牌及祖先神主”[1]100-101。同时,一些反教文人还认为,传教士一方面以反对偶像崇拜为名禁止教民供奉祖先木主和神灵牌位,而自己却供奉耶稣十字架,这是排斥打压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独断主义。
19世纪90年代,爆发了1891年长江流域教案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随着反洋教运动的高涨,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达到最高潮,其中尤以湖南士绅周汉的反教文本和华北地区流传义和团反教揭帖中最为典型。
周汉(1843-1911年),字铁真,湖南宁乡人,晚清著名的反教人士。他早年曾参加湘军,深受反洋教思想影响。1884年因病寄居省城长沙,参与宝善堂刊布善书活动。1889年开始刊刻一本朱墨套印的反洋教图册,题名《天猪教》。自此开始了以印制和散发宣传品为形式的反洋教斗争。1889年至1898年间,在其领导下散布的反教宣传品不下数百种,备受湖南士流推崇。这些揭贴就其内容而言均以“崇正黜邪”为主旨,以封建道统为根本,对“洋教”发动猛烈攻击,抵制外国侵略和基督教的渗透。
周汉在《防驱鬼教歌》中写到,基督教“其教不敬天地,祖宗牌位全无。扫灭圣贤仙佛,只拜耶稣一猪。邪鬼冒称上帝,罪该万剐千株”[1]204。近代士大夫阶层虽然尊崇儒教,对民间信仰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但他们仍然会利用民间信仰批判基督教。如周汉抨击基督教混淆基督教“上帝”和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玉帝”,诈称耶稣降生是“玉帝分了些神气投入闺女(指玛利亚)肚里”,亵渎祖宗神灵,号召民众阻止传教士入境,禁毁《圣经》。
周汉在用儒教抨击基督教的同时,对民间神灵信仰也进行了辩护。不过他所辩护的民间信仰神灵,仅是被列入祀典的“一切大小正神”,不包括民间的淫祀神灵。从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末,“辟邪崇正”的思维模式是中西宗教文化论辩的焦点。近代士大夫阶层以儒教卫道士的形象回击基督教的挑战,其主要文化策略就是振兴儒教,断言“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一日不绝,西国之教一日不行”[1]34。同时,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正统性认知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释、道二教既有维护也不乏诟病。至于对民间信仰的辩护,则更是仅限于少数所谓的正神信仰,民间信仰神灵系统中占多数的非正统神灵则不在被庇护范围之内。
二、神助灭洋:义和团的反洋教思维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状,处于下层的乡村社会占据绝对比重。尽管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宗教体系中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但乡村社会中真正的主体信仰是融合儒释道三教和原始巫教的民间信仰。因此当基督教深入中国内地乡村时,下层民众会本能地以他们所熟悉的民间信仰回应基督教所带来的挑战。
由于西方列强的对华不断侵略和晚清政府的对外软弱无能,近代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面对基督教的强势入侵时逐渐失去了国家政权的有力庇护。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教案事件的激增,清政府慑于列强与教会的威势以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制肘,被迫不断饬令地方官员加强对传教士的保护力度,压制官绅民众的反教斗争,并给予教会和传教士种种特权。在这种情形下,官员士大夫阶层逐渐退出了反教斗争前线,广大民众在民教冲突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只能从民间秘密结社及民间神灵信仰中寻求自卫。民族危机的加剧、民教积怨的累积以及晚清官、绅、民、洋、教之间不平衡的畸形关系,最终导致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一)义和团反洋教的神圣性来源
义和团运动是晚清反洋教运动的最高潮,也是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的巅峰。义和团的主体是华北下层民众,民族危机的刺激、艰难的生存处境和对现实利益的关注,促使义和团对基督教的态度不再局限于义理上的正邪之辩,而是直接借助民间诸神的名义进行灭洋斗争。
从义和团文献来看,基督教在华传播上干天怒,玉帝遣全神下界助义和团“扶清灭洋”,是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核心思维方式。神秘的民间宗教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是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思维逻辑下,义和团将其灭洋行为均视为“天意”“天谴”,宣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汝辈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2]14。在神的名义下,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洋教,而且扩延至所有外国列强以及所有洋人、洋物,斗争对象的扩大化既反映了民族危机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特征。
义和团“以狂热的宗教迷信的形式来表达‘杀洋灭教’的政治宗旨”[2]208-240,在义和团纲领性的重要揭帖《神助拳》中有很好的体现:“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2]34
该揭贴宣示了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宗教思想以及斗争对象、手段、目标,在华北各地流传甚广,并在民间传抄和口头传述过程中产生了多个版本。[3]124-127揭帖前四句批判基督教劝人只信天主,亵渎众神和祖先,灭绝人伦。这一点与明末清初以来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批判思维是一致的。第五至十句则反映了义和团独特的宗教思想:义和团将自然灾害(旱灾)视为天谴,并将责任归咎于“全是教堂止住天”,通过焚香、念咒、升黄表和降神附体等仪式请各洞神仙下凡协助灭洋。
从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可以看出,19世纪末遍及华北的旱灾是引发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导火索。1898年,黄河流域六省发生了大规模的持续干旱,不仅严重影响华北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大量的流民,而且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焦虑和恐慌心理。在这种紧张的心理状态下,人们迫切需要寻找精神的寄托和发泄的途径,而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长期的民教积怨使华北农民本能地将罪魁指向亵渎神灵的洋教。义和团对旱灾原因的认识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劫变”观念,将旱灾视为“天谴”和“世道将大乱”“大劫临头”的征兆。
在义和团看来,基督教不拜祖先、亵渎神灵是引发上天震怒、产生天谴(自然灾害)的元凶。义和团将教堂作为攻击的主要对象,认为上天震怒皆因洋人修建教堂所致。教堂是基督教的象征和传教士的据点,攻击、焚毁教堂成为晚清反洋教斗争最常见的形式。
晚清教堂一般只对教民开放,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宗教场所,尤其男女信徒共同参加宗教仪式,这与儒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相冲突,部分封建士大夫和民众从封建礼教、道家炼金术和民间巫蛊之术来理解传教士的行为,认为传教士打着劝人为善的幌子,实际却是摄人魂魄、采生折割、迷奸妇女的妖。在民众看来,教堂俨然成为传教士诲淫诲盗、藏污纳垢的邪恶之所。文化习俗的差异和误解极易使普通民众对于传教士和教民在教堂内的宗教活动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以致于谣言四布,引发暴力冲突。晚清重大的习俗教案,如1870年天津教案和1891年长江流域教案多由此类谣言引发。
教堂的塔尖式结构造成直冲云天的视觉冲击,高耸的教堂建筑伫立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与乡村破败的庙宇、低矮的民宅相比显得格外突兀。教堂的建筑气势与传教士、教民的跋扈行为相互映照,给普通民众的信仰心理造成双重的压抑感。义和团宣称“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就反映了人们对于教堂阻碍天人相通的愤恨情绪。传教士正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堂口不断向内地偏远地区渗透。因此,地方官、士绅和民众(尤其是后两者)对于传教士建立教堂一事普遍具有恐慌感,“教堂立,则洋教行;洋教行,则淫祸起”[1]161,因此他们往往竭力阻挠传教士置地建堂。
“庙堂之争”是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冲突的重要内容。寺庙宫观尤其是供奉乡土神灵的民间祠庙,是民众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资源,在维护乡土基层社会秩序稳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代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庙堂之争”源于清政府同意赔还禁教时期被没收的天主教教产,后来又因传教士获得了可在内地自由购地建造教堂的特权而导致庙堂纠纷扩大化。传教士也意识到民间祠庙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严重障碍,因此要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就必须对其予以打击和清除。于是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不断挑战民众的信仰底线,引发了一系列庙堂之争案件。同治八年(1869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民教双方围绕村中一座破败的玉皇庙的拆与建展开长达30年的拉锯,教民依仗教会拆庙修堂,非教民则拆堂修庙,教民屡向官府提告,非教民则组织护庙,民教双方更拆更修,相持不下。地方官为息事宁人,曾多次提出民教双方相互妥协,由官府出资为其中一方另觅他址重建,但均遭到双方拒绝。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特权不依不饶,地方官只得向民众施加压力,汉教一方还涌现了所谓的“四大冤”“十八魁”等民间的护教“英雄”。在官府的压力下,孤立无援的民众最终迫使向当地的秘密结社组织——梅花拳寻求帮助,由此引发了声势更大的义和拳运动。义和团宣称“上天文愠怒,皆因毁了玉皇庙。玉皇大帝看出只有义和团虔诚信天,向天祈求”[2]15。玉皇大帝作为汉教神灵信仰的最高尊神,既赋予汉教民众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神圣性,同时也赋予他们与洋教斗争巨大的精神力量。可见,晚清庙堂之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财产纠纷范畴,反映出民族利益和中西宗教文化的激烈博弈。其灭洋的正义性、神圣性、权威性,主要源自民众对“天”的敬畏及各类民间神灵的信仰,突破了士大夫阶层的正统神权范畴。
(二)义和团反洋教的民间信仰仪式
利用宗教来武装和团结自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普遍特征。义和团没有统一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先进的武器,其战斗力远不及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因此,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信念和勇气,主要来自对神灵的敬畏以及降神附体等巫术仪式。义和团宣称凡其所在之地皆有天神暗中保护,义和团所奉请的神灵亦五花八门,既有儒释道三教圣哲正神,也有民间信仰中的各种杂神,这些杂神大多来自戏文、小说、神话、传说中的神怪精灵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义和团的《请神咒》:“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2]147
义和团所崇信的神灵体现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普遍的泛神崇拜传统。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出于招抚、利用义和团目的,对民间秘密结社采取“不论会不会,只论匪不匪”的宽容政策,使得在华北乡村长期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的各种拳会、教门组织得以松绑,民间宗教中五花八门的各路神灵信仰和巫术仪式,在华北乡村乃至城市蔓延。这些长期沉寂在底层社会看似荒诞神秘的宗教现象,在义和团狂热的反洋教斗争中被迅速激活,19世纪末,义和团活跃的华北地区几乎成为全神下界、众神狂欢的场所。
义和团大力渲染其请神、降神仪式的目的,除了宣示其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外,还用于鼓吹其可以“排刀排枪”“刀枪不入”的神术。鸦片战争以后,从统治阶级到下层民众对于洋人的坚船利炮普遍感到畏惧。“排刀排枪”是当时华北地区比较流行的一种硬气功表演杂技,许多下层穷苦百姓以之作为谋生的手段。义和团通过降神附体仪式,渲染其刀枪不入的神术,以与洋枪洋炮抗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术对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乡村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当然,刀枪不入神术不过是义和团进行宣传动员的手段,根本无法抵挡洋人的枪炮。对于战斗中的受挫,义和团则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认为洋人用“秽物”破坏了义和团的法术。如北京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于是义和团将原因归结为教堂内有秽物所致:“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黏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墙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既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八,故难取胜,反多受伤。”[4]28
义和团视洋教为邪教,他们从民间巫术的角度理解基督教,认为“洋鬼子”不仅有剪纸为马、撒豆成兵的妖术,而且还掌握一种以妇女裸体或“秽物”破除神拳法术的淫邪妖术。义和团对洋人也有反制之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利用民间的女性禁忌限制妇女行为,以防冲破义和团法术。义和团在降神附体及与洋人开战期间,有许多针对妇女的禁忌,如严令妇女“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5]147,或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以红布遮掩。当时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5]147这些禁忌,往往成为义和团战斗败绩的借口,也有一些妇女违背禁令而成为义和团战败的替罪羊。
二是引入红灯照仙术专门破解洋人邪术。红灯照是义和团的妇女组织,一般由年轻未婚女子组成,被义和团尊称为“仙姑”“圣母”。时人曾这样描述红灯照的形象:
“(义和团)又取十八岁以下到十二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固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一上法。”[6]346
义和团认为其“法术虽大,然尚畏惧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5]163,“红灯照尽是少女幼妇,故不畏脏秽之物耳”[4]191。因此,红灯照的处女之身可以去秽辟邪,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时曾邀请红灯照施法助攻。红灯照的神术主要是“能治枪伤,应手即愈”、腾云驾雾和水上漂以及隔空取物、纵火等。民间传说她们可以轻松盗取洋人大炮上的螺丝钉,使洋人的大炮失效,还可以飞往外国“阻其来兵”,更最神奇的是他们能够“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焚毁外国京城。其实红灯照的形象和神术多是来自传闻谣言,她们并不像义和团那样经常公开进行宗教仪式表演,其活动隐秘且很少直接参与战斗。因此,红灯照的作用主要是协助义和团与洋人斗法,鼓舞义和团的斗志。
三、近代中西宗教文化冲突的时代特点
本文主要从“正邪之辩”和宗教战争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两种冲突模式。与明末清初相比,两者之间的冲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上述两种模式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仅反映了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在近代不同时期和社会阶层中的表现有所差异。实际上,自明末清初至近代以来,中西宗教文化的正邪之辩始终贯穿于两者冲突的全过程,义和团借众神之名与洋教“大开战争”,也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义和团虽然以农民为主体,但地方乡绅精英在这场运动中实际起到了领导和操纵作用。从正邪义理之辩到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战争,反映了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不断激化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与晚清民族矛盾的激化趋势大致同步。
第二,与明末清初相比,情重理薄、盲目排外的非理性特征是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的整体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近代民间信仰和基督教对话平台的失衡,以及下层民众的普遍介入直接相关。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和基督教向中国内地的强势渗透所致。基督教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庇护下向内地乡村迅速扩张,中西宗教文化冲突的主体从上层封建士大夫阶层向下层民众转移,使基督教与广大乡村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传统直接碰撞交锋,对乡村基层社会秩序权威构成严重挑战。外来因素的冲击加速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生态的恶化,特别是部分传教士和教民的恃强跋扈行为,不断挤压民众的信仰空间,威胁到民众生存的现实利益。因此,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的非理性特征,是民间信仰在“敌强我弱”的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本能的、过激性的自卫反应。
第三,与明末清初相比,反洋教斗争与反侵略斗争的合流,是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之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本文重点是从宗教的角度分析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宗教矛盾背后的政治隐喻。如王炳燮就曾引用清初杨光先的话,指责传教士在华传教“谋夺人国”“挟邪猾夏”“包藏祸心”。[1]27义和团揭帖中甚至明确表示“最恨和约,一致误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2]82,誓言要“扶保中华,逐去外洋”[2]18。民间传闻红灯照的可以飞往外国索还割地、赔款,就是民族矛盾影响的结果。这种反侵略民族主义爱国思想在近代反洋教文献中比比皆是,表达了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坚强决心。因此,深重的民族危机既是近代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的时代大背景,也是二者冲突不断激化的深层次的根本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