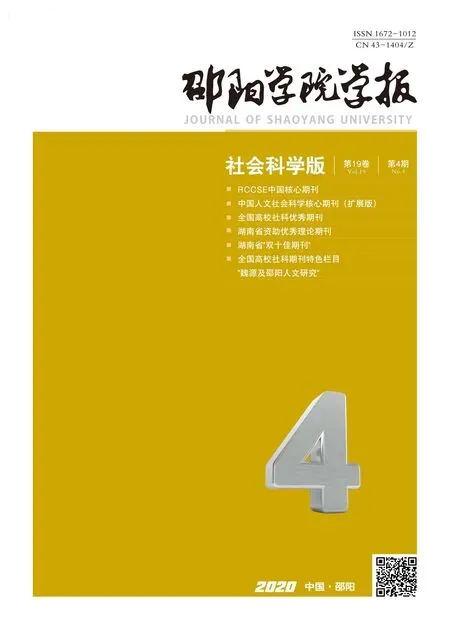程颐宗法思想的治道意涵
姚季冬
(邵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北宋承残唐五代之后,礼乐崩坏,秩序紊乱,重建礼乐秩序成为北宋儒者的使命。一个完整的礼乐秩序包含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然而北宋初期君臣着力点多在中央,地方礼乐不兴,如蔡襄说:“宋兴五十余年……朝廷礼文,罔不修举。……然四方之俗未闻由礼乐,专用法。”[1]卷二十二,507上有鉴于此,北宋中期的儒者们开始着力于地方礼乐秩序的建立,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这一时代浪潮中,作为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颐主动参与进来,提出了自己的宗法思想。学界对程颐宗法思想的具体内容和社会功能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在研究方式上,或是将程颐宗法思想置于理学宗法思想研究中考察,或是将其作为宗族制度、家族制度研究的一部分展开,或将其置于理学、儒学脉络中讨论。对二程宗法思想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不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1)在程颐宗法思想研究上,大体有两种进路:一是将其与中国古代宗族制度联系起来考虑,比较注重社会功能等外在内容。如邱汉生的《宋明理学与宗法思想》(《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62-73页)即认为程颐将宗法提高到天理高度,这是前代所无的,有力地维护了封建统治。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汝南:中州书画社,1983年)、徐杨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认为除了维护封建统治之外,保护地主阶级的世代荣华富贵也是理学宗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国外学者不太使用“封建统治”之类的词汇,因而其基本结论稍有不同,如日本学者井上徹的《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从宗法主义角度所作的分析》(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则围绕科举官僚制展开讨论,认为官僚身份世袭化是理学家主张宗法的目的。无论倾向如何,学者们在理学“宗法思想是服务于亲族结合的观念”这一点上取得了基本共识。另一种进路是从礼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比较注重程颐宗法思想的内涵。在具体研究中,有将其置于理学、儒学脉络中研究的,如吴飞的《祭及高祖:宋代理学家论大夫士庙数》(《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第28-38页),林鹄的《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社会》,2015年第1期,第49-73页)。有单独研究二程礼学的,如王启发的《程颢、程颐的礼学思想述论》(陈义初主编,《二程与宋学:首届宋学暨程颢程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154页)、殷慧的《二程礼教思想的形成与冲突》(陈义初主编,《二程与宋学:首届宋学暨程颢程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4-204页)等。上述两类研究构成了二程宗法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本文有重要意义。除上述礼学进路的研究外,对二程宗法思想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中,潘富恩、徐余庆在《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1-377页)中的研究较有代表性。潘、徐两位将二程的“齐家之道”归纳为四点:以法度齐家,严长幼尊卑之义、男女之别;树立家长的绝对权威;治家必须从严;家长要言行身教。并对程颐复宗子制的思想做了梳理。二位先生主要是依据相关资料梳理二程的治家思想,但尚未对二程宗法思想的内核进行进一步挖掘。。对程颐宗法思想做治理层面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程颐学术的落脚点和归宿,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理学治理层面的含义。
本文将首先从地方礼乐秩序重建的角度对北宋地方治理思想做一概览,以确定程颐地方治理思想的历史语境;其次会对程颐宗法思想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以确定程颐宗族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最后会讨论程颐宗族治理与天下治理的关系,指出程颐实质上将宗族治理定位为朝廷治理必要的补充。
一、北宋中期地方治理思想概览
在正式讨论程颐宗族治理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背景做一个简单介绍,以明确讨论的背景和语境。综合考察,北宋中期对地方礼乐秩序重建的思考与实践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由政府来主持地方礼乐秩序的建设,其基本思路是将地方礼乐秩序视为政治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以政治的手段来建设社会秩序,在稳定的社会秩序基础上,再追求礼乐秩序的建设。但正如赵秀玲指出的,在北宋的乡里制度的实行过程中,负责具体基层工作的里正、耆长等职权和地位日益萎缩,在地方上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基层治理也就愈发混乱。虽然有一些地方官提倡礼乐教化,但实际上礼乐秩序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2]25-32。北宋政府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地方礼乐秩序的效果并不好,欧阳修形象地描述为:“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天下祸患,岂不可忧?”[3]1159有鉴于此,王安石提出将保甲法作为地方政治、社会秩序建设的手段,但这离礼乐秩序愈行愈远了。
成长于“文治”环境中的庆历儒者试图通过宗族治理来建立基层礼乐秩序,从而在地方上实现礼乐秩序的重建,是为第二类。其中提倡力度最大、影响最大者为范仲淹的义庄建设、欧阳修和苏洵的族谱建设。范仲淹于皇祐元年(1049)出于“敬宗收族”的动机购买义田、创设义庄,并订立十三条义庄规矩作为保障。治平元年(1064)应范纯仁的请求,范氏义庄得到朝廷的承认,其规矩有法律作为保障。范氏后人的努力使得范氏义庄不断发展,成为宗族治理的典范。范氏义庄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义庄的济贫措施,来达到儒家安定社会的理想”[4]192,即通过宗族治理来实现社会治理。大约与范氏义庄同时,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6)欧阳修和苏洵先后进行了修族谱的活动,并希望能将此行为推行天下。欧阳修、苏洵倡导族谱是希望达到“尊尊亲亲”的目的。实践中,族谱和义庄互为补充,二者的结合成为宗族治理的典范(2)请参看王善军:《宋代谱牒的兴盛及其时代特征》(《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第124-128页)。义庄与族谱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共同性,可以说义庄是宗族的物质基础,族谱是宗族的精神内核。范仲淹在《续家谱序》中说:“皇祐中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补编》,《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1-732页)可见是先有族谱,方有义庄,义庄所服务的人群是以族谱的记载为准的。。
在政治手段和宗族治理之外,第三种建设地方礼乐秩序的思路是乡约,在北宋以蓝田吕氏乡约为代表。乡约与族谱、义庄等宗族治理类似,都希望通过基层的礼乐教化来建设地方礼乐秩序。但在治理对象的涵盖范围上,宗族治理仅限于宗族内部,乡约则超出宗族之外,以实际的聚居规模(乡、村)来确定地方治理的范围。正是这种超出血缘关系的尝试,蓝田吕氏乡约被称作中国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举动”[5]27。但乡约在北宋产生的影响其实不大,因而它对地方礼乐秩序的重建贡献不大。
由于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儒者在士林中的崇高声望和义庄、族谱卓有成效的典范效应,北宋地方礼乐秩序重建的主流开始向宗族治理方向靠拢。程颐建设地方礼乐秩序的思路也大体延续了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的做法,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二、程颐宗族治理思想的特点
程颐属于上述三类建设地方礼乐秩序思路中的第二类,这首先与他的家族背景、生活经历有关。程氏一族颇有厚待族人的传统,程颐之父程珦堪为典范[6]273-311。据程颐在《先太公家传》的记载:
始公抚育诸孤弟,其长二人仕等朝省,二十余年间皆亡。长弟之子九岁,从弟之子十一岁,公复抚养,至于成长,毕其婚宦。……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瞻亲戚之贫者。[7]650-651
程珦所作所为皆合义庄精神。程颐之母亦如此:“仁恕宽厚,抚爱诸庶,不异己出。从叔孤幼,夫人存视,常均己子。”[7]653程颐在这种家庭中成长,必然受到影响,如尹焞说他“赡给内外亲族八十余口”[7]346。虽然现存资料显示程氏家族从未有过义庄行为,但这应该是出于条件的限制,而不是反对义庄(3)据李学如研究,义庄的实践需要丰厚的财力支撑,因而义庄在北宋仅12例(李学如:《宋代宗族义庄述论》,《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第40-45页)。无论是程珦还是程颢、程颐都未曾显达,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这种行为。如程颐在《家世旧事》中的记载:程羽为醴泉县令时曾购买产物,以待久居。后程羽留居京师,但产物多在醴泉。程珦的四叔程逢尧留居醴泉(今陕西礼泉),其后人保管不善,“散失尽矣”,程颐也只能“思之痛伤”,无法赎回(见《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57-658页)。。相比于义庄,程颐在宗族治理上更重视宗子法。
(一)立“宗子法”:宗族治理的制度构想
程颐曾简短地回顾宗族制度的发展历史说:
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7]162(4)此条又见《经学理窟·宗法》(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9页)。《经学理窟》一般归于张载,但张岱年先生在为《张载集》所作的序中指出,《经学理窟》“当是张载程颐语录的类编”(《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页),可见其中具体条目的归属仍当继续考证。林鹄认为此条应属程颐(《〈经学理窟·宗法〉与程颐语录》,《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2期,第64-71页)。我们虽不必持如此强的立场,但笔者以为程颐至少可以赞同此条的观点。下引程颐论“管摄天下人心”“立宗子法,亦是天理”等条亦见于《经学理窟·宗法》,并做如是观。
宗子法指西周式的封建宗法制度,谱牒指魏晋时用以作为选官和婚配依据的谱牒制度。程颐认为北宋社会“虽至亲,恩亦薄”的局面正是宗法、谱牒皆废的后果,因而相应的办法就是恢复谱牒和宗子法: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7]85(5)在已确定的材料中,程颢未言及谱牒,而程颐屡言谱牒与宗子法,故程颐至少可赞同此条内容。另,本文引用《河南程氏遗书》中的内容时,如属未明确表明归属的语句统一在引文前加“*”号,判定其属于程颐的理由在脚注中表明。
虽然程颐确实勾勒了一个“宗子法行—宗子法废—谱牒行—谱牒废”的过程,并暗示了这是一个不断倒退的过程。但他讲的“明谱系世族”和“立宗子法”不能简单地看作西周封建宗法和魏晋谱牒制度的复归,而是他根据北宋实际情况所设想的两种宗族制度:族谱制度与修改后的“宗子法”。对于族谱的作用,程颐并不否认,但其重视程度显然不如欧阳修、苏洵等人,这或许与他的家世背景有关。程珦在其自撰墓志中说:“姓源世系,详于家牒,故不复书。”[7]645可见程氏的族谱保存得较好。但这对“敬宗收族”似无太大的正面作用,程氏族人间亦多有不睦(6)就程颐自身来说,族人不睦之事多,举其著者如先有族翁程逢尧为了族产猜忌其父程珦;后有族侄程公孙因利出卖,导致他编管涪州(前事见《家世旧事》,《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57页;后事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1页),这难免影响他对族谱之于“敬宗收族”的意义的判断。。程颐认为能真正建立起宗族礼乐秩序的是“宗子法”,而不是代表小宗法的族谱、谱牒,这是他与欧阳修、苏洵不同的地方。程颐认为小宗法会导致“亲尽则族散”的后果,并非好办法:
凡小宗以五世为法,亲尽则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则见为宗子者。虽是六世、七世,亦须计会今日之宗子,然后祭其父。[7]180
需要注意的是,“亲尽则族散”并非无的放矢。欧阳修、苏洵编制族谱虽依循小宗法,只收五服之内的族人,但他们也都留下了合小宗谱为大宗谱的空间,即各房子孙各编其谱,待时机合适合编,即可为大宗谱。苏洵还制作了《大宗谱法》作为范例。可见,小宗法实质上是从现实角度考虑的权宜之计,并非最终理想。而他们之所以采取权宜之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情见乎亲,亲见乎服,服始则哀,而至于缌麻,而至于五服”,即五服之外情尽服除,相视如途人,此为势所必至(7)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苏氏族谱》,《嘉祐集笺注》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引文在第373页。欧阳修以“断自可见之世”为原则制作族谱,与苏洵的理由实质是一致的,这代表了庆历时期儒者的典型看法。。正是在这个地方,程颐和欧阳修、苏洵产生了差别:五服之外皆如途人固是现实情况,但是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是认可五服之外的族人相视如途人的现实,还是改变这一情况呢?程颐选择了后者,他推荐的办法即大宗法。
程颐认为实行大宗法是天理内在的要求: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干,(原注: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处,自然之势也。[7]242
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兽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飞鸟是也。惟人则能知祖,若不严于祭祀,殆与鸟兽无异矣。[7]241
程颐将大宗法提高到天理的高度,认为大宗法是“自然之势”。因此人要祭祀祖先,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应该得到践行。从实践上考虑,程颐大宗法的构想似不合实际(8)如茅星来在注《近思录》的时候引用沈磊的说法,认为程颐大宗法并不能行于后世(程水龙:《〈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17页)。朱瑞熙亦指出北宋一般只能实行小宗之法,即“五世而迁”之宗,程颐的大宗法近乎空谈(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汝南: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99-101页)。,但若认为程颐仅是出于崇古的信念而推崇大宗法,似亦不合实际。其实,程颐的大宗法抛弃了西周式封建宗法的具体形式而保留了其精神,程颐想恢复的是同一祖先的族人之间的“亲亲”之情。为此,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首先程颐重新定义了宗子:
宗子者,谓宗主祭祀而已。[7]179
程颐认为宗子主要是主持祭祀,这与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宗子是完全不同的(9)徐杨杰在《中国家族制度史》中把西周宗子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五点:占据统治地位,主持祭祀和占卜的权利,团聚家族、管理家族事物的责任,庇护家族的义务,处分家族成员的权利,统率家族武装的职责(《中国家族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3-87页)。可以看出,程颐对宗子的定义已经远离了西周式的宗子。。程颐所以如此,是希望能说服“无百年之家”的后世中“至亲恩薄”的人。程颐认为争财夺利是“至亲恩薄”的根本原因:“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7]177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程颐强调宗子最好不和族人发生具体的利益纠葛,而主要负责主持祭祀,这样人们接受起来便容易得多。为了说服世人,程颐甚至不要求祭祀的时候人人到场:
古所谓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主祭者不异。可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已也。[7]165
程颐认为在祭祀时支子“致其诚意”即可,而诚意的表达形式非常人性化:条件允许,支子从旁参与祭祀;条件不允许,支子则以物助祭,本人不必亲自到场。唯一的强制要求是支子不可别立一庙去行祭祀之事。这是符合实际的考虑。正因如此,程颐强调“收族之义,止为相与为服,祭祀相及”[7]179。所谓“收族”并不是要恢复西周封建宗法,只是别亲疏、序昭穆、祭祀相及而已。
祭祀必定要有场所,因此程颐又特别强调家庙的作用,认为“凡言宗者,以祭祀为主,言人宗于此而祭祀也”[7]242。家庙就是实行祭祀的场所,每个宗族都应有庙:“家必有庙,庙中异位,庙必有主。”[7]241在家庙中的祭祀分为月薪之祭、四时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襧。至于家庙的具体数目,程颐认为并不是非常重要:“七庙五庙,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虽或三庙二庙一庙,或祭寝庙,则虽异亦不害祭及高祖。”[7]167程颐对家庙和祭祀的相关论述在当时是较为激进的,对后世亦产生较大影响,成为比后民间宗族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10)如常建华在《中国宗族社会》里面说家庙与祭祖制度是程颐宗法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应该说,程颐在宗族治理方面所提出来的大宗法、宗子法虽然在名称上与西周封建宗法相似,但内容上有极大差异,不应将二者等同,更应将其看作北宋儒者为重建宗族秩序所做的努力之一。除了强调宗子法外,程颐宗法思想另一大特点是对修身和礼法的强调,实质是对“礼”和“理”的强调。
(二)修身与礼法:宗族治理的两个核心
由于主张大宗法,程颐的“家法”涵盖了同族所有成员,这是其特点之一:
*凡人家法,须令每有族人远来,则为一会以合族,虽无事,亦当每月一为之。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更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会不相见,情不相接尔。(11)《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第7页。庞万里先生说凡祭祀与立宗子法都是“程颐的专门研究领域”(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4页)。程颢有对禘、袷的论述,虽然极少,但不能说没有(如《遗书》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页)。至于宗子法,程颢确实无一言论及,故凡论宗子法的内容皆可视为程颐语。
程颐认为家法应该让族人“骨肉之意常相通”,此即“收族”之意,这是温情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严格的法度。其宗族治理思想的核心就在于“确立亲族内符合道德的人伦秩序”[8]。
程颐认为家人之道是:“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7]884所谓“伦”实质就是“理”[7]182,就是“上下尊卑之序”,就是“礼”,如程颐在解释《履》卦时说:“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7]749程颐希望通过严格的礼仪制度来实现宗族治理,让族人相亲相爱,从而建立良好的宗族礼乐秩序。换言之,在程颐看来,宗法本质上是“礼”(“理”)在宗族里的流行,其实质是上下尊卑有序的人伦,其表现形式为各种各样的宗族礼仪规范,其效用是收族。可以说,宗法之中,上下尊卑之序是体,收族是用,而礼仪规范则是“体”的具体体现和实现“用”的必经之路。在这个意义上,程颐“立宗子法”实质上就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来治理宗族。程颐认为,若不能严格践行礼仪规范,家道只是空谈。程颐在解释《家人》卦时一再强调:
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7]885
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废,伦理之所由乱,安能保其家乎?[7]886
以严谨为本,以法度为尚,不毫无限度地顾及人情,这就是“正伦”,“理”自然在其中(12)这里遵从吕祖谦的说法:“伊川云:‘正伦理,笃恩义’,此两句最当看。常人多以伦理为两事,殊不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所谓‘伦’也;能正其伦,则道之表里已在矣。”(吕祖谦撰,吕祖俭录、吕乔年编:《丽泽论说集录》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4页下)。所谓“法度”就是具体的宗族礼仪规范,若不能严谨地实行法度,不仅无法“正伦理”,而且无法“笃恩义”,所期待的收族效果自然就实现不了。程颐为了“正伦”曾煞费苦心地试图制作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即使中间因被召入朝而中断,也不曾放弃(1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40页。为了避免枝蔓,有关程颐所制定的礼仪细节在此不多讨论。大体情况可以参看《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中所收的各篇文章。亦请参看殷慧:《二程礼教思想的形成与冲突》(陈义初主编:《二程与宋学:首届宋学暨程颢程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4-204页)。。
程颐认为要想“正伦理”,除了崇尚礼仪规范外,治家之人必须首先做到身正:“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7]888正身必须保有至诚之心:“治家之道,非至诚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则能常久,而众人自化为善。”[7]888至诚之心是正身之本,也成为“正伦理”的根本。于是修身便成为治家之人的义务和责任,也成为家道实现的根本,这可以看出理学家的特色。程颐说:
治家者,在妻孥情爱之间,慈过则无严,恩胜则掩义,故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慢生也。长失尊严,少忘恭顺,而家不乱者,未之有也。[7]888
一方面程颐认为家人相处不患不亲,患在无礼法将亲情限制在适度(中)的范围之内,因此宗族治理应以礼为核心;另一方面程颐也强调了正身在宗族治理中的重要性,长辈失去尊严,晚辈忘记恭顺,家道必亡。因此宗族治理必须以正身为本。程颐说:“保家之终,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7]888威严即礼法之严谨,有孚即族人亲亲之诚心,有诚心方为正身,正身方可行家法。可以看出,在欧阳修那里只是略微提及的“尊尊亲亲”在程颐这里得到了理学式的发挥,威严以尊,其形为礼,其实为理;有孚以亲,其本在诚,其体为理。诚以行礼,礼以固诚,二者又归于天理。说到底,行家法去治理宗族,根本在于践行天理(礼)。这样庆历一代儒者所冀求的宗族礼乐秩序就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不止停留在礼乐仪式和心理情感上,更得到了形而上的支撑和心性的保证。程颐宗族治理思想中鲜明的理学特色集中展现在这里。
总之,程颐宗族治理思想以恢复封建宗法精神的“宗子法”为制度依托,为此他进行了家礼的制作工作;在具体治理方法上,程颐强调正身以行家法,以正身为本,以家法的严格法度为核心,希望达到“正伦理,笃恩义”的目的。本质上是追求天理在宗族领域的流行。这是程颐宗法思想的理学特色所在。从治理的角度看,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宗族治理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族治理和朝廷(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
三、地方治理与天下治理
程颐希望通过以礼为核心的宗子法来实现宗族治理,进而恢复社会秩序,那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宗族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一种方式,它如何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第二,宗族治理作为一种宗族自治方式,它与天下治理(以朝廷为主)是什么关系?程颐认为宗族秩序的实现可以成就人才,进而化俗成礼,这是宗族治理对社会秩序恢复的积极意义,也是宗族治理对天下治理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程颐进一步强调,宗族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自治,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它是朝廷治理独立的、有必要的补充。
(一)化俗成礼与成就人才:宗法的现实意义
程颐认为得人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而人才不仅出于天性,更出于教化。在教化人才中,最重要的就是礼。圣人制作的“礼”对民众有规范作用: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7]327
依李晓春的说法,程颐有一种“性体情用”的立场,即情是性接物之后所产生的,是性的发用。因为发用的不同,情有正有不正[9]183-188。出于人情的礼通过具体的礼仪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规范人情,让情的发用“正”,合乎人性,合乎天理。程颐认为礼仪制度的这种规范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有益的:“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7]1006好的礼仪制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成才,而人才的成就又可以促进礼仪制度的适时演进,人才成就与化俗成礼是一体两面的。这正是程颐礼学思想的核心[10]194-204。因此需要恢复古礼的精神,制定出适时的礼仪。宗族礼仪制度当然只是整个礼仪制度的一个部分,但这是最基本的部分。毕竟,对个体而言,能为官的总是少数,多数仍属于民;且为官者亦必有家,家为国之本。这样个体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宗族的领域内,由此可见宗族治理的重要性。
就宗族内部来说,强调礼法的宗族治理可以收到成就人才的作用。程颐认为,一方面适时的礼仪可以让人熏染,渐知礼义,如其自陈作“六礼”的目的:“人家能存此等事数件,虽幼者渐可使知礼义。”[7]241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人的德性,成就人才。如其论祭祀,在所有宗族礼义中祭礼最为重要,程颐认为由宗子主持的家庙祭祀可以让族人不生惰慢之心,“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7]165。人才的培养不仅在品德方面,其实也在才能方面。邓小南在概括北宋士人心目中的“家法”的时候说:“士人之家的‘家法’,也并非仅仅行用于私家内室的原则。以敬奉祖宗的虔诚去对待国家事业,推治家之法意临民,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11]62这个论断对于程颐来说同样适用。
宗族治理的意义还不止于宗族本身,它也是社会礼乐秩序的基础,即化俗成礼。程颐认为宗子法可以让人“顺从而不乱”:
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只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后顺从而不乱也。[7]242
宗子法能使人各有所统,各有上下尊卑之分,如此才能“顺从而不乱”。这既是人才的成就,人人皆顺其本分而行;也是风俗的改善,天下不乱。这里体现的价值观,正如王启发所说:“二程所看重的价值观,确实有着维系亲情,保障家族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意义。”[12]119-154可以说,程颐宗法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基层治理思想,他希望从社会基层(宗族)来让上下尊卑之分定下来,保持基层的稳定,恢复基层的秩序,从而推至天下,恢复社会秩序。
(二)必要的补充:宗族治理在天下治理中的定位
程颐认为宗法制度有“管摄天下人心”“厚风俗”的作用,这体现了宗法、宗族参与天下治理的作用。然而在传统政治思想中“管摄天下人心”“厚风俗”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族(民)的职责范围,它是官的责任,是皇帝的责任。制礼作乐更是天子的职责,所谓“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高扬,以天下为己任,故其希望在地方制作礼乐,程颐也是承其风而然。但士大夫制作礼乐与朝廷制作礼乐之间的矛盾是切实存在的:士大夫制作礼乐是否侵犯了朝廷的权威?这一问题是极严肃的,蓝田吕氏乡约引起的争议体现了这一点。
吕大钧推行乡约始于熙宁九年(1076),至元丰五年(1082)吕大钧去世为止,约五年半的时间[13]。蓝田吕氏推行乡约的目的同样在于重建地方礼乐秩序,只是它超出了宗族的界限,处在“家”与“国”之间,属于“士绅领导、民众参与的一种民间组织”[14]18。因此吕氏乡约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各种质疑中最严重的是:吕氏乡约的实践有地方士大夫与朝廷争夺地方权力的嫌疑(14)乡约引起的质疑实质上是超出血缘界限的地方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杨建宏认为“建立在乡约基础上的地方士绅权力场域触动了以皇帝为首的国家权力场域”,因此它一出现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杨建宏:《〈吕氏乡约〉与宋代民间社会控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26-129页)。在这里,血缘界限是非常重要的边界。。程颐与蓝田吕氏往来密切,曾在元丰三年(1080)入关亲见乡约推行的情况。虽然在今存的各种资料中找不到程颐对乡约的评价,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程颐对乡约这种处于“家”“国”之间的地方治理方式的看法。《遗书》卷十记有两条:
子厚言:“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正叔言:“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子厚言:“亦是自家规矩太宽。”[7]114
正叔谓:“洛俗恐难化于秦人。”子厚谓:“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东方亦恐难肯向风。”[7]115
程颐曾称赞张载“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7]23,可见他是赞成张载礼教的。但从这两条记载看,他对“关中”诸人的做法似不以为然。此时为熙宁十年(1077),吕大钧已于上年开始推行乡约,从“用礼渐成俗”“先自和叔有力焉”等来看,程、张所论或即指乡约。从语气上看,程颐对这种立足于“乡”来建设良好社会秩序的做法似乎并不赞成。而且,程颐曾与吕大忠在书信中讨论过如何面对现实法令与价值理想的冲突的问题,他说:
既为今日官,当于今日事中,图所设施。旧法之拘,不得有为者,举世皆是也。以颐观之,苟迁就于法中,所可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为邑,及民之事多。众人所为法所拘者,然为之未尝大戾于法,众亦不甚骇。[7]605
程颐认为儒者求有为之事当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中积极发挥,务求合于义理,不必再另起炉灶。依此态度推测,程颐对乡约似不会持赞同态度。
就治理思想而言,程颐与北宋大多数儒者一样,关注点始终在朝廷,而不在地方(15)包弼德说:“第一代理学家和11世纪的其他思想家都是政治思想家,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改变政府对社会运作方式是学术的目的。与之相反,在南宋兴起的理学,则主张应该减少对社会的干预,而地方士人应该自发地采取更多的行动。”(包弼德著,王昌伟译:《历史上的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6-237页)这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察,程颐之所以对乡约不敢兴趣,或许正在于他的目光仍集中在政府(朝廷)身上,他对宗法的强调,也与此息息相关。。他对宗族治理的强调是在天下治理的框架下进行的。程颐认为宗法治理本质上只是朝廷治理的一个补充。
程颐在解释《尧典》的时候强调唐尧治理天下的次序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这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反映。程颐认为,修身是治理的根本,但在实际治理活动中,齐家则是第一步:“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于以睦九族也。”[7]1035齐家不仅是第一步,而且直指天下大治的根本,即得民心:
天下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过于宗庙,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则萃道之至也。[7]929
程颐认为立宗庙是得民心的诸种举措中至大者,这就点明了宗法对朝廷治理的第一重意义:对王者而言,宗族治理实质就是朝廷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王者之治的起点所在。更重要的是,联系到上一节讨论的齐家之道中修身和礼法的关系,可以说在“修身—齐家—治国”的连贯过程中,宗族治理是修身和治国的中介环节——当然这是逻辑上的中介,而不是实践中的。实践中,修身、齐家、治国应是同时发生的。这样,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修齐治平思想在北宋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发。
在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程颐亦未忽略掉朝廷治理的另一主体——大臣。程颐认为世臣之有无与宗子法之废立息息相关:
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7]242
所谓“世臣”是指“累世修德之旧臣”(16)此为孙奭疏《孟子·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一句中的“世臣”所说。北宋世臣出于故家,即不断通过科举等正规方式为朝廷提供贤能大臣的家族。因此很难说程颐宗法制度向往的是复辟门阀制度(王雪枝、仇海平:《宋代故家在北宋的发展轨迹及世臣的作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第12-17页)。,即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臣。世臣对朝廷治理能起到什么作用?张载说得很清楚:“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15]259张载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宗法在化俗成礼和成就人才方面的作用,只不过重点放到了公卿上面。公卿们良好的宗族治理可以“立忠义”:一方面在宗族内部培养起忠义的气节,从而锤炼人才;另一方面在社会上起到模范效应,带动大夫、士、庶人的仿效(17)参见李静:《论北宋的平民化宗法思潮》,《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80-85页。但需要指出的是,就实践次序而言,程颐的关注点并不在“平民”(无官身者),而是在王者与大臣身上,希望通过“巨公之家”的试行造成模范效应。但在理论上,程颐宗法思想确实有平民化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公卿的宗族治理和王者的宗族治理一样,都是朝廷治理的内在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王者和大臣宗族治理之所以是朝廷治理的组成部分,这不是因为朝廷治理在本质上包含了宗族治理,而是因为王者和大臣天然地带有了“官”的性质。如果抛开王者和大臣的身份性质来看,宗族治理和朝廷治理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程颐自觉地把宗法限定在“家”的领域之内,如他曾因“既在朝廷,则当行之朝廷,不当为私书”[7]239而中止制作六礼的行为。这里的“私”指的是家、宗族,“公”指的是国、朝廷。程颐在宗族治理和朝廷治理之间划了一条公私界限,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将宗法限定在“家”的范围之内,从而将宗族治理定位为天下治理的补充。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蓝天吕氏乡约那样的与朝廷“夺权”的境况。另一方面,程颐为宗族治理保留了自身的独立性,也正是因为保留了宗族治理的独立性,宗族治理才能成为朝廷治理的补充。
这种公私的划分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它首先是对北宋族权和政权复杂关系的反映。北宋时期,一方面族权和政权有分离的趋势(18)参见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族权与政权的分离是相对于汉唐时期世族制下族权和政权的紧密互动而言的,并不是说族权不再和政权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北宋宗族建设主要由士大夫推动,士大夫们在进行宗族建设的过程中自觉地维护王朝统治,族权和政权以新的方式紧密关联(19)北宋宗族组织对维护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发挥往往是从宗族自发开始的,由下而上的。关于北宋宗族组织的社会作用,请参看王善军:《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15-21页);申小红:《略论宋代的宗族自治》(《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70-72页)。。程颐对宗族治理在天下治理中的定位实质上就是族权和政权既相对分离又紧密相关的社会现象的理论反映。而当程颐将宗族治理定位成天下治理必要的补充之后,鉴于他作为理学奠基者之一的地位,这一思想不可避免地对后世产生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宗族组织和国家政权关系的发展。此外,宗族治理独立性的保留,也为士人保留了某种独立和自由的空间,为士人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保留了空间——毕竟,无论何时何地,有人必有家,有家必有族。也就是说,宗族治理无关身份,是一定可以实行的。于是,当士人面对出仕的困境退下来之后,他便可以退回到家庭领域中来,一方面修身以俟时,一方面也参与家族治理,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出处原则得到了拓展:士人“穷”不再止于独善其身,而可以齐家。士人活动的空间便被拓展了——学术向实践转化的空间得到了扩充。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北宋以后,士人在无法出仕的情况下往往选择退回宗族去实践自己所学,在宗族中构建起礼乐秩序,从而承担起自己的使命(20)参见包弼德著,王昌伟译:《历史上的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215页。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士人的选择除了宗族之外还有书院、乡约等。但在诸种选择中,宗族是最根本的、所需条件最少的。。他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在于,理学为“退”做出了理论上的证明——程颐的宗法思想恰恰是一个源头。
综上,在北宋中期恢复社会秩序的各种努力中,程颐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以礼作为核心,希望通过恢复宗子法和家庙制度来实现宗族治理。宗族治理在实质上是社会的基层治理,宗族治理的卓有成效就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成功,社会秩序的恢复。程颐进一步讨论了宗族治理和天下治理的关系,他认为宗族治理能起到化俗成礼、成就人才的作用,但宗族治理在整个天下的治理中只是朝廷治理的补充。当然我们应该同时看到,宗法对于天下的良好治理来说是一个有必要的补充,它的独立地位并不因为朝廷的存在而消失,只不过应该严格区分宗法权力与朝廷权力的界限。我们可以说,程颐对宗法制度参与天下治理的思考体现出一种“共治”的思想:朝廷与宗族共同治理天下,政治与宗法共同治理天下。